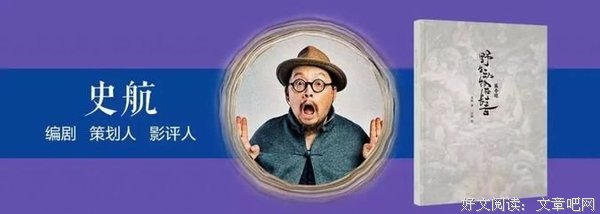
《《刺杀小说家》创作实录》是一本由电影《刺杀小说家》剧组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98,页数:1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刺杀小说家》创作实录》读后感(一):影视爱好者必看
冲呀!!!
一直很想了解电影背后的故事,这本书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看目录就觉得很详细。
以下摘自豆瓣阅读:
这是一份面向电影爱好者、从业者和普通读者的读物,也是一个关于信念、勇气与热爱的「中二」故事。
《一场「中二」的冒险——<刺杀小说家>创作实录》是单读书系和电影《刺杀小说家》主创团队合作推出的国内首部电影书,全方位展现了一部国内顶级视效大片从种子落地到长成苍天大树的过程。
本书由文字和图片素材两部分构成。文字深入到整个拍摄制作过程的细节,包括特效制作的难点、演员和技术人员融入其中的思考;图片总量达五百余幅,呈现了大量视觉细节,补充了文字有限的示意功能,同时也是珍贵的幕后资料。
2021 年,让我们一起阅读这本书,开始一场「中二」的冒险。
《《刺杀小说家》创作实录》读后感(二):为什么要给电影《刺杀小说家》做一本书
第一次跟路阳导演见面讨论电影出书的事是在2020年的6月,那时,电影还在后期特效渲染阶段、也没确认上档的时间,可就在那个初夏的傍晚、走出工作室的当下,我们就动了心:要做一本真正自己原创的电影设定集。
我们是被《刺小》导演组和团队成员表现出来的专业、热情,他们在几年间积累下来的丰富素材,以及他们分享的那些故事打动的。编辑部几乎所有成员都是电影爱好者,可一部电影,是怎样从一篇小说,经过编剧、美术、造型、特效、动作各个环节,最后走上大银幕的?我们没一个人讲得清楚——历时五年、上千人投入其中,这个过程,既神秘浪漫、又严酷漫长,若能通过一本书把一部电影的从无到有,图文并茂地讲出来,应该是一件有价值的事。
回来后做功课,除了翻阅路导给我们展示的他个人收藏的电影设定集,发现国内出版的影视类设定集大都是海外电影,比如读库出品的“御宅学”书系中《异形全书:经典四部曲终极档案》、后浪出的《黑镜:创作内幕》,没有一本国内电影的设定集,围绕具体一部电影的创作过程所做的书也是少之又少。既然《刺小》这部电影已经为我们展示了它成书的可能性,那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海量的图片素材让这部图文书有了成书的根基,但我们好奇的是——电影背后各个工种、角色的分工、协作?导演组的工作方法?以及整个工业化的流程是怎样的?电影具体又是怎么“拍出来”的?——我们意识到,要想让这些图片开口说话,必须做一些基础的文字工作,要请出这些素材背后的“主人公”,业内人士为我们讲述他们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于是,我们找到了超级外援——张雄,一位有着丰富采写经验的资深媒体人。他善于提问、写得一手好文章,又在影视行业工作过,找他代表读者来向导演组的各位主创人员发问、撰文,再合适不过。于是,接下来的四五个月里,他分别采访了导演路阳、编剧禹扬、摄影指导韩淇名、美术指导、视觉指导、造型指导、动作导演……在整理了录音材料后,张雄提出,可能文字部分最适合的体例是第一人称的讲述,几经删改、增补、修订,终于在12月定稿,总共五万多字。
同步推进的另外一条线,就是设计师政坷的图片遴选、编辑工作。如何从五千多张图片中选出体量合适的图片,并结合已有的文字采访稿找到一本书内在的结构,在文字逻辑和影像逻辑中找到平衡,是最困难的事情。为了帮助负责内容编辑的同事理解,设计师在白板上对已有的图片做了详细的分类和耐心的讲解——当时,还没有看到最后成片的我们,面对单篇单篇的人物采访稿和几百张没有图注的图片,多少有点犯懵。多亏这张图,既扫了我们的盲,又帮助大家理清了思路(在这里还要再夸一句我们的设计师,他何止是处理了图片的问题,他其实凭借自己丰富的“业余”常识给大家做了一场讲座)。
接下来就是书稿结构的确定、调整,人物补采,文本的进一步打磨。也是到了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电影的上档时间才最后确定,我们也对这本书的最终定位更加明晰了:它将不会是一本传统意义的设定集,而是一部创作实录:因为它不光是描述了重要角色的设定,收录了原画手稿、概念图、分镜脚本……还有关于整个制作流程各个环节的丰富素材,更有意思的是幕后工作人员分享的经验、心得,那些充满细节的讲述,让我们以更具体、可见的路径重新理解了“创作”这件事,比如:
小说中的“云中城”具体是什么样?里面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为什么要选在重庆而不是别的城市?城中十三坊的名字怎么确定的?每个坊的属性和职责?白翰坊的街道氛围是什么样?很多片子里一闪而过的,那些藏在武器、盔甲和道具里的细节,原来之前都经过了如此细致的追问和推敲……
再说灯光的运用,光作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经常是被观众忽略的,可一部电影的气质,往往就是被这些具体的技术影响的。大量的棚拍如何模拟自然光,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实拍,都是问题。
还有主角赤发鬼,他是如何从一个小说家笔下同时具有兽性、魔性和人性的、想象中的人物,变成在大屏幕上那样一个实实在在、仿佛触手可及的形象,如果不是亲耳听导演的讲述,完全想不到这背后还有这么多工作:
最初导演对赤发鬼的想象是,虽然身形巨大,但应该是“特别灵活、很有思考力、能够预见到你的战略和战术,总是能提前做出判断的角色,而且柔韧得像体操运动员一样”,为此,导演、摄影指导和执行导演经常在屋里摆各种动作,拿玩偶、模型来模拟,用来制作分镜,给画故事板的老师展示,导演说,“执行导演就演赤发鬼,摆一个小人在地上,我们摆了一个下午,弄出半场戏”,刚觉得不错,突然执行导演说,“不对,赤发鬼应该是四只手,完蛋,重来。之前全部是按两只手来设计的,所有的动作就都错了”。接着,四个人又重新在屋子里排这场戏怎么打、怎么演,怎么在地上爬…… 到了动作捕捉环节,动捕演员就只有两只手,另外两只怎么办?
最后,想来想去,找到“两个身材接近的演员,经过配合和训练之后,尽量保持上肢躯干的节奏一致,分开来演四只手,采集之后再合到一个模型身上。我们要做无数的测试,才能让这两个人尽量达到同步”,“许多模型得推倒重来,重新设计,最后让他变成一个合理的有四只手的生物”。类似这样的问题,数不胜数,几乎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照。
这些不断的“推倒重来”,为最后呈现中的一个细节(很可能是其他人未必会留意到的),一帮人精益求精、不厌其烦、不计回报的投入,真的非常热血,已经超越了专业的范畴,变成了一种富有感染力的精神气质。这让我们想到了小说家为了一个词语不断斟酌、修改,一遍遍的重写;也想到了我们编书过程中为了一个看起来完善的文本,一次次讨论篇目、改换书名,一编、二编,核对文献、复查人名。重新设置边距、字号,不断推翻已有的版式,常常折腾几遍,只为一个读者未必会被注意的细节;想到了设计师为了做出一本让读者有美好阅读体验的画册,一遍遍修图、调图,在几种甚至十几种材料中选择、试验,在印刷机旁跟着师傅反复调整机器压力、调整水墨比例……
不能不说,正是主创人员的这些故事,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创作的困难,同时更明确了做这本电影书的意义和价值,一方面,通过这样一本书,将创作过程中大家曾经遇到的困难、尝试解决的方案,走过的弯路、绕开的陷阱记录下来,是行业经验的累积和分享,对于带着电影梦投身其中的同伴来说,可能是一本有启发的 “过来人之书”;我们相信这本电影书可以拥有更长的生命周期,走出《刺杀小说家》,走出白翰坊,陪着更多电影人在未来拍出更多精彩的片子。
另一方面,我们相信,这样一本展示了一部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创作实录,对每一个有创作热情的人来说,都会是一种激励、一种鞭策:他们告诉我们,想要做成一点前人没做过的事情,让自己出手的东西看起来有一点点不一样,信念之外、更需要付出与之匹配的,持久、专注的付出。出版这一本《刺杀小说家》创作实录,正是一次这样的尝试。
《《刺杀小说家》创作实录》读后感(三):《刺杀小说家》:这世上究竟有没有不骗人的希望呢?
电影《刺杀小说家》上映后,因为双雪涛的原著小说和电影本身都蕴涵了丰富的隐喻,引发了很多讨论与解读。今天的文章来自学者饶静对《刺杀小说家》的评论,她提出,从小说到电影,都在以虚构与现实博弈,博弈不仅表现为文本中虚构对“现实”的侵入,更表现为小说/电影对读者/观众的召唤。但小说的悲剧性体验在电影中被一种神话视野置换了。 这里的现实指的是以人的牺牲为代价的发展,历史写满了罪与不幸,小说用虚构与现实边界的坍塌给出微渺的希望,而电影则以偶像崇拜的视觉奇观展开了神话叙事,一面造神,一面弑神,用神话允诺了从压制中获得解放的自由力量。电影的狂欢式结局是“幻想”,却也实在地照亮了现实。
一位濒于绝望的父亲接受了一项刺杀小说家的任务,这竟是命运的垂怜,他将在这险境中遇见丢失六年的女儿。就故事而言,《刺杀小说家》直面着儿童拐卖的沉痛现实,通过异空间叙事抚恤着那些因此而破碎的家。在叙事理论层面,则是一次带有元小说性质的书写实践,透过双重叙事的交织,作者不断地反思着虚构的边界和价值,“说清楚一点,想死和想活,都是因为写小说这件事,是原因也是结果,反复推动着我一直这么生活着。” ——“写小说这件事”关乎生死存亡,既见证生活又被生活见证着,继而成了这部小说反身直面的究竟。
然而,“写小说这件事”并不自足,小说的完成终究依赖于读者的接受,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促成了从文本到行动的转变。在小说中,我们看到这位父亲最终倒戈,闯入了小说家的虚构世界,他们并肩作战,从赤发鬼手中解救了女儿小橘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刺杀小说家》还给出了一种读者接受美学,读者(刺客)帮助(杀死)作者(小说家)完成了虚构,也将寻回自身失落的宝物。
然而,这样的洞悉并不能抵消小说结尾带来的困惑,一个字面意义上的疑惑:千兵卫的现实到底是被虚构侵蚀还是拯救了,他到底是精神分裂还是被疗愈了?这世上究竟有没有不骗人的希望呢,给出肯定的回答如此之难,似乎就成了虚构的全部理由。小说悬而未决的结尾非常高妙,既肯定了虚构的意义,又对虚构严防死守,将它囚禁在故事的故事中,宛若一个谜。
对小说读者而言,这个结尾已足够带来慰藉;但对影片观众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一个即时的证明是必须的。伴随着小橘子的儿时歌谣,父女在现实中重逢了。这个悲欣交加的结局,是个超越了任何拯救叙事的团圆场景,让观众们揪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这才是现实该有的模样,以及相信的报偿。
小说结束于虚构和现实边界的坍塌中,藉此传达了一种微弱的可能性,像是投入虚空的一枚石头,影片则将这种可能性兑换成了现实,不仅描画了抛物线的轨迹,还让我们看到石头的落脚所在。影片不遗余力地回应着小说的核心关切并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不过,对虚构之奇幻力量的呈现和接受,并非一蹴而就,从不可见的信念到失而复得的小橘子,从文字到影像的转化,叙述基调已悄然转变,小说中的悲剧性体验被一种神话视野置换了。
《刺杀小说家》始终被一种悲剧性的荒诞笼罩着,面对罪与不幸,小说在情节推进中不止一次地安置了伦理反思,这种探问在赤发鬼的一段陈述中集中地展示了出来,“阿弥陀佛,是死了些人,流了些血,世间万物有什么东西是没有代价的呢?想要永久的自由,想要无穷无尽的金子,这十几年的代价不算大,小姑娘,秩序就要建立起来了,到时间你就知道,你,正可以享用他们留下的果实。”可是,从小橘子和久藏的眼睛看过去,“树上没有果实,都是脑袋”。
果实是进步的允诺和诱惑,脑袋则是被牺牲的时代与人们,以牺牲为代价换来的发展是不可能均衡的天平两端。这是一副本雅明式的历史哲学场景,朝向过去,背对未来的新天使被来自天堂的进步风暴推搡前行,他见证的历史只是接连不断的灾难,进步的风暴肆虐之处,皆为废墟,无辜者承受不幸的厄运,历史也成了野蛮的记录。而小说家与新天使承担着相似的记忆责任,凝视那些遗落在时间中的人与废墟。
影片则深入到这些情绪褶痕中,将这些浓缩着愤懑的意象客体转化成为偶像崇拜的视觉奇观了。作为理想的反派角色,赤发鬼与现实中的李沐灵犀相通,当影片在李沐震撼又荒谬的时间演讲和幻城中对赤发鬼的迷狂崇拜中切换时,观众几乎直观到了技术资本与遥远部落之间的相似感,现代人并不自由,同样被物神迷惑并甘之如饴。一寸光阴一寸金,以发展和效率之名,堆聚的资本成为一种邪祟,在源源不断的增值中索取着前仆后继的牺牲。
影片的反乌托邦想象折射着登峰造极的资本拜物教寓言,资本摧毁了过往时代的诸神,却使自身成为新的偶像。自我封神的赤发鬼,成了不断延异的历史与实在之恶的自然象征,我们可以在其中辨认出历史车轮的无情碾压,资本之贪婪与巧言令色,大数据时代的隐私窥视,烦恼与戾气的无明深渊等等,当下现实最令人沮丧的一面似乎尽可以归结于此。这是无限地再生产自身的现实系统,被裹挟其间的个体几乎无力做任何抵抗。
影片的这种寓言化再现渗透着批判的锋芒,神话的两极就此张开,造神与弑神的张力也在于此。一方面,作为集体性的权威叙事,神话的泛神论视野天生就带有膜拜特征,赤发鬼成了象征性的膜拜客体,构成了必然性的专制;另一方面,神话也允诺了从这种压制中解放的自由力量,“一介凡人,竟敢弑神”式的傲慢召唤着对抗的力量,关宁和路空文共同扮演着弑神者的角色,关宁寻女心切,路空文书写复仇故事,面对至亲之人的离去,他们都陷入了迷雾之中,必须斩杀幻境的暴君,方能开辟新生之路。
有意思的是,两个落魄之人的狭路相逢不是巧合,竟缘自李沐借刀杀人的计谋。原来资本大鳄也充满了恐惧,他有一句颇具反讽意味的剖白:“我信因果。” 在造神和弑神的对峙之外,影片补充了因果逻辑,虚构和现实因此严丝合缝地衔接了起来,其中疏离隐晦的人物关系至此也环环相扣了起来。菩萨畏因,众生畏果。因果就是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精神感应,轮转的动因也就是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台词“相信”,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相信”,彼此交织的相信,构筑着意志的共鸣。相信就是一种意志,承载着灵魂最深的渴望,也是凡人属神的力量,是在摧毁中重建,在怀疑中确证的行动。
影片结尾的对决几乎成了一场审美动员,观众也受邀加入了这场狂欢式的弑神战斗中,在“冒蓝火的加特林”“代表月亮消灭你”的爽点节奏中会心一笑,这是奇幻叙述释放力量的时刻,希望压倒了恐惧,集体无意识愿望获得了满足。在大众文化批判的视野下,这种满足也许洗脱不了“幻像”的嫌疑,终究还是文化资本把控的闲暇时间。然而,这幻像也是感性解放的路径,正如小说在双线叙事中安置了对读者的召唤,影片也凭靠观众证成了虚构的力量,文化消费者化身为生产者,让可能性破壁而出了。于是,我们在结尾看见了小橘子,一个果实,一段失而复得的时间,历史和记忆的真实客体。
从小说到影像的改编总是一场翻译,原作内核在影像中得到了转世和再生。小说家视虚构为绝境中的希望,仿佛一根稻草的力量,影像则毫不含糊地奏响了希望的交响。种子是简洁的,它们的生长却难以料想。在神话允诺的自由中,虚构和现实看似不可化约的对立中蕴蓄着振翅欲飞的势能,以轻盈刺破承重,我们背负的现实被光照亮。——这就是《刺杀小说家》在这个春节给予我们的究元决疑的纯粹感动。
《《刺杀小说家》创作实录》读后感(四):这是一场“中二”的冒险,也是一次重要的教育
上个月,《刺杀小说家》导演路阳、原著作者双雪涛和吴琦、罗丹妮一起分享了和这本书有关的故事。他们回忆了从小说发展成电影再到创作实录的机缘,就像双雪涛形容的那样,小说提供了一个火种,更多东西被创造出来了。吴琦和丹妮还聊到做这本书给自己带来的教育,关于在今天我们还可以怎样工作,怎样去谈论理想。虽然电影会离开院线,但这些故事会一直滋养我们。
《一场“中二”的冒险——〈刺杀小说家〉创作实录》新书分享会活动现场路阳:电影本身就是疯狂的
2016 年春天,万娟老师(编者注:电影《刺杀小说家》制片人)来找我,当面强制我迅速地把《刺杀小说家》看完,然后马上给她一个答复,拍还是不拍。我看完之后,马上就请万总帮我约雪涛的时间,我非常想见到他,非常想跟他聊一聊关于小说的事情,以及我怎么理解他的小说。我想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的,我很想拍这篇小说,但是我必须要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小说。
其实 15 年我们看了很多项目书,到 16 年那个时候,已经在筹备《绣春刀 2》的拍摄了,离开机还有一个月,我有点焦虑,因为不知道《绣春刀》之后该拍一部什么样的电影,正在寻找之后的内容。看到雪涛的这篇小说,我才终于找到不用通过理性分析,完全凭感觉就知道想要去拍的一个好内容。
电影《绣春刀 2》剧照所以这部电影雪涛满意是非常重要的。是他的这篇小说给了我们一个创作的开始,给了我们很单纯的想拍东西的想法和感受。我不想去偏离这个东西,如果说雪涛不认可的话,就说明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可能已经偏离了最开始刺激我们去拍电影的想法、念头、情感,或者那一句话。他最清楚他的小说这句话要说的是什么,他可以在一个既主观又客观的视角上去看待这件事情,他会很直接地告诉我这是不是他想象中电影该有的样子。
我在每个阶段都会把素材拿给雪涛看,每次他看的时候我都会很紧张,无论是 5000 字大纲,还是 2 万多字大纲;无论是初稿的剧本,还是定稿的剧本,还有片子剪辑过程中的无数个版本,我折腾了他很多次。包括有的时候,一句台词也会去问雪涛,这句话应该怎么说,我们俩会一块想办法。第一次把片子全部做完给雪涛看的时候,我就坐在他后面,我始终都在看他的反应。我希望雪涛能第一个看这部电影,我觉得我们是能互相明白的。
我跟雪涛第一次见面,是 3 月上旬的一个下午,那天是个晴天,雾霾没这么严重,阳光还比较温暖,在我们办公室的大厅里。我的制片人张宁就说,老路,这个小说你再想想,你是不是真的要拍。我就说不用想,我肯定要拍。
虽然想要去拍的想法当时一瞬间就形成了,但在真正开始剧本创作之前,我反复地考虑过怎么去做。有很多种方式来改编小说,把它拍成不同形态的电影,但对我来说该怎么拍,想了挺久。
之所以做《“一场中二的冒险”——〈刺杀小说家〉创作实录》这本书,最开始是因为我们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踩了很多雷,尝试建立了一些新的工作方式,想要把这些工作方式系统化地记录下来,分门别类地把各个部门的工作都记录下来,也许可以提供给同行一个或许有价值的参考。拍完电影之后慢慢去想,会觉得电影其实是送给观众的,但是我又很希望能够记住制作电影过程中的很多细节,不要时间久了就把它们忘了,所以想要做这样一本书。
这部电影的很多主创我都已经合作过很多年,长的可能超过 10 年了。我对他们很熟悉,但是看了张雄老师采访完后整理出的文字,发现在他们的心里还有很多我没有想到的角落。我能看到他们对电影的情感,我特别感动。我觉得他们一直都没有变过,这是让我最开心的事情,他们一直都比我想象得要更加热爱电影,也难怪这样的一帮人会走到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也很庆幸我们当时有这样一个想法做出这样一本书,无论是交给读者还是交给我们自己,都是一个挺珍贵的东西。
电影是不能脱离商业体系的,在商业体系里面有一些规则,或者有一些套路。但是雪涛的小说给我的感觉是没有套路、完全新鲜,那种新鲜给了我特别幸福和愉悦的感受,我很想在电影里面分享这种感受。我们有一些疯狂的念头想要在电影施展出来,那些东西可能经过算计就会显得比较疯狂,但我觉得不要,那是小说以及我们要做的电影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当然我也要考量,如何通过其他办法把我想要分享的这些东西传递给更多的观众。其实我觉得电影本身就是疯狂,它必须要带有某种探索性或者冒险性才有意思。所以想把很多疯狂的想法、念头记录下来,提醒我们不要去忘掉这件事情。
电影上映之后有一件事我特别开心,很多观众会在评论里面留言,说看完电影之后要去买雪涛的书,这是让我特别高兴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文字是很独特的,文字是不可以被影像、声音或者其他形态代替的,是一种很特殊的人需要的东西。
双雪涛:小说提供了一个火种
准备把《刺杀小说家》改编成电影的时候,我刚来北京。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万娟来找我,在一个特别难吃的西餐厅喝了特别难喝的两杯咖啡。然后她跟我说,你觉得小说找谁来拍?我就想起了前几天晚上在电视上看的《绣春刀 1》,我觉得特别好看,台词特别舒适,叙事也很清楚扎实。
我之前也不认识导演,我就跟万娟说,这个导演你听说过吗?万娟说前两天好像刚刚见过面。我说咱们就去试一试。老路看完小说之后,就决定开始做这部电影。
我们俩见面就聊天,不光聊这篇小说,因为年龄相仿,天南海北地瞎聊。其实聊的内容不重要,人的感觉比较重要,两个人得找到一个合作的契合度。契合度有时候并不一定指见解完全统一,而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对于好东西的认识,有耐心甚至有胆魄来做这件事,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最满意的地方是这部电影不是通过理性计算出来的。因为电影产业跟资本、工业甚至跟产品的关系越来越近了,尤其是现在,我们社会发展得越来越快,大家一个一个都变成会计了。我们能看到很多计算出来的电影,那可能也是一种做电影的方式,但是对生态是不是真的好,我是怀疑的。《刺杀小说家》是一部不经过理性计算的电影,但是它又有这么大的投资规模,所以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东西。我最后看到成片的时候,当然觉得很震撼,很激动。
我觉得这就是思想的力量。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你的一个想法变成了一个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就变成了一个产品,还可能会变成更复杂的产品,不光是电影的形态,还有很多衍生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会思考的人类很有成就感的地方。
从小说到电影,其实我觉得没有一种原则说,什么样的小说能改电影,或者什么样的小说不能改电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就是得从个案来看。
我觉得文学能给电影带来的东西还是蛮多的,不是因为我是搞文学的,我客观地认为电影非常需要文学,而且我觉得电影从业者也很需要文学。有的时候我跟做电影的朋友一起合作,实话实说,我感觉到有些电影人很有热情,但是因为他的阅读和接受的审美教育可能不足够,他受限于,不是自己的热情,而是自己的能力。
我会跟做电影朋友交流,最近有什么新书可以看一看。文学对人的滋养是非常缓慢的,需要慢慢浸润。当你成为了一个文学人,同时又是一个电影人,还是一个热爱某一种美学的人,你就成为了一个复合型创作者,这样的创作者特别适合搞电影,如果单有某一项,不够均衡的话,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文学对电影的作用其实是对人的作用,而不是具体的某一个项目。
我当然希望有更多好的文学作品能变成电影,严肃文学作家们其实写了很多很好的作品,只是没有被看到。问题的第一点是,很多人认为有些卖得好的书就很牛逼,其实这是很扯淡的,很多人默默地在文学上耕耘,写了很多好东西,只是你们没有看到,那是你们的损失。另一点是,不要以为情节很复杂的小说就特别适合改编成电影,或者看起来跌宕起伏的小说就能变成一部好电影,这也是非常扯淡的。
有的时候小说提供给电影人的是一种启迪,但是需要有悟性的电影人去捕捉。小说是一个火种,把你心里的蜡烛点亮,而不是给你一个巨大的火把,把你烧毁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我特别希望我们的电影人有耐心去阅读一些好的当代作家的作品,然后他会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在认真地耕耘文学,这可能对他们有一些帮助。
活动现场吴琦:在今天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工作
开始做《“一场中二的冒险”——〈刺杀小说家〉创作实录》这本书,其实是因为一个商务合作机会,电影的出品方之一华策跟单向空间之前做过衍生品的合作,所以我们之间互相认识,后来他们就跟我们说起这部电影。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们的想法并不是把这本书做成电影的衍生品,而是希望这本书能用书的方式去记录电影诞生的过程,我一下子就觉得自己的专业得到了尊重,做书是被认可为有自己独立的专业精神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开始。
然后我们直接就去找导演了。这其实也是很离奇的一段经历,因为通常中间可能要经过很多重沟通,比如先谈条件,要谈合同,谈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合作,我们这些都没有谈,只谈内容。我记得我们还在导演的公司里吃了特别好吃的面条,一切都出人意料地愉快。这跟我熟悉的或者偶尔接触到的整个影视行业那种非常焦虑、高速、算计的工作方式完全不同。
当时我们随手就开始找身边的哪些书可以做参照,然后导演突然想起来说,有两本书放在家了。他立刻就开车回家,把那本书取过来,我们马上就开始讨论了。这本书出来之后,导演的同事就问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些赠书给导演,他已经忘记了赠书到底是多少册。
对我自己来讲,做这本书的过程是很重要的一次教育。可能对我们小团队来讲合作并不困难,但是这样庞大的一个规模,这么艰难的专业工作,用这样的工作方式完成是很困难的,用“中二”来形容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相反,它是非常实际的。所有人在做书的过程中又再次被这样的内容所打动,他们对自己作品的那种相信、欣赏、开放。整个合作是特别美好的一个过程。
我在淘宝、朋友圈看到好多《刺杀小说家》的衍生品:面具、胸针、衣服……他们都不把衍生品当做衍生品对待,比如衣服就用衣服的结构、专业,衍生品本身的质量和审美都特别在线。所以你就看到,它变成了一个种子,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专业里面得到很多回响。
路空文的面具被做成了衍生品我看到片尾字幕的时候非常感动。那种感动一是来自于一个庞大的阵容,二是来自于它的开放程度。这部电影在每个具体的环节上都找到了非常具体的合作伙伴,而且真的是合作伙伴,不是甲方和乙方那种利益绑架的关系。那个字幕本身带来的震撼是巨大的,而且特别真诚,所以我会觉得这部电影可能不只是一部电影而已,它从一个概念慢慢地生发,长出那么多东西。我觉得即便过了上映期,《刺杀小说家》也会一直留在电影行业,留在文学行业,或者留在其他行业里面,成为一个故事,然后成为一个重要的案例。这其实也是我们做这本书的一个初衷。
导演一直强调说,他做这本书并不是想要宣传自己多么厉害,而是希望把他和他的团队在完全中国的语境下,把一个高难度的强视效电影做出来的经验留存下来。日后我们的电影工业肯定会继续往前走,会有更多的导演或者创作者走同样一条路,希望他们能从中得到很多具体的帮助。
做这本书是一次教育,而且我觉得教育是泛文化意义上的,不只关于电影、文学或者出版,而是关于人怎么在今天这样一个环境下继续去工作,甚至是去追逐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已经不在公共领域讨论这些词语了,我们甚至以这些词语为耻,或者觉得今天社会里面这些词语太奢侈。
这是一部完全用信念构筑的作品,对我们来讲,要去理解信念构筑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只和电影专业的人有关,也关于你在生活中、工作中怎么与人合作,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他人的劳动。这本书很鼓励我,单读做出版以来,我自己的私心是能被每一个作者、每一本书所鼓励。
我们都是一个行业当中的链条,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在这本书中,大家会看到很强烈的小共同体的感觉。我印象深刻的是,每一次他们都会先开会,把大目标制定下来,然后再去各自工作,可能各自的工作状态导演未必都知道,大家自己去想办法,想完办法后再开会,看是不是偏离原初的想法。他们特别自觉地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忘掉一开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觉得这种“中二”、乐观的精神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方式。
这本书或者说做这本书的过程,让我找到了重新去谈论所谓理想和信念的方式,你得在具体的实践中展现它,不能特别抽象、空洞地去谈信念,信念是一个过程,信念也是一种方法,把信念作为方法。
其实我自己不是工业电影的观众,我更愿意看更文艺、艺术的电影。所以这也是一次教育,看到《刺小》的整个拍摄过程,并且用一本书的方式把过程记录下来,你会意识到,每个人有自己的审美偏好,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个意见之下,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东西,关于电影的复杂和专业程度,以及电影人如何工作,这些与你个人的审美好恶相比,的确是一个很庞大的世界,从那个世界能够得到的信息,远比说我不爱看某种电影要来得营养更丰富一些,这是对我们自己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启示。
我特别有信心,大家可以把这本书当做方法论的书。说得更俗气一点,也是一本很鸡汤的书。它提供了在今天的社会中,大家怎样去寻找调试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的方法,尤其是一起工作的人。我们听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工作不愉快,合作上痛苦,同事之间互相折磨。可是导演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状态,真的是在互相理解,互相体贴。我们和他们合作时,也不是在互相倾轧或者互相索取,而是互相给予,这些都是特别美好的经历。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工作。
丹妮:要实现理想,付出的努力是很具体的
第一次见路导以后,有个非常明确的想法,虽然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看到成片,但是我非常清晰地知道这个电影是能够支撑一本书的。有两层原因,一层是它的素材非常丰富;另外一层是,当时路导在不停地给我们讲故事,讲得非常细致、生动,我特别难忘,包括演员是怎么工作的,搭场景要怎么样去运筹帷幄,怎么解决自然光不足的问题,造型指导怎么设计赤发鬼……
我和编辑部的同事们都很喜欢电影,但是都不知道一部电影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但那一天我的感受就是,我好像可以通过这部电影了解一点点一篇小说是怎么变成我们最后在大屏幕上看到的东西。做这本书的原因,特别简单地来说,我需要知识,我需要知道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做的。
整个导演组非常开放,让我们大胆去想、放手去做,他们全力配合。我们一开始想以设定集的体例做,但是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有兴趣的是电影是如何拍出来的这件事,所以人物设定之外,创作的其他环节也非常重要。
当时就想,我们需要一位电影行业的“门外汉”来提问题,问一些我们希望知道,但对于电影专业人士来讲可能是常识的问题。而且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脉络,把相关的主创人员都问一遍。很幸运,张雄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记者,而且他也做过相关的工作,我们一聊他就说很愿意做这件事,一拍即合。
这个时候其实我仍然不知道这本书会长成什么样子,我只知道我们有海量的图片和很多愿意接受我们采访的主创人员。接下来三个月的时间,路导和他的助手一直在帮我们联系各位老师,然后张雄就挨个去采。录音很多,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整理、撰文、编辑,第一版初稿有 5 万多字。随后又补采了两位老师,补充了几万字。设计师也去了好几次工作室,剧组那边保存了海量的大图,几经筛选,最后拷贝出了五六千张作为配图素材。
面对这样一个体量,再来重新考虑,我觉得我们不能只把它做成几个主要角色的设定集,实在有太多故事和经验需要分享。所以大家今天看到,最后我们把这本书改成了创作实录的体例,包含了电影各个步骤流程的主创人员的分享。这本书我们并没有赶得特别急,没有让它一定要在电影宣传前期上市,我们还是觉得要首先保证它的质量,而且对它的长销非常有信心。
这是一本不会随着电影下线而下线的书,它会跟电影一样走得非常远,会留给很多喜欢电影喜爱文学的人。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创作者的分享,只要你对内容创新有热情,就会在这里面看到很多具体的启示。
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其实有点激动。我首先是一个读者,看过雪涛老师很多小说。那一刻我的内心有小小的震撼。这篇小说是双雪涛在二零一几年写的,写的时候还在沈阳,他写的时候绝对没有想过,这个小说决定了几年后,有这么多人花 5 年的时间,用这么多钱、这么大精力做这件事情,这非常疯狂。
同时我理解这篇小说给导演和整个创作团队都提供了一种刺激他们创作神经的元素,我觉得这是文学的魅力,有点像给人下了蛊一样,就是你觉得这东西特别有魅力,你就想投入其中。这让我作为一个读者也好,或者作为一个文学出版编辑,感到非常兴奋,这样一篇小说自己长起来了,变得像有生命力一样,然后长出了这部电影,接着,居然又能有一个机缘,让它再一次以书的形式往前走。
如果一部电影最后能让我们有兴趣去追根溯源,回到文字,看到故事起始的部分,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所以我也非常关注电影上线以后《飞行家》的销量,我很开心。我以前觉得这部小说是有一些固定读者的,可能是喜欢作者的人,还有一些是原来印象中读小说的读者,但可能因为电影的缘故,很多本来不会打开小说的人也去看小说了,这是一件非常牛的事。
我们做这本书的一个想法也是真正去学习其他行业同事的工作方式。不同阶段的那么多素材,剧组的同事整理得非常清晰。每一次我们把文稿给剧组看,他们很快就会返回来,而且看得很仔细,让我惭愧,文稿还会有错字,还有演员的名字前后不一,他们都认真修改,而且非常快,我们每一次把照片拿过去,他们对照片的反馈,应该写什么样的图注,也处理得非常快。
编辑做一本书的生产周期大概一年,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我们投入的成本就是那样,我们都经常觉得苦不堪言。说实话,有很多槽可以吐,比如说书号难拿,作者拖稿,设计师给的封面不满意,我自己能感受到我们业态现在的工作状态。
可是去导演工作室的几次观察会让我觉得,他们很热血、也很淡然,没怎么感觉到他们身上特别倦怠的部分,是一群很乐观的人,气势昂扬,而且如此细碎的工作也没有不耐烦。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做一本 5 年后才会出的书,不知道会怎么样,而电影的不可测因素是更多的,比如说疫情期间能不能上线供应都是个问题,可是书还是有很多具体的期盼,有了书号就可以出版。
所以我会觉得做电影其实对人的心性折磨得更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书的几个人得到了一种教育,就是在不同行业的创作者,他们要真正实现一个理想,付出的努力是更具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