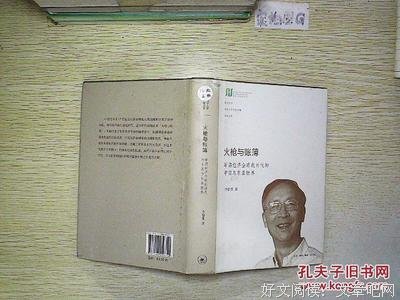
《火枪与账簿》是一本由李伯重著作,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40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火枪与账簿》读后感(一):从未闭关
本书全球史视角,全面而非茅海建式脚注,圆融而非杨念群式乡愿,没有直接的观点,更像一幅近代化中国研究综论画卷。书中所引书目可做书单。三联书店装帧素雅明快,优于社科文献出版社。bug两处:P244,最后一行,“唐太和三年(829)”应为“唐大和三年(829)”;P316,第一段,第三行,宁远之战发生在天启六年,而非崇祯初年。
《火枪与账簿》读后感(二):用现代视角,讲古代故事
诚如某书评言,这是一部伪装成世界史的中国史,但李伯重老师这本《火枪与账簿》从内容上而言无疑是精彩的。有明一代,在传统的印象里总是东西方初识的懵懂时代,然而书中所详细列举的火器革新、贸易来往的证据却表明,火器技术随着商路的传播与应用远比想象中快了太多,而欧洲人的出现,自其伊始便立刻引起了诸多东亚国家的关注,也早在19世纪的直接军事入侵以前,便深刻介入了东亚国家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语境下,之前所零碎知晓的徐光启、郑成功、王直、土木堡、白银、倭寇、澳门,以至于最终的满洲征服,竟全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十七世纪整块旧大陆因火器和贸易重新赋权的一部分。上国的崩溃与重建,也并非传统上王朝周期律的死板答案,更有地缘政治重重的死结纠缠在其中。
这一灰暗的图景,是当代的我们所更熟悉的,却也是我们所更陌生的。李伯重老师言:历史书写是可怖的。诚然,但读毕也有一丝或许无关的深觉,历史的读者也是可怖的。一目几行过去,遍地是沧海桑田,铁马金戈,仿佛历史总是充满了变迁成败的激情,然而当把今日放入无数历史的因果网里去,将己身作为仅代表自己生命的滴水放入这漫长的大河里去,历史终究又太漫长、艰苦、细碎、平凡、而茫然。我们这个时代的结果是什么?后人会怎么叙述这个时代?我们在相似或不相似的环境里会上演相同或不相同的故事么?问向虚空,却又无人回答。一双浮在宇宙,滤去无数渺小的悲欢离合,从而看透漫漫兴亡的眼睛,是多么地奢侈而又傲慢啊。
《火枪与账簿》读后感(三):还是有注释好
不知道历史学者或者出版者怎么看待公众史学,公众史学不需要注释是一个看似合理但又很荒诞的想法。如果嫌弃行文中脚注,那完全可以以尾注来替代。注释的意义在于,寻根溯源找到一手史料,验证论述和结论。没有注释怎么办呢?假如作者误解了原材料的意思呢?谁来纠正呢?
史学著作,无论是严肃史学著作还是公共史学著作,终究要戴着脚镣舞蹈,超脱一手材料是不可能的。所以注释是必要的,无论以什么样的理由。李先生屈从编辑或者出版社的需要,费了很大功夫删除注释,非常令人遗憾。
关于这本书。全球史的观念是非常火的,而且有越来越火的趋势。不同的史家当然会有不同的视角,也没有必要求全责备。而且本来副标题,李先生就是要观察这个趋势下的中国。作为中国的史家,观察全球背景下的中国变化,本来也是人之常情。更何况,作为15-17世纪,人群“被动”但商品“主动”的大国,从中国视角出发,对于研究全球史的学者来说本来就是比较新的视角。从整体来说,李先生从整体到局部的论述安排,我以为还是比较合理的。
在书中李先生涉及到了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宗教的变化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然“火枪与账簿”隐喻军事和经济两个最重要的主题,表明了此时西方人群所主导的这种所谓贸易扩张,是带有暴力性质的。而这一点相较于1498年之前的全球联系非常不同。不同之处就在于大规模组织和暴力。我时常在想的问题是,所谓西方、欧美的先进性,不就是建立在这样赤裸裸的血腥抢掠基础之上的吗?所谓的现代化的世界市场规则,不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原罪之上的吗?是不是想要获得在国际上的先机,必须经历这样的铁血洗礼呢?
《火枪与账簿》读后感(四):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近代中国的衰落,国人扼腕痛惜,对其动因和经验的研究,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热点。李伯重教授的新著,希望以新史潮、全球史、公共史的视角来解释中国何以在近现代化的转型中落伍。作者认为,一切重大的历史变化都不是忽然发生的,都离不开国与国间的联系与相互影响。如同歌德所言:我认为但丁伟大,但是他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经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些事全部隐藏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深。以15世纪末欧洲地理大发现为标志,经济全球化开始萌芽发展,作者以“火枪与账簿”来概括当时的时代特征,火枪代表了军事革命导致的新型暴力,账簿则意味着对商业利益的积极追求,两者共同构成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丛林法则”,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这一点上,作者与史景迁有着高度共识:从1600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和其他国家交织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国家一道去搜寻稀有资源,交换货物,扩大知识。作者尝试把中国置于邻国和欧洲国家的镜像中来观察,晚明转型失败一定程度上是世界史上著名的“十七世纪总危机”的一个部分,无论是在热兵器主导下的新型军事体制上,还是在适应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方式的近代经济体制上,晚明都未能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抓住机遇,由此导致的路径依赖使东方大国不得不等上两个世纪,才又在新的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中开始近代化进程。本书资料翔实,尤其第四章和第七章谈及15世纪文化圈及其演变,对中国周边的“佛教长城”如何抵御伊斯兰教东扩、君士坦丁堡陷落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关系、明朝与缅日荷清4场战争的不同结局等的讨论,令人眼界大开。当下,中国正面临重构国际秩序的难得机遇,读500年前的这段历史令人感叹不已,变局之下的历史使命必须勇敢担起。
《火枪与账簿》读后感(五):读后感
在英语里近代化与现代化是同一单词。过去主流观点认为:世界现代化就是西方的现代化及其在全球的扩展过程,现在观点逐渐改变了,认为现代化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虽然西方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其他如亚洲、美洲、非洲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无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得利者还是损失者,都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就我们而言,现代化与近代化是有较大区别的、甚至是两个概念。现代化多指十一届三中开启的改革开放道路,近代化是指从单纯的封建制开始被打破。中国而言近代化开端,有多种说法。有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自发说: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从宋朝开始,当时土地、人丁税赋仅占税赋总额的30%,而工商税赋占到总额的70%。有互动说:认为大航海时代,欧洲人扬帆东来,与中国人下南洋、走西洋互动,特别是在南洋,形成了环中国海的庞大华侨势力,从台湾海峡到马六甲海峡,都是华侨势力的天下。还有被动说:认为中国近代化是1840年以后,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的,导火索是鸦片,又叫“鸦片战争”。
全球化引发的重商主义,也一度挫败了近代化进程,如西班牙、葡萄牙掠夺的巨大财富成了中国丝绸、瓷器的购买力,培育的对金银货币的巨量需求,东西方两个最大的王朝,大明王朝和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最后都战争引发的银元供应短缺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倒了下去。到了清初,为了困住郑成功实行禁海迁界政策,那知道反而使郑成功独占通洋之利。萧一山在《清史大纲》中认为:郑成功是中国近代民族革命第一人,正是郑成功驱逐了台湾的荷兰人,使得荷兰在近代化竞争中衰落下去,间接促使英国崛起,从而改变了世界大格局。
《火枪与账簿》读后感(六):全球史作为理解中国的基本视角
《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是中国经济史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的最新作品,是中国学者从全球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重要专题著作。作者对本书的定位是:“这是一本体现国际学术新潮流、面向社会大众的全球史研究著作。”(第1页)这本书从新史潮、全球史和公共史学三个角度,为我们重新梳理了15到17世纪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东亚世界互动时的特点,抓住了在国际贸易规则还未形成的阶段,经济全球化所具有的商业与军事暴力同时存在的特征,为我们重新理解明清易代提供了新的视角。
作者主要从贸易与军事两个角度为我们描绘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具体特征。从贸易角度讲,以白银流通作为主题曲,以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市场为舞台,以生丝、丝织品、陶瓷、蔗糖、香料、茶叶等商品为道具、以包括来自西欧、东亚、东南亚各国的商人作为演员,“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联系日益密切的国际贸易网络”。(第95页)这一观点挑战了 传统的明清“闭关自守”论。作者认为:“到了16世纪,欧洲人从海路到达中国之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东部地区和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其他地区开始在经济上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掀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大潮。”(第57页)作者评论道:“没有中国的参与,经济全球化虽然可以可能也会发生,但肯定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在世界历史上真实发生的经济全球化了。” (第57页)
从军事角度讲,16世纪发生的火药革命和军队组织革命在17世纪的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第一,由于各国间利益冲突增加、战争频繁,火器技术得以广泛传播;第二,由商人形成的全球性网络使得知识和技术(尤其是先进的火器技术)可以更加便捷的传播。而军事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作者认为其中最核心的角色是商人。“唯利是图是商人的本性。如果某种有用的知识和技术在某个地方可以带来更好的回报,商人就会把这些知识和技术出售给能够出最高价的主顾,而不问他们是何人,这就破除了国家对先进军事技术的垄断。”(第168-169页)
作者以火枪加帐簿来概括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并通过充分的史实印证了“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第397页),并对明代灭亡提出了新的解释。作者总结道:“导致‘丛林法则’成为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东亚世界国际行为准则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东亚世界最主要的国家——中国未能充分认识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在创造一种国际新秩序方面未能发挥作用。”这对今天仍有启示。
《火枪与账簿》读后感(七):未见账簿,只有火枪
冲着书名,入手了一本,但读完全书,却发现,账簿在哪里?!其实本书主要说的都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东亚世界中的血泪史,商业部分的描述并不占据重要部分,而拿账簿说事儿更只是个噱头,诶,不跟作者计较,幸好内容上还是可圈可点的。
读上几页就能够感受到了加州学派的味道。相比之下,本书第一章可读性最强,篇幅不长,但基本上已经把本书的立意、方法与布局都交代清楚。这种写作手法,对于不具备长期海外教研经历的本土学者而言,是值得借鉴的。
新史潮、全球史、公共史学、东亚世界、大变局,这是第一章的关键词,也是理解全书主旨的几把钥匙。作者强调对历史须有“当代”意识,要通过新的材料与方法重写历史。而当前,以全球史替代世界史是必然结果,要更好地诠释自1600年至今的历史,首先需跨越国别,然后还要关注中西方往来的“双向”关系。在此基础上,什么是东亚,什么是大变局,都可能需要有着更为“当代”的理解。为什么全球史视角在1600年之后才具有意义?通常回答是西方此时开始渐次对外扩张。但当年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军队不也横扫亚欧非吗,为何不能算作历史上的大变局?作者同意前人的观点:经济全球化的最终归宿是统一的和唯一的全球市场。西方的原始积累掀开了资本积累的序幕,早期经济全球化由此开始,这是成吉思汗时代无法想象的。而贸易,必然会打破国界。大众希望更多了解历史的渴求,迫使史学者必须尝试用通俗易懂的著作来陈述见解,这可谓之公共史学。作者对本书为何一个注释都没有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是为了通俗易懂,且不打断行文的连续性。但作为研究者,读这类本应有大量注释却一个都没有的书,总是会心生疑问:相关数据、材料究竟从何而来,这反倒是更加打断了阅读的连续性。也罢,个人习性而已,作者也说,他还会有一本与之相关的针对专业学者阅读的著作,就等着吧。
在扼要交代了贸易打造的早期世界后,论述进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各个方面:军事革命如何促进技术推广,宗教传播如何驱使文化圈的形成、进而又如何促进经济的整合,东亚世界各国之间又如何在纷争中交融。作者对明朝的军事史似乎是比较熟悉和感兴趣的,不过对我而言相关部分倒是写得过细了。
经济全球化肇始最关键的是海路的连通,在1600年以前以陆路为主的时代,中国其实并未完全闭关锁国,可一旦海路打通,欧洲海外贸易大国就K.O.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了。1600年以后,一国本应更加开放的时代到来,东方世界的中日等国却逐步走向封闭,故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落后于欧洲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有些论述非常有意思,例如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意义究竟如何有限,在我国西北地区一直延伸至缅甸等地(只是大致说明,书中有更精确的表述)的佛教长城如何抵挡伊斯兰教的入侵,还有朝鲜、越南等周边诸国如何看待自古以来与中国的关系等等。
但对于学术型强迫症患者而言,还是比较期待有脚注的严谨的学术专著的出版。
《火枪与账簿》读后感(八):你不跟我做生意,我就打你。
火枪与账簿,源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形象——“左手拿着账册,右手拿着刀剑”。火枪意味着新型暴力,账簿意味着商业利益,因此“火枪加账簿”就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的写照。其含义是这个时期蓬勃发展的国际贸易与暴力有着程度不等的联系。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各种利益主体在相互交往中往往运用暴力。 我想,这个标题的大意也可以简化为:带着武器去做生意,你不跟我做生意,我就打你。 里面有一些观点比较新颖,当然,也是因为我书看的少,没接触过类似的观点。以前看李子暘的文章,不知道他的观点出自何处,现在看来,他肯定看过李伯重老师的书。现将一些观点摘抄如下: 1.明末时期,当局经过对日本、越南、葡萄牙等传来的火枪、大炮进行改良,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火药类武器,后面成为后金攻下明朝的利器。起码在武器上,并没有落后西方世界。
2.虽然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实行海禁政策,官方基本停止了对外的大规模活动,海上力量也一落千丈。但是民间的交流一直没有停止。以郑芝龙为代表的海盗成了东西方交流的主要中介,他不仅会闽南话、广府话和官话,而且也会葡萄牙语、卢西塔尼亚语(一种犹太商人使用的犹太-葡萄牙语)和日语。后面被明朝收编,成为明廷强大的海上力量。许多沿海的商人,亦商亦盗。
3.倭乱跟日本本土政局紧密相关。前期倭乱主要以日本海盗为主。那时日本本土没有统一,天皇也无法约束各地的领主,遂导致日本流出大量海盗,勾结我国东部沿海民众大肆骚扰、掠夺。后期海盗则以我国东南沿海民众为主,勾结少量倭寇作乱。
4.佛教在我国周边取得的支配性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伊斯兰教的东扩,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都意义非凡。“从从蒙古、新疆北部、青藏高原,到中南半岛的缅甸、暹罗、柬埔寨和老挝,佛教取得了支配性地位,形成了一道环绕中国西、北、南三面的“佛教长城”。这道“长城”遏制住了伊斯兰教的东扩,从而使得中国避免了印度的命运。因此对于中国以及东亚世界来说,这道“佛教长城”的出现,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5自秦汉以来,中国没有外扩的基因。以前我一直把这句话当笑话看的,因为不可否认,中国的面积从秦朝以来,总体而言是向外不断扩张。但本文提出的观点说服了我,“中国到秦汉之后,所谓“中国本部”(China Proper,即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内地)疆域相对稳定,还能扩张的空间基本上都是沙漠、高山、寒冷荒原等贫瘠甚至寸草不生的土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耕社会来说,这些土地没有多大经济价值,而占有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开支。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中国向外扩张,成本太高而收益太低。耗费巨资,派遣大军去征服并占领那些从经济上讲意义不大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是很不合算的。因此,由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决定,中国命中注定不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国家。”但是四处环敌,又注定了中国不得不在实力强盛时,主动出击,毕其功于一役最好的方式就是将敌人势力范围纳入自己的统治范畴。
中国解决国际冲突关系的体系是朝贡体系,“在解决冲突时,尽可能不使用战争手段。费正清说:“中国的军事传统含有许多非暴力的方法。……打仗的目的是使敌人屈服,并不一定要消灭他们,要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而不是肉体上的战果。”因此,只有在直接威胁到中国本身的安全时,中国才会把战争手段提上日程。”
这种外交思想一直延续至今,中国对侵略、统治外国没有兴趣,以和为贵是我们的外交传统。
《火枪与账簿》读后感(九):局部文字可圈点/全书逻辑有问题
此书似乎很受追捧,曾经出现在各种推荐书目中。
图书馆借阅,粗粗翻阅一遍,外行看热闹之余,胡乱评论几句。
一、 可以长见识
正如作者定位:公共史写作。书中针对中国进而延及东亚,综括了有关经济全球化、军事史、国际纷争等方面研究的已有成果,以比较通俗的语言(取代拿腔拿调的学术语言、取消让人心生厌倦的繁琐注释)呈现出来。如果你原本对相关主题的内容不了解,读此书确实可以长见识。
以下试举几例。
围绕白银的国际流转,形成独特的全球贸易平衡格局。
国际商路和商人的复杂性:海盗也可能是海商,倭寇未必是日本人。
火药的东西传播与火器技术的西东传播。
“佛教长城”的形成以及对伊斯兰教的抵御。
作为一类特殊对外贸易形式的中华朝贡体系。
中国是否对周边国家有侵略行为:双边叙事的不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爱恨交加。
二、 全书的基本逻辑似乎不太通
书名副标题为“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亚与东亚世界”。无论文字如何摆布,结合第一章“这是一本什么书“的解读看,经济全球化是此书的第一关键词,其他所有内容都应是围绕这个主题而设计。
把经济全球化这个词再拆分一下:一个是经济,一个是全球化。经过这样拆分之后再看此书,似乎就会出现问题。
统揽全书,1)贸易肯定是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第二章),我们很容易接受。2)军事革命(第三章)、文化圈洗牌(第四章)、国际纷争(第五章)与经济全球化的联系则需要解说,为此作者在每一章正文叙述之外会专门设一小节,讨论这些主题与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关系。这个有点勉强,但也可以接受。3)然而,第六、七章对晚明国家安全和军事改革的介绍以及所经历的四次周边战争,似乎已经无法与经济全球化联系起来,作者也干脆不再对此做任何交代。
所以,我的疑惑是:如何处理经济、军事、文化三大要素的关系,并将其纳入经济全球化这个主题框架之下,似乎还是一个问题。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是经济史学出身,最近这些年对军事史多所涉猎,书名“火枪”和“账簿”很好地概括了作者想真实写进去的两大内容(从实际篇幅看,应该说军事部分还超过了经济部分)。但怎样顶着经济全球化这个帽子,处理好这两部分内容的关系呢?
再说研究对象。东亚的中心肯定是中国(第一章有详细交代),东亚关系似乎就是中国的周边关系。但是,如果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去写中国和东亚,我觉得似乎应该包括以下三层:1)中国与全球化,2)东亚与全球化,3)中国与东亚。我还觉得,重点应该是前两个部分,只有放在前两层平台上第三层才有存在的必要。但从书中内容来看,似乎正好颠倒过来:最大的份量(第五六七章)似乎落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所以,我的疑问是:什么是全球化,地理大发现(全球化开端)之后所有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各国周边关系)演变都可以看作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吗?
三、最后的结论
再把此书内容排列一下,我发现:如果没有“早期经济全球化”这顶帽子,当前呈现的这些内容是无法组合成一本书的。所以,这顶帽子虽然不合适,但还必须戴着才行。
唉!
《火枪与账簿》读后感(十):《火枪与账簿》: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看晚明
在当今史学界,把西方的大航海运动,视作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标志,已经几乎成为共识。最著名的世界史普及性教材——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一书,也是以1500年为界,将世界史分为地区史和全球史这样上下两卷。按照这样的界定标准,晚明时期的中国,恰好处于早期的全球化时代。
近些年来,在中国的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赞同“晚明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的说法;然而真正把晚明时期的中国,放在早期全球化背景下加以考量和分析的论著,仍然相对较少。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先生于2015年8月出版的《晚明大变局》一书,已经开始了这种尝试。而新年伊始,三联书店推出了清华大学李伯重先生的《火枪与账簿》一书,则代表着中国史学界在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看待和分析晚明时期中国的最新成果。相较于《晚明大变局》,《火枪与账簿》一书尽管在篇幅上明显短小许多,但在论述的聚焦性和系统性上,可谓是更胜一筹。
在李伯重先生的笔下,晚明时期的中国,尽管在表面上,仍然维持着上国朝贡体系的格局,但实际上已经是危机四伏——一方面,荷兰、葡萄牙等欧洲新兴国家,出于殖民主义和商业贸易的双重需求,积极在中国沿海地区寻求殖民据点和更多的商贸机会;另一方面,隔海相望的日本、东北方向的满洲、西北方向的蒙古、西南方向的越南和缅甸,其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都在迅猛提升,不断对明帝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性地位提出挑战。这种诸强争锋的地缘政治格局,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而这种经济全球化,又促发产生了军事全球化的进程。至于西方列强和明帝国的四邻国家,军事上的革新与投入,是挑战明帝国权威与地位的必要保障;而反之对明帝国来说,军事上的革命,则是维护自身帝国地位,保障国家安全与利益的必然之举。这样的内在动力,使得在这一历史时期,无论是明帝国,还是其周边国家或政权,在军事现代化程度上,跟此时的西方各国相比,可谓是毫不逊色。经济上的全球化和军事上的全球化,成为理解这一时期东亚世界变局的两把钥匙。
经济全球化随之带来的,是对资本和利益的无上追求。在李伯重先生看来,这种利益至上的追求,已经让身处这一大变局之中的许多人,开始摆脱家国情怀的羁绊,转而完全以利益关系,作为衡量其举动的唯一标准。汪直等人抛弃父母之邦,成为倭寇的首领;郑芝龙在明帝国、日本、荷兰之间腾挪自如,今日是敌,明日便成友;一些所谓“兄弟之邦”,转眼之间就成为刀兵相见的敌人。所有这些历史现象背后,只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可以解释,那就是“利益”。
面对这样的“丛林法则”盛行,东亚世界里的主导者——明帝国未能充分认识最新的国际形势,从而创建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相反,却反应迟缓,行动不力,不仅没能利用新形势带来的机会,反而被其带来的挑战弄得焦头烂额、无所适从,最终走向灭亡。李伯重先生在书中,对明帝国在履行国家角色与国际责任方面的失败之举,表示出强烈的惋惜与遗憾。
李伯重先生早年重点研究明清江南经济史,最近几年才把研究视角转向晚明时期中国和东亚世界的政治史、社会史和军事史。在经济史方面多年来的深厚积淀,使得他在这本论述全球化背景下东亚世界历史变迁的书中,非常看重军事变革、政治动荡和地缘关系变化背后的经济因素与驱动力。正基于此,他不只反复强调资本和利益追求在这一时期东亚变局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把这本书的副标题,也命名为“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这样的分析视角,不只跟马克思的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一脉相承,也能在中国积极践行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参与新时代下的全球化的今天,给我们以足够多的借鉴与启示。
鉴于以上原因,这样一本“小书大作”(万圣书园刘苏里先生语)的论著,一定能在国内史学界和学术界,发挥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2017.1.15中午作于竹林斋
(本文首发于2017年1月17日的腾讯文化“华文好书”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