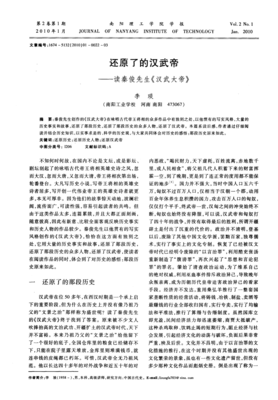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是一本由辛德勇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精选点评:
●其实我觉得本书写得真心不错,最精彩的莫过于两点:第一是戾太子为何喜欢谷梁学——因为谷梁学最看重嫡长,对于母后可能被废而失位的太子而言,提供的即位理据最足;第二是王俭的《汉武故事》有王俭为自己父亲参与的刘劭身为太子谋反南朝宋文帝的感慨与同情。我觉得遗憾的是,尽管辛德勇在南京工业大学的讲座中反复强调“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但对于什么是科学却了解有限,实际上科学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可参照查尔默斯《科学是什么》一书。辛德勇勤力沟梳文献自然应予肯定,但文献学之外,实有更广大空间。我很欣赏辛德勇正文里提到所有人都只提姓名,不言身份,亦不言身份。这种态度值得肯定,否则就有以身份压人的嫌疑了。历史学本身就存在着如王明珂所说客观的历史和主观的“历史们”,而如何展演也有意思,值得思考,辛德勇和田门弟子皆如此。
●“现象级”的政治史著作。王俭的部分略扯,减半颗星,四星半。
●在田余庆先生数十年前对于《轮台诏书》的论证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的情况下,敢于走出来大胆质疑本身就是件需要勇气的事,虽然我不怎么治过秦汉史,不敢妄议各派观点。
●二刷,辛神的文献学功底和考证功夫真令人叹为观止,当然更厉害的还有他一如既往的满级吐槽能力……此次增订本附录了《汉武帝太子据施行巫蛊事述说》和《〈制造汉武帝〉的后话》两篇文章,借用某豆友的话来说,“一篇答疑,一篇补刀”,这可以说很辛德勇了。
●在「輪台罪己」問題上對《通鑑》的政治構建問題爬梳得相對合理。但在巫蠱之禍這一問題上對漢武帝和戾太子關係上的分析就顯得心證過度了。諸如在第六章:〈漢武帝謂戾太子不類己故事的原型〉中,對王儉建構漢武帝與戾太子關係所參考的「漢家故事」僅憑心證,在沒有文獻證據的支撐下便推測王儉是通過漢高與漢惠,漢宣與漢元之間的「子不類父」建構出了漢武帝與戾太子的矛盾關係,顯得太過單薄。此外,在附錄:〈漢武帝太子據施行巫蠱事述說〉篇中,對「壺關三老」勸諫的過程亦做了心證十足的分析,從而間接證明太子據在巫蠱事上的「不清白」,亦顯得很奇怪。作為一本志在通過文獻整理梳理《通鑑》對漢武帝「史學建構」的「製造漢武帝」過程的論著,存在這樣的論證薄弱環節,會使得作者本身的論述亦是在「製造」一個作者心目中的「漢武帝」。
●新版,老辛一如既往的怨念、吐槽加开黑。本文考证过于繁冗枝蔓且论述的先后顺序似可调整,更重要的是个人感觉其论证存在很大的逻辑漏洞,即使加上回应商榷的文章,我依然不赞成他的观点。。。
●想不到居然这么短。主要(能立得住的)结论是:司马光为了政治需要将汉武帝塑造成“那都是年轻时犯的错啊”,但实际上茂陵刘郎其实是“余之生涯一片无悔”。其他相关的推论就真的很推论了,反正材料不够多随便推。
●增订本后加的几篇文章都是在网页上搜索阅读的,假装自己读了增订本吧 大二刚买这本书的时候完全看不下去他在写啥,现在可以认为自己看懂了,并且可以一本正经跟同行复述 完全认同其深察史料来源及史源写作时具体政治背景与作者价值取向的研究方法,但因为对秦汉史一无所知所以难以判断其结论究竟有几分靠谱。辛老师在《生死秦始皇》中写,他赞同“道不远人”,即学术研究路径的采取不应悖戾平常的人情事理……私以为,探究历史书写理应也是从好奇写作时真实的人心开始。无有数十年学海积淀,人间浮沉,难以做出这样的成果,也难以真正理解这样的成果。 我一直都私心认为及希望,历史学科会发挥其对于人心最深的悲悯和最广的关怀。
●8.7分,果然不错。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一):读《制造汉武帝》司马光制造了汉武帝
支持辛德勇 司马光制造了汉武帝 年代早的史料可信 就像 汉书 虽比史记所引用的史料多 却都是画蛇添足 如对贾谊董仲舒的书写美化成分太多 这种衬托似乎更显现了汉初汉武帝对儒家 儒术的重视 却不知武帝朝的 儒术 仅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史记的作者是 当局者 他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而汉书的作者不过是拾人牙慧帮腔作势的远观者 自以为拆解了当局者迷的藩篱 实则是墙倒众人推把虚伪和聪明砸在了墙角下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二):简单说说读后感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三):史料真伪的辩驳,于无声处听惊雷。
《制造汉武帝》辛德勇
阅此书,还要多谢几位同学的推荐,加之今年有《秦汉史》一课,因此不免怀着功利之心。
之前久闻辛德勇教授大名,此书切入点虽小,但范围广博。以轮台之诏切入,史料广泛,指出史学界所公认“刘彻彻底转变其治国方针的纲领性文件”仅仅只是军事上策略的调整,而《汉武故事》中武帝与戾太子的故事系作者王俭自己的政治意向,却又阴差阳错,为司马光用于《资政通鉴》。司马光,王俭为何要重构汉武帝与戾太子的故事,原因各自不同的时代与政治背景。
司马君实先生大作《资治通鉴》,被朱熹评价“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蒙文通评“(司马光)毁斥用兵之类,盖亦以激于熙宁间事”。因此,辛德勇先生指出“王安石兵法所主张之富国强兵政策,与汉武帝之敛财于民、用兵于外,正相类似,而这却是一贯主张“以拊循百姓为先,以征伐四夷为后”的司马光所极力反对的”。
而王俭的背景则更加复杂,在宋文帝刘义隆与太子刘劭的宫廷斗争中,其父母也受牵累,因此“借神仙故事来曲折地表现他对这场宫廷斗争的看法”。
正如封面所言,“本书是一个案式的史学研究,提示研究者和普通读书史料的正确性是历史著作立论的基础。”此书大兴考据之功,简单史料,作者却能准确找到端倪,值得历史研究者前去学习。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四):。
论证得很好啊。 而且提到相反的论点时好礼貌委婉啊,如果是我可能做不到这一点。感觉依作者的脾气好像已经很克制了,有种按捺不住的感觉哈哈,讽刺的心蠢蠢欲动,很多地方虽然委婉但因此也像“阴阳怪气”的“内涵”(褒义),感觉蛮有趣的。 正如他所说,对《汉武故事》的创作缘由、原型的探讨其实是文学范畴了,是有很大相对性的。但总体觉得他的猜想还是合理的。 然而主要是附录里的对巫蛊之事的述说、论证过程,越写到后面,也是观点为先,按照预设的观点来解读史料,颇生出牵强附会的味道了。个人认为史学考证更好是那种从证据出发来推理,而不是预先认定一个观点、然后费心搜罗史料、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来力争它是对的。 的确也如作者所言,以历史褒贬时政、劝谏长上,还算无可厚非。如果官方改本朝史,则是更令我痛恨的,因也正由此,历史才会被说成是任人装扮。在我,希望史学是纯粹的,不管是记史还是史学研究,都以真为本,历史最大就是如实记录,探求真相,还原本来面目,求真而已。包括作者在附录讲演里讽刺了一把的新闻学,个人认为本质也在乎此,所以才说这是新闻沦丧的时代了。真善美,真善美,先是真,再是善,再是美。 我自然认同史学研究是一门要讲逻辑,讲求实证,用实实在在可靠可信的证据说话的学科。但说历史学是科学,一贯觉得这太看得起历史学,把史学一厢情愿地抬得太高的。不可能的。基本都是,如作者所说,“信不信由你”,很多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史学研究论文,即使是奉为史学家的那些人物,也太多臆测之词、想当然之言了,更别说寻常论文,让人感觉好像史学研究不掺入一点猜的想象的成分就根本进行不下去。它颇有很多“公认”(很讨厌史学研究里这个词)的标准,然就连这些标准、这些前提都不一定可行。当然即使以上,并不是认为史学研究不能有对错之类的判断,这里面还是有区分的,合乎逻辑和不合逻辑、客观和主观之间、甚至细节到哪里客观哪里偏主观都还是能做出判断的,正如作者所言,史学研究是一个可以重复、可以同行评审的过程,“历史学中一个研究结论,同样是可以依据研究者的路径重复实现的”。考证的高下之分依然是能够辨明的。考证,一言以括,应该是个精密活,要求精密、精审。很难很难,需要细 ,需要胜其烦,需要广博,需要条理、有序、逻辑,需要苛刻律己、把想当然、钻捷径的思路剔除尽净的理性思维,需要超越本人时代的独立性,而非太自然地以今人推古人或以己度人、以人度人,也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历史文本本身(甚至权威史料)都可能成为遮盖真相的迷雾。即作者所说的乾嘉学派以来史学研究传统。这种传统是值得传承的。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五):卫太子施行巫蛊了吗?
按照辛德勇老师的说法,《汉书》从未提到过江充陷害卫太子一事,而石德和太子的惶恐表现也可证明其确实施行了巫蛊,且太子并没有打算亲自面见武帝证明自己的清白,更说明他确实施行了巫蛊,因此心虚。
仔细检视,辛德勇老师的这几个核心看法,都可有不同的解释,足以对其论文的观点产生冲击。
其一,《汉书·戾太子传》明言:“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可知江充与卫太子及其拥蹙早有嫌隙,担心武帝驾崩,卫太子即位后会对其不利,正好赶上武帝穷治巫蛊事,因此江充借这一机会陷害政敌,带有自保的性质,《汉书》字里行间早已将导火索指向江充,如何能说没有证据证明其陷害卫太子呢?江充陷害卫太子的性质,与赵高矫诏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打击某人,未必是因为支持另一人,只是权衡利弊下的选择而已。
其二,辛德勇老师认为石德听说太子宫内挖出巫蛊一事后第一反应不是问太子是否确有其事,而是“惧为师傅并诛”,所以石德可能也知道太子施行巫蛊的事情。辛老师这一说法其实存在很多破绽,在太子宫挖掘出巫蛊道具前,丞相公孙贺父子,阳石公主乃至皇后弟弟的儿子卫伉都已经因为巫蛊之事而被诛杀,武帝统治下本就人心惶惶,第一时间众人想到的自然是很可能因为这件事被杀,更何况石德为太子少傅,无论巫蛊之事是否为真,他都有不可推卸的失察之责,是很有可能作为最终担责的替死鬼的,如何能不首先为自己的性命着想?
其三,辛文认为石德对太子说“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邪?无以自明。”是在暗示卫太子将此事指向江充。其实实际情况就是江充在太子宫确实掘出了巫蛊,众目睽睽,太子确实并无绝对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无以自明”一句,如果按照辛文的说法,该是对江充讲才对,这不合史实。
其四,辛老师认为如果卫太子是冤枉的,可以轻易见到汉武帝说明被陷害的实情,而他却直接造反,更说明施行巫蛊确有其事。其实政治上的事情绝对不能这么简单地思考,彼时“上疾,辟暑甘泉宫”,且因为年事已高,久在养病,太子本人很久没有见到武帝了,羽翼也被武帝剪除了不少,可以说是不再受到信任。而武帝晚年尤其宠爱钩弋夫人之子,甚至以“尧母门”暗示偏向,37岁的卫太子怎么不心生畏惧?他一定担心自己的地位,一定担心被取而代之,而且这确实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当他听说在自己的宫里发掘出巫蛊时,不管是否属实,他都会认为这是武帝开始废长立幼行动的开端,再联想到扶苏之事,他自然会觉得造反是最好的选择。
巫蛊案我觉得回归到事件本身,就是汉武帝晚年因为有了更多儿子,在储君问题上他存在一个徘徊不定阶段,晚年又多疑,对巫蛊又敏感,又确实有人干了,他就授意江充去看看太子有没有干,其实是一种政治考察,而江对武帝这个想法有体察,趁机兴风作浪。
至于太子是不是真的施了巫蛊并不重要,这一问题并不能得到实证,即便江充挖到的巫蛊不是卫太子埋下的,也不能证明卫太子没有在其他地方埋。但三个对武帝忠心耿耿的臣子去掘地三尺调查太子,太子必然认为自己有很大被废的可能,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听从石德建议,先下手为强,终致起兵造反而败亡。
武帝自身身体和精神状态存在不稳定,导致其在储君问题上发生犹豫,赋予了野心家们施行阴谋的空间,这就是巫蛊之事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