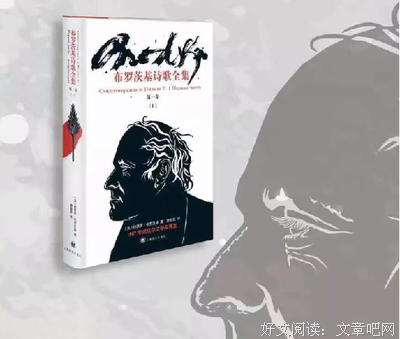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 上)》是一本由[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48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 上)》读后感(一):耐心点读。不要什么都归咎于翻译。
刚看完前面的《佩修斯之盾》,语言很干净,没杂质。这不是小问题。像某诗丛出的某退休官员译的耶麦的书(《春花的葬礼》),那个语言,陆离斑驳的,像个陈年臭水沟发了酵一样,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忽而村言、忽而俚语、忽而书面气十足的书面语,其中的较好的诗句也像是从臭水里捞出的白石头一样,只令人恶心。 布罗茨基的诗本不易读好,许多诗人都说不易读进去,所以还是耐心点读吧。不要归咎于翻译。当然,书里也有些常识性的争议点,比如叶芝译作耶茨,我看了半天才想通了。这样的点在《佩修斯之盾》里有四、五处吧。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 上)》读后感(二):翻译与校对
布罗茨基的诗极难翻译,所以出版前一直也不敢抱太大希望。五一期间买了书,现在还在读《佩尔修斯之盾》,娄老师对某些译名的处理着实令我吃惊,编辑也不够严谨啊。
目前才读到65页,试举几例:
1.经作者A.苏梅尔金认可的译本,应该是经作者认可的A.苏梅尔金的译本
2.LESS THAN ONE《小于一》译成了《小于本人》
3.他的恋人玛莉亚·韦切尔男爵小姐(???)
4.美杜莎译成了墨杜萨
5.在50年代下半叶和0年代初(不够6啊)
6.Moby Dick《白鲸》译成了《莫比·狄克》
7.帕斯捷尔纳克译成了帕斯特纳克
8.infinite漏成了infnite
9.《穿裤子的云》译成了《裤子里的云》
10.Architekten误植为Akhitkten
11.叶芝译成了耶茨
12.winter漏打成winte
(至于T.S艾略特变成了T.C艾略特,据编辑说是尊重原著的处理。)
然后随手翻了一下注释——
Watermark漏打作Watermak,New York错成了Ner York
好了,先这样吧。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 上)》读后感(三):以名为名
如果我忘记了你的名字,那是我已经了解了你的内心。
就如同从太宰治的书中开始日本作品的阅读,黑塞的作品让我发觉欧美作品如何阅读,这本书也给了我一种别样的领悟。
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象,我们必须要落在那样的文化环境里(冰岛的《萨迦》我实在是啃不动了),才能理解那些意象背后我们早已了解的共同的情感。
这本书的诗歌反而不是主角,对诗人生平的描写以及书最后的注释,令我受益匪浅。关于他的"哀诗",让我能够联系日本"物哀"的思想。关于《圣经》《希腊神话》《神曲》,这是许多诗人的词典,这不光是一个名字,而是如同《圣经》中的名字那样,每个名字代表的含义才是重点。
到了这里,我的领悟才呈现出了色彩,这世间所说的"返璞归真",纪德所说的"抛弃书本",简单与繁杂的比较,本质上来说,便是抽丝剥茧之后,人类共同认知下的事物。就像"死亡"不同语境下的名称,而它们都指向了死亡这个基本概念。
不被表象所干扰,拨开迷雾,站在无垢的阳光下。
注释里所有诗歌的意象,化用他人作品的章节,将人类情感延续并创造,以传递悠久的讯息,用来积累,并努力回答"我是谁"这样的问题。
之前阅读波兰作家的作品,再回到俄国作家的作品,有相似,有不同。
战争(国与国、人与人)源自少数人的欲望,源自少数人的恐惧。
兴亡皆苦。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 上)》读后感(四):短章与叙事的布罗茨基
根据某种不成文的说法,在俄罗斯诗人中,布罗茨基是最后一座高峰。是否果真如此,还需专家学者进行论证,但在这里引出这句话表明,不可否认布罗茨基具有无远弗届的影响力,至少在俄罗斯和英美世界如此。最近几年,随着《小于一》《悲伤与理智》《水印》等作中文译本的问世,布罗茨基在中国也收获了一大批忠实读者。这位俄裔美国犹太作家身上,究竟存在怎样无法抵挡的魅力,使东、西方的读者都为之?
布罗茨基以散文作家的身份闻名遐迩,当然,多数读者都清楚,本色当行的他终究是诗人,即便他的诗歌并不那么易读,即便他的诗歌竭力排斥通俗,让诗歌继续保持为一种精英事业,需要持之以恒的学习和琢磨。尽管如此,但晦涩的布罗茨基并非一日练就,他也在逐渐寻找自己的风格,因此不难看到部分诗歌显得平易。若套用维特根斯坦“用法即意义”的命题,我们可以说,布罗茨基在寻找建构起布罗茨基的语言和规则。
给布罗茨基的诗歌做注的研究者和评论家,往往会抓耳挠腮,因为布罗茨基的诗歌阅读极为丰富庞杂,从本土的普希金、莱蒙托夫、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到英国的艾略特、奥登,以及美国的罗伯特·弗罗斯特,更不用提他们共享的西方古典资源,尽管它们最终造就的是世界性的诗人布罗茨基,而不只是表现俄国或美国的某位诗人。
虽然19世纪末以降的诗歌往往以抒情诗为主,侧重诗人对自身的关注、发掘,以及想象,但是,在布罗茨基那里,叙事诗占据着不容忽视的相当的比例,如源自《圣经》故事的诗歌《以撒和亚伯拉罕》,源自史诗《埃涅阿斯纪》的《蒂朵和埃涅阿斯》,以及源自古希腊神话的《俄耳甫斯和阿尔忒弥斯》。对布罗茨基那里,这种有意为之的互文关系的营造,并非只为了增加阅读难度,相反,它们往往能道出现实无法或(出于禁忌)不能道出的政治意涵。
这并不表示布罗茨基完全将抒情逐出了自己的文学小花园。相反,抒情同样在其文学生涯中占据着突出位置,特别是他与诗歌缪斯阿赫玛托娃之间的感情纠葛(主要是参见《致A. A. 阿赫玛托娃》,其他诗歌中包含对阿赫玛托娃诗句的化用),他与文学同道的友谊,以及他与俄罗斯母亲的关系(特别是其文学传统)。在那些诗歌中,布罗茨基展现了自己私密的情感世界,普通读者从中亦能收获自己的感动。
因此,试图给布罗茨基贴上某种标签,比如存在主义诗人、意象派诗人,无疑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他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从《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上)》中就可明白瞧见。事实上,布罗茨基一直在探索语言、存在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以自己的诗歌创作为媒介,铭刻下自己对语言作为存在之基的远见卓识,尽管他对语言的重置或取用往往需要穷尽人的想象力。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 上)》读后感(五):诗人与人类之问
1964年,布罗茨基在捷尔任斯基区的法庭上接受审判,罪名是不劳而获,几近于莫须有。记者维格多罗娃在被法庭撵走前写的庭审记录震撼了西方的知识界,其中有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问讯:
“女法官:总之,您有什么特长?
布罗茨基:诗人,诗歌翻译家。
法官:谁承认您是诗人?把您列为诗人?
布罗茨基:没有谁。(没有挑衅意味。)是谁把我列为人类的呢?”
对于这次审判,布罗茨基后来在谈话中说到,除了辩护证人的发言,“其他的都是动物园。”这种人与动物的对比也体现在他那一年稍早时期的诗《穿着棉袄的园丁像一只鸫鸟……》中,写这首诗的时候诗人正遭到公民证登记科的骚扰:
“在严冬的树上,我们
唧唧喳喳,而不是及时歌唱,
我们是不是太落后了,
落后于‘如今落后于我们’的生灵?
生存的短暂再加上
家庭和忘情于
歌声,我以为,
我们就能认清自己的处境。”
逮捕、监狱、法庭和精神病院这一系列的荒诞构成了布罗茨基一生中“最难过的时期”,那是一个人类本身的意义不断磨损直至虚无的时期,官僚主义驱动的国家机器醉心于无中生有,语言和文字无限趋近于无意义,没有诗人内心所向往的诗的音乐,谈话的片段只有单调的“二月永远跟在一月后面。/然后就是——三月”,就连鸟儿的啼鸣也仿佛只是粗糙的“刀刃和刀刃摩擦的声音”。
尽管精神病院的折磨几乎将他逼疯,布罗茨基对这段经历表现出的更多是坦然而非愤慨,既因为他意识到这些痛苦只是那许许多多的受难者所遭受苦难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也因为在诗人这里,受难本身成为了人类生存的条件:“只有生命——任人摆布”。宽容地拥抱苦难使诗人得以投身于自然和艺术,随后的流放生活成为了他“生命中最好的时期之一”,“不曾有比这更坏的,但似乎也不曾有更好的。”流放地国营农场的雇农工作并未使他气馁,相反,他“从自己的生活中看到了最抽象的东西”,某些关于世界的生命的真理。
“无疑,艺术的感染力就
在于真实,而不是吹嘘,
因为艺术的基本规律
是细节的独立性,这一点无可争辩。”
1968年的这首《烛台》展现了诗人对诗歌艺术的思考,清晰,明确,隐秘的激情在诗行里产生混响。日常生活的平凡细节与充满荒诞的自然现象之间的碰撞,让他看到了艺术真理的纯粹,也使他得以清晰地阐述艺术的力量,“艺术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尝试,相反,它是种赋予现实以生气的尝试。”
或许,这一话语恰好回答了布罗茨基审判中关于人类的问题。存在就是列席。尽管现实残酷,人类无需困扰于自身定义,意义由人类创作并赋予自身,写作本身就存在着意义。于是,我们得以重新理解诗人对生存之短暂的思考,经历过苦难的诗人在《雅尔塔的冬日黄昏》最后对人类的真实处境发声感慨,不是满怀悲悯的抱怨,不是对未来虚无的恐惧,而是对世间美好的感恩:
“停下,这个瞬间!与其说
你美好,不如说你不可重复。”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 上)》读后感(六):你不知道,人们已经宽恕你了
首先请允许我在开端再次真诚的给译者娄自良先生道歉,为自己在刚一翻开书本尚未完全了解内情的情况下就出语轻蔑译者而深感愧疚,我为自己的浅薄无知浮躁轻狂以及偏见而抱歉。
因个人习惯先阅读了诗歌部分,后翻阅了传记,最后才读了最前面的译者前言,娄先生的前言算是较为凝练简短的,有助于了解这套书的整个规划,毕竟目前只出版了第一卷的上部,根据娄先生个人的规划来看,这套书会是一个较为巨大的工程,布罗茨基定居美国后出版了六部俄语诗集,这本2018年出版的书才只译了第一部而已,又因这本书的评价较多对译者不太友好,略担心后续计划会搁浅或延迟,虽然娄先生翻译的很多首诗歌的确不尽如人意一言难尽,但不该因此全盘否定娄先生对布罗茨基诗歌在国内引入和流通的贡献。毕竟布罗茨基自己也多次强调自己是一个诗人,而国内除了他的几本散文,在这本出版前并无什么诗歌。
布罗茨基一生坎坷,历经了政治压迫、写作自由的限制、精神病患的折磨、爱情的曲折、审判流放驱逐移居美国,名校教授文学奖项的各种囊获,以及身体病痛的折磨,但他并未被命运击败,这些经历反而丰富了他的诗歌。就如关于自己战后遗民的身份布罗茨基认为:“如果真有人从战争中获益,那就是我们——战争之子。我们除了生存下来之外,还获得了浪漫主义想象的丰富素材。”而与女友玛丽娜痛苦的恋情也给了他一部抒情组诗《幸福的冬季之歌》,看似自嘲的名字却满是当初恋情的回忆。
正如他拒绝承认,审判和流放是自己人生中的特殊的、命运攸关的事件,被驱逐出境、移居美国,他认为不过是“空间的延续”。人们对他生平这些插曲的过度关注引起了他的抗议:他希望被看作诗人,而不是制度的牺牲品。关于身份的自我认同,他在成年时期形成了一个简明的公式,并一再使用:“我是犹太人、俄罗斯诗人和美国公民”。
而略显讽刺的是,人们对于布罗茨基的关注重点似乎一直都不是他一再强调的诗人身份,除了那些他人生的插曲,他在西方确立的作家声誉以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才华肯定却是因他移居美国后发表的英文散文随笔,并不是因为他的诗歌,布罗茨基被誉为“最伟大的随笔大师之一”,这于他自居的诗人身份大概有些悲哀的意味吧。
个人觉得布罗茨基并不是天才诗人中的一类,他的诗歌才华多为后天勤奋学习和模仿钻研所得。布罗茨基幼年只上了几年学,后面几乎全靠自学,读夜校并去大学旁听,靠自学掌握了英语和波兰语,后来可以凭借词典阅读拉丁文、意大利文和法文,在生前的最后几年又开始学习中文。伟大的作家都离不开不知疲倦的自我学习,一如博尔赫斯一生对多种语言的学习及他的博学,他们都是令人敬佩的。
而造就布罗茨基诗歌才华的除了他对语言和诗歌的终身学习,不可忽视的还有他的幸运。在俄罗斯,在文学之路的开端,布罗茨基结识了白银时代最后一位伟大诗人阿赫玛托娃,在人生巨变的前夕,在西方的门口,受到了最伟大的英美诗人威斯坦·奥登的欢迎。(PS:俄国另一位伟大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是布罗茨基毕生仰慕的诗人哦)
比布罗茨基年长近半百的阿赫玛托娃可以说是他人生中的良师益友,虽然他们在诗歌很多方面截然相反,但阿赫玛托娃对布罗茨基的人生道德影响深远,她的赠言伴随了布罗茨基的一生。
【尽管如此,这时布罗茨基已形成个人的风格,与阿赫玛托娃作品的基本取向——暗示性、言而不尽的诗风、语言倾向于质朴的诗意不仅不相似,而且在很多方面是截然相反的。布罗茨基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后来他解释道:“我们去她那里不是要得到称赞,我们去她那里,因为她会使我们的心情活跃起来,因为有她在座,你仿佛会放弃自己,放弃自己在内心,在精神上——我不知道这该怎么说了——所达到的水平,放弃你与现实交谈的‘语言’,而选择她所使用的‘语言’。当然喽,我们谈论文学,当然喽,我们散布流言蜚语,当然喽,我们跑去买来伏特加、听莫扎特的音乐并嘲笑政府。可是回顾过去,我的所见所闻不是这些;从我的意识里浮现了出自《野蔷薇》的一个诗行:‘你不知道,人们已经宽恕你了……’它,这句话,与其说冲破不如说甩开了语境,因为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因为宽恕者永远比冒犯本身和冒犯者更伟大。因为对一个人说的话,其实是对全世界说的。它是——灵魂对生活的回应。我们向她学习的大概正是这一点,而不是作诗技巧。”】(出自传记)
在布罗茨基的伦理学和诗学中,与罪恶的主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宽恕的主题。阿赫玛托娃的话:“你不知道,人们已经宽恕你了……”——他带在身边走过一生,作为护身符。
而布罗茨基与奥登并不算熟识,因奥登因语言的关系对布罗茨基的诗歌并不了解,只能算布罗茨基单向的对奥登崇拜,并终其一生都完全自觉地以奥登作为典范来审查自己的诗作。
而关于诗歌,布罗茨基认为诗作不是源于异想天开的幻想,而是源于现实生活。正如他在诗中所写:
“无疑,艺术的感染力就
在于真实,而不是吹嘘,
因为艺术的基本规律
是细节的独立性,这一点无可争辩。”
他注重诗的基本情调、构思、结构、细节的独立性、抒情性、节奏、格律、韵脚等等,认为在心理上,诗人应该只遵循自己的直觉,不论直觉把你引向何方,要绝对独立于准则、规范,不必顾忌权威和假定的读者。也认为情感的感染力在于言不尽意,在于意味深长的潜台词。
布罗茨基诗学的哲学原理是:受难被看作人类生存的条件,世界就是它本身的样子。大概这也是阿赫玛托娃那句“你不知道,人们已经宽恕你了……”伴随他一生的原因吧
正如奥登所说:“语言需要诗人,使语言始终是鲜活的语言。”而时代和人类也始终都需要诗歌,使生活始终是鲜活的生活。(这句是“使生活始终是鲜活的生活”还是“使生命始终是鲜活的生命”好一些?)
写到这里差不多到了该结束的时刻,在尾声我又想起了布罗茨基在第一部诗集《在旷野扎营》开篇前的引用:
Men must endure
Their going hence, even as their coming
hither;
Ripeness is all
——King Lear, Act V, Scene 2
(PS:0、这只是关于传记部分的感想,诗歌还没整理。1、忘了说传记名称中的佩尔修斯之盾是一面镜子,化用了布罗茨基诗歌中的句子。2、传记作者是美国人,写俄国历史和文学时角度会不同,自行体会,但作者还是较为客观的,调查查阅了很多资料。3、布罗茨基的长诗和排比诗句很厉害,他是我女神辛波斯卡推崇的诗人(弱弱说句,辛波斯卡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因为诗歌,而布罗茨基是因为散文)书中的长诗《以撒和亚伯拉罕》写的超棒。4、最后,布罗茨基好多诗都是模仿别人写的,但女神辛波斯卡也曾模仿过他。)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 上)》读后感(七):布罗茨基与“诗中的布罗茨基”
人们阅读文学作品可能总会有种倾向,习惯把作品中的主角与作者建立起某种联系,或者干脆认为那就是作者。这种倾向很自然,毕竟作品中的文字都出自作者的内心,不管它们如何奇幻,如何“客观”,总有一刻闪现出作者的影子。
诗歌更容易引起这种倾向,因为其中的文字自带诗人独语的效应,让读者想象在听诗人说话,或与诗人对话;而有些诗人独特的人生经历则会为他们的诗歌增添传奇色彩,让人更自然地希望在诗歌中寻找诗人的影子。
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特别是他在出境前创作的诗,很容易就使读者燃起在诗中寻找其身影的兴趣。约瑟夫·布罗茨基是美籍俄裔诗人、散文家。他出生于一九四〇年的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凭借天赋在诗坛年少成名,到西方生活后,更荣获一九八一年的“天才奖”、一九八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等;在享誉诗坛的另一面则是他曲折的人生——入狱,被流放和长期监视,后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驱逐出境。
布罗茨基十五岁退学,做过司炉工、医院陈尸房助手、水手、勘探工人等多种工作,他这首作于一九五七年的诗带着“矿业学院学生”的诗风:
“闯过一切障碍。走遍一切沼泽。
翻山越岭。
去吧。
工作就是这样。”
直白青涩,似乎还带着喜悦与兴奋。此时的他带着“探索”的雄心与激动行走于森林与大草原,享受着原始的劳动愉悦感。而即便是在数年后因“不劳而获”的罪名被流放在偏远地区劳动时,被批判为社会的“寄生虫”的诗人仍然表示出他精神上的愉快,他说:“在那里我黎明起身,清晨六时左右跟随执勤人员去管委会的时候,我明白,此时在整个所谓的俄罗斯大地上正在发生同样的事情:人民都在上工。因而我有权觉得自己是属于人民的。这个感觉太棒了!”
布罗茨基身上似乎总带着坦然、真诚和希望,这些因子让打压者成为笑话,也让诗人蛰伏不死。在一九六四年获罪后,他在流放期间劳动于指定的农场,又成为了苏联政府定义中的劳动者,不过此时作为农场杂工的他已无当年的豪迈:
“子粒在耙子下面扎煞,
发动机的轰鸣响彻四周。
飞行员在乌云间留下自己飞舞的笔迹。
面向田野,背朝震动,
我自己是播种机的点缀,
满身粉尘,好像莫扎特。”
在诗中,我们读到的是麻木的、如草芥般的农工形象,但他心中似乎还残存着理想,诗句中提到的“飞行员”和“莫扎特”正是布罗茨基长期兴趣的化身——航空与音乐,而他的第一次入狱也恰与这两种兴趣有关。
时间拨回到一九六二年,布罗茨基结识了音乐同好、前飞行员沙赫马托夫,却也因此以类似“莫须有”的罪名入狱——对航空有浓厚兴趣的布罗茨基因与其讨论过“劫机”飞到其他国家而被捕。少年诗星布罗茨基从享受着众人簇拥的文化世界堕入了黑暗冷酷的现实牢笼。这位仅有二十二岁的诗人震惊、彷徨、失望,至少在他写下诗句的那刻有如此感受:
“……
而我又若有所思,
步履艰难地从审判走向审判,沿着
通往遥远国度的走廊,那里不再有
一月、二月、三月。”
从这首作于当时的《十四行诗》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人联想到他首次入狱的情形:他“步履艰难”,在反复审判中疲倦不堪,长长的走廊那头仿佛是另一世界……
越是遭受磨难、人生曲折的诗人,写下的诗句越让人有将其与诗中形象重合的愿望,似乎是悲伤与痛苦在纸上留下的墨迹更浓一些,因而也更易让人注意到它们的轮廓。布罗茨基在写于一九六二年的一首诗中似乎“作弄”了一下这种“先入为主”的倾向:
“ 我搂着双肩,看了看
出现在我背后的情况,
看到的是,拉出来的一把椅子
与照亮墙壁融成一片。
灯泡里的炽热度升高,
不利于磨损的家具,
因而墙角的沙发闪烁着
深棕色的皮革,似乎是黄的。
椅子无人坐,时而微微闪现着木板,
小火炉变得更暗了,满是灰尘的炉框内
画面凝固了,唯有一个餐柜,
那是我觉得是有灵性的。
不过一只螟蛾在室内盘旋,
它把我的视线从静止移开。
假设有一个幽灵曾在这里居住,
那么他已经遗弃了这个家。遗弃了。”
当我们跟随我们以为的“诗人”在房间里默默环视时,真正的诗人,那个幽灵却离开了。
以上当然是猜测,但“局外人”与文学创作者间的“附会与反附会”的确存在。布罗茨基改籍美国后,总有记者在采访时提到他人生在一九七二年的“分割”,以及询问移居西方对他的影响,他总会拒绝承认这种人为的切割,根据列夫·洛谢夫在《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的序言里的说法,布罗茨基会“耐心地、时而气愤地回答说,这不过是‘空间的延续’”。同样,也有人将布罗茨基的流放生涯引导和想象为“古拉格”似的苦难垂死生活,但其实那却可能是他精神上最愉悦的时光。
作为读者,当然想竭力避免附会与误解,所以,要理解诗人的文字,不仅要尽可能多和全地咀嚼诗人的文字,还要结合诗人的谈话回忆、生平传记、文学思想研究等资料来琢磨。而在这些之后,适当地作联想和想象也有必要,毕竟,像布罗茨基这样的“二十世纪俄罗斯唯一的大诗人”(洛谢夫语)也会有不愿触及的空间。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 上)》读后感(八):《布罗茨基诗歌全集(一·上)》:我的灵魂将以两个面孔出现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593.html
在这里,我想到的 不是诗歌,而是:罪孽。我写诗 越来越少了。 ——《寄语诗歌》写诗越来越少,是因为那条路足够漫长,是因为可能被岁月淹没——连同诗人,在“罪孽”的世界里,一种诗意的心被遗忘,悲痛会像死亡一样降临,而其实真正痛苦的事,不是死亡,而是未死而死,而是还走在那条名为诗歌的路上却没有了言语。布罗茨基以“寄语”的方式回望诗歌之路,不是寄语诗歌,而是寄语不忘记诗歌的人,是从诗歌里获得爱的人,“我相信,人们会因为这一切而爱/你们,胜于爱现在的/你们的创造者。”诗人作为创造者,在诗歌之后被记住,在返回本体的体验中,或者真的不再有被岁月淹没的悲痛,不再经受漫长道路的罪孽。
可是,真的可以在诗人这个创造者之外阅读诗歌?“我写诗越来越少了”似乎又将一切置于矛盾之中:创造者隐匿在诗歌之外,谁来书写被阅读之后的下文?布罗茨基木刻的肖像,是作为创造者而存在的标记,但是在这《第一卷·上》的孤立版本中,布罗茨基所说的“我不为你们担心”还是成为了某种担心:是全集,却分割成第一卷和第二卷,是整体的卷集,却又分离为上册和从册——在第一卷上已经出版之后,其实远远看不到后续的下册以及第二卷的上册和下册,一种被悬置的感觉,总是无法抵达总体的完满性意义——它只是在封底被标注在那里。没有总体的完满性意义,或者只是阅读者追求整体文本的一种主观感受,但其实,这提早抛却出来的第一卷上册更像是在漫长的路程中自我迷失的拙劣行为艺术。
LESS THAN ONE,布罗茨基的《小于一》被译成了《小于本人》;马雅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被翻译成《裤子里的云》;叶芝变成了耶茨;有时是帕斯捷尔纳克,有时却是帕斯特纳克……如果这一切还可以用翻译的可能性来解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50年代下半叶和0年代初”这样低劣的错误?如果这也只是校对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娄自良的前言完全是摘抄了洛谢夫为布罗茨基所做的传记《佩尔修斯之盾》?7万余字的《佩尔修斯之盾》作为理解布罗茨基的背景材料,只是一种补充,但是在这里完全变成了重要的文本,而译者娄自良根本没有自己花心思去撰写这一篇“前言”,这里摘录一段,那里复制一段,拼合而成了布罗茨基诗歌的介绍——再加上文后几十页的注释,使得布罗茨基的诗歌在第一卷、上册中完全成为了“夹缝中”的存在。
“于是将会出现多么混乱的局面啊。因为最可怕的莫过于死后的注释,无法想象。”布罗茨基曾经这样对“注释”存有不满,而他也引用了卡夫卡的一句话:“注释者肯定地说,对现象的正确理解和不正确的理解是互不排斥的……作品本身是不变的,因而对它的注解乃是绝望的表现。”布罗茨基的“无法想象”和卡夫卡的“绝望的表现”,都是一种“去注释化”的努力,而在诗人作为创造者极力还原诗歌本体意义、让阅读者自己扩展诗歌阐释空间的时候,7万字的传记、几十页的注释,以及拼凑而成的前言、带有硬伤的翻译,却将这一切带入到混乱的境地,而被悬置在整体之外的第一卷和上册,又让“全集”变成了分裂的存在,仿佛真的听到了布罗茨基的预言:“要是它/被岁月淹没,首先感到悲痛的是我。”
出版意义上的混乱和割裂,如此真切地传递过来,也许真的需要一个在完全阅读意义上的布罗茨基,“我在自己的生活、行为中的出发点向来是——会有什么结果,那就来什么结果吧。”一种自然而然的呈现,是对诗歌以及诗人最起码的尊重,于是,封存了那些注释,于是保留了中间地带,于是在让创造者回归的状态下读一首首诗——即使布罗茨基在诗歌的世界里创造了割裂,也完全是一种对于生存、信仰、语言的探寻,也都是自我心路历程的审视和反思,那一句引自《李尔王》的题辞已经说出了布罗茨基在曲折人生道路上的终极向往:“人要像忍受出世一样忍受离世。全部问题在于成熟。”
出世和离世构成了一种矛盾,或者说这两种人生状态构成了两个端点,一个是生,一个是死,生是起点,死是终点,而用生和死作为起点和终点构筑起来的人生无非是肉身意义的,甚至只是一种表象,在这个表象后面“成熟”支撑起了全部。什么是成熟?如何才能成熟?要走上成熟,必然是要审视死亡,“死神——这是和我们同在的一切”,因为它们“什么也看不见”,布罗茨基说,死神是一切机器,是我们的力气,是我们的血管,一个人被斧子劈死了,鲜血流了几个小时,另一个由于心脏破裂,当场丧命——无论是鲜血和心脏,都是在肉身意义上抵达了死亡,而且布罗茨基假设“凶杀发生在结婚的日子”,那么“牛奶就会变成红色?”——当死亡代替充满爱的婚礼,当牛奶变成红色,它已经是一种毁灭让“什么也看不见”的恐怖存在。这样一种死亡,需要还原的是“事件性”意义:是两个人,“沿着不同斜坡走下丘陵/沿着不同的斜坡走下去,他们之间的空间在扩大。”而正是因为两个人的空间在扩大,所以之后每个人面前都出现了两个人,他们的“手里微微摆弄着铁器”,于是死亡发生了。
分开的两个人,两个人各自面前的两个人,这一种割裂制造了凶杀,“灌木丛猛然分开,/灌木丛突然分开。/灌木丛仿佛被惊醒,/而它们的梦境可怖。”凶杀而死亡的“事件性还原”之后,布罗茨基开始审视这“猛然分开”“突然分开”的夜晚,从斜坡走下丘陵,而丘陵“是我们的青春期”,是苦难,是爱,是呐喊、呼号,甚至是梦想,它永远在一种疾驰的状态中展开,“有人在丘陵上飞驰,披着月光,靠近天穹,/沿着结冰的草地,驰过黑色的灌木丛。森林渐渐临近。(《你将在黑暗中疾驰,沿着一望无际的寒冷的丘陵地带……》”披着月光疾驰,是在黑暗中被光亮照见,是奔向一个目的地,即使寒冷,也勇往直前,“那个人回来了,他曾在黑暗中沿着丘陵飞驰。/不,别以为生活就是——虚构故事的循环,/因为成百的丘陵——是惊人的母马的臀部,/骑着母马在夜间而有月光的时候驰过沉寂的周围地区,/快要睡着的时候,我们在梦境里急切地向南方飞驰而去。”疾驰而唤醒沉睡的人,疾驰而打开梦的境界,甚至疾驰而回家,是可以击败黑暗和“摇摆不定”的梦想,但是正是丘陵是一种苦难,丘陵是被驱逐以及我们“不了解”的爱,所以在丘陵变成青春期生活呈现的一个隐喻中,平原便在其对立面出现了,那就是死神,“死神——这不过是平原。”一望无际,而又不可逃避。
丘陵和平原构成了如被灌木丛猛然分开的两个人,但是这一种矛盾之构成并非仅仅是疾驰和死亡之间的对立,在丘陵本身存在的隐喻里,也是两个人:“就这样,他俩从来不待在一起,/穿过小树林和林间小径,穿过没有水的池塘,/不像车站哨兵那样骑马同行,/仿佛在他们之间没有成百的灌木丛!(《傍晚他冻僵在门口……》)”没有灌木丛,两个人似乎不再像从那个斜坡走向丘陵的两个人,“他们之间的空间在扩大”,而是“一男一女在夜色中并辔而行”,但是在夜色中他们本身成为了如幽灵一般的存在,他们只是回归自己,他们只是听见自己的名字,他们只是在自我世界中驰骋,一切的苦闷和安宁都沿着各自的方向,当然,“驰往他们能飞向天堂的地方”的美好也在各自的路上,所以布罗茨基将这种“他俩从来不待在一起”而“并辔而行”的状态看成是自己的两个灵魂,“我的灵魂将以两个面孔出现。”也正是这种灵魂意义上的双面性,使得疾驰在丘陵中的青春期变成了一种分裂状态。
一男一女在夜色中并辔而行,青春期里有爱,它是《蜜月片段》里“像鱼儿一样跳动着”的生命,“呈现出我们/两人生活的细节”;它是《预言》中自造的灯,大陆在那边,这里只有惊涛拍岸中的隔绝,甚至还想好了生下的孩子的名字,他们有着有皱纹的小脸蛋,他们不忘记俄文字母表,他们甚至在重回旧地后“越过堤坝”;它是对未来的希望,身影是门,门始终敞开,“我们就是穿过这些门扇,/走出暗道,奔向未来。(《六年后》)”;青春期里也有道路泥泞时的歌唱,“在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在投身大自然的半路上/歌唱。(《在道路泥泞的时期》)”即使寒冷,雪从棚顶下的缝隙落在杆朝上,也是一种温暖,“在黄昏的雾霭里/只有我们两个。/我的手指很暖和,/宛如七月的天气。(《黄昏》)”——这是一种美好,如“雅尔塔的冬日黄昏”一样,是可不重复的存在,是永恒的瞬间。
但是,这一种温暖,这一种美好,这一种对未来的期许,却是在无法逃离的对立面展开的,爱是两个人的细节,其实也是分化,在隔绝的海边,堤坝永远在,走向未来的门是现在的影子,而那冬天里的歌,在春天却切开了血管,“是呀,静脉里的血/太满了:刚一切开鲜血便潮涌而出。”1964年布罗茨基说这是《幸福的冬季之歌》,其实那时的他已经离开了“冰天雪地的乌斯季-纳尔瓦”,为的是躲避警方的迫害,而切开血管听到的幸福之歌,其实是走向一种决绝的死亡,正如阿赫玛托娃所说,“约瑟夫曾想割断自己的静脉”。冬天的歌里是,空气抽打着灌木丛,枝条在战栗,一种隔绝成为活着的主题,所以布罗茨基说:“学会与人群隔绝以后,/我想与自己隔绝。”
与自己隔绝,所以离开那片土地,所以逃离那种现实,所以成为漂泊者,“倘若我们不能有别于失败者,/上帝会剥夺一切奖赏,/避开欢腾的民众的视线,/也命令我们保持沉默。我们只好离开。(《前往斯基罗斯岛的路上》)”因为这里有审判之剑,因为这里将诗人带入“耻辱”中,因为“继承者和权力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所以船舶停航,所以大海结冰,所以云端的飞鸟都变成了乌鸦:
一只乌鸦(有成群的乌鸦, 不过傍晚它们都躲进了赤杨树林) 选中了电线杆的顶端, 另一只选中的是——雪白的绝缘子。 这么说吧,彼此是相反的 (正如勿忘草指令所要求的那样), 对电话的监督设立在 不想造反的荒野, 它们安置在大门前的台阶上方 高悬于灰白色栅栏之上, 针对被流放的歌手, 针对他的长发伴侣。一群乌鸦中的一只乌鸦,一只沉默的乌鸦,一只被流放的乌鸦,所以在布罗茨基诗歌中出现了39次的乌鸦就是诗人的写照,“这时,被活活埋葬/的我在暮色中徘徊于庄稼地。”徘徊而终于离别,当这样一种心情投影于自然界,对于布罗茨基来说,仿佛看不见了自己,“是的,这里好像真的没有我。”如被上帝砍掉了手,是听不见话语的人,是纷乱爬着的蚂蚁,“我步履艰难地从土堆走向土堆,/没有记忆,只有脚板/踏在石头上的什么声音。/俯向黑暗的溪水,/我惊恐地看着。(《献给奥古斯塔的新四行诗》”这样一种异化的存在,即使回来,也是一种流浪,“城市/对它的居民而言,/通常是从中央广场和塔楼/开始。/而对漂泊者是一—从市郊开始。(《前往斯基罗斯岛的路上》)”回来看见了工厂、半岛、乐园,回来“跑着穿过一千个拱门”,但那只不过是和“贫穷的青春年代”重逢,甚至自己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人,“谢天谢地,我留在地球上而没有祖国。”回来的青春,回来的祖国,都变成了一种虚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看见了真正的死亡,“我们四散奔走。只有死神在召集我们。”没有回忆的故土,没有爱的孤独,没有冬季的歌,一切都如平原一般是一望无际的存在,无遮无掩。
但是在布罗茨基那里,丘陵并没有在平原的存在中消失,或者说丘陵/平原的对立存在,恰好为布罗茨基在“两个面孔”下变成成熟的诗人创造了条件,就像那一匹马,“它是黑的,感觉不到有影子。/那么黑,不可能更黑了。”没有遮掩的死亡存在,却还在等待一个疾驰的人,“它是在我们当中为自己物色一位骑者。(《那天晚上我们看见……》)”马“不可能再黑了”,但是昏暗的苍穹比马腿亮些,不能融入夜色却可以在骑者的世界里创造一个驰骋的意象,而这个骑者便如语言中的动词。在布罗茨基看来,围绕着的是一些沉默的东西,是别人的脑袋的动词,是饥饿的东西,是赤裸的动词,是耳聋的东西,甚至是没有名次的动词,“全都住在地下室”,而天是一个隐喻,“浮动在我们上空!”所以要激活这些动词,要开始说话,言语,以及让诗人成为创造者。
没有真正动词的语言只是一具肉身,“以撒”这个词少了一个元音,便是“蜡烛”,就是“空有一张嘴”,就是仅有一具肉体,它是“一滴,一点,微不足道”——布罗茨基从词语本身切入,讲述了“以撒和亚伯拉罕”的故事。以撒作为一个词语出现,他“迟迟不答”,即使说出“马上”,也总是隐匿在那里,而亚伯拉罕“情况完全不同”,“丘陵、灌木丛、敌友聚集/成群,墓地、细细的树枝、教堂——/然后迫使它们诉诸于它——”他总是说着“我们快点走吧”,他总是在丘陵中行走。平原和丘陵,隐匿和行动,缺少元音和完整的语言,构成了以撒和亚伯拉罕的对立存在,但是在他们走向献祭的过程中,一场梦似乎在对立世界中建立了联系,字母在跳动,在说话,在开启一个更大更宽的世界,所以最后即使一只手是匕首一只手是亲骨肉的献祭,也在“上天也很高兴”中结束,“列车在无休止地飞快穿过数字8。”数字8,倒卧而成为无穷,或者就是苦难之后的救赎,就是牺牲之后的得道,就是肉身之后的信仰。
所以在死亡的“哀歌”里,布罗茨基看见了天启的光,死人已经睡了,生者已经睡了,地狱睡了,天堂睡了,上帝也睡了,“如果说可以与人同生,/那么谁能与我们共死呢?”在这个多恩的哀歌里,从卧室开始,房间、街区、伦敦以及整个孤岛和大海,都不只是世界,而是从外部对世界的观察,作为布道者,多恩其实让可见的天堂乃至所有的等级都变成了他所关注的苍穹,都是天使般的境界,所以在《献给约翰·多恩的大哀歌》里,布罗茨基也找到了自己的苍穹,“诗句入睡了,躺着。/所有的形象、所有的韵脚。强弱/难辨。恶习、忧伤、罪孽,/一样地沉寂,睡在自己的音节里。”睡而复活,睡而醒着,睡而为生者。
平原/丘陵、离开/回来、沉默的动词/行动的动词、以撒/亚伯拉罕、肉身/信仰、地狱/天堂,在布罗茨基的诗歌里,他们都是两个面孔,是两个路人,是两步之遥,但是在睡而醒着的诗歌里,二元对立的世界被破解了,诗人成为灵魂的造物主,种种的罪恶,种种的苦难,种种的放逐,在“对半平分死亡这个同义词”之后,在“亲爱的诗歌”里,成熟为一种真正自我创造的灵魂,“噢,我的上帝!/这湿润的空气——只是灵魂的/肉身,灵魂放弃了自己的使命,/而不是你的神的新创造!(《致A.A.阿赫玛托娃》”也是一种启示,在第一卷、上册的隔离中,在被语言制造的断裂中,在“无法想象”的注释中,宛如一种光,照亮那些强有力的动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