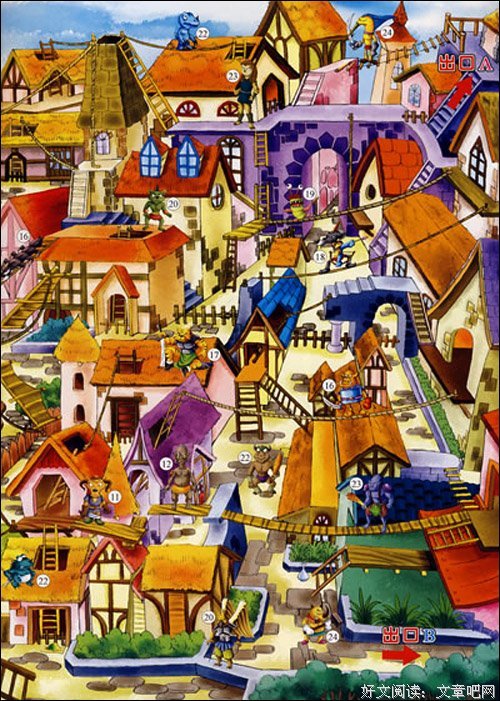
《鲤·我去二〇〇〇年》是一本由张悦然 主编著作,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6.00,页数:1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鲤·我去二〇〇〇年》精选点评:
●201912/04 读了前几篇还不错 到了访谈就看不下去了…阅读能力有限,真的从来都不喜欢班宇。
●90年代是永远明晃晃的太阳。班宇最好,是冬日暖阳下读也感觉冰冷刺骨的迷人。
●见到一半是朋友的杂志,感觉像午后闲逛,闯入了一个事先没有邀约的聚会
●读于北京初雪的夜晚,命题作文也很喜欢。后半小说倒是没意思
●郑执那篇确实还行
●差到想要求退钱
●也就班宇郑执,其他都是些什么玩意
●其中有一篇尤其差……
●龙荻的底色和郑执的凯旋门
●郑执还行,魏思孝还行,主题还行,一样一星。
《鲤·我去二〇〇〇年》读后感(一):关于90年代个体经验的回溯
大概是一个月前读完的这本书,果然读后感和随笔应该边读边记录,时隔一个月来看已经全然不记得当时的感受了。隐约地记得这本书读来有种初高中时候看新概念的感觉,不是说文风和新概念很像,而是对90年代的聚焦,对个人经验和少年时代的回溯。80年代对我来说有点距离,读过的小说也大多聚焦在小镇青年、工厂职工、下岗、农作等一系列带有一点粗粝感的内容,90年代则因为隔得太近而显得无法脱离出来。这本书是那些在90年代经历少年时代的人回顾自己的青年时代,对我而言却十分亲切。因为生在小乡村,于我而言的21世纪头十年就如同大部分人记忆里的90年代一般,充满了一些“过时”的元素。
家里贴的伟人头像(从十大将军到十大元帅),充满了乡村特色的挂式日历(还有猪饲料广告), 藤椅、黄历、晚霞报、《读者》《故事会》、夏天需要洒水降尘的小院子,如果不是读了这本书大概这些细枝末节就慢慢地消失于回忆中了吧。
因为实在记不清每一篇的具体内容,以及很久都没有看书了,感觉自己对所有文章除了努力去同感之外,难以发表任何评价。
不过看完之后也很想写一写自己的小镇生活。回忆一些“过时”的简单和快乐。
《鲤·我去二〇〇〇年》读后感(二):我去二〇二〇年
19年读的最后一本书。书里有笛安、毕赣、班宇老师郑执老师,还有龙狄老师和最最可爱的bo,反正都是些熟识的老朋友,所以非常愉快的在今天用一整个下午看完了。
在读的时候完全没有什么一年的收尾之书甚至last in this decade这种念头来偏执地替我进行选择,也根本没有想到说非要用一本书来给今年给这十年做个总结或代表的,毕竟上一个十年里我刚刚才从出生长到十岁,因此刚刚过去的这十年就是我读过最多书的十年,读到过最好的作品本来就都应该出现在其中了。
但是书本身还是很好的书,因为这期专题自身就带有一个交界的意义,况且2019好像对这个世界都有些糟糕,就比其他任何一个十年的末尾都带有1999那种千禧前夜的仪式感,二十年前朴树唱《我去2000》唱《New Boy》的时候审视新世纪的目光和年纪实际上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代人站在此刻看几小时后的视角和心境,就是在末世又憧憬的氛围中忍不住思考一些终极命题的。
最近至少在接触智能手机上过的很九十年代,可能这也能更容易和书里的记忆共情一点,最喜欢的还是bo的那句“没有想到我们已经身处未来”,对2020也适用,又好像朴树唱的“我要走了我去2000年”一样决绝。
《鲤·我去二〇〇〇年》读后感(三):掰扯掰扯石牢
石牢这个故事时不时要在我脑子里转一转,像块磨刀石。主要因为总有些地方弄不明白所以就老是在琢磨。 “我”来到石牢后低声说的词汇是语言,建设,暴力,语言,峡谷,道路,语言,斗争,忘却,语言,煤炭,原谅,妈妈,语言,妈妈,妈妈。 说实话这形式有点纳博。我倾向于这是一段为了让“我”可以轻松地活下去,必须逐步舍弃的关键词。
在我的推断里,第一个故事中在锅炉房发现的那女尸就是“我”的妈妈,由于文中有一处描写“我”使用弹簧刀是“用过几次,相当趁手,所以朋友在送女孩来锅炉房那一夜,先见到白骨再说一切已经安排妥当估计是倒叙,事情很可能是喝醉的女孩被轮奸后,在锅炉房上班的“我”杀死她,把尸体投入了炉中,才有那白骨从煤渣升出的一幕。 这一部分尚且可以这么理解(不过失踪女孩的蓝色滑雪棉袄怎么时有时无还是个谜),但那一段“我”,孙程,李德武,杨树在石牢中的生活实在有点意识流,我只能大概猜一猜。 我觉得,我的真实身份是孙程,第一个消失的李德武象征被执行死刑的罪犯,杨树则代表执法机关。 推断的依据之一是石牢的监管人杨树有一段扑克牌隐喻说“三分之二是明牌,三分之一是暗牌,他盯着这些牌逐一移动位置”,也许就是在说明这个牢里玩的就是一个取代游戏。 杨树说李德武明天该“走了”,孙程说我不叫孙程,我是李德武。我没理解错的话,应该是暗喻“我”才是那个该死的人。 而代表执法者的杨树说:走的人是李德武。 他的意思是,谁死不要紧,死的人就是罪犯。 推断依据之二就是“孙程会用尽一切办法,消灭父亲在世上的痕迹,而我现在要顶着孙程的名字,等待来接他的那辆车。” 这里的消灭父亲在世上的痕迹,应该是我将替换父亲无辜者的身份,轻松地活下去。至于那辆来接“我”的车,其实就是文章开头,父亲安排来接我的那一辆。 故事里有两个人从石牢放出,李德武离开时,杨树说的是“李德武明天就走”,而轮到“我”,就变成了“明天有人接你”。 走可以代表死,而接你,代表的是新生。 得到外出资格的“我”在离开前夜,幻听到李德武消失那天的枪响,“我”想起那尊佛像,佛像的隐喻可能是拯救之类的吧……我不熟这方面,而后李德武的脸替换成杨树,一场烈火将其化为灰烬,我听到火车的引擎声,高声叫喊起来,声嘶力竭。 我用父亲送我的刀杀了人,父亲选择替我去死,我在父亲被枪决后如释重负,终于能走出阴影。 甚至我怀疑整个石牢都只是一段臆想,我以为我在牢里度过了一段拷问内心的时光,其实只是我在车厢里撒癔症……因为开篇那一段车厢旅途时主角就已经丧失时间观念了——“我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当时觉得这辆车根本没有目的地,它的使命就是一直开下去,没有尽头。”
无论我在车厢中如何煎熬,只要想通,明白了文末那一句父亲的用意,我就能走出车厢,到那时我就自由了。
哦,至于那个“我”掰出来的名字潘宇,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一个恶趣味,班宇写的小说主角说我有个朋友叫潘宇,建议加入冷笑话套餐。
《鲤·我去二〇〇〇年》读后感(四):摸鱼日碎碎念
第五次入手《鲤》了,不得不说这里头有赌的成分。每次下单都是抱着能再蹲到《仙症》、《巨猿》级别作品的期待,但是次次都落了空啊……
吴琦的《我去二〇〇〇年》作为首篇,对于阐发主题来说非常合适,是个虎头,可惜之后都近乎蛇尾了。李静睿这篇《喇叭》,现在拉到微博上,不被喷成媚外公知,就算我大天朝的键盘侠失职了。龙荻在《底色》中提到,艺术就是每天的生活,我很认同,但就这篇文章本身而言,作为随笔尚可,登在杂志上就显得“水”了。《大事皆与他无关》提供的上世纪乡村生活图景,其实是我一直偏爱的,可是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要用第三人称切入一段个人化的体验。
杨庆祥的《九十年代断文》,从形式上我们就能看出他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一篇学术论文,杨庆祥的学问,我想我没资格评价,在这里只想说说他的开头和结尾,也就是叙事部分。
“时间的指针回拨到1991年7月。”第一句话我就看懵了,你要是说,让我们把日历翻回1991年7月,我觉得有情可原。但是你拿一块表,怎么拨回1991年7月啊?这不合理吧。接下来,有一段描述“我”第一次见到客运大轮船时的情景:
那晚的所见是极其震撼的场景,巨大的船体停泊在宽阔的江面,灯光从几层楼高的舷窗、甲板、旗柱上投射开来,辉煌灿烂,这是我以前从未亲眼看见的场景……泛滥的形容词。你问他,第一次见大轮船,感觉怎么样啊?他说,极其震撼。你问他,客运大轮船什么样啊?他说,特别巨大。在这之前,我在知网上读过杨庆祥的论文,他的名字也在我的论文里出现过,但看他写叙述性的文字,这还是头一次。我不得不说,平时说起别人头头是道的批评家,没事的时候也不妨琢磨一下小说技法。对80后这代作家的批评,从他们诞生起就从未间断,或许他们十多年前的确胡写一气,没有任何所谓“笔法”值得重视,但现在可真不是这样了。相反,理论知识垒起的大山,在局外人那里也许横看侧看都是风景,但在我看来,“张悦然”和“杨庆祥”未尝不是五行大山压住的孙悟空。
周嘉宁和她的《风暴天》,在我这儿拔得头筹了,这次要是没有她,我这书就彻底白买了。新文人的两篇都有共鸣,尤其是海带岛的《恋物癖与纳骨堂》,差不多也是我对旧物的态度,但文字稍显华丽,有一股淡淡的“萌芽”风。小说《石牢》,像是一个赶制出来的作品,看起来奇怪的成分多于梦幻。郑执的《凯旋门》和上次《仙症》的结构差不多,开始读到生猛结局的时候,我不禁问自己,你是在跟他做爱吗?(我这种小可爱怎么会说这种话。。。)——同样是豹尾狠抽,但整个故事的层次感明显下降了。《北方天使》,看起来就像一个加长版的小学生作文,之前没看过春树写东西,所以难免怀疑她是故意的。《岛屿的另一侧》,有一种消磨岁月的感觉,很抱歉只快速地看了一遍。
最后说一个卷首语吧。《鲤》杂志的内容有时候七上八下,只有张悦然的卷首始终保持着一贯的水准。
一提起九十年代,她好像真的来了精神,肯德基变得复古,炒股只是为了酷,一个神经质又爱扮酷的女孩,马上浮现在了作为读者的我的眼前。但细想想,这个女孩,不是杜宛宛,不是璟,不是春迟,也不是李佳栖。这些人物多少让我觉得有点失真,如果你非要问我什么是真,我只能说,恐怕小说外面这个提线的人是真的。
《鲤·我去二〇〇〇年》读后感(五):悄悄的打开时光的一道缺口
看见这一期的主题,想到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朴树在1999年推出的音乐专辑《我去2000年》。里面收录了我非常喜欢的《那些花儿》和《白桦林》。 第二件是,离我认识悦然还有三年。
这也不是《鲤》第一次探讨和「时间」有关的话题。 这也同样印证在各种电影、广告甚至餐厅里。那些电影里回顾青春的题材电影已经拍到烂但却依然有人看,而那些80后90后怀旧主题的餐厅总是能成为网红代表。
或者正如同悦然在卷首语里说的那样:未来的人是会惦记从前的人的。
1990 年代对我来说,有一层类似车祸时候的濒死体验的光晕那时候会不自觉地受周围年长一些人事的影响,想加速长大,去体验看到更多的东西。那时候看过的电影和书都印象深刻,成了一种抹不掉的底色。 哪怕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自由长大的人,也不一定不能适应后来更趋于正常的成长路径,那层光晕最后成了一层保护,存留至今。—— 《底色》龙荻很认真的看完了每一篇文章。 会这么 “认真” 可能是因为 “好奇”,好奇别人是如何看待我出生的那个时代的。
说起九十年代,大家最深刻的时代记忆好像都差不多,大多都是 “下岗潮” 和 “发洪水”,以及香港回归这样的大事件。
「视野」和「访谈」的专栏里,几位笔者讲了一些自己关于九十年代的印象。有趣的是,他们的记忆都是具象到和某一样东西、甚至某一件事情挂钩的。
例如,李静睿关于播报邓小平逝世消息的社区大喇叭、周嘉宁高中时代总是遇到的台风暴雨天、毕赣对故乡小城凯里的执念、笛安世界观构成奠基石的日本动漫《新世纪福音战士》。
我很喜欢这种接受不同记忆和观念的时刻,非常有趣。 让我想起前几天和家人一起吃饭。姑妈说我小时候最喜欢吃板栗肉粽,妈妈说不是粽子是龙游发糕。我很认真的思考了一下,最喜欢的应该是外婆每年过年都会炒上一大锅的八宝菜。 想着想着就忍不住咽了口水。记忆会错乱,但是身体不会、味蕾不会。
说说我心中的九十年代吧,只和两个名字有关。
张曼玉和林青霞。
小时候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总会说:「张曼玉的曼、林青霞的青。」总感觉这么说 会让我的名字更美一些。 今年年初,重看了数码复刻版《滚滚红尘》。真的太美了,仿佛是有人吹散了时光的尘埃,每一个脸庞都变得焕然一新。
二十八年前,有一个男青年在深圳的放映厅里看完了《滚滚红尘》。 他太喜欢这部电影,也太喜欢电影的两位女主演张曼玉和林青霞了。决定取两位女主演名字中的各一个字做名字,送给即将出生的女儿 —— 我就是那个女孩儿。
这让我在整个童年时期都在探索香港电影和这两个女人的奥秘。我的内心深处觉得我和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这种关联让我觉得亲近、安全和快乐。 而这种情绪,至今也依然影响着我。
我很感谢我的爸爸,他是这种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制造者。他给我的当然也不仅仅只是如此,他的聪明机警让他在九十年代就已经嗅到了经济发展的趋势。 他从深圳回到江浙,除了给我带回了这个好听的名字之外,还带回了他的人生的第一桶金。 我已经不记得我们的家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的了。我只记得有一次爸爸喝醉了酒回来,他落寞的和我说了一大堆曹雪芹家道中落的故事。 那时候我饶有兴趣的听着故事,完全没想过未来的人生轨迹会和这个陌生名字有这么多重合。 —— 现在回忆起来,却已经像是上辈子的事了。
如果人生有四季的话,那么十二岁之前,我的人生只有春天。
最后安利一波我最喜欢的「小说」专栏吧。
这次的「小说」在数量上没有以往几期的丰富。 但是质量并没有减少。几千字的短篇,篇篇都是精品。分别收录了:班宇的《石牢》、郑执的《凯旋门》、春树的《北方天使》、张玲玲的《岛屿的另一侧》。
郑执的《凯旋门》真的好看到让我忍不住想要敲黑板、划重点、标高亮了!!! 《鲤》的每期小说虽然没有严苛的规定,但是总有点儿命题作文的意思,毕竟主题在哪儿摆着嘛。 郑执的这一篇《凯旋门》写得好不仅仅在于贴近了时代的文章主题,更是写出了一种掏心窝子的坦诚——这种走心的感觉让我想起了身边的东北朋友,让人感觉很舒服。
千年虫的形象理应更接近蚂蟥,它们同样无法被杀死。一个反噬时间、一个五十痛楚,都可以成为人类的偶像。上一次读郑执,是匿名作家比赛里那篇惊艳的《仙症》。好看到要掐大腿!
近几年,东北文学界输出的优秀作家堪称是井喷式的。 双雪涛、班宇、再到郑执,今年有幸都读了几本他们写的书。 写得是真好呀!初读的时候都能嗅到那股子生猛的东北泠冽气息,回味的时候才发现冰山下藏着的暗潮涌动。
呀,写得真的太好太好了。我都忍不住要为南方作家加油打劲了呀,哈哈哈哈哈哈。
很喜欢这一次的主题。怎么说呢,因为「19」这个数字对我有很特别的意义,不仅仅只是因为我出生在 1991 年。
在即将过去的 2019 年,我参加了一场重要的面试并且即将完成一次职业晋升、我花了半年的时间甩掉了 26 斤的赘肉、我近十年来第一次超额完成了年初的读书目标(今年年初打算看 24 本,现在已经看完 31 本)。
总之,我相信 2019 年对我应该是一个好的年份,毕竟下一次等到年份里有数字「19」的年份已经是 100 年后的事了。
我看见时光的缺口打开又被合上。 再见二〇一九年,我要去二〇二〇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