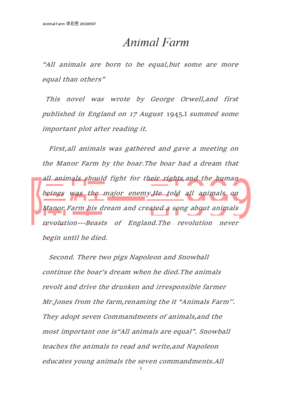
《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是一本由[法]基佐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7.3,页数:46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精选点评:
●国内啥时候出下卷
●可惜只是原著上篇的译本,到查理一世被处死就结束了,我想看到克伦威尔上断头台
●一六四O年英国革命史. 171113
●查理,何苦生在帝王家!
●高中时读的书,那个时候对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感兴趣。现在书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
●经典打卡
●马克思评价基左是天才历史学家,天才没看出来研究确实是扎实
●文笔极好
●这书的翻译质量应该在全套书里算比较好的了吧。。想想那本三十年战争史
●「我想在其中找出一个作者对他的研究对象所怀有的自然同情,想找出那种会给历史以生命和光明的东西……」
《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读后感(一):查理一世与雅典
查理一世的死很大程度是被自己帝王的傲慢所害。
当看着查理一世一次次拒绝议和一次次背信弃义时不经让我联想起伯罗奔尼撒战争时的雅典。
查理最后的死让人痛心,但也是他自己造成的,他的死和雅典的西西里远征一样,源于傲慢。
《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读后感(二):现实总是一次次的重复历史
第一卷开篇第二段写到:“全英格兰确实在尽情地欢乐,满怀着希望。一个新的国君等位了,不仅自然而然地产生不分明的希望与乱哄哄的欢乐,这些希望与欢乐还是很严肃认真的,普遍存在的,看来又还是很有根据的。查理做王子时为人严肃,行为端正......”,这段描述与公元2012年的中国是多么的类似啊。但愿我只是猜中了这前头。
《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读后感(三):查理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深渊的?
新登基的查理一世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为各方所拥戴。然而,查理从娶法国公主开始就一步步走向失败,一来这桩政治婚姻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益处:彼时英法在全球的竞争已有征兆;英国的新教和法国的天主教天然不可调和;二来王后尝尝在耳边吹风说到像法王那样的绝对权威是君主本就有的权利。接下来,查理一世召回了爱尔兰总督,但此君却被议会处以极刑,而查理却没有采取实际行动,以至于议会也非常惊讶如此不费多少力气就处死了总督。殊不知,爱尔兰总督是国王团队中最有能力的也是为数不多的人才。再然后,查理一世在思考的时候总是一厢情愿的认为苏格兰人和法兰西人会来帮助他,可事与愿违,雇佣兵是世界上做不靠谱的群体,他们秉承的是谁付钱就听谁的这一准则。最后,查理没有想到军队会在克伦威尔的幕后运作下成为独立于议会和国王的第三股势力,而查理一世就被断头在这股新势力的手下。
《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读后感(四):英国革命
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谓声名远播。是我们在历史书中的重头之一。可是我对它的所知也只限于历史书。究竟怎么回事,还是读本书吧。 读完此书第一印象是查理一世是“很傻很天真”,还是那个时代那个阶层的特性。他的性命就是自己送掉的。在书中至少有近十次他可以与议会或者克伦威尔达成协议,周围所有的保王党,家人乃至其他王室也劝他妥协。可是他以一种高傲的“君授神权”的姿态英勇的拒绝了。结果最后自己送了命。真应了主所说:上帝要人灭亡,必使其疯狂。 历史是逐步发展的,英国革命也不例外。开始时,只不过想限制君主的某些权利。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出色的表现。使得斯图亚特王朝的两位君主令人失望。而查理更大胆,竟然解散议会。结果到需要人民支持时,人民也大胆回应了他。内战爆发了。其实原因有许多,并不止是资产阶级想夺取封建贵族的权。还是天主教(国王)与长老派,到后面还有独立派(克伦威尔)的宗教冲突。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在历史书中是没有的。而在欧洲历史上因为宗教原因而发生的战争与革命确屡见不鲜。其实包括最激进的克伦威尔开始也没打算成立共和国。充其量想满足自己和派别的利益。可是查理太高傲了。总想恢复独裁权力。一次次拒绝和谈以及耍两面派。可惜他的对手不是傻子,当事实清楚后,他们也决无退路了,于是查理一世被砍头了。 书中结尾处对查理审判的描写令人感觉缺乏法理依据,查理是冤死的。出于作者的角度当然可以理解。不过我不认同。当查理在法庭上被判死刑时固然令人同情。可是回想一下,当他在进行统治与发动内战时,又有多少人冤枉死去。法庭没有权利审判国王。可是国王的权利又是哪里来的。查理可以说是继承的,但王室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按作者在《欧洲文明史》中所说,当各种力量都宣扬自己的合法性时,都有意无意的不谈真正的“合法性”,即武力。当国王们用武力夺取政权时,也就寓意着人民有用武力夺回的权利。当你使大地流满鲜血,大地也将吸吮你的鲜血。 这也就是英国革命的意义。人民有权利。
《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读后感(五):基佐的历史观与英国革命史
为了更好的理解《1640年英国革命史》,我们或许可以从基佐的历史观入手。在该书的第一版前言中,基佐概括的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他认为欧洲的历史就是一部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但是基佐所说的文明,既非制度亦非物质,而是原则,例如自由、平等和理性等等。由这些原则构成的文明本身是历史的动力,因为原则要求人们为之奋斗。一部欧洲文明史,就是上述这些原则出现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历史。
将历史解释为原则的自我实现,这个观点看起来与黑格尔的哲学很类似,然而,两者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在黑格尔那里,原则或者说绝对精神是自在自为的,它不依赖于时空,相反时空恰好是真理自我展开的结果;而在基佐那里,原则是根植于历史的,具体的说,是人类的良善通过伟大贡献在历史上的闪现。因此,原则来源与人类自身,而不外在于人类。
原则是有价值的,因为他是人类良善的展现。它一旦出现,就会被人们牢牢铭记,并且通过人们的向往,最终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亦即实现自身。如果说,革命前的欧洲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原则是如何出现的,比如封建时代的自由、教权时代的理性(通过鼓励科学),以及君权时代的平等,那么,革命的历史就是这些原则最终全部得到实现的历史。
只有懂得了基佐的这个进步文明史观,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认为英法两国革命是同一个战争的胜利,以及为什么他说“如果第二个革命不曾在历史上发生,那么我们就无法彻底了解第一个革命。”正如基佐所说,两个革命的趋向和起源是相同的;他们的愿望、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进步,也指向同一个目标。它们致力于同样的任务,即公众在公众事务中必须取得支配地位;它们都为争取自由而反对绝对权力,为争取平等而反对特权,为争取进步和普遍利益而反对居高位者的个人利益。简而言之,它们的目标是:人民主权、自由、平等和博爱。
如果说上述分析不错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就能够赞同基佐对英国革命的基本评价:只是看见一个朦胧的影子、未完成自己的全部使命、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革命。至少《1640年英国革命史》这本书验证了基佐的这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