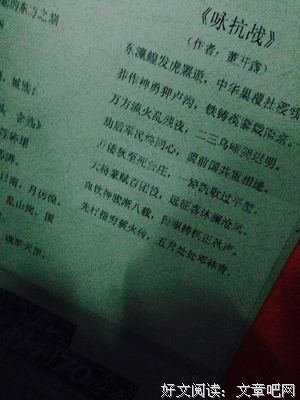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是一本由[俄]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页数:4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精选点评:
●1.自然辩证下的无限客体化。2.主观的介入,自由走向不自由。3.主观对自然辩证的模仿和依附。上帝的规则也好,现代的规则也罢,资本家的追求都是类似的依附。4.依附新的东西的人打倒依附旧的东西的人,并把被新的东西奴役称作绝对自由。5.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人的主观意志在每个过程中都试图介入和超出,人需要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为了这么做不惜去毁灭世界,追求痛苦。6.于是建立一个国度,一个人自身矛盾的世界来承载人心中的矛盾。7.人对绝对的追求,恰恰是在制造一条笔直的下坠路线,所有绝对都是幻觉,其实是沿着直线无尽下坠,就像人对极限的想象不过是将对有限的幻想扩大到极限中一样。8.矛盾是必须的,上帝和魔鬼是先验存在于精神中的东西。9.精神和身体交融,身体和世界交融。上帝在人之中。杀死上帝,你就杀死了人。
●每一个投入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最终都成了一个个新人
●彩页加增订。完美: )
●火源,一大一小。
●陀思妥意识自由到自由意志到“所有都允许”的再到恶再到罚的转变 但那不是道理式的 而只是迷狂的上升必经之路 在人的深处 隐藏着非理性的双重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读后感(一):这本书写的有点深奥
这本书写的有点深奥,就不好懂,看了半个多月了,当然也可能是自己的水平还要大同提高,欢迎交流,顾适的小说有一种精妙的平衡感,以清晰的结构和娴熟的文字,去表达科学的严谨与美,探寻人性的细腻幽微。她的小说既满足了我们这些科幻迷的期待,也能让对科幻不那么感兴趣的读者乐在其中。顾适是一位有潜力出圈的科幻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读后感(二):这本书写的有点深奥
这本书写的有点深奥,就不好懂,看了半个多月了,当然也可能是自己的水平还要大同提高,欢迎交流,顾适的小说有一种精妙的平衡感,以清晰的结构和娴熟的文字,去表达科学的严谨与美,探寻人性的细腻幽微。她的小说既满足了我们这些科幻迷的期待,也能让对科幻不那么感兴趣的读者乐在其中。顾适是一位有潜力出圈的科幻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读后感(三):一个包含了人的辩证世界
1.在科学的影响下,自然辩证的世界观下,我们处在一个被其他人无限客体化,被理性限制的必然世界。
2.宣称自由理性,因为压抑了非理性、反而导致了不自由。
3.这个过程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主观对自然辩证的模仿和依附是本能的,是一种诱惑。上帝的规则也好,现代的规则也罢,资本家的利润度量,都是类似的依附。甚至建造一个人间天堂,也是类似的诱惑和依附,但这之后呢?
4.依附新的东西的人打倒依附旧的东西的人,并把被新东西的奴役称作绝对自由。
5.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人的主观意志在每个过程中都试图介入和超出,人需要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为了这么做不惜去毁灭世界,追求痛苦。
6.于是建立一个国度,一个人自身矛盾的世界,一个真实的地上国度,来承载人心中的矛盾。
7.人对绝对的追求,恰恰是在制造一条笔直的下坠路线,所有绝对都是幻觉,其实是沿着直线无尽下坠,就像人对极限的想象不过是将对有限的幻想扩大到极限中一样。起点是自由的,但如果妄想贯彻自由就会遭难。
8.矛盾是必须的,上帝和魔鬼是先验存在于精神中的东西。
9.精神和身体交融,身体和世界交融。世界外的上帝其实在人性之中。人性以上帝为对照,以高出人性的东西作为人的基石,杀死上帝,就杀死了人。
(突然发现,当思想通过小说表现时,思想不再被客体化,而是真实感知。现在这样,逐条列出观点,表面上更清晰了,但反而失去阅读原文时深刻的体验。这就是比真实很真实比哲学更哲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魅力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读后感(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追随者们
每年写至少一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这似乎成了自己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虽然自己从未刻意这样做,但它似乎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从自己确立这一点后就没再变过。我从大量阅读文学名著的早期便接触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久后便将其视为最喜爱作家的唯一,至今一直没变过。
长期视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最喜爱的作家也不是容易的事,这几年对他的情感也降低了不少,我已经很少阅读他本人的著作了。但若希望找到能取而代之的人也不容易,一方面他的著作实在太有趣了,从他身上总能看到其他作家身上看不到的东西;另一方面,文学成就能在他之上的着实不多,与他平级的也不多,而对这些作家的喜爱能超越他的则一个没有。
所以较早地接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来说是幸运,也是不幸。幸运的是能很早地就知道文学的巅峰在哪里,并为这巅峰而深深着迷;不幸的是太早地确立了这个巅峰,对于其他作家的作品总难免与之比较,也自然容易得出不如他的结果。所以我算得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狂热追随者,有许多思考是以他为基础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得到越来越多新的见解,实在是奇妙。
近来让我深思的一件事是:那些与我一样,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狂热追随者的人,是否真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追随者,而不是被其笔下的人物所打动,成为他们的簇拥?大约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都知道,巴赫金谈到他文学创作中的一些特点,“复调”、“对话”是其中的精髓。
这两者的含义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些声音之间,还能彼此辩论。而真正的他本人的声音,则隐藏其中,如果不仔细考证的话,是发现不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一个幽灵,附身于笔下的人物,使之能说出自己的思想,尽管他本人也许从未有这样的想法。这是他在艺术上不可超越的核心之处。
读者们也是同样的,我们难以辨别究竟哪些是他本人的声音。在他生前,便有许多人因为这“可怕的思想”而指责他,使他背上污名。后世的一些批评家也借由小说中人物的习性,而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是如此。这大概是他作为一个顶尖的作家最无奈的事。但这着实不能怪他们,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太过掩藏,不是一般人能发现的。
与批评者相对的是那些追随者们,他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追随方式也是多样的。我时常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追随者们相互辩论,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才是正确的,最后谁也说不服谁。细细品味他们的话,我才发现,他们未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追随者,甚至未必了解他本人的思想(即使知道,也未必赞同)。更可能的是,他们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追随者,斯塔夫罗金的追随者,基里洛夫的追随者,韦尔西洛夫的追随者,伊万·卡拉马佐夫的追随者……
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作家本人实在太掩藏了,而取而代之站在台面的是超人哲学论者、无神论者、虚无主义者、残忍的暴徒、高贵但空虚的灵魂、自杀哲学论者……这些人的声音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声音要大得多。人们不由自主地为他们所吸引,为他们的思想站台,成为他们的簇拥。
于是我时常见到这一幕,一个无神论者与一个超人哲学论者进行辩论,一个虚无主义者与一个自杀哲学论者辩论,他们都是书中这些人的影子,就像拉斯科尔尼科夫身后的斯维德里盖洛夫,斯塔夫罗金身后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伊万·卡拉马佐夫身后的斯麦尔佳科夫。而真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隐藏在他们身后,静静地观察自己笔下人物的争斗。
这并非只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年代到现在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这类型的争斗发生了许多回。那些认为自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追随者或反对者的人,都无意中踏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设下的陷阱,成为其笔下人物的代理人。尼采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他是与自己最接近的人。但他也只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继承者,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超人哲学的发扬者,是一个理论更加缜密、更具思辨能力的大号拉斯科尔尼科夫。
后来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如纪德、毛姆、鲁迅、纳博科夫,都曾仰慕或批评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他们仰慕或批评的是否真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还是他笔下的影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很会骗人的作家,他创造了如此多具有自己思想的角色,使得如此多人都能成为他或他的影子的追随者。
行文至此,我才发现自己早已偏离本文的重点。我的本意是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的书评,却发现自己讲了那么多与之无关的内容。当然也不是完全无关,自我狡辩一下,上文所讲的都是我在阅读本书以及思考本文过程中渐渐成熟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和其他一些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籍或文章不同,它是真真正正尝试越过那些影子,直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思想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有两部作品是不能忽视的,一部是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探讨了其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的问题,“复调”、“对话”、“狂欢”等概念都是在本书中首次提出;另一部就是本书,从宗教哲学的角度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尝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内核进行探讨。
不能忽视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经常是围绕着宗教,也就是东正教进行的,别尔嘉耶夫恰好是一个宗教哲学家,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读也正是围绕于此。尽管本书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读较为空泛,经常有一些比较大的词语去形容他。这对非基督教信徒的读者实在是不友好。
但它的确开了一个先河,真正尝试从宗教的角度去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经历和边缘著作的不断挖掘,如《书信集》和《作家日记》,我们越发能感受到,宗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中所占的重要比重。只是很可惜的是,我并非基督教信徒,“上帝是否存在”对我而言并不重要,别尔嘉耶夫在书中提到的“宗教大法官对耶稣的三大诱惑”我也是一知半解。
从自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困惑不解,甚至批评反对中,我发现自己已经不是个合格的追随者。如果回溯自己的所思所想,会发现自己也是那些影子的簇拥,头脑中的虚无主义倾向不时地冒出来。而虚无主义者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大力批评的对象。这使我感到羞愧难当。
人们经常是思想未动,身体先行。身体上的某些异常行为是瞒不过大脑的,它预示着自己思想的某些变动,而让自己的意识察觉到这一点却还需要一段时间。当厘清了近几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行为异常,便慢慢意识到自己大脑深处的变动,或者说那才是更本质的东西。
近几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注少了许多,几乎不阅读他本人的作品,在许多时候也不容易再想到他,自己的身体已经在对他进行疏离。这意味着自己慢慢理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意识到自己的核心思想与其有着难以逾越的不适应的地方,于是选择了疏离。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吸引力仍然很大,它仍然会不经意间便拉住我。而且如前文所说,想要找到能代替他的人实在是太难了。于是我便一直处于这一拉一扯中。时而靠近它,想要理解他内心深处的秘密;时而又远离他,继续往前探索新的事物。这样的拉扯经常发生,而且可以预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不会停止。
更多精彩好文,欢迎关注公众号【杰瑞书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读后感(五):只要投入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的人都会成为一个新人
花了一个多星期读完了白银时代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因为太喜欢了,抄了上万字读书笔记,小指头关节每天都粘着黑色的墨水,恨不得全文背诵哈哈哈哈哈哈。
这本书是别尔嘉耶夫1921年到1922年间,在宗教文化民间学会所做的系列讲座的集结,书后收录的《大法官》《斯塔夫罗金》等文是在1907年至1918年发表的。从他的第一本哲学著作《自由的哲学》(1911)到他自认最完备的哲学著作《论人的使命》(1931),“这二十年是他的哲学观形成、发展、成熟的重要阶段”。
他一生的思想核心就是他的新基督教精神(以精神自由为基础),这精神的起源就是陀(懒得打名字下文简称陀,别尔嘉耶夫简称别)《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中的基督形象。他说:“《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中的基督形象走进了我的灵魂,我接受了《传说》中的基督。基督永远与自由精神相联系,对我来说,终生如此。”“在对自由的第一直觉中我遭遇了陀,他一同我的精神之父。”“还是在小男孩的时候我就形成了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习性,他比任何一位作家和思想家更震撼我的心灵。”
因为俄罗斯的东西我读得少,在读这本《世界观》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别是谁,也不知道他都在思考啥,买这本纯粹是想丰富我脑壳中的陀。看到译者耿海英的代序里提到,别是根据陀的创作创造了自己的“自由哲学”,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别自己也说:“我不仅试图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并且也融进许多我个人的世界观”,我就大概理解了这本书的定位,反正甭管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陀的世界观》也好,《别的世界观》也好,这本书也确实天才地从宗教哲学的角度系统阐释了陀,就……磕得十分开心……我也只读过陀,别的阐释和我自己理解不对付的就辩证地看吧(比如说女性角色那部分)。
《世界观》里别说起陀用得最多的一些词是“火一般的”、“迷狂”、“激情”,但是我看别自己写这本《世界观》的时候也挺激情的,整个阅读过程经常是这样的:看两页就得起来在家里走走,对着空气念叨刚才读到的别的鲜活的话,顺便与空气打打关于“自由”、关于“反基督”的辩论……这样才能稍微消化消化他热情洋溢的观点……文盲哭泣……
下面整理一下几个别重要的观念,免得过几个月就忘求了。
1、陀创作的“思想”
思想在陀的创作中起着巨大的核心作用,思想生命永远是动态的、充满活力的,永远在在火一般的氛围中流淌;在陀那里根本没有静态的思想,思想本身就构成情节,甚至是作为角色之外的角色。它构成悲剧的张力,构成整个艺术作品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形而上的思想构成整个情节的跌宕起伏,形成强大的冲击力;是思想带来的激情,是思想的利刃把人物逼向最极端的境地,把人物推向悲剧的最高峰”。他小说中的所有对话,都是惊人的思想的辩证法,所有的主人公,都专注于某种思想,沉浸于某种思想。
我印象最深的是《群魔》中的基里洛夫,他为自己的思想实践自杀的那一段看得几乎落泪;他是一个最纯洁的,几乎是天使般纯洁思想的化身,他要把人从一切恐惧中解放出来,达到上帝的状态。“谁战胜了痛苦与恐惧,他自己就成为上帝;那时就有新生活,那时就有新人,一切都是新的。”“所有想得到首要的自由的人,他就应当敢于自杀……谁敢于自杀,谁就是上帝。”
但这并不意味着,陀是为了贯彻某种思想而写一些片面的论题式的小说,思想完全内在于他的艺术,他艺术地揭示思想生命。他是柏拉图的“思想”一词意义上的“思想”作家。他非常谦虚地这样说自己:“我在哲学上是外行(但不是在对它的爱上,在对它的爱上我是强有力的)。”他在经院哲学上或许非常糟,但他的直觉天才告诉他独特的哲学地思考的方式。
拉斯科尔尼科夫——是思想,地下室的主人公——是思想,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沙托夫、彼·韦尔霍文斯基——是思想,伊万·卡拉马佐夫是思想。
陀整个的艺术,就是“思想”的艺术,它的诞生,它的道路,它的毁灭。
2、人
别认为,在陀那里,除了人,别无他物:没有自然,没有物质世界,在人的内部,也不存在使之与自然界,与物质世界,与日常生活,与客观的生活结构连接的东西。存在的只是人的精神,“他只对此感兴趣,只研究它。”“他为此献出自己所有的创作力量。”
在彼得堡,有贫民窟,有肮脏的酒吧和发臭的出租单间,但是城市只是人的环境,只是人悲剧性命运的一个因素,只是人的背景,是内在精神世界的符号和象征。一切都紧紧围绕人之谜旋转,一切都为发现人之命运的内在因素所需。
“在陀的小说结构中有一个巨大的中心。一切人和事都奔向这个中心人物,或这个中心人物奔向所有的人和事。这个人物是一个迷,所有的人都来揭开这个秘密。”
例如《少年》,一切都围绕着韦尔西洛夫这个中心人物旋转。一般的观点认为,陀的主人公让人产生无所事事的印象,其他角色几乎没有别的“事情”,所有人只有一件“事情”——揭开韦尔西洛夫之谜,揭开他的个性,他奇异的命运之谜。
非常有趣的是,黑暗的人——《少年》的韦尔西洛夫、《群魔》的斯塔夫罗金、《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被人们解读,所有人都向着他们运动;而光明的人——《白痴》中的梅什金、《卡》中的阿廖沙,解读人们,他们向着所有的人运动。《罪与罚》是另外一种结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命运不是在人的多样性中,不是在人们相互关系的白热化中得以揭示,而是面向自己来揣度人性的界限,他拿自己的本性做实验。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最严肃的、唯一严肃的“事情”。人高于一切,人就是唯一的“事情”。
陀用狄奥尼索斯式的艺术方式,把人性置于隐秘的深渊,在其中刮起迷狂的旋风,以此来进行自己的人学实验,他是一位“人学家”。
“在世界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一个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对待人,即使在最低级的人身上,在最可怕的人的堕落中,依然保留着上帝的形象。他对人的爱不是人道主义式的爱。在他的爱中,他把无边的怜悯和某种残酷凝聚在一起,他向人宣扬受苦之路,这与自由思想位于他的人学意识的核心相关。没有自由就没有人。”
别认为,陀的所有作品都是对人性的实验,是在对自由之中的人的命运和在人之中的自由的命运的发现。他选取解放了的人、摆脱了定规的人、进入宇宙秩序的人,研究他们在自由中命运,揭开自由之路的必然结局。
鲁迅谈起陀:“读他二十四岁时所作的《穷人》,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而这陀思妥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这决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就因为伟大的缘故。但我自己,却常常想废书不观。”
3、自由
自由位于陀世界观的核心,人的自由决定了人的命运,决定了他饱受苦难的流浪。
对他来说,自由既是他的人正论也是他的神正论(后面大法官会提到),应该在自由中既找到为人的辩护,也找到为神的辩护。整个世界进程就是完成自由主题之使命,是一场为完成这一主题而产生的悲剧。
陀发现了人身上非理性、两极对立、二律背反的部分,《地下室手记》中揭示的就是非理性,他彻底否定“人在本质上是趋向益处、趋向幸福、趋向满足的”,否定人的本性的是理性的,在人的身上隐藏的是对为所欲为的需求,对无限的、高于一切幸福的自由的需求。“人——是一个非理性的生物。”一个重要的论题:“是否一切都是允许的?”
他自由的辩证法在于,自由意志“保留了我们最主要的和最宝贵的东西,即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但另一面,自由意志和反抗会导致扼杀人的自由,瓦解人的个性。别指出,陀揭示了在自我意志中自由怎样被消灭,在造反中人怎样被否定,自由转化为自我意志,转化为人反抗式的自我肯定;自由成为无目的的、空洞的自由,它使人变得空虚。拉斯科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伊万就是证明。基里洛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恶魔般的自由杀死了人。这里,自由,作为自我意志,消解了自身,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瓦解并断送了人。这样的自由从内部、内在必然地导致奴役,吞没人的形象。不是外在的惩罚等待着人,不是法律从外部使人遭受沉重的统治,而是从内部、内在地显露的神性始原击溃了人的良心;由于上帝之火,人在其自己选择的黑暗与空虚中被烧尽。这就是人的命运,这就是人自由的命运。
但是,陀深知人神的诱惑,他让所有人物都走过了人神之路,正是这样,人神的谎言在无限的自由之路上被揭穿了,在这条路上,人找到的是自己的终结和死亡。在伊万之后,出现了佐西马和阿廖沙的形象,“关于人自由的悲剧的辩证法是以《传说》中基督的形象结束的。这也就是说,人,经由无限的自由之路,发现了通向基督的道路——神人之路,在这条路上,人找到的是自己的得救和对人的形象的最终肯定。”
陀是“残酷的”,他不愿意卸下人的自由之重负,不愿意用失去自由的代价来换取人免于痛苦,他把自由人的尊严相称的重大责任赋予人。即便是善、真理、完美、幸福,也不应该以失去自由的代价来换取,而应当是自由地接受,对基督的信仰也即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传说》中基督不愿走下十字架,不愿以奇迹、强权获取信仰。
别认为,正是在这里隐藏着基督教最主要的秘密,自由的秘密——基督是给予自由的人,基督教是自由的宗教,真理不是强制的真理。拉斯科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韦尔西洛夫、伊万都是在经历“怀疑的大熔炉”之后,从他们精神深处,从他们自由的良心深处响起来彼得的话:“你——基督,上帝活着的儿子。”
4、恶
在陀那里,自由与恶联系着,没有自由,恶便无法解释,恶出现在自由的道路上。自由是非理性的,正因为如此,它创造善,也创造恶;自由之路会转化为自我意志,自我意志会导致恶,恶会导致犯罪,犯罪内在的不可避免地导致罚。实质上,罪与罚的问题,就是恶和对恶负责的问题。在人性的最深处,罚注定在等待着人。
别指出,陀一生都在同对待恶的肤浅的、表面的态度作斗争,反对“以社会环境肤浅表面地解释恶和犯罪”(对人性深度、精神自由、自由相关的责任的否定),并在此基础上否定罚。这种惩罚需要的不是来自外在的法律,而是来自人自由的良心的最深处。
恶就是恶,“恶的本性——是内在地,是形而上的。人作为自由的存在,对恶负有责任。”另一个方面,恶还是人的道路,人悲剧的道路,是自由人的命运,是同样可以丰富人,带人走向更高的台阶的体验。但恶不是善进化必须的阶段。恶是悖论的,而乐观的进化论对恶的理解,是理性地取消这一悖论。从恶的经验,可以使人的意识敏锐起来,但为此需要经历磨难,需要经受死亡的恐惧,需要揭示恶,需要要让恶经历地狱之火,需要赎罪。苦难也是人深度的标志。
赎罪恢复人的自由,还人以自由。因此,赎罪者基督就是自由。
佐西马和阿廖沙被塑造成认识了恶并走向更高境界的人,在阿廖沙的身上有着卡拉马佐夫家族恶的元素,他是一个经过了自由体验,走向了精神复活的人。在《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遇到了恶与罪的宗教问题:“是否一切都允许”。他按照自己思想的名义杀人,但这一问题的解决不属于人,而属于上帝。以他的精神历程揭示,人所具有的精神性不允许以自我意志杀死哪怕最坏的、最为罪恶的人,人以自我意志消灭另一个人,他也就消灭了自己。
5、爱
陀发现了俄罗斯的自然本能之中情欲和性欲两种元素,爱就像火山熔岩喷发,他作品中的一切事件皆起因于情欲的骚动不安。
“俄罗斯的爱情中有某种沉重的、痛苦的、阴暗的和常常是畸形的东西。我们没有真正的浪漫主义的爱情。没有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但丁与贝雅特丽采、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
在陀的创作中爱情占据了重要地位,但不是独立地位。爱不具有自身的价值,不具有自身的形象,“仅仅揭示人的悲剧之路。是人的自由体验。”
“女人在陀的创作中同样没有独立地位,陀的人学是绝对的男人的人学。”陀对女人的关注,完全是把女人作为男人命运中的因素,女人只是男人的内在悲剧,只是这一命运中碰到的难题,她只是他的命运。
“他揭示给我们的不是真正使人联结与融合的崇高的爱情,婚姻的最高境界没有被实现。”在陀那里,男人被对女人的欲望所束缚,但这似乎依然是男人自己的事情,是男性的欲望本性的事情。“在陀那里,男人与女人从来不结合在一起。陀的女性之所以是如此的歇斯底里,如此的狂暴,正是因为她由于不能与男性结合而注定毁灭。”
(这章观点我不太赞同随便糊弄一下)
6、神人与人神、大法官
别认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是陀创作的巅峰,是“他思想辩证法的桂冠”。陀正面的宗教世界观应当从这里开始寻找。
《传说》有两种世界本原的对立与冲突:
基督——自由、信仰生活的意义、上帝对人的爱
大法官——强权、不信仰意义、非上帝对人的怜悯=反基督
魔鬼在旷野中诱惑基督,被基督以自由的名义、上帝的国的名义、天上的面包的名义拒绝的那三种诱惑,正是大法官的三种诱惑:
-第一个诱惑:地上的面包
大法官以对弱者的怜悯,剥夺他们的自由,组建起地上的国,给予他们面包,并如此指责基督:“你这样尊敬他(人),你这样做,就好像不再怜悯他了,因为你要求于他的太多了。你要是少尊敬他些,少要求他一些,那倒更像爱他,因为那样的话,他的担子会轻一些。他是软弱而低贱的。我们如此温和地对待人们的软弱无能,满怀爱怜地减轻他们的负担,难道我们还不够爱人类吗?”“你拒绝了唯一的、绝对地属于你的旗帜——地上的面包的旗帜,它可以使一切人无可争辩地崇拜你,而且你是以自由的名义和天上的面包的名义拒绝的。你瞧,你以后又做了什么。一切又是以自由的名义!我告诉你,人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折磨他的了,即要找一个什么人,好赶快把这个不幸的存在与生俱来的自由之礼物托付给他。但能掌握自由的只有那个能安慰他们良心的人。”“恰恰是以地上的面包的名义,大地精灵会起来反对你,与你厮杀,战胜你,所有人都会跟他走……在你的圣殿的废墟上将耸立一座新的大厦,重新建起的巴别塔。”
大法官的话极富蛊惑性,他伪装为民主主义者,弱者和被压迫者的朋友,所有人的热爱者,他指责基督的贵族派头,只想拯救被拣选的人,少数强者。陀猜中的和大法官说出的伟大秘密在于,人类自我神化的道路,地上的面包取代天上的面包,彻底脱离上帝的道路,必定走向所有的人都成为神和巨人,必定走向人又重新拜倒在新神的脚下,一个神化的人,一个王。希加廖夫语:“我的出发点是无限自由,结论是无限专制。”
强制性,对自由的仇恨,是大法官的精神实质;
宣扬对所有人的爱,对人的软弱的宽容,是大法官的诱惑。
-第二种诱惑:奇迹、神秘和权威
“当人们对你讥笑,嘲弄,对你叫喊‘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会信仰这是你’的时候,你没有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同样是因为你不愿意用奇迹降服人,你希望的是自由的信仰,而不是因为奇迹而信仰;你希望的是自由的爱,而不是强权之下的俘虏的奴隶般的惊叹。”
上帝的儿子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而不是作为王和掌权者,是一个受尽折磨与侮辱的形象,以此让人自由地认识自己的上帝并爱他。“奇迹应当源于信仰,源于与上帝自由的结合,源于爱。信仰中自由的良心高于一切。”
基督无限地尊重个性,把它抬高到一个超人的高度,但是,那些把人神化、过分神人化的人实质上却是贬低个性,不相信自由的使命。“大法官们否定奇迹,否定那个源于信仰的奇迹,但却又想自己制造表面的奇迹,并以它们来诱惑人类,从而在这些能使人获得幸福的奇迹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权威。
-第三种诱惑:地上王国的诱惑
“我们认同的不是你,而是他,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我们早就不认同你了,而认同他了,已经有八个世纪了。整整八个世纪以前,我们就从他那里接受了你愤然拒绝的东西,那个他指给你看整个地上王国时愿意给予你的最后的礼物:我们从他那里接受了罗马和凯撒的剑,并宣布只有自己是地上的王,唯一的王,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能彻底完成我们的事业。”
第三种诱惑——地上王国的诱惑、凯撒的剑、帝国的梦想,诱惑了教权专制的天主教和君权专制的东正教。“它极端的可怕的体现是罗马国家,神化的凯撒,极权的至高无上的国家,极权的凯撒主义。只有基督之前可以形成东方的专制国家,能够在专制国家中给人以神的荣耀。而基督拒绝地上王国、极权国家的诱惑,认为地上的国是对天上王国的背叛。”
陀在《传说》中给予荒谬的、虚假的地上天堂的神权政治思想以最后的、最有力的打击,只有拒绝谋求地上权力,基督的自由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