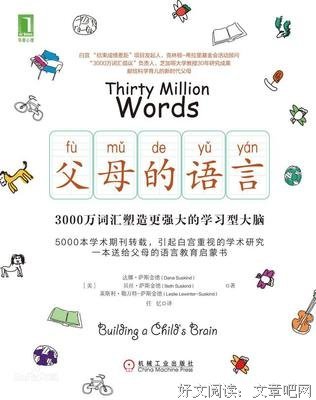
《身体的语言》是一本由[日]栗山茂久著作,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32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25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身体的语言》精选点评:
●哪天我要写点书评
●肌肉VS脉穴
●身体,某年董豫赣葛明童明等在北大论过一次。
●读得比较早的一本书,对不同文化系统的身体与医学的比较分析呈现“风格”,令人耳目一新,但其对材料的选择性遮蔽和对中医不同时代肌肉感知微妙变化的忽视,受到李建民等学者的批评
●草读
●头一次对脉有了这么深刻的认识
●我也是读了澎湃访谈后才找过来的……
●真难为作者了。一个日本人,使用英文,讨论古希腊和中国的医学。
●中医现代化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希腊医学希波克拉底到盖伦转变的时代时,已经遇到了。
●古希腊人对血液过剩的恐惧,并予以预防性放血。联想到当今西医对手术的热充,无不表现出西医对“过剩”、“囤积”的恐惧。 而中国人则恐惧流失,忧心生命能量的消散,堤防元气的消竭。由此也可以看出西方对肌肉的迷恋、对性的放纵和中国对练功的沉迷、对性的节制。
《身体的语言》读后感(一):感受不同是因为认知不同
我理解作者要说的就是古希腊医学和中医的差别来自于认知方式不同,
基于各自语言和文化上的医学知识发展差异也回过来不但影响了人们的思想也影响了人们的感觉和感受。
文字上中国的比喻方式与希腊的明确方式造成的结果是:
切脉的脉是触感与本质的合一,没有也无法区分“什么”与“如何”
脉搏是希腊试图严格区分脉搏现象的定义与感受的结果。尽管开端也是描述性的,直至18世纪简化至计数,一直关注区分事实与观感。
关于色。风。的观念也如是造成了很大的分别。
中医里的‘脏腑”亦非西医解剖观念上明确的各个器官,而是用于储存精气,与身体生病时表现出的现象相对应的的一个概念。
至于作者关于中医里没有也不关注肌肉的说法还是提请中医捍卫者反驳吧,嘿嘿
《身体的语言》读后感(二):谈中西医发展到现状
由本书可以反思当今医学,6星推荐!
我具体谈谈第三部分,中西医的治疗方式。中希医学对“血”和“风”的不同看法。
血
古希腊人对血液过剩的恐惧,并予以预防性放血。联想到当今西医对手术的热充,无不表现出西医对“过剩”、“囤积”的恐惧。
而中国人则恐惧流失,忧心生命能量的消散,堤防元气的消竭。由此也可以看出西方对肌肉的迷恋、对性的放纵和中国对练功的沉迷、对性的节制。
风
西方医学用“pneuma”一词来表示风,从最开始希波克拉底的《论气息》对风向的关注,导出空气流动的受阻即为疾病的成因,到后来风只指代人体内在的气息——也即为后来二元论中灵魂的部分。而中国的风就是疾病的本身,就是外来侵略者,不可测也。
自此,中西医由古到今发展了几千年,由于中西对触摸、文字表述以及观察的侧重点不同,导致了现代中西如此多的差异。
近300多年来,西医以动物为解剖学中心的迅速发展。相对于中医以植物生长意象为望色核心的停济不前以及当代中医盲目跟随西医的步伐,深感叹息!
《身体的语言》读后感(三):《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读书笔记
导读:身体感的历史——李建民
1身体观的历史 研究途径有二:第一,经由文献讨论医学观念的形成与变迁,例如气、阴阳五行、心与气等课题。这些研究可以是思想史或社会史的取径。第二,从图像入手,藉由身体相关的图解来分析医学传统对身体观看的方式。例如对古典医学望诊相法的研究来了解医学论述及其文化脉络。
身体感的历史 (女性感知自己身体的方式是什么?身、心、灵的定义是什么?)
前言
芥川龙之介的故事、滑寿《十四经发挥》、维萨里《人体结构七卷》
问题:P3在医学想象的世界里,什么样的距离区隔了不同的“地区”?我们应如何标定对于身体的不同观点?
主题:P6对于身体的看法不但仰赖于“思考方式”,同时也仰赖于各种感官的作用。
第一部 触摸的方式
第一章 领会生命的语言
中国的切诊脉位,寸关尺,共12种 ;古希腊 脉搏、悸动、“跳动与间歇”、解剖学等(这部分没看懂)
切脉,《内经》《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等,12条动脉。寸尺关对应不同的身体部位,并对应阴阳、天地等。(疾病的空间感)“盈虚静动滑涩”
36:“脉”一字由代表身体部位的“月”部与象征树枝状水流的“ ”组合而成。早期的“脉”字是血部而非肉部——中国第一部字源字典《说文解字》(约于西元100年)对该字的定义为:“血理分衰行体中者。”我们可以想象到流经全身的血流。滑与涩代表了血流的顺畅和迟缓。
把脉与触摸皮肤
希腊医生测量脉搏——跳动和间歇;中国医生诊断脉——脉动,生命的流动。
第二章 文字的表现性
52:如果别人声称他们感受到了他所感受不到的东西,那些人其实可能只是在欺骗自己。也许整套脉搏学即是建立在自我欺骗的基础上,如同国王的新衣。
用于界定脉搏征象的词汇并不具有确定性,每个人对其含义都有不同的理解——脉搏测量简化为计算搏动次数。
57:中国的切诊历史与欧洲不同,从未出现要求明确语汇的呼声,没有对于定义的争论,也不曾怀疑每个人对于语汇的含义认知是否相同。
60:在《脉经》出现的千年之后,即使医生仍然将典籍当中的词汇奉为圭臬,他们还是必须在实际诊疗上能够使用这些词汇;他们必须觉得这些古人所造的词汇明确表达了他们手指的感受,这些词汇对他们来说才会有意义。而他们也的确这么觉得——两千年来皆不曾怀疑过这些古老的词汇。不像欧洲的脉搏测量家为心魔所扰,中国医家并不认为文字带有模糊性。
62:因此“涩脉”究竟为平实的说法或比喻性的说法,便取决于我们认为“涩”存在于脉本身,还是仅仅用来命名脉搏如何对我们显现。……就哲学上而言,客观性质与主观感受之间的界限不但模糊,甚至可能不存在。许多思想家都曾表示,所有的性质——包含砂纸的粗糙以及樱桃的红润——都取决于人类主观的判断。然而,自古以来的脉搏测量家都坚决认为一定要有界限的存在。
64:“脉搏的论述认为对于意义的理解能力取决于想象画面的能力。”P65:“人类无法看见别人的想象。”
古希腊:脉搏的音乐性,节奏。
82_83:(中国的疾病词汇本身就是一个明喻或者隐喻,它们不会受到怀疑和争议,而是不断受到重新定义——那么清代的医学书籍中,对于疾病的描述方法有没有改变呢?从清初至清末,疾病的语言是否从诗意走向自然化理性化?而女性从年轻走向衰老的过程中,所使用的疾病化的语言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87:血气并非经由化学分析而得知的,其中心概念在于个人经验。……“气”的最深层的确定性在于人们对于身体的了解,因为人本身就是身体。……“气”是经由主观感受到的,但从外在也可观察得到。……他(孔子)从“辞气”——语言的“气”——中听出了一个人内心的状态。
第二部 观察的方式
第三章 肌肉与自我认知
解剖学的发展;解剖的动机,《身体部位的用处》;亚里士多德,形式与物质,《论动物部分》,思考大自然目的导向的设计;欣赏造物主对于身体部位的设计,思考肉体和灵魂。
肌肉身体的起源;分节;P121:“生物为长成其最终的形体所需的生长和发展的目的论,即是一种发展分节的过程。”;P127:对于力量、挣扎以及坚实体格的重视,正反映出对其相反者的恐惧。
《空气、水、地方》;P129:清晰可见的关节突显出男性与女性的不同。
肌肉与自主意志的形成,(中国有无相似的对于身体和自我的认知呢?)
第四章 颜色的表现性
143:亚里士多德专注于对于自然的目的予以体现之设计及形体。岐伯则是量测身体以求其量度。
“中国文化传统认为数字证实了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之间的相互呼应,并且概括了世界的规律和秩序。”
150:我们该如何研究由深层组织所构成的身体?
158:望色代表眼睛要努力去看见某种不存在或不清楚的东西。色——脸色;P160:“好色”之“色”为魅惑之物,“望色”之“色”则难以捉摸。道德家要求人们远离前者,医生则被鼓励要仔细研究后者。P165:“失色”不但代表丧失颜色,也代表丧失自我控制。……“再次注意到“色”与言词间的关系,并记住言语的核心并不在于表面上所传达的观念,而在于“辞气”:亦即隐含在言语中的精神。P167:“色”的表现性——反映出内在感受与意向的脸部表情、显示体内五行变化的皮肤色泽。
植物生长,灵魂之“华”
第三部 存在的状态
第五章 血与生命
古希腊和古中国都曾经有过放血疗法——或许是基于人体生理的共通性
古希腊:放掉多余的血液,纾解血液过剩的威胁。
203-204 “虚空”是灵性的最高境界,是自我修养的最高境界;“虚”空也是疾病,病态的虚竭。
205:中国医生所认知到的并不只是相对不均或局部不均,他们想象真正的过度是受外在的影响使然——风、寒冷,或其他邪气。古希腊人所谓血液过剩的充溢起自于身体内在,“实”的充溢则强调外在环境的威胁。
207:欲望代表丧失自我;自我控制的丧失与生命力的流失实同一种疾病的一体两面。另一方面来说,身体的完整性与情感上的自我控制,在健康上是互相连结的。
第六章 风与自我
220:古中国人以及希腊人都认为,吹拂身体的风和维系生命的内在气息有关。
221:问题:一个身体受风的影响如此之大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呢?而古希腊与古中国的医生对于风的影响力所共同持有的看法,如何形成后来完全不同的两种医学传统?
风,风向的改变,变化;P226“风与身体之关系的历史,就是变化与人类之关系的历史。”
241:在中国医学的核心,有种紧张对立的关系,它一方面称颂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之间的相互对应,另一方面又主张身体是独立于风之外的。虽然人类根源于世界,虽然天地间的风与个人的灵魂有互动关系,但身体和周遭的世界却是分立的。
252:从外在的气流到内在的气息;从命运之风不可测知的变化到由内在、自主的自我所造成的改变。希腊人与中国人对于身体的观念都经历过这种巨大转变。但两种传统中对于自主性的定义,则有对于时间的不同看法。
《身体的语言》读后感(四):读后
一位英国批评家曾用如下比喻形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轰轰烈烈的身体转向:“用不了多久,当代批评中的身体就会比滑铁卢战场上的尸体还要多。”[①]如果这个比喻要变得可接受,我们就有理由把“滑铁卢战场”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不只是因为“尸体”的数量已远超过批评家的估计,更是由于研究者早已不再满足于研究欧洲的身体经验和有关身体的叙事,而是追求一种关于身体的跨地域和跨语际的认识论。栗山茂久的名作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以下简称《身体的语言》)[②]就体现了这种努力。
在全书开篇,栗山茂久展现出其旨趣所在:“不同医学传统对于身体的叙述通常有如在描述彼此相异、并且毫不相关的世界。……身体如此基本而且与我们切身相关,为何我们对其理解会有如此大的差异”(第2页)?这里确定了该书的研究进路,即通过分析“关于身体的叙述”来探讨不同文化对身体的认识。作者的目光不在身体如何经验,而在身体如何被经验,以及这些“不同的触摸与观看身体的方式,如何与不同的作为身体(being bodies)的方式产生关联”(第6页)。这部关于身体的历史不仅留意使身体经验得以可能的认识结构,且更关注感官对身体的体验——一种难以经验化、结构化(就是语言化)的风格化的认识途径。这种研究取向既体现在该书题目中难以直译的Expressiveness一词上[③],也体现在该书有意与学院化的写作保持的距离。
该书第一部分以中医和希腊医学中的“脉”与“脉搏”(sphygmos)为对象,分析了触摸身体的两种方式。在希腊医学中,解剖学(anatomy)的发展使得悸动(palmos,“一种模糊、偶发的异相”)与脉搏(sphygmos,“常态生理现象的征象”)得以区分(第17页),医生在心脏、血液和脉搏之间建立了明确的联系,这使盖伦(Galen,129-200)有关脉搏的作品与前人的有关著述相区别。因此,脉搏成为希腊人感知身体的重要手段。而在中国,“脉”指向的不是解剖学下的物质材料,而是一系列生命征象及其图像。脉被认为有十一条(后来是十二条),医者常常用“盈、虚、静、动、滑、涩”(尤其是后两种)来描述各脉的状态,因此中国医家通过诊脉对身体形成的感知往往更加丰富。作者在此进一步强调:“我们研究古人对于人体的观念时,不但是在研究他们的思想结构,也是在研究他们的感官认识”(第46页)。如果前者对应于语言,那么后者则对应于无法被语言所结构和穷尽的“意”(如中医的滑、涩以及希腊医学中触摸者对血管尺寸等要素的想象)[④]。但相较而言,希腊医学仍然对明确性(尤其是对用来形容脉搏的语汇的明确性)和规范性有着一贯的追求,盖伦由此发展出了复杂的形容脉搏的词汇表,其它医家也将可以量化的频率视为感知脉搏的唯一方式[⑤];而中国切诊术的世界则由“一大群稠密、交错、相互关联、互相渗透的感受”构成(第80页),这一套表述是通过颇具修辞意味的、传达文字之“意”的“辞气”来实现知识传递的。也就是说,人对身体的认识不仅建立在“说什么”之上,更与“如何说”有关。
该书第二部分则探讨身体如何被观察。希腊人基于目的论的知识兴趣促进了解剖学的发展——人可以通过理解摹仿(mimesis)的人体来把握人体的形式(idea)。通过解剖学的实践,希腊人认识到身体分节(articulation)的程度在区分“生气蓬勃与濒临死亡的人、成熟的与不成熟的人、独特以及不具个人特色的人、勇敢强壮与胆小怯懦的人、欧洲人与亚洲人、男人与女人”上的重要意义(第130页)。由此,肌肉作为最明显的人体分节得到了希腊医者的重视。而在古代中国,对人体的观察则更多集中于“色”,即人的表情、脸色。医者一般结合有关五脏和经脉的理论推断人的健康状况,更重要的,人的欲望与德性,这根据的是传统中国基于色彩之分类的宇宙论和政治文化。如果说以动物为中心的希腊解剖学将人的图像动物化,那么在提倡“望色”的古代中国,人更近于植物——具有颜色且经过培养可以成材:“人类与植物的相似性不只是在于‘静态生长’(vegetative)的过程——例如成长与吸收养分——而是在于道德发展,经由道德的培养(grow)而成为人”(第172页)。在此,栗山茂久将分析进一步扩展至对中、希文化的对比上,“肌肉和望色之间令人不解的差异”显然只有小部分与生理学或医学经验的差异有关,差异更根源于不同文化中个体“对自己之存在的看法”(第173页)。也就是说,对这种根本性差异的呈现不再像前文那样仰赖于语义分析,而是企图在中、希在思维方式上建立比较,这提示了本书第三部分的分析重点。
然而比较中亦存在着相同(这是比较成立的基本条件),即希腊与中国的医生都将血(blood)和气(breath)视为生命力的来源。那么以上分析的问题就在于,“这种将血和气视为生命泉源的相同看法,如何能够和分别视肌肉与色为生命表征的相异看法共存呢”(第173-174页)?作者在第三章分析了血和气在中、希医学中的位置。希腊人常使用放血疗法,而中国医生几乎很少为病人放血,这里差异的原因在于,希腊人恐惧的是血的过剩,而中国人恐惧的是血的不足(“虚”)。“对囤积与过剩之忧虑”和“对流失与欠缺之恐惧”(第212页)分别建立在人对自我存在本身(the body ‘s self)的两种理解上。同样,中、希对于“气”(也就是风)的理解也几乎完全不同。在中国文化中虽然存在一套将宏观宇宙和微观宇宙(人)进行的对应的图示,但来自宏观宇宙的风仍被人视为外在的、入侵性的、威胁性的;而在希腊文化中,风则更多与内在力量(或性格和灵魂)联系在一起。对于血和气的不同看法,实际上反映了两种对生命本身的认识:“中国养生人像的满实来自于避免生命力因外流而损耗、抗拒精力与时间的流逝。而肌肉人像的自主性则来自于自主行动的能力,以及由意志独立造成、不受自然或极运影响的变化。”一是抗拒外物、保持精力而近乎静止和无为的,另一是自主的、不断运动和追求控制的,这即是栗山茂久在语言之外发现的两种文化更为根本的差异。
这部作品实际上有两个脉络。其一是对“身体如何被经验”的分析。作者首先分析身体作为客体如何被感知(观察和触摸),然后分析主体根据何种思维模式来认识身体(血和气),也就是主体如何将自身客体化。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两部分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也就是缺少了处于社会中的个人如何将社会认知内化于自身的过程,脉(脉搏)、色(肌肉)与血、气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仍是未知的。也就是说,这一脉络下本书的论述存在两个矛盾,一是作者已经意识到但未解决的,即既然血和气在东西方皆被视为生命泉源,那么对于生命表征的相异看法(色、肌肉)和不同的观察方式(脉、脉搏)是分别如何从各自的血气观中产生的呢?作者在本书第三部分是用对宇宙论或社会认识的探讨,事实上遮蔽了对经验身体之方式的发生学探讨。二是作者或许未意识到的,即在两个文化中,血、气与脉(脉搏)、色(肌肉)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作者分别梳理了它们的形成过程,而通过将它们视为“经验身体的方式”和“作为身体(being bodies)的方式”切断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这些联系可能意味着更复杂的知识谱系和权力关系。
这本书的第二个脉络是梳理中、西之间不同的文化风格和思维模式,然而这一分析过于注重结构性的考察,而忽视了历史性的考察。作者时常将跨越数百年的材料并置而论(典型如第四章),造成了许多事实上的误解[⑥]。但我并不想(也并不能举出其中更多错误)以此贬损该书的价值,对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更不用提这是一本跨语际的比较研究)而言,结构性的分析或许远比迷失在重重地层中的琐碎历史分析更加有效。或许,当作者选择以此为题时,就认识到这项研究可能遭到历史系研究者基于史料的种种批评,但仍然选择了此种结构性的分析方式,因此也成就了这本名著[⑦]。
再或许,我们似乎有理由不那么严肃地阅读和分析该书,不只是因为它在风格上刻意与学术流水线产品保持了距离,而在于它本身就是抒情的:“比较研究身体认知的历史,迫使我们不断检视我们认知与感受的习惯,并且加以想象不同的存在方式——以全新的方式体验世界”(第256页)。如果阅读该书能够打开我们审美体验,激发当代人对于“身体的语言”的全新想象——在一个如此缺乏历史想象力的时代,那么作者的目的或许就达到了。
[①] 见《身体工作》,收入特里·伊格尔顿著,马海良译:《历史中的政治、哲学与爱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99页。
[②] Shigehisa Kuriyama: 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9.中译本参栗山茂久著,陈信宏 张轩辞译,张轩辞校:《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以下引用中译本时随文标出页码,不再出注。
[③] 正如一位评论者指出的:“身体的表现性(expressiveness) 这个词汇尝试要捕捉语言与感觉间的特殊关系。 栗山茂久说表现性是藉自声调加诸说话的,不论我们的言辞是大或小声,温和、嘲笑或阴沉平静或激动 。 感觉的文化风格(culture styles)给予身体经验一种语词 。”见费侠莉著,蒋竹山译:《再现与感知——身体史研究的两种取向》,《新史学》(台北)第10卷第4期,1999年,第137页。
[④] 同样来自这位评论者:“栗山茂久提到一个最后的秘密,生命的存在在于它对感觉是可触知的,但最终仍捉摸不住。……东山茂久则反对言辞……他听起来则像庄子。” 见费侠莉著,蒋竹山译:《再现与感知——身体史研究的两种取向》,第138页。
[⑤] 这里不难联想到数学在柏拉图“线段之喻”中的位置以及据说悬挂在学院( academus)门口的“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
[⑥] 参李建民:《比较医学史的再思考》,《历史研究》,2015年第02期。
[⑦] 比较福柯的结构分析作品《疯癫与文明》在史料上遭受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