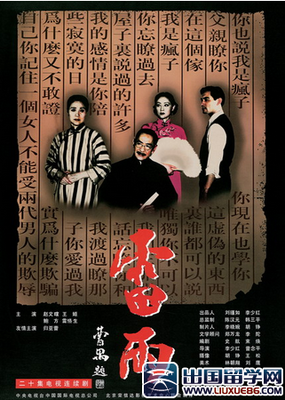
《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一本由[美] 魏斐德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30元,页数:2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门口的陌生人》精选点评:
●也还行,现在看来
●新档案;新理论;新的比较视角(”造就西西里黑手党的原因,也同样造就了三合会……)。了不起的作品。
●讲政府、士绅与民众的关系。士绅如何靠团练崛起,逼出革命。
●出口贸易为主的广东省在两次鸦片战争社会阶层和矛盾的转移和变化,左右为难的清政府一方面镇压革命叛乱,一方面打压夷人
●终于搞清楚起义的烈火为什么会在广东而不是其他地方点燃了,考证有力,功夫不错
●415
●补标
●这套书终于重印了。魏斐德因为来中国的次数多,和中国学人的关系好,已然成了偶像派,不过,再怎么说也比不上我心仪的实力派孔飞力。
●过目已忘
●魏老师总能展现出文学家的敏锐
《大门口的陌生人》读后感(一):历史的陪葬
中国加入世贸,便可以把产品卖给全世界。150年前,英国是世界工厂,也想把产品卖给全世界,可是中国只在大门上开了一条缝,还动辄把门关上。更有甚者,英国的产品中国人不买,中国的产品,丝绸、瓷器、茶叶,却卖给英国一大堆。英国人没办法,开始卖鸦片,平衡贸易逆差。
列宁说,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就是帝国主义。看得真透彻。因为社会生产越来越多,但需求却跟不上,只能国际扩张。要扩张,自然要武力护驾。所以归根结底,经济是目的,军事是手段。
如此看来,当代世界进步太多。有贸易纠纷,大家坐下来谈判,即使吹胡子瞪眼,至少不用兵戎相见。
只是这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却将亿万民众碾轧而过。“兴,百姓苦;亡,百姓苦”。150年前的华南,那些潮热的夏天,官员、土匪、乡民、洋人,也裹挟在这洪流中,为历史陪葬。
《大门口的陌生人》读后感(二):简要记录
作者认为太平军思想来源是儒家公羊学派;广东地方史,选了四个代表事件来讲,三元里、反进城、地方叛乱、被占领;loot,洗劫,印度词源,用在三元里;三元里的胜利是被构造的;对“民”的迷信,中国士大夫神秘方面;失败后,官员求助于迷信技能;保甲并非常态,到了鸦片战争前实行,为禁鸦片,阻止白银外流;论过鸦片合法化;道德主义者占上风;勇和团练,绅士,民众如何武装起来;广东的商业结构与商人;判定、捕杀汉奸,该词来源;蛮夷好利、好色,未以人视之;广东的始原倾向;广东的社学,治理地方事务办团练的绅士联合;钱江;密切尔报告及英国商人政府对华贸易看法不同,英人要求进城,立威;广东排洋;已有传单;广州居民与洋人摩擦多年,还有战争;黄竹岐事件与耆英去职;贸易对中国影响大,失业问题;宗族既是团结又是分裂;江西宗族斗争绅士不参与,广东斗争族长自发动;
《大门口的陌生人》读后感(三):《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摘记
1、排外普遍存在,这和民族主义不同,在《叫魂》中也是如此。
2、正规组织力量崩溃,在防御外敌、叛乱、维持地方秩序时无能为力。士绅组织的地方武装力量起到了拯救帝国的作用。士绅没有反叛,而是站到了帝国的一边。当然集权受到很大冲击,地方获得较大权力。地方自治并不是帝国后期崩溃的原因,帝国崩溃是因为朝廷的不作为,或胡乱作为,如甲午战争、延迟的立宪。和其他朝代一样,中兴可能存在,中兴可能意味着地方权力崛起,但地方自治并不会独立、反叛。
3、这一次皇权的崩溃没有引起以往王朝更迭时的社会秩序崩溃,原因是西方力量的存在。
4、士绅的组织在太平天国时期扮演了最后一次角色,之后不再是组织中国精英的力量了,因为对外开放,原有秩序没有吸引力了。而新的组织还在稚嫩的发育中。这给了法德起源、俄国突变的超强感染率超强杀伤率病毒以机会。
《大门口的陌生人》读后感(四):大门口的众生相
尽管本书主标题为“大门口的陌生人”,但通读后会发现,副标题“ 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才更贴近全书的主要内容。
发生于19世纪50、6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长河的分水线”,该如何认识呢?无疑,“了解这次叛乱时了解中国近代史的首要条件”。为了探求根源,“必须在时间上向后退,在空间上向东方转,回到那一争斗和混乱的熔炉中去”,也就是本书述论的“鸦片战争以后需的头二十年的广东”。“作为中国人与欧洲人交往的地点”,广州、广东、华南——称为分析的历史单位。尽管出发点是为了“研究太平天国的根源”,于是乎导出了“另一种研究”,即“地方史的研究”。恰如书中所揭示的,“在这些苦心经营的商人及行政机构的周围,还有着更广大的南中国社会,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也在酝酿发酵中,文人为中国军队的无能而烦躁,地主组织团练,佃户参加秘密社团,各个家族为争夺当地的财富与势力互相争斗。简而言之,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
《大门口的陌生人》读后感(五):大门口的众生相
尽管本书主标题为“大门口的陌生人”,但通读后会发现,副标题“ 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才更贴近全书的主要内容。
发生于19世纪50、6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长河的分水线”,该如何认识呢?无疑,“了解这次叛乱时了解中国近代史的首要条件”。为了探求根源,“必须在时间上向后退,在空间上向东方转,回到那一争斗和混乱的熔炉中去”,也就是本书述论的“鸦片战争以后需的头二十年的广东”。“作为中国人与欧洲人交往的地点”,广州、广东、华南——称为分析的历史单位。尽管出发点是为了“研究太平天国的根源”,于是乎导出了“另一种研究”,即“地方史的研究”。恰如书中所揭示的,“在这些苦心经营的商人及行政机构的周围,还有着更广大的南中国社会,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也在酝酿发酵中,文人为中国军队的无能而烦躁,地主组织团练,佃户参加秘密社团,各个家族为争夺当地的财富与势力互相争斗。简而言之,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