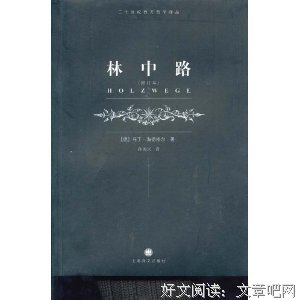
《林中路》是一本由[德] 马丁·海德格尔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4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林中路》精选点评:
●浑然,自成一个世界,几乎无破绽
●读了《世界图像的时代》一篇,简单说来就是工具理性对人类无形的戕害。但是海德格尔的细腻确实让我非常惊讶。
●早些年阅读的,读起来轻快,气氛不凝重
●读过《艺术作品的起源》,艺术与真理有关,而非流行文化的附庸。美因为艺术完成了世界与大地的争执而随真理之际产生。虽然读的艰难,但有收获。
●海德格尔的转变对于西方来说太重要了
●集结了后期海德格尔的几篇重量级著作,前两篇(《艺术作品的本源》、《世界图像的时代》)尤为重要。虽然论题有所不同,但贯穿所有这些作品的是一条共同的主线:形而上学的本质是对存在与存在者之存在论差异的遗忘,是将存在理解为存在者(尽管是最高意义上的存在者)。这种遗忘在近代早期随着世界成为意识的表象对象、普遍主体被解释为面对表象而立的我思意义上的心灵,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随之而来的是存在者的存在被等同于其价值,因此,试图以强力意志为源头而“重估一切价值”的尼采形而上学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并且是它的顶峰。面对着这种虚无主义的危险,海德格尔呼唤形而上学概念化之前的存在,即自我保存和绽出者,并在荷尔德林和里尔克的诗中阐发出了一种“世界黑夜”(同时也是科学的白夜)中的歌声。
●完全看不懂
●满打满算终于看完了 ,比较轻松好东西
●海氏的初衷其实就是,在这个贫困的时代,哲人何为?
●再一次装逼未遂。。。咱能别德文 希腊文 和不是人话的中文一起上不。。。
《林中路》读后感(一):值得吗?至少很愉快。
当初因为考研的关系,终究是只读了一小部分,序言啊,存在啊,对艺术和诗的本质的沉思啊~主要可见于本书中的《艺术作品的本源》和《诗人何为?》~也是那句“通向语言的途中,歌唱命名着大地”使我一下意识到语言,或者说语义学的意义,对于艺术和创作的意义。03年之前我像一个完全没有写过自己文字的人,即使后来尝试写的文字也是相当青涩,但是在那样一种开始和摸索中,也算自觉到了一些文化的意趣,而这种探索终究是多么的辛苦,值得吗?至少很愉快。林中多歧路,而殊途同归,作为一个林中人,探索过的道路自然也别有风景。
这种精神多少是与哲学思考方式有着些些的相似点的,恐怕也是我相当喜欢哲学书的原因之一。人们都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东西。而不止是自恋的人才喜欢类我的。
我想看看,一直喜爱读书的我,会不会越来越幸福。喜爱思考的我,人示会越来越幸福。只是要思考为什么不彻底些,想出名堂来,喜欢想太多而不擅于执着深入思考的人,大概就是尔等凡夫俗子。恩,我承认我俗,跟生活讲和。
《林中路》读后感(二):林中的守林员
对于海德格尔,哲学史重要的,在他的大部分著作里,他只写哲学上的问题。对于海德格尔,哲学不是职业,哲学是一种生活,一种沉思的生活,这或许就是他与众多学院哲学家的分歧所在。海德格尔曾经激烈反对学院哲学,或是哲学的学院化,他认为让伟大的思想被学者们整理、总结与教授是对哲学可恨的控制,也是对哲学之本质——思的背叛。
哲学史几乎是海德格尔所有思考的园地,《林中路》是海德格尔晚年的作品,他早已放弃了对行动的现实世界的干预,专注于哲学。(或者说海德格尔从未离开哲学,他担任柏林大学的校长时仍是专注于哲学的发扬与振兴)哲学史是由一系列的哲学家与其哲学言论构成的,对于海德格尔,哲学史就像一个哲学家的家园,他和其他哲学家生活在这里,而其他的人类生活在自己的社会里。海德格尔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林中的守林人,这片林就是哲学史,而守林人在其中看管树木,与树木们交流,寻找前人走过的小路,探明这些小路的脉络。
由于海德格尔的超越性,他认为存在是一切哲学家们思考的园地,但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他们在这园地里思想。这样的观念使得海德格尔有一种高于哲学史的眼光与气魄,使得所有的哲学家都在他哲学的看照之下,因此海德格尔的思想就是在存在的基础上对以往的哲学思想作自己的解释,同时为可能的新的超越以往哲学的新哲学建立基础。从其思想的反应来说,能够接受并能继续的哲学家还未能出现,而新的哲学似乎要等到历史改变给人们以充分的启示时才能自然的显现。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他的工作很明确,他的生命很充实,很美丽。
一个从头到脚的哲学家——海德格尔
《林中路》读后感(三):关于《艺术作品的本源》的一些思考
从海德格尔起,历史中个人生存开始成为哲学关注的焦点。“存在”是海德格尔提出的重要概念,人如何在现实中确立自身的存在?如何确定知识的来源?我理解的海德格尔,继承了胡塞尔、又打破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二元论。现象学强调知识的确定性来源,以科学的方式解释人类意志,通过“存在悬置”与“历史悬置”直面事物本身,借以揭示意识自身的结构、揭示现象本身。现象学要做的事情是,将外在世界还原,将一切实际事物按其呈现于我们心中的面貌而作为“纯”的现象来对待。胡塞尔看起来抽象、玄虚,实际上是回到具体、回到坚固的基础。但海德格尔不承认主客二体,不是先有一个主体、一个客体,再有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相反,是先有了主体与客体的存在关系,才有了认识,因此,人是通过感觉去把握事物的,人是被抛入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世界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本身。这是建立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之前,海氏关于存在主义的建构,即认为存在是一种有意义的生存,充满诗意趋向崇高的生存。关于艺术作品本源的追思,亦为海德格尔探讨“存在”之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的一环,是海氏基于存在主义给出的一条理解艺术、艺术作品与艺术创作过程的路径。
一、何为物之所在
海氏在《本源》中对物提出了三种解释:物是若干特征的集合、物是感官上被给予多样性的统一体、物是具有形式的质料。着重讲一下海德格尔关于第三点——物是具有形式的质料的探讨的理解。
海氏首先提出,形式是理性的,质料是非理性的,对于形式与质料二者的变式,即所有艺术理论和美学的概念图式。除此之外,形式-质料结构规定了器具的所在。而器具是处于物与艺术作品的中间样态,器具的出现,同时引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有用性。一旦“有用性”的概念出现,人的因素便不可避免的混杂在了物的因素中,是人之所需才确定了物之所是,由此,排除了有用性和制作特性的“纯然物”便受到了遮蔽。
回到对物的第一重理解,物是若干特征的集合。海追溯了古希腊语言传统,物的内核(基体、基底)在语言的更新化过程中被翻译混淆了经验,是为主体(主语);物的特征是为属性(谓语)。由什么定义和衡量属性?必然是以人的认知为尺度。因此,理性再次压倒了物,是为遮蔽。
在此,海氏提出,我们无法确定感官上被给予的是物本身的现身在场,因为物与我们之间往往有所混杂,即遮蔽。但我们习惯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去思考一切存在者,这种先入之见始终如有色眼镜一般影响着对本源与世界的探究过程。他对物的本质的重视、对“去蔽”的强烈需求,正说明他以哲学家的身份对现实作出的切实关怀。在马尔库塞提出的单向度社会中,即使是科技水平远不如当下的二十世纪,哲学家锐利的目光已经发觉技术理性对纯然物的强暴。在原始社会中,器具与有用性的概念联结在一起,而工业时代和资本文明介入以后,科技与理性成为有用性这一概念的合理外延。海德格尔由对物的概念的溯源,警觉地指出了这一点,物与存在相关,只需使用和制造,无需追问存在,也就丧失了精神层面的思索的动力,生活便走向干瘪与匮乏。在人把一切物作为器具的倾向(亦为科技的倾向时),物成为人所执行的客体,人也有将自己作为器具的倾向,在此,我们需要艺术的存在,人需要从日常走入艺术的创作性世界,重新找回与纯然的物打交道的方式,在“悲剧性”的人生体验(“他人即地狱”)中寻求交流和对话。
二、大地、世界与作品
从对物的关怀出发,海氏转向对“作品”的关切。他是悲观的。和被强暴的物一样,作品更多是作为艺术行业的对象,埋没在艺术交易和艺术史研究的繁忙中,来满足公众和个人的艺术享受,在不断的移置中,作品远离了自身的世界。在此,海氏提出了“大地”的概念。大地,是一切涌现者的返身隐匿之所,它为涌现者提供庇护,是其赖以筑居的所在。并讨论了作品之作品的存在——作品的建立是一种奉献着、赞美着的树立。作品之为作品所建立的,就是开启出一个世界,并在运作中永远守持这个世界。《周易》有言:“观物取象。”中国古代的艺术反映论思想也认为,人们用“象”反映世界,如乡饮酒礼中的“礼”,以宾主坐序象征宇宙秩序,而这个“观”和“取”的过程,即作品的建立过程。关于海氏提出的“世界”,我的理解是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境”有所相似,境生于象外,创造主体与欣赏主体,他们的有限存在,都向着无限展开,从而使自己得以融入一种超验的形而上境界,甚至获得具有生命本体意义的真正超越。
海德格尔说,世界与大地是一种争执关系。由于作品建立一个世界并制造大地,作品就是这种争执的诱因。我的理解是,所有的人类文明,包括艺术作品,都是从大地上生发,其质料也源于大地。大地作为人类世界的基础,具有吞噬世界的倾向,让世界回归大地,而作品经久地在不同时代触发新的意义,就使得世界从大地中将自己挣脱出来。
而在艺术与大地的关系中,海德格尔谈到了真理的获得方式:去蔽。艺术作品呈现自身的方式,就是通过去掉来自大地的质料中多余的部分。去蔽的过程就像剪纸,剪纸的生成就是在一张纸上减去多余的部分,而真理,在剪纸的过程亦艺术创作的过程中的作用,是决定哪些部分分离,哪些部分留下。例如,雕塑产生于石或木,诗产生于无数的词,绘画产生于各种颜色,音乐产生于无数的音符。最后,他总结道,艺术是对作品中真理的创作性保存,艺术就是真理的生成和发生。
关于艺术本源的探寻,是海氏基于存在主义给出的一条理解艺术、艺术作品与艺术创作过程的路径。
《林中路》读后感(四):《艺术作品的起源》读书笔记
【原文写于2015年11月,给冯师的读书报告+读书会】
十一月一日读书会的消息很早就收到了,于是借这次机会重新研读了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有许多新的理解。海德格尔是借由此篇文章中借由艺术作品的本源而对他自己真理观的集中阐述,之所以选择艺术作品作为切入点,则是因为纯粹的艺术是一种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建构,是富于概念、集合、抽象和统筹等于一身的具有西方形而上学思维的本质性体现,我们称之为艺术之为艺术的本性。在我的理解中,这里所说的"艺术"似乎具有一种先验的立法,它先验地包含了"世界"和"大地"这两个海德格尔在探寻艺术本源时的两个最大的隐喻。在此,艺术最大的包孕性和无限性正是在"世界"与"大地"的关系中得以展现。
在论及艺术作品的本源时,海德格尔并未直接从艺术作品入手,而是首先论及了艺术家与作品的关系——"艺术家是作品的本源。作品是艺术家的本源。"这是非常清楚且不证自明的,然而正是在艺术家和作品中间,存在着一个第三者,即艺术。海氏在一开篇就说道:"无论怎样做出决断,关于艺术作品之本源的问题都势必成为艺术之本质的问题。"然而在之后的论述中,他也并未跳出这一怪圈,因为在阅读后我们也能够得到一个粗浅的结论——艺术的本质就是真理的无蔽与敞开。海氏先由物入手,梳理了物(即自然物)、器具以及艺术作品三者的关系:"物"是自然物,即处于自然中、外在于人的客观的物;"器具"乃是人化了的自然物,即经过人的改造从而具有了有用性的自然物;而"艺术作品"则是消解了器具的有用性从而建立起一个世界的存在。在对这三者的梳理中,还是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作品中发挥作用的是真理。。。乃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也即,他对艺术本源的追问实质上亦是对真理的拷问,是对真理以何种方式进入艺术的拷问。
首先,在这里需要区分一下对真理的几种理解:一是传统意义上,即自古希腊以来总体论逻辑判断与命题意义上的"真理",这种"真理"可看作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与认识对象的符合,是"是"与"所是"的一致,即判断与对象的相符合。而海氏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却竭力反对以正确性作为真理的判断标准,同时他也打破了自笛卡尔以来以确定性作为真理出发点的传统。在他看来,真理乃是存在者之真理,是"存在者的无蔽状态",是存在者自身的显现。而正是在这种"无蔽状态"中,真理具有了敞开、澄明、绽出等特性。
真理具有敞开性,而存在者就存在于这种敞开领域之中。海氏以他强有力的逻辑论证试图向我们证实"真理是非真理",这句话乍一看上去有些荒谬,但读到海德格尔关于真理存在状态的解释,疑惑便一下子解开。真理只为真理,现身于敞开与遮蔽的争执之中。其一,这种敞开是一种"置立"。"置立"一词本身就意味着真理是一种"本有",它先验地存在于世界中,存在于敞开与遮蔽的夹缝中无法容身,而艺术作品作为存在者,它的敞开性则为真理的"置立"提供了场所的可能。这种"置立"却并非艺术作品将真理拉进某个领域中,而是真理自发地于艺术作品的敞开领地中显现出来,也即海氏所说的"自行设置入作品"。既然"置立"内含了真理对自身自发性的设立,那么就断绝了真理中静止、刻板的"固",生发出"敞开"的第二个内涵——生成性。正因真理无时无刻不处于被遮蔽的大地和渐显澄明的世界的争执中,这一处境则使真理本身成为一种争执的、开放的、非固定的形态。处于遮蔽与澄明两端的真理因而不断地摆动于敞开领域中,也即海氏所说的"当且仅当真理把它自身设立在它的敞开领域中,真理才是它所是,也即是这种敞开性。"因此,艺术作品中的真理实际上是真理在无蔽领域中的建立,这也正是艺术作品区别于器具之处——艺术作品具有开放性,在他被创作之初真理就自行置立于其中,使它能够本质性地开启自身,使艺术作品成为一个自持的存在者存在于敞开着的世界之中。敞开同样意指着真理寓于作品中而没有设限,并且它本身摆脱了所有界限,从而融入进无限中(但这样的融入并未化为空洞的虚无)并且兑现为敞开着的整体。
真理也具有澄明的特点,尽管它处于被遮蔽和敞开的争执领地中,但正是在这种争执之中,真理得以显现出其自身。在艺术作品中,作品作为被创作存在的道说,亦即真理的逐渐显露和揭示的过程,这一过程使真理处于无蔽状态中。尽管某时某刻艺术中的真理被遮蔽了,但这种遮蔽却是短暂的、不长久的,真理最终将走向澄明。海氏在文中写道:"作品本身越是纯粹进入存在者由它自身开启出来的敞开性中,作品就越容易把我们移入这种敞开性中,并同时把我们移出寻常平庸。"这意味着作品之存在通常与人之理解相违背与背离,本真的作品、作品中作为本有的真理原本就意味着艰涩、难解及与世界的格格不入。而正是这种艰涩难解,给予了作品以敞开性,使艺术成为了处于人与作品中的互动性存在。
真理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绽出性,这意味着它同时具有敞开性和瞬间性两种特点。作品置身于作品中生发出的存在者的敞开行中,则意味着一种主动性,但这种主动性并不以它自身为目的。他带给人的始终是一种指向而不是结果,它带给人的是一种具有持续不断敞开意义的启示而不是固化为一个具体启示的存在着。因此这种启示实际上就是一种瞬间性的绽放和澄明。人对艺术作品的观赏,正是对这种瞬间性赢得本真自我的契机的把握,在这时,真理只能赤裸裸地面对自身,在瞬间性中把自己带到人面前。
然而关于真理如何在作品中显现,海德格尔提出了一对概念——"世界"与"大地"。在海氏那里,"世界"并非是一种对象,而是指人身处其中的世界,而艺术作品的存在,就是要建立起这样一个世界。世界是敞开的、公开的,作品中的世界即意味着作品中能够进行广袤设置的空间,意味着一种敞开领域只自由与在其结构中设置这种自由。这里或许能够将"世界"理解为艺术作品之为艺术作品其内涵的无限扩张性和无限生发性,它能够融入这种敞开的世界中并作为敞开者的整体而存在。而"大地",在海德格尔那里现身为作品的回归处,也即作品在这种向自身的回归中,使大地作为大地显现出来。大地是庇护的、闭锁的,作品中的尚未被揭示、未被解释的东西只有被包覆在大地的怀抱中,并以它本身的样子存在着、被感知,它才能够显示成为自身。闭锁着的大地是使艺术之敞开领地澄明的前提——"只有当大地作为本质上不可展开的东西被保持和保护之际,大地才敞开地澄亮了,才作为大地本身地显现出来。"在这里也许能够将"大地"理解为艺术的载体或其外在表现形式,吸收了作品的质料因素而使质料在作品之为作品的特性中已经不那么重要,它使在世界中游离、动荡不安的东西宁静下来。
quot;世界"与"大地"的关系如同矛盾的双方在不断争执对立着,但同时又相依为命、是使对方成其为自身的前提,正是在"世界"与"大地"的争执中,它们二者得以进入本质的自我确立。在这里,艺术作品的被创作存在成为"世界"与"大地"关系的一个契机——"作品建立起一个世界,并制造着大地。"在这里,大地的归属性、庇护性和世界的敞开性、生成性使它们二者成为矛盾的双方,也即使它们陷入"争执"这一存在的基本状态中去。因此,作品的本身形态亦是出于不断的争执与被拉扯中。作品的被创作存在将真理固定于这样一种争执的形态中,而这种争执也可看作是敞开的前提,正因为争执为真理的生发提供了诸多可能性,而又使其不至于在纷繁复杂中趋于飘渺虚无。
因而海德格尔在文章的最后得出"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的结论。我想这里的"诗"所指大概不是一种文学体裁,而是指代"诗性"一词,即"所有的艺术本质上都具有诗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诗(悲剧)是一种蕴含真理、表现真理的体裁,按照海氏的解释,也可理解为一切艺术都具有诗性,都是使真理之敞开于无蔽状态的存在,也即凡是能使真理处于无蔽状态的存在都是"诗"。首先在这里,海氏借用了"诗"这一实体题材来说明。因为诗歌在语言中发生,因而语言保存着诗的原始本质,存在者之澄明正是在语言中不知不觉地发生的。语言铸就的艺术作品之所以区别于音乐、建筑和绘画等,就是因为语言是能够生发的,语言永远处于一种未完成而有待完成的状态,而音乐、建筑和绘画等在其作品完成之时,他们就处于依然完成的状态,讲述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事。这也是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着之澄明早已不知不觉地在语言中发生了"的原因。此外,海氏还认为之所以所有艺术的本质都是诗,是因为自古希腊以来就有诗之本质就是真理的生发于创建这样说法。并且由此,海氏总结了"创建"的三层含义。首先是作为赠与的创建,他在这里将真理在艺术作品中的自行设置看作是真理将自身的赠予,这也正是艺术作品区别于器具最大的一点——真正的艺术缺乏有用性,它的敞开性、可生发性都是以其有用性的不在场为前提的,也正因此,艺术应具有虚构、想象等特点,同作为文学体裁的"诗"相区别开来。其次是作为建基的创建,也即真理向艺术作品的置入既是一种历史性的开启,同时也是在大地这一基础上的建立。作品一旦被创作出来,便被投入了保存者的怀抱,被自行锁闭、被遮蔽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丧失了被开启的可能。大地是首先作为基始而存在的,有了大地这个基础,艺术创作就并非完全依靠作者的个人虚构、想象和凭空捏造,而是具有了一定的现实依据和基础。第三是作为开端的创建,开端即意味着作品中未曾展开但即将展开的无限丰富性。作为开端的创建是真理之争执的引发意义上的创建,它意味着无限包容性和可能性,包括了无限被解释和生发的可能性。每当艺术发生、作为一种开端的创建进入历史时,它也就进入了一种生发的状态中,因此艺术的历史性同时也意味着生发的无限可能。
因此总体而言,海德格尔将艺术作品的本源归于艺术,而将艺术的本源归于真理的无蔽与敞开。在海氏那里,他更强调将艺术看作是真理生发的一种事件和过程,是真理突入其中从而进入历史性存在的一种途径。
《林中路》读后感(五):谁之栖居,大地何为
(一)
电影Life of Pi讲了Pi的两个故事(或两重人生),一个明亮励志,呈现得美轮美奂;另一个恐怖,邪恶,在黑暗中隐而不显。影片抛出的问题是:你会选哪一个?当片中作家选择第一个故事时,Pi说:And so it goes with God.
既然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至善者,那恶一定不是实实在在的被造物。恶是善或存在的缺失,是否定性,是光亮中的阴影,是虚无。奥古斯丁的这一处理,把恶的实存性从我们的宇宙中一笔勾销。否定性或者非存在,是不该被正视、升华、扬弃的,而应被忽视、贬低和驱逐。
在另一个传统上,当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问题转换成:人是什么?这个二人称向三人称的变化,预设了一个关于“什么”的客观世界,人被包括在其中。这个世界由诸多的客体组成,它们有固定的本性或本质,这些本性本质规定了它们在世界中的等级序列里的位置。人不过是诸多客体之一。世界的秩序来自理性的裁定,是合乎逻辑完满无缺的。那些否定的,片断的,阴暗的,非理性的,在这个世界中是没有位置的。有关人的经验,如焦虑,恐惧,操心,孤独,或者那些令人毛骨悚然,但对人性命攸关的经历,并不重要。
问题在于,“思想”认为无关紧要的,对于“我”来说可能至关重要;否定性对于我,这个正在感悟世界的主体,也许是最大的实在。奥古斯丁说,病痛是健康组织的缺失,不是实在,但我所忍受的痛苦,却是真真切切。黑暗是光明的缺失,对于失明的我来说,却可能因此心烦意乱,恐惧焦虑。否定性从外面观察,是没有意义的虚无;从内部体验,则是生命中的实在实存(或非存在)。这里的鸿沟,就是存在者与存在的差异。千百年来,思想家们教会我们关注前者,而遗忘了后者。
回到存在,我们就会发现无处不在的否定性。人的存在中一直有“不”或“无”的在。对人来说,最终极的否定就是死亡。死是不存在,“我”的死亡是“确知而未定的”“最本己的又不可逾越的可能性”。它不是一个确定的终点,在路的尽头等着我,而是弥漫在我的存在之中。从我被抛入此生此世,就带着这不可逾越的可能性,在与不在交织在一起,肯定和否定贯穿于我的整个存在。面对在存在中展开的非存在,我陷入“畏”。畏不是害怕某个具体的对象,畏之所畏者,是在世本身,是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是对无意义的焦虑。在畏中,我们面对的是终极的虚无。
(二)
传统上,真理是命题与对象的符合。海德格尔认为这个还不够根本,应该有个更深的基础:一个敞开的去除遮蔽的场域,在这里对象对我自行显现,我对对象开放。两者同时置于开敞之中,知识与对象才可能相关,从而有所陈述。所以最原初的真理就是去除遮蔽。
除去遮蔽,让真理之光照进来,这一块光亮之地,就是我的世界。世界是我所遭遇的物或他人向我开敞,可以被我理解(intelligible)的域。我被抛入这个文化的历史的遗产造就的场域,在其中面向未来谋划,展开我的人生此在。
但是,真理为存在者除蔽,只能把具体的个别的存在者带到无蔽之下,存在者的整体还会在遮蔽之中。茫茫黑夜的一盏孤灯,只能照亮一小片,大多地方还在黑暗笼罩中。茂密的森林,阳光偶尔洒向几块林间空地,大部分还在阴森晦暗之中。人类的真理,就好比这孤灯或林间空地,敞亮澄明是局部的、零星的,黑暗才是整体的。海德格尔把这种黑暗称为“神秘”(geheimnis),就是非真理,被遮蔽的状态。
非真不是因为我们对存在者的知识不充足,不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够发达,而是一种比任何真理更为原初的状态。先有遮蔽,后有解蔽,先有隐,后有显,存在者整体的遮蔽是更加本源的存在,甚至比存在本身更加原始。Geheimnis的词根heim意为“家”,神秘的不可理解不可说的东西是我们的家,是我们存在的根。
在柏拉图的洞穴中,被缚之人转向光明,找到真理。这正说明,黑暗的洞穴,是人类更古老的家园。洞穴里第一次获释的人不习惯于火光而转向阴影,因为此前被缚之处的阴暗反而更适合于他们的眼睛。
思的对象,该是这神秘幽微的黑暗本身,而不是象柏拉图传统那样力图把一切都带到光明之下。解蔽或澄明,是为了衬托出黑暗;寻求真理,是为了通过显现来接近或达致对遮蔽的领悟。
“我们冷静地承认:思想的基本原则的源泉、确立这个原则的思想场所,这个场所和它的场所性的本质,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讲都还裹藏在黑暗之中。这种黑暗或许在任何时代都参与到所有的思想中去。人无法摆脱它。相反,人必须认识到这种黑暗的必然性而且努力去消除这样一种偏见,即认为这种黑暗的主宰应该被摧毁掉。”
黑暗是我们能理解世界的背景和基础。基于背景和阴影,我们才能描画出事物的形,才能把存在者带入光明。但在久远的历史中,我们的思想着重于形,把它们与周围的背景分割开来,而逐渐忘却图形出现的场地及周围背景的意义,使其隐没入黑暗。一味追求光明忽视黑暗,是我们沦入技术社会的罪魁,是我们遗忘存在,失去诗意栖居的肇始。
我们该把光明小心翼翼地包裹在黑暗之中。“此黑暗却是光明的隐藏之处,它保存了这光明。光明就属于这黑暗。因此,这种黑暗有它本身的纯洁与清澈。”这样的光明,也不再是赤裸裸的亮光,而是充满智慧的,“盛满了黑暗的光明”。
人既生存于真理之中,又生存于非真之中;人更本源的根,是那幽微晦暗不可理解的非真。这启示着人的有限性。理性的人远远不是完整的人,人受制于日常经验,受制于时间,受制于他所嵌入的历史文化遗产。他所遭遇的,远非理性之光所能照亮。“觉悟到人的一切真理不仅对着周围的黑暗闪耀,甚至充满着他自己的黑暗。认识到这个,才能把人环抱着万物的原始神秘意义归还给人。”
(三)
世界建基于大地之上。大地是“人在其上和其中赖以筑居的东西”,它“作为家园般的基地而露面”。大地为世界提供自然材质。我们伐木做家具、建房屋,采石修桥铺路,开垦土地种植庄稼,使这些自然物向我们敞开,进入我们的世界。
大地不仅是材质。大地是原初意义上的自然,physis。这里的自然不是后来技术文明时代成为客体的被认知被开发被征服的那个自然,不是一堆没有生命的冷冰冰的质料。在古希腊的早期,自然有发芽、开花、形成之意,它自我生长,自我涌现。它包括了一切存在物,它就是存在者的整体。在它之外,没有一个创造者或认知的主体。
“思大地不是去凝视一个冷却了的现成对象,而是去倾听从而跟随大地本身的不断放出着又收回着在-此的召唤。在这样的倾听和跟随中,思通达着大地本身筑造着的承纳和庇护:大地承纳着万物的绽放和归隐,滋养着那些开花结果者,庇护着水流、岩石、动物和植物等等。”
大地提示着那个神秘幽微的黑暗,因为大地本质上自行锁闭,退遁于任何展开状态。世界努力把大地带到光明中,大地则不断绽出又返身隐匿,且试图把世界带回遮蔽并加以庇护。“大地是说:由此涌现也由此收回,并隐匿自行涌现的一切。在此自行涌现中,大地作为隐蔽之道而到场。”如果世界与敞亮、真理相联系,大地则启示着遮蔽与非真。大地是不可显示不可理解的,是虚无。大地通过进入世界得以显现,就象通过光明显示黑暗,通过有显示无。
我们的世界原本浸没在混沌与黑暗的大地之中。因为有了人生此在,存在得以天光一现,于是有了澄明的世界。然而,世界中一切器具也好,产出也好,包括人自身,都来自那个看似虚无的大地,而且大地还将把这一切收回它的内部,使之重归虚无。正是“不知何所来兮何所终”。
人在黑暗混沌的大地上,会有ungeheuer之感。这个意为“庞然大物的、惊人的、阴森的、神秘的”的词,海德格尔用来形容一种“异己的陌生感、莫名其妙的恐惧”。在敞亮的世界中,我们面对的存在者亲切、熟悉、可理解,但我们有在世之“畏”,不在“家”,无意义之感。亲切敞亮的背后,是黑暗而不可理解的大地。对这个隐匿不显的家园,我们一无所知,一无所见,犹如黑漆漆神秘莫测的深渊,难免有“莫名其妙的恐惧”。不在家,无意义;在家,却惴惴不安。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世界之中,天地是被驯服的,风调雨顺,一切都在技术的组织下。但世界照亮的只是很小很小一部分,自然不会总是和平宁静。帷幕后的大地上,可能是暴风骤雨,毒虫出没。在此栖居者,该有此洞见:安居家园,非坐享太平,无所筹划;而应心怀敬畏,更以极大勇气,直面生生不息变幻莫测的自然。
康德曾给歌德写信:“你才二十岁,不应该这么老气横秋,你就像一位牧场诗人。”诗人坐在牧场上,勾画着静谧美好的世界图景。沉浸其中,难免忘却生活波谲云诡的真相和可能的危险。康德此言,该是智慧长者的善意警醒。
(四)
这个有生有死,受苦受难,带着否定性有限性的人,在神秘莫测,令人惴惴的大地上寻找家园。这就是我们被许诺的栖居?难怪荷尔德林发问:
如果生活纯属艰辛,人
或许举目仰望说:
我就甘于如此存在?
是的。人生是有勇气的担当,勇气是对充满否定性的存在的肯定,是寻找“黑暗的光明”。生命来来去去,可能不会被证明有什么永恒价值;人生可能是荒谬的、被抛弃的甚至不可救赎的。但真正要紧的是,人能否正视困境,对此困境有所回应?
在茫茫大洋中漂泊的少年Pi,何尝不是人类处境的一个缩影。他孤身承担的,正好是Paul Tillich所言的威胁存在的三种方式,即死亡的威胁,道德的责难,和无意义的空虚。这三重焦虑在绝望的境遇中得到完全的实现。问题不在于Pi的双重人生——光明的或黑暗的,励志的或违背人伦的——哪一个更可取,而在于我们有没有体验到其中的绝望,有没有勇气把它担待起来。
敢于绝望,是大勇的表现;盲目乐观,则是生命力孱弱的表现。绝望的勇气是存在的勇气所能达到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