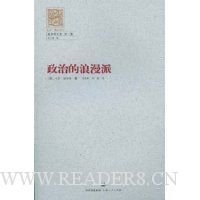
《政治的浪漫派》是一本由(德)施米特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2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政治的浪漫派》精选点评:
●《浪漫派》中了好多枪;《议会制》有助于消除现代政治概念的混乱。
●在A Dictionary of Legal Theory中,Brian Bix幾乎把Carl Schmitt化約為「幹你娘」這個詞。我這樣不徹底的浪漫主義者,讀罷立時想回罵某狼豬賤男:「你這Carl Schmitt!!」
●政治部分的我不管了。。。浪漫主义哲学立场部分读完了。。
●装X和打脸利器
●毒舌。
●卢格 (Arnold Ruge)宣称:“所有浪漫派的基础是不安分的反叛勇气”,这就是为何浪漫派被说成脱胎于新教主义。
●浪漫派的混乱无序,来源于主体机缘论的简单原则——共和也好,复辟也好,我的审美与感情创造一切。可以和朱谦之的宇宙论一战!
●约翰米勒和你有多大仇多大怨。这么黑浪漫派,有冲动要为浪漫派洗白。
●“政治的浪漫派”,范围仍显局促,“浪漫主义与政治”在我看来是更为广阔的话题。
●08年10月。
《政治的浪漫派》读后感(一):这次算重读
和第一次一样,有跳跃。
读的过程感到极大的启发,但同时又有隐隐不爽,对施密特的整体论述和论述风格下意识中产生着尚不明确的抗拒。
不过虽然思想内容上如何判断我吃不准,但施密特对浪漫派的具体批评,却可用来作为对我的生活气质的一种有力警告和提醒。
《政治的浪漫派》读后感(二):尔等举族皆浪漫
换句能听懂的话,你们全家都是浪漫派。
纵观德国百年,魏玛民国是德国文化的最后一个高峰,此后的德国已经一蹶不振,文明的历史彻底结束了。
施米特担心的一切都在当今德国发生。交往对话理性、政治的浪漫派、机会主义的立国政策……
浪漫主义的核心并不在于以自我为中心(刘小枫序)。浪漫主义的核心在于审美,浪漫主义者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和评价一切事物,从文化到政治。
因此浪漫主义具备一定的共同特征,虽然浪漫主义者喜好的事物可能会因人而异。
浪漫主义发端于当时欧洲大陆最衰弱的民族之一,除了其他欧洲民主唯恐避之不及的神圣罗马帝国,几乎从来没有过值得自豪的历史,而现状又如此让人伤心,法国拿捏德国如同没牙的老太太最喜欢的柿子。由此让人怀疑,审美主义是精神空虚和神经衰弱的结果,来源于无力改变现实的挫败感。
浪漫主义者的一些特征:
1、歌颂别国发生的暴力事件,因为浪漫主义者对强力之美有一种强烈的爱欲,这是一种补偿心理,因为他们的双手没有丝毫力气,肺病是浪漫主义者的经典疾病。
2、但是他们一定不会愿意这样的强力之美发生在自己的国家,因为他们觉得把房间打扫干净太麻烦,或者干脆就是没有举起笤帚的力气。
以上两点就是德国浪漫派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
3、渴望冒险和神秘,但是没有导游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出门,他们害怕迷路之后耽误了自己的晚餐。
4、浪漫派喜欢说“不”,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德国女孩举着牌子,上面质问道:“China,would you shoot me too?”她们觉得,一个人对着一个国家说“不”,最能够表现自己的力量,前提是她们和这个国家的距离大于任何武器的射程。而且她们看见鸡鸣狗盗之徒的时候,一般都会绕着走,不去自找麻烦提问对方是否打算向自己射击。
5、浪漫派喜欢写自传或回忆录,例如纳粹党员撰写的《西藏七年》,包括了3、4两点浪漫的要素。
《政治的浪漫派》读后感(三):昨天的浪漫派,今天的自由主义者?
本书分为《政治的浪漫派》和《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两部分。前者可以视为后者的思想史基础,后者体现的现实关怀又影响了作者对浪漫派人物的褒贬。
《政治的浪漫派》认为,浪漫派否定一切固有的规范,转而诉诸不确定的情感,因此缺乏(并且不追求)恒定的政治立场,不愿在政治领域的争论中做出坚定的决断。施米特和伯林都认为,否定固有规范是浪漫派的一大特征,但两人对这一特征的态度截然不同。施米特对浪漫派持明显的贬斥立场,伯林则认为浪漫派催生文化多元主义的贡献值得肯定。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在于两人对自由主义的不同态度:伯林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而施米特对自由主义充满怀疑。
《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开篇就把民主、自由主义和议会制区别开来。施米特区分了古代和现代两种民主,认为古代民主基于同质性,具有排他性;现代大众民主则讲求所有人作为人的平等,无论各群体间的分歧有多大,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这两种民主观念之间的冲突让我想到了当代关于种族和文化多元主义的争论。议会制的核心是公开辩论,对议会制的信念来源于“公开辩论能够达到真理(或者说最优解)”的信念。议会制的这一理论基础面临两方面的危险:一方面,公开辩论后妥协的结果未必是真理,也未必是最优解,可能是某一派煽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一旦政治决策成了小团体的游戏,公开辩论不能真正影响当权者,民众就会对议会制失望,转而寻找其他的政治解决方式。一旦自由主义的议会制失去人心,各类激发情感的政治神话便会趁虚而入。例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就是利用民族神话兴起的。这些关于议会制危机的论述,令人联想到当今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西方世界会不会重蹈魏玛德国的覆辙,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中,施米特提到了政治的浪漫派,把本书的两部分串连起来。两部分的联系在于,政治的浪漫派和支持议会制的自由主义者都拒绝真理的唯一性,希望通过意见间的不断竞争达成妥协。施米特认为,在议会制面临危机的时代,这样的态度只是在逃避问题。至于如何解决问题,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认为得到万众欢呼的专政也可能表达民主的实质,令人联想到纳粹党的上台;他对消解真理唯一性的担忧,则与列奥·施特劳斯的观点相似。
我并不完全认同施米特的观点,但也不得不承认他在某些问题上的洞见,例如认为议会制的核心是公开辩论。施米特在本书中的文风汪洋恣肆,有些章节又略显晦涩,总体上不是很好懂,以上的文字也只是一点粗浅的理解。
《政治的浪漫派》读后感(四):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小摘要
【按语:只读了“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1923)”一篇,觉得如Richard Thoma所批判的,Schmitt这篇文章的视角是混乱的。觉得施米特对民主的界定是偏颇的,尤其在主张代议制与民主可完全分离的时候:一方面偏技术定义,另一方面又甚至将专政也涵盖在民主中,是不妥当的。一种以自由民主制为例子的规范的民主理解显然更优。】
“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1923)”
“学术旨趣不在于证实或否定议会制,而是想要找出现代议会制度的内核。”【174】
1. 民主制和议会制。 19世纪的历史是民主制的胜利进军。但Schmitt说“民主…自身并没有实质性的明确目标。随着其最重要的对手君主制原则的消逝,民主本身也失去了自身本质上的明确性。”【177,Schmitt这种理解显然难以让人接受,可谓从根子上错了,他搞了一个民主的纯技术理解】“民主原则的本质——对法律与人民意志的同一性的肯定。”【179】
2. 议会制原理。议会制不是民主。“议会的本质是公开审议论证和反驳,是公开争论和辩论,所有这些都不涉及民主。”【185】浪漫派是自由主义,【187】议会制是自由主义的一项制度,核心是辩论(discussion),由之有:公开性;权力制衡;议会立法的概念,理性法律的普遍性质;限于立法的议会。“公开性和辩论是两条原则…宪政思想和议会制都取决于这两条原则。”【199】但这些在当代已经丧失了意义。
3. 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专政。对辩论的两种回应:理性的专政和非理性的专政。前者有漫长的传统,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那儿体现。后者在下一节。
4. 直接运用暴力的非理性学说。这里涉及的是普鲁东、巴枯宁和Georges Sorel。在注解中,Schmitt说,“西欧文化传统观念的真正敌人,首先是和俄国人,尤其是巴枯宁一起出现的。”【215】Sorel“痛恨一切理智主义、一切集权主义、一切统一性。”【216】“要用暴力来代替权力。”【217】“俄国人和无产阶级如今都在资产阶级身上看到了一切试图以致命的机械方式奴役生命的事物之化身。”【218】Sorel赞美神话尤其是民族神话。
附录:论议会制的意识形态(1925)by Richard Thoma:Thoma赞美schmitt”此文以其思想上的丰富性令人着迷。”【221】但视角混乱。Schmitt仅仅选择了议会制的一种并非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予以抨击。Thoma不相信“欧洲面对如此两难选择:议会制抑或专政。”【224个人觉得施米特对民主的界定是偏颇的,尤其在将代议制与民主可完全分离的时候,一方面偏技术定义,另一方面又甚至将专政也看作民主,是不妥当的。】
江绪林 2014年5月16日星期五
《政治的浪漫派》读后感(五):浪漫的无能
作为施米特的入门书来读似乎不那么恰当啊。就个人立场是想将其与韦伯的《以政治为业》做参照的,毕竟同时作为自由主义立场的反乌托邦批判文本,而且施米特这篇文章也是在韦伯演讲激励下写出来的,两相对照,应该有收获。但是韦伯更像是一个慎重的父亲,更多是奉劝你谨慎行事,不要头脑发热。施米特则是直接上来就开撕,将讽刺的笔尖直接对准天真的浪漫派们。这个,取径还是不一样的。不敢乱评,手码一段以示敬意:
2016年版 第92页
为了理解浪漫派的状态和两种新实在的浪漫主义意义,必须考虑到一种复杂的现象,它来自可能性和实在之间的浪漫主义冲突。浪漫主义最初是一场青年反对老年的运动。成长中的一地啊人为反抗老一代掌权者而寻找口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从大功告成的东西中并不总是能够找到这种口号,这就是这一代人为何要求助于自己的青春,求助于活跃的因素,求助于自己的能量和活力,换言之,求助于自己的可能性的原因,新生代引入种种新理想,由此创造一个发挥自己才干的空间,结果是下一代人还会认为他们属于老派人士。18世纪结束时的浪漫一代,处于一种特别困难的境况。他们面对取得古典主义成就的一代;在回应其最伟大的代表人物歌德时,他们所能表现出来的唯一创造力,就是赞美与强烈的热情。他们的产品限于批评和性格刻画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之外,他们的一切自负都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他们制定鲁莽的计划,作出大胆的许诺。他们发布通告,描绘前景。他们用新的许诺来回答对他们落实许诺的期待。他们撤出一书,进入哲学、历史、政治和神学。但是他们用以抵抗是在的大量可能性,从未变成实在。浪漫派解决这种困境的办法,是把可能性说成更高的范畴。浪漫派不能再日常实在中扮演创造世界的自我的角色。他们更细化从未落实为具体实在的永恒变化与可能性的状态。这是因为在无数的可能性中只有一个能够成为实在。当它思想是,其他无限多的可能性就都被排除了。一个世界因头脑狭隘的实在而遭到毁灭。“丰沛的观念”成为了可怜的具体化的牺牲品。于是一切说出口的话都成了谎言。它限制着没有边界的思想。一切定义都是无生命的、机械的东西。它限定不可限定的生命。一切基础都是靠不住的;因为基础总是与限制一起出现。
于是关系被颠倒了。空洞无物的不是可能性,而是实在;不是抽象的形式,而是可靠的内容。这也意味着一种哲学的颠覆。时代追求实在,是为了结束现实实在中的神秘主义的非理性因素。如果它的出现利用了一种例行化的过程,则生命的无限性就再次被它消灭。哲学家的一切精巧设计,以及许多头脑发热的浪漫派言论,其意义在于他们要把握实在并解释它,但并未放弃不可捉摸的可能性的刺激。不过,有关这一点的任何论证,都未能表明如下事实带来的问题:从事论证的人实在运用理性的而是不是非理性的能力。还可以举出理智的直觉、惬意的想入非非或任何本能过程,他们要利用这些东西获得纯粹的理解力(用施莱格尔的话说——单纯的理性)所难以企及的知识。但是,只要存在着哲学体系的妄想,这个体系中的矛盾就是不可克服的。无论如何,在浪漫主义的表现中,只要文章于警句是在传达直觉活动的结果,那么它充其量只能是向志同道合者的灵魂发出呼吁,换言之,只能是向一个浪漫派群体发出的呼吁。全部哲学努力的目标——从哲学上达到非理性的境界——并未达到。新的实在,即社会,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压倒了浪漫派,强迫他们向它发出呼吁。
好了,这杯反鸡汤,先喝为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