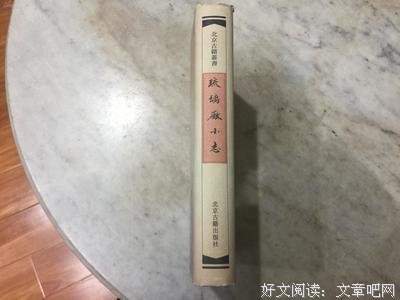
《琉璃厂小志》是一本由孙殿起辑著作,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3.00,页数:5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琉璃厂小志》精选点评:
●滿蒙混血男主角的遊樂場之一。
●那时就有知道分子在出没了
● 未有想象那么好。竟然不少是店铺里掌柜和伙计的名姓记录,不过最可取的应该是旧时收集藏品的故事(拍照笔记了)。
●那些消失的书肆
●这个丛书都是从史料记载琉璃厂变迁的。此书则更为详尽~~
●“旧时图书馆之制未行,文人有所需,无不求廠肆;外省士子,入都应试,亦皆趋之若鹜。盖所谓琉璃厂者,已隐然为文化之中心,其地不特著闻于首都,亦且驰誉于全国也。”今日去求一个闲章,手艺人精湛的技法让我想起核舟记里技艺灵怪的奇巧人~虽然价格设置的很旅游胜地性质…最后顺了几本书便离开了
《琉璃厂小志》读后感(一):夜读随札
三九寒夜,诸事懒做,随手翻读《琉璃厂小志》。
浏览第三章《书肆变迁记》,李文藻(南涧)《琉璃厂书肆记》、缪荃孙(筱珊)《琉璃厂书肆后记》以及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中,都有江西籍业书者身影。
比如,李文中有:“其余不著何许人者,皆江西金溪人也。”缪文中有:“路南有善成堂饶氏,大文堂刘氏,皆江西人。”
其中,孙《三记》中对此记录尤详,江西籍店主、书肆名号一一列名者,有将近20家,例如文光楼(周秋门)、三槐堂(夏麒麟)、藜光阁(某姓)、文盛堂(王姓)、龙威阁(李姓)、文华堂(某姓)、玉生堂(王姓)、铭德堂(王鼎魁)、文宝堂(曹光圃)、善成堂(饶起凤)、二酉斋(徐春祐)、槐荫山房(曹姓)等等。
不过,根据孙的记录,这些最初店主为江西籍的门面,多创设于咸丰、同治、光绪年间,逮至清末,几乎都易手或歇业,等到孙外甥雷梦水做《琉璃厂书肆四记》时,琉璃厂业书的江西籍人士差不多已经绝迹。
这其中,可能有时代变迁影响,但作为一个地域业书群体,其消长,背后当有一定的决定性因素在内。如能对此作一番考证,或者也可见出清代以降,江西地方书业发展的一些史实来。
癸巳腊月十二日夜
《琉璃厂小志》读后感(二):《書邊雜談:底裏細讀識小街》
《書邊雜談:底裏細讀識小街》
一書在手,底裏細讀,已經成了習慣。裝幀、題簽、插圖、書葉天地、版權文字,都在關注之中,當然,序跋、註釋與內容更是不用說了,這般讀書,說實在,端的長見識。
知道北京有一條楊梅竹斜街,就是從一冊民國線裝書的扉葉牌記裡讀得的,有一家名字呌作龍光齋的刻字舗開設在“前門外楊梅竹斜街西頭路北”,初識不經意,祇覺得那一條小街名字新鮮。雖也曾在北京那麼多年,大多數日子,每朝必九,每晚過九,辦公樓、公寓樓,兩點一線,哪有閑功夫去前門外大柵欄逛呢,自然,不曾知道的小胡同、小斜街居多了。
後來,一路尋讀方才知道,北京的這一條小街,明代是沒有名頭的,就呌小斜街,也許是京城裡小斜街忒多了,什麼煙袋斜街啦,櫻桃斜街啦,東斜街、西斜街、上斜街、下斜街的,於是乎,後來這裡以一個居住在此地的楊氏媒婆呌上口、揚上名了,楊媒斜街一呌就這麼呌了多年。晚清民國初期,堂堂乎皇城,也開始講究一個名堂規範了,豈能容得了一個媒婆來市井炫耀,於是乎,官衙下令雅正小街名字為楊梅竹斜街,故事若真如是,這一個楊氏媒婆應該算得上天下第一大媒了,京城名姓作街名,那還了得,真與蘭陵笑笑生筆下的那一個王婆堪得一比了。
其實,那一個官衙也忒沒見識,楊梅,在其故鄉浙江一帯,從來是不與竹子共一處方圓的,不聞雨後春筍遍地生嗎,那一擠兌,楊梅樹兒要扭了腰的。祇是,竹子多名堂,鳳尾竹、湘妃竹、龍拐竹、龜紋竹、羅漢竹的,興許,哪一處要不也有楊梅竹吧。
再後來,又翻讀孫殿起的那一冊《琉璃廠小志》,讀得了這麼一段文字:
“楊梅竹斜街,中華印書局為齊家本所創立,最盛時在民國二十年前後,所出書為京調、大鼓詞及各種小唱本,鉛字排印,下鄉售賣。”
“世界書局及會文堂書局亦在楊梅竹斜街設立分店,所售書來自上海總店,皆自印自銷也。”-《「琉璃廠小志•概述•北京琉璃廠書肆逸乘」-張涵銳》
再再後來,又拉雜讀得,從1928年到1933年間,北新書局在北京的店鋪,地兒也設立在楊梅竹斜街上,魯迅先生的那一冊《華蓋集》,好幾版再印,就都是在那裡刊行的呢。
亦是長見識,知道了北京的那一處楊梅竹斜街,應該在前門與宣武門之間,離開和平門外的琉璃廠也不太逺,就如昔日的上海,緊緊挨著四馬路的那一處棋盤街一般,也書肆林立,這可不,中華印書局、世界書局、會文堂書局、北新書局,就四家了,也算上那一家龍光齋吧,就五家了。
下一回去北京,得閑,一定要去那一處楊梅竹斜街逛逛了。
-ZY.S. 2009-April-12
《琉璃厂小志》读后感(三):《琉璃厂小志》续札
昨晚读《琉璃厂小志》,留心琉璃厂江西籍业书者资料若干。今晚继续翻读,所获更多,并对昨晚所记予以补充和佐证。
先录书中资料数条:
厂甸书业,乾嘉以来,多系江西人经营,相传最初有某姓者,来京会试未中,在此设肆,自撰八股文试帖诗镌版刷印出售,恃以生活。后来者以同乡关系,颇有仿此而行者,遂成一集团;直到清末科举废后,此种集团始无形取销。代江西帮而继起者,多河北南宫冀州等处人,彼此引荐子侄,由乡间入城谋生。偶有他县人插足其间,不若南宫冀州人之多;若外省人,则更寥寥无几矣。
——张涵锐《琉璃厂沿革考》(P16)
琉璃厂书肆,自前清乾嘉以来,多系江西人经营。相传最初有某氏,来京会试不第,在此设肆,自撰八股文试帖诗,镌版出售,借此谋生,后来者以同乡关系,亦多仿此而行,遂成一集团;至清末科举废除,此集团亦无形涣散。代之而兴者,以河北省南宫冀县等处人为多;盖彼此引荐子侄,岁由乡间入城谋生者也。古董字画业,则以北直深县人为最多云。
——张涵锐《北京琉璃厂书肆逸乘》(P48)
以上两条几完全重复。
琉璃厂于前清乾隆年间,已成书市,四方来京会试之举子暨朝野文人,恒视此为消遣岁月之地。书商获利既丰,辄归功于文昌之保佑,遂建馆祀之,此琉璃厂文昌馆之所由来。书肆最忌火灾,迷信者祀火神以求免,此又琉璃厂火神庙之所由来。此两处馆庙,为厂肆商贾最重要之祀典,兹述琉璃厂故事,亦不容忽视也。
文昌馆,在琉璃厂有二处:一在厂东门内路北,一在小沙土园内。缘清咸丰同治年间,厂甸书贾,江西人居多,盖来京应试落第者,改业为此。向在厂东门路北建立文昌馆,每届二月初三日文昌诞辰,书业师弟皆来拈香,以江西帮派为主。至光绪中叶,河北冀属人业书者渐多,足与江西派抗衡,而往文昌馆拈香者,辄被江西人所拒绝。北方书贾愤甚,遂集资在小沙土园购地,修建北直文昌会馆,于每年二月初三日文昌诞日,献戏酬神。
——《文昌馆及火神庙》(P273)
文昌阁,清咸同间,北直旧书同业中人,集资剏建。光绪间,镌有碑记,民国六年,曾一修之。先是,鬻旧书者,皆江浙人,而江西籍者居多数,其学徒则皆北省人。尝闻旧有文昌馆,坐落在厂东门路北,每岁至文昌诞辰,同人拈香致敬,而北省人禁不得与,故另建此阁,又名北直书行文昌圣会。倡其事者徐君志油、李君崇山。先后董其事不惮劳者,则魏君宇翘及魏君文厚父子也。举其经过,是为记。
——《北直书行文昌会馆记》(P280)
据这些资料,并结合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其余不著何许人者,皆江西金溪人也”,大致可以勾勒出江西人在琉璃厂业书轨迹:
乾隆时四库开馆期间,有江西(或是金溪)人进京会试未中,在琉璃厂刻卖应试之类的小册子,然后同乡带同乡,组成商帮,并带了不少北京附近的乡村人做学徒。
书业忌火,江西商帮因此在厂东门路北建文昌馆祀火神,“书业师弟皆来拈香”,但或许将祭祀事看得极为隆重,又或许祭祀时同乡相聚,本就有很多业务机密要交流,所以“北省人禁不得与”,矛盾产生。到光绪中叶以后,河北冀县、衡水等地业书者增多,于是另行在小沙土园修建北直文昌会馆相抗衡。
相对而言,江西毕竟远离京城,不如冀县等地就近京城,方便“彼此引荐子侄,岁由乡间入城谋生者”,再加时代变迁,科举没落,江西进京会试举子也逐渐减少,所以江西人渐次被挤出琉璃厂书业,直至清末“无形涣散”。
癸巳腊月十三夜
《琉璃厂小志》读后感(四):琉璃厂访书记
北京琉璃厂原来是烧制琉璃瓦的窑厂,据说海王村之名在辽代就这么叫了,当时是城外郊区的一个小村落。后来,元、明时代烧造琉璃瓦,烧窑取土形成许多“窑坑”,交通来往,只能依靠桥梁。所以琉璃厂附近的许多地名多有“桥”字。现今琉璃厂的牌匾也挂在一座天桥上,可见其文化传承。
清朝中叶以来,琉璃厂逐渐形成文化市街,旧书肆、古董、字画、金石等行业云集,孙殿起先生曾撰《琉璃厂小志》,博采约取,翔实记录了琉璃厂的名胜古迹、书肆变迁、贩书传薪以及学人遗事,为北京数百年来旧书业的珍贵史料。
五四以来,鲁迅、胡适、郑振铎等学人,也经常逛琉璃厂买古书、碑帖、字画,鲁迅先生居北京十余年,据《鲁迅日记》记载,就去过琉璃厂四百余次。可见其对文人的吸引力之大了。
对于北京琉璃厂,我慕名已久,这次趁着到北京跑马拉松的机会,总算抽了一个小半天的空,难以悠游畅览,权当到此一游。
在八大胡同里循着地图指引,逛到琉璃厂,还没到开张的时候。逛了一圈,看看各式匾额书法,也蛮好看,如晚清翁同龢题的“茹古斋”、吴昌硕题的“清秘阁”,近代徐悲鸿题的“荣宝斋”、王世襄题的“贤燕堂”等等。
踱到琉璃厂东街1号,抬头见到“天禄琳琅”牌匾高悬于上,这个名字是乾隆皇帝赐的。“天禄”一词取自汉朝天禄阁藏书,“琳琅”为美玉之称,意为内府藏书琳琅满目。乾隆帝御览善本珍籍,列于昭仁殿,“天禄琳琅”遂成为清代皇室典藏珍籍的代称。
前人曾有诗云:“势家歇马评珍玩,冷客摊钱问故书”。珍宝古玩吾辈既无财力,也无眼力,无力罗致,线装古书于旅次途中也携带不便,既是匆匆过客,且到中国书店看几册建国后出版的旧书吧。
到访中国书店时,经过一家古董店,店内的一幅对联吸引了我的注意。是一幅花梨木镶嵌青花瓷的对联,联语曰:“读书已过五千卷 横剑曾躯十万师”。我驻留观望许久,查了下资料。
这幅对联是清代戏曲作家、陶瓷艺术家唐英专为清代名将年羹尧烧制的。后来年羹尧功高震主,身死家破,此联亦藉没大内。辗转百年后,曾国藩铲平“太平天国”,位极人臣,慈禧太后又将此联赐于曾氏。曾国藩面壁此联,遂尔归隐,此联一直悬挂在双峰荷叶塘曾府。
其后“湘学复兴大师”邓显鹤湘皋先生找曾国藩筹款刻印《船山遗书》。曾氏不仅慷慨解囊,亦将此联持赠以弥补印书经费不足。此联之事典大略如此。余好奇叹问店主此联售价几金,索价却并不甚高,盖今日景德镇仿制之工艺品也。
中国书店是郭沫若题写的匾额,我径直步入旧书区观览起来,每册旧书后面均用铅笔注明价格,常常是书好价也高。例如文革期间,专为毛主席印制的大字本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牛皮纸盒两函十册装,字大悦目,库存如新,价已逾千元。我摩挲良久,慨叹时光之易逝,而书比人长寿。
又见中华书局影印本《文选》,三册全,1977年初印,也是触手如新,几乎可闻昨日墨香,却是几乎四十年前的出版物了。寒斋已藏多部《文选》,有李善注,有五臣注,有影印亦有排印,此版见过多次,而品相均不遂心意,难得此部品相莹洁如玉,我见猎心喜,遂购而归之,算是珍藏一段旧日时光。结账时,女售货员用中国书店的广告纸包裹并以尼龙绳四方系之,笑曰:“此书年纪比你大吧?”答曰:“是也!”
旧书店常见残本,以其多价廉,余见可读之书,亦收之,不以未能完璧为忧。多年来,余藏读鲁迅先生著作多种,全集也藏有多个版本,此次琉璃厂访书,偶然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的《鲁迅全集》散本,又购入第九册一部,布面函装,收录《嵇康集》、《中国小说史略》两种,今年适逢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和逝世80周年,得此好书,亦为一段书缘。
辗转书架之间,众里寻踪,百般搜求,不意间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世纪50年代初版的《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布脊精装,文字排版十分悦目。
满涛先生翻译的果戈理和别林斯基著作,闪耀着文字的激情与光芒,别林斯基是一代文学批评天才,此书收录其批评成名作《文学的幻想》以及《论俄国的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等评论十篇,当从容精读之。
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小说中,李劼人先生的长篇小说《大波》,我久闻其名,一直想读。近日读史家高华遗作,高华先生亦推崇此书,认为李劼人先生笔下是活的中国,他的小说是拥有巨大场景的史诗,是活的风俗史,是极为难得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小说。诗可证史,好的小说亦可证史。
在中国书店的旧书区,我发现了《李劼人选集》第二卷全三册,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初版,品佳如新,收录的正好是完整的长篇小说《大波》,书缘真是冥冥之中如有天定。
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旧书,多数价格略高,也是时代变迁使然,品质好的古旧书多送拍卖行,普通的旧书随着城市化进程又难以搜集,渐渐湮没,少量留存下来的旧书,自然水涨船高,随行入市。
在中国书店旧书区逛了一个多时辰,书囊渐重,家人催归已连续下了十二道金牌,余仍留恋未忍去,正待急遑遑走出书店,忽然在拐角一排书架上层瞥见一书,抽出一看,是朱学勤先生的《书斋里的革命》,学勤先生是博览精思的学者,余曾读过几篇他的文字,留有鲜明的印象。关于人文启蒙、卢梭学说、家国命运等文化与思想方面的思索,值得一读。
琉璃厂访书之后第二天,我参加了第36届北京马拉松,3万名选手从天安门跑到奥林匹克公园,全程42.195公里。我平时跑得不多,总算顺利完赛,家人和朋友已在终点区等候多时。这是我完成的人生第七场全程马拉松,当我挂上沉甸甸的镶金完赛奖牌,想到归途时还有那一摞沉甸甸的书籍,感到此次北马之行,真是一次难得的人生经历。
读书与跑步,于我而言都是砥砺心智,宛若在幸福的行旅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6.09.20于北京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