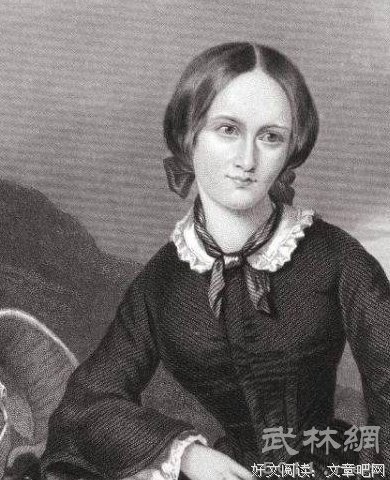
《夏洛蒂.勃朗特书信》是一本由杨静远译著作,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00,页数:4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夏洛蒂.勃朗特书信》精选点评:
●为何她总是能当头一棒击中要害,要知道,她总是年纪轻轻。阅读中每每自问,可有一点人样,凭什么“要这要那”?“我的调色板调不出更鲜艳的色彩。要是试图把红色加深或把黄色加亮,那只会一团遭”。所谓经久不衰的趣味和慧智,如此这般定够得上了。
●《简爱》所展现的,远远不是夏洛 蒂 勃朗特的全貌,在这近300封的私人信件中,才显露出一个立体而光辉的女性形象。初露锋芒的柯勒 贝尔,优雅而从容的应付于书商,一个家庭大姐,对弟弟妹妹爱之深,责之切,对其才华的发掘与肯定;一个逐渐蜚声文坛的女作家,与各个作家之间的酬唱笔札;一个深闺淑女,对爱的矜持,犹疑,闪烁,肯定与释怀……人的情感的小小漩涡……
●比《简爱》还好看
●辛辛苦苦买来的,居然是盗版啊盗版
●正确的道路,乃是那条要求你在个人利益上做出最大牺牲、对别人有最大好处的道路。
●非常喜欢。这个不求名声不求团伙的坚忍女性~
●把《简·爱》看完之后就看了这本书,女主人公的形象更加全面了。
●译得真好。
●翻译不错
《夏洛蒂.勃朗特书信》读后感(一):真实带来触动
最大的感受是真实,夏洛蒂写这些信的时候应该没有想到会被收信人以外的人看到,她在字里行间表达的都是最真实的想法,完全没有怕被别人看到而产生误解的担忧,因此下笔的时候干脆而真挚。
读到后面,我仿佛变成了收信人,真切地感受到夏洛蒂写信时的感情和思绪。真实文字的神奇力量,穿越近200年的时光,丰盈了写信人的形象,让我跟随她一起喜怒哀乐。
200年前安居于英国偏僻乡村的一个女孩子就有追求独立人生的想法,同情那些坐等嫁人的女孩子耽搁了美好的一生,她认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生活都应有一定目标。夏洛蒂36岁结婚,之前拒绝了多次求婚,虽然她在信中提及自己作为一个老姑娘,生活孤单,不免有淡淡愁苦,但是她选择接受并享受这种生活,为创作而愉快。
夏洛蒂妹妹们的英年早逝,26岁的花样年华因伤寒离世,那样才华横溢的生命却如此短暂,让我痛心。但艾米莉留下的《呼啸山庄》让她年轻的生命留下了永恒的纪念。反思我自己,珍惜生命和时间,在这浮躁的社会中是否还保有初心。
夏洛蒂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在20多岁的时候去世了,她自己也在39岁的时候离世了。当时的人们很容易被疾病带走生命,现如今很多病都可以治愈,即使被认为是绝症的癌症,也可以在药物控制下延缓很多年爆发,人们的平均寿命超过了70岁。20多岁正是青春洋溢的时候,看起来未来还长,有很多畅想和挥霍的空间。看了夏洛蒂从少女时期到生命终点的300多封书信,让我更加觉得时间宝贵,未来风险不可期。所以,即使会活很久,也要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间里,不去哀伤和担忧,去行动来实现理想——健身以储备健康,远行去近观美景,动笔而留下心声。
《夏洛蒂.勃朗特书信》读后感(二):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在我偶尔还力求上进的中学时代,被一个学习好的女生问:都看过什么世界名著?怯怯的答:看过《简爱》。她严肃而确凿的驳回:《简爱》不是世界名著,《呼啸山庄》是。从此对被打上 “闲书”标记的《简爱》只敢偷偷爱着,在被窝里打着手电一遍又一遍的重温那些对白。而因为“不是名著”的缘故,我从来都没有注意过作者,不知道那是位女士,更不知道她的两个妹妹也有写作的天分,尤其是其中一位,还写了世界名著《呼啸山庄》。
很多年我都把《简爱》当成是我的一个新发现,一个小秘密——一部名不见经传的小说,不知道怎么落到我手里,也许除了我,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读它呢。当发现这个故事居然有那么多人跟我分享,我未免觉得失落,当它堂堂正正的“当上”了“名著”,我发现竟不知道该怎么去读它评论它了(难道还能跟对待一般言情小说一样,说什么“我喜欢罗切斯特”?不用有点什么深奥的揭示和伟大的体现?)。
“看世界名著是有品位和上进(爱学习谓之上进)的象征”“看武侠和言情小说是低俗和堕落(不爱学习谓之堕落)的表现”,这道压在心上的成见之阴影直到多年以后,金庸古龙成了“经典”,学生时代久远而淡薄成了履历,才渐渐的被克服。这时历史的车轮已经将年逾而立的我带入了一个名著云集经典丛生大师遍地的盛世了。这时我开始偶尔像从自己的花园里采集一小束装点居室的蔷薇一样,念及曾经糊涂又美好的青春,偶尔想到我曾经“秘密”阅读的闲书《简爱》。我依然觉得那些对白那么真诚,不相信那仅仅是一个编写出来的故事,我猜想夏绿蒂就是那个叫简的小人儿,穷,不高不漂亮,性格略嫌古怪,不合群,可是善良,聪明,敏感,有骨气(对了,小的时候,我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固执的认为《简爱》的作者就叫简爱,认为所有用第一人称写的“故事”都是真的在作者身上发生过)。
有了这些渊源,这本被同事誉为地摊货的《夏绿蒂勃朗特书信》比那些腰封华丽的“大师经典”更早被我“宠幸”,也就不奇怪了。而从此,简爱也和夏绿蒂女士分开了,夏绿蒂有了自己的身份和故事,她和简爱虽然有相像之处,可又有更多的不同,而世间居然也就真的没有那个罗切斯特,能让人对着表白:你以为我穷,不美,就没有感情吗?我也有的!。。假如上帝赐予我美貌和财富,我一定会使你难以离开我,正如我现在难以离开你!!。。啊,时隔那么多年,这段台词的杀伤力从未减退,而夏绿蒂的生命中从未出现过一个罗切斯特,她等他到38岁,然后嫁给了那个苦苦追求她的副牧师,一个正直善良却古板无趣的人。是的,我猜想。
那些写给康斯坦丁•埃热的信,我心里是暗暗欣赏的,虽然另外一些爱她的人,将这段感情视为“不洁”而讳莫如深,我却欣赏她的坦白和勇气,其实爱的分量就在于你肯把自己不计代价的交出去多少,如果惺惺于世间的毁誉,如果怕这颗交出去的真心遭受屈辱,如果希求着回报或者满足于“私密”的爱人关系的结果,那都不是爱;而如果没有丝毫犹豫、没有与自己的苦战没有原则没有克制以及最终的放开,那又不过是爱中的一个溺者,一个奴隶或者一个俘虏。可惜的是,埃热先生并没有这份同等的襟怀,又或者这根本不是一次“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的遇见,只是蔷薇如雪,随时绽放,随时凋零,那个“墙外行人”,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罢。
《夏洛蒂.勃朗特书信》读后感(三):比简•爱更丰盈的心
即使你没读过《简•爱》原著,也一定或多或少知道故事女主人公简•爱坚强勇敢、不惧不屈的故事。简•爱在罗切斯特面前的表白已经成为女性要求自尊与平等的经典台词:“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自尊吗?不!我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正像你和我最终将通过坟墓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一样。”一直都有这样一种说法,《简•爱》这个故事有很浓厚的自传色彩,因为它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和简•爱一样,也曾做过家庭教师。读着杨静远翻译的《夏洛蒂•勃朗特书信》后,我看到的,是一个比简•爱更加丰厚的灵魂。那些诉诸笔端的情感小漩涡,让夏洛蒂•勃朗特比简•爱更迷人。
夏洛蒂•勃朗特和两个妹妹分别所著的《简•爱》《呼啸山庄》《阿格里斯•格雷》已经成为文学上的经典之作,他们一家也被后世形容为“荒野中天才般的一家人”,但夏洛蒂•勃朗特在写作这条路上内心却几经波折。二十岁时,她曾写信给著名的湖畔派诗人罗伯特•骚塞请教,并附上了自己的诗作。罗伯特•骚塞的回信严重挫伤了她写作的热情:“最好不要选择这样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你惯常沉湎其中的白日梦,很可能会导致心性的失调;由于世上一切平常的劳务在你看来都是平淡无味而毫无裨益的,反过来,你也会变得不适于从事这些劳务,同时也不适于从事其他任何事务。文学不能也不应成为妇女的终身事业……。”这封信让夏洛蒂•勃朗特深受震动,她在回信中说:“我父亲从我小时候就用如你信中所用的那种明智而友好的口吻对我进行规劝。遵循他的劝导,我不但竭力克尽一个女子应尽的职责,而且力求以此为乐。我并不总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有时当我在授课或缝纫时,我宁愿读书或写作,但我力图克制自己……我相信我再也不会雄心勃勃地希望看到我的名字印在书上;这种愿望只要一露头,我就重读骚塞的信,把它压下去。”
那个时代想要成为女作家是多么不易,罗伯特•骚塞无疑代表了主流观点,世人对女子的期待,不外乎是结婚生子,尽好对周围人的义务。她们幽微深邃的内心世界在渴盼什么,这都是不重要的。即使写出了好的作品,也不得不在意世人对女作家的偏见,夏洛蒂•勃朗特三姐妹最开始出书,也是选择了用贝尔三兄弟作为笔名掩盖自己女性的身份。尽管信服罗伯特•骚塞的观点,并把自己大多的时间或交给了琐碎的家务或去做家庭教师养活自己和家人,在她早年写下的一些信中,常常倾吐作为家庭教师的苦闷,或是弟妹们的前途担忧。后来,她又目睹了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的接连死亡。在重重生活琐屑的干扰之下,夏洛蒂•勃朗特还是成为了一名作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许在她的内心,成为作家的火焰从未熄灭,即使要操心那么多琐事,内心的渴盼,才华的光芒,却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住的。
作为家里年纪最大的孩子,夏洛蒂•勃朗特温厚、安宁,一直把对家庭的义务放到自己的写作欲望之前。但她表面温顺的外表下,有着自我、幽深的内心世界。她温厚地对待家人和朋友,但并不是世俗意义上温顺的女人。面对自己并不喜欢的求婚者,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感到亨利对我太不了解,他简直意识不到他是在给谁写信。要是他看到我天生就有的自然本性,定会大吃一惊的。他会认为我是一个疯疯癫癫的、罗曼蒂克的狂热家。我不能成天正襟危坐,在丈夫面前摆出一副不苟言笑的庄重面孔。我要笑,要挖苦讽刺人,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我的丈夫是个聪明人,爱我,那么全世界比起他最微小的愿望来,就会像空气一样轻”。
夏洛蒂•勃朗特38岁才结婚,那时她已经完成自己所有的作品。之后不到一年,她就去世了。她早年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对现今未婚女子和永不结婚的女子命运考虑得很多。我几乎已经认定,一个未婚女子,没有丈夫或兄弟的扶持,安安静静地、坚毅不拔地自食其力度过一生,到了四十五岁或更高的年龄,还保持着有条不紊的头脑,愉快的情性,能以享受简单的乐趣,保持着坚强的性格,能以经受必不可免的痛苦,同情别人的疾苦,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乐于济贫助人,——这样一个未婚女子,世上没有比她更值得尊敬的人了。”她在另一封信中说:“我是命中注定要当老姑娘的。没关系,从十二岁起,我就下定决心接受这一命运了。”
在我看来,“安安静静地、坚毅不拔地自食其力度过一生,到了四十五岁或更高的年龄,还保持着有条不紊的头脑,愉快的情性,能以享受简单的乐趣,保持着坚强的性格,能以经受必不可免的痛苦,同情别人的疾苦,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乐于济贫助人”这样的表白,比简•爱在罗切斯特面前的控诉“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自尊吗?不!我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正像你和我最终将通过坟墓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一样。”更加动人,后者说到底还是因为对对方有要求因而感到的痛苦与愤怒,而前者则是自己丰盈内心的一种体现。在那样的时代,对于一个女人,不管对写作充满热忱想要有所成就,还是追求真正的爱情,都是多么不容易。
《夏洛蒂.勃朗特书信》读后感(四):夏洛蒂伴我找自己
高中时,在图书馆深处,我读到了勃朗特一家的传纪。
我对勃朗特姐妹并不陌生。多年前,我读完的第一本小说,就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
“难道就因为我贫穷、低微、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当我们两个人经过了坟墓,站在上帝脚下,是平等的”,有一回,父亲满怀感慨地对我复述着这些句子,“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这样的句子真是振聋发聩啊!”
可当时我只在冷眼旁观:我可没那么容易跟着感动,虽然这本书很好读,虽然我也曾在夏洛蒂编织的世界中迷失方向,但一个特别强调尊严的女子追求爱情的故事,总让身为女孩的我感到缺了些什么。
直到打开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书信集,我才在她身上找回了这种缺失。夏洛蒂也许就是简·爱,但她无疑是一个更丰富立体的人。
“我感到亨利对我太不了解,他简直意识不到他在给谁写信”,在一封给好友的信中,她这样解释自己对求婚者的拒绝,“我不能成天正襟危坐,在丈夫面前摆出一副不苟言笑的庄重面孔。我要笑,要挖苦讽刺人,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我的丈夫是个聪明人,爱我,那么全世界比起他最微小的愿望来,就会像空气一样轻”。
这是1839年23岁的夏洛蒂写下的信,我读了简直要喊出来:“天,这才是女孩子的真正心声吧。”人们都说女孩要文静而美好。在读到《简·爱》之前,我所知的完美女主角,就是“林妹妹”或者“宝姐姐”式的人物。她们起码长得赏心悦目,多半也衣食无忧,纤弱需要保护。至于是爱耍小性子还是贤惠大方,那都是无伤大雅的“女孩子脾气”了。
但一个女孩所面临的真实人生也许会像夏洛蒂·勃朗特这样充满磨砺:她与男生一样接受教育,工作养家,却被视为物质生产资料式的存在,重要的价值在于嫁人。她的身上有被人称颂的品质:沉静、温厚、辛勤耐劳,可这不是这女孩子生命的真相,即便能在所有人的面前温婉沉静,她的内心也并不会比男人少一份个性、棱角与热情。
生活在维多利亚中期的夏洛蒂似乎也感到自己的要求与时代的格格不入:“我是命中注定要当老姑娘的。没关系,从十二岁起,我就下定决心接受这一命运了。”
这个外表平静、内心激烈的姑娘,让我感到心有戚戚焉。我佩服她能把我内心萌动却说不出的想法,如此清晰又坦然地表达出来。
那时节,读高中的我也习惯于每天呆呆地坐在教室中,作出毫无想法的样子来。从小,人人都喜欢文静懂事的孩子,我也习惯了这样生活着。所有人都告诉我高考是最重要的事,于是我仿佛在为此奋斗着。偶尔恶作剧的心一起,捧着书去问历史老师:历史教科书上说这个师在解放战争被我军全歼了,为什么黄仁宇的书里说他们是全体自杀的?老师说,嘿嘿。
只是这样提问又有什么用,至少,对近在眼前的高考,全无一点积极的作用。
在夏洛蒂留下的书信中,我看到她苦恼于自己不温驯的个性。她羡慕朋友有着基督徒式的温柔良善,但她无法放弃自己的棱角与思考:“我渴望圣洁,可我永远、永远也达不到圣洁……如果一个人必须有基督徒式的完美才能得救,那我将永不能得救。”
庆幸的是,勃朗特姐妹们找到了能投入热情的方向。《勃朗特一家的故事》中描述的动人场景一直在我脑海里:寒冷空旷的约克郡乡间,荒野中的石屋里,昏暗的烛光映照在勃朗特姐妹脸上;她们年幼孤独,离群索居,但以纸笔构筑着一个细腻而宏大的史诗世界。灌注在书写中的热情,照亮了她们的内心,也最终照亮了英国的文坛。
每天晚祷过后,三姐妹会放下手里的针线活,绕着餐桌一圈圈地踱步,聊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打算。看上去当家庭女教师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家中贫困,她们要挣钱去帮助家中唯一的兄弟——勃兰威尔·勃朗特。他自小英俊帅气,才华横溢,擅长写作与绘画,是姐妹们与老父亲的骄傲和希望。
没有人知道,三姐妹已经以“贝尔兄弟”的名义在伦敦出了书,独立卓然的《简·爱》受到了读者欢迎,迅速地蜚声国际。
还在上高中的我也找到了投入自己热情的地方。每周六中午,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总会拐去市里的图书城,在其中淘换更多的“闲书”,其中也包括一本《夏洛蒂·勃朗特书信集》。每周省下的零花钱仅够我买上两三本书,而我在那个周末一定会读完。事实上,这也是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所在,我并非存心要学夏洛蒂的叛逆,只是实在难以停止罢了。
可是这有什么用呢?为什么不趁着这段时间多做几道我不擅长的数学题?我怀着愧疚感贪婪地读着那些全无用处的书,想起夏洛蒂在17岁时写给友人的话:“凡是我作出的正确决定,都那么短暂,那么脆弱,那么易碎,我有时不禁担心,恐怕我永远不会成为我应该成为的那样一个人。”
在这样的孤独中,是同样孤单的夏洛蒂陪着我。读着她年轻时写下的书信,我至少知道,有这些困惑的,并非我一人。
后来在大学中,一位台湾来的历史学教授的讲座,为我长久的困惑给出了一个答案:“历史吊诡的地方在于,再复杂、再重大的决定,往往都是在一两分钟的思考之后作出的——这一两分钟却要仰仗你过去所有教养的集合。所以人文素养对学生来说是那么重要。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需要它,但这样的机会却随时可能在你生活中出现,改变你的生活。甚至改变你所处的社会。”
而那样的学生,是他们在高校中想要培养的。
我应当后悔那样度过我的高中吗?其实当时能想到的最糟糕的事情,后来都发生在了我的身上。但也许我应该感谢夏洛蒂·勃朗特,她的经历与信念帮助我一直寻找并坚持着最后的一丝自己。事实上,几年以后,因为一直未放下的兴趣,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事情,也悄然降临:我终究还是成了自己。
但在大学中听着教授讲座的我,尚不知道这一点。我只是听着他的讲话,感慨唏嘘。
“所有我们学习的东西,都是一块敲门砖。你拿它一遍遍地敲击知识殿堂的大门,你以为自己会看到什么名家、大师、神仙、上帝……但是最后从那门里走出来的,一定是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