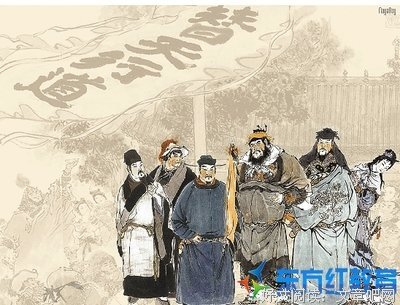
《和平与战争》是一本由卡列维·霍尔斯蒂 编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的341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005-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和平与战争》精选点评:
●非常标准的正统学术著作,引文丰富,方法严谨,资料扎实,当然也比较枯燥,可读性很差,作者是典型欧美老学究,对近几百年的(欧洲为主)国际冲突与和解进行相当系统的研究与分析,对历史演变阐述的很全面也很认真,仔细读的话还是有不少收获的。缺点是后半段过于冗长乏味(尤其是对威尔逊的歌颂),成书时间过早(80年代末),对近期的国际战争变化毫无论述,稍嫌过时
●回答了三个问题:1648年以来国家卷入战争所求的目的是什么,国家(主要是政治领导人)对战争的态度演变是怎样的,战后的和平协定该如何评估。反对现实主义,不赞同克劳塞维茨在核时代的适用性。霍尔斯蒂持着一种历史进步主义的论调。
●“从数据中反映出的一般模式是:相对抽象的问题——民族自决、政治基本原理和意识形态、队同族人的同情心——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战争根源,而诸如领土和财富等具体问题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对此模式的一种可能解释是,政府有能力针对具体类型的问题创建法律体制和其他避免冲突的体制,而针对抽象问题则很难形成这样的体制。”
●努力构建合理、稳定、较少战争倾向的国际秩序
●我敢打赌,读完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读完这本的效果是一样的……
●唯二能读下去的俄国作家的长篇小说
●看看作者和我理解的人为什么战争有啥不一样
●这个名字也好难认,看完脑子好乱。
●罗列 了许多,很多数据,挺喜欢这样子的编排的,因为之前很多战争具体数据如何不是很清楚~
●有矛盾-------战争----------和平后解决战前矛盾,但又造成新矛盾------战争
《和平与战争》读后感(一):和平与战争
本书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战争?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即提出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进行切入:是什么样的争议问题引发了冲突?决策者对待战争的态度是什么样的?调停人为建立国际秩序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及措施?调停人的策略可分为三类:一是以惩罚与优势来实现和平的策略,二是通过均势实现和平的策略,三是通过变革来实现和平的策略。作者认为,最为可行的办法是均势策略与变革策略的结合。本书论证逻辑有力,但又不囿于严格学术论证,更为诉诸人们的常识和直觉没在叙述风格上体现了历史的描述与科学分析的有机结合。
《和平与战争》读后感(二):和平与战争
正在看Holsti的这本书
感觉真的很好
作者并未试图解释战争的原因
而是从历史的角度 用描述细致了刻画了威斯特伐利亚至现代以来的主要战争 这种刻画是在连贯的三个命题下进行的
战争的议题 是因为什么打起来
战争的意义 打的目的是什么 什么背景下打起来的
以及战后的合约和下一次战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没有仔细看 案例部分只看了冷战至今的部分
案例之后作者归纳总结时又概括了战争议题几百年来的变化等内容
总之 这是近期来看到的比较好的一本著作
Holsti字里行间透露着一种对历史驾轻就熟 闲庭信步的感觉
同时又掌握了近代以来战争的数据
言之有据 言之有物 言之有理 言之深入
赞赏!
另:译者翻译的很好,流畅、准确。
《和平与战争》读后感(三):讲和不丢人
文/柳展雄
lt;<新周刊>>第441期
在漫长的历史中,战争似乎是唱主角的。据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的5164年中,世界上共发生战争14513次,只有329年是和平的。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何等慷慨激昂,何等痛快淋漓,但当敌我实力悬殊,是否非要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赌国运之战呢?
战的反面就是“和”,“和”通常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或给钱,或割地,有时甚至付出女人,总而言之,就是通过一定的利益支付达到息兵止戈的目的。
讲和在人类历史中早已有之,无论西方的埃及艳后,还是中国两汉时的和亲政策,无不是在以和为贵。在力量不如对手的时候,以低成本使国家暂时获得安全保障。
经过几千年的演变,讲和已经变成了国与国之间经常使用的外交手段,这比过去动辄开战,不仅减少了生灵涂炭,还让世界进入现代秩序之中,国家运营成本更加合理。
但讲和必须建立在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必须以民族与国家生存为根本目的,或卧薪尝胆,或四两拨千斤。一味卑躬屈膝,下场便如慕尼黑协定之后的捷克,亡国指日可待;一味地强硬,更如庚子年与天下万国宣战的大清朝,不作绝不会死。
宋朝每年只用30万两白银就换来百年和平,这买卖太划算了。
宋代的澶渊之盟,无论成本还是效果,都是讲和的典范,它使敌对双方保持了百年和平。
民间演义把宋真宗塑造成宋高宗的形象,事实上,赵恒从小喜欢排兵布阵的打仗游戏,并不是怯懦之辈。公元999年9月,契丹犯边,宋真宗御驾亲征,打赢裴村之战,击退辽军。公元1004年,辽军再度入侵,深入宋朝境内,澶州之战是真宗第二次亲征,也不是寇准逼的。
在人们印象中,宋朝总是积贫积弱,其实,宋军一点也不弱,辽国南侵的途中,打了三次败仗,损失最大的瀛州之战,伤亡三万多人。抵达澶州后,统军萧挞凛自恃勇武,率数十轻骑在城下巡视,结果被伏驽射杀,头部中箭坠马,辽军士气受挫。在这种腹背受攻的情况下,萧太后只得罢兵议和,是为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的性质,和后来秦桧、贾似道签订的耻辱合约完全不同。南宋先后对金、元称臣,但在澶渊之盟中,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而且从辈分上讲,宋朝还占了便宜——辽圣宗年幼,管宋真宗叫大哥。
《辽史》讳言自家皇帝当了小弟,便委婉地称萧太后当了人家叔母。在领土问题上,宋朝也是寸土不让。萧太后开战的借口就是,后周从辽手中占据了关南十县地,契丹人要讨回来。宋真宗的态度是可以给钱,坚决不能给地。
宋朝谈判代表曹利用出使之前,真宗出价底线是一百万银两,而寇准则更少,只给了三十万。
契丹人总共不过百万人口,天天打猎游牧,土豪的世界哪里能懂?遂提出了一个在契丹人看来数目极大的开价——数十万两。面对如此“屌丝”的开价,曹利用真是做梦都笑出声来,这买卖自然很顺利地谈下来了。
曹利用回来请见时,皇帝正在吃饭,侍者就问曹利用许给契丹多少银两。曹利用没有说话,只是伸出三个手指放在额头上,意思是三十万两。
侍者误以为是三百万两,真宗得知后大惊:“太多了,太多了。”便召见他亲自盘问。曹利用战战兢兢地答道:“三十万两。”
赵恒听完嘀咕一声:“才三十万,这么少。”
三十万确实是很小的数字,相当于一个经济发达州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但对于契丹国而言,却是一笔巨款。宋每年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岁币。看上去吃亏,但如果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军费要三千万两,成本远高于岁币。再考虑到两国的边境贸易当中,先进的宋朝占优势,仅茶叶一项的入超就能弥补岁币。
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划算的一笔讲和买卖,创造了双赢的结局,贫穷的契丹获得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北宋则了却最大的边患,为仁宗朝的文治巅峰创造了前提条件。
边境自此“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于戈”,在接下来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内,宋代创造了后人再难比肩的灿烂文明。
难道宋代真的是丧权辱国吗?史学家黄仁宇倒说了句公道话:“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这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
宋朝也不是不思进取,宋神宗留下遗训,恢复燕云者封王。可以说宋朝初年的隐忍,只是力量不足时的权宜之计。到了北宋末年,他们在辽国虚弱时也与金国订下“海上之盟”,谋夺回燕云十六州,但那已是另一个故事了。
内忧外患的明朝,因为死不讲和失去了最后的生存机会。
现在,在民间流传一种看法:大明朝是“不和亲,不割地,不输款,天子守国门”。这等民族主义炙烈的豪言壮语虽无确据,但大明270余年历史,的确是这么做的,只是到头来,强硬反被强硬误。
大明朝的强硬一直持续到17世纪,岁月的年轮进入到崇祯皇帝当朝,只是这时的大明早已外强中干,连年天灾,断绝了国家的税收,导致大批百姓造反起义,而外部也有强大的敌人——满州崛起,国家进入了生死存亡之时。
陈新甲,时任兵部尚书,主持明朝最后一次对满洲的和谈。当时,松锦之战即将结束,明朝失去对东北的控制权,而南方的李自成、张献忠横扫中原,官军两线作战,左支右绌,疲于奔命。
即使强硬如大明,也不会在这样的局势下死心眼到底。陈新甲主张与后金暂时达成和议,缓解危机。但一向愤怒惯了的大明朝野很难扭转牛脾气。之前,大明朝已经有过两次议和,结果袁崇焕以“谋款通敌”之罪被磔,支持他的内阁大臣钱龙锡发配边疆;杨嗣昌主持议和,弄得举朝哗然,被迫辞职。
有了前车之鉴,这次和谈不得不私下进行。陈新甲派遣手下马绍愉潜入沈阳,携带崇祯敕书,与皇太极议和。然而皇太极认为和谈“真伪不得而知”,但他还是本着和平友好共处的原则,做出回复,派人保护信使回国。
马绍愉返回京师后,将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呈送上来,陈新甲赶着上朝议事,就将信件随手放在一边。
接下来,历史给大明开了一个大玩笑。秘书把办公桌上的密件误以为是公开报告,未请示领导就开始抄传,拿到《邸报》(当时的政府机关报)上发表了。这一下可惹了大祸,本来是保密的议和过程,一下子被群臣百官览阅,朝野为之哗然,很多大臣上书弹劾。
即使强势如崇祯皇帝也抗不住打了鸡血的文官群体。朝野上下一直坚定地认为满州建奴是国贼凶寇,势不两立,主和之人无一不身负恶名。
陈新甲也有错,他作为国防部的最高长官,没有分毫保密意识,以至于机密文件外传。最终,崇祯只得将陈新甲抛出平息舆论,可怜这位国防部长被斩首弃市,明朝也失去了起死回生的最后机会。
两年后崇祯上吊煤山,死前的遗言是“诸臣误我”。真不知道他说的是陈新甲,还是那些反对议和的“满朝忠正”。
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大清把英国公使当皮球踢,结果踢来了洋枪洋炮。
近代史上,拿中国和日本进行对比,成了一个习惯。传统的印象里,满清不懂近代国际秩序,而日本则是欺软怕硬。实际上,满清与其说是无知愚蠢,不如说是小聪明太多。
江户幕府和普鲁士建交,由于不了解德国正在统一的特殊情况,日本人以为只和普鲁士一国签“不平等条约”,结果对方把参加德意志关税同盟各诸侯国通通算进去。日本全权代表崛利熙发现吃了大亏,为此忧愤自杀。
反观大清朝,耆英在修订《南京条约》的时候,想的不是和战大局,而是用人情笼络英方公使璞鼎查,给璞爵士的大儿子做干爹,还互相交换老婆的照片。
事后诸葛亮地看,《南京条约》是近代史的开端,是国家的奇耻大辱,可回到历史现场,当时的大清完全不把它当回事。《南京条约》签订后,签约文本一直存放在两广总督衙门,从未颁行过。两江总督何桂清曾向咸丰奏报,历来办理夷务的大臣,只知道有和约之名,而未见其文。而大部分下级官员根本不知道大清签过这条约。
《南京条约》签完后,西方列强相继模仿英国,和清政府签约,其中就有一项解禁基督教的条令。法国修士感谢天主的恩赐,兴冲冲跑到内地去传教,结果地方官员不知道朝廷下达了宗教弛禁令,把福音拦在门外。1845年8月,法国人向北京政府抗议,强烈要求中方公布弛禁令,半年后道光帝不情愿地下令:各地官吏不得查禁天主教。
条约体系建立后,原本的蛮夷与天朝平等相待,让人有些不习惯。官府在战场上打不过洋人,暗中怂恿民众搞“非暴力不合作”,今天烧洋人的铺子,明天砸使节的公馆,原本繁华的广州也日渐衰落。
其他的通商口岸更是如此,厦门所谓的贸易,更多的是劳工出口;宁波更不值一提,1850年的海关收入只有110余两。福州的情况最差,最先来到福州的是一艘美国船,停在港口一个月都没人理睬,无奈只好减价,可是减价也没生意。1846年到1847年,再也没有一艘外国船到福州做生意,清政府成功地维持了“闭关锁国”的奇迹。
英国人哀叹,五口通商徒有虚名,要不是还有个上海,《南京条约》简直成了一纸空文。
无奈之下,英国公使找清朝高层上访,先找到了两江总督,但两江总督告诉他们,只有两广总督能代理夷务;公使只得再找两广总督,两广总督说,他虽是钦差,却无便宜行事之权,外交事务都需皇上恩准。
英国人最后来到天津,希望直隶总督替他们投书皇上,直隶总督回复:夷务全归两广总督管,请南下回广东。而两广总督早在给皇帝的密折附片里留了一手:夷人有什么事,只管往地方推。
1857年,英国人受够了大清君臣互相“踢皮球”,操起洋枪洋炮,进入北京城讨要说法。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因为对外界无知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是知道游戏规则却不遵守,咎由自取。
英国人发动的战争,还有个意外收获,军队攻下广州时,发现了耆英的奏折,这厮当面认外国干儿子,背地里向皇上解释这是“驯兽”之道,对付“犬羊之性”的蛮夷要虚与委蛇。
英法联军打到天津后,清朝再次派耆英和谈。双方会面时,英国人拿出这份奏折,当面朗诵耆英背后骂夷人的句子,然后向对方表示,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
铁血宰相俾斯麦最懂得讲和的艺术——打赢了也得见好就收。
俾斯麦或许是被误解最深的政治人物,世界名人语录簿不会漏掉这句:“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演说和多数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而只能用铁和血来解决。”这条格言让很多青年热血沸腾,但是俾斯麦讲这句话的背景鲜为人知。
铁血宰相不是向敌国喊话,而是当议会否决他的提案时,俾斯麦才发飙撒泼。人家针对的,可不是外部敌人。
如果仅仅靠强大的武力就能取胜,那么德国早在腓特烈大帝的时代就该统一了。俾斯麦不是穷兵黩武的鹰派,而是灵活务实的外交官。在普法战争后,俾斯麦不主张割去洛林与阿尔萨斯,一直摆出法德和解的姿态。
面对庞大的俄国,俾斯麦安抚和好,从来不把他们当做劣等斯拉夫人。“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才是俾斯麦的真正信条。
历数统一德意志的进程,普奥战争最为反复曲折。传统上,哈布斯堡家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正宗嫡传,许多民族主义者希望由奥地利领导日耳曼人,是为“大德意志”方案。俾斯麦的算盘则是踢出奥地利,宁可要一个“小德意志”,也不要全体日耳曼的大一统。
战争开始前,欧洲的观察家普遍认为奥地利会获胜,俾斯麦本人对于军事胜利也无绝对把握,他是怀揣毒药上的前线。在萨多瓦会战,依靠大胆的战略,参谋本部的计划还有及时赶到的后备军,普军打了一场漂亮的战役,但后面发生的事更为重要。
在大获全胜的时刻,俾斯麦要求见好就收,及时撤退,用他自己的原话,这是“往国王和将军手中的香槟酒里泼冷水”。军人们只想着光荣的胜利,长驱直入占领维也纳,迫使对手缔结城下之盟。俾斯麦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样只会让法国人渔翁得利,只怕普军未入维也纳,法军已过莱茵河。
威廉一世表态,普鲁士的军队必须在维也纳举行凯旋仪式,奥地利必须受到割让土地的惩罚。无计可施的俾斯麦断然递交了辞呈,然后发飙撒泼打碎瓷器,甚至萌生跳楼自杀的念头。关键时刻,王储出来调解,国王终于遵从了俾斯麦的建议。普奥签订了《布拉格条约》,德意志南部的诸侯与哈布斯堡王朝脱离臣属关系,和普鲁士结成联邦。
对失败者奥地利来说,这算是一份宽大体面的和约。在接下来的普法战争中,奥地利并没有想复仇而支持法国,从此往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哈布斯堡家族一直是德国忠心的跟随者。
《和平与战争》读后感(四):讲和不丢人
文/柳展雄
lt;<新周刊>>第441期
在漫长的历史中,战争似乎是唱主角的。据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的5164年中,世界上共发生战争14513次,只有329年是和平的。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何等慷慨激昂,何等痛快淋漓,但当敌我实力悬殊,是否非要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赌国运之战呢?
战的反面就是“和”,“和”通常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或给钱,或割地,有时甚至付出女人,总而言之,就是通过一定的利益支付达到息兵止戈的目的。
讲和在人类历史中早已有之,无论西方的埃及艳后,还是中国两汉时的和亲政策,无不是在以和为贵。在力量不如对手的时候,以低成本使国家暂时获得安全保障。
经过几千年的演变,讲和已经变成了国与国之间经常使用的外交手段,这比过去动辄开战,不仅减少了生灵涂炭,还让世界进入现代秩序之中,国家运营成本更加合理。
但讲和必须建立在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必须以民族与国家生存为根本目的,或卧薪尝胆,或四两拨千斤。一味卑躬屈膝,下场便如慕尼黑协定之后的捷克,亡国指日可待;一味地强硬,更如庚子年与天下万国宣战的大清朝,不作绝不会死。
宋朝每年只用30万两白银就换来百年和平,这买卖太划算了。
宋代的澶渊之盟,无论成本还是效果,都是讲和的典范,它使敌对双方保持了百年和平。
民间演义把宋真宗塑造成宋高宗的形象,事实上,赵恒从小喜欢排兵布阵的打仗游戏,并不是怯懦之辈。公元999年9月,契丹犯边,宋真宗御驾亲征,打赢裴村之战,击退辽军。公元1004年,辽军再度入侵,深入宋朝境内,澶州之战是真宗第二次亲征,也不是寇准逼的。
在人们印象中,宋朝总是积贫积弱,其实,宋军一点也不弱,辽国南侵的途中,打了三次败仗,损失最大的瀛州之战,伤亡三万多人。抵达澶州后,统军萧挞凛自恃勇武,率数十轻骑在城下巡视,结果被伏驽射杀,头部中箭坠马,辽军士气受挫。在这种腹背受攻的情况下,萧太后只得罢兵议和,是为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的性质,和后来秦桧、贾似道签订的耻辱合约完全不同。南宋先后对金、元称臣,但在澶渊之盟中,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而且从辈分上讲,宋朝还占了便宜——辽圣宗年幼,管宋真宗叫大哥。
《辽史》讳言自家皇帝当了小弟,便委婉地称萧太后当了人家叔母。在领土问题上,宋朝也是寸土不让。萧太后开战的借口就是,后周从辽手中占据了关南十县地,契丹人要讨回来。宋真宗的态度是可以给钱,坚决不能给地。
宋朝谈判代表曹利用出使之前,真宗出价底线是一百万银两,而寇准则更少,只给了三十万。
契丹人总共不过百万人口,天天打猎游牧,土豪的世界哪里能懂?遂提出了一个在契丹人看来数目极大的开价——数十万两。面对如此“屌丝”的开价,曹利用真是做梦都笑出声来,这买卖自然很顺利地谈下来了。
曹利用回来请见时,皇帝正在吃饭,侍者就问曹利用许给契丹多少银两。曹利用没有说话,只是伸出三个手指放在额头上,意思是三十万两。
侍者误以为是三百万两,真宗得知后大惊:“太多了,太多了。”便召见他亲自盘问。曹利用战战兢兢地答道:“三十万两。”
赵恒听完嘀咕一声:“才三十万,这么少。”
三十万确实是很小的数字,相当于一个经济发达州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但对于契丹国而言,却是一笔巨款。宋每年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岁币。看上去吃亏,但如果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军费要三千万两,成本远高于岁币。再考虑到两国的边境贸易当中,先进的宋朝占优势,仅茶叶一项的入超就能弥补岁币。
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划算的一笔讲和买卖,创造了双赢的结局,贫穷的契丹获得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北宋则了却最大的边患,为仁宗朝的文治巅峰创造了前提条件。
边境自此“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于戈”,在接下来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内,宋代创造了后人再难比肩的灿烂文明。
难道宋代真的是丧权辱国吗?史学家黄仁宇倒说了句公道话:“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这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
宋朝也不是不思进取,宋神宗留下遗训,恢复燕云者封王。可以说宋朝初年的隐忍,只是力量不足时的权宜之计。到了北宋末年,他们在辽国虚弱时也与金国订下“海上之盟”,谋夺回燕云十六州,但那已是另一个故事了。
内忧外患的明朝,因为死不讲和失去了最后的生存机会。
现在,在民间流传一种看法:大明朝是“不和亲,不割地,不输款,天子守国门”。这等民族主义炙烈的豪言壮语虽无确据,但大明270余年历史,的确是这么做的,只是到头来,强硬反被强硬误。
大明朝的强硬一直持续到17世纪,岁月的年轮进入到崇祯皇帝当朝,只是这时的大明早已外强中干,连年天灾,断绝了国家的税收,导致大批百姓造反起义,而外部也有强大的敌人——满州崛起,国家进入了生死存亡之时。
陈新甲,时任兵部尚书,主持明朝最后一次对满洲的和谈。当时,松锦之战即将结束,明朝失去对东北的控制权,而南方的李自成、张献忠横扫中原,官军两线作战,左支右绌,疲于奔命。
即使强硬如大明,也不会在这样的局势下死心眼到底。陈新甲主张与后金暂时达成和议,缓解危机。但一向愤怒惯了的大明朝野很难扭转牛脾气。之前,大明朝已经有过两次议和,结果袁崇焕以“谋款通敌”之罪被磔,支持他的内阁大臣钱龙锡发配边疆;杨嗣昌主持议和,弄得举朝哗然,被迫辞职。
有了前车之鉴,这次和谈不得不私下进行。陈新甲派遣手下马绍愉潜入沈阳,携带崇祯敕书,与皇太极议和。然而皇太极认为和谈“真伪不得而知”,但他还是本着和平友好共处的原则,做出回复,派人保护信使回国。
马绍愉返回京师后,将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呈送上来,陈新甲赶着上朝议事,就将信件随手放在一边。
接下来,历史给大明开了一个大玩笑。秘书把办公桌上的密件误以为是公开报告,未请示领导就开始抄传,拿到《邸报》(当时的政府机关报)上发表了。这一下可惹了大祸,本来是保密的议和过程,一下子被群臣百官览阅,朝野为之哗然,很多大臣上书弹劾。
即使强势如崇祯皇帝也抗不住打了鸡血的文官群体。朝野上下一直坚定地认为满州建奴是国贼凶寇,势不两立,主和之人无一不身负恶名。
陈新甲也有错,他作为国防部的最高长官,没有分毫保密意识,以至于机密文件外传。最终,崇祯只得将陈新甲抛出平息舆论,可怜这位国防部长被斩首弃市,明朝也失去了起死回生的最后机会。
两年后崇祯上吊煤山,死前的遗言是“诸臣误我”。真不知道他说的是陈新甲,还是那些反对议和的“满朝忠正”。
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大清把英国公使当皮球踢,结果踢来了洋枪洋炮。
近代史上,拿中国和日本进行对比,成了一个习惯。传统的印象里,满清不懂近代国际秩序,而日本则是欺软怕硬。实际上,满清与其说是无知愚蠢,不如说是小聪明太多。
江户幕府和普鲁士建交,由于不了解德国正在统一的特殊情况,日本人以为只和普鲁士一国签“不平等条约”,结果对方把参加德意志关税同盟各诸侯国通通算进去。日本全权代表崛利熙发现吃了大亏,为此忧愤自杀。
反观大清朝,耆英在修订《南京条约》的时候,想的不是和战大局,而是用人情笼络英方公使璞鼎查,给璞爵士的大儿子做干爹,还互相交换老婆的照片。
事后诸葛亮地看,《南京条约》是近代史的开端,是国家的奇耻大辱,可回到历史现场,当时的大清完全不把它当回事。《南京条约》签订后,签约文本一直存放在两广总督衙门,从未颁行过。两江总督何桂清曾向咸丰奏报,历来办理夷务的大臣,只知道有和约之名,而未见其文。而大部分下级官员根本不知道大清签过这条约。
《南京条约》签完后,西方列强相继模仿英国,和清政府签约,其中就有一项解禁基督教的条令。法国修士感谢天主的恩赐,兴冲冲跑到内地去传教,结果地方官员不知道朝廷下达了宗教弛禁令,把福音拦在门外。1845年8月,法国人向北京政府抗议,强烈要求中方公布弛禁令,半年后道光帝不情愿地下令:各地官吏不得查禁天主教。
条约体系建立后,原本的蛮夷与天朝平等相待,让人有些不习惯。官府在战场上打不过洋人,暗中怂恿民众搞“非暴力不合作”,今天烧洋人的铺子,明天砸使节的公馆,原本繁华的广州也日渐衰落。
其他的通商口岸更是如此,厦门所谓的贸易,更多的是劳工出口;宁波更不值一提,1850年的海关收入只有110余两。福州的情况最差,最先来到福州的是一艘美国船,停在港口一个月都没人理睬,无奈只好减价,可是减价也没生意。1846年到1847年,再也没有一艘外国船到福州做生意,清政府成功地维持了“闭关锁国”的奇迹。
英国人哀叹,五口通商徒有虚名,要不是还有个上海,《南京条约》简直成了一纸空文。
无奈之下,英国公使找清朝高层上访,先找到了两江总督,但两江总督告诉他们,只有两广总督能代理夷务;公使只得再找两广总督,两广总督说,他虽是钦差,却无便宜行事之权,外交事务都需皇上恩准。
英国人最后来到天津,希望直隶总督替他们投书皇上,直隶总督回复:夷务全归两广总督管,请南下回广东。而两广总督早在给皇帝的密折附片里留了一手:夷人有什么事,只管往地方推。
1857年,英国人受够了大清君臣互相“踢皮球”,操起洋枪洋炮,进入北京城讨要说法。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因为对外界无知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是知道游戏规则却不遵守,咎由自取。
英国人发动的战争,还有个意外收获,军队攻下广州时,发现了耆英的奏折,这厮当面认外国干儿子,背地里向皇上解释这是“驯兽”之道,对付“犬羊之性”的蛮夷要虚与委蛇。
英法联军打到天津后,清朝再次派耆英和谈。双方会面时,英国人拿出这份奏折,当面朗诵耆英背后骂夷人的句子,然后向对方表示,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
铁血宰相俾斯麦最懂得讲和的艺术——打赢了也得见好就收。
俾斯麦或许是被误解最深的政治人物,世界名人语录簿不会漏掉这句:“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演说和多数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而只能用铁和血来解决。”这条格言让很多青年热血沸腾,但是俾斯麦讲这句话的背景鲜为人知。
铁血宰相不是向敌国喊话,而是当议会否决他的提案时,俾斯麦才发飙撒泼。人家针对的,可不是外部敌人。
如果仅仅靠强大的武力就能取胜,那么德国早在腓特烈大帝的时代就该统一了。俾斯麦不是穷兵黩武的鹰派,而是灵活务实的外交官。在普法战争后,俾斯麦不主张割去洛林与阿尔萨斯,一直摆出法德和解的姿态。
面对庞大的俄国,俾斯麦安抚和好,从来不把他们当做劣等斯拉夫人。“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才是俾斯麦的真正信条。
历数统一德意志的进程,普奥战争最为反复曲折。传统上,哈布斯堡家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正宗嫡传,许多民族主义者希望由奥地利领导日耳曼人,是为“大德意志”方案。俾斯麦的算盘则是踢出奥地利,宁可要一个“小德意志”,也不要全体日耳曼的大一统。
战争开始前,欧洲的观察家普遍认为奥地利会获胜,俾斯麦本人对于军事胜利也无绝对把握,他是怀揣毒药上的前线。在萨多瓦会战,依靠大胆的战略,参谋本部的计划还有及时赶到的后备军,普军打了一场漂亮的战役,但后面发生的事更为重要。
在大获全胜的时刻,俾斯麦要求见好就收,及时撤退,用他自己的原话,这是“往国王和将军手中的香槟酒里泼冷水”。军人们只想着光荣的胜利,长驱直入占领维也纳,迫使对手缔结城下之盟。俾斯麦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样只会让法国人渔翁得利,只怕普军未入维也纳,法军已过莱茵河。
威廉一世表态,普鲁士的军队必须在维也纳举行凯旋仪式,奥地利必须受到割让土地的惩罚。无计可施的俾斯麦断然递交了辞呈,然后发飙撒泼打碎瓷器,甚至萌生跳楼自杀的念头。关键时刻,王储出来调解,国王终于遵从了俾斯麦的建议。普奥签订了《布拉格条约》,德意志南部的诸侯与哈布斯堡王朝脱离臣属关系,和普鲁士结成联邦。
对失败者奥地利来说,这算是一份宽大体面的和约。在接下来的普法战争中,奥地利并没有想复仇而支持法国,从此往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哈布斯堡家族一直是德国忠心的跟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