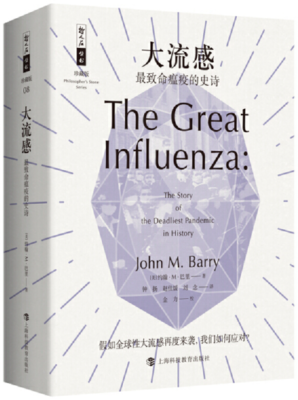
《史学导论》是一本由约翰·托什 (John Tosh)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3.00元,页数:31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史学导论》精选点评:
●补标记
●开篇宏大,语言精妙,全书内容涵盖历史学科诸多重点,还是很informative的.但是后面几章结构较散乱,逻辑性与关联性并不如人意。看起来很像一门导论课程上上课提纲。 PS:做完笔记和整理,思量一下,我决定还是由4分改回5分。
●重点阅读第五章、第八章,条理清晰。
●本书名为“pursuit of history”,翻译成“史学导论”还是较妥的,因为其结构比较零散,也无统略性的议论,标准而优秀的教科书。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独到评论值得思考,译者在后记中也进行了探讨。
●最后几章囫囵吞枣了
●翻译捉急。。。。
●提綱挈領
●这本书告诉了我两件事。 第一,这种跨专业的比较难懂的学术书,不要去借图书馆的,笔记会死人的。 第二,后现代真闹心啊……
●干货不多,可读性很强
●初中時讀過的一本書
《史学导论》读后感(一):真的觉得不错,理由如下
题目如题
从导论来看
至少从思维框架和多视角的反思而言,本书让我比较满意,由于我不是历史学专业人士,不好评价其框架的体系是否够全,但是我可以说至少这些不同的范式被提出来让我对历史学有了一个比较有启发性的认识。
最为重要的是本书体现了一种反思性,做手中的事情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和不断对其意义进行思辨,那么事件的意义将不仅仅局限于事件本身了。
另外有限的阅读中认为其逻辑体系是很清晰的,换而言之有一个清晰的框架知道我们理解历史学这门学科,这不就是导论能够完成的最为紧要任务么?
《史学导论》读后感(二):一本引人入胜的教材
这本书详略得当地介绍了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主要内容,也较为客观公正地评述了世界历史学研究中主要的思想流派。内容翔实,较之国内大多数的课本,让人耳目一新,因为作者是站在这个意识形态之外的史学家,他的观点与评论不受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把握。正如书中所言,开放的历史学家应该心胸宽广。乐于接受对历史学研究过程中产生的不同观点和思想,而不是千篇一律地用一种方法一个思想去研究历史,或许是我们应该解决的最大问题。毕竟历史不是政治,历史主义的态度也不局限于政治。所以阅读该书,对广大喜爱历史本身(不仅仅是存在与故事传奇之中的历史)的朋友们来说,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感觉。推荐!
《史学导论》读后感(三):“人人都是他自身的历史学家”
“人人都是他自身的历史学家”
——《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读后札记
面对隐瞒真相而探望真相,出于人的好奇与证明事实的天性。
寻找社会纪忆与对抗集体健忘症,除了勇气之外,重要的是方法和方向。
《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是实际上是一本现代历史学概论的教科书,它作者英国人约翰•托什(John Tosh)写作此书时,秉持这样的理由:“有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已经超越了文化政治学的范畴,而将历史学的专业技能置于优先的地位。”这即所谓的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的问题。
约翰•托什(John Tosh)在第一章“历史意识”里,提出了“社会记忆”这样的观念,并说“对任何一个拥有集体认同的社会群体而言,必然有一种对事件和经验的共同诠释,而这个群体就是在这些事件和经验中逐渐成的。”
他还特别指出:“但社会记忆也可能被用于维系一种受压迫、被排斥或身处逆境的感觉,这些因素说明了社会记忆的一些最强烈的表达方式的产生原因。”
2008年5月1日《南方周末》刊登的《读林昭十四万字书》一文,就是一篇发掘出来的“从历史中隐去”的命题,不少人首次阅读这样震撼的文字,产生出大地骤然摇晃的感觉。
历史主义就是将过去从现在解放出来。透过去的视点进行观察,并以奥林匹亚山上的希腊诸神的那种超然的和不受情感左右的公正性和准确性的记述历史。
为了做到如此,约翰•托什(John Tosh)提出历史意识的三个原则:一是不以时代错置,即一种历史研究中的错误,将来自一个历史时期(通常是现代)的因素应用于较早的一个时期,诸如将现代语言和观念用于历史题材的电影和戏剧中;二是将“另一种过去”置于其背景之下;三是承认历史过程的存在,并重视它的连续性。
以上历史意识的三个原则,实际上胡塞尔的“现象学”在历史学中的运用。“回到事情本身”的方向,将事实“悬置”的方法都于之相似。
约翰•托什(John Tosh)还提出了“传统的扭曲效应”,并说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挑战由社会因素促成的对历史的错误陈述。还说直面痛苦:作为疗伤手段的历史学。举例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1991年间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讨论苏联体制缺陷中执行了公开性政策和从根本上重建苏联社会政策。这样向历史学家公开档案资料,允许苏联人民公开表达在斯大林时期遭受的极度痛苦。不管俄罗斯未来会发生什么,但对过去的集体经验不可能被取消。
这有点类似一场巨灾之后的社会集体心理干预。约翰•托什(John Tosh)引用了另一位历史学家詹姆斯•约尔用治疗学的术语来描述这种与前时的痛苦的纠葛:
“正如心理分析家通过揭示如何认识有关动机和个人经历的事实,以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一样;当代历史学家也是通过使人们能够理解那些将我们的世界与我们的社会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力量(不管是多么的骇人听闻),来帮助我们去面对现实和未来。”
实际上有了这样的历史意识之后,“人人都是他自身的历史学家”。
当下许许多多的新散文随笔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如谢泳先生、傅国涌先生等诸公关于民国的随笔,还有2007年众多网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回顾与正视,无不如此。
怎么样进行触摸到历史的真相?在《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中除了运用一般常规的技术手段之外,如利用官方的报纸、档案、文学艺术作品、私人信件、日记,还专门着重了口述史与计量史学运用的讲述。这就开辟了在民间的历史研究的可能性。
“人人都是他自身的历史学家”。在有关非精英的历史研究中,还提出了对商业史、性别史、地方史、家庭史等等的研究,让其在历史历时性中连续事件,在历史的共时性显示意义。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探索人们动机之外的解释:潜在的原因和长期结果;多层面分析;不管怎么样历史研究都是后知的。
编撰与解释。如果以约翰•托什(John Tosh)目光观察,历史编撰的形式一般有两种——作为描述的历史和作为叙述的历史——而当下,无论是谢泳先生、傅国涌先生等诸公关于民国的随笔,还是2007年民间网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回顾与正视,都只能归类于作为高度通俗化的描述的历史。
在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和语言霸权的论述时,约翰•托什(John Tosh)指出“解构”这种解读文本的创造性方法——依次是戏谑、反讽和颠覆——是后现代学术的标志。
为了避免进入误区,他说:“话语”不仅是一种语言使用的模式,而且是指一种形式的“权力/知识”并指出后现代主义的局限性:不过,有一种限度,超出这种限度,大多数历史学家是不会赞同后现代主义的。
“人人都是他自身的历史学家”。有时那怕为只言片语的诉说,对于被隐瞒与被毁坏的历史重建也是一砖一瓦。
2008-6-7于成都天开居
《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英]约翰•托什(John Tosh)著,吴英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33•00元。
《史学导论》读后感(四):一门高度多样性的学科
很庆幸能在大一就读完这本书。(虽然该书存在诸多问题,但应该仍碾压大陆史学概论的所有中文教材。非常适合历史学入门者阅读。另:15年英文版已出第六版。(有能力的话还是看英文最新版比较好,相比第四版变动较多))
本书为约翰·托什教授(主要研究英国社会史(性别史为主)、非洲史)为英国大学历史系“史学概论课程”写的教材。作为通识教材,它尽到了较客观全面地概述各种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责任【虽然有勉强地各打一棒取其中的嫌疑(比如对资料导向型历史研究的看法,对年鉴学派“总体史”野望和借鉴社会科学理论的态度,对后现代的回应,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介绍),而且全书弥漫着英国史学“历史主义”的传统“偏见”(划掉)?(相当和我口味的主张,一见钟情)】,全面(但毫不深入)地介绍了当代历史学学科(以英国历史学学界为主)的几乎所有方面的内容(尤2、5、7、8、11章改变了我对历史学的想象),适合入门者仔细研读,深思。
就目前来看,大陆大学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教育非常落后,至今仍有许多学生,甚至学者,竟把卡尔的《历史是什么?》作现代史学导论书籍推荐,令人惊愕。国内对近现代史学理论的介绍情况似乎极其糟糕,更遑论应用于学术研究了。史学大师巴勒克拉夫1979年写成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至今仍是大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中极广泛引用的参考资料,在历史学日新月异的当下,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国内以马克思主义史观为准绳写成的几本史学导论书籍,更是狭隘陈旧,令人难以下咽。我想,相比之下,约翰·托什的《史学导论》,可以作为史学导论/史学概论课的教材一用。托什大概认为,立志学习历史学者,应具有一定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知识,才能步入历史殿堂,才可能做出自己的史学研究。(就托什看来,英国历史学家在这方面的关注(至少时间上说)不如欧陆、美国)
自兰克以来,历史学这门学科飞速发展,日益多样化。如今,它的领域已经拓展到19世纪的先辈们难以想象的程度:历史学已成为一门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缺少一致性的学科。不过,正是近代史学研究高度多样化的特点,为历史学带来了无穷的发展活力。历史学应当避免成为一门狭隘划一的学科,多元的资料考证和选择(“作为选择者的历史学家”)、解释(或者不支持解释/深层次的因果分析(如泰勒))、撰述(或者不支持撰述(如加尔布雷斯))、研究内容(或是书写“总体史”的野心)……早已成为这门学科的魅力所在。如果用一种理论框定历史学研究,我会认为这门学科遭受了毁灭性的灾难,不再具有学术性意义。
托什建议,历史学还是应该保有一些基本的学科范式,在这个基础上,再做多样化研究。托什本人秉持历史主义(历史主义(historicism)有两种意义,本文取其中一种,即兰克等人所确立的一种历史研究倾向:对历史的研究必须是完全历史的;尽可能不受当下的观念或原理的影响(进入当时的历史背景);追求纯客观的叙述和历史的最大可能的还原/再现过去)的传统理念(这一点他非常坚持,以致失之偏颇地攻击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史学的挑战),他认为,尽管现在看来,传统(历史主义)史学的诸多目标已难达成(客观性、再现可能、理解可能、普遍的宏观叙事、拒斥理论等),但历史学家不应该放弃对历史真相的追寻、理解和最大可能地客观性复原。为此,应当有一些公认的学术准则和研究方式。虽然托什对后现代质疑的回应显得沧桑无力,但这种努力重构过往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在托什看来,这也是(至少是英国史学界)大部分历史学家的治史观念。出于对这一种精神的贯彻,我们必须不断拷问自己,这是否能最大程度接近过去的真相?永远保持怀疑的姿态,随时更新研究方法和范畴,勇于突破过往的观点,摒弃先入为主的理论和陈见,警惕任何历史意义、历史规律、历史必然、历史预测,不为当下价值取向扭曲学术研究……这是托什所倡导的治学理念。
托什绝不是保守的历史研究者。例如,他不抗拒理论,将理论作为具有启示意义的工具是“历史学家应用理论的最低合理性”,更进一步,他认为,不应用理论,历史学家很难把握一些重要的议题。对待理论的正确方式不是拒斥一切理论,而是求真地使用理论,不犯化约主义的错误,将理论放在历史下检验。他质疑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历史解释只有满足了写作时代的需要,才能被视为是真实的“的主张,但他支持,历史学者应该努力关注当下的现实性议题,研究具有现实相关性的论题。这并非出于宣传,而是希冀从研究中挖掘对现实有所意义的洞察。这种洞察不大可能具有什么“科学性”“规律性”,但他们或许能提供一些模糊的理解和对现实不大靠谱的短期序列预测。“只要历史学家还支持这种目标,那么,他们的学科就仍将会保持活力并要求获得社会的支持。”事实上,现实性话题总能反应在历史学研究趋势上。作者认为,新城市史、家庭史、非洲史、环境史、性别史、疾病史、宠物史等研究,都出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比起一昧强调历史主义原则,托什更愿意强调历史研究的多样化。在他看来,面对同样的史料(史料也需更多元、更广泛),不同的历史学家做出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撰述,这是历史学应有的模样。“历史学是一门包容性的学科,难于进行学科分类。这些区分(事件/结构,个体/群体,心态/物质力量)不应被视为正反性的对立特征,而应被视为在侧重点上是互补的,将他们总和在一起,就提供了真正把握复杂过去的可能性。”“如果历史学家将他们的视野局限在该学科的某一方面的话,如果他们对一种虚假的逻辑一致性感兴趣的话,那么,他们将会失去对很多研究对象的把握。”作者在书末如是说。多元的社会应当有也必然有多元的历史学研究;多元的历史学研究,亦是对多元社会的一曲礼赞。这一门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将保持其高度多样性的特色行走下去。
附:英文第四版、第六版目录
第四版
Historical awareness The uses of history The raw materials Using the sources The themes of mainstream history Writing and interpretation The limit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History by numbers Theories of meaning History by word of mouth第六版
Historical awareness The uses of historyMapping the fieldThe raw materialsUsing the sourcesWriting and interpretationThe limit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Cultural evidence and the cultural turnGender history and postcolonial historyMemory and the spoken wordHistory beyond academia(该章为第六版新设,其余章节同第五版)中文版翻译存在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