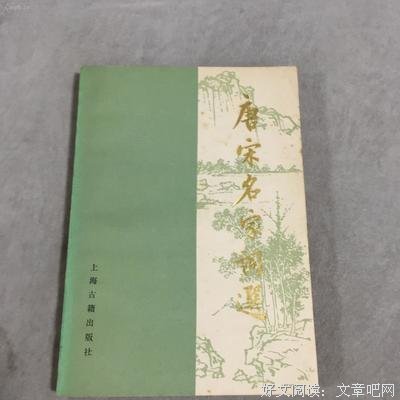
《唐宋名家词选》是一本由龙榆生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3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唐宋名家词选》精选点评:
●很多篇熟稔如旧友忽访,很多篇恍惚间似曾相识。原先最爱白石瘦拔清空之仙气,亦喜东坡旷达豪迈之性情,又叹稼轩只得梦里倥偬,竟求不得一腔热血报家国,而这一个选本里却念念难忘秦少游,或许是因为“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像是大悲喜大圆满中永远不说破的梦。
●好亲切,好熟悉,好喜欢!
●裒集选本,难就难在如何取舍篇目,如何用篇幅不长的小传,为词人发言。龙榆生先生全部做到了,并且还让古人一并来说话,取众人之不同声音,留待读者品析。
●不是这个版本
●本科时的启蒙书,大一之后的暑假读的
●趙杏根推薦的,讀了一遍抄了一遍。
●以为丢掉的书,居然又找到了,欣喜啊……
●好像读过,看着封面眼熟。
●排版不太喜欢
●印刷略弱==
《唐宋名家词选》读后感(一):想读读看
呃。
喜欢词比诗多一点。
总觉得词似乎比诗多一点味道。
这个版本看起来不错。
最近还有想找找看版本比较不错的《诗经》。
不想读那种一看就是应试教育下应付考试翻译默写的标准读本。
《唐宋名家词选》读后感(二):不如胡云翼的宋词选
昨天买了,看了。手头上是60s竖排繁体的胡云翼宋词选,高中时代就看。比较如下:
1、有人对胡云翼的词选角度和范围重点有意见,意思是豪放派多了。这个是时代的影响,中性一点说是审美观不一样,没法说。
2、胡云翼的本子资料多,有助于我们这种水平略低的人理解,同时提高文史水准。龙氏的这本资料太简略了,文化低,很多时候只能读个大概不求甚懂了。
3、现在的胡云翼版我没看过,不知道质量,手上这本龙氏的09年版比60s版的胡云翼本子印刷差多了。
《唐宋名家词选》读后感(三):如果你是个作人
如果你是个作人, 不喜欢简体字的大片空白,不喜欢看矫情兮兮的白话文赏析,不喜欢词作被一个个小数字小圈圈标注的密密麻麻, 那这个版的唐宋名家词选绝对是好选择, 其实...新书店里是找不到这书的, 反正我是没见过有重印,能不能碰的上就看运气了.
唐宋名家词是龙榆生为了讲课所选的, 选按时代和词家分, 每家选词若干. 它最让人喜欢的地方, 就是历代对一首词的点评, 或所作不同版本, 都会集在该首词后. 每个词家的最后又会辑录"集评"并且做"小传".
词选毕竟是选, 并不是全集, 但它的好处就是通过经典的选词和点评, 提供了一个比较快的途径, 让读它的人大致了解唐五代宋词的一脉相承, 与不同词家的风格.
这本书也是10年来唯一一本我不论在哪,都带在手头的书, 其他的书托运, 或暂存某处, 只有这本是跟着我, 我在哪, 它就在哪. 一直想找本新印的, 替代这本, 把它好好保存, 但是找不到, 每次去书店看到都是满坑满谷的精装彩绘插图本, 所以就这么着了吧.
《唐宋名家词选》读后感(四):是余香满口,有暗香盈袖
不听音乐时,我喜欢读词。手边这本《唐宋名家词选》我常翻看,有时是妙手偶得的词句,有时是可细细琢磨的词牌名,还有各家集评给予的历史定位,常读常新。找到这本书是偶然,龙榆生先生也非如今盛名鼎鼎的红人。是在一个杂文集子里读到黄永年黄老忆龙榆生先生的文章,认为其《词曲概论》的价值不亚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且提出词曲作法上音律与表情的关系多有创见,自然,我要找来看一看。
龙榆生的这本词选的多是婉约一派,且自己填词也偏婉约,但选词手法极好。词家小传与集评可对照着细读,想来是各家文论读得熟,信手拈来的词解是简而不约。且我向来看重词作版本,这本书也一并交代出来。“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柳永词二十余首入选,自然少不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但词作者为何人依然是文史公案,我曾认为它不一定出自柳屯田,而欧阳修那样的大官吏、大文豪也不必俯身去就如此俗曲情致,那么,或许可以是冯延巳。
相较于诗,词在叙事性和音乐性上有更多变化。长短句形式的错落暗合跌宕曲折的声韵调和情感起伏。当然,诗也有叙事,但囿于形式,一句诗中的叙事在勾勒出一个画面上往往过于“实”。且从古诗十九首起,一直是抒情,或对各种人生主题发议论。而无论是小令短调还是慢曲长调,用长短变化的词句控制节奏能在一阙词里使得自然声律变换更加贴合表情达意。“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情最苦。”
豪放派不会不喜欢苏轼,且词家苏辛并称,辛词爱用大开大阖,纵横驰骋的笔阵。“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但苏词中又有“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这样的细腻柔婉和“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的娴雅清丽。
名家词作都有成熟的风格样式,寻声知人大抵不会出大差错。要不是这本词选,我大约不会认真读到周邦彦。少时读众人词,多浮光掠影,美成是其中一位。周词初读似乎不那么圆润、浑成,无论是用字、结构还是音律。他在一阙词里可以一节一换韵,而长调中对去声字运用熟稔确实独具一格。所谓周的“艳词”,格调不高。同是写情事,秦少游写来就是“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周美成写来是“问伊可煞於人厚,梅萼露、胭脂檀口。”所以王国维评论“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
虽则长短句发展的巅峰词在格式上的变换相对自由,但倚声填词仍要受声律的严格约束。而曲在可以另添衬字后,其表现形式更加灵活自由。词在诗与曲之间,闪转腾挪,更有兴味。
人生无常,空有余恨,词家早已写尽。这既是“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又是“当年不肯嫁东风,无端却被秋风误”,更是“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恨”也可到极致,可遗憾,可悔过,可怅惘,可嗔怨,还可希冀,只是不再咬牙切齿。
曲子词的选本很多,龙榆生先生的这本正合我意。不是逐字逐句赏析,不是囫囵吞枣概括,选词和选注背后未尝不是一种个人化的理解和偏好。而后世更有学界名人称其所作曲词胜过他的老师疆村先生,许是融合几家之长,深得奥义之果。
读书勤时,曾想以小短文的形式写满“二十四桥明月夜”,后来发现写不下去。只是生活中常常毫无征兆会有词句悄悄跑到脑子里,念熟后,又莫名其妙地隐遁消失,默默等待下一句的填满。而我常常,是的,常常在新鲜而浓烈的瞬间感受里失语,找不到那个最准确的表达。唐和宋,诗和词,甚至杂剧和散曲,在摹写某些人生经验上已无可超越,虽然我偶尔会去寻找那个脉络,但面对更复杂幽微的情感表达时,我知道它们不是全部。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高峰,后人无论是另辟蹊径还是小心突围,都无法绕过这些绝响。许是晨起伸个懒腰,或是深夜按下相思,都可与这些词句相遇。没有音乐的时候,我默默读词,也常想古人曾如何谱曲吟唱,会不会也和我一样,有满口余香。
《唐宋名家词选》读后感(五):是余音绕梁,也是莫名其妙
中国的学者里,我痴迷的有那么三五人,龙榆生先生是其一,能与龙先生并列的还有一个吕思勉。然后下来也许还能有王利器,再有蒙文通……想想,就好开名人大会了。
其实也都不是什么名人,说来都是生疏的名字。他们这等人没有入得了时兴的大作,也没有犯得上批判的忌讳。是历史课本的书眉页脚上手写的铅笔字,到再版的时候就会消失。总会记得,因为不忍心。再譬如会做古小说钩沉的鲁迅,擅写西南马帮的艾芜,或者把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与明清章回小说融会的李劼人(他还做过遗老风格的成都市市长,有一院漂亮的芭蕉树),因为没有一心要捧红他们的当代红人,所以也就渐渐地淡出。淡出也没什么不好,电影里淡出的镜头是诗情画意的表示,总比一味阴冷的长镜头要好,譬如季羡林,仿佛一出漫无结束的长篇悲情电视剧,乏味到后来连广告也没人愿意来插播了。
又或者捧也是捧不红的吧。连张爱玲也说“张爱玲五详红楼梦,众看官三弃海上花”,所以私淑只是私淑,谁心里都有一根隐秘的弦,弹拨得响也只是于我心有戚戚焉。
可是我之知道龙榆生却是因为当代的一个红人。说来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晓得分别好坏,也曾迷恋过汪晖:汪在文章里忆及扬州师院的青涩年代,有一个章石承先生是他的导师,且似乎王小盾也与那章先生有些师承的关系——看看,都是现今炙手可热的人物。却说章石承正是龙榆生先生的弟子。汪的文章里隐约也提到了龙先生与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却不说明白,只说那龙先生身后连名字也不敢示人,墓碑上只刻着“九江龙七”。那九江也不是他祖籍,是夫人的乡里。沦落到这田地,且是文人,总难免叫人同生身世之感。汪文中也述及在龙先生墓前矗立神伤——文人,但凡被卷上了风头浪尖,多少也排遣不去些忧惧,因此那时节的汪一定是有些真心的。所以,汪晖是可以原谅的,顺带着我也原谅了自己的曾受蛊惑。
龙榆生的词学现在也不大出名。我常常读的这本唐宋名家词选,选词手法好,注释简而不约。且虽他自己填的多是婉约一派,却也大是推崇豪放派的作品。这样说来说去我也觉得似乎不妥,没有说服力。只是那流传最广的宋词三百首,一无章法,二无注解,选词的疆村是大名士大遗老,当时的风流人物穷途末路,老来无所依,批词的砚是授给了三十不到的龙榆生。先先后后多幅授砚图是一时代的佳话。也是一时代最末的佳话吧。师承这件事情,早已经不见重视了。
总是发牢骚是不好的,做人要有审美的态度。要不是这本词选,大约我也不会认真读到白居易那几首忆江南,真有词味的是“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连带着想起岳飞的“特特寻芳上翠微”,虽是诗,却也脱不了词味。词比诗更有叙事性,一阕词里绵延不去的是一个情事。只是欲说还休。诗是从古诗十九首,一直是抒情,对宏大的人生主题发议论,或者心有余恨。但诗经却又不同,“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是对人哀哀地诉求,反复唱着那句“忘记你我做不到”;又譬如“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则是无以为报,以身相许的表白,古今传奇里随手都是的段子。
词又是最讲体面的,诗可以打油,曲到了今天人多只晓得那“铜豌豆”的无赖。词最多是词牌里有下里巴人的遗迹,也不多只是“丑奴儿”“鸭头绿”,连“菩萨蛮”也因为“杨柳小蛮腰”而不陋也不俗了。且说到词牌,也是最感伤的,凡是离乱的时世,却要唱“定风波”,凡是同心而离居的,却定要填一阕“点绛唇”。但有时候却又现实得不怜惜自己,我最爱是《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是等着人问“尚能饭否”却等不到了,只好半夜里仗着酒胆想象魔兽世界,接受老泪纵横的结局才是聪明吧,总比“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却还只遇到冷眼要可靠。
再有“相见欢”和“永遇乐”,我喜欢是前者,因为更口语一些,又因为后面那个总容易联想到“长乐未央”,不是好兆头。语言有就是巫术,要小心不要给自己给生活念了咒语。但对于强悍的人来说,也无所谓,因为不是我要听生活的,是生活要听我的。那么只要相见就一定是欢欣鼓舞,惟有见也见不到是最糟糕。
龙榆生先生是喜欢李煜的,这其实也是废话,因为只要按着规矩来,读词就应喜欢他。以前觉得浪淘沙好,因那句“梦里不知身是客”有自觉的改正与调整的意思,有终于还是与现实相遇的解脱。只是昨天看到朋友文章要让一个曲子送到不可知的某处,祈愿“阴阳畅达,关津勿阻”,不见踪迹的故人与这清明的节气,总还是人生无常的局限。这局限也就是“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就是“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而没有局限,大概也就无所谓相见欢了吧。
拉拉杂杂说了些废话,其实是想在诗歌里找一个出口,奈何却找不到。既然在生活里面,那就是出不去的,况且,出去做什么呢?还在这世界上的人,有无限的感伤的可能性,对着具体生动的生活,或者变幻莫测不可认识的规则。诗也好,词也好,唐也好,宋也好,它们有各自的表达和突围,我只是想知道,哪里才能找到那个表达。而表达的需求总是不断滋生变化的,有时候甚至不是表达,只是一不小心,某根弦就被弹拨响了。是余音绕梁,也是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