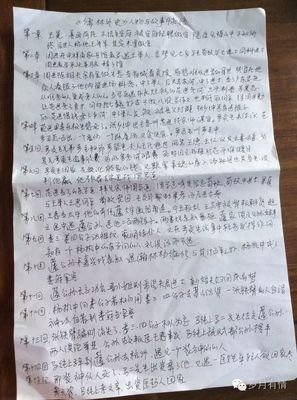
《告别理想》是一本由张乐天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0.00元,页数:4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告别理想》精选点评:
●大三那年读的。该书用了剧场社会等人类学概念,有新意。但缺乏政治经济学角度的分析批判,还是没有说透。
●福州路上海古籍出版社书店
●好,但是还不够好,这部书告诉人们,如果没有先进生产力做物质基础,社会主义也只是一个比资本主义好不了多少的,虚幻的泡影。
●人民公社是一把钥匙,透过它可以看到今日中国的一切都不是凭空而来。中国从那个时候走到现在这一路上的进步,让我们相信未来值得更加充满希望。
●“走进Y公社”,对当代史上的人民公社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察,并以人类学方法进行分析。看来世纪初的当代史受人类学、社会学的影响很大哪
●考证派大作,不错的入门读物,原来传统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真实、严谨,能让人心目中以前很多不解的地方得到合理的释疑。俯下身来踏踏实实搞学问,真是难得,真实造福后人。这本书有时候数据表格过多,论证繁琐,弄得我很多地方跳着读,怨我知识储备和耐性不够,一本好书。 《中国经济专题》姚洋推荐
●都说比较好
●困的不行过来吐个槽…怎么会有资料这么扎实,结构却这么松散的书…
●好书
《告别理想》读后感(一):变与不变
人民公社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好像在看一副很长很长的画卷,人物、事件都那么鲜明,不禁把自己代入。 革命仪式创造出革命表象,而革命表象以其净化的道德、似真非真的美好未来以及charima权威吸引着农民大众参与仪式。革命表象渐渐替代传统村落文化…剧场社会成为支配乡村社会生活的文化模式。也许这一幕幕仪式、高建起来的道德便是维持乡村社会及联系中央的基本结构。是“革命”开展的必需条件。
从50年代土地改革到7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历经土地的私有、共有过程,也有许许多多的“政治”运动,在运动中,乡村的基层权力不断发生变化,传统模式也在打破。乡村的变革是外部冲击和内部传统互动共同影响,大的政治或经济变革中,总有些不变的是乡村的传统道德。正是内外部的不断磨合发展,才有了现在的乡村。其中,土地问题,劳力问题,党政权力及经济发展问题是值得当代农村发展借鉴的。忽然想到邻里东京里对于现存社区的描述,并不是传统的回归,而是不断发展的结果。现在的农村和传统农村差异颇大,变与不变的交织,如何巧妙的运用,是农村发展的切入点之一。
《告别理想》读后感(二):对农地关系的探讨
晚上无意间看到一集中国粮的奇迹 讲新兴的科技手段如何运用到农业中。 田头的科学家保证种植品质,开着农机的农民劳作耕耘,并有远程的科技公司提供最新的天气信息给农民。还有大片大片的田头延至山前,在视觉上也给人以振奋,当然最打动我的是叔叔婶婶们脸上的笑容,真的是很灿烂的笑容,不经有点哽咽。我想在这样的画面面前很难不产生民族自豪感。 能让科学家和大型农机在中国的田野上发挥作用的背景很重要,即对农业生产的规划。这也是张乐天老师在书中提到的人民公社的创举。让中国人吃饱饭的不是小农经济式的自给自足,吃苦耐劳也不是让农民富起来的关键因素。而是对生产的调拨与规划——种植的经验在规划之后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在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中,生产大队及其前身人民公社制的功劳不可磨灭。 人民公社制最有创造性的是将田地的种植规划权统一至公社,是一种新型的人地关系。如果当初没有发明公社制,则中国的人地关系依然是个人与田地的关系。按照农村传统的惯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提高。生产内卷化或者类农佃关系出现也未可知。 后来的生产承包制也正是继承了公社制的规划性优势,并改掉了一些弊端调动生产积极性。中国的农业成就也能够一个阶段紧接着一个阶段达到腾飞。 如果当初没有做出其中最为关键的人地关系的改善,也不会有现在的成就。
《告别理想》读后感(三):人民公社研究入门书
我先谈一下对这本书的一些感性认识。这本书题为“告别理想”,所谓理想自然是指人民公社制度。既然称之为理想,必然是认为其不具备存在的可能。或是脱离现实,即使存在也不能长久。自然而然,我会想到人民公社出现的原因。但是在书中,作者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或者说作者把答案隐含在了叙述中。作者在自序中就提到,五十年代初期的浙北农村,农民压根儿就不知道共产党、毛主席,凭借什么能在短短几年就树立起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实现政权的更替?共产党靠什么来争取民心?作者接下来就提出了他的新观点,所谓的剧场社会。通过革命仪式创造革命表象,来吸引老百姓参与革命。通过剧场社会,共产党领导人民进入一个迥然不同于小农社会的新时代,就是人民公社。可以看出,作者把人民公社当作是领导阶级隔绝传统,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是因为统治的需要。
作者也提到了,旧传统和新制度之间的互动,一直是本书贯穿的主题。人民公社是在传统自然村落的基础上建筑起的制度大厦,但对于公社制度来说,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性质。村落支撑着公社,因为公社很多方面与传统村落同构;村落瓦解着公社,因为农民的原则与公社的原则有时候是相冲突的。公社与村落、农民之间的巨大张力,必然需要公社去努力克服。但强制性的手段难以长期维持,而妥协性的手段又继续遵循原来的传统。公社到最后必然走向终结,终归是一个理想。作者以“外部冲击-村落传统的互动”来研究人民公社制度,第三者的研究角度,比以往那些站在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更具客观性,也更能深挖出很多有趣的东西。比如说公社时期,生产队和农民们就把国家的规定抛到脑后,只按自己的传统交换方式行事。在书中,作者举了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挖边的故事”。大公社解体之后,农民家庭自留地重新恢复。在一般情况下,自留地可以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5%-10%,最多不能超过15%。这条资料来自中共中央的档汇编,大多数研究者都会利用。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政策的方向性转变,是国家范围内的事件。人民公社体制的改变并没有为农民提供粮食和其它物质,只是给了生产队自主地使用土地的权力,同时也部分地给农民家庭以自主地使用土地的权力。土地上的产出一旦与农民的收益相联系,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于是,在浙江农村,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挖边”高潮。所谓“挖边”,按照作者的说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零星小块土地种作物。具体如下:1、挖土地的四周边,畦畦挖,横挖,竖挖;2、挖交通要道边,地沟里种蕉藕;3、芋艿田里挖边,拔掉生长不良的芋艿,及时挖边;4、芋艿缺棵的地方种上高梁、玉米;5、芋艿田的四周种上黄豆、豇豆、赤豆,见缝插针;6、桑树地里种南瓜秧,旁边种烟叶、长豇豆;7小队17张鱼池,面积13亩,种茭白……。书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看出,在中央政策的背后,农民的真实反映仍然遵循了传统的家庭经营观念。对于公社时期,普通老百姓在中央文件和政策精神下的真实做法,也不失为我们研究的一个好方向。理想之中的生存挣扎!
另外,本书在详细论述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各个方面和发展过程后,也肯定了人民公社的奠基作用,特别是对公社之后的土地问题,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一些制度尝试,为新时期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诞生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农村集体企业、党政权力方面,人民公社制度也为今天开了个好头。
《告别理想》读后感(四):公社制度的迷茫
三农问题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道难题。当我们或以责任心或以同情心关注今天的三农问题时,我们也该关注农村的昨天——试图从历史中寻求现实的答案未免可笑,但无论如何现实中有太多历史的回声。而在建国以来农村的发展进程中,人民公社更是绕不开的一环。那段已经过去二十多年的历史对农村的影响至今仍或多或少的存在,可是二十年间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几乎没有遗传到公社年代的任何记忆。
这些,是我对“公社”产生兴趣的缘起。
基本分配原则:“先国家,后集体”;“留足集体的”;“处理好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之间的关系”。(《人民公社制度研究》P271)
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重视群体观念(表现为宗族观念等)而忽视个人价值的社会中,以“先国家,后集体”“留足集体的”制度作为分配原则,首先抢占了道德上的制高点;再加上解放以来农村不断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其他政治运动,让农民既不能也不敢与国家至上的原则对抗。此外,党和政府还在经济领域引入了一系列捆绑政策(如奖售等)巩固了这一分配原则。即使改革开放后的“大包干”时代,分配口号也仍然有这些原则的影子——“缴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至于“正确处理好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之间的关系”则更是一套缥缈的说辞。根据《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两书中的研究成果,在整个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中的分配制度无不是“名曰‘按劳分配’,实为‘按需分配’”——在孱弱的生产力状况下这里的“按需分配”不过是满足个人最低温饱需求之“需”;按照基本口粮分配后农村可供再次分配的收益已经所剩不多,“按劳分配”的产品比例自然少的可怜。那么在这种没有活力的体制之下,农村的生产力(即使这种生产力只是“小农”层次的)又怎能得到解放和发展?!“只有在农业劳动与产量直接挂钩的情况下,农民才能自觉得保证农活的质量”,此言大哉!
二、 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化与现代化之间关系
在《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一书的结尾,作者提出了一个命题——如何看待公社时期农村“没有发展的增长”、“中国基本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中国整体实现现代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实现工业化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这样的发展路径值不值得?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清理下,当我们以今天的视角或得失去评价当年的决策时,未免有些苛责。联系当年中国一穷二白的国内条件和四面楚歌的国际环境,我们要快速的实现工业化尤其是资金设备密集型的重工业,不举全国之力何以发展?没有重工业的铺路在中国这种后发型国家能否有工业化甚至现代化的基础?即使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在当时中国还否能够找到一条比这条路径更不糟糕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欣赏西方一位作者的言论——“没有毛时代所取得的成就,邓的改革将失去对象。”其次,毛泽东在当年大力推进农村集体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全面控制农民进而通过“剪刀差”更好的剥夺农民还是为了发展农村试验他的“新村”理念进而进入幸福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这里的过程与目的是否统一?就我目前看到的材料仍无法坚实的支撑这两个观点中的任何一个,我将继续关注此问题。再次,今天看来,我们认为现代化的概念更复杂包含着信息化工业化等诸多因素,但是在四十年前工业化能否说是现代化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某种意义上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