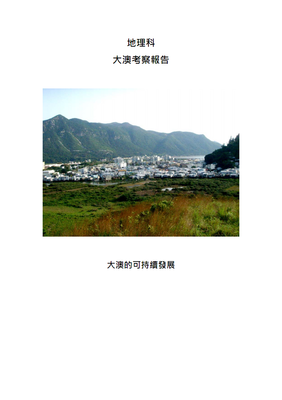
黄桥村西边是河堤,挨河堤是河地。住在河边的人都知道“紧沙满淤”的道理,大水流过之后,河中心留下的是一床的沙,挨河堤是慢水,是“淤”,留下的便是肥沃的泥土,在肥沃的泥土上种庄稼,泥土就是肥沃的土地。这地下边是黏土,耕作层是壤土,不漏水,不漏肥,耐涝耐旱,种出的庄稼:地上的籽粒饱满,像大豆、小麦、谷子,地下的个大味正,像花生、红薯。杨宝强家就有祖上传下来的一块四亩这样的河地,也是他们杨家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根本。
杨宝强家的这块河地,北边紧挨着官道,其他三面都被地主黄朝五家的60 亩河地包围着。以前不是这样,以前杨宝强家的地西邻是一块姓张的地,黄朝五也不知用的什么办法,把姓张的地买去了。现在杨宝强的这块地是十八亩地里的一棵谷,成了单根独苗,又处在黄朝五巨大的包围之中,有时候他真有一种沿独木桥的感觉,害怕一不小心就会掉入水中。不过这只是他的一种感觉,有时候他在自己地里劳动时又想,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你黄朝五虽有钱有势,总不能把我家的几亩地明抢了去!
黄朝五在黄桥村也并不是什么大地主,家里总共也只有300来百亩土地。家里虽有佃户有长工,可他知道他爷爷、他爹爹和他三代人挣下这分家业不容易,每逢又收又种的大忙季节,他都要带领家人到地里去劳动。他平时邋里邋遢,常年头戴一顶黑色的帽垫,舍不得穿,舍不得吃,却把土地和庄稼视为自己的生命,又把粪肥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进入农闲,有时候她还要挎起粪箕子,到村子里大路边拾些粪回来。他的60 亩河地更是他的命根子。美中不足的是在他的60亩地中间,嵌入了杨宝强的四亩地。这对他那60亩的整地、播种、管理、收割都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杨宝强的这块地,对黄朝五来说,就像极美的姑娘脸上长了一块黑痣,又像极平坦的大道上栽上了一截木桩,黄朝五一心要买杨宝强家的四亩地,如果这四亩地被他弄到手,等于是医好了黑痣,拔掉了木桩。
他托长工头雷念子找到杨宝强,说他愿意出高价买他家的四亩地。被杨宝强的一句话“这是祖业,多少钱都不卖!”给顶了回去。常言“有钱难买不卖之物”,黄朝五也没有办法。不过他又想出了新的办法,他要用其他地的一亩二分来换杨宝强家的一亩地,这样杨宝强就能得到四亩八分地,不过不是河地了。他又托私塾的先生黄四峰找到杨宝强,这回杨宝强有点活动,不过他说一亩二分换一亩不行,提出一亩半换一亩。黄朝五说杨宝强太过分了。最终地没有换成,事情就拖了下来。
第二年杨宝强得了病,医生为他号了脉,开了方子,抓了药。之后特别嘱咐他说:“这是发汗的药,喝下去要用被子捂严出汗,记住:捂汗时就是天塌了也不要出被窝——等汗出透病自然就好了。”这天杨宝强喝了妻子为他熬的汤药,盖了两床被子,正在捂汗,长工头雷念子急急地走来,说要找杨宝强说话。杨宝强的妻子挡驾说:“他不在家,有什么和我说吧。”雷念子说:“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主家新来了一个长工,去地里犁地时把你家的地和主家的地一块犁了……”他的话被被子下边的杨宝强听得一清二楚,一时火气上涌,竟把医生的嘱咐忘得一干二净,揭起被子,跳下床质问雷念子:“新来的长工——狗屁!这是阴谋!霸占!巧取豪夺!”雷念子看杨宝强一腔怒火,便避开锋芒,和他妻子说:“主家说了,你们要是要原来的地呢,丈量后还归你们,不过要出几文钱的工钱。要是不要呢,北地的地也不赖,就拨给你们五亩。这怎么能叫霸占呢?”
听了雷念子的话,气氛有所缓和,不过杨宝强坚持说:“我要我家原来的地,那是祖业!”
谁知还没有等要回原来的地,杨宝强的病就急剧恶化,再去看医生,医生说:“你不听我的劝告,我已无能为力了。”杨宝强去世后,黄朝五又让私塾的先生黄思峰送来了20 块银圆。妻子强挣着为丈夫办了丧事,带儿子给丈夫三天圆坟回来,竟一病不起,也去世了。这次黄朝五亲自走来,说出了这种事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还说他们的儿子杨大印还小,无依无靠的,要收他为义子。杨大印不答应,怀揣剩下的几块银圆,寻找队伍去了。
这年杨大印1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