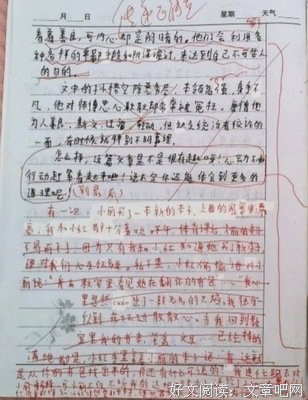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是一本由刘志伟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9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精选点评:
●纷繁复杂的明清赋役制度,梳理得这么清楚,丝丝入扣,合情合理
●断断续续四个月才读完。不算厚的小册子,读罢算是把齐民编户和赋役制度的关系弄清楚了,简单来说两者就是互补的制度,齐民编户的方式方法是为了赋役制度而设计的。这就不难理解明清以来为什么齐民编户,户籍制度发生了根本变革:从以人为主变成了以地为主,人捆绑在地(财产)上。这样也算打破了我长期以来的一个误区:觉得摊丁入亩的完成是对人的一种释放。实际上恰恰相反。读本书还有一个重要启发:即明清时期西南土司辖地的所谓“以茶(或者矿)抵税”的说法,实际上是有误的,都没有齐民编户何来税呢,应该是误解了“折色”的概念。可见户籍制度不搞清楚,很多税赋的东西不能乱用。
●明代里甲社会组织的户变为清代图甲税收单位的户头,而这个变化又是与地方宗族组织学生崛起相勾连的,神奇
●这是硕论啊啊啊!
●“每个王朝设立户籍制度的最直接的目的,是向编户齐民征调赋税和差役。尽管儒家正统的思想一向标榜重义轻利,苟言理财,反对聚敛,主张藏富于民,但其目的,亦不过是为了培植更丰富的税源。”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
●刘志伟教授,原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和科大卫、程美宝等被誉为古代史华南学派领军人物。先生著述并不多,这是仅仅能够查阅到的一本专著。既是经济史又是区域史,还要扎根于繁杂的家谱和地方志中,还是很不容易的。改天会认真的写一个书评。
●終於可以點“讀過”了。“戶”,就是一個api。之前的體制,就是還沒有api的操作系統。
●三篇附录也很精彩
●非常好看的书!主要是从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入手,从一个地区的赋役制度的运行变革入手,窥探出国家政权在地方的运行、变化以及地方社会的反应,并进一步引申带传统中国的某些社会特征的变化。明初的里甲试图对地方进行全方位的控制,这本来在实践上就困难后面又遭到破坏,折银、货币化给z赋役征收更简洁化的契机,赋役制度的变化进而引发了里甲(国家管控)性质的变化,里甲仅成了登记土地和税粮的造册,而不在具有整合地方的能力来。同时,地方势力利用一些象征性手段顺势而起,成为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中介。所谓中国传统社会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互接应,也就源于这个过程。附录三篇也很精彩,感觉刘先生非常重视把某一现象当做过程去解读,而不是当结果,挖掘里面的互动关系。从社会史中解读出政治实践、社会特质,很高明!
●必须读多一次才懂啊~附录的论文还不错~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读后感(一):笔记:在国家与社会之间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读后感(二):从等级户役到比例赋税
大约一个月前,花了一个周时间,来读这本书。之所以要花一周时间,有客观与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其实每天只有一点时间来读这本书,主观方面,这本书写的实在太好,使我不能不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下来,读普通书的扫描式的办法在这书上是不适用的。
读完的笔记记了很厚,所以本来是做了准备要写一个很长的笔记在豆瓣上的。不过从那时起拖了很久,直到现在,仔细想了一想,其实这是不必要的,经典如这样的研究,不论是整体架构还是细部分析,都是难以置喙的。而且,刘氏的行文是如此的谨慎、内敛,如果把话讲白了,美感顿失。
所以沉淀到现在,关于这本书唯一想说的是,刘氏所勾勒出来的,叙述赋役制度变化的线索,是从等级户役体制到比例赋税体制,而后者,包含了转变为现代财政体制的契机。更有兴味的是,我总是猜测着,关于等级户役的十分内敛的描述,是否包含了对中国式的单位体制的某种映射。关于等级户役制的经验性的体会,尤其是“画地为牢的里甲体制”一句断语,如果不是曾经生活在那样的单位体制中,恐怕是难以成言的。
刘氏上次在报告时指出,梁方仲先生《明代粮长制度》结尾欲言又止的,是对集体化失败命运的预言,而其自身对里甲体制的内敛的表述方式,总觉得应当是抱持了某些对当下的关怀吧。然而这实在只是一种猜测,有时间要向刘氏求证的。
又按,如此经典的著作,拖到现在才来读,也实在是一种罪过。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读后感(三):研究应有的广阔视野
对于非本领域的我而言,·阅读本书最大的收获还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一本好的著作,往往永垂不朽的,还是提供了一种怎样的方法。
就本书而言,内容实则相当精炼,就讲述了明末清初发生的赋役制度改革。全文紧扣此主题,对广东地区这一制度的沿革透彻阐述。这种研究应当就是一种大历史观的体现。我对《万历十五年》中的大历史观一直不太理解,因为在我看来,本书所具备的才是大历史观,突破断代的窠臼,直击制度变革的逻辑。从文中可以看到,清代摊丁入亩的变革,是明代一条鞭法的延伸,而明代一条鞭法的产生,则是明初赋役制度本身留下的漏洞,是对这种否定的否定,于是历史产生了一种螺旋上升。
本书的学术价值自毋庸赘述,而更值得学习的,应该就是体现在这种研究中的思路与路径,以指导研究者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做出深刻而隽永的内容。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读后感(四):在国家与社会之间 读后
提到明代里甲制度与赋役制度,对于明史爱好者来说几乎是耳熟能详,这是明史的基本知识,在一般大学课本中也是常考的重点之重点。但是,明朝是一个既高度整合化又分散化的以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帝制农商社会,在广袤的帝国境内既有南北差异又有东西差异,各个不同的人文地理十分复杂,帝国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文化环境之下,即使是高度的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也无法将个人的意志完全转变为各地区通行的无差别的制度。传统的大学课本知识仅是大线条的国家法令,法令虽然历史上确实曾经推出过,地方也的确积极响应了统治者提出的法令制度要求,但是地方响应与中央要求从来就不是一回事,中央制度的要求很大程度上在地方社会会被地方话,因为制度的推行一定要结合当地的社会实际情况,如在明朝西北偏远地区粮产量极低的地区推行粮长制度就是天方夜谭。同理,由于各个地区的差异性很大,那么地方在贯彻中央法令时就会推出带有一定地区标签的“国家-地方”制度。
作者认为,法令虽然全国同行,但是地区差异性很大,如果贸然以全国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忽略地区差异性则会成为研究出现谬误的重要因素。作者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与制度在历史上的推行情况,选择广东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入手,探寻基层社会与国家在这个制度中发生的互动关系。
国家-社会中探寻相关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出现,这个研究方法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互动从而产生的在历史学范畴内的新研究范式。这种研究方法虽然早已出现,但却并不过时,我认为,在实证史学探明大多数史学空白之后,将历史学由知识转向致用是合理的,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探寻中发现的关系可以当做一种对现实社会有帮助的方程式,也许会对未来的社会有所帮助,这种现实关怀体现的较为明显。
作者在本书中,他从明初的户籍登记开始,研究户口登记与赋税直到清朝图甲制,在明初到清中期这段时间内,作者发现国家与社会还有制度都发生了相当改变,其改变不仅仅是制度名称而是根本内涵发生了转变,由此不难发现,社会与国家层面实际上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是以往大历史视野下以国家层面为高度学习历史知识时所经常忽略的动态内容。
从登记人口到登记土地,从税人到税地,从里甲到图甲,从两税到一条鞭再到摊丁入地。社会与国家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改变,但是到底改变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呢?什么促使了转变?为什么要转变?解决这些疑问是回答国家-社会互动的关键,作者根据较长时段的转变中发现了思路,他认为制度一开始要适应当下的社会,当制度推行之后这项制度又会改变社会的文化等因素,在社会的文化发生转变时,旧有的制度就显得与新出现的因素格格不入,因素推出新的制度成为必然,就在这样的互动中,社会与国家相互影响,构成了我们复杂而又简单的历史。
这本书虽然研究范式是传统的西方学者常用的具有较高现实关怀的多学科交流下国家-社会研究方式,这种研究方式虽然很好,但是我国的学者是否能掌握确是个难点,毕竟听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作者做到了,作者能较为出色的与这种研究范式结合相适应,并能从这种西方的方法论中更好的体现中国学者的特色,这是难能可贵的,不仅没有出现排异现象,还更好的完善了这种范式,我觉得,这是作者基于史学成果之下贡献了更多的史学理论要素,后者这种贡献可谓是“授人以渔”,可敬可敬。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读后感(五):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萌芽?
一、内容概要
本书以广东为考察对象,详细介绍了从明代到清代前期的户籍制度、赋役制度的实施和演变,试图以此为视角,观察明清时期的官民关系(即本书题目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户籍制度是历来统治者为了控制人民、剥削财物而制定的,为此,统治者也给有户籍的人们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利,比如有合法拥有土地和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要想了解历史上的官民关系,就必须考查户籍制度。
明代的户籍制度,由开国皇帝朱元璋颁布,称为里甲制:以家庭为单位,每十户为一甲,配一户里长,而十甲(共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共有十户里长,轮流带领其手下的十户人家到官府应付差役;同时,编户册时,注意登记各家土地的数量、质量差异,以便按照各家的实际情况征收税赋。但里甲制实行百年后即失去效力,地方上的豪家大族不断兼并土地、瞒报户口,致使小农之生日蹙,纷纷逃亡或改业,于是,国家的赋税来源渐渐枯竭。又由于内外战争和皇室的奢侈,财政支出有增无减,于是到明代中后期,各地纷纷开始了赋役制度的新探索,最终由内阁首辅张居正在全国统一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试图简化税法,用白银取代过去的实物税和劳力差役,限制地方官的横征暴敛,从而稳住小农,保住政府财政。
到清朝,在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敕令下,完成了摊丁入地的改革,使得在一条鞭法改革后就以土地计算的“丁税”终于合并到了土地税中,进一步简化了税制。
明代初期的户册,登记的既有人丁也有地产,到了中后期,则仅剩地产的登记了,而不再能反映真实的人口、家庭状况了。这一变化体现了社会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地方宗族势力的兴起。到了清代,户籍已经被地方上的宗族势力所控制。宗族作为介于官民之间的一种组织,在组织生产、上交赋税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政府既要借助其力量,又有限制其发展。
二、问题与短论:统治精英的分工和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萌芽?
很明显,随着财政压力的加大,公平分配税赋的理想就渐渐淡出了统治者的视野。为了在广大的领土范围内有效地征收税款,政府放弃了复杂的劳力差役制度,而统一改用土地税。这时,税款出自土地,却并不需要知道出自何种具体的劳动过程和哪些具体的劳动者。也就是说,统治精英开始了如下的分工:政府抽取税收,同时负责向地方宗族提供其统治乡村的保障(文化“软实力”和军事“硬实力”)和科举做官的机会;地方宗族从经营土地和工商业中获取财富,同时负责将从劳动者身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上交给政府。这种分工在以白银作为全国统一的赋税单位时运行得前所未有地高效,至今未有本质上的变化(期间经历了一百多年“地方军事化”的小插曲)。因此可以说,这种分工反映了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社会结构而言,国家渐渐退居幕后,成了生产组织者(即“资本家”)的代理人,发挥着间接但却依然重要的作用。明代粮长制度的消亡,则为这一结构变化提供了注脚。其不同于前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不是生产技术的发展,而是统治技术的进步,这一进步使得社会的等级结构更加稳固了。唯一重要的区别仅仅在于,地方宗族对于所积累的财富的使用方式,还停留在简单的土地买卖和个人奢侈消费的阶段,尚未进入到投资于节省人力和提高资本利润率的技术的阶段。追求利润作为资本家一切行为的主要动机,已经露出水面,只是在不同的环境中,这一动机引发了不同的行为而已。
就社会关系而言,劳动人民从直接与国家的人身隶属关系,转而与地方宗族建立依附关系,而地方宗族与国家之间的直接关系,则是建立在土地财产的基础之上。劳动者与统治精英之间的带有温情的家长-庇护式关系,逐渐被更讲求实际利益的金钱关系所取代。
明代海洋贸易的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开发拓殖、清代人口的增长等因素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应该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考察国家管理制度时不能不把这些背景考虑在内,但本书并未完成这一宏大的任务。此外,本书缺乏与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比较,因而也难以从中作出进一步的理论发挥,以上所论,仅是个人猜测,请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