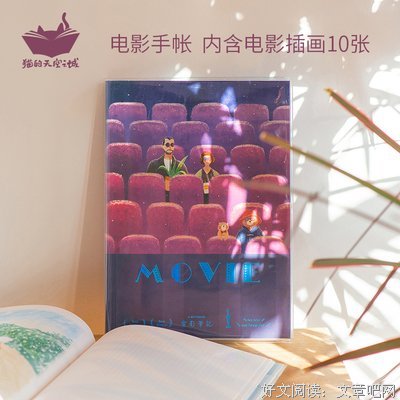
《无望的人们》是一部由米克洛斯·杨索执导,佐尔坦·拉蒂诺维茨 / Tibor Molnár / Gábor Agárdi主演的一部剧情 / 战争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无望的人们》观后感(一):无题
初看时觉得乏味,不过随着剧情的发展,心境也随之变化。特别是结尾处,军队因为始终未找到起义军领袖,假传“圣旨”说已经赦免义军领袖。在义军残部高歌,犹如打了一场胜仗之时,“圣旨”又说,对义军残部不可原谅。全部被处死……这里,也许就是我喜欢扬索的开始。
《无望的人们》观后感(二):绝望的人,无望的世界
如果说看了<红军与白军>之后,备受震撼的话,那么再看<无望的人>,也只能用再度震撼来形容了.
《无望的人们》观后感(三):【11】《无望的人们》:一念地狱——鲸鱼推荐872部好电影
在这部电影中,被奥地利俘虏的匈牙利农民,被奥地利军官所利用,通过他们杀过人的负罪感,来指使他们互相揭发。比如加诺斯就被要求找出比他杀人还多的人,他就可以被赦免。于是他就暗中了解情况,然后检举其他人。他的行径被同伴所不齿,不久他就被同伴掐死了。军官故伎重演,又找来一对父子,再让他们指认凶手或者出卖游击队队长桑德尔。就这样,农民的懦弱和内心的纠结恐惧,成了他们自我毁灭的毒药。事实上,战争年代杀人并不算什么稀罕事,只是过于犹豫和顺从,就如同开启了低语之门,毕竟对于敌军来说,杀死他们就跟杀死一只绵羊没什么区别,影片的结尾就印证了这样的阴谋。
亮点
第18分钟,很多蒙住头的俘虏在监狱中围着圈转,镜头从中摇到右,又摇到左边,拍摄这些俘虏居住的环境,接着镜头又推过去,拍摄加诺斯查看俘虏的情况,而贝拉的出现又带着镜头继续移动。杨索的影迷们称这样的长镜头叫“赶羊长镜头”,镜头中的人其实就像是羊,被驱赶着做事,就连回到牢房都像是羊进入了羊圈,一气呵成的镜头不但将环境交代清楚,还把俘虏的悲惨处境直观地表现了出来。
《无望的人们》观后感(四):力所能及的努力才是对生命的热爱
线索很简单,军队要找到藏在被镇压的起义游击队士兵中的领袖。
猛一看是粗糙的故事,但回味中会发现,主题不在电影中,也没有主角,主角(或主角的精神)也不显现(有多个人物组成的一种呼应主题的精神),仅在一次被指认的过程中偷偷换了队伍,黑暗中给了侧身1秒。这被镇压的游击队,单独来看,一个个也不像领袖,但回到人群中,又觉得一个个都像领袖。
电影中,丧失人性的刑罚镜头并不多,大多数是威逼利诱。但这些不会因电影本身的省略,而导致观众淡化思考。这一点,比一些导演过于主观的镜头去解释甚至代替观众自身的思考要厉害很多。大概就是用少讲多和用多灌输的区别吧。
又要拿姜文来说了,虽然我老说他不好的话,但抽象的象征、强烈个人风格与主题融合的这类导演,国内市面上也就只有他了吧。《萍水之遥》是强烈个人风格的、抽象的象征,却没有融合主题。《让子弹飞》是强烈个人风格的,融合主题的。《太阳照常升起》是强烈个人风格的、抽象的象征也融合主题,厚积薄发的结构,最后喷发出一种积极的浪漫理想主义。
抽象的象征、强烈的个人风格、主题融合,他们俩都有。不一样之处,《无望的人们》是一种以无讲有、以少讲多的结构,做到了“电影不在屏幕上,而在观众的脑中”,这些是在没有给观众过度压力的情况下,调动观众思考。一些主题不明,故弄玄虚,强迫观众思考,自己却还没有思考清楚的导演,大概连这种手法的边都摸不到吧。
然而这电影还不止这些东西,无处不在的严肃性,笼罩的具体历史感,又将高度厚度层层叠加。
《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浪漫属于我个人偏好,但面对《无望的人们》还是不得不得承认略孙一筹,不过总体上,这两部电影属于同一层次的电影。
其实能做到个人风格、主题融合已经是不错的导演。在这些基础上上,能把上面或其他主义融入,叙事结构再玩出花样,或是加入最新科技……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影片最后,听到消息,最真切的笑容在人群中散播开来,歌声迅速整齐有力,片刻过后,再一次陷入往日循环。
力所能及的努力,才是对生命的热爱。
《无望的人们》观后感(五):荒原死屋:杨索和《无望的人们》
荒原与死屋:杨索和《无望的人们》
到了1965年,杨索推出讲述1848年革命党人被镇压的电影《无望的人们the round up》,正好迎合了国内民众稳定中寻求改变的复杂心理,如燎原之火在国内创下了奇迹般的票房记录,之后更走出国门,在各大影展获奖连连的同时震撼了全世界观众和电影人,杨索迅速成为了扬名世界的电影大师.本片的故事发生在1869年,但实际背景则要追溯到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当年在巴黎,意大利,柏林,维也纳接连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属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属国的匈牙利国内的民间运动也是风起云涌,下议院反对党议员科苏特趁势逼迫议会和奥皇同意匈牙利废除封建制度而建立宪政,但是匈新内阁中充斥着温和派资产阶级和大地主,而激进革命派和守旧贵族皆对现政府不满。1848年9月各方矛盾激化,匈政府集体辞职辞职,时任财政部长的科苏特成为国防委员会主席,率数万自卫军和数十万农民军抵挡奥国军队,在1949年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均遭到镇压的民主低潮下,只有匈军革命情势在各国进步势力支持下一度大好,却在5月因 “欧洲宪兵 ”俄皇尼古拉一世派20万大军支援奥,加上作战总指挥戈尔盖在紧要关头公然背叛投降而彻底失败。本片的中被囚禁在土堡的一众囚犯,就是由1848年革命的叛军旧部和后来持续加入的零星农民反抗者组成的,他们中有人在饱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后当了叛徒,不但出卖同志甚至还想帮助政府抓住叛军首领,最后被愤怒的革命者暗中杀死。结尾得知“叛军首领”已经得到了皇帝的赦免时,一众1848年革命的旧部下高兴的唱起了军歌,可此时等待他们的却依然是无可逃避的死亡。。。虽然从性质上来看1848年革命只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但在依靠力量上则带有浓厚的民族独立与劳动人民起义的味道,应该说正是完全符合共产党意识形态偏好的红色题材,但是杨索却并没有利用这一天然优势将其炮制成一部“可歌可泣”的革命悲情电影来赢得话语权,而是从各个层面极力弱化其政治意味,用冷漠压抑的手法把一部情节简单的电影构造成了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普适寓言。
首先就是故事发生的环境,一个简陋的无名土堡,单调重复的内部构造强调了其作为囚笼的特点,圆形的厚墙,一模一样的单人室,空无一物,灰尘漫天的营房,而导演在表现这个环境时更是隐忍不发,几乎没有特写,镜头也是循环返绕,相似的景色让半天的镜头移动后画面好像还在原地打转.而与此相反的是土堡所在的大荒草原则辽阔到漫无边际,遥望远方除了连绵的地平线之外什么也没有,依然是单调到让人心头发紧。全片的第一个镜头就用骑兵队和天幕的对比展现出人被自然所重重包围的困境,之后更是多处使用这了这种凸现人之渺小的构图。每当剧中人向远方跑去或者走去的时候,在固定镜头下的大小对比就会变得格外明显,而他们无一例外都在即将步出画格之时被迫停住了脚步。除此之外杨索还使用了诸多技巧,如水平线和对角线的爱森斯坦式冲击构图,环绕推轨镜头和景深全景镜头的大量运用,正面近景的稀缺和高低远近的对比一起营造出令人窒息的情绪气氛,片尾庄严的管风琴音乐更是加深了宿命的悲怆感,一个“无牢之牢”的寓言意象在高度形式主义的画面中逐渐浮现,默默沉积之后又重重的压到了观众心上。人在政府的管制下窒息,无论如何挣扎都找不到出路,杨索曾表示自己就是出于对56年暴动表示同情而拍摄的这部影片,另外他的某些言论表明,本片背景的二元设定实际也在暗指当时冷战背景下的两极世界,土堡-封闭-社会主义,草原-开放-资本主义,但是无论在怎样的社会制度下人民的命运都不会有太多不同。主题固然可以做政治上的解读,却也因形式上的暧昧而产生了更宽广的外延,无际的荒原不过是封闭土堡的另一形式,芸芸众生都是这个没有出口的荒诞世界里永世的囚徒,所谓自由只剩下嶙峋的骸骨,一切逃生的希望都被自我指涉的绝望所彻底断绝。利用环境背景来展现情绪本是安东尼奥尼等古典文艺大师的拿手好戏,而杨索在此片中则将其进一步延伸到了对主题思想的探讨之中,虽然尚未达到波兰瓦伊达在《下水道》中将环境和主题天衣无缝融为一体的境界,在60年代的一众东欧导演中却也算是不凡了。
除去空间,还有时间,本片发生的时代背景同样耐人寻味,没有放在19世纪50年代匈沦为准军事占领区,奥军司令海瑙血腥镇压革命者,领袖科苏特出逃国外继续宣扬匈之独立并一度声势浩大,各地叛军残部还在努力抗争的烽火岁月,而是放在了奥国因克里米亚战争与俄交恶,又因意奥战争.普奥战争而丧失了大半领地,困难之中决定对匈牙利采取怀柔让步政策,终于在1867年建立了给予匈牙利和奥同等政治地位的"奥匈帝国"后的两年---1869年,此时奥匈二元政局远未稳定,匈牙利内部极左,中左,德阿克三派政党根基未稳,奠定匈牙利十九世纪下半之大局的1875年国民议会大选尚未召开,正如片头的那段旁白所说的一样,这个时期的匈牙利因封建势力的削弱而获得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失地农民和赤贫工人却也与日俱增,人民心中充满迷茫困惑但只能被时代的潮流裹挟向前,总之,一个前无大道后无归路既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混沌时代.杨索选择这样暧昧不清的时代背景,有力的支持了由空间环境所支撑的封闭主主题,无疑也在暗中讽刺本片上映时1965年匈牙利的国内局势,匈共意识到顽固铁腕高压无法维持长久的统治,两年后就开始全面推行有限自由化的“新经济体制”。角色的设置同样强调“模糊空洞”这个特点,无论是囚犯还是守军,每个人物都只是导演手中自由挥舞的脸谱,表情僵硬寡言少语,服装发型都极为相似,毫无个性特征可言,不但可看作是对匈牙利人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下精神状态空虚麻木的嘲讽,还加强了本片的寓言性。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幕后线索人物“叛军首领桑德尔(sandor )”,在大经周折的追查后被认为压根就不在此地,叛军残部的精神信仰沦为虚无飘渺的幽灵,连政府军的行为也在军官含糊的话语中变得可疑甚至可笑,一切元素都在杨索的精心调控下化为了“无牢之牢”寓言框架的组成部分。
1967年杨索推出《红军与白军》,故事背景设在革命后陷入内战的苏联(乌克兰地区),影片原是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同时也可能是由于在这一年苏匈牙友好条约续约20年),由苏联和匈牙利联合制作,但杨索却把故事背景推迟了两年.这部绝对不是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大唱赞歌的影片在苏联被禁映但在国际上依然获得绝高赞誉。1968年的《静默与呼喊》则是关于1919年的匈牙利大革命时期的故事,这两部电影延续并进一步提升了《无望的人们》带来的成功,杨索今后独步天下傲然绝尘的复杂长镜头调度此时已经日渐成熟。1968年的《冲突confrontation》讲述了1947年一群苏维埃信徒对某所大学的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故事,,原本平和的观念交流很快变成了卑鄙的诋毁和争斗。在不断拍片的过程中杨索对超长镜头的迷恋愈加严重,一个半小时的<静默与呼喊>只有区区11个镜头,《冲突>只有31个镜头,而他1969年关于30年代南斯拉夫恐怖分子的<焚风>甚至只有9个镜头.
随着匈牙利有限自由化的进程进一步展开,完成《冲突》后杨就长期在国外工作,尤其在意大利居住了将近十年,他的国外作品包括1970年的《和平主义者pacifist》,1972年的《技巧与礼仪technique and rite》和1973年的《罗马需要第二个恺撒rome want another caesar》,都是用民间戏剧的形式来表现历史和神话的尝试,但是得到的评价都很低。这段时间他定期回国处理家庭事务并拍摄一些充满民族特色的作品,1971年获得了嘎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红色赞美诗》和1972年改编自希腊神话故事的《伊莱克特拉elektreia》都是这一尝试的成果,普遍被认为是杨索电影美学的最高成就,此时他的长镜头强迫症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这些作品虽然镜头调度流畅强妙场景变换潇洒自如但却透出雕琢过分的工匠气息,人物和道具很多时候简直好像潺潺流水一般按照一定顺序从摄影机前面流淌而过。太过执着于个人理念的杨索在70年代中后期终于从颠峰跌落,他的作品从反响不大逐渐沦为无人关注。特别是他在1979年同时推出的三部曲计划中的前两部《匈牙利狂想曲》(李斯特创造的音乐体裁,大量采用匈牙利农民音乐曲调为基础,)和《快板巴巴罗(Allegro Barbaro)》(20世纪前半匈牙利伟大的音乐家巴托克的代表作),因混乱的剧情和夸张的表现手法而令无论国内还是海外的观众都大呼如闻天书,三部曲的第三部《前奏曲》最后只能是无疾而终。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对女体裸露镜头的大量使用也引发了了匈牙利国内保守人士的误会和恶评狂潮,1976年由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联合制作的关于奥匈帝国皇室堕落的古装剧《惩恶扬善private vices,public virtues》在欧洲部分地区甚至被放到软色情片院线放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