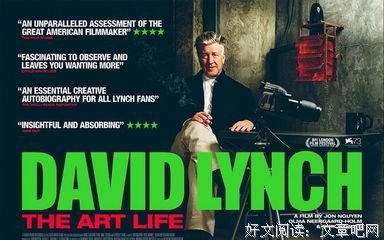
《大卫·林奇:艺术人生》是一部由乔恩·阮 / 瑞克·巴恩斯 / 奥利维亚·内尔加德-霍尔姆执导,大卫·林奇主演的一部纪录片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卫·林奇:艺术人生》观后感(一):林奇的饥渴
做艺术家,做到大卫林奇这个地步,真是太幸福了。 他在纪录片里,除了抽烟,就是画画,搞创作时,即便身边有个孩子,也各做各的,非常和谐。从小,林奇就因为特殊的癖好被爸爸当做怪胎,但我们都知道,他只是更为敏感。 片子里,林奇对着一架话筒回忆往事,他有自己的节奏。他说到儿时在自己家门口,遇到一个裸体的女人。那是他第一次发现世界如此不同。他看到女人时,仅仅是黄昏。但女人走过街角,天已经黑了。 他回忆起带父亲去停尸房,那种头皮发麻的兴奋,我感同身受。林奇最幸运的,是他的这种感受,他一直不停的通过创作来表达,而且,他因为这种表达,获得了第一笔创作资金。这影响了他一生。 幸运的人,大概就是在需要时,总会从天而降援手吧。 而这种幸运的获得基础,是你一直保持着表达的饥渴。
《大卫·林奇:艺术人生》观后感(二):Voice from Mind
[David Lynnch] Today's comment. Aquite strange kindly man. Seems have lots of special skills. The film use the thought of D's mind voice, describing a biogragph for people. But bad side is the whole film always use his thought voice, little use others, single way to express would make this film too boring. 内心独白,简单明了,直至内心。不足之处在于,单一模式化的内心独白,使影片索然无味。
《大卫·林奇:艺术人生》观后感(三):上豆瓣之前就觉得这部片子会有“非议”
这部片子给我们展现的是大卫林奇不一样的生活,作为一个画家、或是说有些“表现主义”画家的样貌。
就像有些人觉得不拍有关电影的事迹,好像索然无味一样。实际上,一个伟大的人的高光时刻,需要那些“索然无味”甚至“苦行”、“被误解”的经历铺垫、洗礼,而这些是组成他的艺术、他的电影风格的一部分,或者说真正的内核。
在看这部纪录片时,我就会想到有人会拿不列举电影事迹为由批驳一番,我只想说,如果你想读懂大卫林奇的电影,去仔细看他的电影、拉片子、解读镜头语言、写影评、画分镜、仿拍...
纪录片,尤其是艺术纪录片,应当聚焦在一个个体身上,一个艺术家身上。很显然这部纪录片,不是要我们看到他电影创作的幕后,而是让我们了解一个更加立体的大卫林奇,一些我们看不到却左右他艺术审美与风格的身份,一些难以启齿、难以回忆的过往故事。
在纪录片里,毫无防备地表达、回忆,或美好、或苦痛,很有勇气,开始接触这个领域、纪录、拍摄,便知道有多难能可贵。
关于失焦等等,我认为,导演处理时就想把镜头拉到焦外,更多是一种艺术语言的问题、而不是技术的问题。
以上。
《大卫·林奇:艺术人生》观后感(四):好莱坞导演大卫·林奇的40年冥想生活
“有很多人饱受精神压力的折磨,这不仅仅是压力,而是一种令人痛苦的精神创伤,”大卫·林奇说。
“当他们学会了静坐冥想的技巧,就像把高压锅的盖子给瞬间打开了,这种力量能改变一个人,非常不可思议,非常地美。”
1973年,大卫·林奇在妹妹的强烈建议下,开始学习冥想。“真正的幸福不在外界,而在自身”。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他,让他开始愿意坚持练习。
“就像冥想给每个人带来的改变那样,我更加开心了,心里的怒气不见了,我的精力更好了,各种想法都从脑子里自然地蹦出来,我感觉特别好,很积极乐观。那种改变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而这之后的每一天都是这样的。”记者在问冥想对他的导演工作有什么影响时,他这样回答记者。
“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有源源不绝的智慧、创造力、快乐、爱、能量和平静。每当人们真正地超越知觉的时候,他们就能感受这个地方,然后注入这些能量,他们的知觉感官就会开始扩展。”
“人们总是觉得,哎,我太忙啦,没有冥想的时间。但是我们每天浪费的时间远远多于四十分钟,你只需要把冥想作为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在早上你开始工作前,你冥想二十分钟,然后晚上再冥想二十分钟。当你冥想结束以后,你就完全恢复活力了,这就像在银行里面存钱一样。”
大卫·林奇希望凭借自己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认识冥想,并把冥想作为一项健康的生活习惯。
大卫·林奇在洛杉矶的电影工作室,如今已经成为了练习冥想的场地。
前“火柴盒20”乐队的成员亚当·盖纳向记者讲述了冥想是如何帮助他,摆脱母亲去世的悲痛的:“我以前听说过冥想练习,但都没在意,没想到现在对它充满了感恩之情。”
来林奇工作室练习冥想的明星们,都表示从保持定期冥想的习惯中,获得了无可比拟的好处。
“只能说,在完成目标的路上,一切会变得越来越好。有句话说,你,即是世界。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你戴上绿色的眼镜,你看到的世界就是绿色的,所以如果你压力很大的话,世界看起来也会很糟糕,如果你开始清理这些东西,然后注入美好的东西,世界就会看起来越来越美。”
“现在,人们总是很累,大家压力都很大,这是一个极度疯狂的世界,但是如果你每天都给自己注入能量,一切就会变好。所以你可以这样来看这件事情:在一个黑暗的世界,每个人都变成了一道光的话,就没有黑暗了。我们应该是开心的,应该是一群每天带着笑容的快乐的人。”
如今的林奇,是否他对冥想的不倦热情取代了拍电影的兴趣?或者是他发现了更高的人生追求?
林奇站在巨大的电影放映屏前,用单调如诵经的声音描述冥想是如何帮助人们改变困境的。林奇曾告诉他的听众,做出练习冥想的决定并不难,“就像让你在虚弱呕吐与身体强健之间选择,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林奇也许已经选择另一种人生了,尽管这会使得电影院里少了一抹惊悚、暴力、荒诞的超现实色彩。
也许,努力通过宣传冥想来创造世界和平,这才是林奇所做的所有事情中,最具有“林奇主义”色彩的事。
《大卫·林奇:艺术人生》观后感(五):你以为是什么让艺术家成为艺术家?
《大卫·林奇:艺术人生》
这是一部大卫·林奇导演的纪录片
词穷到满脑子就是重复这个一点含量都没有,但是充满力量饱含崇敬的词语。真心牛。
关于这个艺术家
只看过《穆赫兰道》这一部作品,一遍。但是印象也是极为深刻的,一个多重解读的梦境,一场各种可能的相识。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人有不同于常人的思维方式。
童年无法言说的阴影导致他整个成长过程中的黑暗思考。虽然直到最后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经历了怎样的过去。但是讲述过程中几度停顿,他说他讲不下去了。大量的留白、叹息,让观看者也倒吸一口凉气。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成长过程中的叛逆,过度的敏感,对底层生活恶的全盘吸收……
他无时无刻不在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在画作上。
持续地、不间歇地
专注地、执着地
作画
大卫·林奇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动态画”,他迷上了电影
他近乎偏执狂的人生就此开始
大卫·林奇好像总有抓住一切幻觉、梦境、黑暗、想象,并把它们变成现实的能力
真实的恐惧
关于这个纪录片
节奏真的非常棒,不亚于看了一部悬疑电影。大卫的画作、大卫的音乐、大卫的独白,一起营造出凸显人物性格的氛围,很赞。
他和女儿一起坐在工作台前听得音乐感觉太赞了,好像是他自己的创作。回来搜了一下,只找到了意境非常相似的歌。为了这首歌也想再看一遍这片子啊啊啊。
大卫·林奇如何理解人生,又是为什么这样理解?
他如何成长到现在?他经历了怎样的人生?
这些黑暗的画作、电影、他的思考是从哪里来的?
他为何执着?为何执着于艺术?为了艺术他放弃了什么?
纪录片展现的淋漓尽致。
通过什么表现的的呢?
他的独白、他的作品、他对每一段关系的处理、他人生中的每一次选择
除了女儿外,他大量的自我独处
大量的留白,全景、固定镜头里,大卫·林奇在思考、抽烟、玩着手指
仰拍
在一个角落里,面对话筒自我讲述过去,非常有感,像是大卫·林奇应该存在的一个空间,融成这纪录片真实的一部分。
许多过去故事的讲述用照片、旧视频也并不觉得枯燥,内在有推动力,已经对观众形成吸引。
片子的结尾
大卫说
It's all about it
It's all about it
It's all about it
艺术 就是他人生的 全部
《大卫·林奇:艺术人生》观后感(六):成为林奇
兴许是《双峰》第三季开播,影视圈一针兴奋,纷纷做起林奇主题放映。我应该没正经看过他的电影,但也知道诡异的《橡皮头》、超现实主义梦境《穆赫兰道》还有神秘且神奇的电视剧《双峰》,更不用提另佐杜罗夫斯基大笑不已的“烂片”《沙丘》(虽然我觉得就算集合全明星、筹集足够的资金,大佐杜也会把《沙丘》拍得乱七八糟)。因此在纽约的时候,也就顺路看了《大卫·林奇:艺术人生》。这部电影还是众筹的产物。我在格林威治村的IFC看的。这个影院主打艺术电影、独立电影、纪录片还有外国电影,是众多电影院之一。放映厅不大,但是也挺舒适,等待时放映一些名人拜访的影像,片头是预告。除我以外就一位老人,毕竟可能一大早没什么事就看看电影(何况放映很久了,估计看的人也少了)。大概这是美国电影生态的一景吧。
知名的天才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定义过林奇主义:一种极具特殊意义的反讽,将极度的恐怖与极度的平淡相结合,且前者蕴含在后者之中,欲语还休。
纪录片讲述大卫成为林奇之前的故事。其实没怎么谈电影,除了一些早期短片外,也就谈了《橡皮头》。整体是林奇的自述,听他絮絮叨叨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加以绘画、短片、照片、录像等,同时拍摄他的作画以及和带小女儿的日常生活。我草草翻了翻罗德雷编写的《林奇谈林奇》(中文旧版叫《我心狂野》,新版叫《与火同行》),有些内容好像差不多,因此顶多是对林奇的初步认识吧。
林奇并不愿意接受采访,不过导演乔恩·阮到底说服了他,可见这个机会多难得,就像他说的,“你没法直接走到大卫面前让他和你掏心掏肺。大卫不是那种很好采访的人,采访会被他牵着走。”。
1946年,林奇生于蒙大拿州的密苏拉市,后来跟着家庭到处搬。罗德雷评价:“将这种漫游式生活方式看做林奇影片那种独特而又充满不安的特征的重要根源。”用他在访谈录里的话来说,“我倒真有个田园牧歌式的童年。”“我的童年的确像个梦。”不过,他还说了,“唯一令我不安的是许多精神病患者也号称他们有个非常快乐的童年。”在简单快乐之余,他还能回忆起一段如梦境般诡异的经历:在街上遇到一个裸体女人。听他绘声绘色的描述也能感到种不安的恐怖。大卫从小就爱绘画,很感激母亲,“不给我看着色书,怕我会被框住。”因此他慢慢变为了画家。
然而他在波士顿博物馆大学(也不懂在哪儿)并不开心,不打算继续学习,而是飞到欧洲游学——不过十五天就回来了。之后去“穷人版纽约”费城学习,在绘画同时,也制作“视觉艺术”短片,直至拍摄《橡皮头》。“他一直说费城对他的艺术的影响远超过任何其他东西。”
影片中出现的绘画短片都有超现实色彩,如一团诡异的梦境,“一只穿过我家的扭曲的手的阴影”。小时候他便从美国中部的平静生活中感受到了恐怖,“从那时候起黑暗就悄悄爬了进来;童年记忆是灵感源泉。”结合生活经历,他将自己的想法投射到画布上、胶片上,用惊悚、暴力、荒诞的超现实色彩描绘生活,并一直追求艺术表达。他还得感谢他人的资助和鼓励,“他的父母也不想看到他成为一个落魄艺术家”。
阮评价“大卫只会做一些细碎的琐事,他从来不会迎合镜头刻意表演。从早到晚,他都是一个人闷在工作室里,而且他从小就是这样。….他是个硬核的艺术家,他绝对是作为艺术家而活着的。”
2006年的《内陆帝国》后,林奇没有拍过长片;他已经宣布退出电影业,而巨制《双峰》再次回归电视(前两集在戛纳电影节放映)。现在他还沉迷灵修,“也许林奇已经选择另一种人生了”“也许努力通过宣传冥想来创造世界和平,扎尔才是林奇所做的事情中,最具林奇主义色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