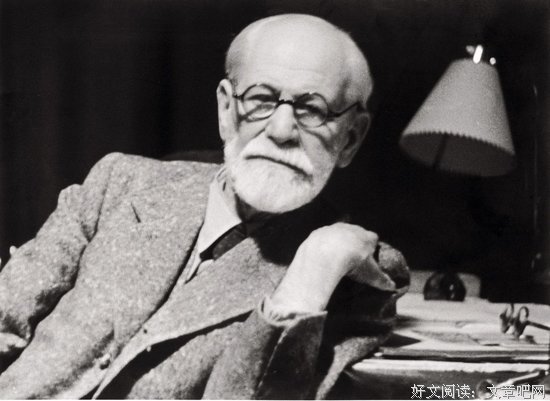1、但这个他人也是一个欲望主体,他也欲望被承认或被认可,同时,人要真正地成为人,就必须超越保存生命的单纯动物式的关注,甘愿为了他作为人的欲望而冒付出生命的危险,这就导致了主体之间为获得对方的耳鬓厮磨代号确认而进行的生死之战:谈论自我意识的“起源”,就必须谈论为了得到“承认”的生死斗争。
2、“物”并不就是实在界,“物”只是处于实在界之中,它是象征侵入实在界之后所呈现出来的实在界的一角。但从这个一角已足以让我们看出实在界的特征。
3、对象a是悬置在主体与他者之间的东西,它既属于主体和他者,但也不属于这两者。它是内部与外部的悖论性结合,其与主体是一种外密性关系,即它既在主体之内,是主体自身最隐秘的一部分,但又不属于主体,它总是出现在主体以外的他处,总是躲避主体对它的捕捉。
4、在镜像阶段,自我与力比多之间有一种类似于跷跷板的游戏。自我本来是力比多投注的结果,可它一旦形成,自身便成为力比多的贮存库,不仅把自己想象为一个理想的“我”,还进而以这个理想形象占据他人的位置发挥其功能,以自我的欲望形式去想象自我与他人和世界的关系,把异于自身的世界想象为一个内在于自身的统一世界。殊不知这个自我本质上就是一个他人,这个自我的欲望其实就是他人的欲望,当它以自已的欲望形式来想象他人和世界的时候,那其实已经是一种误认。也正是因为这个误认,在自我与他人和世界之间就开始了一场无穷无尽的求证过程,自我总想从他人那里辩认出自身,殊不知其本身就是一个他人,而对他人形象一次又一次的认同带来的并非自我欲望的满足,而是欲望在他人那里的一种达成。
5、我只是我,我就是那个不可言述的东西,我就是那个把一切符号性的委任都减去后所留下的剩余-我只是那个残余、那个废料; 我只是一个残渣,一个渣滓;根本上说,我只是一个“人渣”,一个不可符号化的,无名的遗落物:我在这样一个位置,从那里,我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宇宙是纯净的无中的一个缺陷”
6、主体最初不仅是以自身的镜像为中介,而且是以同伴的躯体为中介来定位和辩认欲望的。恰恰是在那个时刻,人的意识以自身意识的形式辨识出自身。正因为他是在他人的身体中辨认自身的欲望的,交换才可以发生。正因为他的欲望朝向了他人的一方,他才可以把自己同化于他人的躯体,并辨认出作为躯体的自已。
7、“我”的分裂则在于,我在获得“意义”的同时,我的存在有一部分必定要被切割,成为有意识的“我”根本无法参透的“非意义”,“我”与那个被切割的部分是分离的,“我”的有所得是以失落或牺牲作为代价的。这意味着,“我在”作为一种寻求确定性的主体化行为其实是主体在“思”和“在”之间的两难选择,并且是一个被迫的两难选择,就像“要钱还是要命”的选择一样,在这个二选一的选择中,主体并无选择的自由,因为他必须选一样,且只能选一样——或者要钱,或者要命。
8、从其所朝向的对象的观点看,主体的欲望只有通过一种竞争,通过同他人的一种绝对敌性才能达一关系中得到确证。并且每当我们走近某一给定主体中的这一原始异化,最根本的侵凌性就会出现--这就是欲望他人消失,因为他支撑着主体的欲望。所谓人类共存的书面是不可能的,这并非社会现实意义上的,“欲望他人消失”并不是真的要去对他人实施谋杀,它指的是自我的那种侵凌性,是停留于想象的自恋中的主体的无意识之“思”--社会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就是这种无意识思维的体现。
9、作为受语言制约的一种动物的一个特征,人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
10、阉割意味着原乐必须被拒绝,为的是在欲望之大法的相反层级上可以得到它。
11、人的欲望是他人的欲望还意味着人的欲望是朝向或者说“针对”他人的欲望,因为人的欲望不能像动物的欲望那样只针对一个自然的给定物,那种欲望的激发下的否定活动只会产生出一个与给定物一样的自然的自我,而人的欲望是要产生一个不同于动物的“自我”的自我,这种属于人的自我只有当否定的行动是“针对”他人时才有可能。
12、对于笛卡儿的那个公式,应当改写为:“我在我不在的地方思,所以我在我不思的地方在”;“在我是我的思的玩物的地方,我不在;在我没觉得我在思的地方,我思着我之所是。”
13、实言是瞄准、构成真理的言语,因为它是在某人为另一人所确认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实言是行事(perform)的言语。
14、误读式的意义漂移:因为德语的“Es”(它)与“subjekt”(主体)的首字母同音而把主体置于“它”的位置,在主体与“它”之间进行嫁接,而这个“它”根本上就是无意识的结构,这样,主体被置于这个位置其实就是被置于无意识结构的位置。于是,所谓“在它所在的地方,我必在那里生成”,似乎可以翻译为:在无意识所在的地方,“我”必作为主体出现,“我”必作为主体生成。拉康的嫁接不过就是为了在一个不可知、不可控制的力量中来定位主体的存在。
15、潜意识是人类行为的源头,我们所有的感受,判断,分析和选择都源于潜意识。所以,既然梦是潜意识的释放,那么我们所说的现实只是虚幻,梦才是真实的。 ----《催眠师手记》
16、什么是主体被剥夺了的那个东西呢?是菲勒斯,正是从菲勒斯那里对象获得了它在幻象中的功能,进而,从菲勒斯那里,欲望由作为欲望指向的幻象所构成。
17、原乐的伦 理学,因其把我们引向死亡的境域,故而可以说是一种有关不可能性的伦理学,主体总是且只能在不可能的实在着死亡舞蹈,那致死之快感/享受便是主体的抒情诗般的内核,是主体朝向其本真之在的最后一跃。
18、面对阉割威胁,男孩最终放弃了对母亲的欲望,转而认同父亲而欲望母亲以外的另一性别,而女孩依旧认同于父亲,欲望从父亲那里获得她想要的东西,当这一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时,她又转而欲望拥有一个孩子,把孩子当作补偿自身欠缺的对象,用拉康后来的术语说,当作一个想象的菲勒斯,在想象的层面来定位自己的性别位置,女孩只能以另一性的形象作为其认同的基础。
19、任意性原则,即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和在文化中约定俗成的,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内在联系,或者说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不可论证的。
20、眼睛与凝视-这就是对我们而言的分裂,在那里,驱力得以在视界领域的层面呈现。
21、被菲勒斯能指禁止的原乐和通过拥有菲勒斯能指而获得的原乐。
22、我只能从一点去看,但我的存在中,我却在四面八方中被看。
23、正是父之名在那个位置上的缺失,才在所指中打开了一个洞穴,并由此引发了能指的一连串变迁,而想象中那日益扩大的灾难就是从这些变迁中产生的,直至最后能指和所指在一个谵妄的隐喻中稳定下来。
24、对于拉康所讲的这种“不对称性”,我们需要在最充分的意义上来理解,因为它恰好显示了笛卡儿的我思主体的逻辑困境:在笛卡儿那里,由“我思”指向“我在”是通过一系列的自我确证来完成的,虽然“我思”的确定性是通过所谓的“普遍怀疑”获得的,可这并不能保证“我思”的主体和“我在”的主体是同一个主体。
25、从欲望的角度说,自恋的想象性认同是为了从他人那里获得对自身的辨认,在这里,他人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欲望主体而存在的,在想象层面,自他人的关系是一种想象关系,它们之间并非如各尔和科耶夫所说的一个独立的自我与另一个独立的自我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不是一个欲望与另一 个欲望之间的关系,而是欲望与欲望对象之间的关系,自我欲望从他人那里辨认自己的理想形象,它想占据直到取代他人的位置,因此,自我对他人的想象性认同实际上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换句话说,在想象的层面,所谓人类共存的局面根本上是一种不可能性。
26、虽然侵凌性和力比多冲动仍被归于想象的移情的主体间关系——它仍然是主体的自我与作为镜像对体的小他者的关系——但在象征的移情中不再是主体对主体的关系,而是主体对作为位置能指的大他者的关系,分析师至多只是他者位置的一个代理,就是说,现在重要的不是他的言语的内容,不是他的言语的揭示功能,而是他作为分析师在言谈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是主体对分析师所处的这个他者位置的辨认和认同,就像拉康在同时期的论文《典型疗法的变体》(1955年)中所说的,“他在回答中所说的内容远不及他做出回应的位置重要。
27、你有多少个恋人有用吗? 如果他们没有谁可以给你一个宇宙。What does it matter how many lovers you have if none of them gives you the universe?” ----《Jacques Lacan》
28、这一为了确认的生死之战最终导致了主奴关系的形成,获胜的一方成为主人,失败的一方因为恐惧死亡只得放弃自己的欲望,屈从地成为奴隶。
29、能指的差异作为“标记”首先标记的是主体位置的差异,是主体在意指链条中所占据的位置的不同,就像那两个相向而坐的小孩,因各自对自身所居位置的完全认同而使他或她看不到单一能指本身的空洞和不完整性,从而“把能指的位置和所指混为一谈” ----《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
30、再明确不过的是,人的欲望是在他人 的欲望中发现其意义 的,这不是因为他人掌控有所欲望对象的钥匙,而是因为他的首要目的在于得到他人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