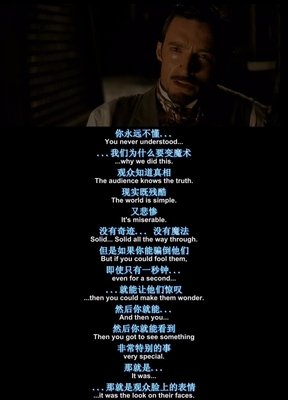早年间的第一份工作,为了办理户档迁移的事宜,向领导要来半天假期。
人山人海的排队中,从一个城区的有关部门,办理了第一部分程序;而后赶往第二个城区,继续拿着号码牌在等待着。
直到接近下班的尾声,终于听到了我的名字。走到柜台,工作人员说,你的材料不齐全。原来是第一阶段的证明纸张里,少改了一个章。
“总之上个阶段的材料不完善,我这里就不能给你通过。”
后面的场景,大部分已经不大记得了。或者说,是我不愿意回忆起来。
唯一记得的,那是我成人之后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崩溃,声嘶力竭。甚至说,算是人生里,第一次在公众场合接近“大哭大闹”的那种挣扎跟讨伐。
我厌恶那些不负责任的工作人员,我厌恶他们坐在舒适的大厅里,准点上班准点下班,毫无同情心。
我甚至厌恶那些与我一起办理手续的同期同事们,因为他们一切都很顺利。于是可以像看待一个怪物样,看着我在柜台前跟工作人员交战、求情、苦恼、指责、甚至憎恨。
之所以忽略这件小事的细节,是因为,细节并不是影响我成为如今的自己的主要脉络。
我并没有为此而感到丢脸——在那么多不熟悉的陌生人,或者半是熟悉的同事面前。
我的关注重点是在于:在那样一个场景里,世界的运转即便没有遵循我的意愿,但是我尚未找到可以处理的方式。
那是唯一一次,或者也是最后一次——以那样的崩溃之程度呈现。
几年后,在当时居住的某处城中村里,夜里去楼下买东西。街道的一处角落冲出来一个女生,在大声叫喊着什么。身后跟着跑出来一个男生,在一旁试图想要将她安抚,顺便带离现场。
女生并不妥协,本来是稍微激动的情绪,眼见着围观的人越多,终于开始接近崩溃。她一句一句地数落着那个男生的全部,像是沉淀了数年的委屈,像火山爆发一样冲破了出来。
我站在远处,观察着那些围观的人。他们只是看着,不作评论,不作行动——至少那两人只是在相互拉扯,而不是真正地动手脚。
我拎着几袋水果,脑海里突然冒出一句话:如果我是那个正在哭泣的女生,此时此刻,我又会作何感想?
我会不会恨极了眼前这一切——
走到这一步,并非我所愿;可是我偏偏走到了这一步,跟眼前这样一个男人;在发生这么多之后,我发现自己无力解决任何难题。
于是我在夜里时分,与他争吵的某个导火线中,破门而出;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往哪里,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先逃出来。
于是我逃到了大街上。
尽管意识中我觉得这样的举动并不体面,甚至极其幼稚——可是这一刻,如果我无法将心中的苦闷,以某种形式宣泄出来,我可能等不到后来的反省时刻了。
因为这一刻,我觉得自己就要死去了。
脑海中想起那一次在办证大厅里的歇斯底里。这一刻我终于意识到,一个人悲伤、失望、绝望到某个程度,会大脑产生空白。
迎面而战,说的是跟这个世界呐喊——借用眼前某个“背黑锅”的人——那个工作人员、那个男人、大街上那些围观的人——在某种奢望的虚幻期盼中,你以为,那样是可以有用的。
我是在那一刻,开始意识到,“坐以待毙之无力感”这件事情的恐怖。
从延伸的角度来说,算是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需要创造自己的缓冲区(地带)的重要性。
那个几乎人人都彼此熟悉的小镇上,男人跟女人的吵架,大多是女人会走到大街上,先是大哭大闹,再找到某个有威望的族长进行申诉——并且邀请其他的亲人、邻居、一家老小进行围观。
就像是一场盛大的仪式——请你们参与我的伸冤大会,帮我一起数落这个男人:他花天酒地,夜不归宿;他好吃懒做,不照顾孩子;他跟另一个女人往来亲密,在另一处地方有了家。
而那个哭泣中的“我”——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门多,而后得到的是这样的结果——“请你们替我指责他、讨伐他、甚至以神的名义惩罚他!”
年少时候,我从不喜欢出门。除了上学的时间,其余都是待在家里。于是大多时候,都是在母亲口中,听到这些故事。
偶尔有几回跟母亲出门,亲身经历过几次那样的画面,觉得震惊、并且不可思议。
“你知道的,他们会吵闹,然后继续生活在一起。”
“可是,既然这样,为何还要过下去?”
“那怎么解决呢?”
“哪有什么解不解决的。最多就是,直到其中一个人先死去,这场战争才会结束。”
这是母亲的原话。
她告诉我,这就是婚姻,大约就是这样的。
并且疑惑在多年之后得到了解答:
母亲当年向我传达的,其实不仅仅是婚姻的困局,更是关乎人与人(这个世道)之间的相处困局。
人与人之间,或许并不存在直接对应的“不是你对就是我错”,而是在于,有些事情它就是发生了——以一种不受控的方式。
这些不受控,几乎无法追本溯源。
那个因为当初忘了给我盖齐所有印章的某个工作人员,或许是他故意的,或许是他无意的;但是我不能因为“为了原谅他所以就当是他无心的”——那样我自己会不快乐。
再往前假设,或许是他中午没有休息好,或许是那段时间失恋了不在状态,或许是公务员的岗位太舒适、于是并不需要多少责任心跟细心。
于是在百密一疏中,我就成了那个无辜者。
我的“受害效应”是:当时我处于人生第一份工作的试用期,半天的假期对我来说太难得;我害怕自己因为私事耽误了工作,会让我的直系领导不满意;如果领导不满意,会影响到我的转正、薪水、甚至前途。
这些效应,是我自己的问题,可是又不仅仅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的人生、我的前途、我命运,也是要搭配所有的外事外物,而后呈现出来的综合结果。
所以,当下那一刻,我无法原谅那个失误的工作人员。
我当然不记得他的样子,第二日再去补办印章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还是不是同一个人。我就像没有发生过前一天的歇斯底里一样,平静地处理好剩余的流程。
我已经清醒过来了,在那一刻。
并且,他也没有义务知道,他的无心之失,究竟对我的个体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在那个阶段而言。
我至今觉得,我之所以记得这件小事,不是因为这个委屈的经历,而是某种更深刻的反思:
在往后的人生里,我会遇上更多这样的“失误”时刻——无论是具体的某个人,还是历史进程的发展——总之我就被推入到了某个被困的境地。
到那个时候,那我又该如何处理这一类“并没有直接负责人但是结果需要我来负担”的不对等局面?
那个在马路上歇斯底里地哭闹的女生,或许她哭泣的不是眼前那个男人,那夜忘了给她过生日;而是一想到自己要跟这样的男人生活,过此一生,于是为此感到某种心碎。
或许她也想过离开,换一个人会不会更好;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自己并没有离开的能力,或者勇气。
这种看似无能为力的结果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清楚地知道,这个结果是你亲手选择的。
你选择了那样的生活,走入了那样的不归路。
你几次那样冲出到大街上,想要借用“群众的力量”分担一下自己心底的苦闷;可是你最后哭累了,还是只能任凭他半扶半拖着你,回到那处阴暗狭窄的房子。
你在夜里继续哭泣。
你知道,第二日你会醒来,继续辛劳度日。他还是那个样子,你也还是这个样子。
其实你并不觉得,现在的这处阴暗狭窄的房子住起来有多委屈;你委屈的,是一想到这一生,都要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这是你崩溃的理由。
一个女人想要发疯,其实不必有任何具体的逼迫跟冲击。只要她能够识别出一些现象背后的本质,那就足矣让她惊恐到发疯。
不仅女人如此,人本来就是如此。
于是总有过来人告诉你,难得糊涂。其实不是糊涂很好,而是只有糊涂着、继续糊涂着,大多数人才可以过此一生。
那么,那些清醒的人怎么办?带着已经知晓的参透,麻木而虚无地度过此生吗?
我倒觉得,不必非得如此。
快乐的猪,痛苦的哲人,都是活法而已。而真正值得我去采纳的是:我需要在识别出所有现象背后的本质之后,再去将新的版图拼凑起来。
那些活在小情小爱中的人们,我自然不羡慕他们;但是我会祝福他们,希望他们可以那样在“小小的烦恼跟忧愁”中过此一生。
至于我要的,则是识别出所有大悲大喜之后的部分——
我带着已经发生过、经历过、被撞击过的种种感受,去将其一点点地编织成一张网。
于是,我可以确保自己,这一生都不会落入“心碎到无力回天”的境地。
七年前大学毕业,走入社会江湖的第一个夏天。那一次的歇斯底里之后,我再也没有在任何除了家(是我自己的那个私人领域的小家)以外的场合,与人争执、甚至纠缠过。
而后我继续练习,从在家里的一些肤浅的哭泣中,渐渐将眼泪转变成能量,埋藏进我所能够敲下来的纪录文字里。
人们总说,平静之中的绝望,是大多数成年人的日常。我倒觉得,越是往后走,你的承受底线会更深——以某种你无法想象到的韧劲。
以及,在某个节点,突然发现自己开始变成了从前我所期待的那一类——
悲伤的时候不再哭泣,而是平心气和地感受、继而去解决难题本身;与此同时我把眼泪留给了那些美好的、感动的、触及到了柔软深处的领域。
寻思这样的结果之缘由,我能想到的是:
即便人生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的叠加,但是也意味着是一个个“更优选择”的持续放大效应;
我在反反复复的追寻中,并没有打算让自己成为那种在同一个错误中跌倒两次的人;
我期待、并叮嘱自己,要借用一次次的“唯一的一次”,来将其后续的反思效应变得深刻,提炼出指引法则,来使得我后来的生活变得更好——从里到外。
如今我所能得到的重要力量,或者说当初那个夏天的委屈,带给我的后续影响是:
我知道没有人在那件小事中需要承担巨大的责任,最多不过是我第二日费些时间、精力、车费,去补齐这一切而已。
可是,这还没结束。我没打算放过它——某种无力感对我所造成的恐惧。
我希望从今往后,我可以尽可能地处理周全生活的碎事;即便有所耽搁,但是我拥有属于自己的缓冲区——有了对应的处理思维跟资源。
倘若某一类事情——天灾人祸、生老病死,发生到某种极端的程度,我也知晓了如何躲藏回到安全地带,进行疗伤的方法。
写到这里的时候,终于可以说一句:如果创造快乐是一种能力,那么学会处理痛苦,是一种更大的能力。
不要任凭那些“本可不必”的事情发生,而你只是坐在原地哭泣。
那不该是二十年后的你,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