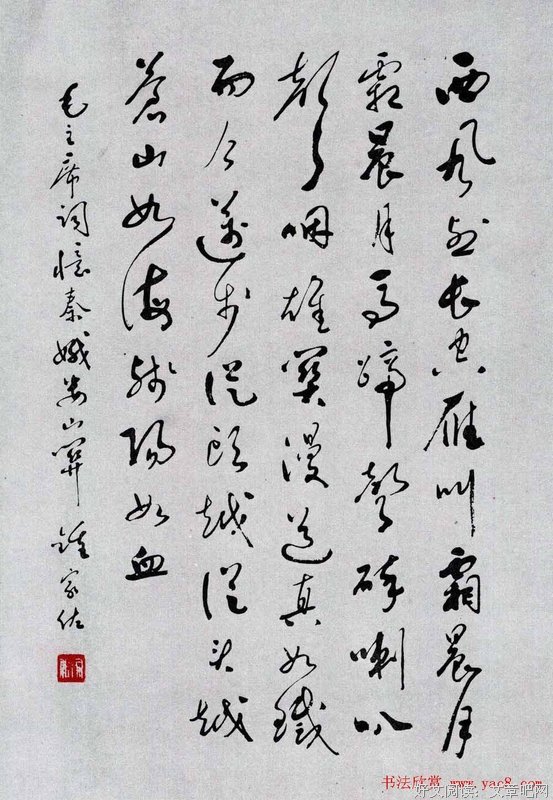近年来我搬了好几次家,
每次搬的时候都引来许多围观的人。
书不像西瓜,可以甩着来,一捆书太重,
甩接几次就没有手劲了。摔破一个西瓜不要紧,
摔坏了书却叫人心疼。
书架直达壁顶,一架架连过去、围起来,
书房成了一个典仪,操持着生命的盈亏缩胀。
睁大眼睛慢慢地巡视一遍,
然后又站在中间凝思良久,
已张罗起了一个很像样子的书房。
图片
而我则依然故我,因为有这些书的围绕。
在石窟和禅房中吞吐着一个精神道场。
友人中多的是放达之士,一进书房便爬上蹲下,
随意翻阅。有的友人一进门就宣布,不是来看我,
而是来看书的,要我别理他们,照样工作。
这种时候我总是很高兴,
但是,担忧也隐隐在心头升起,
怕终于听到那句耳熟的话。
那句话还是来了:“这几本我借去了!”
我没有学别人,在书房里贴上“恕不借书”的布告。
我也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
但对于书,我虽口头答应,心中却在嗫嚅。
图片
其一,怕急用的时候遍找无着。
然而那本书却不在,这下就慌了手脚,
因为文思的梳理、文气的酝酿,
于是只好定下心来,细细回想是谁借走了这几本书。
拿走几本我“也许用不到”的书。
其实文章一旦展开,谁知道用到用不到呢。
有时我只好暗自祈祷:但愿最近真的用不到。
即如我写这篇文章,几次想起周作人几本文集中,
不知被谁借去了,刚才还找得心急火燎。
其二,怕归还时书籍被弄“熟”弄脏。
捧着一本挺展洁净的书,自己的心情也立即变得舒朗。
图片
整个气氛回荡着雅洁和高尚。但是,借去还来的书,
常常变成卷角弯脊,一派衰相。有时看上去还算干净,
却没有了原先的那份挺拔,拿在手上软绵绵、熟沓沓,
如果书店里还有这本书卖,我准会再去买一本,
把“熟”了的那本随手送掉。
或问:“你不是也购置远年旧书吗,
旧书还讲究得了什么挺拔?”
我们不能因为古铜鼎绿锈斑剥,把日常器皿也都搞脏。
其三,怕借去后彼此忘掉。
我有好些书,多年不见归还,也忘了是谁借的,
不想故意吞没,而是借去后看看放放,
3年前我去一位朋友家,见他书架上,
正是我的书,忘了是什么时候被他借去的。
“你要看就借去吧,我没什么用。”
我怕他尴尬,就笑了一下,把书放回书架。
图片
我已有了新出的版本,就算默默地送给这位朋友了吧。
好在他不在文化界工作,不会看到我的这篇文章。
但是,有些失落不归的书是无法补购的了。
有人说,身外之物,何必顶真?
倡这些书曾经参加了我的精神构建,失落了它们,
既有约约绰绰的印象,
不是个中人很难知道:失书和丢钱完全是两回事。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赵景深教授。他藏书甚富,
或他自己临时要用,借书者就会收到他的一封信。
又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半年前,
他竟在报上发表告示,
要求借了他书的人能及时归还。
却是个不记事的马大哈,久而久之突然发现,
自己的书少了那么多,不知向谁追讨,
除了登报别无良策。
图片
我见报后不久来到他家,向他表白,我没有借过。
问了一声“真的?”我不无惶恐,尽管我确实没有借过。
更是一丝无存。有时我也想学学赵景深教授,
我算什么呢,区区那一点书,
面对亲朋好友,也敢把登记簿递过去?
他本也是个买书迷,身边钱不多,见有好书,
夜间书店又不开门,等到星期天又怕书卖完,
他死时,家里的一个书架已经相当充盈,
但他长年守寡的母亲并不识字,
能把这些书买下来,即使有,
图片
我估计这位母亲会永远地守护着这些书,
假设这架书还在,我敢断言,当年同宿舍的同学,
大多还能记起,哪一本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买来的,
当时引起过何等样的欣喜。这是一截截生命的组接,
当买书者的自然生命消逝之后,
这些书就成了一种死灰般的存在,
或者成了一群可怜的流浪汉。
如果说这一架书不足为道,
逝世的时候,如何处置丰富的藏书,
大多没有让自己的子女承袭己业。
但在钻研深度上往往不能望其父亲之项背。
总而言之,老学者的丰富藏书,对子女未必有用。
劝家属不要让藏书随便流散,以保存永久性的纪念。
家属对这些言词大多抱有警惕,
背地里悄悄地请了旧书店的收购员前来估价。
旧书店收购了他们所需要的书,
学校图书馆也就因恼怒而不再登门接洽,
余下的书籍最后当作废纸论斤卖掉,
图片
死后把藏书全部献给图书馆。
但是这些学者并非海内大儒,
图书馆不会开设专室集中存放。
个人藏书散入大库,
哗啦一下就什么踪迹也找不到了。
但无可否认,这是学者的第二次死亡。
有位教授对着书房反复思量,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最后忽发奇想,决定以自己的余年,
教授寻找的,其实是自己第二生命的延续,
能谈得上延续的至多是自己写的书;
至于藏书,管不得那么多了。
写藏书写出如许悲凉,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
但我觉得,这种悲凉中蕴涵着某种文化品尝。
常常随着生命的终止而终止。
需要耗费多少精力和时间。苦苦汇聚,死死钻研,
筛选爬剔,孜孜矻矻。这个过程,
图片
让你占领世间已有的精神成果,
又让这些精神成果占领你。
当你渐渐在书房里感到舒心惬意了。
也就意味着你在前人和他人面前,
开始取得了个体自由。
越是成熟,书房的精神结构越带有个性,
越对社会历史文化具有选择性。
再宏大的百科全书、图书集成也代替不了,
一个成熟学者的书房,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越是如此,
这个书房也就越是与学者的生命,
带有不可离异性。
书房的完满构建总在学者的晚年,
因此,书房的生命十分短暂。
新的一代起来了,他们必须从头来起,
先是一本本地购读,一点点地汇聚,
然后再一步步地自我构建。单单继承一个书房,
就像贴近一个异己的生命,怎么也溶不成一体。
历史上有多少人能最终构建起自己的书房呢?
社会上多的是随手翻翻的借书者。
而少数好不容易走向相对完整的灵魂,
随着须发皓然的躯体,快速地在书房中殒灭。
历史文化的大浪费,莫过于此了。
嗜书如命的中国文人啊,
你们的光荣和悲哀,该怎样裁割呢?
【伊人婉韵雅致】编辑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