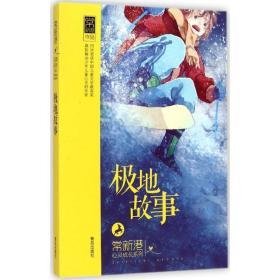
电影《逆冰之行》(Against The Ice)让我满心期待而来,一脸失望而去。我对有关极地的探险故事总是有所期待,因为那里依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神秘之地,大自然依然占据绝对主导权。而且,极地的风土又能提供一种独特的观感,和绝大部分电影完全不同。
看完《逆冰之行》以后,我突然理解了《奥德赛》为什么要那么讲述一个归家的故事,为什么要在海路上布置巨人和海妖。原因是极为伟大的探险,就是极为漫长的无聊。《逆冰之行》里,两位丹麦考察队员在孤立无援,队友撤走的情况下,于北极营地苦苦支撑了800多天,这听起来是了不起的壮举,拍成电影一定会好看。但是仔细想一想就知道,他们的伟大是一天天捱出来的,一天和另外一天之间没什么太大分别,于是等才是苦等,熬才是苦熬。请问,这样的故事怎么拍?用什么内容去填充和表现这段时间,观众在电影院里才不会走神?
几乎没有什么好方法。
我记得有部电视剧《极地恶灵》(The Terror)算是个例外,可能是迄今为止我最喜欢的极地故事。它好在哪里?好在成功塑造了一个心怀恶意的大自然,要用计谋手段诱惑水手、围困水手、毁灭水手,仿佛大自然拥有某种邪恶和神秘的人格,同时还拥有层出不穷难以预料的手段。可能是觉得这种抽象的威胁还不足够,剧集里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巨大而凶残的生物,在雾气中无声无息前来,一把抓住船只上的牺牲品远遁消失,只留下浓雾深处撕心裂肺的惨叫。
当然,《极地恶灵》是通俗小说改编电视剧,《逆冰之行》是真实历史改编电影,不能在故事情节上强行进行比较。但是从观赏性上来讲,毫无疑问,故事胜过了历史。史实会说:1、一支探险队进入北极,船只为坚冰所困;2、次年物资消耗过半,全队决定放弃船只,步行返回;3、整队人马进入风雪从此消失;4、几年后捕鲸人发现他们的遗迹,营地周围有埋葬的人类残骸,骨头上有人类啃噬过的痕迹。1和2之间是空白,可以填入争吵和冲突;3和4之间是大片空白,想象力让人不寒而栗,但是没人知道真正发生过什么。
但故事就不同,故事编造出了恶意的大自然,雾气中的狰狞怪兽。没有任何空白,一路上都是充实的抗争。所有人面对非常具体的威胁,做出非常具体的努力和反抗。也就是说,险恶的命运,严酷的环境,漫长的时光,这些概念都过于抽象,无法让人感受和想象其中的艰苦。所以,要把这些概念转化为非常具体的存在,把说出口的话直接冻成冰块落在地上的寒风,或者是无法发现和抵御的怪兽,当然要现实和具体很多。虽然是编造出来的故事,但是因此引发的情绪和感受,却和当时当地的人感受类似,这同样还是一种准确。
奥德赛受到神罚,在十年特洛伊战争之后,不得不在海上继续漂流十年,才被允许回到家乡伊萨卡。十年漂流有什么?有大量空白,面前是复制粘贴的大海,人活在复制粘贴的日子里。纵有海难,也只是一时,大海不会年复一年地沸腾咆哮。那是不是一种痛苦,是不是一种煎熬?的确是,而且超乎人们的想象。所以最一开始,人们听过奥德赛的故事,感受到他这一路的痛苦和煎熬,会让他的十年归家路变成一个传奇。
接下来不免有人就要怀疑,奥德赛是不是和所有港口酒吧里刚下船的水手两杯黄汤过后一样,是个职业吹牛犯?把大海上平平无奇的航行,硬是吹嘘成伟大冒险?再然后,一部分人在承认奥德赛是个吹牛犯的前提下,试图去理解他那么做的动机。最终承认:如果不使用这种故事形式,不能让人们的想象力有个落脚之处,大家也许永远无法相互理解。因为人就是这样,他们必须借助具体的存在才能去理解伟大,必须借助超乎寻常的存在才能去想象伟大。
有一部关于吹牛老爹的电影,叫做《大鱼》(Big Fish)。大约20年前,我在观后感里写出自己的想法: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在你所爱的人之外,才需要辨别所谓真假。而在今天,我可能要补充一句:有些对生活,对人世的理解,不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无以准确传达真实意图。只有当一个人真正接受了故事里的所有不可能和不合理之后,他才可能获得完满的理解,打破了自己和世界之间的障壁,用一种先前不可能预料的方式见到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