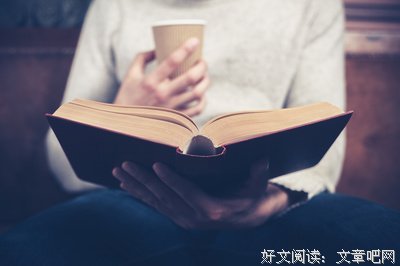
《与父亲书》是一本由向迅著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2,页数:3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与父亲书》读后感(一):《与父亲书》:与父写信,见信如面!
提起父亲这个词,我除了会想到我爸爸以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觉醒年代》中陈独秀父子了,从开始的互相怨怼,到后来的互相理解,这是大多会发生在父与子之间的人间剧情,另一个就是买橘子的故事,来自于朱自清的短片散文《背影》,讲述了他爸爸在火车上和他告别的故事。 之所以提起这些网剧和散文,是因为最近看了《与父亲书》,与父亲书,其实就是与父亲信,可能这本书是以儿子和父亲的书信来往为主要内容,全篇可能都以信件为主。这本书的封面很简单,整个封面以两张写满字的信纸为主,封面的下面是对于这本书的大概评价,整个封面看起来干净整洁。 从这本书的题目就能看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向迅与父亲的故事,书中还夹杂着象迅写给父亲的信,在我没有读这本书之前,仅仅看完他写的这封信,也能够感受到作者对于其父浓浓的眷恋以及满满的遗憾,读完唏嘘不已。 其实在我看到这本书的题目后,就已经猜到这本书的大概内容,但我把作者看成了鲁迅,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我没有看过鲁迅写这本书,所以就入手了一本,等我收到书,仔细一看是向迅,好吧,好吧,也可以先看看这本书的内容,如果不错的话,就当是意外收获了。 这本《与父亲书》除了自序和后记以外,其余的主要内容分为6个章节,整个故事不单单讲述了向迅和父亲的故事,更是全家的故事,是一代又一代无名之辈们,父与子以及父与母生活的缩影。 在向迅的自序中,身为读者的我,了解到了一个鲜活可爱的父亲 ,他会用笔记本或者练习册剪下来的纸张填满各种温柔的情绪以及啰嗦的嘘寒问暖,其中还夹杂着各种错别字以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字。 而作者自己都会惊讶,身为儿子的想迅能够隔着纸张精准的了解到他父亲的情绪,以及他父亲要表达的意思,双方对于各自的关心或许早已胜过纸张上的千言万语吧! 这本《与父亲书》厚厚的一本,但是只有300多页左右,而且尺寸不算很大,可以很随意的就装进书包或者化妆袋中,可以在空闲的时间当做故事,仔细读完,去体会向迅作为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怀念和眷念。
《与父亲书》读后感(二):你是否会从这本书中想起自己的父亲?
向迅写给父亲的信
我是始终相信文以情胜的,所以面对这些篇文章,我只能叹气。关于写作,一般来说,议论动人以理,而记叙则动人以情,我写文章偏向理,读文章却偏爱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一直为自己的状态感到不安和尴尬,我总是怀疑自己不够真诚,没办法处理一些人事。倘若是自己未曾想明白的,自然也是不足以成文的。这本《与父亲书》写得动人,诚实,实在。要我说,里面大部分都比朱自清的《背影》写得好。朱自清的《背影》难得在他用了极少的笔墨刻画出自己的父亲,但老实说,情感泛滥起来了,在朱自清那,情感泛滥成灾,我不喜欢不节制的文章,所以我不喜欢朱自清。 中国现当代文学里写父亲的似乎很少,直面的似乎只有一个朱自清。许子东在现代文学课中讲,“这些现代作家的启蒙老师大都是母亲。中国现代文学里面说父亲好的极少,算来算去只有一个半。一个是冰心,她不仅有个好老公当科学家,还有个好老爸开军舰,真难得。半个是谁呢?就是朱自清爬铁路月台那个老爸。除了这一个半,几乎找不到哪个作家说他老爸是好的。曹禺的戏剧里面写出来的父亲都是周朴园那个德性。巴金《家》里的高老太爷,也是个反面角色。这些作家写的父亲,要么去世,要么很坏,但他们笔下的母亲都是好的,比如鲁迅的‘鲁’,就是用了母亲的姓。母亲被作家恨的大概只有张爱玲。”像向迅先生这种专门写了一本书的,以我的读书少,确实我找不出来第二本。 文学史上有弑父情节,所有的男人都自己的父亲有过误解与仇恨,这几乎是人性之必然。人无法在自己有限的视野中理解和自己最像的男人。当父亲逝世后,似乎所有的男人都能够理解自己的父亲。麦家终于和父亲和解了,他等到父亲去世之后,用了8年的时间,创作出了《人生海海》,通过文学来记录自己与父亲之间的一些经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是身为人子最大的遗憾”。董卿曾这么说,我们不必为向迅先生感到遗憾,因为他已经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纪念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有了《与父亲书》。
番茄盖饭的《与父亲书》
《与父亲书》读后感(三):尴尬的亲人,真实的情感
一、一封手写信 打开这本《与父亲书》,掉落了一封手写信,这封信一下子拉近了我和作者的距离,明知道这实际上是一个印刷的手写信,但是我仿佛也在这手写的字体里看到了作者的身影。我感觉这个形式还是非常成功的。展信观看,知道了作者的父亲已经离开作者五年了。这是一封写给已逝五年父亲的不寄之书,作者在头一个段落就写下:这封书信父亲是能够感受到的,因为这个世界对于父亲而言已经没有了秘密。选择在父亲生日的前夕写下这封书信,作者表达了自己对父亲的思念之情,因为父亲的生日,想起父亲,因为母亲离开父母共同的老家而想起父亲,因为每一个相似的背影而想起父亲……在这样的思念中,作者也会忽然发现有关父亲的印象,变得非常的模糊,于是作者写下了这本书纪念他的父亲,也留下对父亲的记忆。 二、因为普通,反而有了普遍性 作者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父亲,不曾惊天动地,不曾有什么值得大家一提再提的业绩,甚至也没有和母亲作为一对恩爱夫妻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他就是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甚至还有一点大男子主义的中国男人,中国父亲。这使父亲的这个形象有了一定的代表性。在身边见过太多像文中父亲一样的形象,他们普普通通却还竭尽全力地在自己的最小势力范围(别人的感受)和最大势力范围(他所能掌控的最大的范围)挥洒自己的权利。他们对这世界对亲人并不身怀恶意,可身边的人依然会感受到粗暴。 三、无处安放的情感 在这本书里,我觉得写的最好的就是亲人们无法安放的那种情感,他们彼此关注着对方,但是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作为主线的“我”和父亲如此,作为副线的“我”和母亲,妹妹和父亲母亲、“我”和妹妹,父亲和母亲,都是这样。在本应该最亲近的人中间,流动着一种无可奈何和尴尬。他们不习惯用语言表达关心,不习惯用行动表达爱意,对于他们来说,一句贴心的话,会在肚子中打多少个来回,然后最后还是胎死腹中。一个简单的拥抱的动作,对于他们就是最难攻克的难关。一些简单的行为,比如去逛一逛动物园看一看动物表演,也会被莫名其妙的一拖再拖,最后拖成永久的遗憾。 亲人们之间仿佛离得很近,但又仿佛非常遥远。《九月永存》中父子两个之间的一组互动,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询问父亲身体还有没有其他不适。父亲是“思索了片刻”,才“犹豫”着解开了纽扣。在和成年儿子的交流中,父亲带着那样的一种隔离感。父亲的措辞也是带着某种保留:“这里有些肿。”而成年儿子的反应就是“瞄了一眼”,就“习惯性”的将眼离开……这一段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一对不善表达的父子的日常,也仿佛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同类型的中国家庭的日常。不习惯沟通,不习惯交流。长辈不习惯向晚辈诉说情感,晚辈也习惯性地漠视长辈,而这一切发生的是那样的熟极而流顺理成章…… 四、放得开的别致语言 作者的语言很放得开,读起来有一种猝不及防的惊喜。 这种文字在文中处处可见,我就举一个例子吧。 作者在《时光城堡》里写到妹妹出生的时候,把啼哭声比作了夏日的花瓣。 作者在这里使用了三个短句子:“像夏日的花瓣一样绽开。夏日攀在篱笆上的喇叭花。握着紫色拳头的喇叭花。” 三个越来越详细的句子把妹妹出生时候的那种生气勃勃、昭告天下,力量迸发。展示的非常到位。 这本书作为情感作品,作为文学作品都是很成功的。
《与父亲书》读后感(四):《与父亲书》自序:锦书谁寄来(向迅)
父亲曾给我写过许多封信。
那些信,寄自北京密云,贵州某县,乌鲁木齐,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我据此知道父亲正在哪里谋生。每每有他的信被邮差送来,我都会怀着隐秘的喜悦,躲到一个无人打扰的角落,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抽出两三页叠在一起的信纸——多半是从笔记簿或练习册上裁下的内页——展平折痕,逐字逐句读。
父亲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十分陌生的一面。这个父亲,就像是换了一副嗓子,换了一个性格,换了一副面孔,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了许多平日里听不到的话,甚至还有点噜苏(啰唆)——在他嘘寒问暖的时候。而且每封信的开头,他总是模仿古人的笔调 : 吾儿向迅,近来可好?读着这样的句子,总觉得怪怪的,令我忍俊不禁。
实际上,父亲识字不多,好多生僻字不会写,信中因此时不时地蹦出一个错字、别字,乃至他自己造出来的字。但我都会毫无障碍地认出它们,并准确领会他要表达的意思。只是那时,我从未设身处地地想过一个问题:他提笔给远方的儿子写信之前,是否有过片刻的犹疑?
我想象过父亲给我写信时的样子:夏日慵懒无聊的午后,或是春雨霏霏的凉夜,父亲在外省临时的寄居之所左顾右盼,确定房间再无他人,于是鼓起勇气,快速地从枕头下翻找出页面边缘卷曲的笔记簿和圆珠笔,然后正襟危坐于床沿, 把笔记簿摊开在沾着泥浆的双膝上, 深吸一口气,开始捉笔写信。
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对父亲而言,要把那些散落于记忆深处、已经爬满青苔的汉字搬到信纸上,就跟在没有门窗的羊圈里摸黑逮羊一样困难。他需要凭借顽强的毅力,才能把那些奔跑跳跃在无尽黑暗中的汉字一个个捕捉到,再使用一根无形的绳子把它们穿连在一起,费力地赶上坑坑洼洼的道路。
终于写完了,父亲抬起头舒了一口气,望着窗外出了一会儿神,再俯下身子,把信从头至尾默读一遍,在某个地方添加了一句话,又在另外一个地方修改了一个别字,最后庄重落款——“父亲某年某月某日” 。
搁下笔,他在信纸里侧折出一道痕迹,把它们小心翼翼地从笔记簿上裁下,举到胸前,拢起嘴唇吹了吹,然后按照一贯的严谨作风,把它们工整地对折成两折或三折,揣进上衣衣兜,并用手轻轻地压了压。
当天下午或次日早晨,父亲搭乘摩托车或卡车从喧嚣的工地出发,翻越一座座山冈和绵延不绝的山丘、庄稼地,最终到达镇上的邮局,购买信封和邮票,装好信,写下收件地址,郑重地投进邮筒。——收到信时,我仿佛还能触摸到父亲的双手留在信封上的余温,他落在信纸上的目光,还有他火焰般明亮的寂寞。
我自然也会给父亲回信。但很多时候,他都会特地在信末嘱咐,不必回信。因为他所从事的工作流动性强,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收件地址。 “你寄给我了,我也收不到。 ”父亲说。但不管怎样,几年下来,我攒下了一摞父亲写给我的信。
这是我比哥哥和妹妹幸运的地方。那时妹妹还在镇上的寄宿学校念书,有母亲照拂,而哥哥已经跟随父亲到外省谋生了 ; 当妹妹到县城乃至遥远的平原地区念书时,电话已经成为我们最主要的通信工具。他们都不可能收到父亲的信;即使收到过,肯定也不会比我收到的还要多。
正是因为这一点,我自觉比家人中的任何一位都要理解父亲。我们所熟悉的那位父亲,是一个出了名的直性子和暴脾气,不会花言巧语,更不会虚与委蛇,与人理论,八成会擦枪走火。在母亲面前,他极少表现出作为丈夫的温柔;在我们兄妹面前,他也极少表现出一位父亲应该具备的耐心。
而在信中,父亲真的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在他朴实无华的措辞中,我不仅充分感受到了他发自肺腑的关心与爱意,还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位父亲的无奈与悲哀,我甚至还隐约感受到了他为试图敞开心扉与我沟通而做出的巨大努力。
信中的父亲与现实生活中的父亲,恰如地球的南北两极,也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合起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父亲,立体的父亲。 这个父亲,有幸被我看见了,读到了,感受到了。而哥哥和妹妹,只看见父亲的一个侧面;母亲或许也是如此。
这大约是天意。因为我将在日后一次次尝试书写父亲。更有意味的是,我识字的启蒙老师,不是别人,正是父亲。在我未满七周岁之前,是他手把手教我读完了一年级语文教材上的课文。下雨天,他躬身二楼的窗前教我朗诵课文的画面,如今仍能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模糊的轮廓。
我曾把父亲写给我的那一摞信件视为珍稀之物。我把它们放在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里。它们跟着我挤公交,搭乘长途巴士,乘坐绿皮火车。我把它们从江汉平原带到珠江三角洲,又从珠江三角洲带到湘江之滨。
正是在湘江之滨,我开始书写父亲。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男人。同时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 某一日,我怀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把父亲写给我的那些信件和其他一些比较私密的信件,悉数销毁。我把它们撕成碎片,扔进了垃圾桶。
二〇一五年春天,我野心勃勃地计划为父亲写一本书,我第一时间就想到那摞信件正是最佳的创作素材,可任我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父亲写给我的只言片语。冷静下来,我才想起前几年做过的蠢事,后悔莫及。
一年之后,那摞信件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那年夏天,父亲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如果那些信件还被我完好无损地保存着,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阅读每一封信的时候感受到一个真实的父亲。否则,我们就只能通过回忆了。
而回忆是多么的不可靠。我当年销毁那些信件时,极有可能在心底给自己列出了一条减轻负罪感的理由 : 我已记住信件的内容,销毁也无妨。事实如何呢?我已不能回忆起一个完整的句子。
而这,也是我这几年不停书写父亲的原因。我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父亲的记忆会越来越模糊。我要通过书写的方式,让父亲活着,让他逐渐模糊的形象重新变得清晰起来。这既是我理解父亲的方式,也是我怀念父亲的方式。
自从父亲离开我们以后,每天总有那么几个时刻, “父亲”这个字眼和他的身影会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逝。他的离开,在我的生命里制造了一道永远也无法弥合的伤口。即使我身在地球的另一端。
两年前, 我随团去智利访问。在圣地亚哥辛普森街 7 号,智利作家协会为我们安排了一场特别的文学活动。他们邀请我们在小礼堂朗诵自己的一首诗歌或文章节选。轮到我时,我不假思索地朗诵了我写给父亲的一首小诗。
朗诵时,礼堂里安静得就像是父亲曾经带我经过的雨后的马尾松丛林 ; 朗诵完毕,过了好一会儿,掌声才从听众席上爆发出来。
我相信这异国他乡的听众,听懂了一个中国人写给他父亲的诗篇。
2021 年 3 月 15 日定稿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