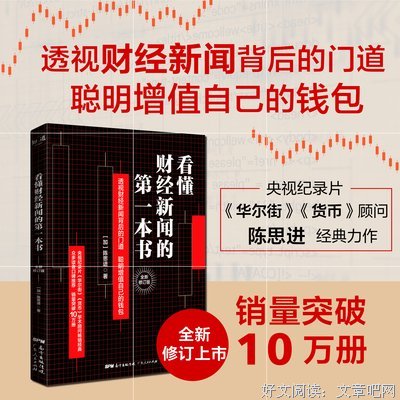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是一本由Anna Lowenhaupt Tsing著作,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Hardcover图书,本书定价:USD 29.95,页数:3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精选点评:
●la地区第一干松茸拥有者以后在发松茸的时候会想起广岛核爆后长出的那第一个松茸。是不是有一点章回体小说开头的意思了。//读完好久忘记标了,最打动我的其实不是松茸的故事,真的写的太散了。Hmong族的处境大概是华裔必须要正视的了。
●第一部分相当有启发性,每一个小节都试图用松茸生活图景中的一个部分创造一个后资本主义生活隐喻,可惜后半部分就有点迷失了
●like first half. second half seems diverged
●非专业角度读本书还是很喜欢的,推荐。几个关键概念:Precarity, Assemblage, Salvage, Symbiosis, Latent commons. 涵括数个学科边缘的架势和作者本身的见解一致:作为局外人对中国的现状把握得也很到位
●太过个人化了。题目很吸引人,但内容有点令人失望
●2018 fall: 本假期最惊喜 在仿佛快要失去新意的时候看到这本书真是太新鲜脱俗了 2019 fall: 重读真的太可怕了 读成一本新书 只有此时才懂得为什么要anti-scalability 什么是the arts of noticing / if we are still trapped in the dominance-resistence or the progress model we are missing way too much
●没有想象的INTENSE,整体大框架在现下的学术潮流中极其政治正确,所以并没有看出任何的特殊,而其刻意追求地新颖形式也使得全书的叙述太散与无力。感觉他提到的书会比这本书本身有意思很多。
●非常愉快的阅读体验,从supply chain到precarity到最后谈到做学术都很有趣。
●感情大于逻辑
●论文用过,补标。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读后感(一):故事性大于学术性
个人很喜欢这本书,因为很喜欢这种以小见大讲一个故事的叙事。这本书从一种偏门的菌类(比起口蘑什么的)串起了东方和西方,近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甚至学术史,故事讲得太精彩了。我觉得要是完全以此书为脚本拍个纪录片肯定是个特别有看头的纪录片。
但是要从经典的学术结构来说,好像这本书只是提出了问题,没有回答问题。如果按照副标题来说,要探讨的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生存,这个问题似乎并未被解答。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说,松茸也更像是一种比喻和象征,而不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当然作者最后的章节都用anti ending作为标题了,得出一个结论似乎也并不是她所追求的,当然这个问题能得出一个特别确切的答案吗?不能,我想很多章节也表示了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即使是似乎可以公式化的科学问题。
也许当代的人类学研究已经以讲故事为主,那倒是蛮不错的,10年研究,最后以很强的讲故事能力穿起研究的片段,我倒是蛮喜欢这样的学术写作的(绝不是因为我自己的论文也没有什么结论回答不了什么问题)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读后感(二):倘若夏日将会终结
森山直太朗的《夏の终わり》唱道:“焼け落ちた夏の恋呗忘れじの人は泡沫/空は夕暮れ”(夏日的爱恋燃烧殆尽、人如泡沫被遗忘,空留残阳在天边)。我想这是对于这本书一个很棒的浪漫化的阐释:在夏日的尽头,在丛林的身处,一场秋雨过后,棵棵松茸马上就要悄然从暗处探出头来;这里看不到人类运作的痕迹,只有一股自然的力量在泥土中蓄势待发。书中,在遭到原子弹摧残的广岛市的土壤上,蘑菇是人们发现的第一种重获新生的生物。可想,相对于人类文明经济地建设,自然仍然在我们所占有的土地上保有极大的活力与影响力。
本书作者Tsing追踪着这林间精灵的孢子步伐,去探究当看似稳固且富足的现代生活图景燃烧殆尽之时,以一种半假想的方式去眺望剥离了绝大多数现代化给予我们的方便与规则之后的现代社会。居安思危的人们似乎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作者就以松茸产业为例子,展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图景之外,人类世界在整个地球生态圈内存在着许多不稳定的侧面。
生态上,松茸也是人类活动对自然影响的表现之一。松茸在日本的大规模生长与食用,其实与历史人类活动有极大关系。日本工业革命前夕(18世纪),砍伐树林的行为让阔叶林的面积大幅减少,同时给予了赤松充分的阳光与适宜的矿物土壤,而松茸的最常见宿主就是赤松。同一时间,松茸受到了幕府贵族的青睐,成为了珍贵的美味,也被文人墨客所追捧。随着现代化的步伐,森林砍伐日趋严重,松茸热也在明治维新后登峰造极。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城市化进程与化石燃料的广泛使用,让人们对木材的需求减少,阔叶林回来了,松茸产量降低了,它的价格飞升,成为了奢侈的食材。可以说,松茸的成功上位,是人类从未预计到的商业造星成果。
地质学家提出的“人类世”(Anthropocene),没有准确的开始时间,只描述为人类对地球生态产生重大影响的世代。这个概念的内涵不局限于人类对自然的主动改造,更多地指向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与难以自控的影响。这种生态上的不稳定,深深影响着人类社会,每天都考验着人们的理性,因为现在看来,人类对生态的考量与行动,大多数时候是严重滞后的。Tsing将“人类世”这个还具有争议的概念进行解构,对其内涵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的批判。当老饕和富贾们对松茸趋之若鹜之时,这小小的蘑菇,也在塑造着人类文明与经济的走势。Tsing就是将多物种的共同作用放在生态圈的核心,人与其他生物之间,有着极大的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也投射在了人类生活的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
经济上,由圈地运动开始,为了集中和积累财富,资本主义就把人力与其他生物都归纳为投资对象,把他们视作生产资料。这种生命的异化和自然景观的商品化的后果之一就是生态破坏。同时资本主义为从业者所许诺的就业稳定、经济发展、财富积累,不论是狭义或者广义上,都还没有完成。但是,松茸作为一种商品,其实并不能给采茸人带来稳定可观的收入,那是因为他们并不受雇于现代农业,而是在山林中搜寻自然的馈赠。在这一层面,原始赶山而采摘“山珍”松茸的商业运作可以说是落后的,甚至与资本主义所倡导的相悖的。然而全球对松茸的需求与追捧,又是资本主义所造就的。
这本书并不是对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遐想,它其实更加着眼当下经济态势:并非所用的经济团体与个人都追求进步与增长,世界经济存在着普遍的多相性。但是由于这种多相性在当下仍然是难以预测、难以管控的,所以很多经济学家选择边缘化或者忽视它的存在。这种多相性所包涵的一些情况,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作为使得资本主义覆灭的潜在威胁,但是Tsing却认为资本主义其实有能力内部消化吸收这种多相性的。Tsing挑战的是资本主义所许诺的繁盛稳定的社会图景,以此去丰富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内涵。
从人类学角度出发,Tsing接用松茸产业链条探讨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不稳定,其中难免也有所短处。本书作者并不是会讲故事的人,书中用比较浅显与苍白的文字记录了作者随采茸人进山寻茸的历程,作者对新鲜松茸色香味形的描述过于客观,让人提不起兴趣。这对于学者来说,似乎不是致命伤,然而这本书用了很大篇幅与记录田野研究的日常,浅白的故事让这本书可读性并不强。第二,Tsing并没有完成所谓的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目的,书中对于生态与经济的探讨似乎被“蘑菇”这个对象所限制,并没有真正的触及到两个领域的核心,也没有给出新的研究范式,本书的开放结尾也算是一种遗憾。
说到底,《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仍旧值得一读,Tsing的巧思让人耳目一新。松茸给我们的启示看似偏激,它挑战了我们长久以来笃信的观念——现代化让人类不断进步。许多情况下,人类并没有一直进步,而是以非常规的“节奏”(Rhythms)在自我活动,许多个体尝试把自己的节奏与时代所宣扬的大步走的趋势捆绑起来,然而他们由于不可预见的因素都失败了。松茸作为食品、商品、甚至于科学试验品与文学意象,都以一种不可预见的“节奏”挑战着资本主义的稳定性。资本主义与现代化并非代表着永恒夏日一般的光明的未来,它们只不过是社会运动的机器之一,只是因为他们太过强大,太过有效,所以让人高估了它们的能力以及放纵它们不受拘束地侵入其他人类社会的领域。资本主义把生产资料进行转换与再生产,通过资本去运作广泛的社会机制。事实上,不是所以事情都在这个机器里进行加工。倘若夏日即将终结,我们必须把这颗蓝色星球上的其他生物体不再看作资本,不再用以投资的目光去权衡它的利弊,而是以共生的关系去接触他们,人类社会的边际会有所扩大,虽然Tsing坚信,最后的结果也许是与人类中心主义相违背的,地球既不是生物和谐共处,也不是一类生物征服统治另一类。跳出资本主义的思维范式,人类其实从来不曾远离原始与野蛮,从未获得生命的全面保障与社会进步的永续动力。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读后感(三):松茸与古着:梦游的拾荒者(随笔节选)
自寒假以来,我缓慢地推进着对《末日松茸》(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的阅读,于是也自然地将关于这本民族志的思考带入了本次课堂。《末日松茸》是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人类学教授安娜(anna lowenhaupt tsing)在追踪松茸的摘采与售卖过程中写下的民族志。安娜认为,能够连接其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群、能够在极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必须经由偶然的“遭遇”才能获得的松茸,为这个处于资本主义废墟之中的世界提供了某种可能的希望。
在得知我们需要做一个自己感兴趣并能够做的民族志时,我第一时间便想到了松茸。当然,对于我们生活在北京的学生来说,很难有机会能从源头起进入松茸的产业链。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古着。选取古着作为民族志的对象并非偶然。首先,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挑选和购买古着的经验;其次,无论经历多少次,整个购物过程依旧会带给我巨大的困惑和难言的感受——这种感受被我阅读《末日松茸》时找回,如同置身于松茸采集和交易现场。古着和松茸是相似的。我将沿着安娜记录和分析松茸的脉络展开,提出我的问题,展现我的关注。
古着和松茸的相似性主要见于以下几点[ 因为本次作业只需要简单陈述研究主题,在下文的论述中逐句找出并标注某句话在《末日松茸》中的对应未免有累赘之嫌,因此下文不对松茸的相关论述做出出处标注。另外,碍于笔者经验和研究可行性,本文对“古着”“古着市场”的定义、形式、历史等的论述以日本-中国为主要起点,且古着、古着市场、古着产业链专指女性的古着、女性古着的市场、女性古着的产业链。]:
一、诞生于废墟的旧日希望
松茸能够在极恶劣的环境中生长。近世以来,资本主义对环境造成了无法忽视的破坏,似乎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沦为一片废墟。但是松茸并未为此而遭受某种威胁,无论是工业化污染后的森林还是核爆后的大地,松茸都能在其间生存。从这个意义来说,松茸不啻是上天赐予这个岌岌可危的人类世的礼物。
松茸的奇妙气味和味道是这一礼物的另一注脚。在消费松茸最为疯狂的日本人看来,松茸的气味和味道勾起他们对旧日美好时光的回忆——那是一种童年般的、未受污染的、亲近自然的想象,是一个与都市文明不再处于同一时间经验层的伊甸园。
古着同样具有以上内在维度。2019年夏天,我去东京之前,特意做了东京古着店的攻略。古着市场成熟于九十年代末期与新世纪之交的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碎冲击了此前二十多年来日本人对奢侈品的狂热消费。一方面,日本人大量转卖他们的奢侈品;另一方面,日本的消费热潮仍未消退,使得这些价格较低的二手奢侈品大受欢迎。这一循环持续至今。在东京的古着店里,诸如香奈儿、爱马仕、路易威登等品牌的二手商品随处可见。可以说,每一件古着背后都有一片湮没在历史中的废墟,这些废墟是资本主义行进车轮留下的痕迹。
这样,也不难理解古着对于古典优雅的旧日想象的承载。这种想象是带有西方主义色彩的、从东方发出的想象: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模式促进了日本战后的经济辉煌,而来自西方的文化是日本消费主义高涨的推力之一,直到泡沫破碎,日本人们转卖的所有品中最为抢手的依然是西方品牌的商品。
从我在网络平台上购买古着的经验来看,进入中国的古着大多来自日本。那么,我们面对古着时,很有可能面对着双重的想象:一重是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及其历史的,一重是东方(日本)对西方(欧美)的。前一重想象流动于当下,而后一种想象已定格在过去,显现在形形色色的古着的风格、产地、年代里。对于消费者运用和实现这种复合想象的冲动,我姑且称之为希望。这是意在发掘和赋予自己独特性,以抵抗越发不稳定世界的希望。
二、以遭遇为进路的商品
在采菇人们看来,松茸的出现完全是偶然的。他们无法去寻找松茸,只能遭遇松茸。这也是为什么松茸价格如此高昂的原因之一。同时,松茸也是无法人工栽培的。这意味着,整个跨国的、庞大的、资金数额巨大的松茸产业链,几乎紧紧地依赖于采菇人与松茸的相遇。
松茸也必须依靠遭遇获得。松茸的气味、附近地层的特征、动植物对它的反应,都构成了遭遇松茸的现场,缺少一个因素,这个现场就不可能存在,采菇人也无法采到松茸。遭遇的现场贯穿于整个松茸产业链:采菇人、交易商、食客,无一不在与松茸遭遇,无一不在进入松茸的一个个现场。这是松茸以其自身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逼迫资本主义商品逻辑在经过它时发生波折的体现。
有过进入古着店(无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挑选商品的经验的人,应该都会同意,购买古着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意外和探索,一如采菇人进入茫茫森林,必须把森林之外的经验抛掷脑后。采菇人以自然间千丝万缕的线索去遭遇松茸,古着买家以自己对旧日的想象样式去遭遇古着。古着所承载的想象图景既是其历史注入的特征,也是买家建构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只有在买家遭遇到其所满意的古着的那一刻,关于这件古着的想象才能完成,达成闭环。就此而言,购买古着的过程有着现象学意味:只有投入意向,事物才能存在。
三、扩散的特性
能够克服恶劣环境的生存能力,和孢子式的传播,使松茸能够扩散到世界各处。松茸的扩散并非全是自然的进程,而更多是资本主义链条下人类活动契合了其特性的结果。
在对“洋垃圾”的担忧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古着的“扩散”与这种扩散背后的认识和想象。“洋垃圾”是古着的理想类型的反面。在古着商家的文本里,我们能清楚地辨认出古着的理想类型:富有品位的商家从一个个原主人处逐件地收购服饰,这些服饰最好携带着原主人的某种故事,经由商家小心地收集、打理、编排,最终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剧目式地售卖。在这个理想类型中,商家与原主人的交易更像是一种仪式,宣告原主人对其服饰的所有权终止,这件服饰重新回到了需要被赋予所属身份的状态,是可用于再次交易的。尽管我们知道,不可能所有古着都经过这么温情脉脉的前资本主义式的商家与原主人的交易,但规范化、模式化的成熟古着产业(如日本的古着连锁店)也能够用标准化的商标祛除古着上(原主人的)魅影。
“洋垃圾”完全颠覆了这套似乎可以放心的对古着的认识。据深藏在网络中的种种声音所言,如果某家线上古着店的发货地是广东,那么千万不要买这一家的商品,因为广东的某个地方(依据不同的发言者,这个地方可以是不同的地名)是专门处理“洋垃圾“的。他们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一幅“洋垃圾”“入侵”的图景:从国外而来的垃圾(垃圾性来自于仪式的缺失,比如,“直接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衣服”),带着(不可见却致命的)病菌,停靠在南国边陲某个港口(地点的不确定更凸显了其遥远感,加剧了“洋垃圾”的伤害性)。这是对外来灾难的刻画,也是对资本主义链条下不断扩散的灾难——厄运、禁忌、死亡的刻画。
诚然,当我在布局精美、介绍详细的线上商店里挑选古着时,我很难把它们和那种成吨进入、不怀好意、蝗灾式的图景联系起来,可是倘若发货地显示是广东某处,我依然会有所不安。伴随着在欧美-日本-中国的航道和都市市集里扩散的古着的,是它出身低微的孪生姐妹,以及关于不洁的忧虑和传说。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读后感(四):一朵松茸开启的末日微光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据说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广岛地区最先恢复生机的是松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都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之后,媒体展现的广岛满是荒芜,没有生机的荒芜,广岛成为世界末日的想象模型,也成为警惕末日的警钟。就在人们对广岛感到无望时,突然冒出来的松茸打破长久以来笼罩广岛的末日气氛,在通向末日想象的路途中,末日进程似乎因为横空出世的松茸按下暂停键,也开启末日微光。人类学家Anna Tsing正是从这一株株松茸身上看到世界一连串的不稳定性以及生物与非生物之间共生共长的联系,松茸开启的不仅是末日进程的暂停也是我们思考世界方式的转变。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是一本围绕松茸展开的民族志,与大部分民族志不同的是它缺少清晰的逻辑线,作者力图展现的是事物之间纠缠繁绕的状态,这一纠缠关系以动态不稳定呈现,同时这些联系并不是单向联系而是多向联系,这就让人愈加迷惑。为解释这一团乱麻,我试图以松茸为主体展开分析,但这不意味着松茸占据主要地位,它只是方便我们厘清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载体,同时这些关系也不是均等平衡状态而是动态不稳定状态。
松茸缘何而来——作为生物的松茸
松茸的诞生是自然馈赠的礼物,科学家分析松茸生长的原始生态环境包括松树,真菌,充足的阳光,硫质土壤,足够的空间。松茸生长的必要条件决定了我们改变任意一个条件,就将改变它的出现与否,基于松茸生长的复杂环境,目前来说它的出现与否仍然无法预料,正是这种无法预料的不稳定性给我们带来唏嘘也带来惊喜。
日本地区松茸的大面积消失为我们揭示人类世演进对松茸消亡的影响。作者在书中详细梳理了日本社会的发展间接导致松茸消亡的历程,将松茸,人类,树木等因素紧紧联结。事情要从日本江户时期开始说起,江户时期为扩建佛寺和使用燃料,浓密的森林遭到砍伐,被砍伐的阔叶林为日本赤松腾出空间,并能接受更多阳光,松树的繁盛使得和它伴生的松茸繁荣生长。明治维新时期在现代化目标之下,人们继续砍伐森林,松茸继续繁盛。然而1950年始,随着国家现代化发展,森林规划,林地私有化,大面积的标准化林地出现,以及人类燃料的使用变化,居住在日本乡野的人纷纷抛弃森林,走向城市。森林的生态环境缺少人类干扰,多种植物在森林大舞台展开竞技,日本赤松逐渐败下阵来,松茸至此变得稀有。松茸在日本的历程带来惊喜也带来唏嘘,而美国俄勒冈地区的松茸更多带来惊喜。美国早期发展工业森林的需求给森林留下巨大创伤,当采伐撤出森林时,保护森林成为国家政策,但是国内对于森林的需求并没有减弱,战后美国提出皆伐计划,皆伐是指将伐区内的成熟树木短时间内(一般不超过1年),全部伐光或者几乎全部伐光方式,伐后通过种植生长快速的同龄树木恢复森林。能够快速生长的海滩松被选中,辅之以国家森林火灾排除计划,海滩松的生长环境得到保障,与此相伴松茸惊喜出现。除却日本和美国,作者还分析了芬兰和中国云南的松茸历程,尽管松茸出现的情况不一样但其中都不缺乏人类阴差阳错的干扰。所谓“干扰”正如作者所言,它不是单纯带来“好”与“坏”,而是开放式的结局,我们能够看到消亡也能看到新生。
松茸生长历程促使我们意识到松茸的生长联结了人类与非人类的诸多因素,它们纠缠在一起促使松茸出现与消亡,Anna Tsing关于松茸的这本著作回应了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中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主张,“作为本体论转向的重要声音,哈拉维抵制对诸如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等术语所暗示的性别权威基础。从她熟悉的生物领域着手,她坚持把其他生物引入人类学的记述中,并且希望能够想象和制定一个可以为这些生物创造空间的伦理和政治。”这是一种关于“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的尝试,在谋求多物种共生共长这一点上,Anna Tsing无疑是成功的,她对松茸出现与消亡的详细书写揭示不同事物之间纠缠繁杂的关系,正是这种纠缠繁复造就我们的世界,人类不能以“人类世”为中心生存下去。
松茸去往何方——作为商品的松茸
原本松茸只是作为一种山野蘑菇,却因为不可人工生产以及无法预料生长与否的不稳定性备受喜爱,尤其是对于日本来说,松茸的消亡间接性催生他们的松茸情节,紧接着催生跨国松茸贸易,我们看到美国和中国云南采摘的松茸几小时后便以高价出现在日本市场。Anna Tsing为我们揭示松茸商品的旅行历程,这段旅程勾连不同的人群,也勾连不同的经济形态。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一书用“自由”这个概念统摄美国俄勒冈地区的采摘者。俄勒冈地区采摘松茸的人群主要有退伍的白人军人,迁居乡间白人以及东南亚人,不同的采摘人群因为“自由”汇聚在一起采摘松茸,“自由”也不是同质化的自由,而是具有异质性。白人群体聚居此地回溯创伤进行创伤治愈,也有人希望生活在山林里以回归战争生活的相似感,迁居到此的白人更多是希望逃逸资本主义。东南亚人多为政治难民,战争移民,初入美国的他们有的借战争经验在山林自力更生,有的借山林生活找回族群曾经的生活模式(瑶人与苗人),有的则是迫于福利政策取消后于山林中寻求生计。不同人群对于自由的追寻与记忆紧密相连,而记忆与世界政治经济变迁紧紧相连,我们从采摘者身上看到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运转。
松茸的商品化历程需要经历“采集者-bulkers-买家-出口商-进口商”这多重传送才能到达日本,这条供应链既把松茸变成商品,也伴随一些不同于马克思界定的资本主义经济链条的有趣现象。马克思论述资本原始积累的实质是用经济手段使得劳动者与生产要素分离的历史过程,通过这种方式,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被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困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逻辑,认为只有当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才能完成资本积累,松茸商品化历程却为我们揭示出不一样的资本积累方式,即松茸的出现并不受资本家的控制,但是资本家却也通过松茸完成积累资本的目的。作者认为这才是资本主义运作的特征,她将其称之为“残余积累”(Salvage accumulation),即“企业在不控制商品生产条件的情况下聚敛资本的过程”。这一积累方式又是如何完成的呢?Anna Tsing借用Shiho Satsuka的“转译”(translation)概念,以及生态学的“区块”(patches)概念即不同的社会政治空间来解释。转译之前我们需要需要回顾松茸到达买家手中的open ticket现场,open ticket是松茸进行第一波买卖的行规,即采摘者卖给买家的原始价格如果在同一晚上出现波动,可以掉转头回去找买家议价,这鼓励采摘者尽快将手中的松茸卖出去投入下一场松茸采摘过程,同时也避免采摘者的收入降低。松茸在美国分散生长的形势使得松茸不能以采摘者个人售卖到达日本,因此懂得采摘松茸的人将松茸卖给bulkers,bulkers收集好松茸后再将松茸卖给出口商,出口商通过程序化的加工使得松茸变成商品出口到日本。这中间由于涉及不同的文化,很难说有人能够直接跨越中间过程直接连接采摘者和日本进口商,有也是个别且基于行业规则不受待见。这整个过程之后松茸被异化为资本主义商品,成为资本市场的存货,至此松茸的自由被抹去,而“残余积累”使得不同的人群共同创造了资本,完成转译。转译成功后我们不得不提到的一个有趣现象是松茸到达日本后又被作为礼物赠出,这一转换又消解松茸的商品性质。
作为商品的松茸就这样完成它的旅行,变成一盘珍馐出现在日本人的餐桌上,满足人们的松茸情节。Anna Tsing在序言中坦言,当代的资本主义过度强调资本主义的“进步”,与此同时忽略了其他,通过“残余积累”的方式我们看到资本积累的不同方式并非充满着资本主义的剥削。然而我认为作者对于采摘者的叙述,尤其是基于自由的强调忽略了采摘者的生存,他们采摘松茸更重要的是为生存而非自由,如果他们能够享受更好的福利待遇,还会采松茸吗?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然而不能将这种开放理解为同质,我们或许可以说迁居的白人出于这一原因,但其他族群未必。仅仅依据这一点为资本主义的不稳定辩驳缺乏效力。
实验——作为研究对象的松茸
当人们对松茸展开科学研究,不同国家表现出不同的科学呈现方式。日本研究者认为日本对于森林的干扰程度还不够,这样就导致松茸无法出现,而美国则认为人类过多的干扰只会破坏松茸的生长环境,残害物种,中国则趋向于位于二者之间,开展中日合作,中美合作,美其名曰“国际化”。不同国度对于松茸的不同期待产生了不同的知识区块,这些知识区块相互分离,但也偶尔汇聚。通过关于松茸的知识区块分析,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世界的科学是由知识区块拼接而成,相互之间的碰撞将会产生新的知识,不断壮大。
从松茸的产生,松茸的商品化,到松茸的知识区块,作者始终在探讨多物种存在的可能性,世界是一个纠缠繁复的聚合体,结局是开放式的,聚合体内不稳定的动态关系为我们带来唏嘘与惊喜两面,正如松茸般让人看见新生也看见消亡。一朵松茸展现的是末日废墟之上的生命,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异质性,不同知识区块发展壮大的可能性,这些倡导轻而易举能够俘获受困于后现代权力理论的我们,使得我们能够从结构之下抽离出片刻喘口气,然而回来以后还是会发现这一倡导的艰难行进。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读后感(五):罗安清:《不受控制的边缘:作为伴侣物种的蘑菇》(2012)
封面图片:盛产于云南雨季的青头菌人性是一种物种间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哈拉维的“伴侣物种”(companion species)概念引领我们超越熟悉的伴侣,去向丰富的生态多样性。没有了生态多样性,人类无法存活。谷物驯化了人类。种植园给予我们称其为种族的亚种。家封锁了物种间和物种内部的爱。但是,蘑菇采集带我们去到其它地方——去到不受控制的边缘,去到帝国空间的裂隙。我们无法忽视种族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赋予了地球上的我们以生命。这里有很多大的故事要讲,它们不应该留给控制这一领域的人类胜利者。本文将打开作为世界历史主角的多物种景观之门。不受控制的边缘:作为伴侣物种的蘑菇 UNRULY EDGES: MUSHROOMS AS COMPANION SPECIES
作者:罗安清(Anna Tsing,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人类学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1 (2012) 141-154
献给 唐娜·哈拉维 For Donna Haraway
统治、驯化和爱深刻地纠缠在一起。家是物种内部和物种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最令人窒息的地方。鉴于它被夸大的快乐,对地球上的多物种生命而言,家也许不是最好的主意。相反,考虑一下边缘地带丰富的多样性。考虑一下蘑菇。
本文不仅得益于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伴侣物种”(companion species)概念,也因她让我们能够既科学又文化地去批判,拒绝把科学和文化隔绝开来,敢于用一个简短的句子或一篇精悍的文章去讲述世界的历史。
本文以伴侣经验(companionate experience)和生物学开篇,随后进入驯化的历史和欧洲人征服的历史,并探索全球资本主义裂隙间政治与生物多样性的潜力。这些材料提出了一种有关真菌的论点,反对过分热衷于驯化的理念——至少是对女人和植物的驯化。
译者注:有关哈拉维提出的“伴侣物种”概念的更多内容,参见其著作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s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2003).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评价人数不足Donna Haraway / 2003 / Prickly Paradigm Press多物种景观中的蘑菇 MUSHROOMS IN A MULTI-SPECIES LANDSCAPE
在林间徘徊和对蘑菇的喜爱相映成趣。行走与身体的愉悦和沉思同步,这也是寻找蘑菇的速度。雨后,弥漫在空气中的新鲜臭氧、汁液和落叶的气味让我活跃的感官充满好奇。没有什么比在黑暗而潮湿的场所遇到橙色褶皱的黄蘑菇,或在松软的泥土上看见大牛肝菌更美妙的了。且不说自己是第一个找到它们的人,那色泽、气味和图案带来的兴奋感油然而生。
牛肝菌但我认为,这些快乐中有两种极致的快乐,一种是偶得的馈赠,一种是指引了我接下来的行走路径。这些蘑菇不是我劳动的产物,因为我没有付出辛勤的汗水,没有替它们操心。它们带着未经请求和意料之外的快乐来到我的手掌心。有那么一刻,我厌倦了疲惫的内疚感,就像一个中了彩票的人一样,被生活的甜蜜点燃。
喜悦给人一种印象,一种对“场所”(place)的印象。感官的兴奋使我想起那色泽、气味、光线的角度、刮擦的荆棘、这树坚挺的位置,以及我面前隆起的小山。很多次流连忘返间,我突然想起曾在此处见到的每一个树桩,每一个洞窟。自己曾在此采摘蘑菇的景象映入脑海。我有意识地回溯过去,毕竟找到蘑菇的最好方法就是回到你曾找到过的地方。
菌丝体(mycelium)长成蘑菇,一些蘑菇的菌丝体是特定树木的终身伴侣。如果你想在加利福尼亚中部找到鸡油菌,那么你必须在橡木脚下寻找。但你要找的不只是橡木,你必须寻找与鸡油菌菌丝体共存的橡木。你一看就知道,因为你以前见过鸡油菌。这里你来了足够多次,你了解这里的季节性鲜花和出没的动物。你在风景中找到了一片熟识的场所。熟识的场所是多物种互动的起点。
鸡油菌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觅食的过程都大致如此。为了寻找一种有用的植物、动物或菌类,野外觅食者认识熟悉的场所,并一次次地回来。通过熟知的地点,野外觅食者不仅了解总体上的生态关系,还能了解特定物种及其在特定场所生长的难以准确预估的自然史。熟悉的觅食场所不必独占为领地,人类和其他生物都能认识这些地方。广泛而交叉的地理区域抵制着划分“你”和“我”的普遍模式。
此外,野外觅食者与众多“居民”和“访客”滋养着并非单一生物的景观。熟悉的场所产生了身份认同和友谊,这与我们熟知的过度驯化和私有财产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你在寻找一个共荣的伴侣世界,你可以考虑一下蘑菇。
蘑菇是众所周知的伴侣。“共生”(“symbiosis”)即互惠共生,这一概念是为地衣(由真菌和海藻/蓝藻构成的复合有机体)发明的。非真菌共生伙伴通过光合作用刺激地衣代谢,真菌则使地衣能在极端条件下生存。反复的干湿循环不会破坏地衣,因为真菌共生伙伴可以遇水后立即重组细胞膜,令光合作用得以恢复。地衣可以在冻土带和干燥的沙漠岩石中找到。
叶状地衣对于蘑菇爱好者来说,最能引发好奇的物种陪伴是真菌和植物的根部。在菌根中,菌丝会包住或深入植物的根部。如果没有真菌援助,许多兰花甚至不能发芽。植物从真菌那里获得营养。然而更多时候,真菌从植物中获得营养。
这种菌类叫菌根菌(特定的真菌与特定的植物的根系形成的相互作用的共生联合体),它并非自私地吸收营养。它带来植物露水,并使周围土壤中的矿物质可供宿主使用。真菌甚至可以钻入岩石,使岩石中的矿物元素可用于植物生长。在地球悠远的历史中,真菌富集土壤,使植物进化。树木能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多亏真菌带来了磷、镁、钙。
在我居住的地区,林业工作者给杉树幼苗根系接种乳牛肝菌,以帮助重新造林。同时,许多最受欢迎的烹饪蘑菇大多是菌根菌。在法国,种植松露的农民将树苗接种在有篱笆的土地上。当然了,真菌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这项工作,但要有更开放的地理环境。于是我们蘑菇迷四处游荡,寻找陪伴彼此的树木和蘑菇。
黑松露真菌在物种间关系中并不总是良性的。真菌在碳转化(carbon conversion)习性中具有令人生畏的杂食性。各类真菌依靠活的和死的动植物生存。有些是凶残的病原菌。例如,新型隐球菌杀死了许多艾滋病患者。有些是令人恼火的寄生虫(想想皮癣和脚癣)。有些从宿主的肠子里滑过,静静地在粪便里等待发芽。
一些真菌找到了完全意料之外的基层(substrates)。最初在树脂中发现的芽枝状霉竟出现在飞机燃油里,造成了燃料管道的阻塞。有些真菌在与一个宿主愉快共存的同时,正伤害着另一个宿主。禾谷类秆锈菌与伏牛花灌木结合,用它的花蜜喂养苍蝇,以产生小麦生长时杀死小麦的孢子。
真菌的口味总是矛盾的。真菌有降解木质纤维素和木质素的能力,对保护木制建筑不利,但这也是真菌对森林再生的最大贡献,否则森林里就会堆满枯木,其他生物的营养基础也会越来越少。与此同时,真菌在生态系统升级的过程中扮演着更显著的角色。真菌总是与其他物种为伴,物种间的相互依存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人类的例外主义使我们失望。科学从伟大的一神论宗教中继承了人类主宰的故事。它们一方面指导人类控制自然,另一方面点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而非物种间的相互依存。这种遗产有诸多局限,其中之一是它引导我们把人类物种的实践想象为自动地自我维持,并因此在文化和历史中永恒不变。
人性的观念已经转交到社会保守主义者和社会生物学家手中,他们使用人类的永恒性和自主性假设来为最专制、最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背书。抛开咄咄逼人的遗传学,一种物种间框架为生物和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人性是一种物种间的关系。例如,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与我们人类纠缠在一起的驯化网络。
驯化通常被理解为人类对其它物种的控制。这种关系也可能改变人类,但这种改变通常忽略不计。由于这种二分法源自人类主宰的意识形态承诺,因此它一方面支持驯化控制那令人发指的幻想,另一方面支持野生物种的自我创造。
此外,驯化粗鲁地划分开界线,动物要么在人类的怀抱里,要么在野外。通过这般幻想,家养动物被判处终身监禁,遗传信息被标准化;野生物种“保留”在基因库中,它们的多物种景观却被摧毁。然而,包括人类在内的大多数物种都在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中生存。对这种多样性的关注也许是认识跨物种存在的开端。
真菌是人类状况的晴雨表。几乎没有真菌能被人类驯化,除了少数真——比如用于生产工业酶的真菌,它们的基因组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超市里卖的人工白蘑菇和草地上生长的双孢蘑菇是一回事。
干朽菌(植物干腐病致病菌)一度只在喜马拉雅山脉出现。在对南亚的征服过程中,干朽菌进到了英国海军的船上。19世纪初,英国海军舰艇木结构腐烂被称作“国家灾难”,并引发恐慌,直到19世纪60年代铁甲战舰问世。然而,随着真菌在英国潮湿的地下室和铁道上生根,植物干腐病不断蔓延。在这个例子中,英国的殖民扩张和干腐病的蔓延同步。
人工栽培的白蘑菇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谷物驯化了人类。人类与谷物之间的韵事是人类历史上最浪漫的事之一。一万年前近东地区的人们开始种植小麦和大麦。在这种新的驯化过程中,人们将情感从多物种自然环境转移到一种或两种特定的作物上。
近东地区谷类驯化最奇怪之处在于,即使不辛勤耕作,这个地区也很容易采集到大量野生的小麦和大麦。即便在上世纪60年代,野生谷类也易于觅得。我们提醒自己,在家种植农作物的目的是“便利”和“效率”,这种观点并不属实。几乎在任何地方,种植都需要比野外觅食付出更多劳动。
驯化的原因可能很多(宗教或地方性稀缺),但让谷类种植得以维持和扩张的是社会等级制度的出现和国家的崛起。比起其它存在形式,精耕谷物农业能更好地供养精英阶级。国家把收成的一部分征为公用,并将其制度化。
在整个欧亚大陆,国家和专业化文明的崛起与精耕谷物农业的传播相关。某些地方,国家服从农业;某些地方,农业服从国家。在任何情况下,国家通过象征和军队促进农业发展。有时,他们将其它生存形式定性为犯罪,只有不法分子才会拒绝国家的丰饶。
驯化选出的谷物有更饱满、碳水化合物含量更高的种粒。高碳水化合物饮食使女人生更多孩子。和野外采食者不同,人们突然想要尽可能多的孩子,不仅出于对生育的迷恋,也因家庭需要更多劳动力种植谷类。
14世纪的意大利打谷场国家鼓励长久而稳定的农业生活。国家鼓励以家庭为单位的劳作,并保证家庭资产和遗产的形式。这些形式在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划定了界线。家父(pater familias)是国家在劳作家庭层面的代表,正是他确保了税收,收成的十分之一(“什一税”/“十税一”)会抽成给精英阶层。这种政治格局限制了女人和粮食,并将生育率最大化。
谷类不关心是不是家庭劳动力种植了它们,也没有人类的死亡。并非所有动物都能最大限度地繁衍后代。失控的、非持续的繁衍是人类驯化(人与谷类)的特征。对生育的痴迷反过来限制了女人在育儿之外的能动性和机会。公平地说,这种物种间的亲密关系呼应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的名言:
(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译者注:相关论述参见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8.8恩格斯 / 2003 / 人民出版社随着加紧劳作的农民养活了愈来愈多的人口,他们不断减少农作物种植种类,并不断缩小家庭形态。不过,农作物和人类家庭的标准化尚未完成。无论国家权力在何处衰减,生物多样性和社会多样性景观持续繁荣。
然而,长久禁闭的理想模式本身在维持边缘地带的边缘地位方面一向效果显著。在我对印尼加里曼丹岛轮作耕种者的研究中,一些女人谈到我的财富和特权:
如果我拥有你所拥有的,我永远不会下地干活。对女人的禁闭位于这个美丽的秩序之梦中心。
真菌是单一作物农场和农民的敌人。古代国家鼓励集约农业,因此农作物标准化的压力很大。19世纪以降,科学农业在农作物标准化方面力压早年间的驯化。它使标准化本身成为“现代标准”(“modern standard”)。
今天,只有标准化才能让农民的农作物卖出去。然而,标准化使植物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影响,包括锈病和黑穗病。如果没能开发出抗体,农作物会马上大规模减产。植物寄生菌受惠于大规模粮食作物的出现,它们成了文明和进步的敌人。由于非粮食作物的种植以集约的谷类农业为理想模式,因此这些作物也屈服于各种霉菌和枯萎病。
最著名的真菌灾难要数爱尔兰的马铃薯枯萎病。英国的殖民统治将爱尔兰推向最边缘化的领土。军事袭击烧毁和没收了粮食作物,爱尔兰人只能靠地下的块茎植物存活。18世纪晚期,马铃薯已然成为爱尔兰人的主食。
有政治动机的地主为佃户开垦新土地,小农场增加了。得益于马铃薯,佃户结婚更早,生育的孩子也更多。五十年间,即使经济在殖民统治下摇摆不定,人口也从五百万陡增至八百万,对马铃薯的依赖也加强了。
单一栽培引发恶果。欧洲人仅仅进口了南美洲驯化的几千种马铃薯中的几种。1835年左右,马铃薯晚疫病菌被作为英格兰的地方问题被首度报道。这种真菌慢慢累积,直到1845年阴雨绵绵的夏天,感染遍及爱尔兰的每一株植株和储藏的块茎。此次饥荒导致一百万人饿死,大约两百万人移居美国。
上图:爱尔兰和欧洲人口变化趋势;中图:饥荒过后的都柏林街头(1955年)。下图:都柏林街头的大饥荒纪念雕塑。在这场被爱尔兰人称作“大饥荒”(The Great Famine,1945-1952)的粮食灾难中,约一百万人饿死,另有两百余万人移居北美。随着转基因和克隆技术对农作物的影响越来越大,真菌的警报声也越来越响。我们聪明的开发人员认为,金合欢树种植园可以替代(印尼加里曼丹岛)婆罗洲的热带雨林。克隆单一植物会让它们都容易患上掏空树心的心腐病。为什么有人会想种植它们呢?这是另一个故事,它将我们带入欧洲征服和扩张的历史。
种植园是欧洲扩张的发动机。种植园创造了财富和运作模式,使欧洲人能够接管世界。我们通常听到的是先进的技术和资源,但正是种植园制度使海军、科学和最终的工业化成为可能。种植园是由非所有者运营的种植制度,以扩张为目的。
种植园加深了驯化,重新强化了植物的依赖性并强迫生育。借鉴国家认可的谷物农业,他们把一切投入单一作物的种植中,造成单一作物过剩,但缺一样——他们消除了爱。没有了人类、植物和场所之间的浪漫关系,欧洲殖民者强迫引种栽培。
植物是外来物种。劳动力受迫于奴役、契约和征服。一切只有通过极端的秩序和控制才能繁荣。由于种植园决定了当代农业企业的组织方式,因此我们倾向于将这种约定认可为种植农作物的唯一途径。
想想甘蔗,这个关键的参与者。没有人喜欢种植甘蔗。波多黎各的甘蔗工人“捍卫自己”,与甘蔗“战斗”。然而在17世纪至19世纪之间,甘蔗种植园创造了大量财富,促进了欧洲的征服和发展。甘蔗被移植到温暖地带,重新定义了区位。所有者、经理和劳工随即出现了。奴隶从西非被运送到“新大陆”。来自印度和中国的苦力被送到太平洋。印度地区的农民被征服、被胁迫。
在建立一种针对种植园植物的新对抗中,人类改变了物种的本性。精英阶层巩固了他们对其它物种的自主权。他们是主宰者,不是非人类存在者(定义人类自我创造的“他者”物种)的伴侣。对种植园主来说,必须有人去劳作。
生物学表明了自由的种植园主和被迫的劳动力之间的区别。有色人种种植甘蔗,白人拥有并管理它。没有种族法律或观念能够阻止种族混婚,但他们可以保证只有白人才能继承财产。种族隔离在每一段鳏夫(遗孀)婚姻遗产继承中产生并重复。
被砍伐的甘蔗必须立刻处理掉,以免真菌发酵。大规模甘蔗种植园和它们野蛮的劳动纪律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发酵恐惧的回应。然而,真菌的发酵是对种植者的恩赐。加勒比种植园主并没有注意到蔗糖糖浆(一种糖厂的副产品)适合当地普遍存在的酵母孢子生存,并迅速转化为酒精。朗姆酒诞生了。
致命但有利可图的三角贸易为更多非洲奴隶提供了朗姆酒,增加蔗糖产量的同时,也增加了英格兰或新英格兰酿酒商和金融家的数量。早在糖成为大众消费对象和象征之前,欧洲人的征服地就用真菌发酵酿造的朗姆酒创造出同等可观的价值。
海盗把朗姆酒运送到海岸,以换取非洲黑奴。The Pirates Own Book(1837),Charles Ellms白人女人成为“种族卫生”(“racial hygiene”)的媒介。19世纪晚期,科学卫生和优生学的话语使白人女人的种族隔离弥漫开来。巴氏灭菌理论在热带地区获得检验和推广,在那里,白人控制的空间可以作为实验室,微生物留在了白人家庭的边界上。
到热带地区的白人女性被要求跟丈夫一样保持清洁。再次回到大都会,这种公共和私人卫生指明了阶级的二分法。脆弱的上层阶级女人成了家里的天使,贫穷的女人被认为是感染的罪魁祸首。她们都肩负着新的生育义务。贫穷的家庭需要更多劳动力,尤其在成年人依靠童工生活的地方。享有特权的家庭因其种族优越性,女人必须生出继承人。
家的边界也是爱的边界。鉴于对作为纯洁和相互依赖空间的家庭的盲目迷恋,家庭外部的亲密关系——无论物种内部还是物种之间,似乎都是古老的幻想(社区、小农)或转瞬即逝的事(女性主义、动物权利)。
在家庭之外,经济理性和与之冲突的个人利益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外,这种家庭崇拜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大众文化和我们这个时代中都反复出现,就像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一样,允许它从殖民文化的旧政制中汲取经验。
在这里,爱在家庭之外不被期待。在家庭内部,其它物种可以被接纳。宠物是家庭奉献的典范。但是宠物和爱宠模式没有传播爱,它只在家庭内部保持紧密感。
美国公众会把自己想象成富有同情心、道德高尚的人,因为他们爱自己的孩子和宠物。他们知道这种爱会让他们成为“好人”——不像恐怖分子,他们只会憎恨。他们认为,这种爱让他们替全世界做决定。这种爱创造了一个道德层次,美国的“善”(“goodness”)具有了全球的领导力资格。
对其他人类和其它物种的评判标准是,他们是否有能力达到美国家庭的亲密度。如果他们能适当地与家人相爱,他们就应该活下去。其他人则可能成为“美国改善世界项目”的“附带损害”。消除他们可能是不幸的,但不是“不人道的”。
考虑到这种生物社会计划的力量和普遍性,地球上仍然存在着丰富物种和人口多样性这一事实令人惊讶。但这样的丰富性已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
在帝国的裂隙中采蘑菇 MUSHROOM COLLECTING IN THE SEAMS OF EMPIRE
生物多样性和社会多样性在被忽视的边缘地带防御性地挤在一起。在城市丛林和农村死水里,帝国规划者仍然认为多样性的混杂度过高了。小型农场的生物多样性始终高于大型的、资本密集型的农场,而且不仅体现在农作物方面。土壤真菌和其它微生物也更喜欢小型农场。
什么东西能在矿井的污染物中茁壮成长?许多菌根真菌(从红蜡蘑到能毒死人的彩色豆马勃)都能积累重金属,保护它们的森林伙伴,使植物免受污染。新的放射性真菌已经在切尔诺贝利废墟的反应堆室墙壁上完成了殖民。如果有人决定隔离放射性物质,就需要这样的物种。当然,并非所有物种发展都是良性的,但只有在多样性的环境中,适应才会成为可能。
红蜡蘑然而,大多数地方的多样性和资本投资的强度以及国家控制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对于那些热爱多样性的人来说,也许需要一个脱离国家—资本映射的计划。
我们食用的蘑菇聚集在边缘地带。真菌无处不在,但可食用和可入药的蘑菇只在少数地方生长。许多受人青睐的蘑菇在土地裂缝中繁盛——在田地和森林之间,在耕种区的边缘。大牛肝菌和鸡油菌生长在森林和小径的边缘,即使长在树下,它们也喜光。草甸蘑菇更喜欢草地。与此同时,许多物种大量存在于森林和山脉之中,环抱着密集的农业山谷。
自古以来,蘑菇采集者就在毗邻东南亚的中国西南部、韩国、东欧和欧亚大陆北部的山林地区和森林边缘四处搜寻。在当今北美,来自耕地边缘的移民仍能采蘑菇去卖。同时,全球蘑菇市场将采集工作散布世界各地。日本的美味松茸把采集者带去传统的亚洲边缘,还有太平洋地区,如(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美国西北部和(墨西哥)瓦哈卡的群山边缘。
日本的松茸市场商业蘑菇采集让我们看到全球资本主义的裂隙。除了地方的差异化和产品的特性,知识和资源管理的形式也有很大不同,并且它们与蘑菇商业链的关联是暂时性的。东南亚家庭在俄勒冈州争夺领地。日本的鉴赏家发展出地区性的品味等级制。这里有太多偶然性和变化以供想象一种简单的供求关系。沉浸在这个空间中并不能从资本、阶级和管控的世界解脱出来。这不是寻找乌托邦的地方。然而,注意到裂隙是开端。
在整个帝国受保护的家庭中,人们蜷缩在扶手椅上,带着他们的宠物和零食在电视上观看世界其它地方的毁灭。难以想象有人真愿在这样的家庭梦中生存。
真菌没有一席之地。耐寒的地衣也因空气污染和酸雨而死。从核事故中吸收了放射性物质的真菌把自己喂给驯鹿,驯鹿又反过来把放射性物质喂给牧人。我们可以忽视真菌从核事故中吸收的放射性物质,或者思考它们告诉我们的人类的状况。
屋子外面,就在树林和田野之间,自然的馈赠尚未耗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