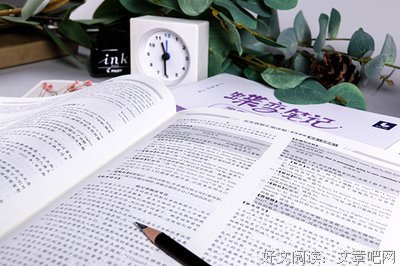
《未来病史》是一本由陈楸帆著作,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80元,页数:3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未来病史》精选点评:
●一种玩弄概念与文字的轻佻感,当然陈老师才气还是挺有的
●奇特
●三星半。还是不错。我发现我现在越来越吹毛求疵了。不仅要内容好看,连装帧排版也要看着舒服,最世在这方面做的确实不错,比企鹅经典都好。
●又是一本硬科幻,让我想到了三体。对于未来科技对人类的影响,这本书是有一些悲观的调调。
●一气呵成的g看得我要下跪 好喜欢作者的语感
●陈老师的作品总有一种偏离常态的非典型性美感。
●感觉作者的小说大部分都是先有一个科幻的概念,然后想办法把这个概念用小说展示出来。也许大部分科幻小说都是如此吧。这个转化过程做得好,小说就好。做得不好,就会显得硬。
●北大中文出身的陈楸帆还是让我对他的技术背景感到惊艳。他在这本科幻集中痴迷地描绘了种种终极的、不可言说的状态与场景,和人细微的情绪。从《开窍》和《猫的灵魂》里,可以看出的的确确的国产科幻逃不开现实沉重的影子,数不清的极权政体、无从选择的灵魂,幻想总应该是飞扬的,可个体总是枉居尘土。
●有几篇挺有趣 有的则故弄玄虚,影响观感
●从情感上看到的是拥有不完整人生的失意主人公们的挣扎与自救,并且强权对人民的意识操控往往成为故事中的对抗力量,极具你国特色。但往深里考究,能发现作者描写的是一幅幅在异化作用下诞生的后人类图景,但比起批判,又更像是展示。另外论及文笔,我想应该是科幻作家中最优美的那一批了
《未来病史》读后感(一):随感
现实介入性极强的科幻,有些都强到露骨了。太露骨于品质有损,小说还是应该观照出某种生活普遍性。“不管所建立的模型简单还是复杂,只要目的不在于揭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机制,而是模拟或解释某一具体的社会现象,特别是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话,其价值是很有限的。”《天使之油》和《开窍》好,《未来病史》太空,对《G代表女神》无感。整本书的结构都是现实主义+轻度科幻的嵌合,科幻只是张皮,引入荒诞和疏离感,或者放大社会不合理,这个思路的极致是《沙嘴之花》,小说内核完全是非科幻的,去掉科幻元素也毫无关系。陈老师的语言还是有限度,在《无尽的告别》里想描写宇宙般博大的融合感,但那几个比喻实在难堪重任。也许这种情感写作应该从诗歌里寻找资源。很喜欢《鼠年》,那种个人在历史洪流前的无力感。个体不再参与命运的编织,沦为了命运显现自身的空空如也的媒介。《动物观察者》也挺喜欢的,然而没了动物性没有欲望我能理解,为什么连情感也没了??小说文风还是有些膈应,幽默感太粗糙了……
《未来病史》读后感(二):想表达的不是病,而是心里的垃圾
前几篇还是挺有意思的,人类变成动物或者人性与动物性融合会变得怎样?大概是这样一种题材。
只是看到中后,大段大段哲学类(对人生,社会,情感)的思考有点芜杂了,从叙事突然转向大篇幅的个人思考,让人觉得很茫然。理解了之后后面的发展也非常跳脱。而且大部分是从男人的角度来描写女人,描写性的内容不少。让人觉得低俗。
有一个短篇是以女孩子的角度来描写的,说是父亲总是送给自己小精灵玩具,貌似那个世界的女孩子正流行收集这个。恕我直言,女孩子喜欢硬质玩具的真的是少数,而且后面父亲疑似变成了猫,过程匪夷所思而且剧情很碎。让我觉得和强调主角是个小女孩似乎毫无关联。里面给予玩家的线索很混乱,读起来就像是作者聊天时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忆和感受一样。
后面几篇让人不知所云。
作者的描写手法让人不太舒服,似乎是科幻背景+乡土题材+男性情感这样的组合。最后出来的作品在未来感中夹杂着对乡土的回忆和抗拒,而且往往搭配一个心中的女神。
直观感受就是西裤高跟鞋配了一件新技能铠甲上衣。头上戴了个狗皮帽子。
想讲的东西太多,可惜没有缕成一条清晰的线路表达出来。作者该做做减法啦。
《未来病史》读后感(三):我们都是棋子
一提起这位来自北大中文专业和编导专业双学位,待过谷歌和百度,现在自己在动作捕捉领域创业的非典型文科生科幻作者,我印象最深刻的依旧是他在09年写的《鼠年》,天知道我多喜欢这个故事。
陈楸帆是非常喜欢打破成规的作者,他从来不复制自己,每一篇文章都有不同的主题,一直在不断突破自我,甚至连文风和遣词造句的语气都会有很大的变化。
在科幻作者中,他是少见的文艺青年出身,因此对文字的把控十分精准。而老王和大刘他们是典型的理工男,技术派硬科幻。别人更注重“科幻”时,陈楸帆注重的是“文学”两个字。这不是说他的文章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软科幻,而是他的文章在文学层面也很有深度。故事中深刻的思考和不断出现的隐喻,使他的文章很少让人能一次看懂。
关于大学生就业形势的绝望,如果让一般人来写,很容易发发牢骚,吐吐槽,最后还是会奋发向上斗志昂扬,写成轻快的大学时光回忆录。但是在陈楸帆笔下,最后的结局格外绝望。原来所谓的天之骄子,北大的毕业生也不过是国家渺小的棋子。
这篇文章特别绝望,它不仅告诉我们天之骄子也没什么了不起,甚至告诉我们人类本身也没什么了不起。被人类操控基因造出的新鼠,也可以发展出宗教崇拜甚至母系氏族。
新鼠可以用幻觉来操纵人类自相残杀,但这并不是本文最绝望的部分。比起这些恐怖的能力,更可怕的是政府早就布好了局,在它们的芯片内写好了自杀程序。一旦和西盟的协议谈妥之后,庞大的鼠群就像森严的军队一样,整齐列队跳入大海。
所以不管是从胆小内向最后变得嗜血杀戮的黑炮,还是呆滞懦弱的最后被同伴杀死的豌豆,以及那个平时凶巴巴但实际上也只是性情中人的教官,还有高冷的班花女同学李小夏,甚至包括故事中没什么性格特征,面目模糊的“我”,都不是故事的重点。
重点是不管我们是什么人,我们都是棋子。大刘说我们都是虫子,但虫子是无法被轻易灭绝的。而陈楸帆其实更绝望,他写在利益集团相互博弈时,个体根本无足轻重。
豌豆被黑炮推下了堤坝,黑炮变成了植物人,教官退了伍当了个拓展训练基地的辅导员,李小夏在外企上班,还打算出国留学。而“我”从一开始的愤世嫉俗,最后接受了自己最开始痛恨的朝九晚五的公务员工作,变得平庸又无能。
多年后我听贾行家在“一席”发表名为《纸工厂》的演讲,听我们河北的骄傲——万能青年旅店的那首《杀死那个石家庄人》里“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云层深处的黑暗啊,淹没心底的景观”这样的歌词时,突然觉得有种感觉似曾相识。
那种感觉,像极了我高中的时候读陈楸帆,他在《鼠年》里写道的:“我们跟新鼠一样,都是这伟大博弈中的一枚小小棋子,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画好铺在眼前的棋盘,我们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按着规定的步法,炮八平五,马二平三,至于这背后的深意,那高悬在头顶的大手何时落下,我们无从知晓。”
《未来病史》读后感(四):The King of the Satellite City of Reality
1 三年
除了《巴鳞》这篇未发表作品、以及收录于上一个选集《薄码》中的《鼠年》和《开窍》以外,本次的短篇集《未来病史》收录的大致是作者2011年底至2015年初掐头掐尾的三年左右时间的发表作品(详情见附录)。
上一个短篇集的18篇作品中有9篇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或展开,而这第二个短篇集的16篇作品中则多达11篇(包括重复的两篇)。一方面,这归究于作者对自身叙事节奏的寻得,另一方面,第一人称视角的作品也确实展现了作者成熟的创作面貌。
由第一人称展开或作结特指《薄码》中的《第七愿望》,以及《未来病史》同名篇章,事实上,这两篇本身即是拼图谜题式的短篇集子,它们就像康德所做的:一种以不同身体机能间的、没有任何现象学能保证的协调为条件的美学;一部通过连续的片段而反复重申的历史,复新或是现代,一番对于日日受到讥笑的人类目的的证明。
至于第三人称视角的作品,包括《薄码》中的《谙蛹》、《双击》、《痛感超人》,以及《未来病史》中的《G代表女神》、《造像者》等作在内,特别是结局的设置——不管是针对世界的历史大事件,还是个人的生死存亡——都隐约透出一种史诗质感。
2 母题
按照作者自己的归纳,他在自己的创作里贯穿着这样的一个母题/主题/意象(参见 知乎http://www.zhihu.com/question/19777452):
异化(Alienation)
- 生物学上的变形、疾病或变异;
- 心理学上的疏离、扭曲、分裂;
- 社会体系/人际结构上的隔离、对立、变迁;
以上表述可见,与韩松的表相如出一辙。不过,韩的作品更为符号化,而陈楸帆有着更为强烈的写实倾向。
现实如果是一座城市的话,那么韩的恶意是在这座现实城中由内至外的蚕蚀;而陈的幻想不见得就是恶意的,甚至还可能更倾向于诗意,且与现实城若即若离。事实上,它本身就是座脱胎现实的卫星城,他本人更是这现实的卫星城之王——其众多作品中隐约所透露的上帝视角的主人。
3 演变
旧的时代,骑士的道具是枪。新的时代,没有人是骑士,而所有人的道具是手机。手机没有杀伤力,却拥有所有揭示的功能。《少女革命》中借由电话传达世界尽头的命运,这是戏剧对现代化道具的一种惊异感运用,而且相当成功,达到的效果就像贞子从电视机钻出来,叫人暗暗吃惊:原来可以这样。《开光》中让世界如鄂谢府般崩溃的APP就是手机中的一个功能应用,实际上小说讲的主题是机器对这个世界的视觉化的感知以及其所洞悉的潜在真相,这一主题似乎算是《造像者》的一次延伸。
陈在这两篇作品中所表达的,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与其说存在与虚无,毋宁说可见的(le visible)与不可见的(l' invisible),并重申这两者并不互相矛盾”,不管是《开光》中开光了的反美图秀APP,还是《造像者》中的结构式超网络信息处理照相机CATNIP——就像维特根斯坦说的,“表达是一个由一架简单机器所完成的、用来输入及输出的粗俗体制”(《哲学评述》)——对于可见者的机器来说,人这个不可见者是“可见性的零度,是可见者的一个维度的开放”(《符号》)。身处其中的不可见者,人这个主体,即使他们在剧中并未察觉到,但舞台之外的我们(读者)却借此出现了另一种考虑现实与历史的方式。
表达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意愿或努力,而取决于一个拥有自身动力和自身链接/意群化(articulations/syntagmations)方式的感官系统。我们所称的表达,也就是说能确定于既定的语言或经过高度加工的文化象征系统(例如文学、科学、绘画或音乐)中的表达,其操作方式是“综合”(syntheses)。这个感官系统或这个“综合”,在《开光》、《造像者》或《犹在镜中》中是机器,借此呈现出某种赛伯朋克气息,但事实上,在陈以往更多的作品中,这个感官系统这个“综合”就单单以更加直接粗暴、更加血肉的“眼睛”来表现,例如《坟》、《深瞳》,或者脑袋中删除的视觉获得(记忆)的《天使之油》、以及获得异族视觉的《无尽的告别》等等。
对于我们读者来说,我们从剧中的机器或眼球获得了相同的发展心智结构的方式,这种生成性(la generalite)表现为:这些作品散播它们的表达方式,而非它们的表达内容;而对于作者来说,从血肉到机器,这是一种新的、开放的历史类型的登场,他将抓住这一类型并以这种方式朝赛伯朋克和属于他的新浪潮事业靠近,而《开光》、《造像者》可视为第一个高潮《荒潮》引发的余波,后面无疑还会有滔天巨浪。
附:
《开光》 首发《离线》 2015/2
《沙嘴之花》 首发《少数派报告》 2012/6
《鼠年》 首发《科幻世界》 2009/5
《动物观察者》 首发《最小说》 2012/5
《愿你在此》 首发《芭莎男士》 2013/5
《G代表女神》 首发《文艺风赏》 2011/12
《犹在镜中》 首发《科幻世界》2012/12
《未来病史》 首发《文艺风赏》 2012
《造像者》 首发《文艺风赏》 2014/5
《万物归其所是》 首发《芭莎男士》 2013/9
《开窍》 首发《天南》 2011/2
《天使之油》 首发《文艺风赏》 2013/11
《过时的人》 首发《科幻世界》 2014/10
《巴鳞》 本小说集《未来病史》首发、同时首发于《人民文学》2015/07
《猫的鬼魂》 首发《魑魅魍魉》 2012/12
《无尽的告别》 首发《科幻世界》 2011/12
《未来病史》读后感(五):灵魂动物园
你去过动物园吗?
去没去过,都没关系。这个动物园,和你记忆中的、想象中的,都不太一样。
这个动物园,时间坐标是开辟鸿蒙到无限未来;空间坐标是微观尽头到星河宇宙。无数现有的、灭绝的、诞生于科学前沿、或只存在于想象疆域的动物,在这里共存。
存在于此的,是这些动物的肉体、也是灵魂。在无尽开放的时间与空间中,二者呈现出种种诡异迷人的映射关系。
包括人类自身。
那么,让我们出发。
展馆一:《巴鳞》。
夏夜、湿热黏稠的风,带着台风前夜的霉锈味。祖屋中央,巴鳞慢慢抬起头来。头颅硕大,极黑的身躯仿佛吸收了一切光线。
异族动物,镜像神经元发达,善于对情感“感同身受”,即“共情”能力超强。强到什么地步?即使被你殴打,也不会逃开,因为不忍看到你失落的神情。就是这样一种生物,被人类残忍地贩卖、实验、殴打、奴役、凌辱……它灵魂的特质,成了肉身的负担。在探讨这二者关系的同时,作者陈楸帆引入了一对人类父子的冲突与隔阂。他们利用巴鳞“肉身模仿”的能力,把它当做情感交流的“沙袋”,将亲情的的操控与反弹宣泄出来。但最终,父子二人还是因为人类自身的拘谨与懦弱,因为缺乏“共情”能力,彼此渐行渐远。
至此,读者开始思索:不管是对待异族,还是对待亲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是否是一个同理心缺失的物种?肉体的模仿能力,和能够“共情”的灵魂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展馆二:《猫的鬼魂》
虚空中,一道白影划开黑暗,两点绿色燃起。
落地无声,猫眼闪动,似能吸入你的灵魂。
未来世界,污水和毒气制造的环境污染,毒死大批动物,只留人类躲在防护罩中苟延残喘。动物的身体在大地上慢慢腐化风干,而灵魂四散而逃,寻找人类肉身作为寄主。经过痛苦的“转生”,被特定动物灵魂挑中的人类,会彻底变成这种动物。
在作者看来,科幻小说的迷人之处,在于其“可以从一个极端真实的语境出发,通过可理解的、逻辑自洽的条件外延及思想实验,将文本中的情节、人物推向一个极端超现实的境地,从而带来一种惊异感(Sense of Wonder)及陌生化(Estrange)效果。”本文的出发点,就是一个极度真实普通的三口之家, 作者通过对人类现实生活的方式(恣意污染环境),做出符合逻辑的推理(生态崩溃、动物死亡),利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人类可以变为动物),在极端的语境下(灵魂寻求转生的痛苦过程),十分“科幻”地表达了自己的忧思和警戒。
此外,作者有意选择了孩子的视角进行叙述。有几种好处:用幼稚感隐藏信息、用局限感精炼结构,用天真感衬托残酷。角度巧妙,技法纯熟。
展馆三:《鼠年》
一棵树,根部垒着许多石头,形状和颜色显示出一种 “精心挑选”的美感。树上,挂着18 只雄性“新鼠”的尸体。树下,一群“新鼠”正在祭祀,身形个个有成年人大小。
最高大的一只“新鼠”突然转过头来,露出带血的尖牙。它眼中闪动的,分明是智慧生命才有的光彩。
基因改造失控,鼠类进化成灾。学生就业紧张,组成灭鼠部队。这篇小说开篇就构建起一种滑稽、反讽的语境,并将人类与鼠族放在了极端对立的冲突两端——生杀战场,你死我亡。通过战争,作者描述了人类与进化的“新鼠族”的战斗,更探究着人类与自身灵魂的角力。一群象牙塔中的青涩的少年,忍受着肉体的伤痛、饥寒,更面对者心灵的恐惧、冲突。这些少年中,有胆怯善良,对鼠族心怀悲悯的“豌豆”,也有人嗜血如狂,对同伴痛下杀手的“黑炮”。战场的冷雨中,有惧怕死亡的泪水,也有残酷非人的笑容。
人类扪心自问:自己是否有资格站在生物链的顶端,以“上帝之手”,控制基因进化的过程?任意屠“修剪”所谓的“进化错误”?已经拥有了智慧的生命个体,是否还应被当做“畜生”一样任意屠杀?在新鼠的毛皮下,的确存在着某种智能、情感、道德,乃至于——“灵魂”?
在此过程中,人类自身又将承受何等生命之重?
修罗场上,人鼠殊途同归。
展馆四:后人类·异化
这是一片开阔的空间,弥漫着来自未来的灰色尘埃,一如电影《寂静岭》的结尾。
作为动物的一种,形态各异的后人类(经过技术加工或电子化、信息化作用形成的人),以半机械的形态,半狼的形态,生瘤的形态,多足的形态……赤身裸体,穿梭其间。
从宇宙的时间尺度来看,人类的进化史可谓十分短暂。在如此短暂的进化史中,科技发展和环境变化,会让人类的“历史陌生感”急剧增大。未来的“进化”,在当今人类的眼中,也许就是一种病症。《未来病史》一文中,提到IPAD症候群(只能依赖IPAD与外界交流)、拟病态美学(病态与畸形成为流行之美)、新月之变(第二个月亮引发的人类返祖现象)、可控精分(多重人格失调症)等多种病症,分别从科技、审美、环境、心理等角度,对“未来病症”进行了想象。
这些“进化”的过程,往往也是“异化”的过程。
作者认为,“异化”是自己作品的母题之一,包括“生物学上的变形、疾病或变异”、 “心理学上的疏离、扭曲、分裂”、“社会体系、人际结构上的隔离、对立、变迁”。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的深入发展,“后人类的进化”势必成为一项日常议题。在后人类社会中,血缘将如何定义?优秀基因能否任意复制?克隆可否达成永生?
后人类的进化,在改变肉体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灵魂和社会规则。
作为本书收尾,《无尽的告别》以主人公第一视角,细腻描绘了人类的意识与一个海底文明的智慧个体意识融合的感受。
“那是我此生最为诡异的体验,令人疯狂而眩晕。仿佛共有一颗大脑的连体婴,我感受到对方的温度、纹理和震颤,但同时也感受到来自自身的肌体刺激,我触摸着它触摸着我,我包容它又包容我,像是一个置于音箱前的麦克风,回输信号被无限循环放大,推向神经冲动的极限。”
对人类与异族肉体、灵魂之间纠缠的描绘,鲜辣生动,将科幻小说中的“陌生化”推向了极致。“宏细节”的运用,充斥着黄金时代的硬科幻的气魄和野心。据悉,本文已改编成电影剧本,令人期待。
地球,只是浩渺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动物,也只是地球生灵调色板中的一格。在历史与未来、疾病与进化的尺度上,本书探讨了肉体与灵魂关系的几种可能性。无法面面俱到,但足见一沙一世界。
至此,灯光亮起,万籁俱寂,肉体低俯,灵魂升起。
在文明的舞台上,在虚空的动物园中,一场肉体与灵魂舞蹈终于落幕。
最后,我的目光停留在书的某处。
灯灭了,一片漆黑。我闭上眼睛,到处都飘浮着五颜六色的光点,像是一整个动物园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