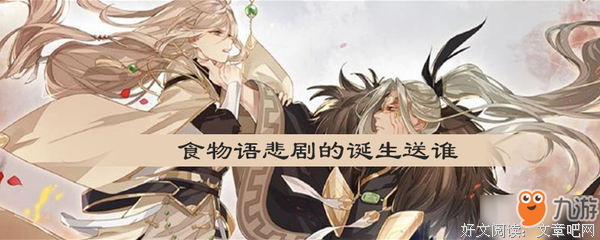
《悲剧的诞生》是一本由{德]弗雷德里希·尼采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38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悲剧的诞生》精选点评:
●周译悲剧的诞生,文笔还是好的,算是常读常新吧。
●啃了一半,啃不下来 abandon.
●4.5 尼采文風真是華麗也具很強的煽動性,關於瓦格納一切慷慨的褒揚到了最後轉折成一種強勢的清算,真是很精彩。其實尼采描述的很多現象都與現在我們所處所經歷的時代感受無二,記得讀到「溺水」那段浮起時背上起了一層汗。他關於藝術家真正的創造評價非常精狠,迷信所謂靈光一閃和天才的人都忽略了背後精確深刻的選擇。
●仅读了《悲剧的诞生》和《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两篇,其余未读。《悲剧的诞生》其实完全基于叔本华的哲学体系之上,在读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之后阅读实在是恰到好处。自己本来对周国平有成见,但这本书译的很顺,豆瓣评分8.1低了。
●看了一年才看完
●尼采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艺术家是生命力丰盈,要给予世界。希腊悲剧的酒神精神,是酒神戴了面具幻化出无数自我嬉戏,在一切生命的变化、毁灭与生成中,意志是永恒的。
●尼采的美学观点:对于生命意志强力的推崇。酒神的激情,摒弃形式主义,强调生命的自然强力。大致理解。
●美妙,艺术家自查手册。
●封面设计得也忒丑,剥开包皮,译者手迹跃入眼帘,嘴角一阵抽搐,以为买到本初二女生批读过的二手书。 古希腊神话比较熟悉,但悲剧了解得不多,歌剧更是从未接触,勉强领悟大意。看到尼采对自苏格拉底延续至今的理性主义哲学与科学精神的批判,念及自身于哲学思辨形式——概念逻辑推理的不擅、反感和恐惧,坚持选择哲学学术之路合不合适,考研哲学与否,不禁迷惘了。
●日神酒神的理论读得如痴如醉,尼采是个充满激情、文笔优美的散文家。除了美学,书中所表述的审美的人生态度也令人感动。尼采明明赞同人生无意义,却又因为热爱艺术而显得这么积极。他甚至认为真理是丑的,“一个人意识到他一度瞥见的真理,他就处处只看见存在的荒谬可怕。”能给人救赎的只有艺术。“只有作为审美现象,生存和世界才是有充分理由的。”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一):《悲剧的诞生》几点有意思的地方
只看了《悲剧的诞生》部分,算是还可以的一部尼采著作,记录几点有趣的观点和现象:1.尼采对“雅利安人”的误用与对“闪米特人”概念的正确使用与Hitler高度一致,有可能认为Hitler从尼采中学到了点什么;2.苏格拉底是不理解因而也不尊重(理解然后美)旧悲剧的第二个观众,审美苏格拉底主义是对酒神精神的谋杀。3.苏格拉底乃是后世对将把具备最好知识能力、为科学效劳的理论家视为理想这一行为范式的原型和始祖,这把整个现代世界困在亚历山大里亚文化的网中。4.康德揭示了范畴的作用如何仅仅在于把纯粹的现象,即摩耶的作品提高为唯一和最高的实在,以之取代物自体的本质。5.尼采固执地认为,歌剧诞生之时就将歌词与和声的关系类比于灵魂之于肉体,是一种对音乐外行的粗野之见——音乐之审美不应转化为任何具体形象,而应当是纯粹形而上的审美。6.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其健康的天然创造力,唯有用一种神话调整的视野,才把全部文化运动规束为统一体。 这个译本的语言还是比较流畅的,这对于翻译尼采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人名翻译不完全按照现有中译名,比如Wotan翻成浮旦,但是因为有注解,也可以从上下文贯通,因此不太影响阅读。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二):艺术、艺术家与形式
似乎评价一位建筑师形式感很强是一中褒中带贬的表达方式,潜在的含义是这位建筑师功能平面功夫不强,哲学探讨意义不强,社会问题欠缺考虑,建筑余下的就仅仅是一具好看的皮囊。然而形式本身作为建筑最最基础和根本的表意手段在现代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席卷下变得孱弱而遭人鄙夷。现代以来对形式的考虑缺席,似乎从另一方面解释了依赖形式取胜的网红流量建筑在当下语境中对建筑带来的冲击。
形式无罪。美是一种追求,是一种虚无缥缈却又实在可感的东西。就像艺术其实并不存在,存在的仅仅是艺术家。人→劳作→美。这样的一个关系生产链从古至今伴随着工艺科技的发展并未改变。纵使观念艺术或者功能艺术如何解构当下,在岁月的沉淀中我们能够看出谁是跳梁小丑,谁是缄默的拾贝者。
关于形式美本身被尼采定义为日神的幻觉,这种幻觉与酒神的醉意阑珊并列,并无高下之分。他赞赏音乐那种本质上的通神,以及共鸣所达到的“醉意”。他也赞赏诗歌亦或绘画所编织的无边梦境。当宗教救赎被启蒙砸得七零八碎时,人如何去获取一种支撑生命的崇高感?崇高的获取途径变得狭窄而凌乱,我依稀辨认出这种灵魂的震颤可以借由信仰、共同体和美三种方式获得。第一个正在日渐衰弱,第二个在上个世纪开启了两个战争,而第三个在当今世界正扮演着越来越迷离的角色。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艺术拯救人生”所代表的尼采美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当下的思维逻辑。我们尊敬艺术家,认为其同远古时代的巫师一般通神而至灵,他们有个性而放荡不羁,他们尊贵而藐视一切资本法则。建筑师也总想拼命向外拓展边界,在庞杂而精巧的哲思大厦上试图守住学科存在的意义。
有时候风格走得太远时回到起源总能发现一些亘古不变的精神。回到形式所赋予的“美”。敬重“美”这个词吧,昔日维特鲁威所述建筑应当具备“坚固、适用、美观”,这里的“美观”指delight——愉悦。可以看到三个词汇再一次回到了人自身,而后者“愉悦”将艺术赋予给了建筑,“形式”二字在这种匠人式的朴素价值情感中带我们回归到建筑营造最开始的地方。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三):在日神与酒神的对抗间
作为一切艺术的根源,尼采选择古希腊文化为起点,以日神与酒神为象征,描绘了两种原初的冲动。
//关于两种冲动
酒神冲动:酒神代表着“醉态”,即放弃对世界的主观态度,融于世界的客观意志中。代表的艺术形式为音乐——自然绝对意志的体现。
日神冲动:与酒神冲动相反,日神冲动代表着绝对的个体化原则,把“目光”聚焦在具象化的事物中,以具象化为最高原则。代表艺术形式为史诗与雕塑。
//关于悲剧的诞生
在尼采的观点中,悲剧是歌队艺术的派生物。歌队,即古希腊的合唱队,最初是作为讲观众与外部世界隔开,从而投入绝对的酒神状态的狂醉之中的屏障。直接产物悲剧,则是日神冲动在其中作祟的结果——自然的悲剧性绝对意志以悲剧英雄即日神的具体形式出现在舞台上,作为悲剧的载体出现。
“酒神说着日神的语言,而日神最终说起酒神的语言来。这样一来,悲剧以及一般来说艺术的最高目的就达到了。”p172
//关于悲剧的没落
悲剧的没落,从以苏格拉底为首的理性派兴起开始。苏格拉底所持有的,是晚期的“希腊式乐观”,即认为一切都能以理性认识,逻辑推理能直达存在深处。这样的乐天精神,与埃斯库罗斯与阿里斯托芬一起,以喜剧的兴盛宣告了悲剧的没落。
后世,在日神观念的主宰下,音乐不再作为一切艺术的本源出现,而被视为“对形象的拙劣模仿”。至此,歌剧兴起。
尼采引用席勒:“自然和理想,或者是哀伤的对象,倘若前者被描述为已经失去的,后者被描述为尚未达到的;或者是快乐的对象。”在歌剧中,两者皆无,有的只是对世界中短暂现象的赞颂,在理性的乐观精神的指导下对现象的幻影大唱赞歌。
“这种假想的现实无非是幻想的无谓游戏,若能以真实自然的可怕严肃来衡量,以原始人类的本来面目来比较,谁都必定厌恶地喊道:滚开吧,幻影!”
//关于审美的冲动
对于审美,尼采批判的主要是以道德角度进行艺术评述的批评家。对于尼采,真正的审美过程,应当剔除道德的成分。艺术如悲剧之美在于个体在情境中的消融,于最终自然毁灭的不可抗拒感,而非传统道德意义上的“悲”之美。
//关于人生态度
尼采主要批判的,除理性的乐观主义外,就是理性的虚无主义。
“他们彻悟了,他们厌弃行动;由于他们的行动丝毫改变不了事物的永恒本质,他们就觉得,指望他们来重整分崩离析的世界,乃是可笑或可耻的。知识扼杀了行动,行动离不开幻想的蒙蔽——这才是哈姆雷特的教训。”
理性直达虚无主义,到是否世界就此终结?尼采倾向于认为,理性始终是有限的,在理性的桎梏外,有的是更广大的无法言说的世界。面对它的方法,只有诉诸艺术。
——————————————————
早期尼采的美学与哲学理论,是如此充满朝气,令人瞩目的更是他在论述间洋溢的文采。或许尼采终生都将酒神冲动与自身密不可分的结合在一起,于酣畅与迷狂之中,俯视这个笼罩着尼采意志的世界。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四):无标题工厂碎石
现代悲剧底命运:只能成为被监视者,哪里有悲剧,哪里就有救火队员。 笑的垄断:在哪里被逗笑了,无论是被尼采还是朋友逗笑,这种笑都是一种夸张,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表情再也不能表达什么,尤其在高考工厂与资本秩序结合碾压一切之后。 骂与幽默:骂只是一种扁平化的可能被取消的姿态,因为它是否定的肯定,高难度动作设计门槛的精致,还是会被现代人拆招。而幽默是隐蔽的,尤其有一种惨兮兮的幽默,把这种痛苦(特别是这痛苦可以上升到面对民族、文化和语言时)当幽默是中国人的特点之一。 中国是从来没有神话的,留下来的是一个信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宁可把这种中心化理解为一种悲剧文化的自傲,一切由血凝结,由血打造,这是唯一的通货,流血太多的就拿来铺路(我由此理解了语言和后发情态史官文明的起源),但“我们”并不能知道这条路通往何方。 如果我把中国理解为一个塔尔塔洛斯地狱,而西方打开中国国门的事件是苏格拉底—亚历山大文化自取灭亡的结果,那么,我就打造出了一个危险的模型——因为这种表象监察机制竟然被冠以一个使命了,看来我们都被古人设计了。因为中国人的乐观精神里面有一个危险的核心:就算大地崩塌,天空塌陷,人间仍然是有情的。这就像渴望在末世寻找到一位女朋友一样,(也许实际上有许多中国人渴望天下大乱?)。 如何理解我们文化里的“恐惧”和人生的“不追问”? 面对这本书,我只能很沉默。但我又觉得,不写些什么,对不起2019年的雨季。从前是,喜欢在梦里面寻找着踪迹,现在呢,我已经归还了一切,那也就无所畏惧了。 这本书写了许许多多根源性的问题,但是是表现为音乐。有谁听见了这音乐,谁就不能再沉默了。无论丑陋,还是美丽,都要来唱下歌,现代人的极力掩饰已经使我疲惫不堪了,看他们始终得不到什么,他们全部只是一句话:表象即实质。 我终于明白什么叫“灼人”,尼采的书是属于这样一种书,不可能安静地读完,必须要有行动,才可能有信心继续读下去。当然现代人是对什么都“视而不见”,他们在这里又有一句话“该有的都会有的”仿佛悲剧和天才可能会凭空发生一样。 我只读了一半,在这个下午,怀着那一如既往的恐惧:仿佛自己做错了些什么,仿佛自己正在做不应该做的事。有一种本能叫回避,这在悲剧现象中是“从连续巨大的放纵转入巨大的惊骇”。在中国人表现为“对放纵的恐惧”,秉持中庸的需要。在中国人的梦中都是些什么东西呢?完全没有故乡,是对现实的杂乱无章的回应。他们这里又有一句话“生命是好的,生命完全是新的源泉。”的确,人生早期的感觉较相近于古代,但并不完全“生命就是好”。 中国文化是这样的漩涡:它引导人跳悲剧的舞谁成功了,就拿来扩张中心地域的荣耀。是的,心灵力量与国力同步增长,圣人在底层举起一切,千年的设计。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挺可怜的,从前悲剧还可以大胆生存于中国,现在,连这种现象级别的崩溃都抹杀了,中文的记录能力和捕杀能力由此可见一斑。尤其是,我读了这书后,心情沉重,刚开始是快乐得整夜读,到后来心情沉重了,连同对瓦格纳的预感的悲伤,使我不得不停下来整理我自己的梦和希望,这个时候,尼采的格言就起到了缓冲的作用。以上自言自语针对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