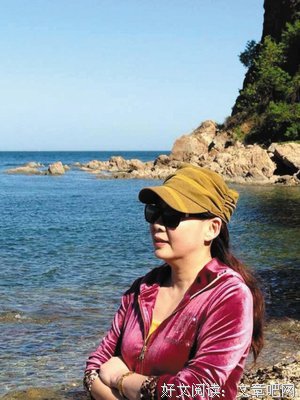
《全民发呆的澳洲》是一本由[美]比尔·布莱森著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2019-8,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全民发呆的澳洲》精选点评:
●原住民永远最惨
●有趣,澳大利亚真是让人很好奇,但看了本书又不想真的去的地方。
●比尔克莱森哈哈
●慢慢来
●2019年第86本。
●原名为In the Sunburned Country,封面和译名赢了。简介说作者比尔·布莱森作品入选《卫报》“生命中不可或缺的100本书”书单,与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比肩而列。我猜入选那个书单的应该是他的《万物简史》可能性更大吧。出来混……真得多学学读客的文案。
●亲切!
●Bill Bryson 的游记很有名,这是翻过的第二本,依然看不进去。
《全民发呆的澳洲》读后感(一):评比尔·布莱森《全民发呆的澳洲》|旅行的王道:来都来了
《全民发呆的澳洲》是比尔·布莱森游记系列之一,原名为In a Sunburned Country,写作于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澳大利亚未开发的广袤土地,即使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也并无太大改变,时间的雕刻对于这里似乎特别宽容——澳大利亚人迹罕至的地方太大,探索这里太需要专业团队和时间。
书中让人感兴趣的,除了有关澳大利亚动植物的“趣闻”——认识了Banksia班克斯亚木花,“这花看上去极其惊悚地像马桶刷”; 但如果被鳄鱼盯上后瞬间在世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被水母蛰后痛不欲生、被野狗追到攀墙闯入民宅等等算是有趣的话——恐怕就属各种通往荒漠地带的“在路上”部分了。前往一个目的地,动辄就需驾车几天枯燥地穿梭在渺无人烟的公路上,大概心里都会期望能遇上什么有趣的事。在眼前渐渐铺开的荒漠景色,也许一开始也会有点儿“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孤独和开阔感。但在持续炽热的围攻之下,一杯冰凉的啤酒就是作者最大的慰藉了。这就难怪每到一处歇脚地,布莱森第一个念想和寻找的就是酒吧,毕竟来都来了。
澳大利亚开发和未开发地带的差别实在太大,身在其中,让人感觉仿佛一时间穿越了时空。前一处还是在安逸舒适的现代文明,下一处便到了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饮血大概还是夸张了些,不过在荒漠缺水状态下饮尿还是很有机会的。当地新闻里有关消失的探险者的报道并不会阻挡新一批的探险者。不过,对于大多数旅行者而言,也许更有可能是对澳大利亚危险的考察不足;毕竟很少有人会想到吃条鱼也有可能中毒吧——鱼肉毒,一种热带水域的毒素,聚集在某种鱼里。“症状包括,但可能远远不止,呕吐,肌肉严重萎缩,失去运动控制力,嘴唇异常,全身疲软,肌肉痛,诡异的感觉错乱——也就是,热的感觉冷,冷的感觉热。大约12%的病例会死亡”。
在澳大利亚,远离了城市的部分,是严苛而丰富的。极端环境的苛求,兀自孕育出了复杂又多样的生命。而人类的加入,是会增加多样性,还是毁灭呢?从每年濒危甚至灭绝的物种数量能窥到点蛛丝马迹。人类有时候大概还是应该试着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
《全民发呆的澳洲》读后感(二):《全民发呆的澳洲》:澳大利亚不止有袋鼠
“我前几天去了澳大利亚……”
“哦?真的吗?在路上真的能看到袋鼠?”
似乎每一个去过澳大利亚的人都会被问到有没有见到袋鼠?这也是澳大利亚被许多人戏称为袋鼠国的原因。
类型写作没有固定的范式,而游记写作更是如此。监管已经有形形色色的关于澳大利亚的游记存在,但比尔·布莱森关于澳洲的描写依旧可以在此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对于现代的旅行者来说,风景与美食往往是出现在游记中频率最高的描写,每一个地域不同的风景、人文带来的不同体验是吸引旅行者们前往的原因,非常态的生活与吃食亦让人心驰神往。
然而旅行者们在享受异国他乡生活的同时往往不想废心去钻研这里的过去,往往会错过颇多精彩的故事。
比尔·布莱森从踏足澳大利亚大陆那一瞬间开始的描写就足以让你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他没有单一地描写某一处风景、某一种美食而是将澳大利亚看做一个庞大的整体,从过去的历史,由远及近,就像他慢慢靠近澳洲中心的旅程那样,代入感十足。
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是如何来到的?这里过去是怎样一片无人区?现代的澳洲人生活是怎样的?他的文字有着如同纪录片一般的镜头感,带领读者去探索澳大利亚每一处不为人知的有趣日常。
比尔作为一个在英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美国人,既有开朗风趣的美式调侃,又有一针见血的英式嘲讽,为这场旅行带来了双重的“味蕾冲击”。
他天生的幽默感好像就是为写作而生的,尤其当到达澳大利亚这个充满乐天派的国度,这一点便更是被无限放大。
鳄鱼、夺命水母、剧毒蜘蛛,那些普通人避之不及的生物在澳大利亚人眼里好像如猫狗一般普通,可能是生物多样性达到了极高程度的原因,澳大利亚人与益虫与害虫相处地都十分融洽。而这些生物好像也遵循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法则,很少主动袭击人类。
既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洲,还几乎是一个半球。世界赋予澳大利亚的多重意义那里的人好像并不在乎,他们对于一切事情的乐观好像让人觉得在那里真的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生活在几乎可以称为半个地球的地方的。
m/,C�'7�
《全民发呆的澳洲》读后感(三):发呆也是一种气质
南半球有两块和其他大陆没有任何联系的大洲,遗世孤立地漂在广阔的大洋上。一块是南极,一块就是澳大利亚。
提起澳大利亚,除了想起考拉、袋鼠,更多人还会马上想起悉尼歌剧院在海边独特的姿态。不过估计很少人知道,最初来到这片大陆的欧洲人,比他们最初踏上美洲大陆的那批祖先要凄惨得多。
比尔.布莱森的《全民发呆的澳大利亚》中,最初这群踏上澳大利亚大陆的人,就像这片大陆一样孤独。面对这块自然环境比美洲恶劣一百倍的土地,更要命的是,这片大陆非常贫瘠,他们被迫上演了很久很大规模的荒岛求生。他们在这里见到的80%的生物都是地球其他大陆没有的,他们还发现这块大陆上90%的土地都不适合人类生存。最初到达这里的殖民者和地球上其他殖民者一样勇于冒险,拥有一样的征服新土地的强烈欲望。但是200多年后的今天,澳大利亚80%的人口和城市,仍然蜷缩在5%的大陆面积上。这可以全面说明这块大陆有多倔强,特别是澳大利亚的内陆,经过几百年,仍然在抵抗人类的改变。虽然澳大利亚的自然生态系统极度脆弱,但是比起地球上其他被人类到访后就面目全非的岛屿,这里的倔强足够激起我们的敬佩了。
布莱森横穿了澳大利亚的大陆,他在书里用他一贯的风趣和夸张,给我们描述了这一段充满了荒蛮和危险的旅途。内陆的各色小镇,有的只居住几十人,有的只能收看到3个电视台还是近几年才开通的。这些小镇也在努力展示澳大利亚的与众不同,几年间反复爆发洪水的宁根镇和五年滴水未下的科八镇,不过相隔了八英里。仿佛就是两块上帝的实验田。
还有一件事,让布莱恩趁机在书里普及了不少澳大利亚的历史,就是那些用人名来命名的地名。最常见的名称是麦考利,它来自把这块大陆命名为“澳大利亚”的一位总督,他叫麦考利。澳大利亚历史里留下姓名的人也同样热衷把自己的姓名留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姓名有时是一个小镇,有时是一条公路,有时是一栋大楼,有时甚至是一片海滩。作为澳大利亚的游客,必须对各种地名异常敏感。否则,假如你在阿特来德没有看清你驶上的那条高速公路到底叫斯特尔特还是斯图尔特,那么走错路的代价可能长达3994公里。
最后读者终于艰难地随着布莱森离开内陆,开始环游澳大利亚的文明城市时,还是无法轻易松一口气。他用各种方式提醒我们,澳大利亚遍地都是致命的生物,水里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难怪这里的人要“全民发呆”,否则真的无法想象他们怎么面对生活。
当然,布莱森不是只会逗笑和小题大做,他除了描绘澳大利亚的地理、生物、历史、经济……之外,还认真地提起了澳大利亚政治的独特气质。这种独特气质首先体现在首都堪培拉。是的,澳大利亚的首都不是墨尔本不是悉尼,是一个只有30多万人口的,被大面积的植被和湖泊环绕的城市——堪培拉。虽然一个国家的首都不见得必须是这个国家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但是像堪培拉这样远离国内主要高速公路和铁路的首都,也是匪夷所思。布莱森当然也体验了这份独特,他的描写让读者跟他一样对这个首都抓狂。
不只是外国人抓狂,澳大利亚自己的领导人也一样。曾经有一位澳大利亚总理,上任后就拒绝住在堪培拉。他在悉尼居住,只有工作极其需要的时候,才前往堪培拉。澳大利亚的历任总理其实大部分存在感都不太高,因为总理人选更迭得太频繁了。能为人记住姓名的总理中,那位消失在海水中的必须在列。他的离世方式给这个国家增加了悲怆和神秘。比起那些频繁更迭甚至直接消失的前任们,现任总理莫里森算是名声远扬的一位。他一直完美地蹭着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热搜。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跟一位中国插画家较劲之后,他在中国的知名度相当高。
有人不喜欢布莱森的这本书,说中文译得糟糕。其实翻开它会发现,布莱森对澳大利亚独特的风景,有独特的描写,而且是非常舒适的风景描写。那些文字很适合国内小学生摘抄进好词好句本。比如“酷热难当,荒漠像洪水,从四面八方困住了小镇。”这些生动的文字,至少比某些苦大仇深的儿童文学作品里的好词好句灵气多了,不知该夸奖作者还是夸奖译者。
如果没有去过澳大利亚的人,可能会说布莱森油嘴滑舌、喋喋不休、夸大其词。这正是他的文字风格,毕竟,任何读者都不会指望一本游记可以拯救失眠。
《全民发呆的澳洲》读后感(四):《全民发呆的澳洲》——看完第一章就不敢去澳洲了
如果不是太想引人瞩目,个人建议你千万不要在咖啡馆等人群中阅读《全民发呆的澳洲》,否则你捧着一本书独自傻乐的景象定会招来许多质疑你精神正常指数的目光。
在比尔.布莱森笔下,澳大利亚拥有全世界最毒的蛇,最致命的蜘蛛,最诡异的箱型水母。连海边偶然拾得的鸡心螺,里面也可能藏着某种小东西,有足够的能量成为你的绝命毒师。如果你有幸逃过了一劫,还有鲨鱼和鳄鱼,热死人的内陆沙漠以及会让人莫名失踪的海滩离岸流。如果这些还不够,那么,还有随时会爆发的森林大火,绵延数月。总之,身在澳大利亚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人们会对活着本身充满感激。
正如布莱森在墨尔本的朋友豪所言,“当知道一切都可能消失在一缕烟里,你绝对会感激这一切。”
比尔.布莱森是当今英语世界非常多产又“最能逗乐”的作家之一。作为在英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美国人,他的文章兼具美国式“搞笑幽默”与英式“睿智幽默”。《泰晤士报》评价布莱森是“目前活在世上的最有趣的旅游文学作家”。
写这本书是因为《星期天伦顿邮报》计划做一期澳大利亚特刊,于是布莱森“拿着别人的钱”开始了这趟愉快的澳洲之旅。他和邮报派来的英国青年摄影师乘坐世界第二长铁路——印度-太平洋铁路,从悉尼前往珀斯,感受了澳大利亚广袤,炙热而荒芜的内陆。之后他又先后两次独自驾车从悉尼到阿德莱德,再到墨尔本,经历了聚集着澳大利亚85%人口的文明地区。最后一趟从大堡礁到大西北的达尔文,期间穿越了西部的沙漠。
布莱森的行程计划通常只有一个大致框架。每到一个落脚点,他酷爱的事情便是坐在某个小酒馆,拿着一份当地的报纸或与澳大利亚有关的政治历史读物,喝着冰凉的啤酒或咖啡,即兴规划着接下来的行程。他对阅读当地的报纸和八卦有种浓厚的兴趣,“发现一个国家的纷纷扰扰和自己毫无干系,这是多大的惬意啊。”
布莱森对澳大利亚总体是喜欢和推崇的。除了开篇所提的“惊吓”,这里更是处处充满惊喜:一大片藏着古老生命形式的海滩;科学家翻山越岭半个世纪,只为寻找一群在地球上生活了一亿年之久的巨响蚁;荒漠大得足以让极端宗教分子偷偷摸摸的排放了第一颗非政府性质的原子弹,四年后才被发现;而这里的生物,仿佛都误读了进化指南,“它们中最有特点的那种生物,不漫步不奔跑,却像落下的皮球一样蹦蹦跳跳的掠过大地”。
一路上闯进他视野的人有层叠岩偶遇的“灰发游牧者”(提前退休开着房车四处溜达的人),有火车上邂逅的认为原住民“每个人都该被绞死”的退休教师,还有因为“很难放弃这些日落”而决定定居在一个只有80常住人口的小镇的汽车旅店老板。他对这些偶遇的人保持着适度的好奇和观察,却不试图因为要获得某种故事性而跨越某种距离。
作者基于自己的行程适度而有趣的穿插了澳大利亚的历史政治事件。从欧洲探险家17世纪随机而不知名的探访,到1770年詹姆斯.库克船长偶然而伟大的发现之旅,再到1787年大不列颠政府决定将他们的囚犯流放至这个当时被随意的称为新威尔士的地方…从与原住民印第安人的爱恨纠葛,到可耻的“白澳政策”,再到开放平等包容自信的现代国家…
布莱恩在其表面的插科打诨和幽默搞笑中处处流露出一种公平正义和人文情怀。除了对原住民的关注,在谈及1861年羔羊洲淘金热中那场白人对中国人的打砸抢掠事件时,他言辞中也包含着某种隐忍和节制的正义。他甚至因此而将曼宁.克拉克标注为他最不喜欢的历史作家,原因是曼宁记载了此次事件中1名欧洲矿工被杀,却没有记录中国人的死伤以及他们的去处。
对澳大利亚人喜欢不紧不慢的板球,布莱森深感诧异。“到了比赛结束的时候,秋天已经蹑手蹑脚的来了,你从图书馆借的书也全部过期了。那就是板球了。”他印象中的澳大利亚人应该是更热衷于在海滩上或者任何一个地方卷起袖子展示肌肉,而非打着运动的幌子,穿着一身洁白的运动服慢吞吞的在球场上喝着英式早茶。
因为书籍出版的时间是2000年,受《悉尼晨报》的邀请,布莱森再度“花别人的钱”去悉尼观看奥运会,作业是一篇观后感。这篇观后感后来也发表在《泰晤士报》和《多伦多环球邮报》。作为全书的附录,阅读这一部分也是一段极其愉快的里程。布莱森那颗善于讥评谩议的心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舒展,不过讥评的不是澳大利亚,而是借悉尼的周到筹备吐槽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各种疏忽。
相比起澳大利亚人的小心谨慎以及事前“自寻烦恼”,“碰到像奥运会这样的大事,美国的做法是:自认为不会出任何问题,一出乱子就傻眼,然后马上一口赖掉。就这样,美国人民愣是把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闹剧倍出——变成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一次伟大的胜利以及所有后续奥运会的榜样。”而对于美国记者有失公允的报道,他的反击更是绝不口软:这些美国记者认为澳大利亚的“咖啡太浓”,“三明治太薄”,美国人的确少见多怪,“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可有些鸟偏偏找不着林子”。
总之全书幽默风趣又简单朴素,虽然穿插了许多历史和政治事件片段,但读起来轻松愉悦。不过也不乏一些小缺点,有些描述有点事无巨细,啰里啰嗦。比如对火车车厢设施的细节描述,我觉得他大可以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来概括。同时,可能是因为澳大利亚的旷野过于广袤,而独驾又穷极无聊,作者不惜重墨的描述了自驾途中收听的一场板球直播比赛。而翻译水平也是差强人意,句子结尾部分非要像小学作文那样用 “哦”“啊”“呀”“啦”“哟”来抒发感情。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话痨的碎碎念也让布莱森显得真实可爱。同时,或许这也是喜欢独自上路的人,在自由与孤独之间的一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