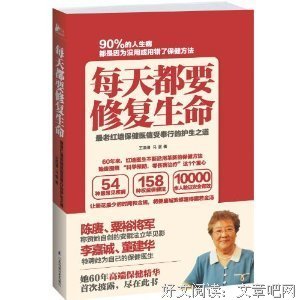
《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是一本由[美] 蕾切尔·萨斯曼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3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读后感(一):植物知道时间的秘密
树非常了不起。在记忆与遗忘的国度,一直背负时间在身。每每过去一年,它便烙下一圈年轮。它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建立起地球进化模式的参照系列。有关这个世界最老最老的过去,树可以告诉你许多许多。
《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读后感(二):不老的探戈——那些关于生命与时间的法则
不老的探戈
——那些关于生命与时间的法则
文/斯索以
蕾切尔•萨斯曼在《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中讲述的,是关于生命与时间的法则,是一个一个不朽的活着的故事。她向我们揭示,在人类的不足百年之外,有些生命已经活过千年、万年,它们正缓慢地攀上时间的顶端,懂得在逐渐老去的一生中唤醒新的生长点,为看似不可逆的生命注入活力。
《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读后感(三):不是拯救,而是希望
七大洲,三十种两千岁以上的生命,一个女人,成了这样一本书。
南极北极,海下山上,任是最热爱旅行的人也难以走这许多地方,况且作者的目的不在于美食好景、奇风异俗,只是生命——最古老的生命。
“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活了一万三千岁的帕默氏栎,“它在这处陡峭的山坡上扎根时,乳齿象和骆驼还在这片地区漫步”——坚韧的生命啊……但是它们都沉默着,从萌芽到如今,把经历过的一切都深深藏起。
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些近乎永生的生命。但是,到了今日,几乎每一个,都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有些已经垂死,有些已经死掉。几千年的光阴,一笔购销——我们太迅速了,生得迅速,死得迅速,生死之间亦是迅速,并把一切带得加快了速度。
这是见证古老生命的感性的书,在科学上不无可以商榷之处,也没有行记的曲折和趣味。作者只是一一展现,生存了数千年的生命,现在处于何样的状态。
“伴随着剧痛的是希望,我们仍然可能修复自己造就的一些破坏的希望。”是的,不是拯救,而是希望。
《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读后感(四):《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以戏剧性的方式,为我们打量身边的生命世界增添了一种迷人的新视角——可以说是恐龙的视角。
现代人通常所谓的旅行只不过是出于逃避生活的冗长、琐碎或重压而外出消闲、美食甚至猎艳。一切都包裹在文明的金属壳里,舒适故然舒适,但谈不上自由行走。抽掉了心灵和激情,感受不到“逆旅”的真实况味,自然也就体味不到生命中的难度或者英雄维度了。波德莱尔的诗是对他们(以及我们——是的,还有我们)最好的写照:“他们只能找到他们逃避的/东西:他们自己/人们从旅行中得到苦涩的知识。/世界又小又单调”。 我以为,萨斯曼的十年“奥德赛之旅”带有某种精神修行的味道,简直是对现代旅行的改写。她并不富足,有时还很无助,甚至怀有真实的忧伤,但她精神饱满,永远带着开放的心态上路。持续地探访那些岁数超过2000年的老寿星使她对地球生命有了真切的体认,并最终改变了她的内心。她说:“我用了将近十年时间研究,摄影,到世界各地去寻找古老的生命,这也让死亡进入了我的视野。面对‘永远’的高深莫测的广度,我对人类个体生命(我的生命,或他人的生命)的短暂有了更直接的理解;与此同时,站在这些古老生命之前,我们却有很多与瞬间的联系,它们小如分子,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都构成了一部持续开展的叙事。任何瞬间都很重要,我们都在其中。”她带着灵魂去旅行,书中还有很多话令我们动容或沉思……
《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读后感(五):遗世而独立
本书的译者刘夙近年来翻译了多本植物类的科普作品,可以说此领域的质量保证。译者在后记中提到的、与之商榷植物中译名的刘冰也是位优秀植物学者,凭一己之力出版了两本特别好用的野生植物图鉴。有两位刘老师坐镇,这本书的译文质量当然是杠杠的。
至于作者,诚如译者在后记中所言,她将科学与艺术无间融合的能力着实令人赞叹。这本书起源于一个金点子,寻找并拍摄哪些单体寿命在2000年以上的生物。任何直面这个想法的读者,大概都会有点儿晕时间。不过作者并没有就此无限发散,把这书变成光怪陆离的猎奇之旅,反而是异常严谨地抓握着现实。这种现实感首先体现在观察目标的确定上,到底哪些生物的寿命在2000年以上呢?听科学家的。虽然2000岁这条线定得突兀,但作者筛选目标时却异常小心。她会翻阅大量论文并向相关学者多方求教,在旅行过程中也往往会邀请、聘请科学家、护林员等专业人士引导,以便在陌生的野外环境中准确找到目标生物的个体。现实的第二层体现在照片的取景上,作者有意采用了与人类观察时相近的拍摄视角,尽力呈现出真实的现场感,而不刻意追求宏大面貌或冲突比对。最后一层现实是关于每次探访经历的文字记录。记录里主要探访过程的实际经历,呈现的是游客视角而非全知视角。照片和文字结合起来,构成了一次次可被读者感知的真实探访旅程。在这样的旅程中,无需更多的阐释或慨叹,那些最老最老的生命自然而然地显露出了它们的神奇之处,也激发了我们的敬畏之心。
《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读后感(六):敬畏天地毋朝生暮死
《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读书笔记
[美]蕾切尔·萨斯曼[著] 刘夙[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325,000字 275页
敬畏天地毋朝生暮死
这是一本艺术摄影作品集,内容震撼人心,16开横板精装装值得收藏。初次见到的时候就惊艳了我,厚厚的书,良心之作。
艺术家蕾切尔·萨斯曼行走在这个古老的星球上,拍摄那些已知的古老生命,古老到我对那些年龄只剩一堆数字的概念。大部分时候艺术家是独自上路的,不论是前往和返回的路途,还是探索集合之旅。让读者关注生态、关注生命。人类在地球上的时间还很短很短,我们需要对地球及其生态系统保持敬畏之心,不在显得“人类”好似地球的毒瘤一般。
关注全球生态的话题早已是老生常谈了,从我年幼时的沙尘暴到现在的雾霾,以及是不是就会提到的全球变暖。蕾切尔没有去谴责,没有对各种治理理论大谈特谈,只是用相机告诉了我们人类有多么的渺小。
书中提到的大部分植物都是“无用”的,不能成为建材、食材、能源等,所以才存活了下来。然后随着人类智力的提高、知识量的储备以及媒体传播的发展,有些植物即使已经被确定为古老生物了却依旧难免惨遭毒手。人类的无知和无畏施多么的令人悲哀呀!
中国古语有“夏虫不可语冰”,生命远比人类短的生物不能理解人类,同理,人类估计也是不能理解生命比我们长的多的生物是什么样的存在。就像发现新大陆的时候一样,人类一直在以自我为中心,一味的索取及破坏。幸好有蕾切尔这种有识之士的存在,在提醒人类要记得放慢脚步,等等我们身后的灵魂。
书中有个“深时间年表”,有些概念不太理解,网络搜索也无所得,找人请教时问我从哪里看来的。介绍了这本书,在网上简单了了解了一下之后告诉,这本书大概是在表达人类对其它地球生物的敬佩和怜悯,以及愧疚。
作为一个普通人,大概此生无缘走这么多如此远的地方,也无缘去朝拜这些古老的生命了,幸好有北大出版社的人文关怀。
附图是自己整理的《深时间年表》,以作纪念。
《深时间年表》
《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读后感(七):探寻古老生命的言语
《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一书,是博物文库·生态与文明系列中的一种,此书的作者蕾切尔·萨斯曼的足迹遍布五大洲,耗费十年的时间与生物学家们一起工作,用镜头定格下了30种持续存在两千年以上的古老生命。包括格林兰的地衣;非洲的猴面包树;加勒比海的沟叶珊瑚;犹他州的8万岁的颤杨群体……它们的寿数超越了人类的文明史,以独有的方式与地球和谐共存,其存在本身足以令人惊奇与敬畏。
本书的摄影作品十分震撼人心,来看这2150岁的巨杉,它的高度仿佛直升天际,另外还有一株称为“谢尔曼”将军的巨杉,它已经2200岁了;再看袒露白色树干的长寿松,它分布在加尼福尼亚的怀特山脉,枝干扭曲,矗立在大地上,充满力量。除此,还有一株可能有5000岁的长寿松,这真难以置信,长着嫩绿色叶片的它已如此高寿。
北美洲有一种植物叫莫哈韦丝兰,它们在沙漠环境中生存。作者用镜头记录下来的个体已经12000岁了。它的样子有点像菠萝,仿佛用绳子将它们细长的枝叶一捆一捆扎起来似的。作者两次造访此地,在本书中可以看到两张照片,一张近景,一张远景。作者见证了它漫长岁月中的短暂时刻。人类的出现真像是一次蚁类的造访,如果意外与它擦身而过,这将是多么令人惊奇的时刻,但这样的植物又是以最为平凡的方式自处,百年、千年、万年如一日的静立。
我不禁想起了英国的巨石阵。它们年代古老,关于它的作用,其中一种说法是用来祭祀的。我们在一些地方也会看到,人们对古老的树木进行拜祭,许下美好的心愿,希望得到它的庇佑。这是人类对生命敬畏时才有的表现。可是看到作者的文字部分,一切显得非常抱歉,由于全球变暖,已危害到了这些古树的健康,其实放远来看,不仅是树木,自然环境遭到破坏,所有的生物都会受其影响。
作者运用自然光用胶卷拍摄的每一张摄影作品里,我最为惊奇的有两张,一张拍的是密生卧芹;另一张是地中海海神草。海水里中常见的有各种珊瑚,但依此摄影作品来看,它们同陆地上的杂草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更加嫩绿、新鲜,就像清洗过的蔬菜一样。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看起来鲜嫩的草,竟然已经100000岁了。
这里还有许多物种分布在地球上的极地之境,比如在智利阿塔卡玛沙漠2000多岁的密生卧芹。“这种像藓类一样盖在岩石上的植物实际上是灌木,由数以千计的纸条构成,微小的叶子一簇簇地在枝条末端着生。它们长得十分紧密,你甚至可以站在上面。当然,我并不建议你这样做”;还有生存在纳米比亚沙漠中2000岁左右的百岁兰,“百岁兰像是停留在了青春时代,让我想到它就像是一个球果树版本的皮特·潘,虽然年纪渐增,却永远长不高”。可见它们为了生存经年累月地与恶劣的自然气候相适应。
但是当人类涉足它们的家园,它们再也没有能力顺应着有悖自然的文明物质。比如本书中,13000岁的帕默氏栋所在的山脚下堆满了人类废弃的垃圾,它们的生存空间就是这样萎缩掉的;还有犹他州的的颤杨无性繁殖群体,有专家认为它已经8万岁了。“它看起来是一片森林,从某种意义上说却是一棵树。拥有硕大的根系,群体里有47,000棵树,其中的每一棵都是从这单一的根系上长出的茎,于是这个群体就成了一个占地106英亩的遗传上等同的巨大个体”。可是颤杨的生命正在衰退,作者呼吁道:我想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名超过2000岁的生物,希望它们得到承认和保护。
作者用她的镜头记录下了这些神奇的生命,感叹物种多样性的同时,发现这些古老的生命好像从未如此脆弱过,它们与人类一同走进21世纪,但随着人类地盘的扩张,科学技术的发达,都对自然环境产生了破坏,对这些古老的生命构成了最大的威胁。它们的消失意味着生态环境的失衡,最终危及到的将是人类自身。从眼下来看,这一点也足够明显,被污染的地下水、空气、垃圾占据的绿地,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人类的健康。
《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读后感(八):有关生命本质的思考
Rachel Sussman的书《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的中文版在2016年出版。本书本质上是一本摄影集。作者自我设定了一个限制,即她必须拍摄年龄在2,000岁以上的生物体。所以,书中绝大部分照片都是某些植物,其中相当比例是植物的无性繁殖群体。实际上,书里面所有寿命超过10,000岁的生物体都是无性繁殖群体。比如,其中有地中海的海神草,其无性繁殖群体的年龄据说已经超过100,000岁了。
我们一般讲的寿命是指某一个生物体的寿命。那么,我们得首先给“生物体”给出一个定义。在人类中,我们讲的“生物体”就是单个的人。虽然一个人的家族可以流传几百年乃至上千年,比如像孔夫子的家系都可以上朔到春秋时期,应该接近3000年了,但是我们并会不认为存在一个叫“孔”的生物个体已经活了快3000年了。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一个人是一个生物体而从某个人传下去的家族则不是呢?这个就涉及到基因层面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果你要定义一个“生物体”那么它至少得有相同的基因。人类是通过有性生殖来繁衍后代的,这个就决定了每一代的基因必然会不同,因为它们是来自于父母双方基因的重新组合。所以,对人类这种以有性生殖为唯一生殖模式的生物,每一代都是独立的生物体。你和你的儿子的基因不同,因此显然你和你的儿子是独立的两个个体。那个,如果你活了80岁,你的儿子活了80岁,你们就是两个个体分别活了80岁,而不是一个活了160岁的个体。这个非常容易理解。
然而,植物的情况却有所不同。植物可以通过有性繁殖。通过传粉,形成种子,种子发芽,形成一棵新的树苗。那株新的树,其基因是它父母基因的重新组合,因此是新的独立的生物体。这个和我们人类的情况没有区别。但是,植物有时候也可以进行无性繁殖。凡是尝试过扦插的人都知道,一根植物的枝条是有可能长出一株完整的新的植株的。而这株新的植株的基因型和它的母体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株新的通过扦插而来的植株和它的母体是一个生物体?如果是这样,那么通过扦插或者任何自然的无性繁殖方式形成的诸多植株是不是等同于一个个体?如果你承认这一点,那么是不是至少理论上,此生物体的寿命可以无限的持续下去?
这些问题听起来似乎只是一个定义的问题。但是它也并非没有意义,因为它涉及到了生命的最深层的问题,即生命的目的是什么?要理解生命的本质,首先必须理解达尔文进化论。每一种生命形式都在进行生存竞争。因此,从终极意义上讲,只有能够最有效的留下后代生命形式才是最成功的生命形式。对于一个个体而言,它的寿命再长,如果没有后代那么实际上也没有意义。而即使它寿命很短,如果它在繁殖后代上非常成功,那个这种生命形式也同样非常成功。这里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昆虫。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每一个生物个体实际上都是一大堆基因的组合。或者你可以说你就是携带基因的载体而已。那么从基因的层面讲,所谓个体之间为了繁殖更多后代的竞争也可以理解为这个物种的基因库里面各种基因为了自己能够成功复制更多拷贝而进行的竞争。那么,现在你有两种不同的繁殖方法。一种是每一个个体都完全的把自己携带的基因拷贝一遍,这个就是无性繁殖。另一个方法则是每一代都把某个载体内的基因与另一个载体内的基因混合一下。这个有性繁殖。前者,你可以理论上无穷的把某一个特定的基因组合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而后者,你实际上每一代都毁灭了原先的基因组合,即你任何一个特定的基因组合的寿命都不超过一代。所以,有性繁殖的诞生实际上就注定了任何一种特定的基因组合的死亡的必然性。“性带来死亡”这句话在这里没有更确切了。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生物会进化出有性繁殖呢?原因是,通过有性繁殖每一代个体都会有一个新的基因组合来面对自然选择的压力。因此,能够进行有性繁殖的物种必然可以有更高的多样性,因此其适应变化的外界环境能力会更强,不容易由于某种外界突变而全部灭绝。所以,如果你不是立足于单个生物体(或者说特定的一个基因组合),而是立足于整个物种的话,显然有性繁殖会带来更长的物种的寿命,或者说这个物种基因库的寿命。
所以,讨论寿命问题实际上也是在于你的视角。回到《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这本书,实际上,作者讲的是最老最老的单个基因组合。这个事实不免给本书的科学性带来局限。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考虑本书给人带来的思考。比如,即使再老的生命也免不了一死。即使可以回避衰老,也避免不了事故,灾难,疾病等等。那么当我们盯着一个古老的生物个体的照片,我们可以同时想想在它的一生中它的经历,它周围发生过的事,以及未来它的命运。所以,从本质上讲,这本书是一种艺术。它的价值也是在于其对读者的思维的激发,因此并没有必要逐字逐句的纠结其列举的生命形式有“多古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