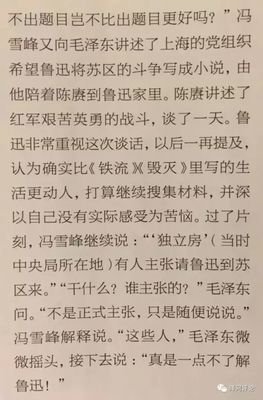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是一本由王汎森著作,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9.00,页数:59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精选点评:
●王真是继承了余的衣钵,本书收几篇论文就思路和话题均有延续其师的一面,如以方东树、邵懿辰、太谷学派、汪士铎、章太炎为例,将近代出现的宋学复兴、经世、反传统、革命等思潮从内在理路的角度进行了追溯,在《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一文,王以新史学脱离社会等缺陷造成最终为马史学取而代之,同其师从晚明发掘考据学传统由来的做法,包括胡适、陈寅恪及知识分子自我想象的转变均与此相同于知识分子自我边缘化后所造成的抗衡统治者正当性与自信的失去,社会决策全面轻视专业知识等后果值得思考。有关传统与反传统的关系,王提供了更为复杂面向,传统中孕育着反传统的倾向,复古引发传统动摇等吊诡的现象,而反传统的人中其思想有往往有引用传统的一面(包括私人领域的政治化),所谓“反西化的西方主义”“反传统的传统主义”更形象的说出了这种纠缠与矛盾
●求求我自己读点书吧
●王先生的序总是让人有所启发
●4.4。作为一般读者,读历史、思想史、学术史可以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一个族群或者人类整体如何走到今天,是什么在推动族群行走的方向。另一方面也可以大概获知此时此刻处在这个时空坐标系哪个位置上,以帮助推动个体做出判断。
●大学者。
●好久没读500页以上的大书了。第一二编收获较大。
●不情愿的五星 《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一文引介了之前闻所未闻的汉学与宋学的概念 总体来说本书的观点散漫 不成体系
●因为更感兴趣,我是倒过来看的。没想到翻完后感觉比按着时间线阅读,线索更清晰了。王是做古史辨和傅斯年起家的,所以明显得感觉到他对这一段学术史的建构游刃有余,无论在材料和方法上。以此为切入点,可以看到他怎样撕开了近代和晚清思想史的裂口。逆流而上,由学术体系的建构而至思想、观念、方法的改变,进而上溯到传统中裂变的萌芽与“旧典范的危机”。读书广博,行文清晰,冶新旧材料于一炉。非要说有什么缺点,那就是厘清与描述历史面貌后,没有进一步的论断和总结。但提出这一个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本身不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吗。
●有几篇文章已收在傅斯年附与三联出的小书里面
●误扣深门,别有洞天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读后感(一):上穷碧落下黄泉—重建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我几乎是带着一种渴望,一种急切的心情读完这五百多页的巨著,先生的文笔简单晓畅,从不故弄玄虚,每篇论文的开头结尾都带有总结性的文字,让人做起笔记来得心应手,如果说让不立偶像的我非要说出一个喜欢的史学家来的话,王汎森先生是当仁不让的。 由于王汎森先生对中国近代与前近代的思想与学术熟稔于心,尤为难得的是对清代学术信手拈来,这使得本书在考镜源流,追溯思想源头和思想之间的联系方面非常到位,此书很多篇论文论述了思想之间或有意无意间的交流往互,这让人们可以更清楚地把握近代思想流变的系谱。 其次,思想的层次性和思想与生活的交集历来是先生所注意的,也是其《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这本书的论述重点,这本书里好多论文论述了思想的公开与私密层次,思想的潜流与正统层次,还有从一个学者的日常生活和交游把握其思想和学术层面。
学术和思想的系谱,顾名思义,就是学术和思想从哪里来,这个来处可以是前近代,也可以是域外,也可以是未被时人注意的异端,这个系谱不一定是师徒传承的那种直线联系,有可能是在当时未有影响力而突然为后人所注意,有可能是表面极力否认而其实暗得其韵的承受,也有可能是目的和精神完全相反的只在手段上传承,传统的强大在于你虽在理性上要摆脱其影响,但感性上却从来不能脱离它的支配。
说实话,我以前由于读书少,所以对傅斯年先生的影响着实估计不够,其实傅斯年先生不仅在先秦上古领域有巨大的史学贡献,还对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和第二次史学革命功莫大焉,这涉及到史料观,史学观点,史学方法和视野的全新转向,是我国学术走向现代的重要一步。
本来是想写短评的,无奈字数多了点,但也不成严谨的长评,写的不好,多多包涵。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读后感(二):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王汎森的第一本书,相当好看了,王汎森的思想史写法很“剑桥学派”啊,本书是王汎森的文集,大致按照可以分成清末的学术演变、近代思想传统与现代的嬗变与错位、近代学术史三个部分。可能限于篇幅原因很多地方并没有展开,但是王汎森的思路具有相当程度的启发性,从这一本开始入手近代思想史应该是不错的。《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强调清末政局与社会秩序的变动使得原先被压制的“传统”中国记忆复苏,从而使得晚清兴起一股“整理国粹”运动。这场带有明显排满色彩的运动使得“国”与清廷相分离,体制内的改革被排斥,并直接走向了革命。从思想与观念的演变来看,这是一种对历史记忆的重构过程也是一种“遗忘”的过程。《从传统到反传统》这一篇启发最大,它实际上揭示了近代思想史当中存在着的相当程度的错位关系。同一个目的之下可以有多种达到的路径,而看似同一个路径也可能通向不同的政治目的。其根本在于近代知识群体在中西文化冲击之下的分裂与纠结。“西学中源说“可以成为抗拒西学的武器也可以是吸收西学的辩护。尊孔可以捍卫传统也可以打破守旧。复古也并非守旧,而为改革传统创造契机。而爱国的动机下更可以存在多种手段,全面西化、彻底破坏、无政府主义、毁家造群等。《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揭示近代思想潮流中对传统理学的功能化使用,以理学树立人的主体性,张大人的中心地位,以造成革命的局面。《思想自然与概念工具》中国实际上接受了大量来自日本的西方观念,集中反映在各种语词的译介与传播上。一个段子,张之洞下令“不要使用新名词。”幕僚答道:“名词二字便是新名词。”《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集中反映政治立场对史学理论的影响,其讨论的基点在对“国家”“国民”“社会”等观念的重新认识。从旧王朝史解放出来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主张历史应当塑造国家记忆形成民族认同以达成政治目的。而其后以傅斯年为代表的“新史学”反思则极力主张客观性原则。《反西方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学习西方以打败西方,复兴传统以寻求改革。从传统的乌托邦思想演进到近代的无政府主义。刘师培为代表。《思潮与社会条件》二者是互动关系。学术史方面,王国维强调地理化的历史观,以西方之周为中心。傅斯年从朝代更替来看,以东方之殷为中心。胡适竟然是傅斯年的老师?我人都傻了(没常识)近代对史料的认知经历了从单纯的书籍经典中心论到多元化的演变,安阳考古是集中表现。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关系。“霜红一枕已沧桑”。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读后感(三):虚伪的“攀登者”与执著的“漂流者”
读第三编第三节“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想到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故在此记录。
经典诠释学在发展中逐渐分化成两个派别——“求其古”派与“求其是”派。前者是要寻求最古的经典注疏,后者是要寻求最为合理的经典注疏。我初以为,“求其古”派是局限的,因为他们只研究他们认为“最古”的那一代的文字典籍。我的这种想法大概是受了前两编大量与清代考据学有关的文字的干扰。事实上,为了找到那“最古”的一派,“求其古”的解经者们需要从当下一代开始,逐代前推,顺藤摸瓜。在这一长久的过程中,便留下了他们对历代经典注疏的研究足迹。因而虽然他们的初衷是找到最古的那一代(与孔子及其弟子生活的年代最近的一代),但从实际结果来看,他们却将历代的注疏都捋了一遍。而与之相对的,“求其是”派口中的“寻求最合理的解释”,其实仅仅是为了找到最符合圣人本义的解释,来作为权威性的社会意识,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思想工具。他们在“求其是”的过程中,并非平等地看待每一代的解经文献,而是将某一代先预设为“最合理”、“最有价值”,然后禁锢在那点狭隘的范围里做研究。
如此看来,便不难理解为何清儒大多倾向于“求其是”,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史家们大多有“求其古”的影子。
新史家们批判清儒“对文字过度迷恋”、“学术带有古董化倾向”。清儒对文字迷恋,并非指一切文字,而是单指经书上的文字,这种“迷恋”是要看文字的载体的。清儒这种“唯六经三史是尚”的研究典范,使他们的研究偏向一种“内循环”,从文字到文字,从文献到文献,即使偶尔有对实物的研究,那也是为了厘清或作证经书文献上的文字,因而往往重视铭文校勘,而不大留意实物还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其他方面的信息。过度迷恋文字而忽视实物材料,过度迷恋经书文献而忽视其他文字材料,过度迷恋汉代注疏而忽视甚至贬斥其他朝代的经书注疏——这三点应该就是清代考据学在研究视角和材料选择上的三大特点了。他们很像一群爬山的攀登者,有趣的是:有时候他们刚爬到顶,又慌慌张张地跑下去,从地下装模作样地再爬一遍;或者他们根本看不到顶,这座山向上无限伸展,但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又或者,这座山从根本上就是虚假的、泡沫塑料做成的,可笑的是这群人还如往常一般哼哧哼哧地卖力气爬呀爬呀……在封建的意识形态天幕下的山峰是虚伪的,那些“攀登者”自然也是“虚伪的攀登者”,只不过他们中间有些是“明知而为”,有些是“不知而为”——可憎与可悲的区别罢了。
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的权威已经,六经在那一批新史家眼里,只是众多史料中的一种罢了。六经是供人研究的材料,而不是让人寻求治国平天下大道理之所在。在这一前提下,他们提倡历史发展的观点,即平等看待每一代学术思想材料的价值,不再以为只有那最高点才有价值。他们能平心静气地顺着时间的长河划舟漂流,每到一处景点,他们都会停舟上岸、观赏游览,留下自己的足迹。在他们中间,唯一的差别大概是最后一次停舟的地点——在殷墟的青铜器重建天日之前,胡适和傅斯年兴许把小舟停在了周代;随着史语所重大考古成果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新史家划着小舟向着更遥远的古河进发。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读后感(四):读书笔记1
其实是一篇读书摘记,但“读书笔记”区域写好后不方便寻找,故写在书评区域。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笔记记着记着就开始画画…[Emm][旺柴]
王汎森先生《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的引论实在精彩。(想到在唐潮读书会上侯亚伟老师也就“后见之明”的问题提醒过我们)有关“去熟悉化”问题,脑子里突然冒出来古人过河场景:真实的古人:“有四条石子路可以过河诶!我咋知道哪条路最稳呢…(不透明的信息),对面这帮人吵着叫我走A路诶(群众),走A路经过A村有熟人可以请我吃顿饭(个人利益),算了不想这么多了,就A路,冲!(不完全的理性)” 一些史家眼中:“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走A路最安全、最顺应民心、最合理,他肯定也是充分权衡考虑以后才走的A路,换个人来走,也还是走A路。”
“我们对百年来的历史知道得太熟了,所以我们已逐渐失去对所研究问题的新鲜感,需要'去熟悉化',才能对这段历史产生比较新的了解。对某个定点的历史行动者而言,后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他所不知道的,摆在他面前的是有限的资源和不确定性,未来对他而言是一个或然率的问题,他的所有决定都是在不完全的理性、个人的利益考虑、不透明的信息、偶然性,夹杂着群众的喧嚣吵闹之下做出的;不像我们这些百年之后充满'后见之明'的人所见到的那样完全、透明、充满合理性,并习惯于以全知、合理、透明的逻辑将事情的前因后果顺顺当当地倒接回去。历史中的人并非处于'完美理性',而是'有限理性'。换言之,'事件发展的逻辑'与'史家的逻辑'不同,在时间、顺序上正好相反,一个是A→Z,一个是Z→A。历史工作者要用很大的力量来使自己变得'未知',即福柯所讲的'去熟悉化'。”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读后感(五):转汪荣祖书评:《未完成的系谱》
现在的学术著作很讲究关键词,以突显一篇文章或整本著作的主题。“系谱”无疑是王汎森先生这本著作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所谓“系谱”,原指有系统地记录动植物祖先情况的档案资料,以推断遗传特性与确定个体间的亲缘关系。作者将“系谱”词,用之于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自然会使读者期盼这是一本对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颇有系统的论述……
汪荣祖:《阅读的回响——汪荣祖书评选集》,文汇出版社,2017年,第109-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