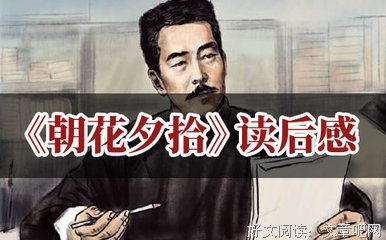
《士大夫的理想时代》是一本由余蔚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3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士大夫的理想时代》精选点评:
●余蔚具有当代宋史学者少有的全域意识和宽宏眼界,既重视宋辽夏金元的横向比较和纵向更迭而又将之复归于兄弟阋墙。具有鲜明的人文关怀。
●文笔怪异
●内容梳理和文笔不错,但书名让人误解,其实就是简明宋史。
●简单扼要说宋史
●理论讲得好,细节丰富,文笔尤佳
●以通俗史学而言,行文不够跌宕有趣
●体例大致类似哈佛那套,篇幅略长,然两者论述事件的重点有所不同。总体看这本写的也很好,让我们对那个时代又多了些了解。
●简明扼要,有叙有议。最后三章总结尤其棒,但应该用更多篇幅扩展来写文明史,而不是只有王侯将相。
●越是读到最后越觉得有意思。特别是最后几篇总结性的文字。反而是前面讲具体史事时会有难读的感觉,说到底还是自己缺乏耐心以及掌握的太少。大概率会再读一遍。是一本知识性,趣味性和思考性于一身的好书。
●2019116: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真是影响深远,后继谈唐、宋史者几乎难以绕过。虽然郭志坤在序言中称许其“以时间为纲,以专题为目”,但本质上仍是传统的政治史写法,将大量笔墨用在了政治、军事、边防与外交关系上,顺便带及经济、文化、科举等方面。着力点在于自身权力结构、官僚体系以及与辽金夏的战争与媾和,和传统史论不同,作者肯定了“澶渊之盟”以及有宋一代防御、议和的正面作用与积极意义。新版将书名改成了:士大夫的理想时代,然而作为新儒学与士大夫阶层的黄金时代,本书并没有充分体现宋朝的种种变革,以及它所营造的更适合士大夫生存的环境。很明显的一大问题是对文献的引用不统一,有些原文引用,有些则将其翻译成了白话,虽是通俗史,也应当严谨一些。
《士大夫的理想时代》读后感(一):其兴也士大夫其亡也士大夫,虽然叹息但也很敬佩,理想也要先保证身体健康,不然到了关键时刻就是打了鸡血的虚壮,敲一下就怕疼。
大致白描,中间有些过程有些仓促,可能是篇幅有限,有了取舍,从赵太祖的起步到宋的大势所去,其兴有时代洪流的裹挟也有太祖家族的才干累积,而其亡也在在建国初期已经埋下祸根,不过北方的敌人在随着历史变迁,由辽夏到金夏再到蒙,强弱对比越来越明显,北宋时的士大夫还有一股股士气,想着再现汉唐时期的大疆之境,改革保守不过是两种途径,皇帝虽然儒弱,但是也是很有士气的,至少敢御驾亲征,虽然没有打赢过,到了南宋,高宗绝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挽救了宋的延续,但是也导致宋将偏安一隅,后面的皇帝或被动或主动大多为权臣所属,而整个国家就像用只破碗在担着水走路,时刻操心着别把水洒了,也有想换只碗的时候,只可惜邻居敲一下头,又回到旧的状态,等到蒙破金后,几代大汗步步紧逼,宋人虽然有了节气,可是节气挡不住大刀啊,宋灭可敬可叹
《士大夫的理想时代》读后感(二):好久没看的历史书
阅读书目《士大夫的理想时代 宋》 阅读章节 一至六章 讲述从宋太祖建国至北宋灭亡到南宋建立的时段。已经都有一两年没有读历史书了 ,如果人类简史是历史书籍的话,上一次看的历史类书籍就是这本了。 当把历史看成一个个事件时,足够宏观,却没有了个体在历史面前内心的心理活动。毕竟,这似乎对历史来说并不重要,立足于个人的爱恨情仇,利益得失,在一本正经的历史书面前应该是不足道也的,这样的描写你应该去看看历史小说,野史,外传吧。以前读历史的时候,会因为奸人当道,忠臣冤死而想不明白。初中看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时,一直无法释怀的是为什么好人得不到好报,坏人得到善终为什么苏轼的一生要被佞臣陷害。现在想想,如果我能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历史就这样发生了,它不是遵循着我们所奉行的理念和正道运转下去。而是就是在时间里,一种也许我们终究无法掌控的变幻中。
就如我们在北宋朝代中,可能会对宋徽宗抱有十分负面的看法,其在位时期一味地自保的统治时期直接导致北宋后期覆灭的结局。光看被金兵打到家门口,无奈慌逃下位,将自己的破摊子留给宋钦宗。我们所谴责的应该只是身为一代君王的个体有限性,但是当我们把他放在历史当中看的时候,或许我们就不会再用那么一个拘泥的角度了。
《士大夫的理想时代》读后感(三):与士大夫共天下者 庶民也
文风端正严谨 有主线有张本 围绕文官系统与赵官家间300年成熟共生互动 讲熙丰革新/宋徽失政/高宗杀岳几篇最是洞察人心 又论坊墙打破市民文化勃兴 绝非泛泛而谈之宋史科普 如此篇幅里能有深度前沿兼具 不易了
首先定论宋代文官地位之高 文官系统之成熟 放诸历代可算首屈一指. 赵官家终崖山之败 秉持太祖历五代教训 抑武重文 诸般兵事周旋 皆出于自固考量
宋辽之间 以澶渊之盟为要 而后宋又以数十万财货 不惜拉辽介入 赎买西夏和平 夏仅于国书上让步称臣 而宋所求 亦不过最低限度之臣属关系以维系其基本国际威望
故真宗仁宗朝 空气沉闷又不失稳固 需作些改变 使其避免运作日渐迟缓 甚而终致失却应激能力之日 但若施之猛药 若王安石熙丰革新之猛烈变革 却很可能是过犹不及之冒险
余蔚氏谈及范仲淹之庆历新政 评价甚高 曰文正公兼具理想与世故 理想在抑制子弟恩荫入仕 正本清源 使学术精英有机上升流动 整合与官僚一体; 世故在直指本心 仅动官僚体制一块 控制改革于较小范围
而王安石新政 则大不同 曰理财为方今先急. 而余蔚氏则直揭其实 生财耳 聚财耳? 青苗法免役法最终皆别为一赋 实生财无方聚财有道 民生愈艰 若富弼言 财聚于上 人散于下
安石之为今朝所称道者 盖其三不足之论 曰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流俗之言不足恤. 此一番革命乐观主义 又兼其大政府经营思路 何其相类也?
北宋之亡 既是固有体制积弊下 政治精英谋求经济破局 与民争利终致不堪重负; 官僚阶层又互斥奸佞陷于党争 当局实富 宋徽进趋膨胀 与金海上结盟 欲谋求灭辽收复幽云
宋徽者 端王时即有轻佻之论 恃其私智小慧 文艺玩物足称一绝 而竟图以此小智侵占金人便宜 靖康之耻 非自造孽乎
南宋朝 康王临安建炎后 无外乎回归攘外必先安内既定路线 高宗杀岳一案 赵官家提防武人之心结固是传统 岳鹏举不习臣礼骄傲单纯亦惹帝王芥蒂 故高宗必杀之
高宗后又孝宗 孝宗后又光宗 而光宗退位与宁宗之立 又是有宋一代政治之极端案例 文官政治鼎盛成熟时代 所谓与士大夫共天下 强势皇权之前 文官集团仍谋求寻找方式限制皇权 日常即是按程序行事 而遇光宗李后这一特殊事件 剑走偏锋逼退再立也算非常之道
帝王史外 论宋代各方各面 皆向平民社会倾转 坊墙打破即是一例. 坊者 城市居民区划分单元 唐以前之坊 四面封墙 宛若城中之城 四墙仅开坊门以为通道. 入夜 坊门则闭 天明方开 其间不得出入 此即宵禁. 而宋代之坊 坊墙完全打开 一切民居皆可临街开门 经商贩物. 故开封不似长安 长安分一百单八坊与东西两市 而开封之坊 既已为街巷割划支离破碎 仅堪作一人口统计与行政单位 而商贸随处也不必再专设集中之市 宵禁亦不复存
篇幅所限 无论著作亦或读者 此书掩卷 绝有意犹未尽之感
《士大夫的理想时代》读后感(四):历史的细节
王安石的政治宣言——“三不足”
“天变不足畏”,是说“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自然界有其运行法则,与人世间的事并无任何关系。不会有人知道,当时的士大夫和百姓,有多少人真正相信“天人交感”的道理。但可以确定的是,“天”被当做是政治和社会运转的最后的制约因素,成为规范人类行为的绝对力量,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天道”是被士大夫着力塑造的信仰。“天道”的制约对象中,皇帝是极重要的一个。士大夫苦心维持着的最高信仰,虽然未必能真正将皇权置于牢笼之中,但毕竟还是起了重要的约束作用。而王安石揭开这个公开的秘密,其目的便是为皇权脱去一切束缚。相比仁宗,神宗及其二子——尤其是徽宗——愈来愈具有拒谏、独断的倾向,王安石的政治宣言“功不可没”。“祖宗不足法”,谓祖宗之法度不可尽行遵奉。宋人宣扬“法祖宗”,并非一切循旧规,而是要尊重“祖宗”多年以来制度建设的成功,维持政策的延续性,尤其是一些原则要世代遵行,譬如崇文抑武、重内轻外等。王安石不愿“法祖宗”,正是针对某些原则。如重内轻外——好静恶动,保守已有成果,不愿主动对外用兵——就是他坚决反对的。“祖宗”是“天”之外,对后世角逐的另一重大制约力量,大而化之的“祖宗不足法”,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不但为他的新政制造自由行动的余地,也为君主的过度自信和任性妄为输送动力。
“流俗之言不足恤”,意指决策者不必顾及多数人的意见。这些人道德水平低下,总出于一己私利反对皇帝的宏伟规划,他们都是国家发展的强大阻力。不认同新法的意见,被强行压制。因王安石不作妥协,不肯接受修正意见,认同部分新法者,也迅速被逼到对立面,譬如苏轼、苏辙兄弟。新法成为一个整体,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彻底否定,朝中人士,必须作一决断。
岳飞之死
自事业的初始阶段,岳飞就显示出他勇于承担的个性。建炎元年上书责让宰相、要求高宗北征,实在是骇人听闻之事。在宋代,一个下级军官上书直言国家大事,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对他所施的惩罚,是免去官职。绍兴七年,岳飞入对前,事先以密奏的形式建议皇帝及早立储。等正式面见,高宗对此事毫不含糊,直接警告说,此事不是你应当干预的。高宗极少以这种干脆直接的方式斥责臣子。据岳飞的参谋官薛弼说,岳飞下殿时“面如死灰”。
岳飞个性之高傲与固执,行为之不合流俗,当时恐怕是有目共睹。正史多载其对下属态度的偏执,比如对牛皋、对养子岳云的严苛,当然,还有对上司的毫不讳言,比如张浚。甚至对皇命,有时也敢违抗。在绍兴七年,欲得刘光世军而不果,又与张浚其争执,一气之下,弃军上庐山终丧,致使军心不稳,此事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骇人听闻。遇丧而起复,带丧履职,在宋代多有其例。但岳飞在二月已起复,四月底却重新要求退居终丧,也就是说满三年之期再下山。这是和皇上赌气,是犯忌之事,更何况此事出自一个手握重兵的武将?高宗当时也慌了手脚,命令岳飞的幕僚部将们上庐山去请,如果请不下来,将治将吏以死罪。可以想见,当时他是非常愤怒的。对皇帝来说,岳飞干预立储一事,十之八九是出于野心,而弃军终丧一事,则表明他没有忠心。
李全父子
来自胶东的李全,与杨安儿之妹杨妙真联姻后,成为忠义军中实力最强的将领,在楚州多年,又吞并了大部分友军。宝庆二年,当他回到山东时,被蒙军困于益都,苦守多年而降,成为中原诸多附蒙武装中占地最广的一支。绍定三年(1230年),李全举全齐之力南下,直至扬州,与宋将赵范、赵葵兄弟对峙于扬州城下,血战累月。次年正月十六日,李全携蒙古使者,置酒高会于扬州郊外,为宋军袭破,李全战死,余军北窜,奉其妻杨妙真、子李璮,继续割据山东,受蒙古之封为益都行省。他的儿子直至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才叛蒙被诛。父子两人,一入《宋史·叛臣传》,一入《元史·叛臣传》,成为绝无仅有的千古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