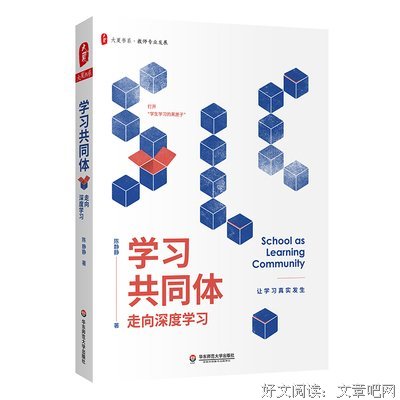
《共同体与社会》是一本由[德]斐迪南·滕尼斯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9.00,页数:56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共同体与社会》精选点评:
●完全赞同滕尼斯的观点
●低年级时从不接触古典社会学理论,高年级来补课了!有一说一,滕尼斯要比韦伯好读(也有可能因为读的新版本……)
●首先,非常感谢译者。在这个时代,翻译经典是一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尤其是对于青年学者来说。我是恰好看了一篇译者写的关于滕尼斯的论文,并了解到滕尼斯是他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便买了这本书。果然没有让我失望。阅读全书,可以感受到译者翻译此书的用心。之前对滕尼斯的了解只存在于外国社会学史中,以及和涂尔干的比较中。但真的只有读原典,从文本出发,才能理解他思想的丰富。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皇皇巨著,虽然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是放在他的时代理解,还是蛮感动的。即便是放在当下,滕尼斯探讨的问题还是很有启发性。
●新译本。不得不说,这是一本任何时候拿起来读,都能有所收获的书~
●好书,说译者心术不正的自己才是心术不正
●斐迪南•滕尼斯是一个出色的马赛克画家,他这里取一块绿色石头,那里取一块红色石头,最终却拼成了属于自己的崭新图画。这幅图画从细处看能发现所有伟大画家的技巧痕迹,从整体看却又是不同于任何一人的创想。
●本身是好书,可惜译者似乎心术不正,提前给点蜡了。你们懂了吧?这就是花千芳为什么叫你们不要学英语的原因
●不太理解,真不太理解。
《共同体与社会》读后感(一):笔记:共同体与社会——滕尼斯的历史社会学思想
(1)基于心理实体的类型学
在滕尼斯看来,一切社群的构造都是心理实体的人造物,它们的社会学概念必然是它们的心理学概念。从个体角度来看,个人的意志存在于人们之间相互的多种关系里,只要关系中的一方是主动者或施加作用者,而关系中的另一方是受动者或感觉到作用者,那么任何这样的关系都是一种“相互作用”。通过相互之间肯定的关系形成的群体一旦被理解成统一地向内或向外发挥作用的生命体或物体,那么它就被称为一个结合。对关系本身,因此也即结合而言,如果我们将它理解为真实的与有机的生命,那么它就是共同体的本质,如果我们将它理解为想象的与机械的构造,那么这就是社会的概念。
(2)共同体与社会的对立
“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对立是一组既定的对立,所有隐秘的、亲密的、排他性的共同生活都被我们理解成共同体中的生活,而社会是公共生活,社会就是世界。共同体是古老的,无论作为事物还是名称,社会却是新的。共同体是持久的、真实的共同生活,社会却只是一种短暂的、表面的共同生活。与此对应,共同体本身应当被理解成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社会则应被理解为一个机械的集合体和人为的制品。
斐迪南·滕尼斯(3)共同体的类型、演进与本质意志
共同体的胚胎形式发源自血缘关系,由家族式的血缘共同体作为聚合的基础,继续扩展为以对土地、耕地的占有为基础的地缘共同体(领地、村社或公社),再随着范围的扩大而以共同崇拜的神祇为纽带建构而成的精神共同体,这就是共同体的三种渐进形态。共同体内成员通过共同生活而具有的相互一致的、结合到一起的信念,是一个共同体特有的意志,滕尼斯称之为“共同领会”,这种意志的三个根源就是血缘的亲密结合、空间内的接近和精神的亲近。而一切以共同体关系的意义为根据的东西,一切存在于共同体关系之中并对它具有一定意义的东西就是共同体关系的法,法是若干结合在一起的人们的真实的、本质的意志,法受到他们的尊重。
滕尼斯认为,氏族或者家族是家庭出现之前的产物,同土地和耕地结合形成为村庄,继而随着人口的扩大与生产能力、贸易的扩展而形成新兴的城镇,在城镇之中就涌现出了劳动合作社、行会、同业公会、宗教崇拜团体、兄弟会和宗教社团,显然滕尼斯对“共同体”的阐述源自于对古罗马、德意志城市、日耳曼村社的历史认识。
从经济生活的角度来看,共同体生活是在同农田以及家的持续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共同体的经济生产以自给自足为目的,商业性质的营利交换违背了“家”的本质,其内部的物资使用与分配的共产主义性质的。
共同体的心理基础以本质意志为主,本质意志是“包含了思维的意志”,每一个意志都表现为一个内在诸要素相互关联的整体,多种多样的情感、本能和欲望都统一到这一整体之中。本质意志是人的身体在心理层面上的等价物,或者说是生命的统一原则,它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并且必须由此来解释,换言之,本质意志是惯习、传统与记忆。
(4)社会的性质、类型与抉择意志
在一个充满了“社会”元素的地方,每个人都只是为了自己,并且每个人都处于同所有人相对立的紧张状态(霍布斯的思想)。共同体为主的状态向社会为主的状态演进,在滕尼斯看来是“新时代”的标志,所谓“新时代”意味着一种“解放”的到来。面对中世纪存在过的个人不自由或者受束缚的五花八门的形式,新时代逐渐进步到一切成年人拥有个人自由或者自决的权利:一种在各种政治权利上实现的自由,包括妇女们的自由。而与自由处于很接近的相互关系中的,还有不同出身、不同能力、受不同教育的人的平等:它意味着个人不再服从个人,而是只有普遍服从法律、服从法制。
这种变迁的动力被滕尼斯归纳为以下几点:人口的增长、技术的发展与改进、大宗贸易和大规模战争、大企业的出现和大城市的崛起等。
“社会”被想象成仿佛由这些分离的个体真正构成的东西:他们似乎为着自己工作,而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劳动却是为着普遍的社会,与此同时,他们似乎为社会劳动,但确是为了自己才工作(亚当·斯密的思想)。
通过协定和自然法,社会形成一个统一的聚合体,我们将它理解成一群自然的个体和人造的个体的聚集。个体的意志和活动领域之间彼此关联,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结合,不过个体同个体之间仍然相互独立,他们无法影响彼此的内心。
社会关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预设了由赤裸裸的个人组成的多数,这些人有能力提供效用,并因此能做出承诺。就其自身的理念而言,作为全体的社会是无限的,在它之上,由各种规则组成的协定体系应当发挥着作用。同时,社会也在持续地打破着所有现实的、偶然的界限。在社会里,每个人都追求着自身的利益,而且只有当其他的人可能促进这一利益时,他才会肯定这些人,所以在达成协定或任何特定的契约之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关系都被理解成潜在敌对状态。
作为“社会”心理实体的是抉择意志,抉择意志是思维对意愿的彻底统治,表现为一种目的的等级结构,是一种目的—工具理性,抉择意志是思虑、愿望和概念。
(5)共同体与社会的法
如果我们将任何通过诸意志形成的、关联着各组成部分的结合的意志内容定义为(客观的)法,那么社会完全有它自己的法。通过法,社会确保了它的各成员的诸权利与义务;但是,法必然从他们原初的、完满的自由中派生出来,并由此组成。与之相反,共同体被彻底理解成身体或血缘的先验的结合,它在本性上就有求生的意志和力量,因此,它自己的法就关联着其成员的意志。甚至于,只要一个人是共同体的成员,那么它就应当仅仅表现为这种有机的完整实体的变更物与流溢物。
共同体的法以家庭法的名义存活了下来,而社会的法则以债法的名义存在。这两种法在它们的中间领域即财产法的领域里显示了各自的本质。
对共同体来说,其现实财产为“占有物”,而对社会来说,其财产为“财富”。占有物与其主体、与其主体的生命是同一的,并且它们完全连在一起。财富则是由一定数量、一定总数的独立物品组成的集合,每一个物表现为一定数量的力,这些力可以将自身转化和实现为具体的享受,财富不仅是可悲转让的物品,而且它必然要被转让。
(6)个人主义的起源
在各个文明的历史里其实根本不存在着现在所谓的“个人主义”或者说“个人本位”,除非它派生于共同体并保持着自己受制于共同体,或者它产生并支撑着社会。现代语境的“个人本位”来自于从“身份”到“契约”的解放,也来自于从共同体到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同滕尼斯的话来说就是“当人越来越作为人本身聚集到一起时,或者说,当各式各样的人越来越集中并彼此承认为理性人或平等者时,一种普适的社会与秩序就越可能最终必然地在他们中间体现或建立起来。个体的解放意味着乡村和城镇里不断劳作和享受着的共同体式的家户毁灭了,意味着耕作农田的社团瓦解了,通过城镇手工业、合作社与宗教维持的艺术丧失了;同样,个体的解放等同于利己主义的胜利,等同于放肆、欺骗、造作、贪财、享乐以及虚荣的胜利。然而,它也意味着平静的、清楚地、冷静的自觉意识的胜利,借此,无论神圣事物还是人间事物,有教养者和学者们都敢于面对”。
(7)滕尼斯对未来的展望
共同体的时代的整个发展是向社会过渡,另一方面,共同体的力量尽管在日益减弱,但仍保留在社会的时代里,而且它仍然是社群生活的实在品质。在以共同体为主要元素的社会生活中,①原始的、简单的、家庭的共产主义逐渐发展为②村庄、城镇的个体主义,随着社会的继续演进,一个“新时代”到来了,这个新时代逐渐以社会为主要元素,③扩大的大城市中的个体主义是滕尼斯时代观察的主要样本,但他预言在新形态的社会生活中,共同体的元素会继续发挥作用,形成重新把人联合起来的④国家的或者国家的社会主义(显而易见受到卡尔·马克思的影响)。
《共同体与社会》读后感(二):《共同体与社会》读后总结和感受
援引欧洲古希腊时期至19世纪的社群生活经验形式,抽象为共同体和社会的对立统一形式,并对其中的社群关系进行社会学分析;然后溯源心理学,用个体意志类型中的二元对立解释不同社群生活形态;最后考察不同意志作用下的社群生活最终形成了怎样的秩序与法。
“如果说社会的方向最清楚地表现在客观的法的内容之中,那么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法、即仅仅视它为文化的产物,毋宁说,我们不但要将它同经济现象、因而同社群生活本身紧密联系到一起,而且必然总要将它同社群意愿的其他表现方式做比较,甚至由后者来衡量它。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社会学思想首先针对的是法学问题……最终,通过区分秩序、法与道德,通过我的关于社群实体与社群价值的学说,我希望呈现一个坚实的理论整体。”(《共同体与社会》第八版前言手稿,1935,p542-543)
滕尼斯通过三个层面的对立,发展出一套社会学的概念体系:
1、社群生活的现实形态:共同体与社会
2、心理学的基础:本质意志与抉择意志
3、社群内部的规范和法权秩序:基于身份的秩序与基于志愿的契约
人们共同生活的经验形式(政治经济学)——共同生活在心理学层面上何以可能(心理学)——源于意志的经验形式如何在现实中维持(法学和政治哲学)。然后,滕尼斯对每个部分进行辩证式分析。
先放上主要概念:
Gemeinschaft(共同体):这个概念指的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团体或社团,而是一种关系的性质。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将这个词放到“关系的范畴”里,意为“协同性”。滕尼斯用它指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有机的、有生命力的关系。
Gesellschaft(社会):该概念指的也是关系的性质,它不是一个实在的整体。它指的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人通过思维、人为构造出的机械性的关系形态。它在法权上的表现是主权或人造国家,而非英译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ozial:从拉丁文socii衍生而来,一般译作“社会的”或“社会性”。滕尼斯用它指群体的、集体的、共同生活的关系,故而同时包括了“共同体”和“社会”的含义。为了和“社会”概念区分开来,张版把它翻译成“社群的”
Wesenwille(本质意志):这个概念由德文词“本质”(Wesen)与“意志”(Wille)合成,它是“共同体”对应到个体心理时的形态。滕尼斯在谈本质意志时,特别强调它的“类”含义,一方面个体的身体脱胎于他所从属的“类”的整体,他的心理也依附于“类”的整体,另一个方面,个体的心理世界囊括了比他的“类”更低的层面,如植物性的意志(被动的感觉)和动物性的意志(主动的欲望)。本质意志背后同时蕴含着个体的身体和心灵自然地生成、成长的过程。
WillkÜr(志愿):它是《共同体与社会》第一版与第二版中对应“社会”的个体心理概念,指个人通过思维确定最高的目的并根据客观条件主动地行动,并非“任意”做某事,而是根据理性规定好的目的、有取舍地做某事。
KÜrwille(抉择意志):它从《共同体与社会》第三版开始使用,取代WillkÜr,是滕尼斯自己造出来的复合词,对应“社会”的个体心理概念。
Gemeinwesen(公社):这是第三卷讨论的核心概念,字面意思是“共同的本质”“共同的生命体”。它是“共同体”在法权意义上的对应者,指一群有机地组织起来的人,这些人遵从习俗和习惯法的规定。滕尼斯论述这个概念的时候,实际上将它历史化地解读为基于共同占有土地而形成的传统父权制家族、乡村和城镇的团体。
一、共同体与社会的理论
1、共同体
共同体的经验形式包括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在意志层面上分别对应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和友谊。这些共同体的形式中都具有父权制气质,秩序依靠首领或身份较高者的威严维持。
在经济特征上,全体成员共同占有土地、劳动工具等财产,每个成员的生产性活动和再生产都是为了增进整个共同体的财产(但是这种财产共有依附于身份等级制,是名义上的共有,财产支配权的完整度取决成员的身份),然后共同享受这些财产。在经济活动上,共同体内部鲜有交换,只有分配;交换行为主要出现在各共同体之间。
在个体意志上,成员受到传统或共同信仰的制约,母语交流成为灵魂之间的媒介,共同体的意志得以最终形成,在共同领会的基础上,成员的行为表现出默认一致的共性。这种“默契”不同于社会中的契约,后者是制作出来的、人为的“一致”,而前者的本质是缄默,其内容很可能无法言说。这种基于意志统一的共同体形式不仅包括男女结合的婚姻与家庭,还有氏族和民族。在这种家庭式共同体的基础上,出现了土地和耕地决定的复合体,如村庄和手工业行会主导的小城镇等。
作为自然形成的有机体,共同体规模的扩张,对应其内部存在着个体成员和次级共同体的分离倾向。在结构上表现为一个原始的首要中心不断向外放射半径直线,在首要中心的影响范围内生成新的次级中心,横向扩展共同体意志的影响范围,纵向影响共同体内的各单元。家庭是充分表现共同体特征的最低一级统一体。
2、社会
滕尼斯在这里以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为基础,借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和术语,展示了一个人为构造起来的社群生活形式:社会。共同体向着抽象理性阶段发展,不仅让人和社会关系变得更为理性,还导致共同体本身的衰落和被社会取代。社会的理论构想人们虽然以和平的方式共同生活和居住,但是他们实质上没有结合,而是彼此分离的。不会产生源于一个先天的、必然存在的统一体的行动。每个人都只是为了自己,并且每个人都处于同所有人对立的紧张状态。每个人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或者受到的伤害最小化),共同参与制定一种能让社会成员达成一致的契约,这种契约必须要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并且在人们最经常参与的社会活动中表现其价值。
由于社会中每个人对财产的独占和独享、以及商人在商品交换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理性的交换与交易渐渐取代了分配,成为最普遍的社会活动。在交易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来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即货币)便成为这种“普遍契约”或“普遍价值”的载体。货币的出现,反映出人们不再只知“使用价值”,形成了更为抽象的、对“价值”的认识。这是每个个体主观意志的交点,在这里,主观的意志获得了概念性的认识,不再仅限于被动的情感和欲望,开始在抽象的层面思考客观关系。这种使社会得以存在的普遍性关系和各种概念却不是人们生来就有的,而是人为构建出来的。由人的意志虚构出的社群生活必然存在许多非自然的、人造的产物。如抽象人格(“人造人”、法人)及其实体(公司、企业等工业组织)支配真实的人(劳动者);债权关系中的信用抵押得以实现;以及资本抽去劳动的价值、以劳动力价格取而代之,进而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商人和资本家不像劳动者那样参与产品的生产过程、和产品有内在联系,商品对他们来说只是用来获得外部物品(货币或资本)的手段和机械力,仅仅具有交换价值,是下一次周转中的准备手段。在商人和资本家的限制下,劳动者只能尽力争取一个维持必要生活消费的劳动力价格。前者是“社会”这种社群生活形式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一方,后者是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一方。我想,这是滕尼斯解释“社会”中政治经济领域诸现象时,使用了马克思的术语、却没有太多批判意味的原因所在。在他看来,这些都来自“社会”在起源时就存在的基因。
二、意志形态的二元对立
滕尼斯将生命的意志分为三种:植物性意志、动物性意志和心灵性意志。植物性意志指生命在外界刺激下保存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是对内的和被动的,关注自身相关的现实存在。动物性意志是生命的欲望和冲动,是一种向外的、改造外部环境与其他生命的运动。心灵性意志则是生命具备用语言交流信息的能力,并在信息交流过程中发展出思维活动的结果,它还使生命通过话语和思维而展现出多样化和特殊化。这三种意志类型逐类演进,同时集中表现为人的本质意志这个统一体。
本质意志对自身的肯定是通过对其他事物的肯定或否定来达成的。本质意志包括三种形式:喜好、习惯与记忆。喜好是一种先赋因素,是人生来就具备的对某些确定对象与确定行动的兴趣,随着感官的发展、生命的成长和繁衍参与到总体意志中,表现为各种基本的需要和欲望;喜好对应植物性的意志。习惯是通过经验产生的意志或乐趣,经验就是日常的练习,具备更多主动性。作为一种后天形成的意志形式,习惯还受不同的先天喜好影响,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它对应动物性的意志。记忆是习惯的特殊的进化,尤为明显地表现在人类身上。它不仅是再生产印象的能力,还是重复合乎目的之行动的能力。记忆使得人类在习惯的基础上把握语言内涵、共享经验,还令感受共同体在时间尺度上的存在得以可能,具备心灵性意志的特征,懂得对自己和他人做出判断(肯定或否定)。
本质意志在经历其各阶段后,发展出了人类的思维,而抉择意志则是人类思维的产物。人类通过对自己思维中的意愿进行排序,并按照目的的等级计划采取行动,是抉择意志的特征。只要我们将任何思想的产物当作一种实存,那么一种观念上的现实就对真正的现实发挥了作用。抉择意志也被区分为三种简单形态:(1)抉择意志与一种对象的选择行动相关联,这种抉择意志的形式被成为思虑。(2)抉择意志被导向了确定的、个别的各个行动,该形式被称为愿望。(3)愿望、决定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于概念同思维本身之间。思维对立于经验的复杂和多变,它造就并把握了简单的、不变的图式,即概念。概念就是一种确定意义的、关于词语之使用的强制性判断,还是一种用来比较、标记种种现实事物及其关系的标准。
抉择意志的总形式包含了本质意志的诸要素,应当被视为思想体系。即由意图、目的与手段组成的体系。最高目的支配着一个人的思想体系,最高目的被想象为未来的、一步步达到的乐趣,它不是可被人们自由掌握的东西,而是区别于人的外在的东西,所有人都期盼着它,这就是幸福。但是,当人们努力争取幸福的时候,人运用自己的抉择意志,以享受、利益与幸福为取向推动自愿行动的产生。不过,自愿正好是人自身的不自由,或者说,因为外来的强制和困境会摧毁自愿,所以自愿就是自我强制。所有抉择意志都包含着一些非自然的和虚假的东西。抉择意志是人为的工具,而本质意志是人的一种自然器官。滕尼斯还将这两种意志形式的二元对立对应到经验中去,分析了两性在禀性、性格与思维方式三个方面上的差异,由于负责繁衍、家政和后代抚育,偏向自然的、涉及本质意志的内容最强烈地存在于女性身上。而与抉择意志关联的品质最强烈地存在于更为主动、对外行动的男性身上,两性都具备这两种意志形态,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两种意志占据的比例逐渐均衡。这种意志上的二元对立在经验现实中还表现在人的不同年龄阶段,以及教养程度不同的社会群体身上。
三、秩序、自然法与道德(这部分我实在总结无力,放上译者在导言中的有关内容orz)
“法是能够做某事或者可能(被允许)做某事的意愿,同必须做某事或应当做某事的意愿加起来的总和……优先权和义务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对应的方面,或者无非是‘法’或‘力’这两个相同的客观实体的不同主观样式。”p94
立足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前提,滕尼斯从法权和政治哲学的角度解析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对立。滕尼斯人为自然法其实经历了从自然到人为的转变,它发端于古希腊的有机的古代文化,经过罗马帝国时期人为制定的罗马法,其理性和普遍性又随着罗马帝国的兴盛,分化成各种特殊法,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中世纪,自然法的处于过渡形态。但是基督教对世界帝国的追求使其召回了罗马文化、恢复了罗马法的发展,加速了古代文化的终结。这个过程的影响不断扩大,人自由地在广泛的地域里流动与混合,每个人都在法的普遍性之下成了普遍者,最热衷于变化、不竭地追逐财富和权力的商人群体成为现代世界的引领者,而近代发明的理性主义的、机械论的自然法则完美地道出了他们的人生观和构建整个世界的理论体系。从精神气质上讲它是罗马法的继承者和“同胞兄弟”。
在这一背景下,共同体的自然法和社会的自然法反映出的是历史进程两端的、互为对反的共同生活的“道理”。滕尼斯构思《共同体与社会》时,曾言及“比较柏拉图的理想国(Politeia)同霍布斯的国家学(Staatslehre)具有十足重要的意义”,他抓住两者的精髓,从历史(古代城邦与中世纪封建—现代商业社会和民主制国家)和思想史(历史主义—理性主义,有机论—机械论)扩展其意义,从私法(第三卷第一章)到公法(第三卷第三章)逐一对它们做了对比性的解读。
探讨私法时,作者形式上采纳了罗马法中关于人法和物权法的分类,人法的实质内容是个体和整体间的权利关系,物权法则是这一关系在财产占有上的表现,滕尼斯立足于第二卷“本质意志”的心理学探讨,提炼出有机的(从属于更高统一体)、目的论的(以统一体的目的作为自身且的)个体,继而将它同共同体理论所揭示的“家庭生活”这一典范紧紧结合到一起,父权制同由整体的身体(永恒不动的房屋和耕地)延伸而来共同占有财产的原则共筑为“家庭法”;与之相反,“抉择意志”刻画的绝对独立的、理性的人格同“社会”的自由交换一道,形成了基于私人之间协定财产关系的“债法”。
两种自然法的内容不止停留于私法层面,它们必然要推及政治体的构建和运作。就像文本安排的从社会学到法权、从私法向公法的过渡的次序,滕尼斯理解政治关键在于政治以社群或广义的社会为根基,共同体的政治体、即公社(Gemeinwesen)建立在自然会聚、天然地服从权威者的基础上,其历史的经典原型是中世纪的封建制,与之相应的是人对风俗的敬畏、对神圣宗教信仰的精神结构;而社会的政治体则是人造国家(Staat),滕尼斯在此重述了霍布斯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状态”的过渡{国家的形成源于自由人的自由集会、合为统一的主权人格,不过在实在的历史进程里,唯有真正占有财富的商人、拥有权力的官僚才是能自由参与政治构建和运作的主体,他们使用人造的科学术语、靠着报刊舆论的手段支配公众的普遍激情。
四、一点想法
滕尼斯在学生时代研究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在自然法的社会学基础部分有许多关于霍布斯的论述。他在写作此书前又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所以在分析社会的经验形式时,引用和借鉴了许多马克思的分析思路。在方法上,他对社群生活形式的构造类似韦伯的“理想类型”,但滕尼斯认为自己提出的“标准概念”早于韦伯,而且认为“观念类型”是一种纯粹观念形态,并非按照所谓的国家的实际发展确定的现实类型(这点我没觉得他和韦伯有太大的出入,可能滕尼斯更为强调从政治哲学的命题演绎出观念类型,并且以概念的方式去理解概念)。
我对滕尼斯关于社群生活的态度也有了新的认识:面对共同体的衰微、社会的兴起,他的态度并不是悲观消极,只是指出社会的表面和平与效能提升之下,个体意志对现实的表象发生了变化,人与人利益出现了本质性对立,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主要靠后天虚构出来、靠基于个体利益的计算维持、短暂而不稳定,且存在社会阶级的对立。因为社会与国家的法在根本上是个体主义的,所以只能尽力维持这种原子化的、机械的生活形态不致失序崩坏,却很难让它变得更为紧密团结。如果想实现社群生活的真正和谐,不能倒退回共同体时代,而是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在个体层面上,劳动者们组织起合作社,为着自己的需求在合作社里消费,并在此过程中感受类似地域共同体或行业共同体的共同意志,发展出各类社团。在国家层面上,将整个商品生产变成国家行政的组成部分,打击寡头的私有财富,但保留商品经济。在民众的经济生活中,国家扮演类似共同体的组织,计划和统制民族经济(即所谓“更广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社团资本主义”),把个体意志纳入社团意志和国家意志,实现团结起本民族成员的目标。
由于我读了新译本,所以阅读过程中没有遇到语义不明的障碍,但是缠绕的概念和严谨繁复的表达常常搞得我晕头转向。因为有阅读韦伯和马克思的基础,第一卷读起来还算顺畅,到了第二卷和第三卷,相对陌生的心理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术语大大拖慢了我的理解速度,很多时候需要边读边在纸上写写画画,才能大概明白滕尼斯的重点是什么。我很敬佩他这种写法:堆叠不同学科的概念后,打通其间的关系,把自己的研究主题放置在一个宏大而连续的脉络里,它是学养深厚、涉猎广博带来的得心应手,能锻炼读者的逻辑能力、开拓人的想象力。不过,脉络再怎么清晰,也难免会被卷帙浩繁拉扯得复杂艰涩。读者需要有打通学科和概念关联的功力,才能真正从勉强跟上、偶尔有些许共鸣,到享受滕尼斯的分析并与之对话。遗憾的是,我现在是花了好久勉强读完,又拖了好久之后才鼓起勇气总结一下。这次只能说读到了皮毛,以后还会再读这本书。希望到时会有更多的感悟与启发,在此之前,我想让自己变成更合格的读者。
最后推荐一下张巍卓版的《共同体与社会》,译者写的导言对梳理全文思路很有帮助。译文的完整度很高,附录包括了各版前言与这本书手稿的导论部分。翻译比林荣远版好太多(我读了十几页林版的做比较后,很庆幸自己读到张版译文),文中的很多注解里,译者对照了不同英译本的内容,对自己的翻译作了比较性的解释。文末附录里还专辟一节,列出对重要概念的译法说明,不可谓不细心严谨。虽然纸书价格比较较贵,但读下来觉得非常值得,建议要读的朋友购入此版支持。
另外,阅读期间看到一篇秦晖老师的相关讲稿(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评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觉得有助于把滕尼斯的理论观点和中国情况放在一起对比,完善我们分析国内社群生活形态演变的思路。附链接如下:http://www.aisixiang.com/data/35582.html
《共同体与社会》读后感(三):张巍卓读《共同体与社会》︱浮士德消逝:古今之变与现代人心
滕尼斯的二元结构
如同标题明确呈现的那样,《共同体与社会》最鲜明的特征莫过于它采取了二元对立的结构、围绕着“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这对彼此相对的概念展开讨论。全书的主体部分由三卷组成,依次是“关于主要概念的一般规定”(共同体的理论与社会的理论)“本质意志与抉择意志”(第一、二版题为“本质意志与志愿”)“自然法的社会学基础”(第一版题为“自然法的序幕”),它们分别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共同体”与“社会”之间对立的意涵:第一卷在社会学的层面上刻画了两种人类结合的关系形态以及它们各自形成的共同生活秩序;第二卷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对应上述两种共同生活类型的个体心理事实与原理;第三卷则透过法学和政治哲学的视野解读了两种关系类型背后的规范以及共同生活的法权基础,其中又包含了双重的自然法脉络:第一重是私法层面的“共同体”或“社会”内部的人与人(“人法”)、人与财产(“物权法”)之关系的诸规范;第二重则是公法层面的、作为整体的共同体与社会为了维持自身所形成的法权秩序(“公社”与“国家”)。
全书卷与卷之间不仅相互对应、互作诠释,而且伴随着文本的展开,内容逐步变得更丰盈。不过关于三卷之间的关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论述心理机制的部分被安排在第二卷,然而从理解的次序来说,第二卷不仅占据着最首要的位置,而且统领其它两卷。滕尼斯认为,考察人的行动以及相互之间结成的各种关系,必须以理解人心、理解个体如何看待他所从属的类为前提,不实在地体会人在不同经验世界中的本能、欲望、情感和理智,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展开社会学和法学的思考。
《共同体与社会》,[德]斐迪南·滕尼斯著,张巍卓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出版,616页,89.00元
(一)
共同体vs.社会
在最为人熟知的第一卷的开篇,滕尼斯即提出了“共同体”与“社会”这对概念,它们呈现出最朴素的意义,前者的本质包含着“真实的与有机的生命”,而后者则是抽象出的“想象的与机械的构造”。可以说,滕尼斯对它们的社会学阐释展现了两重理论特征:一方面,它们分别对应古代和近现代的两种总体文化形态,共同体的原型囊括了从古希腊-罗马的民社与城邦(滕尼斯在早期罗马城邦、共和国同罗马帝国的性质之间做了非常严格的区分,前者本质上仍然是共同体,由于罗马帝国的扩张、古典德性在帝国时代的败坏以及罗马法对所有臣民的“拉平化”的效果,后者实际上变成了社会的国家,滕尼斯也在借罗马帝国影射德意志帝国)、中世纪的日耳曼封建王国直到早期近代的自由市镇的漫长的欧洲历史的诸阶段,社会的历史原型则是近代以来的商业社会与国家;另一方面,他又并非按照纯粹历史的方式阐释这对概念,而是遵循着独特的历史哲学的思维进路、由简单到复杂地揭示它们的层次。
论述“共同体”时,滕尼斯接受了这个概念原本所指的“协同性”关系的意涵,进而创造性地为它注入历史的意义:首先,他用从母权制之家向父权制之家过渡的历史展现了作为“共同体”的人类最初的关系形态,家庭里的母子关系呈现了人类意志完美统一的原型,因为它最直接地体现为身体的衍生或本能的结合,但是这一纯粹自然的关系最终要让位于由精神或心灵主导的关系,父子关系由于其支配的结构表现了最完善的共同体关系;简单的家庭关系将遵循从自然到心灵的脉络,衍生出更复杂的共同体关系,它们是血缘共同体(如家族、氏族、宗族和部族)、地缘共同体(如乡村社团)与精神共同体(如行会、兄弟会);同样,这些关系以及由它们构成的生活秩序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们必然同以“土地”为核心的物质条件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不同的组织结构和活动形态。滕尼斯在讲述这些衍生的共同体时,从不同的历史原型做了对应性的解读,谈及家(Haus)或家族时,他尤其受法国历史学家库朗热关于古希腊-罗马的家神崇拜与祭祀论述的影响,勾勒出“父权”支配下的、以灶火和餐桌为中心的家族日常生活景象;谈及乡村社团时,他以基尔克笔下的中世纪日耳曼封建制下的村庄作为典型背景,指出领主依靠强力和命令确保佃农的服从,佃农们则在领主的采邑或公共地上共同劳作;谈及精神团体时,他用中世纪以至近代早期市镇中的行会为对应者,行会里依靠师傅向徒弟传授技艺、指导人生,形成了牢固的精神纽带,他们过着休戚与共的生活。然而在滕尼斯看来,无论哪种衍生的共同体形态,皆植根于家庭这一典范,家庭天然产生了“共同领会”或“默认一致”的精神,它内在的母性气质和父性气质亦构成了塑造诸共同体关系的原初要素,这些要素彼此交缠,以不同的力量比例、结合方式形成了各种共同体的关系 。
《共同体与社会》的不同英译本
同共同体完全相反,滕尼斯将社会置于现代市民社会的视野,其出发点是断绝了一切自然纽带的、绝对独立的个体。展开论述“社会”概念时,滕尼斯沿着霍布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与马克思指引的理论方向,从人格、财产到制度,对“社会”概念做了逐步推进。在他的笔下,现代个体的基本处境就是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个体间本质上保持着彼此否定的态度;不过他随即以政治经济学的方式疏解自然状态的极端紧张性:社会之所以可能,或者说在这种处境下个体仍然愿望同他人的结合,就在于他永远希望获得比现在手头更好的东西,故而他会同他人交换,同他人缔结契约,在观念里造出了一个共同的、虚构的人格;相对于承载共同体生活的永恒土地,这一抽象人格或社会的外化标志就是永不停止流动的货币,以货币的持有为唯一标准,社会不断地分离为商人与劳动者,前者是社会的主人,而后者则是社会的奴仆;从商人与劳动者的对立出发,滕尼斯追随马克思的脚步,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领域深入剖析了社会具体的制度运作,不过,无论它们表现为何种特殊形态,社会的根本原则始终是商人与劳动者的分裂,商人追逐货币、在整个世界范围里自由流动,而劳动者则是社会这一“无生命的巨魔”的依附者。
(二)
本质意志vs.抉择意志
在滕尼斯看来,要真正理解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就必须深入到两种不同的人心世界,本书第二卷既是第一卷在心理学层面的对应者,也由第一卷的宗旨指引、展现出一套以行动(Tätigkeit)为导向的心理学体系。遵循从早期近代形而上学直到德国唯心论哲学的一贯传统,滕尼斯选择用“意志”概念指称人的全体心理事实及其活动。在此基础上,所谓“本质意志”(Wesenwille)和“抉择意志”(Kürwille)皆为滕尼斯本人自创的概念,它们的实质差别在于:前者是一个有机体的心灵结构,它自然地源于身体所出的有机体,而且是不断生成着的东西,其中的各种情感要素(包括思维)相互关联且都从属于心灵整体,而这个心灵整体亦从属于更高的统一体;相反,后者并不是自然的,它纯粹由思维创造出来、按照思维的指示做决定。
最初,“本质意志”与“抉择意志”看似直接便是“共同体”与“社会”的对应者,然而随着作者详细地铺展它们的内容,它们实际上呈现出更广阔的理论解释空间。尤其当他根据从自然到精神的脉络,依次用“喜好”“习惯”“记忆”的机制表述本质意志的意涵时,本质意志已经跃出第一卷的“共同体”概念所设定的历史背景,变成普遍的心理世界,这不仅表现在滕尼斯调动大量现代的理论资源,充分地同霍布斯、斯宾诺莎、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和斯宾塞等思想大家展开对话,甚至运用时下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尤其从本质意志最终指向“良知”(Gewissen)这一目的而言,他表露了同德国古典主义相契合的人文理想,而非意在单纯刻画古代人性,而且在接下来的“对二元对立的阐释”和“经验的意义”两章里,本质意志与抉择意志之间的对立被置于个体心理世界的内部,作为两种对立的精神气质,它们以不同的比例关系融合于我们每个人的“当下存在”(Dasein),每一个体都经历着浮士德式的命运抉择;进一步地,滕尼斯甚至将对立扩展到社群生活,指出在迄今为止的任何时代,本质意志与抉择意志间的对立都表现在女人与男人、青年人与老人、俗众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心理以及行为方式当中,它们彼此间的矛盾和斗争塑造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如此一来,本质意志与抉择意志各自投射出的心理世界的对立,既跨越了纯粹的历史思维,又为我们打开了思考现实和历史之复杂处境的大门。
位于胡苏姆的滕尼斯半身像
(三)
共同体的自然法vs.社会的自然法
立足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前提,本书第三卷从法权和政治哲学的角度解析共同体与社会间的对立,这一卷既是滕尼斯酝酿时间最长久的部分,也是前两卷的思想积淀、综合的成果。他以“自然法”这一统摄法与政治的根本原则为切入点,然而他又并非以某一特定时代的观念看待自然法的概念,而是延续了从孟德斯鸠直到黑格尔的总体历史观,并遵循第一卷奠定的社会学前提,将自然法视作古今流变中的“人们共同生活和共同思维之原始的、必然的产物”,因而此卷被命名为“自然法的社会学基础”。
在滕尼斯看来,自然法的“自然”之意经历了从自然到人为的转变,发端于古希腊的有机的、目的论式的古代文化到罗马帝国时期被人为制定的、理性的、均一化的罗马法裂解,其后在罗马废墟上继起的基督教文明对世界帝国的渴求促使它重新接纳罗马世界法,加速了古代文化的终结,这个过程的影响不断扩大,人们混合到一起,每个人都成了普遍者,人自由地在广泛的地域里流动,最热衷于变化、不竭地追逐财富和权力的商人群体成为现代世界的引领者,而近代发明的理性主义的、机械论的自然法则完美地道出了他们的人生观和构建整个世界的理论体系。从精神气质上讲,它是罗马法的继承者和“同胞兄弟”。
于是,共同体的自然法和社会的自然法要讲述的便是历史进程两端的、互为对反的共同生活的“道理”。滕尼斯构思《共同体与社会》时,曾言及“比较柏拉图的理想国(Politeia)同霍布斯的国家学(Staatslehre)具有十足重要的意义”,他抓住两者的精髓,从历史(古代城邦与中世纪封建—现代商业社会和民主制国家)和思想史(历史主义—理性主义,有机论—机械论)扩展其意义,从私法(第三卷第一章)到公法(第三卷第三章)逐一对它们做了对比性的解读。
探讨私法时,作者形式上采纳了罗马法中关于人法和物权法的分类,人法的实质内容是个体和整体间的权利关系,物权法则是这一关系在财产占有上的表现,滕尼斯立足于第二卷“本质意志”的心理学探讨,提炼出有机的(从属于更高统一体)、目的论的(以统一体的目的作为自身目的)个体,继而将它同共同体理论所揭示的“家庭生活”这一典范紧紧结合到一起,父权制同由整体的身体(永恒不动的房屋和耕地)延伸而来共同占有财产的原则共筑为“家庭法”;与之相反,“抉择意志”刻画的绝对独立的、理性的人格同“社会”的自由交换一道,形成了基于私人之间协定财产关系的“债法”。
当然,两种自然法的内容不止停留于私法层面,它们必然要推及政治体的构建和运作。就像文本安排的从社会学到法权、从私法向公法的过渡的次序,滕尼斯理解政治关键在于政治以社群或广义的社会为根基,共同体的政治体即公社(Gemeinwesen)建立在自然会聚、天然地服从权威者的基础上,其历史的经典原型是中世纪的封建制,与之相应的是人对风俗的敬畏、对神圣宗教信仰的精神结构;而社会的政治体则是人造国家(Staat),滕尼斯在此重述了霍布斯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状态”的过渡,国家的形成源于自由人的自由集会、合为统一的主权人格,不过在实在的历史进程里,唯有真正占有财富的商人、拥有权力的官僚才是能自由参与政治构建和运作的主体,他们使用人造的科学术语、靠着报刊舆论的手段支配公众的普遍激情。
古今之变与历史的辩证法
这样,《共同体与社会》将发端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臻于顶峰的“历史主义”与“理性主义”世界观间的对立用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学的方式充分展现出来,这种对立不仅贯通欧洲历史的全局,而且囊括了社群生活的所有领域。然而,正如滕尼斯构思本书时表露的那样,理解它们间的“转化”比仅仅呈现事实更重要,这一点是单纯的历史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没有认识到的关键所在,故而它们各自只讲出了片面的真理。他在本书第一版前言里指出,本书要结合经验主义和辩证法,如果说前者的使命是将存在者及其现实的运动变化的规律揭示出来,那么与之相对,后者则意味着将“非存在者”必然地视作真正的“存在者”,看似矛盾的两方面交织到一起,蕴涵着所谓“转变”的两重理解方向:其一是古今之变背后的本质;其二是现今时代自身中孕育出的否定力量与未来的可能趋向。
《近代的精神》,1935年。
《共同体与社会》讲述的历史无疑是共同体正在消逝、社会正在形成并且走向繁荣的历史,这一过程既包含着法权、宗教、经济生活等多方面理解的线索,它本身也非遵循一条简单的、直线式的路径(在晚年未完成的《近代的精神》[Geist der Neuzeit, 1935]里,滕尼斯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发端于古希腊-罗马的“家—城邦”的共同体式的古代文化在罗马帝国陨落;之后从罗马废墟上成长起来的日耳曼诸民族源于自身的古老传统或早期罗马的影响,构筑起“家族父权制—庄园领主制—市镇行会制”的体系,因而延续了古代的共同体文化,然而与此同时,不断形成的基督教的统一信仰、大公教会及其支配下的世俗帝国对世界统一秩序的渴望使它接过了罗马帝国的权柄,猛烈冲击着区域性的古代文化遗产,为现代均一化的、理性的个体和商业社会的诞生扫清障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理性主义自然法是罗马法的继承者,此后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德国历史法学派挑起日耳曼法与罗马法的争讼,本质上正是以日耳曼的“民族精神”或共同体精神同普世的国家与社会对抗。
历史演化的必然趋势是社会的胜利,相较于历史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滕尼斯更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然而正像他在本书第一版结论引用的古希腊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的名言,“任何身体和政治体都会经历自然的成长、全盛直到衰落的过程”,社会本身就孕育着自我毁灭的种子,而他恰恰从社会的内在逻辑出发,在“个体—社会—国家”间环环相扣的关联中抓住了批判的要害:不像浸染在共同体文化中的个体,社会人不再自然地感到自己从属于一个更高的整体,更不必说对整体负有什么天然义务,他变得“不安分”,完全成了孤独者,只基于自己的利益行动,在一个所有人皆如此的世界,所谓的关系、组织甚至国家,都不过是个体人为地制造出的谋利工具,如此人性造就的社会也将走到濒临死亡的一刻,那些占有财富的资产者、手握权力的官僚携起手来,希望利用他们制造的国家机器,最大程度地控制商业、榨取劳动者的价值,与之相对,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城市劳动者却被抛入贫困乃至绝望的生活,他们在辛苦的肉体劳动和精神的麻痹间耗尽生命,一旦被压迫的劳动者认识到他们不幸的根源,通过自觉地联合,发动暴动和革命,那么迄今为止的文化便消亡了。
浮士德
滕尼斯关于社会前景的悲观预判,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俾斯麦治下的德意志帝国的忧虑甚至厌恶,循着青年时代的偶像尼采的脚步,交出了这部“不合时宜”之作。然而他又并非像那些给他扣上“社会悲观主义”帽子的人所说的那样止步不前,而是以本书起点、思考改造社会的未来进路,就此而言,共同体既是对立于社会的历史文化,更是用来反思社会的理论参照系。批判首当其冲便是针对现代人的心理世界,相对于自然情感同人造理性分离的处境,共同体式的本质意志既意味人的自然起点,更指向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的理智与情感的谐和,自身同所属的更大统一体内的情感联系。滕尼斯的人性理想是魏玛古典主义“浮士德”精神的回响,歌德吟诵的人生完整的教化历程、歌颂的女性羞耻感和礼法,席勒反专制君主的呐喊和美育的思考在此合为一体,为重塑现代人的伦理品性提供了理论出发点。此后,滕尼斯关于家庭、教育、合作社、政党与议会一系列改革计划,都是在《共同体与社会》曙光照耀下绽开的花朵。
《共同体与社会》读后感(四):方维规:“形成的”和“做成的”——重评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
此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9年第2期第328—341页。
摘 要
在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热议“社群主义”亦即“共同体”之时,一个曾被长期遗忘的社会学大师及其学说又被重新发现。德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滕尼斯的传世之作《共同体与社会》(1887),不仅是德国社会学界提出的第一个大的综合体系,也是欧洲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著作和现代社会理论的正式登场。在西方语言中,“共同体”与“社会”原本就是同义词,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滕尼斯开创性地将“共同体”与“社会”作为对立概念引进社会学语汇,因此而成为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中重要的关键词设置者。他的追求是,从哲学层面为年轻的社会学提供概念工具和思考范式,用明确的概念设置及其阐释来精准把握社会现实的两极,即自由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与历史形成的“共同体”。滕尼斯借助共同体与社会之显赫的二元框架来叙写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尽力从这两个顶层概念来把握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他的批判性社会哲学把社会性概念分解为“做成的”社会与“形成的”共同体:共同体是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暂时的、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当被理解为活的有机体,社会则是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与此相对应,他区分了两种“人之意志”,即共同体之实在的、自然的“本质意志”与社会之思量的、人为的“选择意志”。对于意志形式的探索,是《共同体与社会》试图向人类学方向拓展社会学的核心部分。无论是共同体还是社会,无论是本质意志还是选择意志,都是理想型概念,旨在强化概念和结构性分析。在滕氏“共同体—社会”理论中,共同体的本质是人的整全性,社会的本质则是人的残缺性。当人类步入“半现代”(贝克语)的今天,重新评价滕尼斯的著作亦即共同体思想,无疑仍能够见出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
滕尼斯 共同体 社会 本质意志 选择意志
“共同体”曾是现代晚期人文社会科学中一个颇具影响的概念,也是国际学术界颇为关注的话题。20世纪晚期兴起于西方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这一哲学“运动”,高举“复兴共同体”的大旗,在美国社会学家埃兹奥尼(Amitai Etzioni)的著述中,能够见出赞美共同体的纲领性文字。他认为,西方世界正处于极端个人主义的冰冷时代,因而期盼共同体的温暖和人性关系的复苏。当然,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桑德尔(Michael Sandel)那样的思想家。或者,人们还会想到鲍曼(Z. Bauman, 1925—2017)的著作《共同体:在风险社会寻找安全》(2001)。对共同体的渴望是一个时兴现象,因为人们对各谋其利、貌合神离的现代生活不满,传统共同体失去之后的社会不能实现“幸福生活”,所以渴望新的开端和社会新变,渴望共同体精神和价值。在当代社会科学中,尽管人们使用“共同体”概念时颇为谨慎,但由于它是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包容最广的概念之一,因此,要论述现代“共同体”概念,滕尼斯(F. Tönnies, 1855—1936)是无法绕过的。他的《共同体与社会》不仅是德国社会学界所提出的第一个大的综合体系,也是欧洲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著作和现代社会理论的正式登场。这部著作也使他成为西方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
一 一个曾被长期遗忘的大师及其学说
尼采(F. W. Nietzsche,1844—1900)的好友、瑞士文化史家布克哈特(J. Burckhardt, 1818—1897)在其名著《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文化》(1860)中说道:
[欧洲]中世纪人的意识有着双重视域,一面朝着世界,一面朝着自我内心,如同戴着共同的面纱,如同在梦中或者半醒状态。面纱由教义、儿童般的拘束和妄想编织而成,透过面纱所看到的世界和历史,呈现出奇异的色彩;人只把自己看作族类、生民、派系、同盟、家族,或其他什么共同属性。这一面纱最早在意大利被掀开,人们开始客观地观察和探究国家,甚至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同时,主体强势而出,人成为精神个体,并这样看自己。
布克哈特让人们看到,在西方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不过,布克哈特所展示的中世纪情境,并未完全把19世纪排除在外,他的论断对时人和后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实,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前和之后,还有不少历史要端:古典哲学、基督教、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等。然而,文艺复兴运动无疑是一个巨变和觉醒的标志,其显著特征是发现了“人”——作为主体的人,谋求成为世界的主人,欧洲因此踏上了征服世界的征程。
由此,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之间发生了断裂,那些地方还沉浸于家族、等级或部族等原初状态。欧洲文明不仅意味着主宰一切,还催生自由——摆脱了传统拘囿的自由。可是,这要付出人与人的隔阂、特别是孤独的代价。这样的代价不是太高了吗?这种孤独的自由意义何在、走向何方?最终会是空无和绝望吗?所有贪欲、统治、压迫,同时也是破坏,对自然的破坏和对人的摧残,到头来不都是“文明人”的自鸣得意、自欺欺人吗?是否要催生新的共同体来抵抗和克服负面发展?
这类问题在西方早就不断有人提出,尤其在德国。现代社会学兴起之时,滕尼斯于1887年发表《共同体与社会》。该书第一稿是作者1881年在德国基尔大学递交的教授资格论文,出版时做了重大修改。它无疑是(德国)社会学的创始文献之一。对滕尼斯和其他早期社会学家来说,高歌猛进的工业化是其发展社会学概念的背景,不少社会学家都从历史变迁中提炼出自己的核心观点。滕尼斯的追求是,通过“共同体”“社会”这两个概念,从哲学层面为年轻的社会学提供概念工具和思考范式,如他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所说,他要对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做出全新的分析,用明确的概念设置及其阐释,精准把握社会现实的两极,即自由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与历史形成的“共同体”。他认为,新的“社会学”的任务是,研究人们为何相互“接受”或“认可”。按照霍布斯(T. Hobbes, 1588—1679)的观点,人与人作对才是常理。滕尼斯则认为,人的相互接受,要么为了集体利益,即共同体的福祉,要么出于算计的个人目的而参与社会行动,例如在一个股份公司。显然,滕尼斯的问题域是宽广的,他要通过“共同体—社会”来理解世界及其发展趋势。他所追求的社会理论,竭力为社会科学寻找哲学以及意志理论所涉及的心理学理由,并且融合了历史哲学和法哲学因素。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分是社会类型研究的经典范式,社会学家、哲学家滕尼斯对“共同体”与“社会”的探索颇具代表性。他试图通过这对矛盾概念,细致阐释社会现实。这位独立的德国社会学的缔造者试图在不同著作中,尤其在《共同体与社会》中,阐释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他区分了普通社会学与特殊社会学,又将后者分为纯粹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和经验社会学。他把“共同体”“社会”看作纯粹社会学的基本范畴,尽力从这两个顶层概念来把握人类生存和发展。换言之,他将共同体和社会置于人类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然古朴的共同生活,第二阶段是文明造成的人为产物: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他不是从法学或历史学视角考察社会,而是注重人对自己和人际关系的思考和感受,赋予“共同体”与“社会”这对概念以不同的社会能量。
《共同体与社会》发表之后,并未得到足够重视,甚至“默默无闻”,直到1912年第二版以后,才被誉为“社会学”这个新学科的里程碑和典范著作,并在滕氏生前出过八版。他无可非议地被看作德国社会学的大师,但大师的美名或多或少也缘于他于1909年创办“德国社会学协会”,是该协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并自1922年起担任首任会长,直到1933年纳粹上台,他被解除大学教职和社会学协会会长职务。这位当时享誉世界的学者,唾弃纳粹专制,鄙视纳粹蛊惑人心的“人民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口号;令他特别愤怒的是,纳粹盗用了他的“共同体”概念。在德国社会学的缔造者中,他也是唯一目睹了希特勒的上台亦即魏玛共和国末日的人。
滕尼斯生前声名显赫,但在1945年之后的德国几乎被人遗忘。在社会学和哲学领域,他的著作都未得到系统研究;不仅如此,人们甚至不知道他一生著述的详情,阅读滕尼斯往往只是出于历史兴趣。在社会学领域,不少人把他看作哲学家,并认为哲学家对社会学没有发言权;可是哲学界把他看作社会学家,几乎未从哲学方向对他进行研究。他被遗忘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提出的“共同体—社会”二分法在一百年前风靡一时,后来成为教育阶层尽人皆知的常识,以致人们不再记得、甚或全然不知这个二分概念的“版权”归属。只是到了20世纪晚期,滕尼斯才与齐美尔(G. Simmel, 1858—1918)、马克斯·韦伯(M. Weber, 1864—1920)齐名,被公认为德国社会学的缔造者之一,甚至被视为德国现代社会学的鼻祖。1980年代以降,滕尼斯重又得到德国社会学界的理论关注,《共同体与社会》又赢得不少读者,二十四卷点校本《滕尼斯全集》也在编纂之中。
与齐美尔、韦伯一样,滕尼斯的学术事业横跨不少专业(韦伯曾做过他的助手),这不仅有利于他转向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也为探讨其他问题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在其丰硕的学术著述中,从《霍布斯的生平与学说》(1896)到临终前的《近代精神》(1935),他专注于使其赢得社会学大师称号的一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即诞生于西欧和北美的近代社会,为何有别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社会,而且也有别于本土传统共同体。这个问题,在滕氏著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在《社会学导论》(1931)中,他针对《共同体与社会》出版之后德国社会学界的一些理论探讨和论争,又进一步论述了“共同体”“社会”及其相关概念。
在他眼中,近现代的思想标识,深深地打上了宣告理性和启蒙将要来临的霍布斯的印记,以及在他看来比历史学家更深邃的孔德(A. Comte, 1798—1857)的烙印。另外,他认为近现代思想亦深受斯宾诺莎(B. d. Spinoza, 1632—1677)、莱布尼茨(G. Leibniz, 1646—1716)、康德(I. Kant, 1724—1804)、叔本华(A. Schopenhauer, 1788—1860)和斯宾塞(H. Spencer, 1820—1903)的影响。“共同体—社会”之命题,既涉及类型问题,也与社会发展史有关。就类型而言,滕尼斯借助共同体与社会之显赫的二元框架来叙写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并对二者做出明确区分,以彰显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就发展史而言,他感兴趣的问题是19世纪受到进化论思想影响的社会发展、近代社会的起源及其可能命运,以及与之相对的共同体的共生共存。
滕尼斯所做的显然是社会学研究,但分析进路是抽象思考,与哲学不分畛域,他称之为“概念思维”,并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告诫那些“不习惯概念思维的人”,不要对“这类问题”妄下判断。他又在1912年的第二版“序言”中说,这本书是为哲学爱好者而写的。也是从第二版起,该书的副标题改为“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尽管抽象思维或许会导致“虚无缥缈”,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诟病作者,尤其是对处于萌芽期的社会学来说,这类概念思维或曰抽象探讨,很可能是唯一取径,往往能给人启迪。但在进行“哲学思考”的同时,滕氏也是德国最早主张让社会学独立于哲学、将之建设为独立学科的学者。
二 “共同体”与“社会”概念小史
“社会”与“共同体”是社会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学的基本术语。这对概念与另一对概念“国家—社会”一起,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尤其在德国)的语言政治和思想政治中具有中心意义。在深入探讨滕尼斯的“共同体”和“社会”思想之前,有必要先对这两个概念作一简要的历史语义梳理。
在西方语言中,“共同体”与“社会”原本是同义词。拉丁语中有各种“共同体”(“社会”)的相近表述:“civitas” “communitas” “communio” “congregatio” “societas”等,主要用于宗教语境,如“神圣共同体”(communio sanctorum),表示所有受洗者都是教会这一心灵共同体和耶稣之神秘躯体的一部分,且包含活着的和过世的信徒。目前已知的最早宣扬生死均属耶稣共同体之信仰的表述,见于公元4世纪的圣尼西塔斯(S. Nicetas,约335—414)所著《慕道者须知六书》(Competentibusad baptismum instructionis libelli VI)。表示宗教“共同体”的“societas”,也已出现在公元5世纪,即信仰共同体或(死者和在世者的)神秘共同体。16世纪,圣依纳爵·罗耀拉(S. I. d. Loyola, 1491—1556)创立“耶稣会”(Societas Iesu)。直至进入19世纪之后,二者亦无明确的区分,常常可以互换。
“共同体”概念可追溯至古希腊,对应于古希腊语“κοινωνία”。这是一个颇富神秘祭礼色彩的词语,柏拉图(Πλάτeων,前427—前347)最早将之生造成哲学词语,从而成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前384—前322)哲学思想中的基本元素。柏拉图在《国家篇》(Politeia,又译《理想国》)中强调,人依赖于共同生活的人,因而离不开“城邦”(polis)共同体。这一思想中已能见出后来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断: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政治动物”(zoon politikón)概念也能译为(理解为)能够组成共同体的生物。亚氏对人之本质的考察,直接将人置于不可或缺的社会关联之中。在自然哲学著作《动物志》中,他把人与蜜蜂、蚂蚁一样划归群居动物,且有共同目的和集体行动的能力。然而,人又不是一般动物,人有明显的政治性,这在亚氏《政治学》中得到充分解说。与一般动物完全不同的是,人的协作不只是为了生存和满足基本需求。城邦的发展旨在更高的、伦理上的追求,即幸福人生和友谊。人是会说话的、理性的、讲伦理的动物,只有在政治共同体中才能发展其潜能。
在现代和前现代关于“共同体”概念的诸多探讨中,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总是一个重要焦点。“政治动物”之说的阐释史极为丰富,而且常常是见仁见智;都从亚氏观点出发,但因语境和兴趣不同,“人”被说成“群居的”“社会的”或“共同体的”。尤其是拉丁语对亚氏“ζὠοv πολιτικόv”(政治动物)的翻译,如辛尼加(L. A. Seneca,约前4—65)或阿奎那(T. Aquinas, 1225—1274)的解读,使这个概念的语义发生了偏移,人不再总被看作“政治动物”,而是“社会动物”(animal sociale)。对这种阐释的接受史,逐渐使这个概念本体化,被赋予天然特性。本体论思维强调原始的、先在的共同生活之基本结构,即人人都分享的共同体形态,这也使这个概念的政治性维度不断褪色乃至消隐。
近代以来的格劳秀斯(H. Grotius, 1583—1645)、莱布尼茨、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或洪堡(W. v. Humboldt, 1767—1835),都在不同语境中论述了人的基本共处形态。嗣后,即便面对历史的快速发展以及别样的政治关联,马克思(K. H. Marx,1818—1883)也强调了社会性的先在状况。尽管工业化破坏了个体的共同体生活根基,马克思依然不忘社会本体论思维传统的价值:“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总的说来,在社会理论传统中,社会性的优先地位一直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本体意义上的整体论几乎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共识。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最迟自霍布斯起,另一思想传统也很强势,即与人的天然群体观念相对立的个人主义,并由此生发出的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在契约理论的建构中,人们主要从个体考察和评判社会整体,个体既是出发点也是方法论支点。
三 滕尼斯开创性的二分模式:共同体与社会
在社会学中,共同体被界定为“人之群体建立在自然的(有机的)、相同出身的、观念相似的或共同命运和共同追求基础上的同本共在,与理性的、追求特定目的的社会相反”。社会是由于外在目的而聚拢的,是包罗甚广的整体。人与人的结盟是社会学的研究主题之一。滕尼斯认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性的学说,“认可”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人们相互认可,建立联系,便是社会性行为;若互不来往,甚至相互斗争,便无社会性可言。根据这一界说,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协作都是社会性的。至于在什么情况下、为何目的走到一起,这不是首要问题。一个强盗团伙,一个家庭,一个股份公司,这些结合都是社会性使然。纯粹社会学中的“社会性”概念,不包含对结盟动机的道德评判。
然而,各种同盟可以根据其性质、紧密性、持续性来分类。有些结合,比如家庭,相对持久而紧密。即便一个人恨其父母而离开家庭,却依然属于这个家庭,这一联系永久存在。而股份公司则属于另一类联盟,股东之间的结盟时间可以很长,却不很紧密,他们甚至不必相互认识,只是对利润的兴趣将他们聚到一起,但他们可以随时离开。这一现象见之于股市,股东可以随时因为盈利或止损而卖出股票。
对于社会概念的早期思考,已见之于17世纪的社会哲学,后来经“社会学”延续至今;并且,人们还在不断思考相关问题。霍布斯(《利维坦》,1651)、卢梭(《社会契约论》,176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21),都是出自不同时代的重要思想资源。将三者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著述让人看到,人需要牺牲部分个体自由,才能分享新获得的共同自由。谁接受这种交换,谁就是社会的一员。社会被看作有目标的契约联合体,这一基本设想在总体上延续至今。即便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批判社会状况,但他们并未否认“社会”概念本身,他们主要钻研的是体现于经济的社会需求。
直至19世纪晚期,滕尼斯才开创性地将“共同体”与“社会”作为对立概念引进社会学语汇,用以界定人际关联的两种类型。他提出的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分模式,即两种理论传统的对照,很能让人想到不少思想先驱可能对他产生的影响,事实也是如此。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对他的重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他曾深入钻研过霍布斯的政治理论,著有研究霍布斯的书籍和论文,被许多人视为重新发现霍布斯的学者。他认同霍布斯的不少说法,例如霍氏在《利维坦》中所描述的理性、自私的世界中的生存状态是“孤独、贫困、污秽、野蛮又短暂的”(solitary,poor, nasty, brutish and short)。可是,滕尼斯的基本立足点是对霍氏自然法(人性的自然状态或性恶论)的批判:霍氏在《利维坦》中把“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every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描述成争夺利益的普遍竞争和自然状态;滕尼斯则认为,那并非生存的原初状态,而是私有制导致社会机制的解体或退化后的产物,即理智权衡的后果。从历史发展或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来看,共同体是原初的、在先的,社会则是后来的,是共同体衰败后的产物,或是社会所要摧毁的。
马克思对滕尼斯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滕氏“社会”理论直接依托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批判。他不仅在《共同体与社会》不同版次的“导言”中,而且还在其他著述中一再申明,他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那里得益匪浅。该书第一版副标题即为“论经验性文化形式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与19世纪欧洲的社会运动有着直接关联。他的观点很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劳动分工和异化是市民社会的标识。《共产党宣言》严厉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摧毁了所有田园传统,“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一切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滕氏赞同马克思的观点,认为从经济视角观察社会关系是最重要的视角。正因为此,他认为马克思是最引人注目、最深邃的社会哲学家(第一版“导言”)。滕氏对“社会”经济秩序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共同体与社会》的一些段落几乎就是马恩对资本主义分析的改写。滕尼斯的学生雅科比(E. Jacoby, 1904—1978)认为,撰写《资本论》的经济思想家马克思,不会是那个撰写《共产党宣言》的“共产党人”,这一点对滕尼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于该书第一版的副标题,需要指出的是,滕氏从经验层面论述的“共产主义”,只是共同体的一种文化形式,例如家庭共同体或教会共同体,“社会主义”则是社会的文化形式。他是要把不同所有制的意义扩展至人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第三版“导言”)。换言之,滕尼斯并不崇尚《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共产主义。他认为,天然的社会基本结构是共产主义的,而现实的、正在形成的结构是社会主义的(第一版“序言”);另一方面,他试图证明近现代的自然法是关于“社会”的理论,必须与历史的、有机的“共同体”理论区分开来。他要借助这种“理想型”区分来把握人类共同生活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并且,滕尼斯的总体倾向,是在向后看“共产主义”,回望那失去的古老而和睦的共同体。
Image
《共同体与社会》第一版扉页
查考德意志的共同体思想传统,可以发现,赫尔德(J. Herder, 1744—1803)率先将契约国家排除在共同体之外,滕尼斯更把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排除在共同体之外。他们都从人的整全性出发,批判启蒙理性对整全人性的摧残,赞美德国人向来珍惜的文化道德传统,并希冀共同体精神的延续或再生。在滕尼斯身上,人们很能见出德国人似乎历来怀有的“反启蒙”倾向和浪漫主义。在他看来,启蒙在其解放思想、摆脱枷锁的同时,始终远离主导性生活形态,否定传统机制和思维方式,而那正是历史形成的、天长地久的东西,更接近自然本性。就社会伦理而言,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共同体理论,是启蒙运动强调个性的契约理论的重要对立模式,强调社会关联的伦理优先性和人的整全性。在滕氏“共同体—社会”理论中,共同体的本质正是人的整全性,社会的本质则是人的残缺性。不难理解,《共同体与社会》的作者常被看作德国特有的、与西欧理性主义的社会哲学格格不入的社会学之代表人物,并以此加载“反西方的”德意志观念形态之特殊发展的历史。
滕尼斯常被视为文化悲观主义者,他的充满怀疑精神的历史哲学,早在19世纪就显示出后来霍克海默(M. Horkheimer,1895—1973)、阿多诺(T. W. Adorno,1903—1969)那样辩证看启蒙的深邃目光。于是,“共同体”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与“社会”对立的概念。对共同体的渴望亦即对现实的批判,往往是对有待实现的美好未来的憧憬,这时常与追忆过去的好时光连在一起,带着对过去的眷恋和乡愁。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尽管现代性充满弊病、矛盾重重,但在社会中,人所追求的是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自我利益,追求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不断变化,也有其进步意义。
四 “有机的共同体”与“机械的社会”
《共同体与社会》开篇即说:“人们的意志在许多方面相互关联,各种关联相互作用;作用源自一方,另一方则承受或感受。各种作用的特定倾向,要么维护他人意志或身体,要么摧毁他人意志或身体,此乃肯定作用或否定作用。本书的理论研究,仅关注相互肯定的关系。”滕尼斯认为,关系即结合,破坏性意志成就不了关系,他因而把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形态排除在其研究之外。在他看来,只有坏的社会,而坏的共同体是自相矛盾、不合情理的说法。他只对社会关联的积极面感兴趣:“不管在哪里,只要人们通过其意志,有机地相互结合、相互肯定,就会有这种或那种共同体。”关于《共同体与社会》的一个一再被提及的“问题”或“缺陷”是,滕氏社会学其实只奠基于共同体概念,这就无法观照不良社会关系,权力、暴力、罪行都被他的社会学舍弃。
如前所述,滕尼斯把人的需求及相互间的认可分为共同体与社会这两种相反的结构。共同体是原初型的结合,如家庭那样,是“现实的、有机的生活”。社会则是自由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如一个城市的居民、市场的参与者等,或多或少是偶合的,只是为了特定目的才相互发生关系,滕氏称之为“思量的、机械的”。他解释说:
首先需要对既存的对立面做一些说明:我认为,所有习惯的、私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都是共同体内的生活。社会则是公众的,是世界。共同体中都是自己人,与生俱来,同甘共苦。走进社会,就如进入他乡。青年人总被告诫,避免坏的社交,而说坏的共同体则有悖语感。与法律打交道的人,若只认可结合之社会概念,或许会说家庭社会;然而,家庭共同体对人的心灵的持久影响,是每个成员都能感受到的。[……]人们说语言、习俗、信仰的共同体,却说行业、旅行、学术的协会[社会:society]。尤为明显的是商业会社,尽管成员之间也会有亲密感和共同体的感受,但人们几乎不说商业共同体。……共同体是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暂时的、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当被理解为活的有机体,社会则是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
尤其在日常语言中,共同体一般是指若干个体的组合,通常有共同特征,以及人以群分的感受(“我们”)。滕尼斯把共同体看作观念、价值观、情谊、常常还是财产的结合体,包括血缘共同体(亲属)、地缘共同体(邻里)、精神共同体(友谊)等。共同体主要通过内在的血缘、亲缘、地缘或精神联系在一起,是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往往是自然而然,或是命运使然,比如无法选择的出身,那是偶然性把人联系在一起并相伴一生。而精神共同体在滕氏看来最少本能性质,纯粹源于习惯,从而也是最具人性的。
滕尼斯首先从家庭来解说共同体生活。亲子关系是最典型的共同体关系,亲密无比;对许多人来说,父母与子女之间甚至没有“关系”,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前者。母亲和子女的关系无疑是最亲密的,来自本能的爱。这种爱无需思考,是一种天然联系。随着孩子的成长,爱会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家庭生活的习惯,以及对以往时光的记忆。习惯和记忆也是连接夫妻或兄弟姐妹的纽带。家庭生活的习惯,给人带来安全感,也在不断增强共同体的感受,另有对同甘苦共患难的记忆。兄弟姐妹之爱在滕氏眼里是爱的最高形式,因为那不是出自本能,而是建筑于共同的记忆。就夫妻而言,“性欲之本能”并不是持久的共同生活的基础。婚姻是意志的结合,比如一方不想离开另一方,尽管多有烦恼,依然不离不弃,不想解除盟约。在共同生活中,失去个人的一些自由,并非就是坏事,“归属”给人带来安全感,人们甚至意识不到这一点。简言之,爱、习惯和记忆是家庭共同生活的基础。
在共同体中,个人意志让位于共同意志。母亲日夜照料孩子,夫妻相互奉献,兄弟姐妹相互保护。通过家庭亦即爱、习惯和记忆,共同体概念得到了最好的解释,但这并不等于共同体生活仅限于家庭。滕尼斯还把他的共同体考察扩展至亲情之外,例如村落、邻里和朋友圈,或者宗教共同体。出身、传统和习俗,或血缘、地缘和精神的同属,将个体联合为整体,习惯是心灵的寓所,共同体成员的结合是真正的结合。滕氏共同体概念所表示的社会属性,是指不同个体顺从其意志,或曰基于人之意志的紧密结合,是熟人构成的道德共同体,因而能被喻为有机体。
以契约为纽带的社会则与共同体不同,滕尼斯指出:
社会理论所构想的人之群体,与在共同体里一样,和平地生活和住在一起,但在根本上不是同心同德,而是分离的。在共同体中,虽有种种分离,仍然休戚与共;在社会中,虽有种种结合,隔阂犹在。因此,这里不存在源自先在和必然统一体的行动,个人行为中也无法见出统一体的意志和精神,很少为了同道,只是为自己。这里只是各归各的,与其他所有人处在紧张状态中。
从“人之处境”的概念模式来说,“社会”与“公共领域”同义,不断把人从自我分离出去;“共同体”则与能够回归自我的“亲密”同义,是“自在”而非“异在”。诚然,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并不都是敌人,其他人也是社会成员,但社会中的结合并非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结合。每个人只是有所图才与他人协作。“没有人会为别人做些什么、贡献些什么、赏赐或给予什么,除非想到报答或回赠,且至少要同他的给予同等的回报。”社会中的人是“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人人都是买家和卖家。因为每个人都想着自己的好处,他人也会为了自己的好处而答应“交换”,所以人与人的关系才会是潜在的、如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尽管有着表面的礼貌来调节人与人的交往,但讨好他人的目的是获得回报:表面现象掩盖着真相。以回报和个人利益为基础的关系,在社会中司空见惯。滕氏用“社会”来描述的现象是,个体为了特定目的才走到一起,这种共处可与受到外在目标驱使的机械现象相比较。传统共同体成员分享共同的理解而非共识,现代社会成员至多只有共识而无共同理解。
滕氏“共同体”与“社会”概念的对立关系,其实来历久远,亚里士多德早就区分过“形成的”与“做成的”。并且,从欧洲古典时期起,“有机体”与“机械体”就是描写社会关系的常用比喻。在滕尼斯的社会哲学中,两个概念传统被组合成一对对立概念,他也因此成为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中重要的关键词设置者。按照韦伯的观点,社会学必须坚持价值中立原则;而通览滕尼斯对共同体和社会的考察和评判,不难看出他的价值取向。他更多地站在共同体的生活形态一边,对共同体的评价远远高于对社会的评价,仅“有机”与“机械”之喻就能让人一目了然。滕氏眼中的社会关系在过去是有机的,当前是机械的,而社会性理当只是有机的。因此,他宣扬的是,回归原初的共同体形态。
也是在这一语境中,滕尼斯常被视为19—20世纪之交兴起的文化悲观主义的早期代表。这种悲观情绪弥漫于韦伯对现代性枷锁的批判,亦淋漓尽致地体现于斯宾格勒(O. Spengler, 1880—1936)的《西方的没落》(1918—1922)一书。崇尚“共同体”及其在社会学中的概念确立,也在哲学领域产生了影响:舍勒(M. Scheler, 1874—1928)在《价值的颠覆》(1919)中,进一步强化了滕尼斯对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分,认为社会“很难说是各种由血缘、传统和生活习俗结合而成的‘共同体’的上位概念,更应说所有‘社会’都只是残渣,是在对各种共同体的内部侵蚀过程中产生的”。另有桑巴特(W. Sombart, 1863—1941)那样的经济学家或神学家特洛尔奇(E. Troeltsch, 1865—1923)一再表达的担忧,即欧洲的逐渐美国化和工业化将会“荡涤所有共同体的发展和一切有机之物”。
五 “选择意志”与“本质意志”
滕尼斯并不只是满足于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类型)的对照,他还区分了与之相对应的两种人之意志,也就是构建社会关系的心理机制:一种是“本质意志”(德文:Wesenwille,英文:naturalwill),另一种是“选择意志”(德文:Kürwille,英文:arbitrarywill/rational will)。共同体的本质意志或社会的选择意志,是两种最基本的认可意志。在滕尼斯看来,本质意志是生命在作用,听从的是性情和良知,行为和目的是统一的。而与社会打交道,就会出现“动机”,需要做出“选择”,这才有选择意志。滕氏原先用的是“Willkür”(自由选择,任意)一词,该书1920年第三版时才将之改为“选择意志”。对于意志形式的探索,是《共同体与社会》试图向人类学方向拓展社会学的核心部分。
与“共同体”“社会”概念一样,“本质意志”“选择意志”也是理想型概念,有助于对人的行为动机进行结构性分析。意志的这两种基本形态,与共同体和社会难解难分,体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此,滕尼斯的分析思路也大同小异。他说,本质意志是人的原初意志,是“实在的、自然的”;选择意志则是“思量的、人为的”。共同体以本质意志为纽带,传统是其根基,也只有从中得到解释;选择意志是旨在未来的意图、方案、决定和行为。在本质意志中,情感因素超过认知目的,选择意志则如阿奎那所说的“理性的欲求”(appetitusrationalis)。本质意志是本能的、自发的,或者自然形成的,体现于不假思索的行为。人与人的相遇,也是各种意志的相遇。若能相投,便形成一种联系,即一种依托于共同体意志的社会性,个人意志融入社会性意志。共同体中的认同感是默契的,建立在共享信念和情感的基础上。规矩往往不是设置的,存在于共同体的下意识,不言自明,理所当然。互助无需商谈,而是发生,且不必监督。在滕氏看来,本质意志依托于爱;并且,原来不喜爱的东西,习惯可以使之顺眼。记忆则是储存爱和习惯的关键,“应当被看作精神生活的原则,从而也是人之本质意志的特殊标志”。爱、习惯和记忆与共同体的关系,构成本质意志的基础,或催生本质意志。
滕尼斯分析了共同体的不同形式,如家庭、世系、民众、村庄、乡镇、行会等,而把大城市看作以契约、商业、金钱为特征的社会。任何一种同盟的形成,不管是共同体的还是社会的、短暂的或长期的,都是人的意志使然,或曰社会性产生于人的意志。在共同体中,集体幸福是重要的,社会中则是个人利益第一。然而,这两种类型都离不开个人意志的相互肯定。并且,社会关系也不受到时间的制约:若以当今社会为例,两个人哪怕只是***,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性取决于双方的意愿,可以只有一夜,也可以如民族间的几百年交好。
结合的意志并不总是昭然若揭,并不像步入婚姻殿堂时的盟约;多半是其他目的在起作用,即通过共同行为达到某种目的。在社会结合中,例如签订工作合同,双方的目的是很不相同的,但是双方在场,都有结盟的意志。雇主与雇员、房东与房客、卖主与买主之间的关系是典型的社会关系。选择意志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先于所要从事的活动,并且主要是对未来的设计,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它的表现形式是个人主义,其重要特征是虚荣心、贪婪、色欲、金钱欲和支配欲,只追求个人利益,而不是共同福祉。因此,共同体中有规矩,社会中则有法律、规章制度和公众舆论,旨在调节社会中的关系和活动。
六 理想型概念的认识功能
有两种社会学思想家,他们以极不相同的原因留在读者的记忆中:一种是其对大量基本概念的区分而引人注目,他们的概念区分多半还有不同的变更说法,并且在其生前就广为流传,或者,人们会在他们去世以后重构和归纳其概念脉络及其著述史。与此不同,另一种思想家则以唯一的重要区分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取胜;并且,这一区分一再出现在其著述之中,可被视为一个论题的不同变奏。韦伯、卢曼(N. Luhmann, 1927—1998)可被归入前一种思想家,滕尼斯、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可被归入第二类,他们的著述涉猎甚广,但总能让人看到相同的基调。在哈贝马斯的著作中,“工作”与“互动”亦即“以成就为指归”(erfolgsorientiert)和“以理解为指归”(verständigungsorientiert)的行为,形成矛盾的主线。而在滕尼斯那里,“共同体”与“社会”的矛盾如同一根红线,贯穿其著述始终。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视角:在齐美尔、韦伯广博的著述中,究竟什么是他们的“社会学代表作”呢?对于这个问题,迄今还有争议。但就滕尼斯而言,他的代表作一开始就毫无疑问,即后来使他闻名遐迩的《共同体与社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共同体与社会》是一部充满歧义甚至矛盾的著作。尤其是对共同体与社会的关系感兴趣的人,有时或许会有雾里看花之感。二者究竟是毋庸置疑的矛盾,还是历史发展中或逻辑上的先后阶段?或许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混合体?对于这些问题,滕尼斯其实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然而,他的思考也对迪尔凯姆(É. Durkheim, 1858—1917,一译涂尔干)、韦伯产生了影响。从学理上说,类似于后来迪尔凯姆在《社会分工论》(1893)中描述两种社会结构之纯粹类型时的“有机团结”(solidarité organique)与“机械团结”(solidarité mécanique)的对比,韦伯在《经济与社会》(1921—1922)中所区分的“共同体化”(Vergemeinschaftung)与“社会化”(Vergesellschaftung),滕尼斯当初是要借助“共同体”与“社会”这一理想型区分,进行结构性分析。
滕尼斯试图用共同体与社会这两个社会学概念,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然而,还不能十分肯定地说,家庭关系自然会带来思想上的共同记忆,而契约社会就一定是冰冷的关系主宰一切。反过来说,在一个由合同关系组成的社会中,也可能有着深厚的人际情谊。“共同体”概念试图与“社会”有所区别,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应当看到,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滕尼斯探讨了社会化理论,这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快速发展中的一个极为现实的论题。作者感兴趣的不是概念的历史功能,或准确再现现实关系,而是解析理想型概念,即纯粹社会学概念,旨在强化概念,从概念层面揭示“社会本质”。他一再强调指出,我们要对纯粹的概念设置与社会现实做出严格区分;换言之,他所探讨的不是应用社会学问题,而是纯粹社会学的理论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很少存在纯粹的共同体或社会,显然可见的是混合形态,即共同体和社会因素的相互胶着。弗莱尔(H. Freyer, 1887—1969)早就指出:社会和共同体不只是社会共同生活的两种可能性,而是社会现实的两个阶段;共同体只会成为社会,社会总是源自共同体。其实,对于共同体与社会,迄今没有公认的说法。
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即对《共同体与社会》之“社会悲观主义”的理解和判断。应该说,这多少缘于滕尼斯对“共同体—社会”的两极化处理。但也有学者认为,不能把滕氏看作文化悲观主义者:他既不认为社会关系是有机的或机械的,也不认为非此即彼,或只应当是有机的。滕氏所言社会关系,永远是近似有机和机械,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其中一种趋势占上风。滕氏的批判性社会哲学把社会性概念分解为做成的/人工制品(社会)与形成的/有机体(共同体),这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或曰考察社会关系的方法。“共同体”与“社会”概念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二者对立却相互牵连、互为映衬,人们能在对照中更好地把握人类生活的社会现实。的确,滕氏所说的两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形态互为衬托:共同体之原初、天然的形态与社会的人为形态彰明较著。
七 滕尼斯理论在西方的不同命运
舍尔斯基(H. Schelsky, 1912—1984)、阿多诺、科尼希(R. König, 1906—1992)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舍尔斯基对滕尼斯的学说置若罔闻,法兰克福学派则对滕尼斯这位马克思的敬仰者不感兴趣,民主德国的社会学界同样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意识形态对“共同体”概念的肆意挪用。滕尼斯共同体思想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巨大影响,也使后来有些学者把他看作纳粹先驱。社会学科隆学派奠基人科尼希极力倡导经验主义社会学研究,与坚持社会哲学方向、崇尚辩证社会学的阿多诺亦即法兰克福学派分庭抗礼。科尼希曾断然反对纳粹鼓吹的共同体观念,1940年代流亡瑞士后,更坚定了他的立场。正是对社会学中运用共同体概念的怀疑态度,使他对滕尼斯的共同体研究持批判态度,认为滕氏哲学和认识论基础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共同体”在社会学中是一个摇摆不定的基本概念。一个基本概念,却又摇摆不定,这就增加了把握这个概念的难度。他认为滕氏“共同体—社会”对立模式不够具体,囊括人际关系的所有可能的形式。此外,他不赞同共同体内存在原初的统一意志,历史过程并不一定就是从共同体到社会的发展,共同体也可以是社会的结果,很难明确区分这两个概念的特征;并且,一个概念不应当凌驾于另一个概念。科尼希对滕尼斯的批判几乎是全方位的,这导致战后德国本土的滕尼斯研究直至1970年代基本上没有展开,其影响远不及他的同时代人齐美尔和韦伯。与对经典社会学家不计其数的研究相比,滕尼斯研究也寥寥可数,两部较有分量的著作只是例外:贝尔鲍姆的专著《滕尼斯的社会学体系:以滕氏社会形态研究为中心》(1966),滕尼斯的学生、二战期间流亡新西兰的雅各布比所著《滕尼斯社会学思想中的现代社会:生平述评》(1971)。
与滕尼斯思想很长时间在德国的命运不同,他的“共同体”与“社会”二分理论在美国社会学界深具影响。帕克(R. Park, 1864—1944)、雷德菲尔德(R. Redfield, 1897—1958)、贝克尔(Howard Becker)受滕尼斯影响,提出了宗教社会与世俗社会、人与城市的二分学说。尤其是帕森斯(T. Parsons, 1902—1979)的“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alism),就是从借鉴滕氏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分法开始的。他在《社会系统》(1951)一书中,引入“模式变量”(pattern variables)理论,分析了社会成员之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五种对立模式,用以描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别。帕森斯不但突破了滕氏二分法,也告别了滕氏共同体学说。帕森斯的学说不但意在揭示“传统”共同体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的观念和行为变化,也对角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他后来又在《现代社会的系统》(1971)中,否定了共同体与社会的对立模式,认为共同体存在于社会,各种共同体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稳定的必要因素。原先得力于韦伯的著作,后经帕森斯的拓展,滕尼斯提出的社会学基本概念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共享财产。帕森斯之后,滕尼斯学说在英美学界的进一步传播,当归功于卡恩曼(W. J. Cahnman,1902—1980)、赫伯尔(R. Heberle,1896—1991)的译介工作。
人类是两个世界的居民:一个是古朴的、稳定的小世界;一个是现代的、不断变化的、几乎无边无际的大世界,越来越让人感受到各种断裂。贝克(U. Beck, 1944—2015)在其论著《政治的发明》(1993)中描写了这种奇特现象,视之为现时代向另一个现代的过渡:“现代瓦解了传统,而现代又正在被席卷。”一切都不是事先筹划的,而是现代社会之理性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始料未及的附带后果。现代世界解决问题的策略(更多理性,更多市场,更多技术,更多权利),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制造出新的问题,一再显示出人们所熟悉的进步工具的局限性。因此,贝克认为,现代的进步只是半现代。他在《风险社会》(1986)中指出,个性化带来的不只是自由和发展,还有孤独和失落。在“半现代”的今天,在西方学术界热议“社群主义”之时,重温滕尼斯的学说,无疑还能够见出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