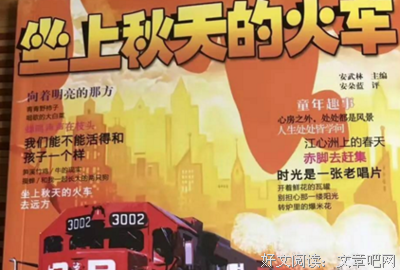
《庆历四年秋》是一本由夏坚勇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33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庆历四年秋》读后感(一):有点小意思
看完这本书,我有几个心得:1、人生一定要有一些除安身立命以外的爱好,和共此爱好的朋友;2、职场里左不过今天被按一下,明天又被提拔一下,一定要尽心尽力做好自己,不被时局境遇打乱节奏,偶尔坐坐冷板凳是好的,挫折是最宝贵的财富;3、无论何时何地不要惹小人,就算无意识也好,除非你有足够的情商和钱去化解危机;4、利益是最好的捆绑
《庆历四年秋》读后感(二):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批政治使命感和文化使命感高度合一的知识精英,他们指点江山则纵横捭阖,舞文弄墨则文采风流。 在那个文治昌明的宋代,一个人政治上失败了,却仍然能够凭借诗文的影响力而东山再起;真忌妒那个文风腾蔚的宋代,一个人可以凭借诗歌和文章写得好而登堂入室,步入权力金字塔的顶层。总之,那个时代彰显了知识精英的空前自信,让我们对政治有了更多文学性的解读。”
《庆历四年秋》读后感(三):诗人在江湖成全了自我
欧阳修,富弼,韩琦,石介,杜衍等等最后都逃不过谪贬的命运,作者说的很对,政治立场往往看着皇帝的态度改变,还有对家为什么黑你,有的时候不是你的主张不好,而是提出主张的人是你。与我而言,官场哲理真的大有启发,并且无奈地再一次的提醒自己真的不适合官场。首先我不会演,第二我也懒得去扳开揉碎看一个人一句话的含义,你tm累不累啊?第三我道德水平自认没那么差,心理素质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类似夏竦和王拱辰干的事,我干不出来。君子党里的人也不可能洁白无瑕,但是小毛病只会让他们可爱无比,欧阳修又去老梅家蹭鱼吃了。比起平和的人,我喜欢这种顽皮,狡黠的人,以前总觉得目标成为宠辱皆忘,泰山崩于前而面色不改的人。可现在我要说我佩服前面说到的人,如果有一天成为这样的人我很高兴。但是现在的我安于做一个大喜大悲,并且喜欢着会哭会笑的人的一个人。他们的窜上跳下是这世间的脉搏,疼痛快乐的感知末梢。文人和文人尊严什么时代都不太值钱,但是不值钱不代表可以抛弃,也许皇权打压,父权夫权迫害,可是我任然坚持我所认为对的,和我爱的。因为这是自我认可,我就是那么爱我自己,爱这样的我。
《庆历四年秋》读后感(四):读罢庆历四年秋
一句庆历四年秋,庆历新政,前相吕夷简致仕,晏殊杜衍上台执政,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样一批君子交游唱和之外,在政坛上也成了风生水起的君子党。仁宗宽厚与疑心之中,新政隔靴搔痒,官场倾轧构陷,西夏之战接连惨败,辽国谈判再加岁币,一件件大事纷至沓来。当然也有小事,办事大手大脚的滕子京被撸了,陈留县的土桥是拆还是不拆,王安石的状元被第四名顶了,进奏院苏舜钦一波人因为花卖废纸的十几贯公款吃喝被罚了......其间开封的太平盛世越来越如火如荼,显贵的绒坐,女子流行的旋裙,天家的罗江犬,大相国寺边的录事巷......点缀着书中人的信件,奏章和圣旨,以及喜怒哀乐,显得细腻而真实。
悠长的梦结束了,宦海浮沉终是沉。大事小情磨完了仁宗新政的耐心,消耗了对君子党的信任。随晏殊杜衍下台,曾经汇集京师的大才子们,曾经欲为国家肝脑涂地的热血男儿们,离散分别,四落天涯。苏舜钦买了沧浪亭,潇洒地写了《沧浪亭记》,欧阳修去了滁州,为寻一乐字写了《醉翁亭记》,终于被撸了的滕子京在巴陵修了岳阳楼,写信给邓州的范仲淹让他作记。老范大笔一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为这个时代划下了句号。
心里只剩下了空落。风起云涌终于在各自文章里成了回忆与未尽的抱负。历史像车轮,往前滚动,像在重复之前的故事,像晚唐的牛李党争,二十多年后,会有一个人叫王安石变法,会有元祐党争,数百年后东林党阉党的不可开交……在这些故事里,分不出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但是可以分出善良与邪恶,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庆历四年秋》读后感(五):乱世浮文来了
文人喜欢翻弄文辞,比如54页偶尔用一下陈继儒的小窗幽记“老僧酿酒”,却显得小气和生硬。
提到:狨毛,必须要文官两制以上,武官节度使以上,每年9月才能使用。
而这毕竟是普通人的享受,圣祖的气魄毕竟不在物质之上,当年宋太祖说我有三条宝带: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这样的胸襟和气魄让吴越王大为叹服。
而作者一开始就说苏舜卿是典型的高富帅,十三页酒当然要喝南仁和,那就是小说家的笔法呀。一场进奏院的宴会就写了20页,这种搞法虽然比较风趣,但是没有什么韵味——把一个文人活动写俗了。是比较流易的段子手写法。
你像这个李定的诬告,说对方公款吃喝。还用中国最传统的人身攻击方式,说他与女妓杂坐。中国人喜欢在私生活上做文章,一旦把你搞臭,你就得下台了。
有人说中国影视作品的命脉不是掌握在文人手上,而完全掌控的资本手上。资本的商业考量成熟了,说你好卖,他什么办法都有,说你比较文气书呆子气,你怎么卖也卖不出去。
跟当时一样,是残酷的社会现实。
所以这样的写作水平,在封套上写上 深耕宋史10余载,这谁相信呢?还说是什么北宋时代的缩影,士人精神的注脚,你们都把士人精神庸俗化,把创造中国最顶尖文化的这一批人都变成了小混混,打流混世的人,没有任何底线的人,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庆历四年秋》读后感(六):读《庆历四年秋》
《庆历四年秋》上个月读得零零碎碎,断断续续,虽然读完了,但几乎读了后面忘了前面,这个月又前后翻了翻。 庆历四年秋的写法比较有意思,选了一个特殊的节点,一个特殊的事件——进奏院聚餐,铺展开一幅长长的画卷,将涉事人员和事件前后种种相关人事一点一点勾画出来,慢慢描绘出一幅仁宗庆历年间表面上太平治世,实际上内忧外患不断,朝廷内错综复杂各种人情利益相互牵制宦海沉浮的众生画卷。 我对宋史几乎没什么了解,所以虽然是看这种通晓畅白且有点强行幽默(叶大师说文字趣味不高)的作品,也并不是很容易,总觉得各种事情人物关系纷至沓来,很难理个头绪出来。我只是弄明白,在这个节点上,借着这件事的由头,参与人员全部被重罚(成语“一网打尽”的出处),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而与新政有关的几位重臣范仲淹,欧阳修,韩崎,富弼等也受到牵连,后继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打压。与此同时,一位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王安石,踌躇满志,崭露头角,将在二十四年之后,出演属于他的那场人生大戏。 北宋的年号中,我唯一知道的大概就是“庆历”,唯一知道的年份就是“庆历四年”了,因为范仲淹那篇我们中学时代背得烂熟的《岳阳楼记》。这位不仅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让当时的我肃然起敬,更因为后来看到他年幼读书时居然能做到“划粥割齑”,让我瞪目结舌。一个人能少年立志,并对自己严苛到这种程度,真的让人觉得强大到可怕。政坛衰落,文坛兴起,北宋年间的这些大名士,个个在官场跌宕起伏,他们首先是政治家,怀着治国平天下的信念,政治生涯受阻后,才更多地寄情于诗词文章。我能读出味来的,就只有一个感慨,治理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看到制度的不合理,想尽办法调整,改革,哪怕是才高且自律如上述诸位,也有太多的不能得志。 历史没有如果,总在按着它既有的脚步讲述一个个令人扼腕的故事。二十四年后,王安石的变法不仅重蹈覆辙,而且留下了一个新旧党争的混乱局面,北宋由此走向覆灭的下坡路,我的偶像苏东坡也因为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而被一贬,再贬。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从庆历新政,到靖康之难,不过八十来年。
《庆历四年秋》读后感(七):庆历四年秋
这种丧事当作喜事办的传统,后来又被人们不断发扬光大,几乎成为一种时尚。
在宋代那种政治环境下,政治上的错误属于公罪,公罪不是什么大问题,不但不影响以后的提拔任用,相反还会赢得直言敢讲的名声。倒是贪赃枉法那样的私罪是要打入另册的。一个对政治错误不很在乎的时代,在今人看来既不敢相信又怀想联翩。
爱国如果再加上主义,那就不仅正确,而且永远正确。
说边区人民像歌颂大救星一样到处传唱,歌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据此,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里认定,这完全是宋方的一种“肉麻当有趣”的“对内宣传技巧”。
所谓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就是不该说的话坚决不说,咬紧牙关打死也不说。
在十一世纪苍茫的夜色下,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面貌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一颗新的太阳升起来了,那是一种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在旗帜上的光风霁月般的人格境界和精神风范。
能体会到全书的基调和最后谈到士大夫时的赞许了吧。
(公号:行云楼)
《庆历四年秋》读后感(八):富庶的宋朝,文人真的有刚
看过了大宋少年志,然后买了这本书来读的~王倦爸爸真的牛气
宋朝其实在大家的印象中总是战乱频繁,其实宋朝的财力在中国历史上是可以排进前三的,不同的统计资料排名有些不同,有的显示是宋朝的GDP占当时世界的65%,比唐明两个大家熟知的富裕朝代,都要大的多,宋朝没有推行历来朝代的均田制,就是大家都来种土地,而是更崇尚让大家做自己擅长的事,所以宋朝的手工业和工商业很发达,从那副名画《清明上河图》里面,我们就能欣赏到开封的繁华,和宋朝的繁荣。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宋代的文人都是在朝身居要职,晏殊、范仲淹、欧阳修以及在书中结尾处出现的王安石。
全书主要讲的都是仁宗在位的事,在位期间宋、夏、辽几国间的关系,宋朝正如我们常在影视剧中那种唯唯诺诺的角色,其实宋朝GDP很高,国家收入不错,而宋朝总是用钱财去和解当时的关系,其实是因为宋朝的财政入账多,出账也多,虽然不打仗,但是养了很多军队,在军队上的花销占据了很大的一笔,所以宋朝的皇帝觉得用钱能搞定的事,就都不是事,相比战争的花销,一些和解金还是很小的一笔。
还有让我感触颇深的是宋代文人政客间的君子之交,朝堂上辩是非,却也相互敬重。
范仲淹和吕夷简是对手,仅仅是政见不和,一个是保守,一个要推行新政,而关键之时,吕夷简不念旧恶,保护了范仲淹,吕夷简因病辞相,推荐范仲淹入朝辅政,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所以才有范仲淹后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名句。而且这篇文章也因这句,被说照亮了整个中国的十一世纪。
十一世纪唐五代,乱世千秋。乱字繁体难写,现在是简化之后的,书中解释,舌代表语言,说明所有的乱中,乱说话最危险。而乱世为何?就是规矩不值钱,人命不值钱,人的气节和风骨更不值钱,那段时期,三朝元老四朝元老比比皆是,并不是他们寿命长,而是王朝更迭太快,也不是他们功劳特别大,而是见风使舵功夫太好,所以范仲淹成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表达的精神也成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史上的千古丰碑。
还有一个小插曲,明太祖朱元璋好专制,曾因一死囚是范仲淹的后代,而免其五次死罪,可见范仲淹对后世的影响。
《庆历四年秋》读后感(九):庆历四年秋
#读书笔记#
庆历四年秋
夏坚勇 著 译林出版社
长篇散文式的笔触,作者执笔游走于文学和史学之间,真的很散,更像是街头巷尾端着茶缸的大爷在讲故事。故事从庆历四年秋苏舜钦秋赛酬神开始,先后引出了庆历新政中关键的一系列人物,吕夷简,晏殊,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梅尧臣,夏竦,滕宗谅,王拱辰等等,结尾处进奏院案的判决,印象最深的就是关于“朋党”以及仁宗的“制衡”手段等一系列事件。
有时候我甚至猜想,祖庙的三誓碑实在是妙,如果士大夫不知道其存在,一方面可以广开言路,言所欲言(理想情况下),另一方面又不会有恃无恐,无所顾忌。
作者总是试图用现代人的方式去揣摩分析北宋年代的事情,尤其是关于新政推行受阻以及官员事务处理上,很多事情的处理,包括遇到的层层阻碍还有繁琐复杂的人事关系,古今无异。
“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
其实真的很难把北宋庆历年间的政坛人物简单粗暴的划分到两个阵营,有些人只是出于私心,有目的的、恰好的、暂时处在一方而已,而有的人也只是部分的否定,所以不能算盘接受而已。
政坛多风雨,变革之艰难,王朝就像一辆笨拙的牛车行驶在坎坷泥泞的古道上,想要推一把都不容易,何况想要改道。
尤其“君子党”人面对政敌的弹劾,要如何应对?若是互相施以援手,刚好坐实“胶固朋党,递相提挈”,若是坐视不管,则人气尽失,树倒猢狲散。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还好那个时代,即便是政治上失败被排挤,也能够凭借诗文的影响力“东山再起”。面对命运之不公,这些士大夫作为受难者,同时也是享乐者,既有苦痛怨尤,也有超然闲适。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
文末写到:
北宋初年承五代旧习,士大夫寡廉鲜耻,唯利益之所趋,少道义之所存。宋代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风盛衰,乃王朝命脉所系。因此,新王朝定鼎之初,除了军事统一南北,恢复国内经济,重建国家制度等要务而外,弘扬士德、转变士风也成为当务之急。一种风气的转变绝非一蹴而就的功业,也不像开国帝王挥剑决浮云那样痛快。宋太祖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碑,其意也在于鼓励士大夫正直敢言,不苟同时俗。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转变士风。至仁宗朝,这一转变大致完成。范仲淹这样的人物走上历史前台,出将入相,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无疑是这一转变完成的重要标志,而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表达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先忧后乐”的精神,则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境界的最高写照,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史上的千古丰碑。
“有的文章,你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一见钟情,如痴如迷,可是等到时过境迁,再看时就觉得很一般甚至不好了。也有的文章,你任何时候看了都会心旌摇荡,由衷叹服。”
《沧浪亭记》如是,《醉翁亭记》如是,《岳阳楼记》如是,而后的《赤壁赋》亦如是。
昨晚看完的时候就隐隐觉得胸中有些汹涌,这回整理笔记这种感觉又来了…
沃然有得,笑闵万古。
上回去苏州没去沧浪亭真的太遗憾了!
《庆历四年秋》读后感(十):甲申九百七十五年祭
相较于明清鼎革之变那个极为出名的甲申年,公元1044年是一个被湮没在《岳阳楼记》背后的甲申年。“文化大散文”名家夏坚勇发现了其背后关键的时间节点:“北宋庆历四年,岁在甲申。自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已经八十四年,而距靖康之难北宋覆亡还有八十三年,也就是说,在北宋王朝的历史上,这一年恰好处在中点上。”于是,梳理史料,推究细节,有了这本“宋史三部曲”之一的《庆历四年秋》。
作品展示了从宫廷到市井广阔的生活面,政治、社会、军事、外交……错综复杂,变革、权争、阴谋、人祸……惊心动魄;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北宋“政治稳定与专制腐败互为表里,体貌宽柔与因循苟且共存共荣,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尚武精神的沦落混搭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两种色调。”
作者笔下,貌似风光无限的北宋与其他朝代相比,在王朝中点遇到的外患内忧,一点不缺:外有西夏寇边,辽国虎视,“在国家财政的总盘子中,至少六分之五用于养兵,仅剩不到六分之一用于维护政权运作”;内有连年大旱,蝗蝻复生,民生艰难,加之“官僚体制臃肿、官府机构庞大、行政效率低下”,势必危机重重。但同时遇到了一位被塑造成中国古代难得守成明君形象的宋仁宗赵祯,以及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蔡襄、包拯等一群毋庸讳言值得载入史册的名臣。一场“庆历新政”,也就毫不意外地推行开来。
随着宋夏和议的达成,新政的直接动因消弭,这场改革很快就走到了尽头。主事官员相继被贬,政策举措陆续被废,短短的一年四个月只落得“水过地皮湿”。关于“庆历新政”的解读,后人往往会将其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前奏。然而,范仲淹毕竟不是王安石,宋仁宗更不是宋神宗。本书作者“不喜欢写改革,尤其不喜欢写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而是特别留意一桩小事引发的轩然大波——庆历四年秋,发生在清水衙门进奏院司空见惯的酬神聚餐,居然令向来宽厚仁恕的君主龙颜大怒,导致参与者尽数贬谪,“一网打尽”。同不久以前涉及十六万缗公使钱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之从轻发落进行对比,宋仁宗态度迥然大变,臣属的应对更值得玩味,见微知著中既折射朝局的转向,又看出人心的波谲云诡。诚如作者清晰提醒读者的那样:“说到庆历年间的政坛纷争,人们总喜欢刀劈豆腐两面光,把当时的人事分成改革和保守两个阵营,然后让他们对号入座。但历史毕竟不是厨师手中的一块豆腐,历史活动是人的活动,只有透过各种人物幽微隐曲的心理动机,才能窥见历史的底色。”
从这个意义上说,《庆历四年秋》作者不以再现“庆历新政”的来龙去脉为出发点,也不以评判其镜鉴得失为目的,甚至仅仅“把新政作为一个背景”,而将目光聚焦于史料中只言片语记载的“小事”,描摹的重点是活生生具体的人——人的命运、出身、性格、才能和利益诉求各有不同,但“民族性格和人性之幽深”却是相通的,而这正是非虚构写作的魅力所在。
如果只是让读者看到了王拱辰、夏竦“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忌妒”,苏舜钦、梅尧臣“虽有层梯谁可履,公干才俊或欺事”,甚或吕夷简、富弼、欧阳修、范仲淹以及宋仁宗为人处世复杂的“月亮背面”,《庆历四年秋》依然还不足以对时代精神有真正的体味——“那个时代彰显了知识精英的空前自信,让我们对政治有了更多文学性的解读。”全书高屋建瓴之处正在于此。全书末章《秋水江湖》,作者以极富感染力的文学笔触,描绘了苏舜钦《沧浪亭记》、欧阳修《醉翁亭记》、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创作心路。面对这些千古名篇,他抑制不住作为一个当代散文名家对前辈的由衷赞叹,总结道:
“贬谪文学当然源远流长,但在这之前还只是溪水四溅,虽偶有激流跌宕却难见拍岸惊涛。在庆历四年秋天以后的那段时间里,横空出世,中国的散文星空中相对集中地涌现了一批出自贬谪者的华彩篇章,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面对着命运中的困厄和不公,他们都应之以适度的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而心中却始终高扬着崇高理想的旗帜。这种特殊的精神气质成就了一种特殊的审美范式,主人公既是受难者,又是享乐者;既有旁人无法想象的苦痛怨尤,又有安之若素的超然闲适。”
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