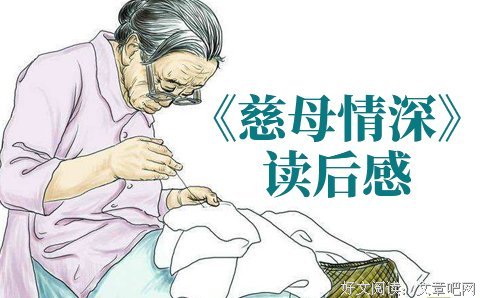
《我和我的命 (梁晓声新作)》是一本由梁晓声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页数:37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和我的命 (梁晓声新作)》读后感(一):周总理诗一处误植
《我和我的命 (梁晓声新作)》读后感(二):沉重的血缘关系
《我和我的命 (梁晓声新作)》读后感(三):作为风筝,总有无可把握的悲哀——读梁晓声小说《我和我的命》
《我和我的命》以二十一世纪初的深圳为背景,是对二十年前深圳打工人状态的一次深情回望。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深圳的高楼大厦、科技成果、DGP都是亮眼的标签,这些无限风光,是深圳人胼手胝足创造出来的,而深圳人的主体,无疑是千千万万不知名的打工者。方婉之、李娟、郝倩倩、姚芸,正是那一代闯荡深圳的打工人缩影。
这部以打工人为主角的小说,在书写命运的母题之下,紧紧抓住现实的脉动,刻录特定历史阶段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小说主要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是主人公在深圳的打拼历程,二是挥之不去的亲情、爱情牵挂。
先说打工人的经历。方婉之来自贵州玉县,妈妈是校长,爸爸是市长,可谓娇生惯养。大二时,校长妈妈病逝前,说出收养她的真相,并告知她的亲生父母在边远的村庄神仙顶。面对命运的捉弄,方婉之选择退学远走深圳,先后从事工地帮厨、医院护工、包装厂线长、经营超市等工作,其间历经风雨折磨,一直坚持上夜大,最终拿到了深圳市民证,也收获了爱情。刘娟来自东北,性格直爽仗义,一直与方婉之携手前行,为保护郝倩倩失去一个肾,最终成为超市主人。郝倩倩家乡不明,是个心眼儿活的姑娘,先是与承包食堂的刘柱结婚,后又跑回深圳,被商人包养。姚芸着墨不多,东北国企倒闭潮期间,被迫来深圳闯荡,因卖淫被抓,但刘婉之一直认可其为人。这四个姑娘背景、经历不同,所选择的方向各异,聚到一起,展示出二十年前深圳打工者的多元生存状态。
再看看四个人身上的感情负累。孙悟空是从石头缝蹦出来的,以天地为母。人不行,都是父母生养,有亲人、有家乡,这是不能选择的“命”。接不来的友情、爱情之类,虽不是天生注定,但机缘到时,也会难以割舍。方婉之远走深圳前,回了趟神仙顶,见到了生父、两个姐姐以及外甥、外甥女们。接下来,这些有血缘的亲人,把这个小姨当成了肉骨头,总盼着得到她的资助。在亲情与道义的权衡下,方婉之尽己所能提供了帮助,并逐渐找到心理平衡。同时 ,她与养父之间多年的亲情,也随着心理的平复,重新归于正常。爱情方面,她也从最初的误解到逐步的了解,与摄影师高翔找到真爱。刘娟有着很强的责任感,除了照顾自己的家里,在她相恋的军人牺牲后,毅然承担起照顾军人孩子的责任,她身上体现出的执著和担当,让读者动容。郝倩倩是自己快乐的典型,没有提到她的家庭,从与厨师结婚到被人包养,她的感情都是功利的,而她在友情方面则没有什么功利色彩,显示出纯真的一面。姚芸在工厂倒闭后从东北跑到深圳,以卖淫为生,同时与厂里的技术员保持着关系,方婉之对她给予了深深的同情。
世界是个万花筒,每个人身上都缠满生活的负累,自我生存与感情牵挂交织出多彩的生活。《我和我的命》通过这两条线索,串起了一些普通的人生故事,不事张扬,毫不做作,总会有某个细节,与读者的生活经历偶合,从而引发对“我和我的命”的思考。
有些耳熟能详反映当下世相的词语,在书中得到了形象展现。比如“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成了一些货车时髦的车贴,书中写到的四个女子,都经历着这种边缘人的感受,即使方婉之成了深圳市民,也难以彻底摆脱。再如深圳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以及复旦大学教授陈果提到的“爱富不嫌贫”,在处处以金钱称量社会地位的深圳,方婉之、李娟们在努力挣钱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坚守着做人的原则,没有掉到钱眼里,她们以强烈的责任感,帮衬着生活困顿的亲人,像郑智化 一样高唱《水手》:风雨中,这点累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读《我和我的命》,头脑中想起两篇作品,一是鲁迅的散文《风筝》,一是贾平凹的小说《暂坐》。
鲁迅先生回忆儿时对小弟弟做风筝的粗暴冒犯,成年已有了胡子,想补儿时之过,弟弟“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全然忘却。因得不到期待中的“宽恕”,作者感叹:“ 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带给鲁迅”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和我的命》中的方婉之等四个年轻女子,也都像风筝一样,因缘聚合相会于深圳,她们都牵系着一根绳子,或者是家乡,或者是感情,也都有着无可把握的悲哀。
《我和我的命》与《暂坐》看似不搭界,但其共同点在于,都是以一群女子为主角,以一个城市为背景,铺陈出一个世相纷繁的故事。《我和我的命》的4个女子,是东西南北聚到深圳的打工人,为生活拼争,与命运较量。《暂坐》的12个女子,是四面八方凑到西京的女商人,想活出自己的精彩。《我和我的命》中的方婉之们是二十年前那一代的移民奋斗者,《暂坐》中的海若们则算是当下移民的成功者,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她们似乎有着代际之间的传承。
《我和我的命》故事平实,格调昂扬,没有刻意的情节设计,是一部接地气的现实主义作品,延续了梁晓声先生一贯的创作风格。结尾处,方婉之的父亲在玉县护校百年校庆发言时,提到“国家扶贫,亲情扶贫”的概念,算是对中国消除贫困事业的反映,此处写得略显生硬,收得有些仓促。
《我和我的命 (梁晓声新作)》读后感(四):《我和我的命》:写下那些我佩服的青年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 梁晓声 2021年02月04日08:47 关键词:青年 梁晓声
应人民日报海外版之约,谈一下《我和我的命》的创作初衷。
作家的职业可以从多方面诠释,但有一点肯定是不会错的,即——塑造形形色色的人物,给更多的人也就是读者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写过一篇长文《扫描中国女性》,文中对某些困难家庭中的长女表达了敬意,认为她们是那些家庭中的“责任天使”。
后来我收到一个女孩的来信,说她的“小五姨”就是那样的“天使”。信中有段文字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小五姨”是姐妹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高中毕业);是家族中最早离开山里农村到深圳打工的人;于是呢,“小五姨”在深圳所租的那间小屋,仿佛成了家乡设在深圳的“办事处”。到了可以打工的年龄,外甥、外甥女们以及同村甚至外村的小青年,纷纷投奔到“办事处”来,多时连地上都横七竖八睡着人。“小五姨”早上像跳芭蕾舞似的在身体之间回旋,寻找鞋子。她从无怨言,尽量为每一个投奔到自己名下的小青年排忧解难。可“小五姨”只不过辈分大,年龄并不大,才25岁……
那封信使我很感动,我附上自己的感言,把它转给了一家杂志发表了;似乎当年的《读者》也转载了。
原来“责任天使”未必是一个家庭的长姐!
那个我从没见过的“小五姨”,从此存活在我的脑海中了。有时会忘记她,有时会联想到她,彻底忘记已成不可能之事。每一次联想到她,从她的样貌、性格到她的心灵和人生观,一次比一次更加清晰。再联想到时,仿佛她在对我说:“还不把我写出来吗?”
我越来越觉得,她是值得我“写出来”的。
她的“出生”非常顺利。因为动笔时,头脑中的她已经呼之欲出了。
中国之大多数“80后”是独生子女,“90后”“00后”及以后若干代可能也是如此。出生政策虽已放开“二胎”了,但多数家长恐怕宁愿选择做独生子女的父母。
独生子女由于是一个家庭的“独苗”,也必然会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心目中的“宝贝疙瘩”,这使他(她)们想不以自我为中心,都不知怎么才算不“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几乎成了他们自然而然的“本我意识”。
故而,以我这一代人的眼光来看“80后”,不免“毛病”多多。
如今,年龄最小的“80后”30多岁了,年龄最大的40多岁了,而我从他(她)们身上所看到的,已不再是“毛病”,而是可敬的方面了。
首先有一点使我十分佩服,那就是——我们成长于物质普遍匮乏的年代,而他们的成长背景物质诱惑多多,有时形成诱惑的泡沫堆,从四面八方包围,撕扯成长期的少年和初入社会的青年,大有淹没之势。第二点是,我们就业后经历了较长的“收入普调”和“住房分配”时期,这使全中国同龄的脑体力劳动者,在收入方面的差别并不大,今天看来,那种差别几可忽略无视。而我们的下一代,在尚未就业之前,就已受到收入差别天上地下般的现实的巨大压力。
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80后”,总体上非但没有自暴自弃,没成为“垮掉的一代”,没成为社会的“零余者”,反而越来越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不消说,他们大多是平凡的,但“拒绝平庸”显然是他们的“代精神”。努力点儿、再努力点儿,优秀点儿、再优秀点儿,也成了他们不言自明的共识。
我常扪心自问,如果我这一代人集体回到少年和青年时期,经历他们所终日面对的诱惑和财富分配差异的巨大刺激,我们果真能表现得比他们更好吗?
以我自己而言,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也常起一种大的冲动,想从他们的内心深处探究他们的真情实感,叩问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我一向是被采访者,没有机会采访年轻人。即使有那样的机会,也未必能获得如实的回答。
于是我又联想到了“小五姨”——她是文学作品中的“那一个”,就经历而言,与后来的年轻人有一致性,也有独属于她自己的特殊性。
然而就那种不甘自暴自弃、不甘“垮掉”、不甘成为“零余者”的内在精神来说,我认为我笔下的主人公们,与当下大多数青年或许会是“知音”。而在这一点上,我笔下人物的性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笔下的方婉之和李娟们,会成为当下青年们的朋友吗?
毫无疑问,“她们”已成为我的“忘年交”,我因有这样的朋友而愉快。
我活到今天,由文学作品而结识的朋友也已不少,有些是别的作家介绍给我的,有些是我自己“塑造”出来的。我“塑造”了他(她)们,并不意味着我比他(她)们高出一等;恰恰相反,他(她)们往往也对我为人处世的态度产生了深刻而良好的影响,成为我精神上的良师益友。
至于方婉之们,她们肯定也会有她们的“社会关系之和”。“她”在人世间境遇怎样,我也只能深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