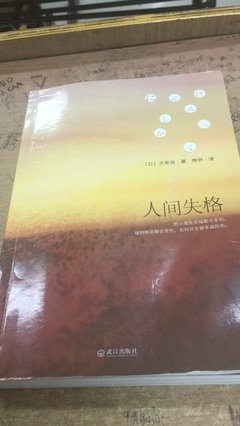
《近代日本的中国观》是一本由(日) 子安宣邦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页数:2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近代日本的中国观》读后感(一):第三章&第四章 内藤湖南的预言
子安宣邦在这两章考察了内藤湖南《支那论》的写作。
内藤湖南是打着“替支那人考虑”的名号写作《支那论》的,但是这并非真正的站在中国人立场上思考中国之前途,而是为了反证支那命运的不可振作、包含歧视的写作。
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内藤湖南意识到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深层断裂和那亟待爆发出的潜流。当见证袁世凯的复辟与独裁政治弊害的重演,他预测长久为独裁所害的中国,“虽偶有一时间回到独裁政治之时,但最终都无法长久。”而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唯有走向共和之一途。他在讨论中国时局的时候,上溯唐-宋变革时期直至清末、民初这六百年的历史,在时代发展的过程里,君主权力逐渐增强(君主专制国家体制虽然经历了包括民族王朝在哪的王朝兴替却依然保留了下来,这是中国式的国家社会特质形成的时代)的同时,人民力量也在逐渐发展。内藤湖南将地方的乡团组织视为人民力量的社会实现形态,而这乡团组织同样是历经元明清三代,与中央权力相对,作为地方防伪性自治组织而稳固存在的社会组织。这些乡团组织是扁面顺逆混杂剧烈的流水深处的潜流——中国式社会的真正实在。他以曾国藩为例,指出中国的自发性革新,只有以乡团组织为基础、组织起军事力量与政治力量之时,才有实现的可能。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内藤湖南是中国人民的同路人。他很快轻蔑地指陈,像支那这样的国家,在军事上暂时没有显示展示国威的希望,其人民又都是爱好和平的、没有发展国力的野心。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将耀武扬威视为极力避免的政治规训而有所忌讳,所以这样的国民特性导致虽然中国人不会追慕法兰西那样的独裁政治,但也决定其不可能出现军事天才从而重振国威,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势。由此,他判断,支那最终走向共和政治,走向平民发展的历史,但这平民的发展却无法改变现状。他以反语否认的形式断言,中国的骚乱不会过于剧烈,因此也不会刺激出类似乡团自卫团的抗争出现。
那么,支那人的自救之道到底在哪里呢?内藤湖南将其移花接木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拯救之上。“必须认识到,当此之际,日本的经济运动对延续支那民族未来之生命,确有巨大的作用。若组织了这一运动,支那民族恐怕是在自求衰死。”
那么,保持冷酷的旁观心理对中国革命的内藤湖南真的预言正确了吗。
子安宣邦戏讽的指出,内藤的预言的确实现了,但是出乎内藤的预料和想象,最终是以抗日战争的形式实现了中国乡民社会的大团结和举国国力的重振。
“日本发动的对华全面战争激活了中国的民族觉醒。”
《近代日本的中国观》读后感(二):筆記節錄
– 這一本書在去年譯出,日本的原著則於2012年時出版,是作者子安宣邦教授原在雜誌上連在超過一年的專欄文章之結集。專欄由2011年開始撰寫,寫作時間為辛亥革命一百年的時間點,也是作者思考日本的中國觀的適合時機。
– 說起會閱讀子安宣邦,大概有幾個原點。一則是經當年老板的介紹,切入了台社(連同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的左翼知識份子)當年有關「超克分斷體制」的討論。這命題的定訂,指向了兩個概念,一為「分斷體制」、二為「(現代/近代的)超克」。
– 關於「分斷體制」,則指向了由白樂晴以降韓國學者針對冷戰格局下的朝鮮半島格局的分析,將國民國家、民族主義革命的夭折置放於世界體系的格局下論述,及後讀到白永瑞關於「核心現場」等概念,也讓我對區域的狀況有了更多思考。
– 關於「(現代/近代的)超克」,則上溯至上世紀20-30年代日本思想界的(不無爭議的)努力,即思考如何超越及克服歐洲、英美所建立起的(思想)霸權。在追尋的過程中,竹內好於戰後重提的「作為方法的亞洲」、溝口雄三在八十年代提倡「作為方法的中國」等概念也進入了視野。值得一提的是,大陸左翼學者在引介相關討論時佔據了頗為重要的位置,當中尤以孫歌老師大力推動溝口雄三及竹內好相關著作的翻譯有關。
– 在這意義下,子安宣邦卻只能在較後時間進入到我的注意。在2014年後充滿迷惘的時候,我拼命的尋找不同的思想資源以應對現實中的困惑,無意中讀到竹內好(亞洲作為方法)、溝口雄三(中國作為方法)到子安宣邦(江戶作為方法)的思想源流與變動。
– 當時的閱讀當然是相當急就張,難以深入相關的討論。事實上每一位作者本身的論著就相當豐富,但卻涉獵不同的領域。竹內好搞的是以魯迅為核心的文學研究,溝口雄三則是研究明末清初的中國歷史,而子安宣邦則是研究日本近世、近代的儒學思想,每一個範疇都不是自己的專業,加上市面資料相當有限,過去大多只能在內地出差時在書店上碰碰,找了一點點溝口及子安的譯作來讀。
– 這裡叉一句,台灣、繁體華文世界對上述的討論好像只停留在學術圈,大概在一些學術論文中會找到,但面向大眾的出版卻甚為缺乏,是故像我這樣的一般讀者只能從簡體材料入手了。大概「左翼」思潮在台灣不大有賣點?
– 回到這書,相比起之前讀過的《何謂「近代的超克」?》,這書容易讀很多。這有可能和書中收入的文章本身就是刊登在雜誌上,並不特別艱澀(當然也意味著文章不會是很詳細的論述);二來可能與譯者的風格有關。
– 子安教授從內介入中國革命的北一輝、開啟近代支那學的內藤湖南起手,再介紹了深入滿洲的橘樸、牽涉入日俄間碟案的尾崎秀實等,單從人物的選擇及他們牽涉進的種種政治,果然如子安教授所講,近代的中國史某程代上就是日本的干涉史。
– 前邊幾篇的文章讓我能更了解當時日本知識份子的視角,當中深入中國的北一輝、橘樸等都有十分獨到(但不受當時重視)的分析。而如何面對戰爭,如何理解日本與中國(及發起事變)等問題,如何理解日本軍隊在中國的劣蹟,都是一代日本知識份子的挑戰。
– 而戰後的(左翼)日本知識份子,則要思考「人民中國」的意義。根據子安的分析,竹內好、加加美光行甚至溝口雄三都在反省日本(思想)的同時存在一種缺陷,即把中國理解成日本的「反面」,作為一種投射,甚至某程度上接受了種種不合理狀況。子安宣邦在這層面有很清晰的批判。
– 他也批判了溝口雄三在這脈絡下提出所謂中華文化圈的講法,認為這種想超克歐洲文明的構想並不一定能帶來多元,反而有點像戰前日本的「東亞協同體」、「東亞共榮圈」的構想那樣,指向一種危險的方向。
– 但子安宣邦不是那種右翼的思想家,應該也無意「妖魔化」中國,否則他的書也不會一再在內地出版。他一直關心近代化的問題,也在現實政治層面關心日本的核問題、靖國問題等。在這意義下他對「天下」、「中華文化圈」等的提醒、警示則更值得我們注意。
– 在最近的《思想41:新冠啟示錄》子安也有一篇題為<重思「日本近代化」:於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年之際>的文章,收入了陳宜中編的《大國的想望》中。《思想》雜誌久不久也會登子安教授的文章,希望《大國的想望》會引起更多華文讀者對他的關注。
– 書的譯後記也頗好讀,譯者王升遠把整本書的脈絡串了起來,很能幫助讀者去了解本書。
– 最後,趙京華教授的《日本后现代于知识左翼》一書有一篇子安宣邦教授的介紹文章,相當仔細完備,值得參考。趙教授應該也是最為著力把子安教授介紹到華文世界的學者,也感謝他多年來的努力吧。
《近代日本的中国观》读后感(三):“为日本人考虑”
《近代日本的中国观》读后感(四):王升远:近代日本如何言说中国
《读书》2020年6期新刊
今年因为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中日两国从援助箱包上印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到“青山一道,同担风雨”,似乎联结成了同病相怜的命运共同体,而这种连带感在近代以降的东亚史上却并不多见。问题是,疫情过后这种命运连带感还能维系多久?借马场公彦的话来说,“进入二〇一〇年以后,日中关系可以说呈现出战后最差状态”,两国“还处在年轻且不成熟的关系中,如此观点才更合乎两国国民的现实感觉”(马场公彦:《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苑崇利等译)。尤其在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各国民族主义声势日盛的当下,对两国而言,与什么样的彼此“共结来缘”,仍旧是一项紧要的议题。子安宣邦的著作《近代日本的中国观》试图回应的问题便是,“如何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构筑日本与中国的相互关系”,因为“与怎样的中国、如何地相处才能确保亚洲和平,这自然是与当代日本国家命运相关联的本质性问题”。
子安宣邦(来源:xinhuanet.com)
策划“二二六”事件、对于日本近代思想有重要影响的北一辉作为一位日本思想史学者,子安之所以要开始这项阅读“中国论”的工作,一方面是因其认识到,“中国问题即是昭和日本的问题,它最终决定了昭和日本的国家命运”,因此,近代以降日本的涉华言论、知识曾以何种形式、路径得以生产,又如何影响了日本的对华观念与决策都亟待学人予以系统清理;另一方面,观察崛起中的中国,可以倒逼他重思竹内好以降沿袭至今的中国形象、中国研究是否可靠。在学术思想与政治的紧张关系中,子安痛感日本的亚洲主义抑或中国主义“已完全丧失了批判性和思想性机能”。 我愿将子安在本书中的基本立场表述为“亚洲主义”。在他看来,“‘亚洲主义’是将日本的变革与中国及亚洲诸民族的变革予以共时性或者联动性思考的活动者的立场”。而在近代以降群星闪耀的日本中国学家、以中国为活动现场的新闻家/革命家、以中国为题材或对象的评论家/小说家中,择取北一辉、内藤湖南、橘朴、尾崎秀实、森谷克己、平野义太郎、石川达三、竹内好、加加美光行和沟口雄三结构篇章,作者基本的判断基准便是其定义的“亚洲主义”。我一直认为,“国际中国学”在其研究对象上存在一个不甚为学界关注的层面,即:海外中国学家(汉学家)是如何以其涉华活动、言论和创作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发展,乃至其母国对华关系的进程。佐藤春夫、林房雄、保田与重郎等皆是这一层面所涵盖的对象,战时他们曾共有介入中日关系时局的政治激情;当然,战后中日复交的历史进程中也有井上靖等左翼人士的卓越贡献,不应被遗忘。有趣的是,思想史家、本书作者子安宣邦在书中亦以“日本的言论家”身份自认,每章结尾都以史家笔法论及研究对象之当下意义,并不掩饰以学术介入当下中日关系未来的意图。 在子安看来,现实层面里,中日两国的疏远实则是一个战争遗留问题。因为“这场发生在大陆但从未被称为‘战争’的战争,却是以太平洋战争的战败而被终结的。不过那是日美之间的了断,而非日中之间的了断”。然而,“中日”“日美”多重双边框架的叠合所形成的视差,让人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之后产生了“俱往矣”的错觉。事实上,就像子安所敏锐察知的那样,长期以来,中日之间的本质性了断始终处于被延宕的状态,而近几十年来两国如火如荼的经贸往来更让人们对此习焉不察。《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各章节自二〇一一年九月起,在《现代思想》杂志连载一年;而这一年适逢辛亥百年,这也是理解子安“读‘中国论’”系列文章的重要思想语境。在这一时点上,子安找到了重建两国已然失去的“本质性联系”的契机,因为参与、介入了辛亥革命的多是留学或流亡日本的中国人,以及日本的“大陆浪人”,北一辉即为个中翘楚,他“身处核心层而经历了这场革命,这在日本人的中国革命体验中是很罕见的”。众所周知,二十世纪日本对华政策的核心策略便是分裂中国,革命时期日本大陆政策也是以 “北袁南孙”二元对立图示为前提制定的,彼邦的“亚细亚主义者”们亦误以为援助孙文即是援助了中国革命。而让日本政界始料未及的是,日俄联手分裂中国的外部威胁反倒成为中国内部统一的推动力,这种对华外交政策是身处革命漩涡中心的北一辉所无法容忍的。他不断告诫日方切勿将中国革命视为“孙文革命”,应直面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并改由宋教仁了解 “革命中国的真正理想与诉求”,据此修正其对华观念与政策——因为“日本有着与中国的国家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相连带的光荣”。 较之于具象化的论述,毋宁说子安更为强调北一辉之中国革命观的生成机制。要言之,即在场、实感、见证。如其所言,“实地观察了中国革命的北一辉,从这场革命中感受到了一些倒逼日本大陆政策改变的气氛,他的确是实地感受了中国革命之为何物的”。对实感主义、现场主义的推崇同样表现在对辛亥革命时进入北京城、“终其一生都始终将危机与变革中的中国作为其报道现场”的日本记者橘朴之评价上。他试图将《支那社会研究》作为“探究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橘朴在危机与变革中的中国所发出的历史证言”。在子安那里,橘朴正是“亚洲主义者”的完美代表。有趣的是,竹内好却不这么看。在一九六三年编辑、出版《亚洲主义》一书时,竹内好以橘朴“其人”远胜“其文”为由,终未收录其著。而就是这个不受竹内好待见的记者,却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临终前,拿着战略地图对中国的前途做了一个令人大为震惊的预测——中共军队终将征服全中国。在日本刚宣布投降、中国国内局势尚不明朗之时,能对中国未来大势明见万里,这得益于橘朴长期在华的活动、报道经验。自一九一二年起立志穷毕生之力报道中国始,他便长期活跃于日本大陆政策的现场——中国。而现场主义、实感主义所要求文体必然是强调即时性、见证性、批判性甚至战斗性的状况论、形势论,是“将状况视为自己思想、实践现场的评论,是包括了状况判断和方向提示之原理与原则的‘思想性’文章”,而非与中国保持距离,仅将其作为观察、剖析对象的稳健深邃的学术论述,这是橘朴与另一位记者——尾崎秀实相通的表述方式。如果说橘朴是以对中国未来的精准预测结束了“以中国为现场”的记者生涯,那么尾崎则是通过在“西安事变”翌日发表的一篇对中国政局前景之精准预测在日本一举成名,最终成为近卫文麿内阁“嘱托”(近于高级顾问),为后来成为共产国际的卓越情报人士、在军国主义政权中枢发挥积极影响奠定了基础。更值得铭记的是,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央公论》头条刊出了尾崎秀实的《“东亚协同体”的理念及其形成的客观基础》。文中,作为一位知性的国际主义战士,尾崎要求日方“完全承认中国以民族自立实现国家复兴并能对其予以支持”,在武汉会战硝烟甫定、中日关系走到十字路口的节点上对日本自身的变革与重组提出的真诚建言,是弥足珍视的。
橘朴(左)和尾崎秀实(右)都是近代日本记者出身、后成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的典型代表内藤湖南(来源:wikipedia.org)橘朴在兜售其中国变革论时有一个颇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常引京都学派的史学巨擘内藤湖南的权威论断以为加持,试图为读者营构出殊途同致的观感。子安通过对二者著述的深入解读,使其貌合神离的一面彰明较著:内藤基于文献,以乡团组织始终存在为依据,建构起了一种结构主义式、静态的中国社会论,他认为中国民族“政治年龄”太大,并有着其独特的近代化道路;而橘朴基于对中国农村的深入踏查和农民革命的长期观察,建构起了动态的阶级斗争论(通过官僚阶级与中产阶级的斗争实现变革),他认为中国民族太年轻了,和日本同样,其近代化道路与西方并无二致,只是起步晚些。这两种不同的历史观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华心态:如果说内藤湖南代表了帝国日本“支那学家”自负的“上帝视角”,那么子安认为,橘朴则表现出了同为东亚人的“同志之感”。内藤湖南试图透视出执拗地流淌在中国历史底层的“潜流”(乡团组织);然而,如子安所言,对“乡团组织”的过度关切、对历史规律的过分执迷,使其对中国的自立化革新持悲观态度,他否定了五四运动的意义,无视中外关系的动态,甚至认为离开了日本的经济活动中国必将“衰死”。“替支那人为支那考虑”的内藤湖南最终以历史学家的奇妙逻辑论证了“侵略主义、军国主义”的合法性,其在认识论层面对研究对象的控制欲及将其落实的知识自负,都是值得今人警惕的。 就像子安所坦言的那样,“中国近代史无非就是一部日本对华干涉史”。近代以降,以学术为帝国海外侵略背书,为建构帝国日本的知识生产和思想建设添砖加瓦、尽心竭虑的不唯历史学家,学术界、思想界诸领域大都被牵扯其间,例如深受橘朴之中国农村调查影响的东京帝大的法学家们。一九四〇至一九四四年,东亚研究所的中国习俗调查委员会和满铁调查部的习俗班,联合推动了一项针对华北日军控制区农村遗存习俗和法意识进行的调查工作,以为帝国的殖民行政提供参考资料。这次以中国社会基底——村落为对象形成的调查报告,让参与了这项工作的平野义太郎和戒能通孝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论争,核心问题在于:中国社会是否存在“村落共同体”。平野在橘朴(他将中国社会中的“乡党”视为“乡土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亚洲式乡土共同体理论——“村落共同体”理论,并以此为“大亚洲主义”提供历史基础。而其论敌戒能则以近代市民主义的立场否定了其主张,他深知只要否定了这一前提,平野的“大亚洲主义”论述便会土崩瓦解。后来内山雅生等人又对经历了人民公社和改革开放的华北农村进行了再度调研,并于二〇〇〇年出版了《从村庄解读中国——华北农村五十年史》。对于这场前后纵贯半个世纪、规模庞大的中国调研,“平野·戒能”论争的是非已不足论,但报告提供的相关数据至今对理解中国农村、中国革命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和思想史意义。 显然,内藤、平野、森谷克己(以共同体理论完成了对魏特夫“东方式社会”的日本重构)都试图对中国的历史潜流及其社会性质给予某种本质主义解释,有意或无意地为侵略战争提供了思想和学术支撑,然而“优等生”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却因误入歧途,最终盛极而崩。战后,军国主义退潮,那些时代的弄潮儿就有些尴尬了,他们大多对自己战前、战时的言论缄默不言。战后日本思想界中国观的转型,不仅是东京审判、盟军司令部战争责任追究等国际政治力量复杂博弈的结果,更受到人民中国成立的巨大冲击。如果说北一辉和橘朴等现场主义者的中国论是建立在“内在于中国”的前提之下,那么,竹内好所建立起的“内在于我的中国”立场,对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乃至日本人中国观之影响都可谓无远弗届,这与平野、森谷等人的中国论类似,皆可视作某种目的论导向的价值判断,后来者加加美光行所谓“内在于我的‘文革’”“内在于我的大众”皆为类似的逻辑构形。某种意义上说,从竹内好、加加美光行、沟口雄三,甚至子安宣邦,都在“中国的冲击”下完成了自己的中国论。 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好在中国的巨大影响与其鲁迅研究关系甚大,以至于“竹内鲁迅”也已成为国际鲁迅研究、中日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对象,尽管学界依然对其价值认知分歧较大。值得注意的是,竹内的中国论亦是被作为鲁迅问题来处理的,他放弃了时间性尺度,以“奴才论”(竹内式的解读)为中心比较了两国的近代化:日本的近代化被描述为屈从的、他律的、虚假的,以此为参照,中国的近代化则是抵抗的、自律的、真正的。无论是鲁迅、毛泽东,还是中国革命,竹内笔下的中国形象始终是以对“近代日本”的自我否定为前提描绘出来的他者形象,其憧憬的对象并非客观的中国,而指向了自我主观层面折射出的“内在于我的中国”。可以认为,竹内对“日本与东方近代”的再审视,是日本战败、美军占领与解放,以及以中国革命为代表的亚洲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等政治事态倒逼的结果,他构建起的对中国之“憧憬”成为加加美光行、沟口雄三那代中国研究者的思想起点。而六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政治状况却使得日本的中国研究受到很大的刺激,进而发生裂变:竹内变得沉默;沟口则带着五分批判、三分困惑和二分共鸣,批判地继承了竹内,并将问题迂回转移到对“中国革命”之历史认知形态的讨论;加加美则在竹内沉默之处通过引入吉本隆明的“大众”概念、重述竹内建构起他的中国革命论,最终奇妙地将其混同为二十一世纪转型时期产生的后现代式斗争课题中,在亚洲革命的框架下肯定了那场 “革命”的价值。然而这一切都基本建立在同一个前提之下——不在场。“内在于我的中国”之提倡者们都未曾像北一辉、橘朴那样以“内在于中国”的姿态见证那场“革命”,这恐怕不得不说是一个先天的缺陷,也成为其论敌们质疑的渊薮。子安试图强调的是,“内在于我的中国”,作为“日本”“日本近代化 ”的反向设定,只能是一种主观性、绝对化的憧憬,据此不可能为中国革命史给出有效的解释,更不可能准确地把握中国乃至东亚的未来,因为那不是真实的中国。
鲁迅与竹内好(来源:westernsydney.edu.au)
子安宣邦这本《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可以从日文原题直译为 “近代日本是如何言说中国的”。它虽 “以中国为名”,但实则是对日本对华观念史、言论史的一次深刻检省,亦可视作言论家子安宣邦以 “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展开的一项介入性工作。他呼吁变革日本近代知识制度建构起来的“中国形象”,重新赋予日本的中国研究以活性和批判性。子安坦言:“二十一世纪的当下,我们仍身处世界性危机之中,并愈发强烈地意识到,东亚共同世界的形成有赖于各国自我的变革。”这里所谓的“世界性危机”,显然是以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大衰退为语境的。二〇一六年,耶鲁大学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犀利地指出,世界经济已大范围地染上了“日本病”:发达世界的主要增长引擎受困于日本式的长期性经济停滞,生存在这个相互依存世界中的其他国家也备受煎熬。我们再也无法对他者的苦痛隔岸观火——“伊斯兰国”、欧洲难民危机以及近来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全球股市大崩盘,都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重审对“全球化”之逻辑的认知,调整对其前景的期许和应对姿态。我们不得不如子安所指出的那样,将本国的变革与亚洲诸国、世界诸国的变革,予以共时性、联动性的思考。 前些年,有日本政治家以欧盟为范本而力倡“东亚共同体”,这一构想尽管在中日思想界反响不大,却颇值得玩味。对此倡议,乐观者有之,也有人念及“大东亚共荣圈”的往事而深怀疑虑。由于种种历史的、现实的原因,泛亚主义构想与人们对其倡导主体、时机乃至对其警惕和批判似乎总是如影随形,但这绝非杞人忧天。以橘朴为例,“亚洲主义”固然为其打开了新的思想视界,然而又不得不承认,加入关东军将校的“革新计划”、参与“满洲国”建设依然是一种“危险的投企”——在东亚近代史上,侵略往往是以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愿景为旗号、诱饵和驱动力的。面对诸种共同体构想,思想界当以何种心态和姿态予以回应,是不得不慎思的问题。知识界需要的恐怕不仅仅是稳健、深邃的历史分析,更需要“在场”的言论家们带着温度、知性和批判性写作的形势论、状况论,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局中人、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