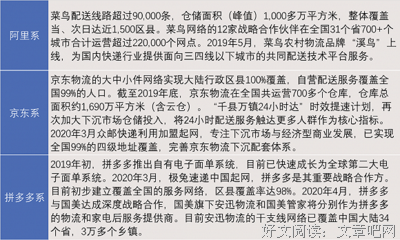
《理念人》是一本由[美] 刘易斯·科塞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80元,页数:40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理念人》精选点评:
●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
●知识分子的类型学
●讲述知识分子演变过程
●很喜欢,本科一度想做知识分子相关的研究。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而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
●知识分子社会学 社会调查
●社会学的角度有助于还原知识分子的凡俗身份
●还行吧,虽然俺再自吹也不是知识分子
●在卡尔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有所发展。知识分子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及其地位影响力不断进步发展的社会学作品。我们有太多被禁锢的头脑,这样的作品很是推崇。
●第一部分阅读快感好过后两部分,尤其是第二章讲法式洛可可沙龙;第二部分的结构功能味道太重了...
●这一年里每当哲哲同学问我怎么变得这么伶牙俐齿的时候我都骄傲的说因为我看了社会学心理学的书 所以接下来的一年里要继续好好看书 这本很好看
《理念人》读后感(一):关于《理念人》
很有趣的一本书,作者原本是想通过描述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社会学背景来说明与之相关的文学风格变化。但最终写成的是一本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学考察。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首先,理念人——men of ideas的概念。这是作者给知识分子的新称号。这个称号显然让人联想起plato的那个著名概念。所以,在作者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暂且不论其立场——都是基于ideal的一类知识人。他们有特定的生存场所(sect),特定的价值立场以及特定的时代风格。这样,知识分子与物质保持了疏立,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时代的心灵。在我看来,men of ideas主要是近代启蒙之后的产物,在西方其前身就是教士。我们可以拿中国古代的“士”(不是士大夫的士)来做并不恰当的类比。
第二,科塞所使用的方法是知识社会学。他曾经告诉本书的策划者郑也夫说,对他本人影响至深的社会学家有三人,即马克思、韦伯和西美尔。郑也夫又给他加上了卡尔曼海姆。这四个人对科塞的影响是显著的。曼海姆的影响自不必赘言,通过考察社会的知识背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西美尔的影响主要在于,西美尔具有的那种敏感或诗人气质,使科塞能够极尽准确的把握社会学中那些并不起眼,或十分纤细的东西。这也是我最欣赏的一点,因为我痛恨大言煌煌的写作。
第三,本书最有趣的是前两部分,即知识分子的场所、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第一部分,通过考察知识分子所处的沙龙、咖啡馆、酒馆、报纸……等来为理念人寻找理念的容器。第二部分,则分别考察了与权力保持距离的、批判权利的、为权利辩护的、从内部影响权利的、从国外寻找价值的种种理念人行为。这些,都为我如何写作论文提供了思路上的帮助。
最后,稍稍谈一下感受。科塞定义的理念人其实就是历史的推定力。西方历史的发展与变化,绝不仅仅是一个制度的演变,在形式化的制度变革下,有着无数理念人各种各样的行为。但无论他们的行为怎样,从启蒙以来,这些理念人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基础:追求言论的自由。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言论的自由,这些理念人无论持什么样的观点都无法对社会产生影响。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的社会,是无法想象作者在书中列举的各种杂志、报纸、书籍、沙龙、集会等的。这当然会让我反观自身,却不得不无话可说。
《理念人》读后感(二):有序的参与VS无知的群众
精英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政治参与的有序调控和对群众理性的无知认定。而大众政治恰恰在反对对有序政治参与的调控的同时实践着群众的无知理性。所以,亨廷顿才会大肆的写到,政治秩序比之自由更甚。尽管他也描述过第三波民主的浪潮,但是较之变动社会所应确立的政治秩序来说,后者显得更为重要。这也是他对于西方政治,特别是拉美政治的得失在战后基本发展的一种梳理,不过,与他相对的一些人,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在实施有效控制的体系下还实践了所谓“大民主”的理论。在那个群众的理性都归于一个人理性的年代,中西方都在某种思想的作用下推崇“反智主义”,这是一种契合或者说是一种悲哀。有序的政治参与怎样才不至于被群众的无知理性所击败,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解读往往是依靠知识分子与权力关系的介定来阐明的。
这就来看看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关系,在读了福柯后,我知道原来知识本身也能产生权力,但是在读了科塞之后,我才发现,原来知识分子和权力有如此微妙的关系。这本科塞的《理念人》(中央编译出版社)是当初四折买的,本来翻过几十页,因为的确应了郑也夫的话,译得的确不好,所以就搁下了一两年吧。之间也涉及过中国的一些“假古董”放出的“知识分子光芒”。实在是很无知。
科塞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在文化社会学的老祖师爷曼海姆的影响下,对西方知识分子的产生、分类以及与权力的关系,还有当代美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分析。其实科塞是搞比较文学出身,所以他所涉及的知识分子往往偏于文学人物。这本诞生于六十年代的书影响,在我看来可能是对权力控制下的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其中,近年美国政治学界中有两位博士的两本书也在探讨政治学中的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第一本书的全名是《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第二本书全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701148/但是,对于我们国家,往往还没有一本反思自身的书出现。
所以,当我们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得不面对任何实施有序政治参与的时候,如何面对对群众无知的假定,将会是一个核心。因为,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往往决定了是对群众无知的赞同还是反对。换言之,到底是精英政治,还是大众政治,这是一个要追问的。假使是大众政治,那么往往会蜕变为“民粹主义”,而精英政治,则有滑入“寡头统治”的危险。
欢迎与我讨论:http://zimingwu.blogbus.com/
《理念人》读后感(三):权力和现代化“双打”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词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可能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俄国人对法国精英的羡称,一个是法国社会对德雷福斯事件中支持德雷福斯那些精英的叫法。知识分子的英文是intellectual,除了该义外,这个词还含有“(a.)想法的,思维的,智识的”等意思,可以看出该词比较强调“主观”上的活动,如”intellectual history”即有“思想史”的意思。与它相较,”rational”(理性的,合理的)偏重“实践”。可以说,intellectual和rational是认识世界的两种方式,它们都是理性的,只不过前者强调主观活动,后者强调实践活动。
在书中,科塞用“理念人”(men of ideas)来形容知识分子。从我们习惯的英文语法上来说,men是从属于ideas的,也就是科塞所说的“为理念而生”(不是用理念吃饭),所以科塞在intellectual和men of ideas中间划了个等号,而在intellectual和rational划下了界线。
在科塞看来,知识分子知识广博,例如启蒙运动中的那些知识分子,名字后面总是连缀着几个“某某家”,关心的是社会核心价值,追求的是普遍真理,对社会中不美好的现象总要加以批判和审查。而对于“用理念来吃饭的人”(窃以为是专家),科塞是不怎么高看的。也就是说,科塞眼中的知识分子是不同于专家的,他们涉猎广泛,先天先下之忧而忧,甚至有一点”ideal”(理想的,完美的,不切实际的),乃至于”idealism”(唯心主义,理想主义),毕竟相较现实的缺憾,只有理念中的东西才是完美的。
总之,知识分子有三个特点:知识广博,批判社会,理想主义。
知识可以产生权利。动荡中的社会为知识分子和权利的联合提供了契机,但追求理想主义又使得知识分子和权利分道扬镳,或者被权利驯服。当权利和知识分子结合时,科塞列了三种关系:掌权、内部穿孔、帮助权利的合法化。置身以上三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最后要么被政治实干家取代,要么放弃自主权变为专家,要么被权利抛弃。当权利和知识分子对立时,作者列出了两种关系:权利的批判者和向国外求助。这两种情境下的知识分子,前者自比社会的良心,利用舆论的力量向决策者施加影响;后者则破坏自己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把目光转向国外寻求更和谐的状态,但容易美化外国。科塞称赞“权利的批判者”,如废奴主义者和德雷福斯派,描述前者为道德运动、良心政治,把后者叙述成在正义的要求与秩序的要求之间斗争。
随着社会的稳定后,知识分子被整合进了公共生活之中。权利渗入智识生活中,管理着人们的专业研究和对社会的态度。知识分子产生于十七世纪,到了作者生活的时代,他们还要面对现代化的挑战。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分工变得愈发发达,一个门类下面会分成许多科系,且科系之间往往不相熟悉。在这种背景下,以往的综合角色正在逐步减少,而专业化则逐步增强。伴随着发达的分工,科系队伍变得膨胀,一个项目的完成往往需要多人合作,这使得管理变得困难,于是行政首脑自然希望手下的队伍变得“规训”,以降低管理成本。进一步,用一套制度把学术研究的制度(例如大学制度)和规范推广和固定下来,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则变成了专家。更严重的,是分工导致的“劳动异化”,乃至“灵魂禁锢”:知识分子是通过作品来确认自我价值,但现代的作品很难说是他一个人的。知识分子很可能迷失自我。
在权利和现代化的“双打”下,知识分子越来越少。科塞说,“只有脑力技术人员和专家的世界,社会文化是会僵死的。”对于现代化加速的学科专业化,科塞并不反对,他反对的是外在强加的专业化,即制度,例如大学的科系,它们只重专业而忽视素养。科塞的呼喊已经得到普遍的响应。大学的改革已经展开,例如国内开展了博雅教育(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
《理念人》出版于1963年,彼时的美国正值社会动荡时期,各类社会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整个美国都在反思,科塞将他的反思写成了这本书。而现在,似乎是处于上一个时期的更改和新的问题滋生时期。克林顿之后,再看看希拉里,都是科塞时代的产儿。
《理念人》读后感(四):作为边缘人的理念人
“他是个犹太人也是个非犹太人;美国人和欧洲人;坚定的社会批评家,热衷于评判和行动,还是活跃的倡议者;左派支持者和批评者;落魄书生和官僚知识精英的辩护人。”
——詹姆斯•B•鲁尔
上文引自科塞主编的《异见》2003年秋季刊的悼文,悼文的主人公正是本次阅读的《理念人》的作者——刘易斯•科塞(1913-2003)。这个出生于德国,1930年代流亡到法国,40年代移民美国的犹太学者,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以社会冲突理论研究著称。该书是科塞继1956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社会冲突的功能》,60年代的《社会冲突研究续篇》的第三本书。60年代以反越战为背景的社会运动席卷美国知识界,各种学生运动、人权运动等相继兴起,科塞因此声名鹊起。然而科塞却在60年代开始转向社会冲突领域以外的其他研究,于是有了《理念人》这本关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社会学著作。该书讨论的是文化和政治等社会制度,对西方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有利或阻碍作用。那么,科塞为什么在此时写一本这样的书?他想通过理念人的历史和现状回应什么问题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对理念人及其文化和政治背景有所了解。
依据韦伯对靠政治而生和为政治而生之人的划分,作者认为“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 知识分子有以下三个特征:超越眼前的具体工作,自命为理性、正义和真理等抽象观念的专门卫士,道德标准的忠实捍卫者;执着追求理念的终极价值,却常常对权贵报以戏谑态度;具有批判的态度。
尽管历史上存在具有知识分子倾向的人,但只有到了17世纪,近代社会才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登场提供必要的条件——舞台和观众。以启蒙运动为背景,公共空间和文化市场的建立,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广泛的听众,也为其提供了与同行交流的平台:17世纪的法国的上层社会的洛可可沙龙、英国的皇家学会,18世纪的伦敦咖啡馆,著作市场的建立使文人作家开始独立于权贵,而19世纪写作商业化却带来金钱和名誉的诱惑,英国的评论杂志为泛滥成灾的出版物建立标准、塑造公众舆论和偏好。公共空间和文化市场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提供正面的条件,审查制度则对知识分子传播思想起负面作用,这个工业时代社会控制的工具,表面上阻止了思想的流动、分化了读者,实质上却提高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意识和使命感。制度化的环境是知识分子直接或间接接触公众的媒介,也为政治宗派和边缘知识群体提供“躲避注意的盾牌”,拿破仑后期的圣西门主义者、美国格林威治村的反主流文化群体及其小杂志为我们提供了案例。
理念人凭借知识和思想在文化空间生存下来,但捍卫真理和批判社会的态度往往使理念人难以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根据理念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科塞把理念人分为以下五类:掌权知识分子,内部渗透者,帮助权力合法化者,权力批判者和诉诸外国者。前三者可以说是积极介入政治,事实证明理念人与政治的蜜月期是相当短暂的。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这样以革命掌权的知识分子、从旁影响政治的费边主义者和罗斯福智囊团、拿破仑时期的国家科学院和持修正主义的戈穆尔卡,他们都以一定的理念介入政治权力,随着国家机器的理性化和官僚化,或被国家机器所整合、或反过来被政治打压、甚至被原来的理念所异化,逐渐失去证成或批判政治合法性的作用。相对而言,废奴运动和德雷福斯事件中的知识分子出于道德良心,跳出狭隘的专业领域,利用公共舆论迫使当权者停止权宜之计,体现了理念人超越具体事务、捍卫理念的批判精神。最后一类理念人在本国出现社会弊病且改革无望之时,往往会把理想寄托在对东方国家的崇拜上,如18世纪崇拜中国和俄国、1930年代吹嘘苏联社会主义,不过,一旦神像倒塌,这些都仅仅是崇拜而已。
前三类知识分子积极介入政治,第四类以独立身份批判社会,最后一类则暂时退却。作者对第一种理念人着墨甚多,特别是帮助权力合法化的知识分子的悲惨结局,读来让人唏嘘不已。如果用整合、疏离(独立)和退却分别对应这三种理念人(当然,积极介入政治的理念人也可能采取疏离的态度,比如韦伯夫妇),那么作者更欣赏抵制完全整合与彻底退却的疏离态度,比如中间穿孔的韦伯夫妇,为了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德雷福斯阵营知识分子。甚至他认为一定程度的疏离是知识分子的宿命:“一定程度的异化(笔者按:alienation,参照上下文,与“疏离”同义)似乎是知识分子永久的命运;批判精神和不受束缚永远是他的标志,因此他总是在一个社会中但又不属于这个社会。” 但是,这种与政治权力的疏离并不是政治冷漠的代名词。理念人的职责和使命在于,以普遍的真理和价值批判社会,这决定了理念人必须超越自身的利益和具体的事务,“这种独立性又是建立在对社会赖以存在的理想和中心价值的深切关心之上的”。
走笔至此,作者此书的目的已甚为明朗。超越具体事务、捍卫普遍真理的批判精神是理念人的特征所在;从权贵资助中独立出来的知识分子注定一方面要面对市场的压力,一方面要抵制政治上的整合和退却的双重诱惑。这本书写作的1960年代,原子化的美国知识界正受到华盛顿这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全面控制,作者忧虑知识分子受到整合而失去批判性。理念人作为理想类型,寄予了作者对美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如果知识分子能设法避免完全退缩和彻底整合的双重诱惑,那么他们在未来的美国当然仍然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游走在完全退却与彻底整合之间,是一种边缘人的状态。科塞一生为边缘人的生活形态做出注脚:背井离乡的犹太人,美国的欧洲人,价值中立的学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左派的支持者与批判者,既为平民又为精英辩护。试想,如果没有理念的支撑,在角色如此多元的当代社会,知识分子恐怕会精神分裂了,遑论批判社会、改良社会道德了。
《理念人》读后感(五):理念人
一下内容仅是个人阅读此书前半部分的读后感或一点归纳,一家之言,希望对想看此书的你有所帮助!
知识分子的定义虽然是如此的含糊且具有争议,但又是如此重要。在讨论知识分子的产生和存在这个问题时,对于知识分子主体的定义和界定是不能忽视的先决条件,我赞同作者书中对“知识分子”进行严格的限定。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而不是靠理念而生的人。对于此我的理解是:不是所有的受过教育的或某方面的专业人员都是知识分子;也不是所有对宇宙作了终极思考或探讨社会的核心价值的人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具有怀疑精神,依靠理性来思维,不满足于一成不变的现状和思维,追求正义和真理,拥有绝对的独立和自由得人。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群体开始出现,作者认为是在17世纪。同时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的存在具有更加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是在远古时代、轴心时代还是中世纪都存在一些“具有知识分倾向的人”。17世纪作为知识分子出现的界限,因为只有到了近代社会才能为知识分子提供其存在必须的制度化条件,这一过程是伴随着近代化的。
在混沌的原始社会,人都还是单纯的自然人,但是这种状态伴随着文字的出现和哲学的突破而结束。当人类具有了自我的意识,自我的反思能力创造了人类的精神世界。最早的巫师是最早的思考者,知识者。当宗教出现以后对于世界和自我的思考能力,以及人类积累的知识传承到了教士身上。教士是中世纪欧洲知识的垄断者,知识分子从教士分化而来。教士垄断知识,也对宇宙和社会有自己的一套思考,但是教士和知识分子的最大差别就是教士的思考来源于坚贞的信仰,而信仰是不容怀疑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核心价值有着强烈的关心,获得知识、运用理性、怀疑一切的精神。中世纪的僵局在文艺复兴的打击之下开始了蜕变,教会的腐败激发了人们对于神权的怀疑,而这种怀疑精神,进而激发了人们广泛的人文主义精神。知识分子在抛弃神权之后来观察世界,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使得知识分子拥有了无止境的动力。但是此时的知识分子还必须依赖于贵族的庇护,没有物质的独立就没有精神的绝对独立。在启蒙运动的洗礼之下,知识分子最终形成。
知识分子以完整的面目最终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应该是在启蒙运动之后,或者是伴随着启蒙运动而产生的。启蒙运动第一次标榜“理性主义”,普遍的理性思维也是之后才有的,完整的理性思维系统的建立之后,知识分子只有运用了理性才能称其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诞生,经过了文艺复兴的“破土而出”,在启蒙运动是才最终“羽化”。只有经过了启蒙运动的洗礼,知识分子才最终出现。将启蒙运动是视为知识分子最终出现的界限,不仅仅是因为理性思维是区别知识分子和旧时文人明显标志。而且,没有启蒙运动的开展,就不会出现独立的公众给予知识分子以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在启蒙运动之前,社会环境的限制,知识分子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无法做到完全的独立和自由。而这些品质又都是知识分子独立存在的思想灵魂。
科塞在《理念人》中指出“知识分子在职业社会中存在并得到承认 ,有两个必要条件,知识分子需要听众,并给予物质和精神的支持;知识分子需要与同行进行讨论接触帮助知识分子建立共同标准和明确的群体自我意识”而这种条件在17/18世纪的一些知识分子活动场所开始得到满足,这些场所分别是沙龙和咖啡馆、科学协会、月刊和季刊、文学市场和出版界、政治派别、波希米亚式的场所和小型杂志以及审查制度。
沙龙和咖啡馆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机会同行的知识分子以及公众得以聚集在一起,摆脱阶级差异带来的隔阂。科学协会帮助科学事业制度化和合法化,并且赋予了尊严。这三种知识分子活动场所的共性在于,将知识分子逐渐集合在一个依附性越来越小的集体,都使得知识分子能与自己的同行及受众直接接触。但是,知识分子活动场所也在经历着变化。沙龙作为最初的场所,本身经历了许多的变化。沙龙的非贵族化和讨论范围有文学而逐渐广泛。咖啡馆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比沙龙更加自由、开放和平等的机会,并伴随着知识分子的专业化。这种变化以专业团体的形式逐渐固定下来(例如皇家科学协会),最终实现知识分子的凝聚。
由于知识分子的局部专业化聚集,知识分子与读者之间的联系由书籍刊物替代了最初的直接接触。另一方面日益扩大的读书届,要传播知识和思想就得借助书籍这一类快速而大范围的传播工具。但是当书籍成为一种商品,写作第一次成为一种独立职业。作为作者和读者之间连接人的书商,将市场化的精神带入了知识领域。资本主义将一切都市场化了,也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写作使知识分子可以摆脱对庇护人的依赖,但又一次陷入了与书商的纠结之中。写作的商业化,使得知识分子直面诱惑,许多知识分子为此而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艺术独立性,但不是绝对的。
“在读者人数急剧扩大,从而引起出版物泛滥的时代”迫切需要有知识分子来帮助读者建立标准、指导品味并且帮助读者表达意见。评论杂志和审查制度有着相似之处,但是审查制度往往发挥着于统治者相反的作用,反而促使了知识分子集体意识的凝聚,自我意识及使命感的增强。
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经历沙龙、咖啡馆一类的是实体场所,到协会团体,最后到以某杂志为中心派别。知识分子的活动场所逐渐的抽象化和多样化。接下来的三种场所分别是排外性的政治派别、反规则格林威治村、反对现行文化和极端创新的小杂志,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活动场所,体现的是知识分子分化的结果。同时他们具有共性,就是强烈的排他性,只走偏锋。这样极端的知识分子群体,表面上看来与社会格格不入,但是他为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当代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进一步的扩展,网络的发展成了知识分子新的活动空间。他又一次将所有的人带入了“沙龙和咖啡馆时代”,同时知识分子活动场所的历史变迁,也在网络这个虚拟社会里再一次出现。网络替代了部分季刊和书籍的功能,同时知识分子对于书商的依赖也有所降低,但是审查制度也进入了网络社会。独特的政治派别、小杂志也在网络里出现了对应物。网络是真实世界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