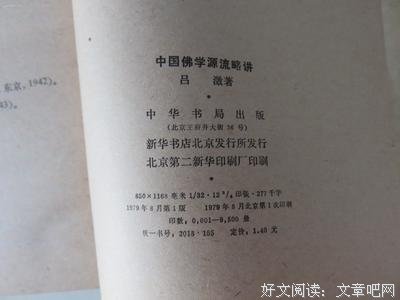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是一本由吕澂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精选点评:
●看了一半,头皮很麻。
●已购
●需要反复钻研的说。这哥们真的很牛,昨天说过中国美术要革命,第二天就扎到佛教义理堆里面献身去了,真狠~
●哇,很专业,略略翻过,不求甚解。因为实在看不懂,这个专业果然也不是一般人想学就学的。
●不服不行!
●厚积薄发的典范
●硬着头皮读完第一遍。作者学养深厚,高山仰止。寥寥数语,厚积薄发。第一遍只得个印象。像预习了一本教科书,发现了一个俱乐部。千年历史中的一些特定人物故事浮光掠影。所谓源流,到宋即止,恐怕因为人生很短,历史也短,区区千百年的间歇,并不值一哂。
●吕老师此书的遗憾,在于其重点是源流二字,重流变和传承,而不得不减少对佛学思想本身的阐释,无基础的人读罢只有散乱的理论和概念,很难对佛学有一个面貌上的了解。但读完翻了翻其他佛学的书,又多是“成一家之言”,在自己的学说里钻着不出来,全无这种并观间的旁通。二者不可兼得,还是建议先有底子,再来溯源流。不然就要像我这样,竟一时不知读何书。
●: B94/6631-1
●19.06.30 /120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读后感(一):虽然略,却是相当精要
不但讲源流,还间涉及对佛教一些基本问题的论述,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本体从语义学上入手的辨析,澄清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此外,我感觉吕老学佛用功最勤的是玄奘一系的唯识学,他能够追本探源,揭示出玄奘对唯识的翻译“每参以己意“,不是最可靠的翻译,应该说吕老不带一点门户之见,唯以事实为本,这种学术精神也是很了不起的。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读后感(二):这是我感到欣慰的事
中华书局编辑部在出版说明里写道:
quot;由于作者在讲课中片中佛学知识的传授,因而未能暴露其唯心主义本质和对人民的毒害作用.对于佛教个宗派的兴衰,只介绍了它们本身发展的脉络,未能深入揭示其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对某些代表人物,也只强调了他们对佛学发展的作用,而未能进行必要的分析批判.这些不足之处,由于作者年老又在病中,已不能弥补,这也是作者引以为憾的事."
----最后一句已至可笑之极,这恐怕只是编辑"引以为憾的事"吧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读后感(三):源流与略讲
中国佛学将近二千年的发展史,留给后人的确实太多,若非精研,要从浩瀚的典籍中认识中国佛学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从吕先生这部不厚的讲稿上认识中国佛学确实不失为捷径,尽管这条路也不是太好走。
书的特色其实从书名也基本体现了。
一是源流。先生条分缕析,将中国佛学从传入到宋明的发展源流一一道来,有背景,有师承,有学术要点,有思想变迁,特别是不同流派间的往来回应,虽然文字不多,却是入木三分,让人深有启发。
二是略讲。由于本书是根据先生的讲课内容编成的,“讲”的特点确实很能体现出来。文中很多写法大概是讲课时的常用手法,如对一些典籍文字的解析,娓娓道来,将原本深奥的佛学语文和思想说得如此清晰、易懂,恐怕也不太找得第二人了。只是书确实有点“略”,让想窥见一点中国佛学门径的人有点畏难,原因大概也正如前言所说,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读后感(四):[笔记]记个系谱
一、佛学的初传
《四十二章经》摘自《法句经》。
安士高译小乘上座部,禅数学。禅即定:安般守意,安:吸;般:呼。数即数法/对法,即毗昙/阿毗达摩)。
支娄迦谶译大乘,般若。缘起性空,自性空。小乘讲禅为十念;大乘讲般舟(念佛)三昧与首楞严(健行)三昧。
二、西域传本佛典的广译
般若的“性空”与玄学喜谈的“无”靠近。
朱士行,汉人出家第一人,讲般若,译《放光般若》。
竺法护译般若、宝积、华严、法华、大集等,勾勒大乘轮廓。推《法华经》以大摄小,以一乘为究竟。
三、般若理论的研究
罗什前的般若学与玄学接近,研究方法主要有“格义(以中国固有概念解佛教概念)”与“六家七宗(能所结合:大智照性空;实践空观)”。僧肇则论三宗:
1.心无宗,支敏度。“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不空境色,空心(不起执心)。脱胎于郭象玄学,未得龙树中观真意:空(非有),假(非无),中。
2.即色宗,支遁(道林)。“色即为空,色复异空”:从概念范畴的色可得物本身的非色(即空),色的范畴即异于物体之空。僧肇批评他从认识论上概念化、虚无化“空”。支遁认识的是共相的色即为空,僧肇批评的是自相的色非空。另有“即色游玄”说。
3.本无宗,竺法汰。既非心无,也非色无。万物本身即无。僧肇批评偏于无。
4-6.本无异宗,识含宗,幻化宗。
7.性空宗(本无宗),道安与弟子僧叡。“功托有无,照本静末”。“本无(自性空)”和“末有”。“五阴至萨云若/一切智(可道之道)”与“一相/无相(常道)”不可相离。般若应与止观(禅、智)结合。
四、禅数学的重兴
小乘四系:上座、大众、说一切有、犊子。慧远主持翻译《阿毗昙心论》与《三法度论》,撰《阿毗昙心论序》(影响《俱舍论》):“显法相以明本,定己性于自然,心法之生必俱游而同感。”
烦琐的毗昙学被用来代替玄学清谈。
《三法度论》以三分法统摄,属犊子系贤胄部,从“受(有情的个体)”“过(连接三世的主体)”“灭(体现涅磐的个体)”三种施设,主张有“胜义我”。
小乘禅从安士高起,讲究对治,分五门:贪修“不净观”,瞋修“慈悲观”,痴修“因缘观”,寻思重修“安般(念息)”,平等(一般)人修“念佛”。到鸠摩罗什、觉贤/佛陀跋陀罗、慧远释达磨多罗等已渐融入大乘,禅观空观与法相结合,“阖众篇于同道”,五门合一。
慧远以“无性为性”,体现了当时对大乘理解的究竟。
五、关河所传大乘龙树学
鸠摩罗什弘龙树、提婆四论《中论》《大智度论》《十二门论》《百论》,释境、行、果中境为“中道实相”(有称罗什为“实相宗”),真谛看为空(非有),俗谛看为非空(非非有),二谛一体,色空相即,即为实相。影响三论、天台二宗。
弟子僧肇《肇论》:《物不迁论》(“动静未尝异”,反对小乘执着“无常”之人;反对三世有)《不真空论》(“不真空”:假名为空。反对小乘以极微的“宰割”式分析,认为万物原本是空,有象形,无自性。自性属于假名。)《般若无知论》(涅磐之能照在无知,所照在无相。内有独鉴之明(能照,寂),万有万法之实(所照,用))《涅磐无名论》。
后有僧朗、摄岭、吉藏三论宗之兴。
六、南北各家师说(上)
罗什徒道生《顿悟成佛论》,重十住最后一念“金刚道心”以得正觉。
《法华》讲“佛身是常,佛性即我”。法显传《大涅磐经》,提出“如来藏”,将“心识”作为“法身”本源,为瑜伽行开启道路。道生提出《佛性当有论》,当果是佛,佛性当有。一阐提也可成佛。
经类繁多,“判教”出现。慧观分“顿教”、“渐教”。顿教为《华严经》,渐教分五时:1.“三乘别教”,《阿含》;2.“三乘通教”,《般若》;3.“抑扬教”,对三乘分高下,《维摩》《思益》;4.“同归教”,三乘殊途同归,会三归一《法华经》;5.“常住教”,如来法身是常,《涅磐经》。
各宗皆讲涅磐,未成宗派。《涅磐》讲“佛性”是常,众生皆可成佛。“性”字面为“界”,意佛性即“佛因”,待缘而起。因此,不光是心,重点在“境界缘”或法相上,“佛性指境。”
吉藏举十二家佛性说,分别列众生、六法、心识、冥传不朽、避苦求乐、真神、阿棃耶识自性清净心、当果、佛理、真如、第一义空、中道为佛性,分为“人(人为假,五蕴为实)”、“心”、“理”三类。随着瑜伽大乘发展,佛性说渐从吉藏重理转向心识方向。
同时出现佛性“本有”或“始有”之争。
《成实论》为譬喻师推动小乘毗昙发展的结果。“实”即“谛”,主要反对有部,认为法无实体,四大为假名(故又称“假名宗”)。意义在“法空”,成为划分大小乘标准。
毗昙师在北方持续兴盛,有注《阿毗昙心论》的《杂心论》,为《俱舍论》前身。毗昙重因缘实法,又称“因缘宗”。开善智藏、庄严僧旻、光宅法云代表的“成论大乘师”认成实论为大乘,或由小入大,被三论宗称为“南方大乘”。
此时大乘包括一切学说,由判教来解释各部联系。
僧朗复兴三论,与新实宗对抗。法朗著《中观疏》,被尊为“山门玄义”,反对成实师仅看到“假名”,用“中道”统归假名和因缘,赞同二谛合一。
七、南北各家师说(下)
北魏推佛。菩提流支译《十地经论》,传播世亲“染净缘起,三界唯心”,形成“地论师”,后出“北道系(道宠)”“南道系(慧光)”,后被贤首宗吸收。北道依阿梨耶识,佛性始有(当果),讲五宗特别是华严;南道依法性,佛性本有(现果),讲因缘宗(《毗昙》)、假名宗(《成实》)、不真宗(《般若》)、真宗(《华严》《涅磐》《十地经论》)。
求摩跋陀那/功德贤译《楞伽经》,达磨传禅法于慧可,“忘言、忘念、无得正观”,重口传不重文记,成“楞伽师”。传僧粲、道信、弘忍,不再行头陀行,定住山林,到神秀蔚成大宗。慧能一系转推《金刚经》,一度埋没了楞伽一系传承。
达磨教人“二入”“四行”:理入(深信、壁观)与行入(报怨、随缘、无所求、称法)。
摄论师:瑜伽行学说变化很大。真谛译《摄论》《俱舍》,主张第九识阿摩罗识/无垢识/净识,结合“如如”与“如如智”,举“三性”为总纲。接近难陀旧说,重视《摄大乘论》。《俱舍》《摄论释》分别代表了前后期思想。法太、昙迁等传续摄论师一脉。后为玄奘重译《摄论》所淘汰。
轮回与犊子有我论:形由识感而成(五蕴结合),神以形化而流传。胜义我为“补特伽罗/数取趣”。慧远论有神,神不灭思想广泛流行。范缜写《神灭论》。
八、宗派的兴起及其发展
南方偏玄谈(义学),北方偏实践(禅法)。到南北朝末期开始融合,形成固定宗派。
智顗创天台宗(法华宗),上溯北齐慧文(“三智一心”,“一心中得”,“三谛一心/一心三观(假中空)”)和南岳慧思(“十如是相”),来自龙树思想。智顗发展为“圆融三谛”,假中空同时存在,对应观照(认识)、资成(对其它法的作用)、真性(本质)。
智顗晚年接触地论师和摄论师。地论师以法性为诸法本源,摄论师以赖耶为依持。智顗提出“性具”,指出法自然存在,既非自生,亦非他生。六道四圣构成十法界,每一法界有十如,互相蕴含则共有千如,配合“五蕴世间”“有情世间”“器世间”三种世间,成为三千法,一念三千。“性具实相”,成为天台宗中心理论。
灌顶、法华智威后,天台一度失势,直到荆溪湛然中兴。
教方面,智顗考察“南三北七”。渐教三种:1.“有相教”讲佛法实有;2.“无相教”讲空、无自性(《般若》《维摩》到《法华》);3.“常住教”讲常、乐、我、净(与无常、苦、无我、不净相反,《涅磐》)。后增加“同归教”(《法华》)及“抑扬教”(《维摩》《思益》),与慧观“五时”同义。
北七:1.北地师举提谓、波利“人天教”,并“抑扬教”入“无相教”,成北地师五教。
2.地论师菩提流支以渐顿分“二教说”。
3.地论师佛陀扇多、慧光分“因缘宗(小乘毗昙)”“假名宗(成实师)”“诳相宗(《大品》《三论》)”“常宗(《涅磐》《华严》)”四宗。
4.护身自轨(“大乘师”)将《华严》分为“法界宗”,成五宗。
5.耆闇凛师将《法华》分为“真实宗”,《华严》《大集》应称“圆宗”,成七宗。
6.《华严》《般若》讲修行次序,为“有相教”,《楞伽》为顿,为“无相教”。
7.佛法皆一,一音异解,“一音教”。
智顗提出“五时八教”:第一时《华严》,第二时小乘教,第三时讲一般大乘如方等,第四时《般若》,第五时《法华》《涅磐》;形式上分为顿、渐、秘密、不定,内容上分为藏(小乘三藏)、通(通三乘)、别(大别于小)、圆(圆满)的(天台)“化法四教”。
天台重教观,形成了庞大的体系。
隋初官方分五众:《涅磐》、《地论》、《大论》(《智度论》)、律、禅。吉藏以辩才兴盛三论宗。禅教并重,推《智论》《中论》并讲《法华》《涅磐》,讲中道、二谛,与天台相近。学说与方法论上来说,三论着眼“无所得”,不执着于“立”或“破”,以否定表达观点;天台“一念三千”诸法实相说则以肯定来表达观点。
吉藏判教分两类:由法讲(菩萨藏、声闻三藏)、由人讲(大乘、小乘)。大乘中分三类:1.“显教菩萨,不密化声闻”(《华严》);2.“显教菩萨,密化声闻”(《般若》);3.“显教菩萨,显教声闻”(《法华》)。为钝根人还有《涅磐》。
三论讲诸法(缘起法)实相(性空),二谛、四重、八不、中道:二谛归于言教,并非二类相等的真实。所谓“俗谛”“真谛”应合称“于谛”,而以中道释佛法,则是“教谛”。兴皇法朗将其释为“三重”:1.俗谛有,真谛无(针对毗昙师“以事为俗,以理为真”的有论);2.有无皆俗谛,非有非无才是真谛(针对成实师一切法空的观点);3.以有无为“二”,非有非无为“不二”,非二非不二才为真。
吉藏联系三性提出第四重:“依他”“分别(遍计)”为二,俗谛,“圆成”为不二,真谛。地论师则认为三性是俗,三无性是真。吉藏则认为三性三无性都是俗,“言忘虑绝”才为真。
八不:1.反“生灭”;2.反“断(胜论积聚说认为因积聚成果,因中无果)常(数论认为因转变为果,因中有果)”;3.反“一(数论认为因果为一,小乘大众系说缘起说为无为法)异(胜论积聚说,小乘有部)”;4.反“来(因由外来,“自在天执”,人由自在天变来)出(因是自有,“宿作因执”,有因才有果)”。
最后是结合八不讲中道,如:非生灭,亦非不生灭,“二谛合明”为中道。而得二智慧:“实智”(“般若”,重真谛)、“权智”(“沤和/方便”,重俗谛)。
三论思想后被吸收,逐渐衰落。法藏(贤首)曾举三论对抗慈恩宗,但非新三论宗。
慈恩宗以玄奘弟子窥基建立,基本继承印度瑜伽行学派,以三性解释诸法实相。
“依他起性”指“缘”,为人意识中的习气,或者说经验,因此必然导致唯识论。《成唯识论》。勾画阿赖耶识/藏识(细微的保存一切经验的基本意识)、末那识/染汙意(不自觉中的自我意识)、六识(反映藏识中经验重新显现的表面活动的意识),交替作用,经验为“种子”,现象为“现行”。藏识为“染净依”,实现由染(实我执,实法执)到净(如性、真如)的转变。事物的本相也叫“法界(清净之因)”。
慈恩宗认为染净依归心(“法”),迷悟依归理(“法性”)。转依中,理为所缘,心为能缘。心理分别与天台宗、贤首宗、禅宗都不同。
以转依依心出发,有五种性之分:三乘既定,一种不定,另有一种非定非不定。也因此受到反对、攻击,未能畅行。
摄论师门下智俨精《华严》,“别教一乘”与“无尽缘起”又来自地论师慧光,又随杜顺禅师学禅法,教观并重。弟子法藏/贤首会通地摄二家,以《华严》“海印三昧”“无尽圆融”融合所有新兴宗派。
贤首判教依法分五教:小、始、终、(相当天台藏、通、别)圆、顿(同取自天台)。又依理分十宗:我法俱有(犊子部),法有我无(有部),法无去来(大众系现在有派),现通假实(大众系说假部,成实论),俗妄真实(大众系说出世部),诸法俱名(大众系一说部),诸法皆空(始),真俗不空(终),相想俱绝(顿),圆明俱德(圆),与窥基相似:六宗,胜义皆空(般若),应理圆实(瑜伽)。
加入顿教是为了随顺禅宗抬头,造成义理矛盾。
“别教一乘”:认为《华严》是与《法华》(将声闻、缘觉、菩萨三乘“会三归一”)不同的一乘论,也是与别教小乘、同教三乘(始终顿)不同的别教一乘。
“无尽缘起”:法藏说十玄无碍,六相圆融。以三性说:依他起性同时具备遍计执性(相)与圆成实性(性)的染净两面。贤首说三性同一,染净统一,真妄相贯,以三性六义的繁琐分析说明缘起法之间的同体异体,相即(同一)相入(包含)的关系。
“六相”用以解释《华严》十句式:一总九别,一同九异,一成(略相、合相)九坏(广相、开相)。十玄(性相、广狭、一多、相入、相即、隐显、微细、帝网、十世、主伴)则表现现象间的相互关系,微尘中有无量刹。
“法界观”讲四重法界:事、理、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法界归心,十重唯识)。
《起信论》与贤首:将中国经纶分四宗:随相法执、真空无相、唯识法相、如来藏缘起(《起信论》)。如来藏即理,化为阿赖耶识为事,“理澈于事”;依他缘起为事,毕竟空无为理,“事澈于理”。“理事圆融”,为终教,圆教的基础。
贤首“性起说”认为佛境净心,顺性而起。而天台认为一念三千,佛心中皆具善恶净染。清凉/澄观遵其发展出贤首性恶说,有净缘起(悟之成佛)和染缘起(迷作众生),试图包括天台。
天台湛然与清凉敌对。贤首认为水与波形象变化而湿性不变;天台则认为波即是水,水即是波。贤首认为有情有性起,无情无性起;天台一念三千则包括有情无情。
宗密分禅为三宗,教为三教:息妄修行宗,泯绝无寄宗,直显心性宗;密意依性说相教,密意破相显性教,显示真心即性教。宗密之后华严宗衰落。
九、南北宗禅学的流行
楞伽师初修头陀行,到道信定居黄梅双林寺。楞伽师曲解作为枢要、中心的“心”字为人心,融入念佛法门。东山法门以“一行(法界一相)三昧”为根本,与念佛结合,重视“明净之心”,到神秀一系一贯禅风朴素。道信偏般若,到慧能逐渐从《楞伽》向《般若》《金刚经》的自然无分别心过渡。
牛头禅则出自三论宗,本与道信楞伽传承无关。
神秀关键在“体用互即”,寂然不动为体,感而遂涌为用,遗嘱“屈曲直”。宗密指其为“拂尘看净,方便(以《起信论》五方便代替《楞伽》,但楞伽的渐修精神未变)通经”。
慧能走群众路线,不与统治者合作。一般认为《坛经》是神会一系的东西。
王维《碑铭》中提到慧能的基本思想是“教人以忍”,“定慧等学”。“本觉超越三世”,赞成顿悟,推崇“即色是空”,自身是佛。
神会批评北宗“传承是傍,法门是渐”,在菏泽立下门户。提倡“无念为宗,直了见性;见即顿悟,不废渐修”。将“一行三昧”与无念结合,定下《金刚经》地位。神会传无名传贤首宗清凉澄观,另一门下法如传南印传道圆影响贤首宗宗密。宗密弘扬禅法,称菏泽禅在于“寂知指体(空寂的知为心体,以心传心,《起信》的根本是以“本觉”为心体),无念为宗”。宗密后衰落,北宗则与皇室共存亡。
神会北上后,南方则分南岳、青原两派。
南岳怀让传马祖道一,创洪州派,江西禅。传百丈怀海时,离开律寺而创禅居,无佛殿唯有法堂,建立“百丈清规”。洪州禅特点“触类是道”,实践上“任心”,讲究“息业养神”。起心动念皆为佛性,顺随自然,一切皆真。将《楞伽》拉回和《金刚经》相等的地位。无著作,只有语录。
青原行思传石头希迁,受般若空观影响,有五言小品偈颂体《参同契》,认为“法无顿渐,人有利钝”。在华严影响下认为理事应会通,相理不应执一边。主要研究“理事”关系,分“物理”“性理”,受坛经影响,影响宋明理学家。石头门风严厉,“石头路滑”。
“行脚参访”风气,“机锋”“机用”“机境”“语录”“公案”等出现。
会昌毁佛之后,寺院僧众和义学受到打击,立足山林和民间的禅宗发展。五代南方禅分出五派:南岳系百丈怀海,传沩山灵佑传仰山慧寂,为沩仰宗;另传黄檗希运传临济义玄,为临济宗。青原系石头希迁,传天皇道悟传德山宝鉴传雪峰义存门下云门文偃,成云门宗;另传药山惟俨传云岩昙晟传洞山良价传曹山本寂,为曹洞宗;又雪峰门下玄沙师备传地藏桂琛传清凉文益(谥号“法眼”),为法眼宗。初仅临济流传于北方,后云门北上争锋。
文益评四家宗眼:“曹洞敲唱为用(讲偏(事)正(理)回互,互相配合构成的形式),临济互换为机(讲宾(事)主(理)位置互换),韶阳(云门)函盖为流(流为理,断面为事),沩仰方圆默契(方为事,圆为理)。”文益则认为“理事圆融”是“一切现成”,不必离开人世去找。中峰明本评“沩仰谨严,曹洞细密,临济痛快(大喝),云门高古(喜用一字禅),法眼简明”。
曹洞讲偏正明暗,在回互中打圈子;临济讲主宾体用,混同于自然之说。临济/南岳系为“触目是道”,以理见事,触目是理;曹洞/青原系为“即事而真”,于事会理(后洞山见水中影,明白理仍需通过自相相传,“即事即真”)。洞山作《宝镜三昧歌》,敲唱契合。理学所受华严影响主要来自华严禅。
清凉文益传天台德绍传永明延寿,著《宗镜录》,举“一心为宗”,结合“顿悟”“圆修(华严)”,统一禅教。又与净土结合,更贴近群众。
沩仰衰微;法眼至延寿衰微;临济回传南方,成黄龙(慧南)宗(又衰微)和杨歧(方会)宗;云门三传雪窦重显,传至北方;曹洞始终不及临济。
宋代禅宗进入上层,失去朴素作风,思想偏向主观唯心论,归为“一切现成”。文字禅、颂古、评唱(舞文弄墨)与看话禅(大慧宗杲)、参话头出现,后与之反动的默照禅(宏智正觉)出现。两家之后走向沉寂。
禅宗重新与玄学联系(周易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