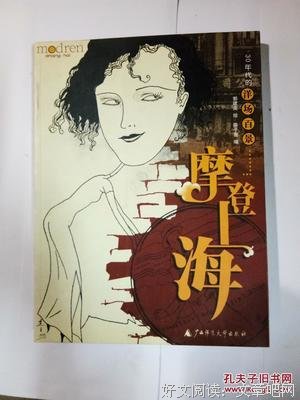
《摩登上海:三十年代洋场百景》是一本由郭建英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页数:19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摩登上海:三十年代洋场百景》精选点评:
●蛮有意思,大部分关于上海女青年的情与爱
●绘画方式记述当年的十里洋场。20071122购于当当网14.9
●18年12月17日购入
●画的那个线条很流畅哦~
●那时候的上海多开放。
●三四年前看的旧上海漫画集,很风趣,很香艳。
●好插画,我乐死了。
●密司陈,密司脱王
●十里洋场的男男女女
●没想到!!
《摩登上海:三十年代洋场百景》读后感(一):原来有人比我们早看透
说的是30年代的洋场百景~
不过那些可笑之人与可笑之事仍旧出现在今时今日~
莫非是社会进步了~而人还是原地踏步~
书中一文犹是精辟~
每个词都击中主题~
末尾的5个大字更是深得精髓~
题为:现代女子脑部细胞的一切
鸡尾酒-电影-“爵士”音乐-GARBO
DEITEIEH-旗袍料子-冰淇淋-SAXPHONE-胭脂-大光明-接吻-拥抱-“华尔兹”舞-密司脱-介绍-蜜会-好莱坞-开房间-揩油政策-汽车-REVUE-不着袜主义-跑狗-陶醉-刺激-NONSENSE主义-ABC-跳舞场-“异性热力”-速力-无感伤主义-钱,钱,钱,钱,钱!
《摩登上海:三十年代洋场百景》读后感(二):这可能不是真实的上海
《摩登上海——30年代的洋场百景》这个书名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它是从整体角度讲上海30年代文化。实则不然,这是一本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旧”书,内容也是从个人角度以小段子形式呈现的漫画集。早在1934年6月,这本书即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初版,名为《建英漫画集》。之后,又收录郭建英散见于上海报刊的部分漫画,于2001年4月再版。现在我们看到的,即为2001年的再版书籍。
不光书名为“摩登上海”,编者更是将郭建英的漫画拔高到“摩登上海的线条版”的高度。
那么,郭建英这本以上海为背景的漫画集是否有能力概括“摩登上海”?
郭建英是20世纪30年代为上海文学作品插图最多的漫画家之一,不仅为自己主编的《妇人画报》供稿,还为“新感觉派”等作家供应插图。但仅从数量看,无法断定他的作品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风尚。
从创作的内容来看,郭建英主要把视角投向了摩登女郎。他画笔下的摩登女郎烫着卷发,长着细长的眉毛,高挑着风情万种的眼睛,穿着时髦而大胆的衣服。她们物化男性,驾驭男性,甚至玩弄男性,可以不甚在意地同时和密司脱王、密司脱林调情。
我们可以把作者描绘的摩登女性看成是欲望都市的符号,这些女性被作者任意大胆地塑造,乃至色情化的程度。而这样符号化的描绘,其实是让我有些怀疑的。我不清楚这是作者的臆想,还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在这千篇一律的,美丽但浅薄的女性面孔下,在甚至有些后现代化生活方式下,我认为作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现实。
所以我倾向于这本书是作者以女性为载体的、对摩登上海放大化呈现,潜藏的是作者对现代化都市生活的恐惧和向往。而经过作者“哈哈镜”放大和扭曲的上海,尽管映射了一部分上海的真实面貌,但不足以作为真实上海的客观写照。
《摩登上海:三十年代洋场百景》读后感(三):穿越老上海
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是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一处所在,多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产生的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一直是人们有兴趣探究的话题。这些年,在一股“怀旧风”的吹拂下,旧上海的题材更是频频露脸:唱歌的、跳舞的、画画的、拍电影的、搞旅游的、设计服装的、甚至开餐馆的,都学会了拿旧上海给自己长脸。向来热闹的出版界就更不用说了,跟旧上海题材沾边的书,用“车载斗量”来形容,绝不为过。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书中,有一本名为《摩登上海——30年代的洋场百景》的书,显得卓而不群。这是一本漫画书,它的作者郭建英,是30年代中国文坛“新感觉派”的代表,在如今这个读图时代,籍一本漫画书,通过一位当时当地目击者的眼去体味旧上海的风景,该是一件惬意的事。
和今天的漫画家相比,三十年代的漫画家笔下的写实味道总是更浓一些,但郭建英的漫画好就好在,他一直在努力摆脱临摹生活的状态,总是试图从一个奇特的角度观察,用一种奇特的方式表达,在他同时代的画家中,这样的做法并不多见。所以,虽然郭建英的画从艺术水准上讲不能说是最好的,虽然我们看惯了三十年代作家笔下的上海滩,但这些都无法掩盖郭建英漫画的独特价值。
打开这本时隔70年重见天日的漫画集,一股急匆匆的味道扑面而来,大到新与旧的冲突、开放与保守的交火、女性主义的抬头,具体到离婚率的升高、西方电影的时髦、街头广告的影响力……这些需要动用无数笔墨才可能交待明白的事,都被简单而柔和的线条轻松捕获。我相信,这才是真正的上海滩的味道。郭建英也许不是一个大画家,但是本书证明,他有资格成为一名好的观察家。他曾在当时上海滩极有影响的杂志《妇女画报》担任两年主编,被称为“独一无二的运用画笔的‘新感觉派’”,这些也都可说明,他的感觉真的很好。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郭建英的许多画配上了精短的文字,这些文字也并非直勾勾地去写上海,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记录日常对话、市井百态中,加上作者的加工处理,有时看上去简直像是《读者》中页的小幽默。看这样一本书,你可以一气读完,因为它可以产生一种支持你读完的快感;当然,你也可以慢悠悠地去品,因为它有很多藏在线条之后的东西,值得你细细琢磨。
《摩登上海:三十年代洋场百景》读后感(四):双城记 ——20世纪初的上海女性与新城市生活
双城记
——20世纪初的上海女性与新城市生活
20世纪初,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发展迅速。在中西方思潮与传统文化激烈交汇,世事巨变的背景下产生了“新感觉派”文学,他们强调主观直感,用感性认识世界。郭建英作为“新感觉派”代表人物之一,用画笔记录下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十里洋场。他的作品展示了当时都市人特有的审美眼光和生活方式,从中体现出现代与传统、中方与西方的交融与矛盾。
当时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对上海的上流社会造成了极大影响,思潮观念的变化对社会风气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自由主义思潮解放了被传统礼教束缚的中国女性,让她们脱离了传统家庭、社会与儒家伦理的桎梏,成为了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城市之中的一个个独立个体。但同时这种“西学”的趋势在三十年代的上海逐步演变成了盲目开放,因此也导致了一种畸形的繁荣,甚至造成了上流社会的堕落和社会风气的败坏。由此,一个上海却被分为了“双城”,这里充满繁华,也衰败腐朽;这里先进开放,也陈旧保守……
郭建英的作品就产生于这一繁荣与矛盾并存的时期,作品以女性为载体,对都市生活做了大量独特的反映,从伦理道德和社会风尚的角度,表现了现代都市繁华背后空虚而病态的矛盾生活。作品不仅能让观者了解到三十年代十里洋场的人情风物、社会百态,也能让人反思当今大城市的灯红酒绿,繁荣与虚无。
一、 在开放中保守
郭建英对女性的表现兼具了中西方传统,他将现代文化所倡导的外在审美与内在修养相结合,通过画作展现了出来。
从整体来看,我们在1934年2月和1934年10月的《妇人画报》封面设计上可以看出,当时上海女性的着装打扮,在保留了中国女性柳叶眉,细长眼的同时,冲破了中国传统观念上女性婉约内敛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性感的红唇和时尚的卷发。这不仅体现了城市生活中女性对美的追求在发生变化,也体现了当时城市生活中,她们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度显著提升。
但在材料中出现的35幅作品中,有22幅作品体现着男女互动的主题,虽然其中基调各有不同,或欢乐、或爱慕、或吵闹、或冷漠,但总体可以看出,作品中的女性依然是以柔美、顺服的姿态或神情示人。有8幅作品更是直接描绘了女性在男性臂弯中孱弱动人的姿态。郭建英对女性美的认知本身却充满矛盾。虽然她不支持摩登女郎过分追求时尚或外表的美,他对女性身体之美充满赞赏和向往,作品中几乎都以刻画女性的美好形象为主。通过对比他的多幅作品可以发现,他笔下的女性角色形象单一:小巧高挺的鼻梁,眉毛细长,眼梢高挑,妆容精致,腰身纤细,眼神斜视,呈现出神秘魅惑之感,缺乏深刻的内涵与性别体验。所有特征并没有摆脱传统美术作品中女性形象给人带来的直观感受——柔美、明艳,对男性极具吸引。由此也能够看出画作的一个基调,与同时期甚至更早的敢于“画丑”,不迎合男性的“女权主义”美术作品相比,可以看出该作品并不具有鲜明的宣扬女权主义,大力倡导女性解放的意图。当然这并不能作为“开放中保守”的最大体现,“保守”体现在其他的细节之中。
郭建英对女性内在修养的体现见于画作与配文的表现细节,也正是这些细节反映出女性身份解放的不彻底,保守性依旧存在。郭建英在《摩登生活学讲座》中提出对女性貌、德、学、体全方位的要求。这些对女性行为规范上的要求体现了现代城市生活中对女性的教养和生活经验上有了更先进和更明确的要求。但也正是这过多过细的要求把女性方从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桎梏中解放出来,却又套上“社交礼仪”等等现代伦理的“枷锁”。从第一讲“恋爱”部分的“女子之部”即可以看出,对女性言语、神态(“时常要装出感伤的样子……”)甚至化妆(“在他之前不可不时常拍粉……”)的要求,依然令人想起传统社会中深宅大院中的大家闺秀。此处女性的矛盾形象也恰恰反映出三十年代上海——这座走在中国现代化前列的大都市的矛盾,西方的观念突破了传统礼教,解放了社会风气,却依然没有解开所有人内心保守的锁链。
二、 在保守中享乐
“享乐”,是材料的画作和文字中最鲜明体现的主题之一。郭建英在《上海街头风景线》通过(一)活跃着的青春,(二)丑恶的极地分别展示了摩登上海的生动与丑恶。“上海女人的青春是活跃着,是创造着”,“火酒般的热情,阿布生酒般的性欲”,同时又是“没有希望的遗物”;“男子的雪花膏,粉;江北人的体臭;市窗低级的色调,卖报者之呐喊;民众的疲乏。”这就是一道新感觉主意的“都市风景线”,表面歌舞升平,其实沉沦于是欲望与私欲的不可自拔,内心的空虚和修养的匮乏让这种生动变得丑恶。又如《都会之诱惑》中性感的女郎和魔鬼缠绵在一起,这里的魔鬼就如黑夜下笼罩在都市上空的欲望诱惑着都市女性去寻求刺激与享乐。而画中的女郎,如同郭建英其它作评中的女性角色,美丽而诱惑,同时又多了一些身体诱惑。健康、活泼、性感,卷发、短裤,鳗鱼式的身体,勾魂的眼神,居高临下的自信,俨然是两性游戏中的主动勾引者和控制者。而这些看似光芒四射的城市尤物却更能体现出城市生活的迷乱和过度追求享乐的娱乐姿态。
不同于密尔“功利主义”中的欲求满足理论,郭建英笔下的女性享乐图景似乎并无事先的“欲”可求。男性臂弯中女性的身姿、体态、眼神,似乎都向外人传达着一种讯息——释放。在“性”的方面,“男女授受不亲”的口号在三十年代的大上海不再适用,甚至成为笑柄。母亲不再反对女儿去和陌生男子跳舞,反倒是被发现,“那——妈也在那儿跳舞啊。”或许这种剧烈的变化来源于中西新旧文化对于“两性”方面观点的强烈反差。
从母亲致“阿囡”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观念的变革并不只限于年轻一代。母亲竟然在信中责怪女儿,“你把旗袍改长到脚膝之下,把一切透明的衣服弃而不穿……”,“竟翻起什么《文心雕龙》、《老子集注》、《西洋哲学史》、《天演论》一类可怕的东西来!”除此之外母亲还干涉女儿的恋爱问题,责怪她不找“一般运动员的男朋友,相反和一种老是穿着青布长衫,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的书呆子交起朋友来!”作为社会风气剧变的一个缩影,这封信足以反映当时上海的一部分上层人士对于传统,对于经典,甚至对于中国文化的负面看法。可以理解的是,作为新旧时代与中西文化最初交替的见证者的一代人,他们对于西方“自由主义”观念的接受过程中很可能包含着一些对传统文化的仇视。两千年的儒家学说虽经过历朝历代的改进演变,但仍被女性当做摆脱不掉的噩梦。儒家伦理观念中妇女的生活范围非常狭窄,几乎仅限于家庭。且她们不具备自己的独立人格,“三纲五常”树立了传统王朝立法之本,“三从四德”奠定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价值取向。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在打破这种尘封的禁忌后女性的心情。她们的生活范畴不再局限于大院闺房中,而是延伸到了舞会、公园等等公共场所;她们的交际对象也不再受到限制,甚至得到来自上一辈的女性大力支持。两千年压抑后的释放,让两性的交流迅速演变成了享乐。
在郭建英的笔下,城市生活被简化为一个两性的故事,通过情欲的交织,体现虚幻、漂浮、失重,乃至失控的感受,浮现出城市人生纸醉金迷的图像。
三、 在享乐中迷失
20世纪的上海,大众文化不再受到封建礼教的约束,文学内容也更为大胆和感性。例如《机械之魅力》中喜欢机械女体的男子,虽然体现了当时社会对不同心理和情感的尊重,但陶醉于物质感的性欲,恰恰体现了内心的空虚。郭建英在这篇作品中,直接走进人的内心世界,对人的感官及潜在心理做了表现,以此揭示人与外部世界漂浮不定的错位关系。人,尤其是女性,此刻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于城市之中,却似乎与城市断绝联系。
三十年代的上海女人成为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人”,所有人都认为她们跳出了传统礼教的束缚,但郭建英却似乎在通过他的作品告诉世人:她们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在依旧由男性主导的繁华都市里,那些被认为解放了的女性又何尝不像《机械之魅力》中的机械女体一样,受到男性把玩。《摩登生活学讲座》中约束女性的条条框框,《婚礼之部》一部分画作中受到一众西装革履的“现代”男士评头论足的女性,无不反映着女性千百年来想要摆脱却实难摆脱的一个词——取悦。
她们刚刚独立的身份,似乎在男性主导的城市中迷失了。
女性虽然在城市伦理和规章制度上实现了独立,成为了“个人”,但这里的“个人”却尤似古典个人主义所指的个体——彼此单一、自我封闭。她们被禁闭于自己的主观性之中。但是她们却没有古典自由主义所言的“个人”那样具备追求属于自己的“善”的权利。她们似乎并没有达到与社群和谐共存的地步,也忘记了家国仇恨。在《1933年的感触》一文中,作者提到了荒木陆相,日本军阀的代表者。由此我们意识到,1933年的上海还饱受侵略者的压迫,国难当头,大上海却依旧一派繁荣。这样畸形的发展使20世纪初期的上海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具有混合气质的城市。从旧时代的繁荣直接接触现代化的西方文化;腐化的,凝滞的甚是濒临灭绝的身躯,却被注入最梦幻虚浮的灵魂。人们似乎是想要用着看似光鲜的外表去忘却战争带来苦闷,享受西方文明的刺激。现代文明熏染下的屈辱与新奇,寄人篱下的安身立命与渴求自由的深恶痛绝……这样复杂而阴郁的气息飘荡在上海的夜空。
新时代的女性和新时代的城市一样,只在追求属于自己的享乐中,再次迷失。只是无人再诵“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却多了个会作画的诗人。
四、 在迷失中变革
女性常常作为载体来揭露新旧观念的矛盾冲突,郭建英也有很大部分作品将矛头对准了突破旧传统而带来新问题的“新女性”。例如,郭建英在《上海》和《妈妈都知道的》中,用讽刺的手法,分别展现了一位认为女儿认真学习不沉迷享乐是病态的母亲,和一位同女儿一起享乐的母亲。这两篇文章也许是郭建英从追求享乐、物欲难填的问题出发,对过分要求个人独立而缺乏传统家庭担当的女性进行的无声批判。这些“新女性”某种程度上确实代表沉迷享乐,她们中的一些人忽视社会及家庭责任,忘记了传统礼教中也有值得尊崇的部分,这也体现了“摩登”或“新”并不一定就是好的。这样的讽刺与批判,展现出20世纪的上海社会日常中,精英理想与民众生活现实之间的冲突以及新旧观念博弈,彰显出社会变革的复杂与艰巨。从新感觉派画家的笔下,我们可以感觉到在当时上海的城市生活中,充斥着各种思想与文化的碰撞,人民大多生活在迷茫和放纵之中。
但虽然迷失着,也在变革着。
我们不能因为强调变革中的保守部分,却忽视了“变革”本身。新时代上海女性获得了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女性从未有过的地位待遇,毋庸置疑。《摩登生活学讲座》的第五讲《夫妇》中,第一条即是“丈夫切勿忽视妻子……”,虽然后面又调皮似地加上了“事已至此,业已晚矣”。第八讲《社交舞》中第二条便提到“男宾应向女主人至少邀舞一次,即使她是半百的老妇人。”第九讲《街头礼仪》还指出,“如果你的脚被女人踏痛了,你也应该面呈着笑容对她说‘对不起’……”虽然后面再次调皮似地加上了“呜呼,现代男性的悲哀?”
我们可以看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女性地位已经与传统社会的女性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一个城市由闭塞落后走向文明开化的极大体现。在当时的中国,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女性还依然接受着“夫为妻纲”,甚至缠足的时候,上海的女性地位已经足以反映这一个地区的发展于开放程度。因此虽然大中华地区各个城市刚刚开始进行东方与西方、时代与传统的交汇摸索,但必须承认,上海此时已经走在了前列,在迷茫中实现了飞跃式的变革。
一个充满矛盾的城市,在时代变革的浪潮中被迫一分为二,也必将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走向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