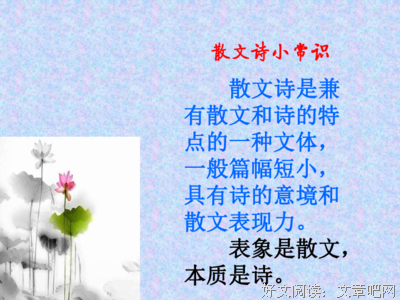
《我本不该成为母亲》是一本由[加拿大]阿什莉·奥德兰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3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本不该成为母亲》读后感(一):作者专访:阿什莉·奥德兰写出了你2021年最爱的书
文/格雷格·哈德森
现在,阿什莉·奥德兰对这一行的了解一定就像指挥家对她的音乐一样了如指掌:作家们通常都拿着笔记本或小说,点上一杯茶,在咖啡馆等待,咖啡馆一般都有足够的特色,但又不会太喧宾夺主,一切都刚刚好。作者分享着故事背后的故事,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或许还会知道应该如何以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讲述和推销它。在她以前的角色中,奥德兰可能为记者和新晋作家们安排了数百次这样的采访。今天,情况有点不同了。她不再是幕后人物了:她成了主角。我看到她坐在德雷克酒店咖啡馆的露台上,面前放着一壶正在渐渐变凉的茶。
在众多即将出版她新作的出版社中,企鹅兰登出版社(目前全球企鹅兰登旗下各地区语种的出版分支也都因此书的诞生而引起了一番轰动)是她曾经供职的地方,她原本在那里担任公关总监。
大约四年前,休产假期间,她下定了决心,再也没回到出版社,因为:“我不要变回职场中的那个我,因为那不是真正的我。”她说,“我心底真正想做的是成为一名作家,我得去写书了。”
因此,她做了所有想要成为作家和准作家的人都要做的事情:一周有两天左右——当帮手来照看儿子的时候——冲进咖啡馆,在笔记本电脑前码字,尽可能长时间地创作,然后在晚上编辑写完的东西。现在,她的小说就要在2021年出版了。
奥德兰在创作的大多时候,都闭口不谈,但现在她已经习惯了随时聊这个故事。她解释说:“它谈及了我们作为母亲的身份和一个社会对母亲的期望,以及我们对此事的看法与真正现实的差距和冲突所在。”这也关乎人们对婚姻的期望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怨恨。“这本书真正涉及的第三件事是精神疾病。我认为它对精神疾病有一个非常诚实和感同身受的看法。”
坦白来说:我不知道这本书好不好。现在都没到收试读本的阶段。但事实是,她曾经的雇主,未来的甲方已经早早发布了关于作品的新闻稿——而且在国际版权市场的反响非常好——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质量的认可。
以她之前在企鹅的工作经验,奥德兰深知,如《消失的女孩》或《火车上的女孩》这类惊悚作品,很容易打造畅销爆款。她说:“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试着用那种惊悚小说的风格写作,这实际上不是我喜欢读的东西。所以,在与早期读者进行了一些艰难的沟通后,她改变了方向。
如果写下她想要的关于母亲的东西并不容易,那么成为一名母亲更是难上加难。当她的儿子大约两周大的时候,病得很厉害。机缘巧合下,奥德兰大约在同一时间成为了一名作家和一名母亲。她说:“当我成为一名母亲时,我真的感受到了巨大的创造力。我就是忍不住想写作,想像这本书最终成型的样子。”这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拥有创造的神圣力量,同时对他们创造的事物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奥德兰一心想把这些力量用在好的方面:鼓励同理心,扩大理解,并表明为母则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
她说:“我一直被讲述女性生活故事的女作家所吸引。‘女性小说’不是我倾向于使用的一个术语,但我能理解这个行业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可以拥有一个独立的创作天地,一个正在冉冉升起的门类,在出版业是件很有影响力的事情。正是在这个独立的天地里,女性出版商正在为女性出版关于女性生活的书籍。”
FASHION Magazine Nov 2019
《我本不该成为母亲》读后感(二):身为母亲,一生中要心碎一百万次
文/***
成为母亲,是神赋予每位女性的权利。是否去使用这个权利,如何成功地使用,却没有预演和练习。一切都像命里注定,每个女孩从小就被告知或是暗示:你长大后一定是个好母亲。
可在我们的人生里,事与愿违的事情,却时常发生。就像《我本不该成为母亲》这本小说里写的,成为母亲,并不意味着喜剧的发生。相反,小说的女主角布莱丝说,“一位母亲,一生中要心碎一百万次”。
布莱丝的说法夸张吗?不,读读小说,你就知道了。
现代小说中素来不缺乏专职育儿的“职业母亲”形象,从美国詹姆斯·M·凯恩的《幻世浮生》到澳大利亚莉安·莫里亚蒂的《大小谎言》;再从日本角田光代的《坡道上的家》到韩国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我们透过小说家的视角,看到了在成为母亲的过程中,女性是如何一步步地脱胎换骨,成为一个连自己都几乎不认识的人。这些小说,真切地呼唤着我们,对母亲这个群体的社会照护与人文关怀。
加拿大女作家阿什莉·奥德兰的《我本不该成为母亲》,将这种需求写到了极致。小说不仅讲述了布莱丝在成为母亲后,由喜悦到心碎的生活经历,还采用闪回的方式,插入了布莱丝的外婆埃塔与母亲塞西莉亚的人生片断,让读者得以发现,“成为糟糕的母亲”,其实是这个家族女性的大魔咒,至今无人破解。
倘若想了解布莱丝在获得母亲这种身份之后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布莱丝这个人。
布莱丝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里,母亲塞西莉亚在她少年时,离家出走了。是因为出轨才离家,还是因为憎恨布莱丝的存在才出轨,即便布莱丝自己已经成为母亲,她依然不知道母亲出走的真实原因,她只知道母亲是个恨小孩的人。她动手殴打女儿,甚至想制女儿于死地。或许,布莱丝曾经以为,自己的出生是个错误。
不应该有人强制女性成为母亲,但母亲也不该抱怨小孩的出生。母亲与孩子,放置于人群之中,本该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拥有各自的身体、思想与行动力。但正是因为孩子是由寄居在母体里的一个坯胎发育而来,在初生时要依靠母亲哺育,因此母子便成了拥有特殊纽带的个体,从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曾经依靠得那么紧密。也许就是越抱紧越想挣脱的感觉,令母子关系由亲密走向撕裂。
在家族女性的婚姻里,布莱丝是幸运儿。她嫁给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她的大学同学福克斯。虽然,娘家没有人来参加婚礼,公婆仍然表示理解,并祝福他们的婚姻。在丈夫不断地鼓励与暗示她会“成为一位好母亲”之后,布莱丝开始渴望成为一位母亲,不仅克服了恐惧感,还一心一意地以为,“我母亲做不到的,我都能做到,我将成为一位完美的母亲”。
布莱丝的恐惧,要从她的母亲塞西莉亚是个遗腹子,外公路易斯在干农活时不幸意外身亡说起。闻此讯,悲痛欲绝外婆埃塔开始变得疯疯颠颠。在生养塞西莉亚的过程中,埃塔几次都想杀死女儿,最终她杀死了自己。坦白说,赛西莉亚是在恐惧中长大的。而后,塞西莉亚又将这种恐惧传染给了女儿布莱丝。
虽然痛苦不堪,但布莱丝生育女儿维奥莱特的过程还算顺利。可哺育一个婴儿,绝不容易。布莱丝边写作边育儿的想法,不得不在维奥莱特的哭闹中放弃。丈夫福克斯依然是那个西服革履的上班族,下班回来享受片刻的天伦之乐。而布莱丝却必须放弃自己的职业理想,每日蓬头垢面地照顾啼哭的婴儿和挫败感日渐增强的自己。产后焦虑症,无需预约,如期而至。此时的布莱丝,是几千万个育儿母亲的缩影,像个溺水之人,淹没在无休止的“养育”人生里。她甚至问自己,“我觉得我是世界上唯一熬不过来的母亲”。做为读者,我知道,同布莱丝感同身受的,何止一人。看到身为母亲的布莱丝,我们无数人就好像看到了无助的自己。谁说身为人母一定是种幸福?谁说生育是女性最大的成就?谁说育儿是个愉悦的过程?现在看来,强加在“母亲”这份职责上的光环,是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缺失,是缺乏同理心的表现。
这本小说的精湛之处,并非让我们去理解与同情布莱丝。而是,设计了布莱丝与维奥莱特的争斗。如果说布莱丝是千百万母亲中的一员,那么她的女儿维奥莱特却是小孩中最与众不同的一个。维奥莱特从小就展示了“好勇斗狠”的一面,既不与母亲配合,也不与同龄人和睦。这个小女孩的形象,让我想起了美国电影《孤儿怨》里的伊斯特。不过,电影中的伊斯特本是个大人,因为患有侏儒症,而被雇主误认为小孩。
书中的维奥莱特却是布莱丝眼看着长大的女孩,看着她向其他小孩伸出“罪恶”之手,其中包括自己的亲生弟弟萨姆。儿子的死,成了压垮布莱丝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女儿教育失败也深深地折磨着布莱丝,“我感觉犯罪的那个人是我。”作者关于布莱丝这种心理的刻画,让我们想起了许多纵容小孩做恶的家长,其实他们知道孩子是不对的,但却不想承认自己的错误。许多时候,成年人比孩子更脆弱,为了维护他们的身份地位与所谓成年人的尊严,袒护孩子成了他们最后的遮羞布。既然父母与孩子都不完美,为什么不彼此承认呢?这正是人类社会需要逐渐进步的伦理与道德观。
本书采用倒叙写法,开头的一幕是,布莱丝从车里,望向再婚的福克斯一家其乐融融地欢度圣诞夜。但夜幕像只黑手,悄悄地伸向了这一家人。福克斯家到底发生了什么?读完小说就知道了。
总之,在这部小说里,我们读到的是,一个心碎了一百万次的母亲和一个脱不掉魔咒的女系家族。
谢绝转载
《我本不该成为母亲》读后感(三):纽约时报书评:我的手轻晃摇篮,却怀疑着里面的她
纽约时报书评:我的手轻晃摇篮,却怀疑着里面的她
By Claire Martin我孩子的行为正常吗?这是个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育儿问题,尤其是在孩子的幼年时期,有些父母会为孩子的每一个怪癖感到焦虑,不管这些所谓的怪癖其实多么正常。喜欢打人的学龄前儿童是否需要专业的干预,或者仅仅是给他们安排跆拳道课?不午睡且爱发脾气的孩子长大会变成暴躁狂吗?阿什莉·奥德兰(Ashley Audrain)在她的处女作《我本不该成为母亲》(the Push)中塑造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紧张,这种极度的绝望与焦虑正是小说的中心。
我本不该成为母亲暂无评分[加拿大]阿什莉·奥德兰 / 2021 / 中信出版社布莱斯·康纳(Blythe Connor)不愿成为母亲——这可以理解。她的母亲在她儿时一直虐待着她,并在她11岁时离她而去。她的祖母同样曾对她的母亲百般虐待,并以一种更可怕的方式离开——她在前院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布莱斯从一开始就对成为母亲这件事深感恐惧。“我觉得孩子讨厌我。” 她说,那时她刚生下第一个孩子,女儿名叫维奥莱特(Violet)。他们的关系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布莱斯产后的经历对有孩子的读者来说是很熟悉的,奥德兰在书中将这段经历描写得完美无瑕。首先,母乳喂养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成功:一名护士“站在我们身边,一直盯着维奥莱特和我棕色的大乳头,因为她试图再一次吸吮”。布莱斯努力适应着母亲的角色,她和丈夫福克斯(Fox)的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母亲完全没有给布莱斯带来喜悦或惊奇的感觉。“我很失望她是我的女儿。”布莱斯提到维奥莱特的时候说。她承认自己对孩子的哭声一连几个小时不予理睬。
如果不是因为书中每一章都穿插着布莱斯痛苦的家族史,我们很容易将这些困难归结为产后抑郁症。布莱斯的母亲经常打她,而且经常失踪一两个晚上。布莱斯的祖母经常在放学后把她妈妈锁在门外,有一次还把她的头浸在浴缸里,差点把她淹死。
维奥莱特的性格越来越充满敌意,究竟是先天因素还是后天因素在起作用?奥德兰在书中巧妙地逐渐揭开了这个谜团。当游戏设施上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不幸摔死,而维奥莱特恰好就站在旁边时。布莱斯更加怀疑了。但是福克斯一直在保护他们的女儿,不愿听这些猜测。而且因为布莱斯本身就有点不正常,所以很难知道该站在哪一边。在故事中她是一个典型的不可靠的叙述者,在与福克斯的婚姻破裂后,她潜伏在他的新家外,并假装成一个单身妈妈,接近他的新伴侣。
这本书几乎完全是用第一人称写成的,就像布莱斯写给福克斯的一封长信。它既是对两人关系的一场事后分析,也是一个预警的信号,让他认真对待维奥莱特那些令人不安的行为。
奥德兰有捕捉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的天赋,而这些瞬间却能深刻地表达当下的关系状态。布莱斯生维奥莱特的时候,福克斯“站在两英尺外,喝着护士给我拿来的水。”几年后,当维奥莱特的哭闹打断了一场本该性感的淋浴,他们的关系已经发展到福克斯“扔给我一条毛巾,就像在更衣室里扔给队友一样”的阶段。
奥德兰描述了婚姻的解体过程,以及代际创伤的影响和养育孩子带来的痛苦与悲伤。在她的描述下,布莱斯之后一系列的脱序行为似乎有情可原——包括她戴着假发接近福克斯的新伴侣,对她撒谎。布莱斯的经历在一个层面上是相互关联的,在另一个层面上是完全令人震惊的,这是心理惊悚片的一个特征,在这里以扣人心弦的情节精确呈现。
本书的第一人称视角偶尔会让我觉得有些重复,我在读书时发现自己渴望听到福克斯的声音——或者其他人的声音,真的。但是,书中回顾布莱斯家庭历史的章节提供了素材,而当福克斯的新伴侣被布莱斯的假身份蒙骗,开始讲述他们的生活,甚至询问她育儿的建议时,故事感觉更立体了。因为终于有人觉得她是个好妈妈了。
(Source:https://www.nytimes.com/2021/01/05/books/review/the-push-ashley-audrain.html?smid=tw-nytbooks&smtyp=cur)
《我本不该成为母亲》读后感(四):也许有些人本不该成为母亲
我们都想要一位好母亲,需要一位好母亲,期望拥有、娶到或成为一位好母亲。——《我本不该成为母亲》 偶然间发现的一本书,读完的时候正好碰上某女星「代孕弃养」事件。
我还没有为人父母,但我想,这本书,每一个已经成为母亲、即将成为母亲、犹豫着是否要成为母亲的人都应该去读一读。
当然,对一个也许会成为父亲的男人同样适用。
这不是一本传统的关于「母亲」的书。
它更像一个陌生人正在向你吐露深埋心底的秘密
在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后,我逐渐开始明白,我们最终结出的果,都来自前人种下的因,我们就这样代代生长,而我就是来自母亲的花园。——《我本不该成为母亲》
原生家庭的影响,不管你是否承认,它都会在你身上或显性或隐性的伴随着你的一生甚至下一代。
这是人类基因的力量,你无法抗衡。
布莱丝很少感受到母亲的体温,感受到的都是冷暴力和疏远,自卑和羞愧。
而她的母亲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的则是来自外祖母的残忍和虐待,困惑和惊恐。
后来,在布莱丝知道自己即将要有一个孩子时,她想着一定会比自己的母亲做的更好,但实际上,她根本不知道一个 ‘更好’ 的母亲应该是什么样子。
虽然没有做好准备,但她还是来了,从怀孕到生产再到后面的养育,布莱丝的心理、身体、社会角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哺乳期的难熬
孩子的疏离和哭闹
身体的疼痛
丈夫的误解和责备
职场的焦虑
照顾家庭生活的崩溃
···
布莱丝爱她的孩子,但这份爱让她时常陷入焦虑。
书中有一段话:
我思索着逃出困局的办法。在这里,在黑暗之中,乳汁在流淌,椅子在摇晃。深更半夜,我想把她放在婴儿床,就此离开。我回想着自己的护照在哪里,思索着机场起飞时刻表上的数百个航班,考虑要不要把自己的手机留在床头柜上。我的奶水要多久才会消失,让我的胸部放弃这一证明女儿出生的证据。这些话我从未说出口,这些想法大多数母亲都不会有。
她没有抛下女儿,她爱她,她要比她的母亲做的更好,她已经做到了,首先,她没有离开她。
以布莱丝的视角回忆,她一直心力交瘁的照顾女儿。
即使女儿从出生就莫名的抗拒她···
夺走了她的身体、她的睡眠、她的生活···
甚至有些不合年纪的心计和阴暗,
甚至她可能已经处于犯罪的边缘或已经吞噬了罪恶的果实,
她依然爱她,这种爱是一种源于血液和本能的情感。
直到小儿子的意外死亡,布莱丝被彻底摧毁了。
丈夫有了外遇,婚姻走到了终点。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更多被隐藏的问题浮出水面。
全书都是以布莱丝的视角进行讲述的。
那如果以女儿的视角来捕捉布莱丝描述的细节呢?
她没做好成为一名母亲的准备,
在哺乳期,布莱丝在身体疼痛、失眠等各种不适的煎熬下,时常看着自己的女儿心想‘求你走开吧’,
曾想过离开她,在她声嘶力竭的呼喊时因为工作将她丢在一边,
从来没有温柔的安抚过她,
感觉到女儿疏远她,认为这是一种背叛,
但实际上她也在疏远着女儿,
不知如何面对女儿的错误,没有告诉她对与错的边界,
认为这是一次 ‘失败’的生育,又生下了一个男孩···
布莱丝的母亲告诉她“我不想你重走我的路,但我不知道怎么把你教育成一个和我不同的人。”
然后母亲离开了她,所以在她面对困境无法解决时,也认为离开自己的女儿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她们都没有正视和治疗过自己的心理创伤和堆积的心理问题,不具备健康的心理环境去应对,更多是消极、回避、放弃,沉溺在自己的命运脚本里。
上一代的问题很难被修正、改变,但自己和下一代的命运却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破碎的家庭是她们‘因果代代相传’的导火索,却不是造成‘因果代代相传’悲剧的直接原因。
布莱丝‘放’过了自己,‘不去想他,也不去想她,不去想她身为母亲所犯下的错误,不去想她因自己所致的伤害而背负的内疚,不去想她无法承受的孤独。’
但她也如同她的母亲,她的外祖母一般,将她的女儿推向悲剧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