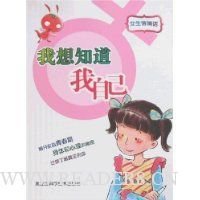
《尼伯龙人之歌》是一本由佚名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2.50元,页数:496 页,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尼伯龙人之歌》精选点评:
●个人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疯狂剧透!人物刚出场,“你一定想不到这个人后来死在异乡”;俩人一见面:“这两个人后来反目成仇惹!害死了好多英雄!”莫名其妙地看得我特别期待,特别想知道究竟是怎么样的大场面,就这么看完了。。。人物众多,场面宏大,人物个性十分饱满,虽然夸大了他们的神勇、聪明、美丽等特点,但每个人物都不完美,也因为个体的性格特征,做出的不同选择导致了最后的大战。呜呼!
●明明是《尼伯龙人的厄运》,说真的,骑士的精神太奇特了=_= 真的挺无聊的
●两年前看的罗兰之歌,相比之下,这本中没有善恶观,用全部便当收场,还是比较特别的。
●世上的欢乐,到头来总是变成悲伤。
●迷日耳曼文化时期读物 初中
●英雄史诗,德国一贯爱搞残酷
●对勃艮第人没有丝毫好感,一直看到勃艮第人最后全部惨死,尤其是哈根毫无尊严地被克里姆希尔德亲自手刃,才大快人心。 我无法融入创作的时代,只能以现代人的观感。实在不明白诗人的善恶观,尤其是已将西格夫里特置于绝对力量与美德的制高点后,安排阴险狡诈的哈根暗下杀手,却在之后又不遗余力地赞颂哈根的美德,对哈根的褒贬前后完全不一致,这种突兀的被吹捧而成的“立体人物”令人十分恶心,而相比哈根和恭特的劣迹都能被形容得大义凛然,克里姆希尔德的为夫报仇却成为不义之举,明显是红颜祸水的双标理论。 最后,悲剧根源应归在恭特这人渣身上,没实力还借西格夫里特之手诈娶布伦希尔德、被人知道真相后为脸面暗杀恩人西格夫里特、为了尼伯龙的宝物诈骗妹妹、最后用自己的无知与自大将所有勃艮第勇士葬送至匈奴。真他妈活该
●想象单田芳老先生把它做成评书
●所以……在男性作者眼里,女性的美好全体现在她清纯不谙世事上。对待不公的命运,她们只能哭泣;一旦她想做正当的复仇,就会被认为是“心怀叵测”“刁妇”。而男性,只要他们有这所谓的勇敢和厉害的武功,就是个英雄,即使他贪婪易怒伪善,他也是个英雄,他的死一定悲壮 何其恶心!
●虽然我做课堂作业的时候被迫论证它是宫廷骑士文学,然而我内心坚定认为它就是英雄史诗!
《尼伯龙人之歌》读后感(一):女人的舌头和眼睛
海伦的美貌曾经被人这样形容过“她的眼睛能够点燃爱琴海上的十万艘战舰”。
尼伯龙人之歌里的克里姆希尔德的美丽大概也可以达到海伦这个级别。因为她的舌头葬送了三个王国的英雄们。因为一场两个女人之间的争吵,结果屠龙英雄被杀死在山泉边,勃艮第、尼德兰、匈奴帝国三个国家毁于一旦。
《尼伯龙人之歌》读后感(二):被迫改变信仰的北欧英雄们
出于仰慕之情,囫囵吞枣地看过《尼伯龙人之歌》(Das Nibelungenlied)。第一次接触诗歌体裁,便以此来写观感吧。从没哪个诗人,诉说这么伟大的篇章。我们的勇士是多么堂堂,我们的英雄是何等勇敢。我们的国王是如何高贵,我们的王后是如此漂亮。成吉思汗不及此等勇猛,马可波罗也没有这般夸张。故事的框架是北欧传说,故事的内容却是骑士文学。不论是虔诚的欧中,还是异教的匈奴——他们都建有教堂,需做弥撒。再见了,尼伯龙人的哀歌,倘若你只是迂腐的中世纪文学。我热爱那悲壮的北欧神话,宁可重温伏尔松格传奇的萨迦。
《尼伯龙人之歌》读后感(三):为什么《尼伯龙人》人物很崩??
关于《尼伯龙根之歌》,已知的确凿史实仅有一条:民族大迁徙时期,勃艮第王国一度建立,于公元434年被匈奴人夷平[1]。《尼伯龙根之歌》内容编排的出发点就是它的大结局,即勃艮第人被匈奴人团灭,屠龙勇士、冰岛女王、绝世宝藏、匈奴求亲等等全部是虚构的传说。史诗的创作者基于这个成王败寇的历史结局,构想出它曾经的光鲜与震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凶悍无畏的冰岛女王布伦希尔德和趋于无敌的尼德兰王子西格弗里特,勃艮第国王恭特平庸地过分,也正常得过分,因为三国君主中唯有他是以人类君王为原型创设而来。
为这篇史诗画出这条历史的底线,便可知《西格弗里特之死》和《克里姆希尔德的复仇》并不是上下部的串联关系,而是前传和正篇的并行关系,前者存在与否并不会对后者有太大影响。一些评论表示《尼伯龙根之歌》的人物缺乏统一性格,从另一个角度看,《尼伯龙根之歌》故事本身很可能是拼凑而来,先有《克里姆希尔德的复仇》,再有讲故事爱好者续貂了前传。假设《克里姆希尔德的复仇》先一步诞生,其开头是“克里姆希尔德远嫁匈奴王,恭特应邀赴鸿门宴”,那么需要前传解答的问题有两个:克里姆希尔德为何远嫁匈奴王,恭特为何出席鸿门宴。对于第一个问题,前传引入了克里姆希尔德对勃艮第王国的仇恨,她的第一任丈夫和丈夫的“清晨礼物”为此诞生,遭到勃艮第国的谋杀和掠夺;对于第二个问题,前传引入了恭特对妹妹的愧疚和信任,他偏执暴虐的妻子和下属哈根为此诞生,这二人给克里姆希尔德留下了永不弥合的伤口。《西格弗里特之死》篇的主要功能就是将这两个谜团解答。在《西格弗里特之死》中,几乎所有主要角色都经历了重大人格裂变,这看似不合情理,但如果将这些碎片般的故事拆开、并列,它们都可以看成是对《克里姆希尔德的复仇》的开头的不同解的尝试。西格弗里特在某些创作中是莽汉一个,误打误撞娶了勃艮第国王的妹妹,在另一些诗人的想象中则是龙血浴身的天选之人,王妹早已芳心暗许;布伦希尔德在某些诗人口中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在另一波诗人的描述里则是满口臣主道德的刻板女;哈根在某些揣测中是宁负天下人的奸雄臣子,在另一些版本里则是和西格弗里特常年并肩的铁汉……这些相异甚至相悖的口传被人为地囫囵剪辑,加之大段大段的时间隔断,被捋成了一个成篇幅却不成逻辑的故事,造就了文中长达三十六年的历史空白。
[1] 《德国文学史》第1卷,译林出版社,安书祉译
《尼伯龙人之歌》读后感(四):吐槽一下几个主角
西格弗里特、布伦希尔德和克里姆希尔德虽然都在史诗中占据不小的篇幅,但都不能算作纯粹的“人类”。西格弗里特是人类英雄和历史传说的结合,克里姆希尔德是人类女性和历史偏见的结合,布伦希尔德成分比较复杂,她是人类女性与历史的首尾两极的结合体。
对于西格弗里特,《西格弗里特之死》最终将其塑造为一个在神话与现实之间切换自如的英雄角色,他杀掉了一只从未有第二人亲眼见过的龙,他的不死之身在克里姆希尔德嘴里是那么理所当然,他的隐形衣从未转手他人,他截获的尼伯龙根宝藏被沉入了海底,而当这个人死去,笼罩在他身上的一切神话也烟消云散,这一切没人能证实,也没人能证伪。作品讲述的西格弗里特的为人所直击的武斗仅有两次:力挫丹麦和撒克逊军,在狩猎比赛拔得头筹。这都是在人类英雄范畴常见的比赛,也只能证明西格弗里特处于人类英雄中的顶端,并不能说他有什么通天入地,屠龙取国之能。西格弗里特的人物形象在天神与人杰中摇摆不定,这也使他徒具神力,徒有人形,没什么野心,甘愿做一条被爱情拴在邻国的狗。或者说,如果西格弗里特形象的诞生是围绕布伦希尔德而来,目的是通过西格弗里特的死亡来孕育布伦希尔德的极致的仇恨,那么西格弗里特就必须被塑造为一个没有女性不会喜欢的,完美的梦中情人,他英俊、富有、强大、痴情,可运天下于掌,却偏偏为了一个女孩做王下臣,应当是重新编纂时受了不少骑士文学的影响,可这也使他脱离了财权争霸的核心英雄圈,成为了一个不能与铁血史诗相融的浪漫符号。
对于克里姆希尔德,她在《克里姆希尔德的复仇》中被直接定义为野心勃勃的妖后,觊觎勃艮第沃野良久,处心积虑,然功亏一篑,是位武则天般的传奇女性。然而前传《西格弗里特之死》强行柔化了她的少女时代,并掺入了酸臭的姑嫂不和戏码,克里姆希尔德的魅力也随之大打折扣。她那天真烂漫,绝代美人的少女时代同样可以看作经骑士文学口味调和的二次编纂,而“姑嫂不和挑起战争”的编排则是历史上女性背锅的优良传统。神话对女性向来有点偏见,夏娃招惹苹果树,海伦招惹帕里斯,克里姆希尔德招惹大嫂子,战争来自人与人的不理解,最不能互相理解的部分就是女人和女人。《西格弗里特之死》多次强调,“是两个王后的争吵,让日后很多英雄死去”,那边恭特和哈根几乎按捺不住杀掉妹夫,抢钱夺权的磨刀霍霍,这边的文本却仍在假惺惺责怪两个王后心胸狭窄,一场野心家的权谋宴就这样化为一次争脸子的街坊吵。《克里姆希德的的复仇》中,克里姆希尔德常将亡夫挂在嘴边,后者成了师出有名的幌子,克里姆希尔德扬言要为亡夫报仇,更多还是在算计尼伯龙根的宝藏。在为夫报仇的苦妇人和醉心钱财的大妖后这两者间,克里姆希尔德同样显得定位不明,她爱也爱不到巅峰,贪也贪不到顶点,一个欲望不够极致的人并不足以促成这场灭国之战。相比之下,她的第二任丈夫艾柴尔,即历史上勃艮第灭国的祸首匈奴王竟然一直旁观甚至劝和。克里姆希尔德先后承担了哥哥恭特和丈夫艾柴尔的野心和欲望所带来的历史罪责。
对于布伦希尔德,她在《克里姆希尔德的复仇》中几乎没有出场,是专属于前传的“原创人物”。起先她的举止像个未开化的原始人(比武招亲的项目为跳远、扔石头、掷枪,均是再原始不过的运动),后又迅速进入封建领主太太的状态,促成这一改变的是勃艮第国王恭特的播种。布伦希尔德的存在如勃艮第本身,在她被人类征服前,是暴虐的,杀人无忌的,被人类播种过文明后,她又固执地遵循着人类自己也不一定贯彻的来的规约野蛮生长,摧毁纯真爱情的童话泡沫——她的身上并行着历史初期的暴戾、野蛮和发展到12世纪的社会的森严、窒息之感。
《克里姆希尔德的复仇》中,前传中浓墨重彩的尼德兰王子和冰岛女王仅仅在对话、回忆和转场上匆匆露了几面,这两个最具传说色彩的极端人物(极端的强大和极端的性格)的退场,一来佐证了《克里姆希尔德的复仇》本身就是一套与前文无关的,逻辑完备、历史性强的故事,二来强调了人类英雄(恭特、哈根)在史诗中的主角地位——这部史诗是彻彻底底的人类英雄的历史。恭特和哈根身为人类英豪,都不曾遮掩过自己巨大的野心,恭特渴望无上的统治,哈根渴求无边的富有,恭特抵不住妹妹的亲情牌前往匈牙利,仍携大批军队时刻自保;哈根始终贯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仍竭力谏主保国。史诗中的其他角色被命运安排,而恭特和哈根安排命运。《西格弗里特之死》中,他们选择杀死妹夫,削弱妹妹,确保勃艮第国的强盛;《克里姆希尔德的复仇》中,他们选择深入匈牙利,解除勃艮第国的潜在之忧。《尼伯龙根之歌》没有神灵,只有人斗,根据上一小节前传-正篇的推理,全文的高潮应在于《克里姆希尔的的复仇》结尾处勃艮第人和匈奴人的殊死之战,在于勃艮第英杰慷慨搏杀,笑谈饮血的壮怀,也对应了历史上勃艮第王国的昙花一现。
《尼伯龙人之歌》读后感(五):对同一传说的不同演绎——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族的指环》与德国民间史诗《尼伯龙人之歌》的简单比较
去年寒假写的东西。欢迎拍。
现在来看有些想法又有点不太一样了,不过还没想好写。
另外看完原著之后我就被许多人眼中的“反派”HvT吸引了,那时是欣赏他的坚毅铁血和近乎残酷的清醒决绝……后来又看了Wolfgang Hohlbein写的以其为主角的小说又被WH笔下HvT隐藏的微妙的温柔电到不行……强烈推荐这本~
好了下面正文。
《尼伯龙人之歌》是著名的中世纪中古高地德语叙事诗,融合了很多源自5世纪的口头英雄传说,被称为德语的《伊利亚特》。它把渺远的神话中遗留下来的历史片段和历史人物结合起来,成为了一部体现本民族品格的伟大诗作,充满了对命运的悲剧、对罪行不可避免的报偿、对正与邪光明与黑暗力量无止境的力量交锋的描写。
1848年到1874年,德国音乐家(同时也被认为是哲学家)瓦格纳历时16年时间从这部史诗和北欧神话中取材创作了《尼伯龙族的指环》系列歌剧。该系列歌剧共有四部,分别为《莱茵的黄金》、《女武神》、《齐格弗里德》和《诸神的黄昏》。
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族的指环》虽然与史诗《尼伯龙人之歌》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对于其中的人物和情节却也做了很多改变。本文即对这些改变做一些简单的、初步的分析比较。
一、中心人物齐格弗里德、布伦希尔德、克里姆希尔德(或古特露妮)形象的改变
1、齐格弗里德
在史诗《尼伯龙人之歌》和歌剧《尼伯龙族的指环》中,齐格弗里德都作为主要人物而出现。他是一位骁勇善战的英雄豪杰,性情直率,待人真诚,但在一定程度上过于自信,如歌剧中所说他是“不知畏惧的人”,而且不够成熟,缺乏对他人的判断力,这一点也造成了他最终的悲剧结局。
但是在许多方面,史诗和歌剧对他的塑造又不尽相同。
第一点,齐格弗里德的身世与性格的形成。
史诗中齐格弗里德是尼德兰(即今荷兰)的王子,“生活养尊处优,从来没有蒙受过任何的羞辱”,“他所需要的一切,应有尽有,不缺纹丝毫厘”,是“装点父亲王国的奇葩”,国王与王后的掌上明珠,拥有父亲封给他的大片土地和城池,“无忧无虑,心内从来不存任何芥蒂”,在“失足跌入滚烫的爱河”之前,他仅仅以“铲除横行国内的一切暴力事务”为己任,形象相对单纯。而在瓦格纳的歌剧中,他不再拥有这一显赫的贵族身份,他的父母是秘密结合的一对孪生兄妹(他们可能是沃坦主神的后裔),父亲在他出生前已经战死,母亲在生下他之后也去世了;他在森林中被侏儒迷魅抚养成人,而迷魅也并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希望利用他夺回宝藏的缘故才收养了他;在此环境中成长的英雄形成了一种近于野性的纯朴和直率,凭借鸟的歌声(也可以理解为自身直觉的表露)指引去做每一件事,不计较成败也从未失败,并且具有强烈的反叛性,就如尼采的评论所说,齐格弗里德“自出生后就继续革命;他……将传统、敬畏、恐惧全都掷于风中,所有不中他意的东西他都要将之打倒。他肆无忌惮地攻击神祗……”,是一位充满激情、肆无忌惮的浪漫主义反叛者。齐格弗里德无敌无畏的品质,正是瓦格纳在创作中重视英雄主义的体现。
第二点,齐格弗里德的经历与情感。
史诗和歌剧中,他都曾经斩杀过恶龙(这也是西方传奇故事的常见情节),但是史诗中这仅仅是作为他被人们传诵的壮举之一,以及对他刀枪不入原因的交代——“他在龙血里沐浴,齐格弗里德从此以后炼就一身铜皮铁骨,任何武器也难以将他伤害”,只是,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基里斯那样,此时恰有一片树叶落在他身上,使得他有了弱点,为后来的遇刺做了铺垫;而在歌剧中,这恶龙是看守尼伯龙宝藏的巨人所变,在消灭它之后,齐格弗里德得到了隐身盔和尼伯龙族的指环(这一情节的背景上,史诗中齐格弗里德通过征服尼伯龙王国获得了他们聚敛的宝物和隐身盔,而按照歌剧,宝藏本是莱茵河底的黄金,用它铸成的指环具有强大的力量,拥有它的人能够统治世界,却也受到诅咒),并通过饮龙血使自己能够听懂林中鸟的歌声,而他的刀枪不入,是后来与布伦希尔德相爱时,布伦希尔德为他祈祷所致(这一点正是歌剧中“爱”的主题的体现),而由于他的勇敢无畏,她无需对他的背脊施法,于是这便成为他的弱点。
在故事中,齐格弗里德在遇刺之前都经历了一场事实上是阴谋的狩猎。史诗中这也是他最后的辉煌:他猎获了比所有人都多的野兽,还生擒了一头熊,将它带回营地;但是在歌剧的改编中,他生擒熊的壮举被移到了在森林中长大的少年时代,而且也不是用暴力捕获,而是用号角声将它作为乐于陪伴自己的好友召唤而来。如果说史诗中他的做法多少有点炫耀自己武艺的意味,那么歌剧中这样的安排就体现了他作为“自然之子”的纯朴、本真的品质。再回到歌剧中对他最后一场狩猎的改编,这一次他没有得到任何猎物,却意外地遇到了莱茵河的三位女神,从她们那里听到了关于指环和他悲剧命运的预言,却毫不置信(史诗中这段情节是发生在哈根身上的,他随勃艮第王室受邀前往匈奴国时听到不祥的预言而不相信,在歌剧中瓦格纳为了完善齐格弗里德的形象,将这段情节转移到其身上,也就是说,歌剧中齐格弗里德的形象可以说是兼具了史诗中两位英雄人物的优点,已经不再是原来史诗中的单一形象了。对于史诗和歌剧在对这两位人物的安排上的差异,后面还会讨论),这一行为可以理解为他自恃武力的骄傲,也可以理解为他作为具有反叛性的英雄人物,对神的秩序、对宿命论的大胆挑战。
对于他与所遇到的两位女子布伦希尔德和克里姆希尔德(或古特露妮)的情感,史诗和歌剧的处理也有非常大的不同:史诗中他听闻克里姆希尔德的美貌之后便爱上了她,“其他的种种思慕和追求也统统付之西风、流水”,不顾父母的担心和反对一心想要与她结为夫妇,在得到了她的爱情之后也十分珍惜,终身未曾改变过对她的爱恋,至于布伦希尔德,他仅仅是在帮助贡特尔追求她,自己并未有非分之想(然而他却在战胜她之后取走了她的腰带和戒指,这枚戒指在歌剧中便成了那枚具有力量的尼伯龙族指环,而且还是齐格弗里德赠送给布伦希尔德的。史诗对此的解释是齐格弗里德此时出于战胜者的骄矜忘乎所以,做了不明智的事,这也体现了他的的性格弱点,即不够成熟,有时做事并不思考,带有“游戏”的性质)。而歌剧着力刻画了齐格弗里德和布伦希尔德之间的爱情,将布伦希尔德描绘为齐格弗里德的第一位恋人,以克里姆希尔德为原型的古特露妮则成为了夺爱者——她虽然也深爱着齐格弗里德,但是她是靠着使人失忆的药酒才获得了他的爱情。
2、布伦希尔德与克里姆希尔德(或古特露妮)
布伦希尔德和克里姆希尔德(或古特露妮)是这个故事中重要的两位女性形象,也是瓦格纳的歌剧对史诗改变最多的形象。
史诗中的布伦希尔德原本是冰岛的女王,后来嫁给勃艮第国王贡特尔为王后。她的容貌十分美丽,但是却绝非柔弱女子,武艺高强胜过男子,向她求婚者必须同她比试投石、跳远和投矛(这倒颇有中国传奇、武侠小说中女子“比武招亲”的意味)。她宣称“他如果能够悉数获胜,我的爱情自然归属他身;否则我自然不能为他做妻,他却应该从此身首分离”,这样的不可一世让前来求婚的勃艮第使团几乎无法接受——“这就是国王爱恋的姑娘?!她的确应该回到地狱去当混帐魔鬼的新娘!”不过比他更为强大的齐格弗里德,作为贡特尔的替身,在比武中战胜了她,使得她放下嚣张的气焰,同意嫁给国王为妻。然而当贡特尔宣布为齐格弗里德和克里姆希尔德缔结婚姻时,她对比武结果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于是拒绝贡特尔的接近,直到齐格弗里德再次以贡特尔的名义制服了她,她才终于“再也不比任何一个女人更加强悍半分”,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这之前她对齐格弗里德所持的感情比较难以判断:在他作为使团成员面见她的时候,她以为他才是向她求婚的人,也许对他存有惺惺相惜之情,甚至可能是爱慕。如果确实是的话,那么她在齐格弗里德和克里姆希尔德结婚时的失态表现,除了怀疑贡特尔战胜自己的真实性以外,还应该有感情上的失落)。当一切似乎都已经过去的时候,克里姆希尔德佩戴着齐格弗里德从她那里取走的腰带和戒指出现在她面前,并且用过激的言语刺伤了她,激起了她对齐格弗里德的憎恨,给了贡特尔和哈根刺杀齐格弗里德一个理由——为她所受的侮辱雪耻——尽管这一行径的真正目的是“如果齐格弗里德不在人世,那么属于他的许多王国都将对我们俯首称臣”。在齐格弗里德死后的故事情节里,并未更多交代布伦希尔德的结局,她可能是在勃艮第作为王后终老。
在歌剧中布伦希尔德不再是史诗中那个强悍的女王。她是主神沃坦的女儿(或许也是他的心上人),负责为瓦尔哈拉天宫收集烈士英灵的女武神,但由于违背沃坦的意愿救助了齐格弗里德的父母,被罚在巉岩上沉睡,周围有火焰包围保护,只有不惧怕沃坦的“永恒之矛”的勇士才能将她唤醒并娶她为妻(这又是西方传奇故事的一种常见情节,如《睡美人》等童话故事也有类似的情节模式)。多年以后,她曾经救助的女子的遗孤,即齐格弗里德,这个不惧怕任何事物的英雄,唤醒了她;爱情的力量使他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惧怕。勇士和女神结为连理,将尼伯龙族的指环赠与她作为信物,她也回赠他自己的骏马,并用自己的法力使他在战斗中不受伤害。齐格弗里德离开布伦希尔德去创造事业,不料却被药酒迷惑忘却了真爱,娶了古特露妮为妻,还去帮贡特尔娶了布伦希尔德,并夺去了那枚指环。布伦希尔德认为齐格弗里德负心背叛了自己,因爱生恨,将齐格弗里德的弱点告诉了想要杀害他的哈根。在齐格弗里德死后,布伦希尔德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她取回了指环,而后纵身投入焚化恋人遗体的火焰中追随他而去。烈火去除了指环上的诅咒,莱茵河的黄金重新回到了河底,“诸神的黄昏”来临,神界在火焰中消亡,人的世界在爱的力量下获得新生。这样的安排体现了瓦格纳的艺术思想中对女性形象的定位:他认为女性身上兼有救赎和毁灭两种特性,这种矛盾性使他创造的女性形象通常是复杂的、怀着巨大痛苦的人物,布伦希尔德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另一位重要的女性形象就是史诗中的克里姆希尔德或歌剧中的古特露妮。克里姆希尔德原本是美丽而单纯的公主,因为一个预言了不幸爱情的梦境而拒绝接受任何人的爱慕,但是却宿命般地与齐格弗里德一见钟情;后来出于年轻女子常有的虚荣,她的言语刺伤了布伦希尔德,导致了齐格弗里德被害,而且还是她自己把齐格弗里德的弱点告诉了哈根,也就是说,是克里姆希尔德自己在无心之中造成了她最爱的人的死亡,这样的打击是这个年轻女子完全无法承受的,再加上贡特尔、哈根等人夺走了她从齐格弗里德那里继承来的尼伯龙宝藏,对她简直是雪上加霜。悲伤和仇恨完全改变了她的性格,她不再是那个纯洁温柔的少女,而成了一位可怕的复仇女神。她与匈奴王埃策尔联姻,又请了勃艮第的贵族们去作客,借着匈奴人的力量设下圈套,诛灭了既是她的亲戚又是她的仇人的勃艮第贵族们,甚至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同胞兄长,最后她也被自己的手下所杀。克里姆希尔德是史诗的中心人物,史诗的后半部分完全在叙述她在失去夫君之后的转变与展开复仇的故事,在我看来是史诗塑造的最成功的形象。
然而在瓦格纳的歌剧当中,也许是为了突出女神布伦希尔德“宿命式原罪和爱的救赎”与开创新时代的形象重要性,克里姆希尔德(在这里她的名字变为古特露妮,即美好的诗之意)的形象被明显地矮化了。她除却用药酒诱惑了齐格弗里德之外并没有更多出场,完全成为了一个陪衬。
二、其他人物形象的改变
1、哈根
毋庸置疑,哈根在这个故事里不容易被读者视为一个正面人物。无论在哪一个版本里,他都是杀害英雄齐格弗里德的主谋,然而史诗中哈根形象的界定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在这里他在故事的前后两部分给人的印象存在不小的反差(前半部分尤其是他刺杀齐格弗里德的行为让人很容易把他直接定义为反面角色,但后半部分他的忠心为国、浴血奋战等又塑造了他的英雄形象),总的来看,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有勇、有谋、有义的优秀骑士、铁血男儿。他是勃艮第国的贵族重臣,对他的君主贡特尔保持着高度的忠诚,对齐格弗里德原本并无私怨,还有些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对齐格弗里德和克里姆希尔德之间的爱情,从行动上看也持的是支持的态度;而后来的憎恨和密谋刺杀,则是出于各为其主的原因,想要通过这种方式为国除去一个隐患,同时使尼伯龙宝藏归勃艮第王国所有。在随勃艮第王室受邀前往匈奴国时,他听到了来自河中仙女的不祥预言,却挑战神明,否定神谕,只相信自己的意志和力量。而后他带有“破釜沉舟”意味的毁弃渡船自绝后路,用必死的决心向战友们做出的悲壮的动员,都具有让人起敬的英雄气概。而当他最终被俘不屈,被克里姆希尔德所杀时,连匈奴王也禁不住对他的死亡感到痛惜:“可叹这位最佳骑士现在却躺倒在一位女人的剑下死于非命,哈根操提战盾在手时,经历了多少战斗厮杀,我不管对他如何仇恨,心中却万分沉痛悲伤。”读者可能会不喜欢这样一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式的人物(事实上很多这一类型的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都不太让人喜欢,因为他们总是那些做了“要担责任的事”——即招人憎恶又不可避免的事——的人,是那些“光明正义”人物背后的阴影),但是却也无法否认他作为成熟理性、值得尊重的日耳曼英雄形象,甚至有一部分观点认为,他才是史诗歌颂的真正英雄,而齐格弗里德的悲剧,其实是他自己的不够成熟所致。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在此暂且不论;必须承认的是,有这样一位优秀的对手,也绝对不算辱没了主人公英雄齐格弗里德。我在这里做一个可能不太贴切的比喻,在《尼伯龙人之歌》中,如果说齐格弗里德是太阳,热烈、灿烂、纯净,象征着感性的话,哈根就是冷静的月亮,是理性的象征;故事以齐格弗里德为主线的前半部分是暖色调的白昼,情节主要是欢快而近乎于游戏的,随着齐格弗里德的死亡,这“白昼”结束,进入冷色调的黑夜;在后半部分的情节里,故事被染上了令人绝望的铅灰色,这一道月光,即在此时成为了夜空的主角,放射出坚忍执着的冷光,照耀了黑夜。但是和克里姆希尔德(或古特露妮)一样,他的形象也被瓦格纳明显地矮化了,史诗中他让人敬重的优点和事迹被转移到了他的对手,故事的主角齐格弗里德身上,而他自己无论是身世还是人格都被一再贬低:瓦格纳的笔下,哈根是贡特尔的异父兄弟,他的父亲正是曾经拥有过尼伯龙宝藏,后来又失去了它的侏儒阿尔布里希。他对齐格弗里德下毒手,完全是为了夺取他的指环,以使自己和阿尔布里希获得指环中的巨大力量。他对贡特尔也并不像史诗中那样忠诚,为了争夺指环甚至杀死了他。最终他在跳入莱茵河寻找沉入河底指环时被河中的三位女神拖进了深渊(在史诗中,他是自己把宝藏沉入河底的)。哈根在这里成为了完全的反面角色,这一形象的绝对阴暗与齐格弗里德形象的绝对辉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贡特尔
这位国王的形象,在史诗和歌剧中的形象差异不是很大。如果按照中古骑士精神的评判标准,他无疑是不合格的。他想向布伦希尔德求婚,自己却没有勇气接受史诗中比武或歌剧中火焰的考验,而是让更为强大的齐格弗里德作为自己的替身去征服布伦希尔德;在哈根向他提出除掉齐格弗里德的计划之后,贡特尔先是支支吾吾,不肯答应,后来才参与了密谋(在歌剧中,哈根刺杀齐格弗里德时贡特尔还出手阻止),英雄死后,他又不肯承认对此所应负的责任(在这一点上,哈根远远比他表现得有气魄),在那个“任何一种否认或者回避都意味着怯懦,而任何一点怯懦都会让人显得有失英雄本色,损害英雄的荣誉”的时代,贡特尔明显不能被称为英雄。在史诗中,他在匈奴人的境内落入圈套,损兵折将之后,还希望通过谈判请克里姆希尔德对她“格外开恩”,直到最终他的属下都已战死,孤身一人时,才稍稍表现出了些血性,奋力一搏,但是为时已晚。
3、其他次要人物
这一类人物包括齐格弗里德的父母、守护尼伯龙宝藏的阿尔布里希等。齐格弗里德的父母,前面已经提到,在史诗中是尼德兰的国王和王后,并无太多可圈可点的情节,但是在歌剧中成了秘密结合的孪生兄妹,他们挑战世俗观念,摆脱道德束缚而大胆相爱,通过对这一对爱侣的塑造,浪漫主义的反叛性主题再次得到强调。阿尔布里希在史诗中是尼伯龙宝藏的守护人,在尼伯龙王国被征服后效忠于齐格弗里德,还在他为贡特尔求娶布伦希尔德时给了他帮助;在歌剧中它却成为了一个为获得宝藏而诅咒爱的邪恶丑陋的侏儒,在失去宝藏后一心想要将它夺回。这些人物在作品中的的重要性较前面所提到的人物要低,但是从他们形象的变化中同样可以看出史诗和歌剧的主题思想差异。
4、仅在一处出现的人物
由于史诗和歌剧的故事结构不同(史诗的上半部与歌剧的最后一部故事重合),有很多人物是史诗中出现,歌剧中未出现,或者史诗中未出现而在歌剧中出现的。前一类型的代表如贡特尔和克里姆希尔德的两位兄弟盖尔诺特和吉赛尔赫;哈根的朋友,既是音乐家又是战士的伏尔克;克里姆希尔德的第二任丈夫,匈奴王埃策尔;伯尔纳国王迪特里希以及他的师长、亲信,最终因为无法忍受克里姆希尔德的血腥复仇而诛杀了她的希尔德布兰等人。后一类型则主要以神话中的人物为主,比如以沃坦为代表的天神们、莱茵河的三位女神、巨人法索尔特和法夫那、还有收养齐格弗里德的侏儒迷魅等。这些人物由于只在一处出现,所以他们的形象也不存在改变。
三、作品主题与体现的思想的改变
史诗《尼伯龙人之歌》作为中古时期的优秀骑士文学作品,描述了古代欧洲列国的战争、联姻等一系列事件。的确,这部叙事诗歌颂了许多英勇慷慨的骑士与美丽高贵的贵妇的事迹,对于出现的人物,大都是赞颂多于批评,即使是非正面角色,只要符合骑士精神的标准,也绝不吝惜“英雄”、“勇士”、“好汉”这样的褒义称谓,其中对战争场面的描写确实让读者热血沸腾,如身临其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史诗中还是具有很浓的政治意味,有一些意见还认为这篇史诗是在影射公元791年前后法兰克王国的军队东征阿瓦尔的战争。而且它似乎把“复仇”作为了自己的主题,最终所有主要人物都死于仇杀,也在表明唯有死亡才是这种仇恨的终结的宿命式的悲壮。
但是在它被改编为歌剧之后,这部作品的主题不再是简单的冤冤相报,而有了一定的提升。瓦格纳深受悲观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曾经说过:“如果众神在创造人类之后,便毁灭自己,他们的意志或者可以达成。为使人类与自由的意志,他们必须舍弃自己的影响力。”他赋予了剧中英雄以反叛的激情、毁灭一切的力量,同时也注定了悲剧性的命运:英雄能够完成救赎的使命,使旧时代覆灭,新时代来临,但走向新生的道路却是绝望的,要以英雄的最终毁灭为代价。于是,歌剧《尼伯龙族的指环》的主题,就是代表旧时代的众神统治的覆灭,和人类通过爱的力量获得救赎与新时代的诞生。被诅咒的指环象征金钱和权力,它是整部剧作的矛盾之源;沃坦的“永恒之矛”象征旧世界的秩序;齐格弗里德的剑象征英雄的意志,代表着新的、具有生机的力量,它击碎了“永恒之矛”,使得“诸神的黄昏”预言应验,众神统治覆灭,属于人类的时代开始——然而最终完成这一使命的却并不是这英雄的意志力之剑,而是爱——当初被贪图黄金的侏儒所抛弃的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它去除了指环的诅咒,使黄金复归于莱茵河底,结束了整个故事。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史诗《尼伯龙人之歌》中的大多数主要人物属于正统的西方基督教世界,但歌剧《尼伯龙族的指环》当中的宗教体系却并非基督教而是来自北欧的远古神话多神体系,且其中的神灵们也并非万能,甚至可以说是相当软弱的,比如沃坦为了建造瓦尔哈拉天宫险些把美神弗莉雅抵押给巨人,后来又为齐格弗里德所击败,“永恒之矛”也被击碎,而众神的统治也在布伦希尔德点燃的烈火中覆灭。这样的安排也正是瓦格纳的艺术、哲学思想的体现:他认为西方社会历史的核心基督教文化阻碍了人性自由发展,人性要获得自由,就应当推翻这种的束缚,于是选择北欧神话而非基督教作为故事的宗教体系;同时,为了彰显浪漫主义的反宗教性和反叛精神,体现比为理性秩序所控的旧时代更具有生命力的自由新时代的必然到来,弱化了神的形象而强化并歌颂了人类中的英雄。
参考文献与资料:
闫铮《论瓦格纳歌剧的英雄质素———以《尼伯龙根的指环》为例》
姜岳斌《尼伯龙根神话: 黑格尔的误读与瓦格纳的扭曲——兼论西格弗里的形象在德国文化中的异变》
尼伯龙根之歌_百度百科
尼伯龙根的指环_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