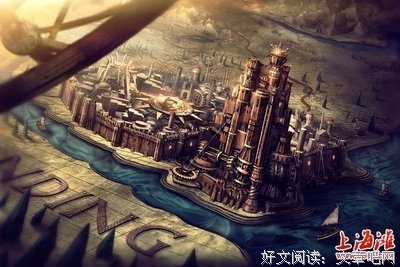
《权利的成本》是一本由【美】史蒂芬・霍尔姆斯 / 凯斯・R.桑斯坦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无盘)图书,本书定价:25.00,页数:2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权利的成本》精选点评:
●【历史】【法理学】 权利有成本。
●很有趣 对现代的政治形态很有揭示意义 因为科技发展现状的政治已经和过去很不一样了 给我很多思考的新角度
●清晰明了地解释了权利的复性特征。有效政府与国家能力。
●作者反复论述的观点就是政府征税的合理性及必要性。结合成书时间,正好是克林顿政府增税改革期间,政府喉舌的著作,御用文人。征税永远不需要道理,需要的只是掌握国家的合法暴力权。对权利尤其是言论权和福利权的探讨完全没有逻辑,作者把所有国家福利归结为同情心和道德心,难道没有想到这只不过是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利益交换吗?
●无政府主义为什么可笑,这本书能告诉你。
●没留下太深的印象,读了等于没读.
●对权利话语绝对化的趋势进行纠偏,指出任何权利的实现都或多或少需要政府积极作为(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所有权利都是积极权利”,这话稍有点偏激,“消极/积极权利”的概念区分还是有存在必要的)、公共财政的支出;而又由于财政资源有限,所以只能通过政治、预算过程来对各种权利的保护程度作出排序、分配。之后,此书对福利权的性质和功能深入分析,认为这实质上是种现代的阶级整合机制,是富有和贫穷阶级达成的妥协(见《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是对贫穷阶级的合作所支付的报酬,并增强其自我完善能力(而非消极依赖于政府福利),从而在不损害社会差异激励的同时,维持了社会稳定。其论证体现了罗尔斯第二正义原则“不平等的安排应使得社会中处于最劣势的成员受益最大”。立场公允,头脑清醒,只是意思重复之处稍多,不够精练。
●带功利的直接与现实,也不忘自然法学的经典与传统,结合的很好的作品。值得推荐一读的作品。视角独特又不空,翻译稍微有点稚嫩。
●所以这本书成为了保研/考研/research proposal/personal statement被问到“你读过什么书”的最佳答案。
●税收是权利得到保障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权利的成本》读后感(一):认真滴对待权利的成本
公民的诞生意味着一个走向权利时代的来临。但真正雅俗共赏的权利哲学专著似乎并不多见。最近新出的《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则是一本难能可贵的代表作。这并不是一本艰深晦涩的学术专著,而是一本既适合学者也适合大众阅读的书。 像很多的书的命运那样,这本书的名字比它的内容更容易被读者记住。书名揭示了这本书的核心问题。首先需要解释的一点,题目中的权利并非自然权利或者道德权利(RIGHT)而是实证法上的权利(ENTITLEMENT),用作者的话来说“权利将被界定为个体或团体能够运用政府的手段切实地加以保护的重要利益。”柏克在《法国革命反思录》曾言国家的税收就是国家,他的意思是说税收构成了国家的财政,从而使得国家具有了生命。但税与自由(在作者眼里,权利意味着某种自由)之间如何发生关联呢?对此两位作者这样解释道,权利不仅仅具有私人特征更具有公共性,因为权利不是免费的午餐。它的创设与保护都需要由公共财政予以支撑,因而是代价昂贵的公共物品。既然如此,那么政府不仅仅是必需的,而且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去捍卫公民的基本权利,否则公民的基本权利便流于一纸空文,永远只能在书本上看得见却在现实中无法实现。 因此我们看到,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和结论部分重复出现的一句话就是:权利是作为由政治创设、集体资助、计划促进人类福利的手段而出现的公共物品。我认为这句话是理解这本的书一个关键点。基于此,他们否认了传统的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的两分法,转而认为所有的权利都是积极权利,进而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哲学观念。权利的本质并不是对抗政府,而是呼吁政府,在他们眼里,政府不再是公民权利的最大的威胁者,而是一个兢兢业业的权利的保护者。 作者的实证主义权利观和经济分析的方法,得出的上述结论却让人值得怀疑。是作者的想法要么过于善良,还是他们希望建立“警察国家”呢?如果是后一种目的的话,则无疑是值得警惕的。这也难怪一位自由主义者,曾经称这本书为“20世纪里对暴政最无耻的辩护之一”。这本书本质是反自由主义的,而且明显展示了与美国建国之父们的观念之间的根本分野。起草美国宪法的那些作者在主张权利的两分法时,并没有否认权利的保护也需要成本。之所以提出这种划分则是源于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权力被滥用的警惕之心。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则背离了这一传统,成为“罗斯福新政”和“伟大的社会”的支持者。而后者则是福利国家政策的典型代表时期,尽管现在各国为了满足公民的经济社会权利而不断扩大自己的作用,但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的艰难历程中,这却是一种饱受争议如今陷入困境的政策,美国学者阿米·斯特基斯说国家卷入社会意味着历史出现“自由的倒退”甚至“重新野蛮化”。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还尤其提到了中国:“不可否认,目前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的经济体制揭示了,一旦合乎时机地并入到世界经济之中,一个没有强大的法院体制的社会,甚至于缺乏对财产权可靠的司法执行时,只能利用血缘关系以及其他非正式的人际网培育可靠的承诺。”在一个中国读者眼里,作者把法院体制是否强大视为解决中国人的权利保护的关键所在,显得过于幼稚。也许这只是目前中国问题的一个原因所在,但这仅仅是次要的一点而已。 在一篇有限的书评里,我似乎说了这本“宪政经典”太多的坏话。在文章的最后,我要说的是尽管这本书争议很大,但它依然带给了我一个新鲜的视角,提醒我们不应该忽视权利的成本这一权利哲学的基本问题。它所采用的经济分析的方法充满了实证的精神,也许我们未必同意它的结论,但一定会对作者们在事实面前的冷静和克制而肃然起敬。
《权利的成本》读后感(二):读后感
私人自由有公共成本。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如题所示----权利的成本。
正如初高中一直被灌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为保障自身权利着而建立政府。由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总是以权利关系的创造和维持为先决条件,所以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从来不是免费。
本书以美国刑事司法体制为例,阐明美国的刑事司法体制是昂贵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既打算避免错误的宣告无辜的被告有罪,又要阻止拥有致命武器的警察和狱警虐待即使是被宣判有罪的人。”
权力拥有成本便意味稀缺。刚性的预算约束则意味政府将对某些事情少管为上或作壁上观。
公民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和自由。但法律意义的权利是“伤人的牙齿”。权利与权力有时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挤压与冲突。如你的舍友拥有话语的权利,而你也拥有在安静居室休息的权利。两者相矛盾,却可调和。同理政府削减公民自由必须令人信服的援用重要社会利益。要侵犯核心的宪法价值,政府一方因该有更重要的价值保护。“权利之间的一些冲突根源源于全部权利对有限的预算费用的一般依赖性。单是财政限制就排除了所有基本权利在同一时间被最大限度执行的可能性。权利总是需要或包含着金钱性质的权衡并且开支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政治决定的。”
本书由财产权引入,探讨了言论自由,,责任,道义,贫穷,公平等一系列问题。认为“是一盘散沙的社会团结起来不仅通过习惯、权威、共享、文化、归属感以及害怕警察,还需要通过广泛接受的互利。这就是他人逃避责任是人们愿意贡献自己的份额的一个原因。一旦个人彼此自制、服从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清晰规则并且齐心协力,社会就会昌盛。”
“把权力视为交易也就是期望,更多的大股东将实际上分得更多的利益。”经济上的马太效应增大社会矛盾,并将不断扩大。同时,纳越多的税的富人明显拥有更大的权利。这里并非只指其用不正当手段贿赂或暴力夺取权利,而是指富人拥有更好的选择——如接受更好的教育,参与竞选,更好的生活,可以请更好的律师等等。即使身为普通者的我们也能清楚的感觉到世界的不公平。更何况身处两级末段的人们。所以绝望下的他们因愤慨而做出的极端举动便可以理解了。那么此时富人便需要作出回应。因此,本书给了一个有趣的解释---------“减低穷人的极度绝望或许也跟至于道德原则、纯粹的怜悯以及同情,但既然小老百姓正在挨饿,富人的城堡并不安全。那么扶贫的出现有时,或许是最确切的,就是富人自卫的策略。········如果那些拥有很少或者不用油彩站的人不愿顽强的对抗外国掠夺者和侵略者,富人的财产权就一钱不值。单是出于深谋远虑的考虑,财产所有者就有动力防止穷人对政治的疏离感。甚至,为了他们的目的,调动穷人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他们消极的默从,政府需要摆出明显的整合姿态。公民权——如投票权,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力,获得公共资助的教育的权利——远远不是消极的免受政府干涉,而是把被排斥的个人拉进共同体的手段。”人类行为者不可能单枪匹马为自己的行为创造所有条件。我们对利益的态度应当包含权衡与妥协。
我们应当记住:一个民主的政府不可能均衡的卖力保护所有他声称要保护的。
《权利的成本》读后感(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应
转入正题之前先扯一下题外话,关于中国的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这个其实我也不是十分了解,但就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看来,似乎在理论上自由派是大获全胜了。新左派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他们所采取的理论工具也没有得到其他人的认同。而我觉得这里面最荒谬的是,在中国,鼓吹反对普世价值,文革、人民公社有理,扯着后殖民主义、后现代的左派比比皆是,真正地为左派的基本主张——福利国家,社会平等认真地从理论上辩护的左派,我基本找不到。一句话概括:中国没有像样的左派。这就产生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例如自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比自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多得多,哈耶克在中国也成为了显学,“大社会,小政府”似乎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毕竟在我党六十多年英明的领导下,大家都很难想象政府会干什么好事出来,所以支持小政府也是正常不过。但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我虽不是左派,但也认为中国的右派,应该拥有一个优秀的论辩对手。
我就是带着以上的看法看《权利的成本》这本书的。我更愿意把这本书命名为《权利的细节》,这本书从许多细节出发,探讨了法律上的权利在实际中是如何运作,如何得到保护的。而正是从种种细节,作者对一些古典自由主义的偏见作出了回应。
一、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一对古典自由主义这经常提及的概念在中国通过伯林等人的著作已经为人熟悉。一般来说,消极自由指的是不受别人干涉(强制)的自由,如财产权,而积极自由指的是控制、或干涉,或决定他人做某事的自由,例如选举权,福利权,等等。积极自由这个概念从诞生之日开始就有被妖魔化的倾向,古典自由主义把积极自由与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认为积极自由的实现难免侵犯到消极自由,因此消极自由优于积极自由,才是基本的自由。由这个立场出发,古典自由主义反对政府以种种理由对消极自由作出限制。
《权利的成本》对这个偏见作了有力的批判。它质疑,消极自由——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它辟出了一个私人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既不受他人控制,同时也不会妨害到其他人的自由——真的存在吗?答案是: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自由,实际上都具有公共性,都是一种积极自由。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财产权
——财产权,即“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不正是消极自由吗?它不要求别人做任何事情啊。
——不要只停留在字面上,我们看一下要保护财产权,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我们要立法保护私有财产。
——之后呢?我们需要警察部队以及军队来保护私有财产。除此之外,还需要建立法院来对侵犯财产权的行为予以制裁。对于房屋这一类不动产,还要建立产权登记制度。
因此,所谓的“消极自由”,并不真的是一个私人领域,它还是要求公职人员的作为,还是要求财政上的支持。除此之外,“消极自由”也有可能影响到其他权利的实现,这就是由于权利是有成本的。
我们假设有这么一个国家,她不像我国这么地大物博,公仆们可以到处出国考察,这个国家的政府非常贫穷,警察都请不起几个。这时既面临一个警力配置的问题。这个国家有两个地区,一个是贫民窟,里面很多穷人,但他们都身无分文,另一个地区是富人区,资源丰富。由于财政是有限的,政府不得不在经历调配方面在保护穷人的生命和保护富人的财产之间做出选择。
财产权,生命权这两个“消极自由”,这时出现了矛盾。
所以,其实不论是像财产权那样的“消极自由”还是如福利权般的“积极自由”,它们都需要政府的作为,需要财政上的支持,两者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没有必要把积极自由、福利国家看作是“通往奴役之路”,如果创设这个权利对社会的确有好处,并通过法定、民主的程序,我们并没有理由感到担心。
二、个人与政府的对立
我们经常谈论的“小政府,大社会”,或者“大政府,小社会”,其实都源于把个人与政府对立起来的偏见,仿佛只要政府所到之处,个人自由就寸草不生。因此最理想的政府就是最小的政府,政府只要做个看门的就可以了。与政府干预总是侵犯公民自由的幻想恰恰相反,政府在保障自由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权利的成本》以1996年的美国财政为例,说明了只为保护一些基本的权利,政府需要支付多少钱: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国防开支高达440亿美元;保护公民各种权利自由的司法系统的开支达到50亿美元;就算是简简单单一项专利、商标登记,也用去了纳税人八千二百万美元。国防、司法、知识产权保护这些领域,恐怕连支持最小政府的人也认为是政府不可缺少的职能,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权利的成本》用具体的数据表明,所谓的小政府可能是个幻想。这个政府再“小”,也小不到哪里去。我们固然要限制政府权力,防止它侵犯公民自由,但吊诡的是,限制政府权力的,恰恰也是法院、监察部门等政府机构。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像索马里那样的弱小政府,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我们把个人与政府对立起来,只是因为很多时候,司空见惯,我们便习以为常,政府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往往被我们忽视。我们的房子完好无损的时候,我们不会想这是政府保护公民财产权的结果,等到房子被强拆了,我们才会知道,这是政府干的“好事”。
除了以上两个主要方面,这本书还在分论中论述了多种自由,如环境权、宗教自由等如何依赖于政府的投入。里面还有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论述,例如谈及社会再分配问题,作者回应福利权“劫富济贫”的质疑,认为政府保护财产权,实际上也是用全体纳税人的钱,用来保护富人的财产,实际上也是一种再分配财产的行为,这些论述的非常有趣,我就不再多说了。总的来说,这本书的立场是相当持平的,但也提供了许多对古典自由主义有力的质疑。不知道古典自由主义者对这些质疑有何解答呢?找找看。
《权利的成本》读后感(四):译者前言
法律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在我国已成定局,甚至于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已不成其为讨论,“权利”这个语词在法学界几乎获得了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并且也正吸引着无数“眼球”的关注。但是,这种“无可置疑”和无数关注却令我有些担忧。通常对一样事物关注渐多、渐热之时,便会有话语的出现,于是论证和研究或者根生于话语、或者追随于话语,热情淹没了理性、口号淹没了具体研究。权利话语亦是如此。当我们忽视对权利实施的具体途径和具体问题的关注之时,权利的实施、权利可能被滥用都会成为棘手问题。而当代著名的公法学家霍尔姆斯和森斯坦这本《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则为我们揭示了权利实际运作的逻辑,掀开表面、洞见本质,作者剖析了潜藏于事物表面之下的权利运作规则。实际上,这些看似“天经地义”的东西是我们的共同体和社会在权利日常实施的过程中仰赖的规则,而人们却常常对此熟视无睹。
根据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权利是天赋的,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为了对抗政府。这样的观点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早期自然能对压制性的旧有制度起到摧枯拉朽之功效,革命时期也往往需要激发出人们对于美好新社会的乌托邦式的憧憬。但是当一种政制得以建立,政府的运作稳定之时,权利如何能获得切实的实施则成为桌面问题。在霍尔姆斯和森斯坦的这本小册子中,权利专指法律上的权利,就是个体或团体能够运用政府的手段切实地加以保护的重要利益。(页3)权利,要想真正成为法律赋予的权利,必须是司法上可执行的。权利不是需要政府撒手,而是需要政府积极的保护。政府若想积极提供这种保护,必须依赖充足可供支配的资金,也就是说贫困、软弱无能的政府无法切实地实施权利。可见,作者不是依赖于道德哲学,而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对权利进行诠释。
法国的贡斯当是第一位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放到一起讨论的思想家,只是他对此分别称作“现代的自由”和“古代的自由”。真正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作出明确划分的是现代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根据他的定义,消极自由是指免受政治权力干扰的权利;而积极自由是指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本书的作者首先针对这个盘踞于权利理论中的“成见”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无论积极权利还是消极权利都需要政府的积极保护,因而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两分法是没有意义的,所有权利都是积极权利,也就是赋予权利(entitlement),需要政府的创设与实施,权利的本质并非是对抗政府的。通过破除权利的神话,作者直面权利的成本。既然权利是有成本的,那么权利的实施必然涉及稀缺问题,因而不可能是绝对的。在此,作者把成本-收益分析引入了对权利实施的研究。一般来讲,经济分析建基于自由市场,但是作者的经济分析却导向了政府规制(regulatory)理论,把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说成是“税收交换保护”,我们通常视为正义的最后防线的司法机关也不过是政府的一个分支。福利国家的批评者们往往认为,福利国家是成本高昂的、会鼓励懒惰。然而本书的作者提出了与之不同的主张,福利国家实际上是一种能够获得社会合作与回报的投资,是划得来的。
对于本书,读者或许会存在两个疑问。其一,是否可以说谁纳的税多,谁就能得到更多的保护?如果是这样,社会平等在哪里?的确,从现实的角度看,由于权利有成本,有些权利的实施是昂贵的,所以富人实际上会比穷人享受更多的权利。但是现代社会平等的关节点在于提供平等机会,比如提供公共资助的教育。作者还区分了“税”与“费”的不同:税是向国家内的所有人征收,而费则是针对特定的事项。私人权利具有公共性,其成本需要由全体纳税人承担。权利在有限的意义上可以被说成是“绝对的”。当基本权利危在旦夕时,政府不得随便以世俗的原因把不实施正当化。(页61)从这个意义上讲,某些权利是绝对的,每个人应该得到绝对的平等保护。
其二,可以说有政府便有征税,但并非所有征税的政府都切实地把税收用于保护权利、执行权利上。是什么使得政府乐意保护权利?这里实际上隐藏着一个政府与公民的博弈过程。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上著名的《大宪章》,其中引人注目的条款之一便是贵族要对国王征税的权力行使监督权:未经由贵族代表组成的大会议的同意,国王不得征收兵役免除税和传统的封建三捐之外的助捐。贵族们与国王的斗争开启了宪政史的新篇章,“昭示了代议制民主和现代法治的一些基本准则:未经纳税阶层同意的征税是非法的;纳税的标准必须由纳税人的代表决定;国家财政预算及其支出要受到代表的审查和同意。由这些代表所组成的大会议后来成为近代议会。一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时,那句响亮的口号也与《大宪章》有着密切的关联——‘无代表,不纳税’。” 本书的作者虽然强调政府对于保护权利的重要作用,但并非片面强调政府的权威。与传统上强调财产权(在本书中,财产权也是法律的产物,需要政府保护)不同,作者尤其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把言论自由视为最珍贵的宪法权利。(页66)言论自由使对其他权利的侵犯更可能得到报道,它有助于确保政治责任,肃清政府腐败,曝光权力滥用,并且通过向官员以及公众以外的专家充分征求意见和批评从而提高制定政策的质量。表达自由是民主自治的实质前提,是所有其他自由所赖以依存的自由,(页66)它为充分的民主协商、审议预算提供了保证。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的一个直观感受是,public是书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它既包含着“公共”的含义,又包含着“政府”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即等同于“政府”。因而我把public officer译成“公职人员”,而非“政府官员”,为了表征其公共性,而避免让人在中国传统的语境下望词生义地以为“政府官员”是高高在上的官僚。同样taxpayer一词在美国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公民”,这令我比较质疑“纳税人”这种约定俗成的用法,因为“纳”往往使人有一种“不自愿”和“压迫”的感觉,而这是与公民社会的实质不大相符的,但我还是屈从了约定俗成。
本书继承了罗斯福新政的传统,在规制型政府的语境下进行论述。罗斯福曾提出过一个所谓的第二权利法案,“人们有在国内工厂、商店、农场或矿山获得有益且有报酬的工作的权利;人们有挣得足以提供充足衣食和娱乐的收入的权利;每一个农民都有权种植和出售农作物,其收益足以使他和他的家庭过着体面的生活;……每一个家庭都拥有体面住宅的权利;人们有获得充分医疗保障和有机会获得并享有健康身体的权利;人们有获得充分保护免于老龄、疾病、事故和失业的经济忧虑的权利;人们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页74)这里确认了一些积极权利,虽然这个“权利法案” 并没有成文法化,但美国政府给付活动比重的不断增加应验了罗斯福的话。我国今天也正处于一个改革期,广大的农民和工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经济领域的自由,但是由于对所谓的积极权利(比方说福利权)重视不够,他们的财产权利、契约自由也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证。由于宪政和权利学者对于政府保证自由的一面重视不够,反而使得政府对公民权利诉求做出积极的回应缺乏知识上的储备与积淀。本书提供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在国家繁荣、稳定的同时实现普遍的权利。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的政治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些激动人心的推动公民权利发展的事件,信访人数的剧增、由孙志刚事件引发的三博士与五学者上书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争取权利的活动中都包含了要求政府(包括人大、行政部门与法院)做出回应的期待和诉求,实际上正是政府的亲民姿态和良性回应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公民权利诉求的温和发展。中国古语讲“民为贵、君为轻”,讲的是民与君的博弈促使君意识到民的重要性。用我们今天的学术术语讲说的就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的确,要促进权利的发展与实现需要政府与公民的默契与积极互动。
我的导师贺卫方先生鼓励我研究税与宪政的问题,与浙江大学法学院的宋华琳君的网上聊天使我对森斯坦发生了兴趣,于是就有了翻译此书的念头。需要感谢北大出版社的副总编杨立范先生、政法事业部的金娟萍主任,他们的热心、包容与支持不仅使得本书成型,而且还有了我们整套的译丛,对外事务部的田秀玲老师、谢娜小姐为本书版权事务付出了辛苦烦琐的劳动。在此格外向他们表达我的敬意。
2003-12-15 于万柳
《权利的成本》读后感(五):王绍光:权利的代价——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
(本文是王绍光写于2000年的一篇书评,原标题是“自由派?自由左派还是自由右派?”)
这是两位知名学者合著的一本小书。[1]一位作者叫Stephen Holmes,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他一直研究自由主义,并以为自由主义辩护为己任。[2]另一位作者叫Cass Sunstein,在芝加哥大学同时担任政治学与法学教授。Sunstein的专长是宪法学和法理学,年龄不大,但著述颇丰。[3]这也是一本极具争议性的书。美国右派认为此书太“左”。如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研究员Tom Palmer指责两位作者“对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充满了仇恨。”[4]另一位自由放任主义者甚至指控作者“希望建立警察国家”,并将此书称为“20世纪里对暴政最无耻的辩护之一。”[5]美国左派虽然认为此书有可取之处,但觉得它分量不够,甚至还有点保守主义的痕迹。[6]只有中间派似乎比较满意。在他们看来,作者是不偏不倚,左右开弓,态度冷静,立论持中。[7]对一本书,居然出现截然不同的评论,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作者到底说了什么话竟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呢?
其实,作者的基本观点用一句话就能概括:不管保护什么权利都必须依赖由公共财政支撑的警察、检察、法院、监狱等政府机制,因此,权利是有代价的。[8]这就是书名及其副标题的由来:《权利的代价: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收》。也许有人会问,这么简单个观察也值得写一本书吗?的确,权利有成本是个显而易见、毋庸质疑的事实,没有人会否认。以前人们之所以对这个事实熟视无睹,恐怕与讨论生存条件时往往忽略空气的重要性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但从这个毫无争议性的观察可以推演出几条极具争议性论断,这却是多数人始料不及的。
推论一:所有的权利都是积极权利。
将权利分为“消极权利”(negative rights)与“积极权利”(positive rights)已有了几百年的历史。霍布斯大概是第一位讨论消极自由和公民社会问题的思想家。[9]在他看来,“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的对立物,是公民行使消极自由,不受政府控制的领域。不过,众所周知,在霍布斯那里,消极自由和公民社会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无政府状态的代名词。洛克则相反,[10]他把消极自由看成人的自然权利。这些权利不是政府赋予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政府的职责是保护这些权利,而不能侵犯它们。法国作家贡斯当是第一位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放到一起讨论的思想家,[11]只是他的叫法不同,将它们分别称作“现代的自由”和“古代的自由”。真正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作出明确划分的是现代哲学家柏林。[12]根据他的定义,消极自由是指免受政治权力干扰的权利;而积极自由是指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
近年来,西方自由放任主义者对积极自由或积极权利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他们看来,积极权利有三大罪状。一是极其昂贵。无论是充分就业、医疗保险、最低收入保障、失业救济,还是残疾人士福利、儿童福利、妇女福利、老人福利都需要政府负担庞大的公共开支。二是侵犯私有产权。政府的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征税从一部分国民那儿搜刮来的。在自由放任主义者眼中,“税收即盗窃”(taxation is stealing)。靠转移支付来保证积极权利的实现无异于劫富济贫,当然是一种犯罪。三是扩大了政府的规模与权限。自由放任主义者的天敌是政府,他们的理想是“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如果政府必须存在的话,其规模与权限越小越好,至多只应扮演个守夜人的角色。而伴随积极权利而来的必然是福利国家;伴随福利国家而来的必然是政府规模和权限的扩大。因此,要实现“让国家缩水”(shrinking the state)的目标,必须把积极权利批倒批臭。在中国,福利国家连雏形还没见到影,但这儿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也鹦鹉学舌,说什么积极权利“易于滑向专制暴政。”[13]
自由放任主义者希望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积极权利的实现要靠政府,是有成本的;消极权利的实现不需要靠政府,是没有成本的。Holmes和Sunstein的第一条推论却是,消极权利的实现也得靠政府,也是有成本的。在这个意义上,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无异。试以几项所谓消极权利为例。
言论自由:为了防止某些公民妨碍另一些公民的言论自由,必须要有警察;为了防止政府机关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必须要有法院。而警察与法院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没有公共财政的支撑就根本无法运作。
免受警察与狱卒虐待的权利:如果政府不设立监督警察和狱卒的机制,无法及时安排公费医生访问拘留所和监狱,没有在法庭上出示有效证据的能力,公民免受警察与狱卒虐待的权利就是一句空话。
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除非政府为穷人和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法律援助,并建立监督整个司法体系运作的机制,否则,这个权利便毫无意义。
财产权:被自由放任主义者奉为神明的财产权实际上是最昂贵的权利之一。直接或间接与保护私有产权相关的开支包括:国防开支;治安开支;消防开支;专利、版权、商标保护开支;自然灾害的保险和救济开支;保存产权及其产权交易记录的开支;合同强制实施开支;监督股票和其它有价证券公平交易的开支等等。在美国,把这些开支加到一起得出的是天文数字,一点也不比社会福利开支逊色。
自由放任主义者试图让我们相信,免受政府干预是实现消极权利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Holmes和Sunstein却告诉我们,没有政府干预,这些权利只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而政府为了保护这些权利必须承担巨额财政开支。捅破了这层关系,自由放任主义者在所谓消极权利上的保护色便剥落了,原来它们也是些积极权利。如此说来,区分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实际上毫无意义。
推论二,权利保护说到底是个政治问题。
权利既有绝对成本,又有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绝对成本是指保护某种权利必需花费的绝对金额。机会成本的意思是,用于保护这种权利的经费就不能用来保护其它权利了。世界上所有政府都面临着经费短缺问题;没有一个政府拥有无限财力,足以保护所有类别的公民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必须有所取舍,决定哪些权利最值得保护,哪些权利可以靠后一些。自由放任主义者认为政府应该优先保护所谓消极权利,诸如私有产权和言论自由之类。他们把这些权利称为“自然权利”,并断言“保护私有财产权是个人自由的基础。”[14]但是,如果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界限是条虚假的界限,他们的立场便失去了道义基础。事实上,在Holmes和Sunstein看来,没有一种权利是至高无上的。在现实中,一国公民享受哪些权利说到底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道义问题。政治问题的关键是,在资源和价值分配中,谁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多少?是如何得到的?很明显,对有产阶级而言,私有产权至关重要;对知识精英而言,信仰与言论自由至关重要。如果政府将资源优先用于保护这些权利,那么用于保护穷人福利权利(welfare rights)的资源就会相应减少。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的,对穷人而言,财产权和很多政治权利只是“形式上的权利”,他们根本无法享用。因此,Holmes和Sunstein认为保护穷人的福利权利十分重要。他们的出发点不是什么道义原则,而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稳定。在他们看来,如果只保护富人能够享受的权利而忽略穷人的福利权利,后者就没有理由不造资本主义的反。保护穷人的福利权利实质上是为他们容忍剥削,安分守己提供一种补偿,仅此而已。如果连这个妥协也不愿意做,资本主义社会就有可能天下大乱。[15]
推论三,权利不是“个人”的;所有权利都是公共财产(public goods)。
自由放任主义的出发点是作为个体的人,它主张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作为个体的人本身。[16]但“权利是有成本的”这个观察揭示了人的社会性和权利的公共性。世界上没有作为个体的人,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社会里,从属于某些不由他们选择的社群(种族、民族、阶级、国家等)。人们之所以需要权利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社会里,彼此间免不了磕磕碰碰。如果他们真是“作为个体的人”,要权利有什么用?只有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才需要权利。更重要的是,权利不是个人财产,权利的成本也不是由个人负担。自由放任主义者虽然信奉“个人主义”,但他们却千方百计地抵赖保护私有产权和其它“消极权利”的成本,试图将这些成本转嫁给社会上其他人。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要求公民单独为自己享受的每一项权利付费。恰恰相反,权利的成本是由全体公民分担的,权利的保护是由公共权威执行的。这就意味着,公共财政与国家行为是任何权利存在的必要前提。所谓“个人”权利不过是自由放任主义者自欺欺人的梦呓而已。
推论四,只有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保护公民的权利。
自由放任主义者有一个基本假设,国家能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是零和关系:如果国家能力太强,个人权利就会受到威胁;只有在弱政府下,个人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他们的逻辑结论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必须削弱国家能力。Holmes和Sunstein的结论恰恰相反: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公民就不可能享有任何权利。他们的这个结论是基于对俄国和东欧乱象的反思。
在转到普林斯顿大学以前,Holmes曾在芝加哥大学担任“东欧宪政研究中心”的主任和《东欧宪政评论》的主编。1997年,他在《美国前景》双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17]在这篇文章中,Holmes指出,在冷战期间,西方自由主义的共识是,苏联政府太强大,构成了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最大威胁。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只要实现分权,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就有了保障。现在,苏联帝国崩溃了,政治灌输停止了,新闻检查不见了,持不同政见者不再担心被送进监狱,没有人会因违反党的路线惹上麻烦。那么政府不管事后,俄罗斯是不是因此变成了自由的乐园了呢?答案是否定的。经过几年的观察和研究,Holmes在俄罗斯看到的是道德沦丧,物欲横流,政府腐败,黑帮猖獗,监狱里人满为患,铁路上盗贼蜂起,士兵在街上乞讨,野狗在邻里乱串,生产能力萎缩,人均寿命锐减。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多数俄罗斯人而言,不要说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失去了意义,连生命安全也没有基本保障。美国能从俄罗斯的乱象中吸取什么教训呢?Holmes的回答是,没有公共权威,就没有公民权利(statelessness spells rightlessness)。公民权利的前提是存在有效的公共权威。一个丧失治理能力的政府是对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可以是最大和最可靠的人权组织。增进公民权利的最佳战略不是削弱政府(destatization),而是改造政府。削弱政府往往不仅不能增进公民权利,反而可能危及他们已经享有的权利。
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财政汲取能力。俄罗斯的财政总收入仅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而在美国,这个比重约为30%左右;在多数欧洲国家,该比重更高达40%以上。看来,权利保护与公共财政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关系:需要保护的权利越多,公民就必须缴纳更多的税。俄罗斯的教训是深刻的:汲取能力低下,政府便无力负担规范运作的国防、行政、司法、执法、监察体系,因此也不可能有效地保护公民权利,包括他们的生存权。苏联崩溃以后,俄国的人均寿命大幅下跌。这意味者成百万的人提前结束了生命。[18]连生命都保不住,遑论什么公民权或财产权?正是基于对俄罗斯的观察,Holmes开始反思美国自身的经验。他在1997年那篇文章的结尾写到:
政治上乱了套的俄罗斯提示我们,自由主义理想的实现有赖于一个有效政府。有人说,只要政府少管闲事,独立的公民便可以享受个人自由。俄罗斯的乱象是对这种谬论的当头棒喝。为了保卫我们的自由,我们必须捍卫正当的公共权威。没有它,自由就没有保障。[19]
虽然Holmes和Sunstein在《权利的代价》一书中没有提及俄罗斯,但俄罗斯的教训正是他们为美国读者写作此书的出发点。
如果美国有必要从俄罗斯的惨痛经验中吸取教训的话,中国恐怕更有必要这样做。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方向,所谓“自由派”的思路是,以个人自由的名义限制公共权威。他们认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20]但却忘了,公民权利和自由最终还得通过公共权威才能实现。中国的“自由派”自称“自由主义者”其实并不准确。他们对美国自由主义学者写的这本书一定会打心底里感到厌恶。他们的“自由主义”显然与Holmes和Sunstein的“自由主义”不是一码事。在国际意识形态的光谱里,中国的“自由派”实际上属于右派。叫他们“自由右派”更为贴切。如果他们实在不喜欢“右派”这个标签,可以将自己称为“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这样才名副其实。站在自由右派对面的是自由左派(他们往往被“自由派”贴上“新左派”的标签)。自由左派追求自由,但追求的不是只有经济精英、社会精英和知识精英才能享受的自由,而是公平的自由(equal freedom),是所有公民都能享受的实实在在的自由。自由左派承认,国家(the state)可能也经常侵犯公民自由,但出路不是消解国家而是用民主的方式改造国家。公共权威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的重要性,只有在它缺失的时候才会充分显现出来。俄罗斯悲剧对中国的教训是,企图用削弱国家能力的方式来达到改变政权形式的目的是极端危险的。其实,除了俄罗斯以外,近年来在非洲、南亚以及拉丁美洲发生的事也一再证明:缺乏公共权威,民主转型就不能持久,社会动荡就会接踵而来,公民权利就难以保障,无政府状态就可能出现。[21]正是基于这些观察,自由左派认为,中国政治转型的方向只能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22]如果Holmes和Sunstein生活在中国的话,想必他们会与所谓“新左派”站在同一条战壕里。
注释与参考文献
[1]Stephen Holmes and Cass R。Sunstein 1999,The Cost of Rights:Why Liberty Depends on Taxation,New York:Norton,本文是作者为此书写的书评,写于2000年8月31日。
[2]其三本代表作是:Benjamin Consta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Liberalism(1984);Anatomy of Antiliberalism(1993);Passions and Constraint:The Theory of Liberal Democracy (1995)。
[3]其代表作有One Case at a Time:Judicial Minimalism on the Supreme Court(1999);The First Amendment(1998);Free Markets and Social Justice(1997);The Partial Constitution (1993);Democracy and the Problem of Free Speech (1993);After the Rights Revolution:Reconceiving the Regulatory State (1990)。
[4]Tom G。Palmer 1999:“Review on The Cost of Rights”,Cato Journal,Vol。19,No。2(Fall 1999),pp。331 ̄336。
[5]Kelley L。Ross:“Positive &Negative Liberties in Three Dimensions”,http://www。friesian。com/quiz。htm。
[6]Daniel Farber 1999:“Review on The Cost of Rights”,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April 18,1999;Jonathan Bing et al。1999:“Review on The Cost of Rights”,Publishers Weekly,Vol。246,No。2,January 11,1999,pp。58 ̄59。
[7]David Greenberg 1999:“David Greenberg on Rights and Freedom”,Civreview,Vol。3,No。2(March-April 1999);Economist 1999:“The Economist Review:Liberty's Price”,Economist,Vol。350,No。8110,March 13,1999。
[8]首先要明确的是,这里所说的权利是法定权利(legal rights),而不是伦理意义上的权利(moral rights)。有人喜欢讲“天赋人权”,但在这两位作者看来,没有纳入法律体系的权利是没有牙齿的权利;无法强制实施的权利只能制约良心,不能制约行为(见第17页)。
[9]Thomas Hobbes,1588 ̄1679。
[10]John Locke,1632 ̄1704。
[11]Henri Benjamin Constant de Rebecque,1767 ̄1830。
[12]Isaiah Berlin,1909 ̄1997。
[13]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第274页。
[14]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见李世涛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17页。
[15]1985年,Adam Przeworski在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一书中已经指出,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阶级妥协:资本主义民主允许工人阶级争取和扩大福利权利;而工人阶级放弃推翻资本主义,转而争取改革资本主义。但在过去十几年里,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式微,自由放任主义者及其政治代表人物,似乎打算单方面废弃这个妥协。他们鼓吹摧毁福利国家,取消基本社会保障。这一切引起了自由左派的忧虑。Holmes和Sunstein表达的便是自由左派的看法。
[16]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280页。
[17]Stephen Holmes 1997:“What Russia Teaches Us Now:How Weak States Threaten Freedom”,American Prospect,No。33,July-August,1997,pp。30 ̄39。
[18]Neil G。Bennett,David E。Bloom and Serguey F。Ivanov,“Demographic Implications of the Russian Mortality Crisis”,World Development,Vol。26,No。11,1998,pp。1921 ̄1937。s。
[19]Holmes:“What Russia Teaches Us Now”,p。39。
[20]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见李世涛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第417页。
[21]Robert D。Kaplan 2000:The Coming Anarchy:Shattering the Dream of the Post-Cold War。New York:Random House。
[22]王绍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区别”,《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