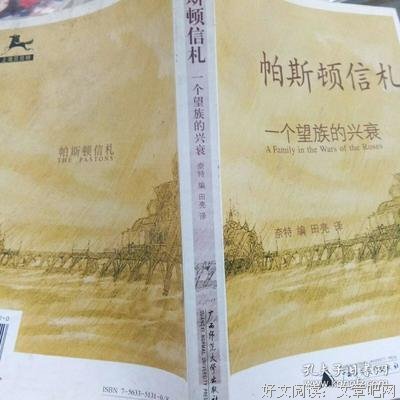
《帕斯顿信札:一个望族的兴衰》是一本由奈特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页数:24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帕斯顿信札:一个望族的兴衰》精选点评:
●“要是帕斯顿家族成员知道,是他们的那些书信而不是他们的政治野心、社会地位和成就使他们名垂千古,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对英国蔷薇战争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是极其鲜活的史料。
●家族史,英国式,信札的形式,话说最近迷上读信了。
●不枯燥,挺好看的呀
●玫瑰战争
●A family in the Wars of the Roses
●实际上每个家族的经历都可以如同赫赫有名的美第奇家族或是斯福尔扎那样波澜壮阔。即便是寂寂无名的帕斯顿。
●作为一本英国红白玫瑰战争前后的史料文集,有许多的可读之处。但是在翻译过程中,因为外国人的姓氏文化,在长时段书信间隔以后,容易造成对于主人公的误判。总体来说,以此来看英国红白玫瑰战争以及贵族之间的纷争还是十分有趣的。
●“要是帕斯顿家族成员知道,是他们的那些书信而不是他的们的政治野心、社会地位和成就使他们名垂千古,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通过一个家族真实书信串联起的一部兴衰史,既关于这个家族,而他们与外部社会,尤其是当时的政治形势之间的互动,又令这份记录得以从侧面呈现了15世纪英国的真实状态。尽管时代不同,但这部作品其实是可以同题材的《金翼》对照来看,家族发展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分工,同样需要“运气”,但不同的地方在于,比起中国地方稳定的关系网络,帕斯顿一家所面临的外部挑战更加复杂,而他们的“战斗空间”也更大——“金翼”的持家之道是勤俭与团结,而“帕斯顿”则是不停的官司,甚至是武力争斗。两种文化的差异,在这里同样可以以小见大。
●读起来挺拗口的,但是还是很好玩,当时的旺族咋写信这么多篇幅都在讲给我买点布这种事。。
●20120619从书架上随手抽出来的一本。21日读完。端午节放假的当天晚上。此刻外面狂发大作,雷声隆隆。
《帕斯顿信札:一个望族的兴衰》读后感(一):倒是出版过程有趣
此书几乎完全不具备可读性,即使读了也体会不到什么阅读的快感,当然这是对于研究者以外的普通读者来说的。
倒是后记中提及的一波三折的手稿寻觅丢失重现过程很是有趣,如果再详尽些,还真是一篇挺传奇的收藏轶事或者书话呢。
《帕斯顿信札:一个望族的兴衰》读后感(二):显微镜下的历史断面
《帕斯顿信札》,玫瑰战争中的一个家族的历史。阅读体验对我来说是寓教于乐。
如果不是书中搜录大量的信件被保存下来并出版,帕斯顿家族可能只是一个曾经在第十五世纪的英国玫瑰战争期间生活在诺维奇附近的富裕家族。正如全书最后一章提到的。要是帕斯顿家族成员们知道,是他们的那些书信而不是他们的政治野心。社会地位和成就使他们名垂千古,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他们大量的通信作为宝贵的史料被许多书籍(例如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所引述,对其家庭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当然,是结合时代背景的。
总体来说,我们当代人在读完这本书之后,会不仅仅明白这个家族当年是如何生存、发展、壮大的,而且会被动对那个主要由泥泞、蛮族和教堂构成的年代有一个惊人的重新认识。
尽管帕斯顿家族并非现代人,但他们却能熟练掌握和运用大量复杂的现代知识。他们既能合法的援引法律流程(以控制他们大量的而又支离破碎的领地上的佃农),有时也不那么合法(择地行诉以确保他们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打财产官司)。同时他们掌握的关系网络几乎和他们手头的法律文件一样重要,因为英国在我们称之为玫瑰战争的那个历史阶段,因为大规模的内乱而充斥着无序和混乱。所以也很容易理解,为何在他们家族财富的上升通道里面,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忙乱乃至狂躁的行为。
时光仍苒,社会和政治都是风云变幻。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有趣的发现,在如此一个变幻莫测的大时代中,帕斯顿夫人写给她出门在外的丈夫的大量信件中,除了那些和政权更替政局动荡的信息,一个持续的关注居然是催他买回高档的织物,这样她可以做一两件新的礼服!作为事实,这似乎过于琐碎。但正是这种琐碎和“大事件”的混合,反而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了一个更为完整和真实的看法,而不是更为常见的对“大人物”比如王室的关注,这带来了更多的阅读乐趣。
:家族成员在信件中常常极为直接甚至赤裸的在金钱的话题上产生冲突,不禁让人感叹至亲即为至疏,这种矛盾与背离在大时代和大家族中会被放大的更为突出
《帕斯顿信札:一个望族的兴衰》读后感(三):应lx六年前的要求,写个出版过程
课程作业需要,写点吐槽,如果有选同一门课的看看就好……(别告诉老师啊= =)
1774年,John Fenn收藏到了大多数帕斯顿书信。一开始他的兴趣在收集手稿亲笔签名上,1780年还登广告试图把这些书信卖掉。后来他认识了俩历史学家给他们看了书信手稿,其中有个叫Horace的大力赞扬说看了这个别的书信都不用看了!于是他决定不卖了,自己把它整理出来(不差钱的古董商)。
1782年他开始誊抄书信,1787年出版了两卷155封。此书一出天下皆惊,用后来一书评的说法是人手一本。当年1月29号他就受到乔治三世的接见献书。差不多同时,Fenn给古物协会寄了书,还表示可以把原件放他们图书馆展出以便感兴趣的学者检验查阅。2月1号手稿原件到达图书馆,在那里展出了两三个月。
2月21号,当时英国首相William Pitt的私人顾问George Pretyman给Fenn写信告诉他国王很喜欢他的书想要原件看看,还说国王要授予他爵士。5月中旬Fenn写信问国王的图书管理员手稿以后会放在哪里,管理员回复国王压根没提过这事。5月23号他接受爵位,同一天把第一卷和第二卷的手稿给了首相希望它们能进入皇家图书馆。
然而这些手稿从此就消失了。或许乔治三世早就忘了这回事儿,毕竟当时他因为威尔士亲王的债务和私自结婚忙得焦头烂额。
Fenn还是很坚强地继续誊抄下去,1789年出版了两卷220封信,1794年去世时第五卷已经几近完成,最后由他侄子William Frere在1823年出版。1823年出版的时候,Frere宣布后面三卷的手稿原件通通都找不到了。慢慢地就有人怀疑帕斯顿书信的真实性——不是凭空来的。John Fenn可是因为擅长模仿笔迹声名在外。
1865年9月终于有个名叫Herman Merivale人站出来公开质疑了,理由时“too good to be true”(这理由真是放之中外皆准)。结果11月,William Frere的儿子Philip跑出来说第五卷的原件一直在他家一个铁盒子里放着他过去没找到而已(谁知道是想私藏还是真没找到)。古物协会设了个鉴定委员会来鉴定真伪,花了一年时间,终于在1867年1月发了个声明:是真的!于是大家也不吵了,专心等待剩下四卷出现。大英博物馆出面把这次找到的这些信和其他文书都买下了。
过了十年(这本书的四年是错的,英文版就错了,原作者太不仔细),1875年Frere家在Roydon的老宅里发现了第三卷和第四卷的手稿,据Frere家的人说他们自己也毫无头绪,因为William Frere不是长子不住老宅自己在Cambridgeshire住着。以前市面上曾经有两封属于第三卷的信单独出现,普遍认为这220封在Fenn去世以后就散失掉了,没想到剩下的全在一起而且还新发现了95封没出版过的,简直是皆大欢喜戏码。1896年大英博物馆把这些也买了。
又等了十几年,1889年,第一卷和第二卷的手稿在Pretyman孙子家发现了,该怎么扎好的还是那么放着。过去传闻手稿最后出现在Queen Charlotte手里出现果然不靠谱,分明Pretyman就没把它往上交。这一批在1933年进入大英博物馆。
《帕斯顿信札》的跋语在这里就结束了,不过昨天查书时发现一个特别可爱的事情也顺带提提。1865年帕斯顿信札饱受质疑时有个晚期中世纪历史学家James Gairdner坚定相信它的存在,11月发现第五卷手稿以后还跑去和Philip Frere一起把整幢房子搜了个遍想找第三卷和第四卷的手稿(当然没找到)。Fenn出版的四百多封信都是从自己收藏里挑的,Gairdner那时候已经在牛津和剑桥的各个图书馆发现超过四百份Fenn没经手的书信和其他文书,于是趁着新发现的机会出了一个更全的新版。1873年、74年出前两本时他靠着对比Fenn的第五卷和原件说,这侄子出的都没啥大错,前四卷肯定错误更少啦!他觉得Fenn的可信度超高于是凡是Fenn誊抄出来的都用了Fenn的版本,现在学者还批评他太过信任Fenn。结果1875年第三本都编到附录了Roydon来了个大发现,他急匆匆对了一遍——
感觉被骗了。
被骗了。
骗了。
了。
第三本的preface他还是先夸了两句什么新发现的这些再次证明了Fenn的可靠啊blahblah,第三页开始画风急转大批Fenn不懂语言学不懂帕斯顿家族谱系语言有错名字有错时间也有错,更糟的是他放个删节版上去还不注明!Gairdner还给找了个台阶,说那是因为Fenn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帕斯顿书信的风貌所以删节不删节无所谓啦又不是搞历史的……
1900年有篇书评还骂他不该公开指责Fenn,因为人家“毕竟是凭着热情在编书嘛”。
我觉得Gairdner也是蛮可怜的。
这个中文本《帕斯顿信札》翻译自Richard Barber的《The Pastons》,想了半天不知道这个“奈特”是何许人也。出版社也没注明是译自何书,这翻译和编辑心都够大的。
《帕斯顿信札:一个望族的兴衰》读后感(四):从家族史看政治与社会
《帕斯顿信札》是一部以书信的形式连缀起来的家族史,讲述五百多年前英格兰一大士绅望族的发迹、兴盛与衰败。由于书信多集中在该家族第三代的约翰与第四代的两位约翰持家的时期,那些早年的艰辛积累与末代的盛极而衰就都一笔带过了。
从约翰第一成为家长到约翰第三封爵,也就是从1444到1487的四十余年,既是帕斯顿家族向上攀登的关键时期,同时也覆盖了英国历史上被称为红白玫瑰战争的三十年(1455至1485年) ,该家族的成长故事因此就与王朝政治变迁有了千丝万缕的关联。
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秩序败坏的年代,绅士只有依靠贵族的庇护才能维持并可望壮大其产业。一旦某位贵族在朝得势,他或他旗下的绅士们就会忙着以一些不那么充分的理由去要求他人的地产。长年战争培养了大量好逸恶劳的闲汉无赖,他们常被某些贵族或贵族照拂下的绅士所雇,公然进行夺人产业的活动。当时,帕斯顿家通信的主要内容都围绕着几桩涉及地产的纠纷,家长经常要到城里去跑关系、疏通斡旋,家族的其他成员则要组织人手、枕戈待旦以防觊觎者抢夺庄园。尽管防范严密,仍有一次寡不敌众庄园被占领,以女主人为首的家人及仆从都被赶了出来。事后,虽经打通上层关系讨回了庄园,但原本殷实的宅第却已被洗劫一空。总之,从这些书信描绘的景象来看,整个国家缺乏秩序,暴力充斥,法律软弱到只能听任有权势的贵族摆弄。
好在帕斯顿家族的运气一直不错。起初,萨福克公爵(王后之密友,享利六世的宠臣)荫庇的一个绅士想要谋取帕斯顿家的某处庄园,并已施加了相当的压力。但萨福克公爵很快失势,并在放逐离英时被一群水手杀死,这样一来,那所庄园就安全了。后来,由于帕斯顿家托庇的贵族基本上算是坚定的约克派,因此尽管地产纠纷不断甚至一度非常窘迫,但家族的产业总还得以保全。当享利·都铎来向理查三世讨要王位时,帕期顿家长重新站到了红玫瑰一边,一举奠定了其家族在随后的都铎王朝统治下步步高升的基础;而他们产业的侵夺者——当时的诺福克公爵则因支持理查三世而在博斯沃斯战死。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上层政治动荡与战争仅仅是帕斯顿家族奋斗的一个较远的背景,帕斯顿家长作为地方绅士而非贵族,并没有直接参与最高权力的争夺——这当然也是当绅士比当贵族更安全的原因,因为即使他们依附的贵族选错了主子,他们一般也会得到赦免。比如,帕斯顿家效忠的海司丁斯勋爵被其政敌葛罗斯特公爵除掉,后者登上王位后就赦免了帕斯顿家长。
绅士们作为中小地主,关注的只是眼前这些产业能否保全、财富能否增长,至于谁当国王他们并不多加关心。正因为着眼于财产,和平稳定和秩序井然才是绅士们最为期待的生存环境。在他们看来,对财产安全更为根本、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秩序而非贵族。即使在封建时代依附贵族不可避免,绅士们也不愿看到贵族之间争斗不休,国家陷于战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为护持财产付出比和平时期多得多的成本,且还朝不保夕。书中的一个事例可以印证上述观点:我们已在上文介绍过,萨福克公爵是帕斯顿家族敌人的支持者,但帕斯顿家对这位贵族死于非命的第一反应,竟是强烈的同情。对此,书中的解释很恰切:“在一个秩序高于一切的社会里,贵族大臣沦为刀下之鬼的惨境,既令人恐惧,又令人不安”。
都铎王朝时期,帕斯顿家族稳步上升,在乡绅与朝臣两个方向上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像帕斯顿家族这样从土地上腾达起来的绅士阶层, 虽然在贵族式的高贵德性、远大目光和宏伟抱负等方面有着先天不足,但却与英国的稳定繁荣紧密相关。这也许就是我们从这部家族史中能够窥见到的政治的“一斑”。
除了财产纷争及其背后的政治背景,我们还可以从本书选编的信件中,获取有关当时绅士阶层的日常生活、经济活动、亲属关系、情感婚姻等多方面的信息,对作为那个时代基本社会制度的父权家长制、长子继承制和婚姻的财产属性有较为直观的了解。
很显然,《帕斯顿信札》的编者和译者对该书的定位更偏向于文学作品而不是史料汇编。但因翻译质量不高,以致信中文字美感不足,降低了阅读快感。因此,我个人认为该书的阅读意义不在于文学欣赏(若以此为目的,该书简直不忍卒读),而在于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信息。然而,就后者而言,该书又缺乏必要的辅助史料和背景介绍,另有一些明显的史实错误和误译,难免使这一作用也打了折扣。
在本书的后记中,译者说:“不是帕斯顿家族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而是他们的亲情、友情、爱情令我们感动。” 也许这番表述只是为了引出译者对家人后勤工作的感激,那自是另当别论。但若要把这句话从实理解,读罢全书的人恐怕都不会赞同。不论对那些书信中的字句如何细细咀嚼,也难以体味出“令人感动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来,我们更容易看到的是:婚姻是赤裸裸的交易,双方家长在嫁妆和未来收入上讨价还价,谈妥了新人才能进教堂;财产争端导致父母子女长期冷漠甚至冲突,家长动不动就以减少遗产要挟子女;还有上流人物之间流行的尔虞我诈和背信弃义;“愿上帝保佑你”作为书信中的例常句式,带来不了多少温馨的感觉。即便抛开翻译的因素,我们也不能指望在细节资料极度缺乏——实际上也不可能获得——的情况下,仅凭信件就能复原那遥远年代的亲情、友情和爱情。这样的任务或许只能由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来承担,英国不乏这方面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