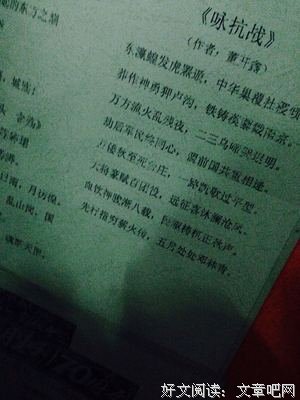
《卡拉马佐夫兄弟-外国文学名著精品》是一本由(俄)陀思妥耶夫斯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页数:95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卡拉马佐夫兄弟-外国文学名著精品》精选点评:
●排版不够舒服
●想说的太多,就不说了。
●读过的对人性最深入追问的作品
●心乱。
●好看的不行
●2018.08.27 ~ 2018.10.05 《宗教大法官》那一章真是绝了。
●这个版本一定要弄到手
●基督徒必读
●我愿意有人折磨我。
●翻译的也很好。记得读完之后将近一个月无法听流行音乐。
《卡拉马佐夫兄弟-外国文学名著精品》读后感(一):我读的就是这个版本……
我读的就是这个版本,基本上一口气就读完了。这么厚的书,这是我少有的阅读体验。真没有想到浮躁的自己能读的下这么厚的一本经典名著。有机会读一下上海译文出版社荣如德翻译的,不知道翻译的差别大不?
《卡拉马佐夫兄弟-外国文学名著精品》读后感(二):群像的极致
伊凡,魔鬼式的人物,类似罪与罚拉斯卡尔尼科夫那种人物,恐怕是书中展现的比较让人印象深的一个价值观了,此外德米特里,阿廖沙,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斯梅尔佳科夫,还有女主叫什么来着,这么多人物简直像是群像的极致描绘,还有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父子五人就像是一个复杂的人具象的五种价值观,其中种种太精彩了,需要在以后拿起来多阅读几遍,其中隐含的某些宝还需挖掘
《卡拉马佐夫兄弟-外国文学名著精品》读后感(三):卡拉马佐夫式的病态
陀神是没写完,后面米佳是否顺利逃脱,伊凡和卡佳结局如何,阿廖沙和丽莎之间又会怎样,科利亚长大以后是个什么样的人。最令我感到恐怖的是——斯梅尔佳科夫用心歹毒,天性中邪恶又狡猾的特质导演最后的自杀使得这一出惨剧达到再无逆转的境地。可怜的米佳。他无罪吗?不,他有罪,他性格中的暴戾凶狠让他确实有过弑父的想法,他拿了卡佳的三千卢布,他跟自己父亲争一个女人(也可以反过来说),这一切是多么疯狂!但童年关于核桃的故事,确实能说明他善良而富有感情的一面。凝视深渊,他明明幸运地抽身而出,却又由于仿佛注定的命运摔下悬崖。邪恶的魔鬼站在每个人身边,偶然才能被窥探。伊凡聪明、善思考、欲探求根本,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可谁知道呢。并不是说愚蠢而麻木就不会落入魔鬼的陷阱,只是更不易在折磨自己以致痛苦不堪意志薄弱时跌落。我不明白卡佳对于米佳和伊凡的感情,就像我不明白我对他的感情。仿佛书中所有人都陷入一种奇怪的病态,所有人的善或恶,最终都造成了悲剧。格鲁申卡等了五年,却发现她的等待是多么可笑,而自己对卡拉马佐夫父子的捉弄,加上世上一切巧合同计谋,有了这桩惊动全国的杀人案。由于真凶上吊,无数罪证指向清白者,荒诞却无从辩驳,于是无力感、悲凉感、绝望感抓住了我。像我曾经在生活中折磨自己时,读卡拉马佐夫兄弟让我也想问,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最后关于阿廖沙,我最喜欢这样的人了。他的存在就是为了使世人喜欢并信赖,在困境中有所寄托。一颗善良真诚聪慧敏锐而美好的心!可只要是人,就无法独自遁走,离不了血缘的诅咒,即使他是他们三兄弟中相较而言最幸福的一个。卡拉马佐夫式的病态,不止是他们,也是人共有的病态。这是以我的眼睛看到的,所以大概我看到的也只能是我自身有的这种病态,但我能感觉到这确实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只是论程度深浅。 悲剧震慑人心的力量。我就是想要这种力量。
《卡拉马佐夫兄弟-外国文学名著精品》读后感(四):为什么要读陀思妥耶夫斯基?
文/张凡
读陀思妥耶夫基的三次死亡 一死。多年前我有位女友,每当我在夸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她都要拿出纳博科夫:看,你崇拜的偶像也不过如此……不见得好哦。她始终不屑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则用尖刻的话反击:纳博科夫算是个什么东西!《俄罗斯文学讲稿》就了不起吗?你更应该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那是认真而天真的年代。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伤、毫无节制的大合唱、无差别表白和逢人就说“我爱你”和“我爱你爱得发疯”,让我以为俄罗斯人一直活在“双手一拍”的惊呼中,但托尔斯泰显然并不如此。我一直又以为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种“巨人”的写作方式,是由于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晨雾弥漫,本该如此。但我忘却了还有屠格涅夫和浦宁似的秀美……经历过几次阅读趣味的世事变迁,甚至乾坤大挪移。在反反复复的阅读中,比如今年冬天,我还是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伟大。当然,我也不再说:纳博科夫算是个什么东西。《白夜》《穷人》《白痴》《赌徒》,一个个形象都会疯狂炙热地旋转,我仍然不能百分百地确定,这种感伤主义是不是就如纳博科夫所说的完全要不得,需要加以攻击:我分明能感到,即使处女作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比成熟时期的茨威格的感伤,更深沉。人生志趣终究难以强求一致啊,为梦境而争执的年代已逝去而微茫。
二死。多年前,我在复旦读书时,王安忆老师问我们:盍各言尔志?你们都谈谈自己喜欢的作家吧。轮到我,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的伟大作家,他的写作,如一砖一瓦,精细地将大厦最终建立起来。王安忆说话一向很直接,她直视着我说:你说得似乎不对,托尔斯泰才是这样——托尔斯泰才是一砖一瓦,把世界彻底建立起来。毕业五年后的有一年,我心有所感,把王安忆的长篇和中篇、托尔斯泰的作品集全部看完,了解了她的写实主义哲学和与托尔斯泰争辉的雄心之后,发出由衷的感叹:王安忆说得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尼采式的、酒神式的、伤感的、癫痫病式的,他不是一砖一瓦。那时,我忽然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和《白夜》里的两个女主人公。她们都哭得杜鹃啼血似的至死不渝,一双蓝蓝的眼睛忽闪忽闪,比茨威格里的女主人公都更加纯洁生动,但最后毫不犹豫抛弃了热郁无比的男主,抛弃了老男人和弱鸡男。我苦涩地想,她们也真是相当“绿茶”啊——这应该也反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种趣味,正因为被这种姑娘抛弃,他获得了心理的纠正和补偿。纳博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屑就建立在这种对感伤主义无节制的利用上。在我少年时,我看到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心里感动得不得了。既长,看过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集,心里想,茨威格的这篇小说,情绪上,难道不是抄袭《白夜》加《穷人》的吗?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在这两篇小说的文末,把基调定在歇斯底里的绝望的呼号……看着爱情远去。正是这种直抒胸臆的绝望,触动人心,仿佛看到虚有的情绪扭曲在地上成为废品。可我又矛盾地觉得,陀氏到中年以后再也不这样单向度的纯度抒情了,真是可惜。他和一砖一瓦的精确,的确毫无关系。他是长江大河、吞风莽雨式的——但是,他和精确的写实没有关系。这是第二次死亡。
三死。我又看到在全世界范围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杀手——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写道——我们应该区分感伤和敏感:一个感伤主义者在空闲时可能是一个绝对残暴之人;而一个敏感者永远不会是一个残忍之人。感伤的卢梭会为一个进步思想而哭泣,但也会让他的众多私生子生活在济贫院和感化所并对之完全不闻不问。一个感伤的老处女有可能会娇惯她的鹦鹉而同时毒死自己的侄女。一个感伤的政客不会记错母亲节却能无情地致对手于死地。纳博科夫要读者知道,当我们谈论感伤主义者,所针对的是熟悉的情感的夸张,为的是在读者心中激起传统意义上的自怜。这是我的三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三次死亡。累觉不爱。 然而,我心中有个声音呼唤:张凡·亚历山德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真是这样吗?你会被这样的妖言迷惑吗?他们都有一定道理,却也是伊凡心中的魔鬼。今年冬天,再次读完《卡拉马佐夫兄弟》拯救了我,我从《三死》一举到《复活》。我感受到了从感伤主义到宏伟的精确和节制的最后的救赎,为此潸然泪下。我在这部小说一环套一环的人物分布和篇幅中,看到了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托尔斯泰的中庸和节制。我甚至觉得没有什么是多余的,他的常常跳开,总是有目的地得到呼应。《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前期很多长篇的增强和删减,最后的和盘托出。例如《白痴》中的罗戈任和《罪与罚》里的主人公,分别提升或净化到了大儿子和二儿子身上,而不坚决的梅什金则提升为少年时代的三儿子阿廖沙和神父佐西马,特别是佐西马,几乎就是陀本人最后的人生观和教义代言人。这种似曾相识、接近重写,作者并不避讳,进行了全面的提升和节俭。因此,虽然卡拉马佐夫兄弟80多万字,确是作者写得最节俭和节制的一部。人们常常会停留在《叛逆》《宗教大法官》这一卷,赞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磅礴、深湛和伟大,但后面的《俄罗斯神父》一卷、以及德米特里的《预审》《审判》、伊凡和魔鬼的对话,同样具有惊心动魄的伟力。它甚至是一部极致的侦探小说、精的心理医学的判定书和一起咄咄逼人的法律案卷,每一个细节都是精确缜密到专业的。《复活》里的审判冷静而灰心,同样伟大,然而没有这种莎士比亚式的诗性和神魔般的狂热。我对这部小说只有一个可惜的地方,觉得格鲁申卡的人物性格比不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不过,卡捷琳娜在最后与德米特里的相视,让我看到了这部小说浓重而炙热的一笔,那一点也不比《白痴》里的逊色。
两种写作路径
我们应该熟读所有的托尔斯泰,我们应该熟读所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它们就是交叉的正负两极,虚与实,正与负。我认为,一切作家的写作技术和写作哲学,都将在读托尔斯泰和读陀斯妥耶夫斯基之中得到检验和照耀。托尔斯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在《战争与和平》里就提到了《死屋手记》,念念不忘《死屋手记》,写信赞美说:“我认为在包括普希金在内的整个新文学中,再也没有比这本书更好的书了。”托尔斯泰宣称自己正在写作一部真正的不同于欧洲的俄国小说,而他首先想起的例子就是《死魂灵》和《死屋手记》。我想,潜意识里,他在盛年时,就在为临终的《复活》的同类式写作做精心的储备和思索。似乎,我在《复活》里看到了托尔斯泰的再次致敬,聂赫留朵夫和喀秋莎一起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而在另一方面,托尔斯泰又似乎并不欣赏真正的或者是主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群魔》的作者。托尔斯泰给别人的书信中,又有很多坏话,这些坏话和指责也是大师级、直接命中目标的,例如写给友人的信:您成了对待陀虚伪、矫饰的态度的牺牲品,不只您一人,还有大伙儿都过分抬高了他的意义,按照死板公式硬要把他这个善与恶的内心斗争处于狂热状态的人吹捧成先知和圣人。这两种看法也可以看到作家的路线和信仰之争。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写到魔鬼和伊凡的对话时,捧过一句托尔斯泰:我可以向你赌咒,连列夫•托尔斯泰都编不出来。在陀的《作家日记》里,多次指责《安娜•卡列尼娜》写作过程中的失误。
主题
《卡拉马佐夫兄弟》最重要的主题就是人和上帝的关系,以及人间生活的解决方案,简言之,基督性和人民性。这两个主题也是托尔斯泰在探讨的。托尔斯泰最终变成了虚无主义,或者另成立自己的宗教,托尔斯泰是一个真正的狂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对虚无主义和理性,最终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现代社会的总体发展就是在质问上帝和信仰,一切可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终于把自己的三观猛烈地呈现出来。似乎,在写作《白痴》以前,也就是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他还没有这样绝对。我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0年就短命死去,会是如何。普希金是否就死得太早,限制了这轮俄罗斯的太阳。最后的致意《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最后一页,是被各鸡汤文引用得最多的一句话:我们首先应该善良,这是第一位的,其次应该诚实,最后应该永远相互记住。但很少有人看阿廖沙为什么说这句话。那句冰冷和痛心就在这句温暖的上面: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担心我们将可能变成坏人,为什么连我们也要变成坏人呢,各位?  生活将永异于从前在生命中的某一阶段,即使你已经僵硬,行将进入坟墓,读到《卡拉马佐夫兄弟》,读之前和读之后仍会变成是两个不同的人。我想引用帕慕克这段话来阐明这种意义,他比我说得更好:我觉得,自己仿佛是第一个读这本书的人。仿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轻声诉说着生活和人性的神秘信息,诉说着无人知道的事情,并且只对我一人倾诉——这样一来当我和父母坐下来吃晚饭时,或者当我在学习建筑的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拥挤的走道里,努力和朋友们像往常一样谈论政治时,我都会感到这本书在我体内震颤着。我明白了,从此以后,生活将永异于从前:与书中令人震惊的世界相比,我自己的生活和烦恼太过渺小,太不重要,只能退居次席。我想说,我读的这本书让我深受震撼,它会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这恰如博尔赫斯在某些地方说过的:“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第一次发现爱情或大海——它标志着人生旅程的一个重要时刻。”我一直觉得,我第一次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就标志着我从此丧失了纯真。续集和几个人物的未完成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前言里,我们知道这部书还有后传,《卡拉马佐夫兄弟》只完成了阿廖沙的少年时代,13年后的当代,却没有来得及写。上帝不允许《卡拉马佐夫兄弟》出现第二部。天妒大师呀。由于这种庞大的写作结构,影响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几个人物性格:一是阿廖沙的旁观视角,他本来是要写成梅什金那样的绝对主角的,但光彩被伊凡和米佳夺走了。不过,阿廖沙身上有两个人,一个是不彻底的梅什金,另一位却是老练而冷静,察知一切的老人。第二个是丽莎。丽莎后面渐渐淡出,明显是要留互第二部去写的。第三个是14岁的少年克拉索特金,他无疑也是下一部小说的主人公。我们还要等待伊凡的复活和德米特里的磨难呢——也没有了。反理性一是阿廖沙对伊凡说的:1. 首先要热爱,而不去管什么逻辑,就像你说的那样,无论如何不去管什么逻辑,只有这样我才能理解生活的意义——这有点像后来舍斯托夫的反理性。《群魔》中的尼采式人物,也把这种理性拆散了。2. 伊凡对阿廖沙说的:越愚蠢越接近真实,越愚蠢越明白。愚蠢是简洁朴质,而聪明是圆滑晦涩。聪明等于卑鄙,愚蠢等于直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让他的主人公发言时,就像曹雪芹给自己的不同的主人公写诗,有着各种境界的衡量,差的好的,主人公有自己的水平和视野,以及声音。比如阿廖沙和佐西马的层次和风格,还是有不同。并不是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人代入。格鲁申卡没有写好格鲁申卡写得最好的地方是“一根葱”,其后,她垮塌得历害。人们通常都会把她当一号女主,而她最后的风采也没有盖过卡捷琳娜。更不用说,和无与伦比的纳斯塔西娅·菲丽波芙娜相媲美了。不过,格鲁申卡的狠性写得比纳斯塔西娅写得要好,她始终把这种狠性保持到最后。她没有纳斯塔西娅可爱。里格鲁申卡的出场完全就是《红楼梦》的笔法呀,未见其人而先闻其声,连“门帘一掀,只见”都是一模一样的。先要在佐西马的修道院,父子反目争吵;然后用卡捷琳娜的美丽和坚韧来衬托她;这还不够,父子还要在他们自己家里再打一场大架,第三次烘托。最后延宕的会面出现在两个女主不能同场的房间中。那么多等待和吊胃口,让人不禁替格鲁申卡担心,到底还能怎么写好你呀。结果,她真的是平平。而卡捷琳娜最后的出场,则完全超跃了她。宗教代神和基督发教谕,需要境界,这点对许多作家是最难的,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则是最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