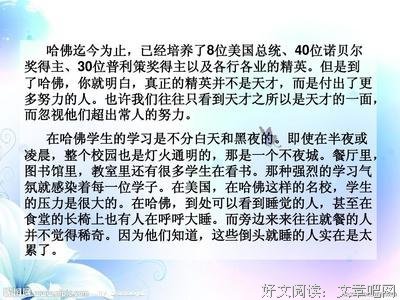
《国家精英》是一本由[法]P.布尔迪厄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715图书,本书定价:37.00元,页数:2004-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国家精英》精选点评:
●此类大牛的晦涩著作最好配合原版,至少要配合英文版看。
●学业资本通过文化资本而与社会资本紧密联系
●旁征博引,笔力恢弘,700页巨著写尽霸权与法兰西穿袍贵族,打破老鼠人想长双翅膀变蝙蝠人的传奇-神话,劝您早日重开(最好开着泥头车再带走几个),光是这点,就,神作,不容争辩的。 也发现了一些新的好玩的东西,ENA,以及IEP与HEC,比起对没落的巴黎高师的考察(包括其他救世学校及其神话)更有意思得多:尽管有预备学校和私立中学的对立,关于那些学业资本上的失败者如何通过学校中介模式得以继承的问题,庇护性学校
●作者说他的教育社会学分析并不是回到支配着诸如子承父业之类的“社会移动”“理论”的朴素哲学中去,可是鄙人浅陋,书中句句经典却实在体味不清比“有其父必有其子”更高维的结构性分析(而且他好像不是结构主义者?)-先到这儿吧,p.325
●后现代果然伟大......
●暴雨屋子塌了书丢了。
●如果说福柯的理论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高考制度以及考试工厂的诞生,Bourdieu的理论能加深我们对近几年崛起的城市精英教育的反思。
●虽然分析的是法国的问题,然而对于就读于名牌大学,骨子里就带预备精英底色的我辈而言,此书却是毫不客气的剥皮之作。或许从现在起往下的若干年内我的轨迹,乃至所有同代人的轨迹,将会以生动的事实证明布迪厄这套话语的持续有效。说到底,人在江湖,真正被在乎的,最终还是“权力”。概莫能外。
●大师们两手都很硬,但终究也还是要找一个落脚点依靠一下。
●一直想写一篇关于“自雄心”的文章。实际上,北大,哈佛的入学学生并非比居于次席的几所大学高出多少,然而处于结构塔尖,自我的高期待,以及环境的不同互动方式,长期会塑造一批人——他们就是国家的精英。
《国家精英》读后感(一):读[法]P.布尔迪厄《国家精英》
34数据分析和理论分析的结合,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范本p189 苦行的力量。p193 人们出生高贵,但他们必须变得高贵。权力场域极其变化比较重要,尤其是对于家族试图维护自身利益的分析。最后一段对韦伯的批判发扬,以及与僧侣、骑士、劳动阶级的旧三级的比较很有意思。
《国家精英》读后感(二):刚翻了一点随便写
太厚。且有时社会学研究让人烦的是诸多论证的采撷只为证明一个présupposé的结论。真不知道啥时候才念得完。至于结论,大概现在中国也越来越进入这样一种暗示着精英主义的媒体声音。虽然曾非常marxisme,但恰恰却越来越反对这种过分“唯物主义”的关于社会观念的看法。
感想
1 事实上就在所谓分层中见到错位,“高位”的自我意识反而不如中下位置的某些人更明确,缺乏和彰显之间的悖论性关系在个体而言是常见的,这反而取决于个体家庭氛围与个人品质。但这种错位和自由却某种奇怪的集体心态下被刻意忽视和掩盖。
2 倒不觉得精英意识和分层在一个各种发展较为完善的社会更“固化”、反过来在譬如此前的中国社会更平等(对某种朴实的“黄金时代”的怀念),因为不完善的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却往往也是最为贫乏和单一的——而真正抗拒阶级固化的并不是维系单一评价体系而在此体系内扩大流动,这反而造成以此评价体系内的种种虚假表层的行为,对个体而言或许甚至呈现为自卑与虚荣的一体两面;
而恰恰是,通过个体的真正的自由主义、和难以全然容纳在社会评价观念内部的“其他”观念和看法的平行存在(所以我想这种观念平行的丰富性还应当在社会的全面完善中培育出来),所谓的分层与固化才会在其纵向上失去稳固。
《国家精英》读后感(三):随手校勘数则
以下仅为实在觉得肯定有问题的地方去对应原文的校订,并非对照细读的结果。
全书各处出现的第一部分附录一的时段(1966-1988)均应改为(1966-1986)。
全书各处的主导性图式均应改为生成性图式(schèmes générateurs)
全书各处的英国公立学校均应改为公学(众所周知伊顿、哈罗、拉格比等public schools恰恰是私立贵族学校)
全书各处与客观结构对应出现的混合结构均应为具身结构(英文为embodied structure,指各种感知和判断的范畴)
全书各处古贝尔丹均应为顾拜旦。
全书各处的象征性普及均应为符号普遍化/通用化。
页9行1:不认同,misrecognition应译为误识,即虚幻的认同,恰好译反了(这是统贯全书的一个核心术语,译误导致共谋游戏不成立)
页9行9-11:整句译错,应为确保后天获致重于先赋,主动谋取的重于消极获取的,实干重于出身,才智业绩重于世袭人脉。
页36行3-7:Modalite一词分析错误导致整句译错,应为……具有怎样形态的关系,取决于……。
页51倒数行4:疯癫应为异化。
页132注1:两处皆应为伯特兰•罗素。
页173注1:应为拉铁摩尔。(其他不少所引汉学家的名字也有问题,不一一指出了)
页310行5:应为希区柯克。
页399行9:迅速协调,应为无中介契合。
页456行13:合情合理的,应为有相关意义的。
页470倒数行4:差异最大的实践领域,应为彼此殊异的诸多实践领域。(英语为the most widely different domains of practice)
页470倒数行3:特征上互成体系,应为各具整体特色(英语为systematically characteristic)
页523倒数行10:应为波伏娃。
《国家精英》读后感(四):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作业
《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读书报告 一:总论:春秋笔法、批判风格——因何而艰涩? 通读本书,最大感受除了在皇皇巨著感受到自己学术水平的浅薄(汗颜),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春秋笔法的风格。 利用二元对立(经济/知识、高自主性/弱自主性)建立的“社会空间”坐标图、个体与其社会出身的列联表,语言分析、社会特征(体育运动、电影、政治立场、俱乐部)、对悼词的社会学分析,布迪厄用多种方法含而不露的进行其对法国教育场域以及与之联系的权力场域的批判性评论,目的显然是为了系统性的揭示国家精英这一群体的上升之路。 就其艰涩而言,首先,作为出生于比利牛斯的一个小镇普通家庭的法兰西学院教授,再结合其对法国权力场域的辛辣批判,可以想象到其日后辉煌中的艰难,这就注定了其对法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批判的隐晦性;其次,世所公认布氏理论的抽象、艰涩,一方面源于其深厚的哲学功底,另一方面,翻译的过程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语言缺失问题。 此外,对于法国经济场域、教育场域及其历史背景的粗陋理解,也使得笔者在读某些片段时如阅天书,但是,所幸在某种程度上“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中法之间文化上的某种同质性为理解本书也带来了些许帮助,但是至于中国以后的社会走向是否像书中所言,笔者不敢妄下判断。 二:第一部分:学业分类形式(或社会分层“预形式”) 作为法国领导阶层的原动力,文化资本在学业分类学的原则下折射出鲜明的分层特征。 法国高等教育体制通过将部分学科(哲学、法语、希腊语等)巧妙地分为智者的、需要才华的学科,从而识别出求学者的社会出身(蕴含在其中的惯习,包括语言组织方式、品味、政治立场等),在中立化的外表之下,通过“才华”、“天赋”这一意识形态化的词汇,产生温和却真实的象征性暴力。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布迪厄通过对法国重要的会考批语并将其与家庭出身做列联表分析,以及对讣告的语义分析,将这一巨大的认知机器背后的逻辑清晰地显示出来:巴黎高师的每一阶层的毕业生的可能人生轨迹不仅在毕业时就已经得到了部分规定,并且在“赞美”的讣告中,将校友的惯习/习性,真实的展露出来(对待不同阶层学生的评价标准之不同,显示这一教育体制早已在心智结构上塑造了学生,并使其成为人们建构现实的“图式”,即布迪厄强调的认知结构)。 三:第二部分:圣职授任礼(“区隔”——“神圣性的建立”) 将现代法国教育体制下的学生与中世纪的僧侣所做的类比尽管看似荒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的社会过程毫无二致:一方面,“正如迪尔凯姆,在传授奥义的过程中,为了使个人服从新的方式,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人们不断地对新生进行刁难与作弄”;另一方面,与苦行的生活方式相对应的群体象征性封闭,以及在盛大的祝圣之中产生的认同和神化的辩证关系,使得学业称号得到了真正的象征性暴力。 教育机构垄断的学业称号的发放权力,通过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合谋行为,为最终的神化效应找到了真实的依据:在分数组成的社会连续统中,教育机构人为设置的鸿沟,形成其内部的认同(自豪感、“内婚制”),即神奇的参股逻辑,将在社会特征上具有极强同质性的个体“拘禁”起来,培养其内部的情感,并且形成强有力的象征效应。 法国社会对这种教育体制的神话和痴迷,根源于法国“大文化”的传统,一方面,法国的大学分类体制已经显示了其内涵的分类原则,另一方面,教育场域与权力场域相连接的,也正是这一原则。 四:第三部分:名牌大学场域及其变化(位置、习性与立场) 提出大学场域的交叉现实:以名牌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对立作为第一方面;以知识极点和经济极点的对立为第二方面,从而将每所大学放到其对应的位置之上。 注意到布迪厄理论中核心的一个命题即是主客观结构的一致性,正如他在序言所说:“在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之间,在社会世界的客观划分(尤其是不同场域中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和行动者划分社会世界的关注原则与划分原则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 由此,布迪厄提出,“引导学生在高等教育机构空间分布的差异化原则存在于学生的习性之中,而习性则是与继承所得资本的总量以及这个资本的结构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能够理解,在关于文化、宗教或者政治方面的立场结构与位置结构之间存在着严密的对应性”。 这一段论述的重要之处在于从微观个体层面完整的阐述了再生产机制:位置(资本的数量和机构)——习性——个体与学校之间的双重选择——体现为在文化、宗教或者政治方面的立场。 实际上,这一部分的分析也正是围绕其他展开:场域各个位置的模态、与之对应的习性与位置、对其立场所做的分析,这几方面相辅相成,完整而又系统地展现了整个大学场域结构和个体的心智结构的对应关系。 但是,这种对应关系具体是怎么在这些精英中进行生产的呢?换句话所,这种群体的象征性暴力/效应如何得以保持呢?这就是所谓的群体精神:大学场域首先对学生进行等级上的划分;同质性个体造成象征性资本的集中;利益、声望等资源可以被共享。当然,与之配套的严格的筛选机制(选拔和超级选拔)等保证的正是这种群体精神的永存。 五:第四部分:权力场域及其变化(与再生产策略对应) 穿袍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与专家治国论者之间的对立,与权力场域的两大变化有关:一方面,学业称号的重要性加强,然而,仅仅只能作为进入最高阶层的必要条件,不是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在文化资本的持有者中,官僚主义式的大文化提供保证的技术称号衰退,然而,社会资本等其他因素开始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在这样的场域结构的变化之中,决定再生产策略的核心是: 不同资本之间的交换率,即,在现有的资本结构和数量下,根据利润差别机会的结构进行再生产的策略制定:教育测量、经济策略、社会投资策略。 从权力场域和教育场域的关系中看,可以看到,一方面,人文科学转向公共研究与实用性研究,以及技术的复杂发展使得传统的手工业式研究者濒临灭绝,从而为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蒙上了悲剧的阴影。 六:第五部分兼结构性评论:国家权力与支配国家的权力(政治哲学家的意识形态“谎言”及其与“精英”的合谋) 布迪厄通过历史学的分析指出:实际上,代替僧侣们的政治哲学家们的伟大工作,在理性化的包装之下,将文化资本包装成为国家精英必不可少的特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的国家精英才成为事实。 有一个例子或许能偶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国家精英的诡秘之处:对于需要“才华或者天赋”的哲学或法语学生在政治上偏左的这一看似背叛的现象,布迪厄给出了这样的评价:通过表面上赞同知识分子流行的价值准则,来塑造知识分子的某种形象。也就是说,塑造对于国家的义务,正是这点,才构成了其作为国家精英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布迪厄在最后一部分又辛辣的指出:“只是他们在提供这项服务的时候,必须能够兼顾到他们自身的利益。” 这里,布迪厄仍然对教育机构赋予了扮演潜在的颠覆性力量来源的重要角色:国家委托教育机构完成其合法化,但是这种让渡中不可避免的风险使得教育机构能够获得相对的自主性,在社会变革的时候,能够通过倒向被支配区域发挥颠覆性的作用。 综观全书,从学业分类形式、精英群体的产生、大学场域的变化,再到权力场域的变化,最后以支配国家权力这一论述作结,前后呼应,尽管对于笔者的学术水平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但是,不得不承认,布迪厄对于社会分层、不平等以及再生产机制的高超的想象力和利用社会学材料组织严密的论证的能力。 本书从两方面对笔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是大胆利用社会学材料,不要拘泥于定量、定性的藩篱;另一方面则是在对社会事实进行思考时,不仅仅要进乎其中,亦要出乎其外,形成系统化的理论观念。 参考文献 1:[法]布尔迪厄 著,杨亚平 译,《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商务印书馆,2004年9月第1版, 2:冯典,《名牌大学与权力场域再生产机制的联系与互动——解读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复旦教育论坛,2008年第6卷第5期, 3:陈卓,《校园里的背叛者——对布尔迪厄《国家精英》相关问题的解读》,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8月第14卷第4期 4:唐琼一,《布迪厄高等教育公平观探析——《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解读》,高教探索,2007年第3期 5:石娟,《场域的力量:高校位置分层的社会学分析——兼论布尔迪厄《国家精英》》,理工高教,2010年4月第29卷第2期
《国家精英》读后感(五):高富帅还是那个高富帅,DS在哪都是DS
最近花了不少时间看完了布尔迪厄(Bourdieu)的《国家精英》(la noblesse d’etat),商务版600多页艰涩晦口的译文。杨亚平女士翻译时的艰辛,实在需要感激,不然对于一个没学过社会学的人,这无异于天书。
本书的题目就很有意思,法语里noblesse和aristocrate有着稍稍的不同,前者是包含了佩剑贵族和穿袍贵族的一整个利益集团,而后者才是真正的“贵族精英”(这词源自亚里士多德,读起来很像吧),所以这个题目其实是暗含贬义的。这本书仿佛是《区隔》一书的应用,他讨论了一个我们必须关心的问题:既然每个人在权利/经济/文化场域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受弗洛伊德式的“童年阴影”所困,那大学教育,这个被寄予“鲤鱼跳龙门”意味的机构,是否可以促进阶层间的流动呢?
而布尔迪厄的回答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
要看清:能跳上龙门的,很多都是龙子龙孙,或是披着龙皮的鱼,大部分鱼连跳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众DS,退却吧!
大学,尤其是那些老牌名校,一直被冠以救世学校(Ecole liberatric)的光环,这里的救世是两层含义:“这里保存了科学和文化的精髓”以及“这里是平民子弟凭着才智打进中产阶级的阶梯”,当然,精髓不精髓的无所谓,后者才是实实在在的。挤破头的高考简直是场噩梦,但是从中一路杀出的“才子们”,他们凭借的真的是康德所称“天赋的缪斯”吗?我们可以看看大学入学考试考得是啥:逻辑分析能力+语言组织能力+超强记忆力。其实这三项和中世纪的贵族公学的要求类似:推演+辩论/演讲+博学。而这三项,与其说是源自个人的天赋,不如说是来自家庭的熏陶,或者更多时候在中国,是用钱堆出来的成长环境。一个真正blue blood的高富帅,在DS们小时候玩泥巴的时候,正在玩钢琴;DS们不知所云地默写课本时,人家听着蓝调在看原版小说;DS们在破教室苦苦背单词的时候,高富帅们在名牌公学和洋妞调情;DS们课堂上憋不出一句话的时候,高富帅们在高级会所和“叔叔阿姨”们谈笑风声。一个DS努力学习伪装出来的“素质”,高富帅们不经意间用平日里的“素养”就可以对付了。更何况凭借着家庭的经济资本和人脉信息上的优势,还可以选择short cuts (出国/艺术生/竞赛),而DS只知道为“再多考一分”拼命。你还别嫉妒,人家的才智是源自生活的,而不是努力训练遮掩出来的“高仿”。如今所提倡的“素质教育”/中国常青藤联考,便是有意将这种入学偏好合法化。“素质”这个东西,显然不是贫寒的家境负担的起的,于是大学的筛选,又对高富帅们开了一盏绿灯。
所以“大学录取”这第一道关口,便已经不是自由通行的“直通车”了,与其说是“救世学校”不如说是“庇护学校”:他只筛选出那些本来就属于中产以上阶层的“二十岁的加图们”,以及那些具有坚忍品质可以顺从地做“家臣”的平民子弟:这个群体作为高富帅们的外围,将是未来的社会构架里连接不同场域顶点,防止社会断裂的要素。当然幸运踏入“高富帅乐园”的DS,往往羞于承认自己的尴尬地位。
但是当丘比特万箭齐发时,隐藏在名校里的DS们就暴露了。高中生物里说过一个物种的产生,先是要靠混血,然后便是隔离了。大学的录取是对新一代基因的筛选和混杂,而大学的“内婚”便是一个有趣的隔离现象。在18-22这么个春心荡漾的年纪把一群“未来的精英们”圈起来,目的无非是最好都intra-college coupling掉。如此一来高富帅们的爹妈可以欣慰:家族血统贬低的可能性下降了,说白了便是没有穷亲戚,一身轻松啊。这方面一个有意思的隐喻便是霍格沃茨:在这里,和布莱克家族有血缘的波特家族和悠久的纯血韦斯莱家族实现了联姻,而韦斯莱家族更是将平民中涌现的天才赫敏纳入家族旗下。《龙族》里凯撒和诺诺亦是如此。所谓的自由恋爱,背后还是精心布置的家族安排。一无所有的男DS们,即便有着极佳的学术资本也是徒劳,而女生则不然:因为娶一个平民的女儿并不会分割家族的资产还能够更新家族的血液,而摊上一个DS女婿,那家族就得出大血了。即便是入赘,家族也需要给他添补经济/权利资本才能够介绍入本阶层的圈子里,总之是桩有风险的买卖。
再来看看大学里教的是什么?可以说,大学里80%的课程,在毕业后的名利场中都没用:有的是太迂腐,有的太高深用不到。那为什么还要开这些令人景仰的课程呢?"贴金"这个词最形象了。越是技术性,实用性,培养技能的知识,便越是限制了一个人所被承认的职位类型,也就是说,以后你就对着这机器/报表/数字过一辈子吧。越是笼统的,博学的,培养素质的知识,便具有更大的flexibility。什么是flexibility?对于高富帅而言,便是占据企业/政府的那些看了名字也不知道负责什么的高位,对于DS便是刷盘子。所以搞技术是永远没有出头之日的,至于选择商科/文科和高富帅争食,舔盘子的可能性也是要考虑到的。但是大学为了显示高富帅们不同于职校/专科学生的博学,一个劲地要弄通识教育。
比如,很多的大学现在开始鼓吹leadership。对于leader的子女,这是废话:这都是与生俱来的,呼吸中都透着一股leader范。所以学校可以名正言顺地安慰DS:看到么,你虽然学业资本不错,可是没有leader范啊,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素质啊。所以给人家打工,没什么好抱怨的。而对于“要么像拿破仑那样用大炮轰进巴黎,要么像老鼠那样钻进去”的有志青年们,如何把自己“漂白”便是十分必要了,就像是ecole poly学生中的箴言:“立刻抛弃你那难听的乡音,从今天起像个巴黎人那样说话”。乡音只是个象征而已,总之来源于外省贫寒阶层的一切不堪的回忆都要完全去除。当高富帅们偶尔陶醉于农村重金属时,披着龙皮的鲤鱼们坚定地只听爵士和充满小资趣味(总之准则是HR和总管们最爱)的流行音乐。当高富帅们搞不清自己穿的是什么牌子时,鲤鱼们开始搜集名牌手表/衬衣和古龙水的商标,YY着以后都要穿在身上。当高富帅们二话没说开始环球旅行时,鲤鱼们紧随其后,开始出没在最有名的景点和最有名的商场,总之,有名就行了。比巴黎人更巴黎人,然后才有望被那个向往已久的群体所接受。有意思的是,先一步踏入“中产阶级”的鲤鱼们,对于暴发户反而有着更切骨的仇恨。因为相信自己是凭着学业资本和“素质”的训练才拿到到今天的成就,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学院精英”集团,并且逐步和原有的“经济贵族”们融合,共同捍卫一个由经济资本维系,权利资本捍卫,和学业资本掩饰的“支配阶层”。
但是并非所有的DS都能成功地钻进去,于是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出身贫寒的名校门徒,对于学校有着更深的依恋,这一群体中选择去考大中学教师学衔(Agrégation)的比例也要见多。有人戏谑“在哪里可以汇聚最多的巴黎高师毕业生?不是外交部的鸡尾酒宴,也不是金融圈的俱乐部,而是外省各大学校代表来巴黎开研讨会的时候”。也难怪,他们所唯一骄傲的学业资本完全仰赖于“伟大的教育”,如果只凭经济/权利资本打拼,毕业一出校门挂掉的可能性很大。对于外省出身不高的高师学生,选择回老家的民政和文化机构“隐居”,或者一所普通大学的教职,不失为明哲保身之途,至少百年之后那些“国家精英”的同学会在悼词里假惺惺地怀念“虽然他的英才足以在巴黎闯得一番天地,但对于宁静乡间和家庭温馨的钟爱使他选择了高蹈隐居,奉献于人民教育事业。他追随了心灵的召唤,然而这却是国家的损失”。这话说的,太感人了。。。
从一个平民的起点通过学校的途径往上爬,虽说不是不可能,但就像是通过议会斗争实现社会主义一样,如此龟速,没有几代人是难以实现的。一个有趣的演变便是,选择Agrégation路线的名校毕业生,他们的子女往往在学业资本上有着先天的优势,于是命中注定地面临了他们父母从名校毕业的尴尬。只是这次家庭所拥有的权利资本已经有所改善:农民和小学教师的子女可以发奋在省城谋得一个小公务员或中学教师的职位,而他们的子女如果继续努力可以进入大学执教或比较赚钱的公务员职位。下一步除了继续巩固文化上的优势(据说巴黎高师已经完全沦陷为稳扎稳打的平民子弟的堡垒了),就是向更高层甚至私人企业进发。如果保持严谨的家教和适当的联姻,这一家族最终会扩张成一个以学阀为基础的所谓“耕读世家”。但是在经济场域中,这个家族地位依旧不是很高,虽然他们可能会垄断对学业资本的解释权,但是权利/经济的巨头们可以轻易废掉他们的武功,比如国家行政学院的兴起直接摧毁了巴黎高师的地位。不过,这样的家族所提供的文化资本总会有买家的,尤其在中国随着第一代白手起家创业者的淡出,有可能会付出一些赎买费来封住怨气重重的知识分子的嘴(然后大学便成了一所收容所,专门安置出身平民又不愿追随高富帅脚步的DS们)。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从而获得合法性似乎是个自然的驱动,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便是大家族倾向于将最小的子女“放逐”到艺术或高深学术的领域,而将经济的继承权交予长子。这并非歧视,而是当“小儿子”在家族的庇护下有所成就之后,原有的经济霸权便获得了文化霸权的支撑,毕竟,艺术品收藏/古董/基金会,哪个不是洗钱的好去处啊。
所以,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最终,还是属于高富帅们的。大学里的DS们,女生就去钓金龟婿吧,男生可以努力地把自己的泥土味洗干净,找个好领主,跟高富帅们走没错!至于不想这么麻烦的,做技术的就好好在企业混,搞学术的就好好拼tenure,然后期盼着自己的子女踩在在自己的肩膀上,向着更高,更富,更帅前进吧。当然前提是,得有高富帅一不小心掉下来才可以啊。(这不,刚掉下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