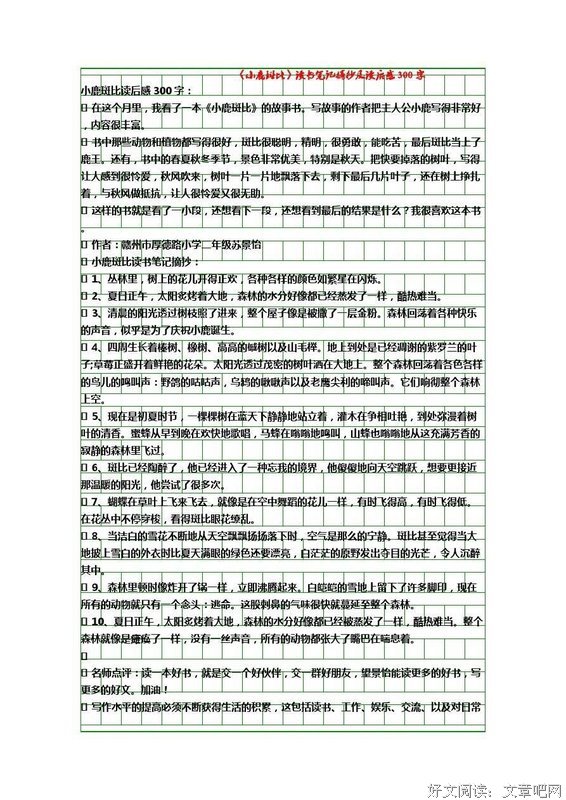
《记忆记忆》是一本由[俄] 玛丽亚·斯捷潘诺娃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页数:4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记忆记忆》读后感(一):四星
文体把控力是惊人的,却非我所关注的重点。玛丽娅这本无法定义体裁的作品,有一种向内无限扩展的思想张力,她本人的经历和在作品中持续延展的经历,让我遥望到一种新鲜而颇具振奋力的视野:在全球悲哀性地趋于保守倒退的当下,俄国文学如何逆水行舟,开拓一种不同于俄国文学传统的、“时刻把眼睛睁大瞧世界”的新界。不过,这种看似新鲜的努力,也是一种危险的努力:如何保持自我的纯真,又接纳世界的冗杂多彩,这可不仅仅是俄国文学在当代的难题。
《记忆记忆》读后感(二):yuki
okioku
《记忆记忆》是当代俄语世界著名诗人玛丽亚·斯捷潘诺娃的新类型复合小说:既有历史,也有哲学,更是文学。 小说主要由两条线串起:一条是作者对于旧物,文献,以及试图“记忆”的人们——所作的文学和哲学的思辨:桑塔格,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塞巴尔德,夏洛特·萨洛蒙等 等等等皆进 入了她的视野。在现在与过去中思考中得到新的诠释。 另一条则是作者通过寻找家族遗迹,回溯俄罗斯近代史中的自我家族史,拼凑出一个犹太家族几代人生命故事的历程:他们有的融入宏大叙事,刚满20岁便牺牲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有的与历史擦肩而过:参与了20世纪初期的俄国革命,成为俄国第一批“留法学医女学生”,回国后却就此沉寂;有的参与了热火朝天的苏联大建设,然而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时毅然决然移民德国,有的——诸如在书中隐形却又无处不在的作者本人,则同一个告别过去又满是记忆的国家一起迈入了新世纪,思考俄罗斯的当下,以及或近或远的未来…… 这两条线相依相交,勾勒出巨大20世纪的诡谲风云与微小浪花。精巧复杂,娓娓道来,又包含了俄罗斯式的辽阔和沉思。在追溯与思辨中, “后记忆时代的俄罗斯”得到思考,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整个欧美文艺界的先贤们被重审,过去与现在、逝者与生者之间的关系和逻辑被再度梳理——“关于他们我所能讲述的越少,他们于我便越亲近。” ———————————————————————— 编辑推荐 ★ “近年来最重要的俄语小说”,宣告俄罗斯文学重返世界文坛之书。 ★ 一部与整个欧美文艺界对话的俄语文学哲思录;一部解构重构犹太民族的20世纪俄罗斯犹太家族史。 ★“当代俄罗斯是一个后记忆的时代”——后记忆时代的俄罗斯一部杰出的“反记忆”小说。 ★ 2018年出版即获俄罗斯国内三项文学大奖:俄罗斯国民级文学奖“大书奖”、 新文学大奖“鼻子奖” ,以及以托尔斯泰庄园命名的文学大奖“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奖之“读者选择奖” ★问世短短两年,迅速被译为德,法,英,意,荷兰,瑞典,芬兰等多种语言,在欧洲取得巨大成功。 ★“我曾经对于自我家族的以下几点确信不疑: 我们家族中没有人在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牺牲。 没有人遭受镇压。 没有人死于屠犹。 没有人被杀。 亦没有杀人者。 但上面中的好几项突然变得布满疑团,甚至干脆是非真实的。” ——《记忆记忆》,玛丽亚·斯捷潘诺娃 ———————————————————————— 媒体推荐 近几年最重要的俄语小说。 ——莫斯科回声(俄罗斯) 一本十年一遇的元小说——杰出的文学重构,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叙述了记忆,时间,与历史的纠葛。 ——《文学》杂志(俄罗斯) 其风格精妙绝伦,其出版切中时代。 ——《新苏黎世报》(瑞士) 片段式的反思和有力的诗性。 ——《柏林报》(德国) 玛丽亚·斯捷潘诺娃早在普京时代前就已经是一位相当重要,充满创造力的诗人,然而时代却呼唤更强硬更公众化的角色。非常不幸,西方对其的认可远远落后于其负盛名的俄罗斯。 ——《洛杉矶书评》(美国) ———————————————————————— 名人推荐 只凭《记忆记忆》这一部作品,玛丽亚·斯捷潘诺娃,就足以进入当代文学大师行列。 ——作家,赵松 趋于宏大与归于微末,涉及时代又潜入生活,苦难与诗意难解难分,叙事与哲思纵横交错。这是一部无法界定文体、难以概括内容、不可能找到师承的个性之书。斯捷潘诺娃写尽记忆对于幸存者的意义与伤痛、记忆对于历史的抗争与补充、记忆对于记忆的执念与无能。就像本书的核心喻体瓷娃娃,它们在承载历史时受伤,也正是伤痕使得每个个体独一无二。而珍视记忆,就是为残缺的瓷娃娃树碑立传,使得它们不至沦为历史车轮下一粒看不到的微尘。 ——学者、书评人,马凌 一次关于家族记忆和时代记忆的旅行,一次关于记忆本质的探寻。 ——评论人、诗人,胡桑 《记忆记忆》,并非只是一本关于追忆(母系)家族的年谱,还带着同时作为一名女诗人关于社会的理性透视与“元”思考。亦如斯捷潘诺娃的诗歌,《记忆记忆》的“文学语言独具特色,语言所有层次上的异化处理均有建树,从而让新的思想潜能得以呈现”。 ——诗人、俄语译者,骆家 《记忆记忆》是一位年轻女诗人关于家族往事的文学想象,也是她关于俄国历史、犹太人命运和记忆本质的哲学思索。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俄语文学译者、学者,刘文飞 《记忆记忆》是一部极具探索性的作品,这一点从书名即可看出。读者既可以把前者理解为动词,而将后者看成名词,也可以全部当作名词。在这部书中,打破惯性思维的语词组合俯拾皆是,充分凸显了语言的诗性,由此照亮了现实中一部分被遮蔽的生活。 ——俄语文学学者、“金色俄罗斯”系列主编,汪剑钊 玛丽亚·斯捷潘诺娃是当代俄罗斯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在这本书中她探索家族记忆(交流记忆)如何转化为文化记忆,俄国知识分子如何通过记忆保留白银时代精神。 ——俄语文学译者、学者,李莎 这本书给我以极大震撼,有种要炸裂的感觉:那种无法言传和捋清的感受,各种记忆的碎片夹杂着情感,让我摸到了俄罗斯文化的不同层次,又好像摸到了自己童年生活的一些片段。 ——书评人、俄罗斯历史文化学者,张猛
《记忆记忆》读后感(三):“写尽记忆的反记忆小说” ——一份极其个人的解读
引:反记忆
尽管玛丽亚·斯捷潘诺娃本人在采访中否认“反记忆”的概念,我仍然“违背作者意愿地”将其作为了本书的定调:“一本写尽了记忆的反记忆小说”。
记忆,诸如家族史,诸如自传,诸如口述史,甚至我们这个时代乐此不疲的对于历史事件的挖掘和试图还原——这构成了层出不穷的人文社科专著,而记忆则是一座可供挖掘的宝藏,对其的探究已成为全球性的事件和习俗:每年回溯过去的书不胜枚举;同为俄罗斯大书奖的获奖作品,便包含好几部传记。但在“挖掘真相,记住过去”的思潮下,斯捷潘诺娃这部30万字,结构复杂的跨文体小说,却提供了另一种思路:记忆之不可寻,以及饶过记忆。
起:夏洛特
《记忆记忆》一书的序幕从封面的瓷娃娃拉开,这种被称为“冰人夏洛特”(Frozen Charlotte)的娃娃由19世纪中期的德国批量生产,至今已成为欧美无人不知的小古董(eBay上就买得到,几美元一个),并且由于其天赋的瘆人感,成为恐怖小说的绝佳取材(顺便一提,瑞典版封面就由这些瓷娃娃铺成,看起来宛若B级小说)。冰人夏洛特作为意象,贯穿了《记忆记忆》一书,斯捷潘诺娃在《记忆记忆》一书中如是描写:
“我在一个专卖各种妇女饰物的摊位发现了一个盒子,里面放着成堆的白瓷娃娃。奇怪的是,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多多少少都带着点残疾:缺胳膊断腿的,带豁口的,有疤痕的。
我当然也随口问了问女摊主,还有没有更完好的,作为回答,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据她说,这些瓷娃娃出产于德国某城市,自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连续生产了半个世纪。当时它们随处可见,食品杂货铺和日用品商店都有卖。但这些造价低廉的瓷娃娃最主要的一个用途,是作为货物运输时的减震垫,以免贵重物品在运输途中相互磨损。换言之,这些瓷娃娃生来就是为了牺牲的。”
线索:我“平凡的族人”与历史的“大人物”
斯捷潘诺娃开始挖掘家族秘史的契机很简单,“不满于族人的平凡而好奇”:“小时候,我非常失望于家族成员的庸常职业:工程师啦,图书管理员啦,医生啦,会计啦,无一例外,全部普普通通、平凡无奇,任何快活或者冒险的气息都无从期待。”其方式也并不出奇:无非是搜集信件,照片,重访家族旧地,譬如全书末尾附上的照片,正是她在文中所描述的:“在低矮的天空下漫步的人群中间,有一位身姿笔直的女性。她独自一人背对镜头而立,穿着浅色夏装的纤细后背构成了照片的纵轴线,好似静止的旋转木马的中间立柱。戴着硬料帽子的头向后仰起,手捧一大束鲜花。面部虽然看不清楚,但我愿意相信,她就是我的太姥姥萨拉。”
太姥姥萨拉·金兹堡中年丧夫,独自将女儿抚养长大。然而,少女时期的她正是因为参与了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才被家人送去巴黎的索邦大学的。彼时索邦大学本地学生对抢占名额,土里土气却学习刻苦(可恶至极)的“俄国女留学生”颇为反感。太姥姥在一番艰难取得医生执照后,回到俄国,一生波澜不惊。她的闺蜜,曾经的革命密友,斯维尔德诺娃,其兄长斯维尔德诺夫正是英年早逝的革命先辈,也是列宁忠实的战友——一次完美的与历史擦肩而过。
其他祖辈们似乎也并非那么“平凡”:另一先祖伊萨克·古列维奇,其名字竟已载入当地史册,更是有一条街以其为名,在当年给这位“工业大资本家”寄信,只须写上“古列维奇,赫尔松”,信件便会准确抵达。然而赫尔松地方志显示:此君并无后人。
这种矛盾贯穿了斯捷潘诺娃的追寻:她一路颠簸抵达先祖的故居,站在院中,似乎能感受到自己与他们冥冥中的联系,心中充满奇异的柔情,几天后却被友人告知——“玛莎,似乎搞错地址了,非常抱歉”;她翻到了一张十分不苏联的裸女照片,又翻到了外祖父和外祖母年轻时(廖尼亚与廖利娅,天造地设)缠绵悱恻的往来情书,联系起来竟挖掘出两人婚后,在孙辈眼中恩爱下的貌合神离;她亢奋地写信给父亲,希望父亲提供其在远东“建设苏联祖国”时的信件——印象中如《鲁宾逊漂流记》一般妙趣横生的生活——却被父亲生气地拒绝:那不过是虚假繁荣。
家族的个人记忆逐渐变得浑浊而令人迷茫,宏大历史节点:列宁格勒大围困,大清洗,排犹,医生案……与族人的平凡生活竟微妙地交织错落,一切宛如浮舟下幽微的黑色河水:
“我曾经对于自我家族的以下几点确信不疑:
我们家族中没有人在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牺牲。
没有人遭受镇压。
没有人死于屠犹。
没有人被杀。
亦没有杀人者。
但上面的好几项突然变得布满疑团,甚至干脆是非真实的。”
——那么,集体记忆如何?斯捷潘诺娃以新的视角切入了对欧美文艺圈的思辨,比如,犹太共同体:嘲笑曼德尔施塔姆“犹太崽子”的吉皮乌斯;“夸赞”“在和这些人交往的过程中完全不会想到犹太人,除了文化之外感受不到任何其他东西”的托马斯·曼;被以赛亚·柏林评价为“只是因为他不喜欢。他更希望犹太人能够被同化,不再成之为一个民族。我注意到,我每次提及犹太人或者巴勒斯坦都会给他带来明显的痛苦”的帕斯捷尔纳克——彼时不安与恶感平等地笼罩着整个欧洲的所有人,“人物”也不例外。
而同时,有倾向性的,走向单一叙事和单一道德诉求的集体记忆同样具有非真实性。如夏洛特·萨洛蒙,在20岁出头闭关创作出762幅水彩——这便是后面惊世骇俗的展览“人生?如梦?”,波洛克评价道:“梵高花了10年的时间创作了大约850幅画作,而萨洛蒙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创作了769幅画作,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形势的紧急程度。”这也正是对其创作认知的一个基调,衍生一下,便是“反抗纳粹——属于犹太人的杰作”。斯捷潘诺娃详细分析了其创作,却认为:“画家化身为又一幅集体苦难的圣像画,变成了好莱坞电影的热门素材——但并非因为她所成就的,而是因为她所遭受的。”仅仅因为她极其偶然地遭遇了一系列历史事件,便将其归入其中,其创作动机和意义便被普遍地简化和扭曲了。
带着这样的怀疑和逻辑,斯捷潘诺娃介入到对20世纪欧美文艺圈和事件的重审中,集体中分割个体,个体中“否认记忆”:从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的论争,到约瑟夫·康奈尔的魔盒;从塞巴尔德的物件清单,到戈德切恩的摄影展览;从多布罗温为高尔基演奏的乐曲,到玛丽·塔廖尼的奇遇。纳博科夫,朗西埃,哈尔姆斯,桑塔格,夏里亚宾,塔可夫斯基,普拉斯,霍夫曼……皆成为玛丽亚·斯捷潘诺娃解构和重构的源泉和参考。
终:幸存者
如果说,斯捷潘诺娃在追寻家族故事时候,“生来便是为了牺牲”的夏洛特们映射了默默无闻,衬托了“历史的贵重物品”的族人们,那么当名为夏洛特的女画家在历史的集体记忆中同样失却自我这一事实,便重赋了“冰人夏洛特”以新的意义:死者同样破碎,生者同样残缺——温柔的别佳和坚毅的萨拉带着毫无二致的庄严去世,正如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关于过去和未来的论战以同样的坟冢为终;市场出售的夏洛特必然残缺,却又不至于破到认不出来。“冰人夏洛特”由此成为了记忆本身,也成为了追逐着过去的,作为时代幸存者共同体的我们,正如斯捷潘诺娃在“中文版序”里所言:“这本书我写了一辈子……当下活着的我们所有人都是幸存者的后代,他们全靠奇迹和偶然才活过了多灾多难的20世纪。这一点将我们联系起来,就像无人荒岛上的一群幸存者,每个人都是亲人。我们的交谈足以跨越代际、跨越距离、跨越语言。我能感受到这一亲缘关系的温度,尽管不无悲凉……我很幸福,我的这本书如今将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或许,它能让我们之间的共同性变得更多一些。” 而过去,“关于他们我所能讲述的越少,他们于我便越亲近。”
文章仅代表责编对此书的理解,期待读者能从中看到其他更丰富的内容。
《记忆记忆》读后感(四):马凌评《记忆记忆》:在历史背阴面枯坐的幸存者,呼唤从未谋面者的名字
多灾多难的20世纪,让我们所有人都是幸存者的后代,而他们全靠奇迹和偶然活了过来。玛丽亚·斯捷潘诺娃看来,我们像是隐在历史的背阴面,聆听并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为素昧平生者哭泣,呼唤从未谋面者的名字。
趋于宏大与归于微末,涉及时代又潜入生活,苦难与诗意难解难分,叙事与哲思纵横交错。这是一部无法界定文体、难以概括内容、不可能找到师承的个性之书。斯捷潘诺娃写尽记忆对于幸存者的意义与伤痛、记忆对于历史的抗争与补充、记忆对于记忆的执念与无能。就像本书的核心喻体瓷娃娃,它们在承载历史时受伤,也正是伤痕使得每个个体独一无二。而珍视记忆,就是为残缺的瓷娃娃树碑立传,使得它们不至沦为历史车轮下一粒看不到的微尘。
「作为“阿莱夫”的“冰人夏绿蒂”」
在希伯来文中,“阿莱夫”是第一个字母。作家博尔赫斯在同名小说中赋予“阿莱夫”以神秘力量,它包含着世间的一切,独成一个宇宙,当你凝视“阿莱夫”,也就明瞭了隐藏的秩序。当诗人玛利亚·斯捷潘诺娃于莫斯科的古玩市场上邂逅并买下一个小骨董,她意识到:“这次讲述的真正的‘阿莱夫’,已经被装进了我的口袋。”多么幸运,作家为自己的作品找到了一个中心喻体!
“阿莱夫”出现在《记忆记忆》的封面上,这是一个残破的白瓷小男孩,三厘米长,光着身子,一头卷发,有点像丘比特,终归是瓷体凡胎。在市场上,它们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多多少少都带些残疾,缺胳膊断腿的,带豁口的,有疤痕的。吸引斯捷潘诺娃的是女摊贩的介绍:这些造价低廉的瓷娃娃最主要的一个用途,是作为货物运输中的减震垫,以免贵重物品在运输途中相互磨损。换言之,这些瓷娃娃生来就是为了牺牲的。
作者这样写:“我清楚地知道,我已经找到了这本书的结尾。这个瓷娃娃有多重寓意:首先,没有任何一段历史可以完好无损地流传下来,不是脚会受伤,就是脸会刮花;其次,空白和缺陷是生存的必然伴侣、隐秘发动机和加速装置;再次,只有伤痕将我们从批量产品变成独一无二的单品;最后,我自己也是这样的瓷娃娃,20世纪集体灾难的批量产品,同时也是其survivor和被动受益人,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
在后来收集家族史资料的过程中,更多瓷娃娃的信息得以浮现。它们出产于德国图林根地方的霍伊巴赫小城,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大批量生产,大约生产了半个多世纪。为了节省成本,只在正面上釉,一两个铜板的价格,使得它们在欧洲随处可见。既可以放在玩具屋当摆设,也可以裹进馅饼里看看谁有运气,似乎还可以放在茶杯里代替冰块——所以在英语世界现在有一个统一的称谓:frozen Charlottes,冰人夏绿蒂。至于充当减震垫的说法,既没能证实,也没能推翻。一个落雨的傍晚,作家的瓷娃娃摔碎了,她哀叹说:“原本他还好歹诠释了家族和自我历史的完整性,突然间却变成了一个讽喻:历史无法言说,任何东西都无法保存,而我,完全无法从他者过去的碎片中拼凑出自我,甚至不能将其据为己有。”
瓷娃娃有三重比喻。第一重: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既像瓷娃娃一样脆弱,也像瓷娃娃一样坚强。他们承载着时代的重量,并因此而伤痕累累。牺牲是它们的宿命,残缺使它们各个不同。第二重:这些瓷娃娃又像普通人的记忆,是幸存的,又是破损的。唯其如此,后代才有强大的心理驱动力要将其修补还原。纵使记忆对客观事实的重构十分有限,记住它们并不完美的样子,总好过让它们化为齑粉。第三重:保存了瓷娃娃的人并不是瓷娃娃的终极拥有者,这里还有伦理与哲学意义上的更深纠葛。
俄罗斯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曾说:世间最无聊的莫过于两样东西——他者的梦境和别人的淫乱。而斯捷潘诺娃相信:“人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聆听并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为素昧平生者哭泣,呼唤从未谋面者的名字。”冰人夏洛特,幸存者的象征,幸存记忆的象征,微小、不美、背对我们、随时可能湮没在时间深处,纵然作者本身有“反记忆”的想法,而以文字将它挽留在纸上的这一刻,我想,终是有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冰人夏洛特”「在“历史背阴面”枯坐的“幸存者”」
斯捷潘诺夫、金兹堡、弗里德曼、古列维奇,一个俄罗斯家族,三个犹太家族,四个家族、五代人历经百年的血脉,流淌在玛利亚·斯捷潘诺娃身上。她从十岁起就试图写作一部家族史,挖掘其中的波澜壮阔以光耀门楣,只因为她“非常失望于家族成员的庸常职业:工程师啦,图书管理员啦,医生啦,会计啦,无一例外,全部普普通通、平凡无奇,任何快活或者冒险的气息都无从期待。”
在小女孩的视野里,家族里值得崇拜的第一个英雄是太姥姥萨拉·金兹堡,地方小镇的传奇女子,她坐过沙皇的牢房、在巴黎留过学、拿到医生执照、给苏联儿童看过病。家里有她繁多的照片和明信片。第二个英雄则是姨外公廖吉克,他二十岁在列宁格勒前线牺牲,女作家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装着廖吉克的信件、照片和阵亡通知书的大信封,也继承了对于廖吉克的崇拜。除了这两人,家族里所有的其他人“集体靠边站”,远离时代的风车矩阵。
就像《追忆逝水年华》里的主题,认识是在时间流逝中的认识,要经过三十五年的不断追寻,“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本档案到另一本档案,从一条街巷到另一条街巷”,家族记忆、民族记忆、社会记忆与国家记忆,方才纽结着、在时间的显影液中缓缓浮出。
家族记忆可能是大大美化过的,“那是世代相传、添油加醋的结果”。萨拉参加了1905年革命,友人中甚至包括列宁的好友、后来当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斯维尔德洛夫,的确了不起。不过,她在巴黎的学医生涯却没有那么了不起——法国医学院学费便宜、而犹太人获得医师执照可以摆脱定居地束缚,所以俄国女学生在法国学医的全部女生中占比高达80%,甚至成为一个现象。回国后,萨拉远离革命,嫁给一位律师,行医直至1949年。1953年发生著名的“犹太医生案”,一大批苏联著名犹太医生被指控谋害党内高官,而萨拉“幸运地”中风,未被卷入政治漩涡,从此成了一名家庭主妇,“终日守着四面条纹墙纸和一个丑陋发黄的奶油罐。”
家族记忆中的空白、缺失与抵牾,是在民族记忆、社会记忆与国家记忆场域下的被动失语或主动删除。斯捷潘诺娃的母系这一方,祖上都是地方的犹太商人、资本家和企业主,在新政权下纷纷失去财产,或沉寂落寞、或不知所终。这个家族的百年经历与资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大清洗、二战、冷战、苏联解体相始终,外加旧俄时代的排犹、战时的敖德萨排犹、苏联时期的犹太医生案。为了自保,祖辈有意隐藏记忆,三缄其口,在文牍表格的出身一栏慢慢“漂红”家世。好在秉承犹太传统,教育被当作头等大事,后代们多是医生、工程师、图书管理员、会计、建筑师这样的知识分子。孙辈终于可以在锅碗瓢盆、郊外度假小屋、茶炊和书信中过上庸常日子——“隐身在历史的背阴面,就这样在那里枯坐一生。”
再则,家族记忆与社会记忆、国家记忆相投契的部分,也常有难言之隐。这个家族处于时代主流位置的是二十岁就牺牲于前线的廖吉克。廖吉克在一封封家书里写着“一切都好”,实际却是“一切都不好”,列宁格勒的鏖战是浴血奋战,惨烈异常,而所有的前线生活细节在家书中一概不能提起。家族里另一个时代中坚是根正苗红的爷爷科里亚,16岁加入共青团,参与征粮别动队,一直做到部队政委,却险些在大清洗中被波及。在后半生里,不论说到别动队时的经历、还是那场牢狱之灾,爷爷总是讳莫如深。斯捷潘诺娃的父亲参加了热火朝天的苏联建设,但是当斯捷潘诺娃想发表他当年的家书,却遭到父亲的坚决拒绝。
就这样,一大家人在时代洪流中隐微地存在着。在斯捷潘诺娃看来,家族历史像是一部未偿夙愿的清单,可是在当事人看来,何尝不是一部侥幸逃脱的喜剧,他们不得不靠边站,也很愿意靠边站,作为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他们与宏大叙事保持距离,倒是在无聊日记、抽屉诗歌、手抄曲谱、业余绘画中消磨了岁月。到最后,斯捷潘诺娃认识到了关键所在:“确定无疑的是,当下活着的我们所有人都是幸存者的后代,他们全靠奇迹和偶然才活过了多灾多难的20世纪。”
「“后记忆”与“无所之地”」
动荡一经平复,总会奏响安魂曲。在历史学者玛丽安·赫希的著作《后记忆一代》中,“后记忆”的工作,就在于使机体复生,赋予其身体与声音,并按照自我经验和理解为其注入生机。她非常强调后记忆的创伤性,提出后记忆是“创伤性知识以及象征性经验隔代回归的机制”;而“俄罗斯,暴力不知疲倦地循环往复的国度,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创伤连锁反应,这个国家率先变成了记忆位移之所”。“后记忆”的重担,于是落在了幸存者子孙们的肩头。问题是,当大量的创伤性“后记忆”文学作品问世,《记忆记忆》会不会只是其中的一本?
斯捷潘诺娃意识到,自己一直所做的,无非是弗洛伊德所说的“Family romances”,感伤的往昔浪漫曲。而斯捷潘诺娃比绝大部分作家深刻且高明的地方,在于她有自反性:时时刻刻的自我怀疑、批判与犹豫。整本《记忆记忆》贯穿着作家的这种纠结,就像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洛佩,白天织造,夜晚拆解。也是基于此,《记忆记忆》一边拆解/编织家族记忆,一边编织/拆解记忆理论,“原本关于家族的书到头来其实并非关于家族,而是关于别的什么。它更像是关于记忆之构造,或曰记忆之欲求。”
最近几十年来,记忆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记忆,连同其不可避免的主观性、谬误及偏差,摇身一变成了新时代的女神。正如法国评论家托多罗夫所说,“记忆如今已然成为新的偶像崇拜”,这种崇拜大致包括两类,一是“过往崇拜”,一是“童年崇拜”。斯捷潘诺娃敏锐地指出:“对二者最为珍视的社会正是那些过去总是遭到扭曲、童年经常遭到滥用的社会。整个因循守旧的当代社会都仰赖后记忆的空气,它试图重现昨日荣光,恢复子虚乌有的旧秩序。”
作者对后记忆的非历史性感触颇深,她总结说:“记忆是传说,而历史是描述;记忆在乎公正,而历史要求准确;记忆劝谕训诫,而历史清算纠正;记忆是主观性的,而历史追求客观性;记忆并非基于知识,而是基于体验,比如感同身受,比如同情怜悯。从另一方面来讲,记忆的领域充斥着投射、幻想、扭曲,是将我们今天的幻影投向过去……” “在某种意义上,如何记忆过往,全凭我们自己决定:一千个人回首,便有一千种过往。无怪乎记忆总被拿来与务求精确的历史相对立:二者似乎都只是自我描述的手段,以便认清自我以及自我在时代中的位置,但较之于历史,记忆更加魅惑更加热辣,更加贴近肌肤,其最大的允诺,大概便是穿越过往的幻觉。”
斯捷潘诺娃区分了三类记忆:关于失去的记忆,忧郁,悲哀,明知失去,却无法挽回;关于得到的记忆,犹如午饭后的小憩,对得到的心满意足;关于非在的记忆,在所见之处看见幻影,幻想的记忆帮助人们逃避赤裸的现实。她的“记忆记忆”,其实是“记忆非在的记忆”。无限绵延的空间、旷野过后仍是旷野、道路尽头仍是道路,英语中对这类空间有个专门的描述——in the middle of nowhere(在无所之地的中央)。在隐喻的意义上,记忆的空间亦是如此,它空旷、辽远、飞鸟不到,可供有心人随意入侵。记忆的叙事者之于过往犹如殖民者之于新大陆,他们对于过往的态度是扣押先人做人质,掘地三尺,涸泽而渔。在对记忆材料的大肆劫掠、任意改造之下,假若无所之地出现奇伟的城池,那一定是源于后人的欲求,而不是祖先的需要。
《记忆记忆》中的一条隐线是斯捷潘诺娃外祖父母的爱情与婚姻,他们热恋时的书信在书中占了整整七页,但是外祖父钱包中一张陌生女子的裸照、外祖母钱包中一张写有陌生男子姓名的纸片,揭示琴瑟和谐的夫妻也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同理,就像在华盛顿纳粹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最残酷的影像会有隔板遮挡一下,以保护这些裸体的遇难者的隐私。在有些时候,如果说记忆即正义,那么遗忘则是慈悲。
「成为“纪念碑”的“康奈尔的盒子”」
斯捷潘诺娃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写作本书,她说:“这是一部家族纪事,又是一部讲述俄罗斯历史的小说,一部关于记忆及其怪癖的随笔集,一次注解20世纪的尝试,还是某种寻根之旅的见闻录。”还应该补上,这其实还是一部文艺批评、一部媒介哲学、一组纪念碑、一个康奈尔的盒子。
约瑟夫·康奈尔,狂热的纪念物品收藏者、美国装置艺术家,以“盒子系列”著称于世。康奈尔制作的这些盒子全都镶有玻璃,使盒子里封闭着的一组物品得以被观众看见。褐色天鹅绒、大颗宝石、16个透明立方体、蔚蓝色的玻璃,就可以致敬一位伟大的女芭蕾舞者。刨花、彩砂、软木球,不起眼的边角余料,也可以通过神秘的方式组合,从而获得被凝视的机会。康奈尔盒子是超现实主义的“奇趣柜”,兼有收藏、展示和记忆的功能,又将偶然性、任意性与艺术性合为一体,可以视为物质材料的记忆蒙太奇。
斯捷潘诺娃对记忆的媒介近乎痴迷,她在书中探讨了私人笔记、官方文件、相册、西洋镜、纪念碑、图纸、书信、回忆录、图片、肖像画、数字摄影等等媒介,尤其对纪念碑情有独钟。她心目中的纪念碑,并非体积巨大的官方勒石,却可以是日用品、碎布头、碗碟、墓志铭、箱子上的图画、两个人私下签署的秘密协定……“纪念碑以其存在本身维持记忆,它虽然无法讲述,却可以直接宣告,……其对人类事务的见证意义胜过任何编年史。” 假如说文件是使记忆官方化,纪念碑则使记忆物质化和情感化,从而个人化。康奈尔的盒子是纪念碑之一种,尽管这种艺术因其狂热与天真而被批评家诟病,但是无可否认,康奈尔盒子也带给人抚慰与温情。朗西埃曾说,“艺术的任务在于展现不可见之物”,而康奈尔盒子的内容物——现成品、或者日常生活用品——它们不自带目光,没有侵略性,却在可见可触中展现了那些不可见不可触的事物——人、爱与记忆。
《记忆记忆》的文体结构别出心裁,恰似一个文字的康奈尔盒子,不同质地、不同形状、不同大小、不同类别,在方寸之地组合成了一个世界。这世界如此微观,却又如此弘深。为了填充盒子,斯捷潘诺娃劫掠了几十位作家、诗人、摄影师、画家、艺术家,翻检他们关于记忆、物品、过去与未来的观点,就地没收,写入《记忆记忆》。从本书译者的二百余条注释中,当能领会这个被劫队伍的庞大规模。俄罗斯人引为自豪的白银时代作家群,几乎一网打尽,而还有更多数量的欧美艺术家,奉上自己的精髓。
苏珊·桑塔格可能是被抢得最惨的一位,也是得到回报最多的一位,关于影像问题,斯捷潘诺娃的段落不输桑塔格的《论摄影》和《关于他人的痛苦》。她犀利地指出:昔日根据基督教义,另有一个智慧的全能记忆,能将一切人与物——不管死去还是活着——都捏在自己手心。在那时,“救赎”与“保管”同义。步入世俗社会,记忆的保管类似仓库,博物馆、图书馆保证了象征性的、局限性的不死。到19世纪,随着技术革命的推进,记忆变成了民主实践,而存档变成了公众的大事,摄影术、留声机、电影、家庭录像、自拍杆,每个人都有机会保存一切。日常生活中产生的视觉和言语垃圾越来越多。新的载体技术改变了接受方式,无论故事、履历、还是文本,都不再被视为链条,即在时间中展开的因果相继的一系列事件。这一方面值得高兴,因为在技术时代任何人都不至于不留痕迹地故去,在广袤无垠的存储器空间所有人都能找到一席之地。但另一方面,旧的等级世界恰恰立足于选择性,和选择性一同消失的,还有对好坏善恶的认识本身,剩下的只是大杂烩,其中既有事实,也有被错当成事实的各种观点。
在这部难以言喻的作品的最后,斯捷潘诺娃打开网购的装有冰人夏绿蒂的包裹,发出如是慨叹:“冰人夏绿蒂,幸存者种群的代表,就像我的亲人——关于他们我所能讲述的越少,他们离我便越亲近。” 只有细读她在第375-376页关于“罗曼司”(Romance)的小插话,才能明白,这里的“罗曼司”是作者对“记忆”的爱恋和追求。到了最后,知道适可而止,懂得“忘却意味着开始存在”,这真的很有情商、也真的很哲学。作者用了389页的篇幅才抵达此处,作为读者,我要借用书中的一句话:这本书会让我觉得很长,长得令人幸福。
马凌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标题为“冰人夏绿蒂在无所之地的中央打开一只康奈尔盒子”。
<燕京书评>原创稿件。转载请后台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