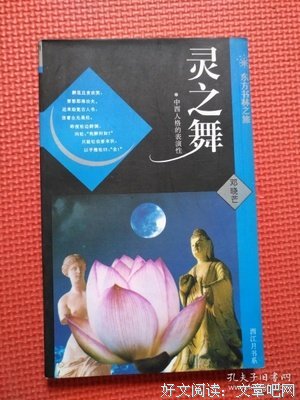
《灵之舞》是一本由邓晓芒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1995图书,本书定价:16.00,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灵之舞》精选点评:
●“我们生而为人,并不足以使我们成为人;我们活着,这并不说明我们进入了人生。”
●痛快!
●用剥洋葱的比喻来讲述哲学问题,很合一个小学生的胃口
●
●对关公和阿伽门农的人格原型进行了临床分析
●邓晓芒
●看过都忘了。。。。喵喵。。。
●不懂
●强力推荐!!!!!!!!!
●出人意料的好书,对西方哲学的认识很深刻。
《灵之舞》读后感(一):百字书评
对我影响最深远的书:《灵之舞》邓晓芒著
这样一本书,它以最平常的语调谈论普通人关心的心灵话题:关于真诚,关于责任,关于孤独、自由和其它心灵世界的语言,如果你有足够耐心并且如果你真正关心,就能进入书中理性而诗意的世界。不论最初看来多么难以理解,就是这本书,它抛开人所共有的理想的虚设和自欺直奔心灵的主题,以论述的形式对灵魂的事实展开追击。
《灵之舞》读后感(二):润物无声
难得的平静,又难得的震撼。
从来没有过的感受,感觉真的是灵魂在舞蹈,独舞却又不想刻意去寻找舞伴。欣赏作者独到的见解,独特的眼光,直面灵魂却又不咄咄逼人,我接受作者的态度,接受他的观点,接受他的平心静气的对话。
那时一种直达内心的拨动,产生发自内心的共鸣,不敢说我理解,最起码我不能表示反对,甚至我的所作所为倒像是对作者实践性的证明。那种端坐云台,洞察魂灵的艺术,我为之倾倒。
我不得不真诚的面对自己。
《灵之舞》读后感(三):自由意志的表演 - 向自由之路
乍看之下,这本书的封面和标题看起来貌似一文艺书籍,而且还是二流。但细看下去,我得说这是本思想纯度24k的纯哲理书籍。
说是纯哲理书籍,但是邓晓芒教授切入的角度比较特别,从心理学入手(作者在前言中也自己说这是本“怪”书,我认为这本书怪到精妙,而非怪诞)。首先探讨自我意识和作为其外在表现的人格的表演本质,这里邓晓芒教授旁征博引,相当精当地从中西两方面对此作了剖析。以此为铺垫,邓晓芒教授探讨了何为自由这个问题,通过历数西方哲学中自由观念的演变,从苏格拉底和智者派之争,斯多葛派,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基督教,康德的绝对律令,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哲学,最后的结论清晰,具有说服力。概括起来就是:选择的任意性,自律是自由的必要前提,但是这还仅止于形式上,要直接地体验自由,还需要自由感。最后邓晓芒教授将自由感归于自我创造的感觉,即表演自己设计的角色的感觉。
在这本书中,邓晓芒教授对中国人的人格和造成这种人格的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基本上没啥正面评价,除了一点。而这点正好验证了我长久以来心中的一种感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再一无是处,但有一点是超越西方人的 - 没有罪感和伤感的自由感,具体地表现在实际中就是诗意的生存,而这正是海德格尔哲学所追求的。可惜的是,这种诗意的生存随着儒家礼法道德宋明以后日益僵化,逐渐丧失了其直接的感受性,成为一种空洞抽象的说教。
这样一本有分量的启示性哲理书籍,竟然没有多少人关注,甚是奇怪。
《灵之舞》读后感(四):自由的宣言,哲学的起点
用4天的时间看完了这本书的电子版本,虽然有很多错别字,但是语言的平易、逻辑的严谨、思想的深刻、批判的彻底,已经力透纸背,甚至让人不寒而栗。
这本书写于80年代末(1988)。通过这本书,可以窥见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对于自由的认识和向往,对于传统的反思和建构。邓教授本书的主题无疑是关于自由的谱系梳理。从人的自欺本质,到人格的孤独—责任二重性,然后到自由的任意—自律—自由感三阶段,构建了自由的庞大系统。我想,这应当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哲学奠基。确实,这样的写作比我以前所艳羡的柯小刚、林国荣之类浑厚磅礴的多。
邓教授深谙西方哲学传统,就本书的学术积淀来说,古希腊—中世纪是源头,德国古典是高峰,马克思—现象学—存在主义是深入。从这里可以看说,当时的知识分子的视野和功力。而这些积淀恐怕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丰富母乳,我们只要想想刘小枫就知道了。
邓教授对于中国传统的批判不遗余力。这种国民性批判起于鲁迅,终于鲁迅。从这里也可以窥见邓教授的“新批判主义”。
本书的不足之处有:文字的雕琢不够,有些文字比较随意;自身的体验不够——比较深刻的部分很多是引用;某些地方比较牵强。
另外,邓教授对说谎、失眠、笑等的分析似乎有借鉴的痕迹。还有对于尼采、克尔凯郭尔的分析也囿于当时的水平。
所以,可以说该书是爱好和研究中西哲学的人的共同起点,我们应当超越之。
《灵之舞》读后感(五):书自有自己的命运。 转:
凝视神秘,说不可说
——为邓晓芒《灵之舞》新版作
(郭勇健)
人称“德国浪漫派的最后一个骑士”的黑塞,在他的小说《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借雕塑家歌尔德蒙之口,道出了他对许多技艺精湛的艺术作品的不满:“它们缺少一点主要的特征:神秘。而最杰出的艺术品与梦境之间的共同点也就是:神秘。”我愿把这里的“艺术”二字换成“哲学”。许多以“哲学”为名的著作之所以索然寡味,就是因为它们往往把哲学弄成一门技艺,从而丧失了使哲学成其为哲学的关键:神秘。一部著作,倘若未能感应神秘、无力凝视神秘,纵使读书破万卷,哲学史料倒背如流,引文信手拈来,注释密密麻麻,外语琅琅上口,仍然处于哲学的外围,只能与哲学擦肩而过。就让各种金碧辉煌的获奖证书颁给那些擦肩而过的“哲学的外围”好了,反正这脂粉也涂不到哲学女神的脸上。获奖证书与哲学无关,掌声亦与哲学无缘,哲学倒是与寂寞、孤独定有三生之盟,一如邓晓芒的《灵之舞》于1995年面世之后,寂寞了十余年。何以故?哲学与神秘为伍之故。“凝视神秘,说不可说。”——窃以为,这既是艺术的精髓,也是哲学的要义。
邓晓芒是一个凝视神秘言说神秘的人,《灵之舞》是一部凝视神秘言说神秘的书。这神秘之域,不在外而在内;不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茫茫宇宙,而是“人心的无底深渊”。这是一个比宇宙还要神秘莫测的所在。人心的神秘,古希腊人曾在悲剧中形象地表述为“司芬克斯之谜”,邓晓芒则称之为“精神之谜”。
人非草木,亦非禽兽,人人都有一颗心,人的生活当然离不开心灵;所谓人生,也就是人心的人生。既然如此,这颗心怎么就成了一个“谜”,成了一片神秘之域了呢?心灵或精神之所以是一个“谜”,是由于它处于日常理性和科学理性所不到之处。心灵中的东西,总是多于我们所能够感知的东西;心灵的领域,远远大于日常理性和科学理性所能触及和把握的范围。日常理性仅能照亮心灵的表层。科学理性将心灵肢解,“七宝楼台拆散,不成片断”,捕捉到的只是心灵的某些局部碎片。心灵的本性是自由,是超越,它永不停息,不断逃逸,抛给科学的永远都只是无生命的蝉蜕,恰似水气蒸腾,纵然强行拦截,也已凝固化为水珠。总之,在日常理性和科学理性之外,心灵中更多更大更深更完整更鲜活更真实的领域,沉入黑暗,沦为神秘,永远保持为一个“无底的深渊”。在某次与艾克曼的对聊中,歌德感叹认识自我之艰难,说虽然每个时代都有人反复提出“认识自我”的要求,但这是一个奢侈的要求,迄今没有人真正达到过。由此可见,自我之谜、心灵之谜、精神之谜、灵魂之谜,是一个永恒的谜。
实际上,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已经以“无意识”概念、“海底冰山”之喻说明了,精神是一个奥秘。与精神分析学家研究和言说无意识的努力相似,哲学家把目光瞄准了这一永恒的神秘之域,“认识你自己”是心理学与哲学的共同宗旨。只是它们逼近神秘言说神秘的方式不同:前者是经验性的观察,后者则是一种超验的凝视;前者是为了治疗、为了实用,后者纯粹是为了自我认识,为了自由。哲学纯粹是,心灵要去认识心灵,自由要去把握自由。归根到底,精神分析探索心灵世界的方式仍然把自由凝固化了。这种方式把精神之谜视为一道数学难题,一旦揭示了它的谜底,谜语本身也随之消失。只要内心的某种秘密被察见、被道出,秘密就不再是秘密了。借用英国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的一个比喻,精神分析学家解决心灵之谜的方式,好比拔掉一颗灵魂的智齿。
与心理学家相比,艺术家的工作显然更接近哲学。人的一切行为无非是一个象征,我们的存在牵连着无边的整体、无底的深渊、无量的神秘。这样的一种体验,乃是艺术家和哲学家的共识。譬如,西方近现代小说传达的最鲜明的信息就是,人确实是有灵魂的。包括小说在内的艺术作品能够如其本然地呈现心灵,使运动持续着运动,将神秘保持为神秘。而邓晓芒在《灵之舞》中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正是描述精神“本来的样子”。举例说,他强调精神是一个封闭体,人应当有隐私权,反对文革式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做法,就是无视精神之存在,践踏人的尊严,将人贬低为物的表现。他反对本质主义的“人性本善”的观点,因为这与精神的“自由”不符,等于剥夺了人的自由意志。要言之,小说艺术直接呈现了心灵世界,哲学则描述、分析、解剖、反思这一直观世界,要找出这一神秘世界的运作机制,要发现它的先验结构和内在规律。这种规律,邓晓芒借用德国艺术理论家康拉德·朗格的概念,称之为“有意识的自欺”;这一内在的结构,邓晓芒命名为“表演性结构”。他在自我意识、人格、自由意志中都发现了“有意识的自欺”,都发现了这种先验的“表演性结构”。
《灵之舞》对精神的结构性描述,形成了邓晓芒的“艺术形而上学”的大纲。邓晓芒的哲学是诗化哲学,甚至可以整体地视为美学。我们知道,庄子的哲学是美学。为什么?那是因为在庄子那里,存在本身就是美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同样地,艺术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那是由于在邓晓芒看来,终极实在本身就是艺术的、创造的。精神、人格在《灵之舞》中就是终极实在,而人格就是面具,灵魂就是演员。“真正的艺术家是人,是纯粹的、作为人的人。第一个艺术家是第一个人,第一个人也必定是个艺术家。”美学家邓晓芒与哲学家邓晓芒,在《灵之舞》中被合而为一。依稀记得李泽厚在《关于“美育代宗教”的杂谈答问》中提到,美学是“第一哲学”。张世英在《哲学导论》中则指出,那种把美学或艺术哲学看作哲学的一个分支、一个组成部分的看法,已经过时了,如今的哲学本身就应当是艺术哲学。李泽厚和张世英的这种看法,在邓晓芒的《灵之舞》中得到出色的证明,当然,结论或观点相似,其学理依据和致思角度却全不相同。
从前人们以为,哲学就是科学,不懂数学就不能懂哲学,恰似柏拉图学园门口的标语“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但这只是属于柏拉图、笛卡尔、斯宾诺莎、罗素的比较陈旧的哲学观念。在叔本华、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之后,我们已经可以断言:不懂艺术就不能懂哲学。邓晓芒似乎就是这么看的。他不但将灵魂视为艺术家,将人格视为艺术品,将人生视为艺术创造,而且在《灵之舞》一开始就指出,时至今日,解决精神之谜的有效方法、抵达心灵之域的有效途径,已不再是科学,而是艺术。换言之,不再是认识,而是体验。顾名思义,与认识的先是主客对立而后寻求主客体的统一不同,体验是“一体而验之”,在契合相关的、乃至于一体化的关系中发生。体验显然先于认识。若无本体论上的一体化体验,认识如何可能,主观如何切中客观、自我如何统一于对象,都是不可解的了。因此邓晓芒说:“认识和道德都是从艺术中派生出来的。”
不懂艺术就不能懂哲学,这不仅是由于艺术和哲学都凝视神秘,也不仅是由于生命是一个奥秘,心灵本身就是艺术家,而且是由于艺术和哲学都试图言说神秘,“说不可说”。神秘本是不可言说的,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谓“说似一物即不中”。自古以来,如何言说神秘、言说那不可言说者,就是哲学的一大问题。白居易曾经质疑老子:“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不过相传老子的著作是被逼着写出来的,老子不得不写下《道德经》五千字,作为出函谷关赴西域的交换条件。《道德经》的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这是老子在提醒读者,不要拘泥于文字,而要透过文字看到事情本身。庄子也说、也写。不过庄子用了一种特殊的说法和写法,即所谓“吊诡”之言。较之老子、庄子的诗化语言,邓晓芒的表述要理性得多。尽管《灵之舞》的表达有意地与刻板僵化的学术论文拉开距离,随笔的特征颇为显著,但邓晓芒既不像老子和尼采那样,以格言述哲学,也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加缪那样,用小说做哲学。把《灵之舞》与加缪的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相比,前者显然更为逻辑化、系统化。《灵之舞》的行文是推理性的。实际上,推理正是邓晓芒的一项极为突出的才能。试看20世纪中国的美学著作,纯粹以推理形式建构起来的美学体系,除了蔡仪的《新艺术论》和《新美学》,大概就只有邓晓芒与易中天合著的《黄与蓝的交响》了。那么,邓晓芒到底是如何做到用理性的语言去言说超理性的存在?
唯一的可能是,这种理性乃是辩证理性。作为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邓晓芒是当今中国极少数还相信辩证法之生命力的哲学家。《灵之舞》出版于《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之后,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已然极为娴熟。只是由于邓晓芒专门将辩证法运用于人的个体精神世界,因此他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有所不同,不妨名为“心灵辩证法”。譬如,在邓晓芒看来,辩证法的灵魂是“自否定”,因此,他几乎在心灵的一切表现、精神的一切现象中都揭示出其自相矛盾性,即“自欺”本性。曾有人质疑邓晓芒何以用“表演性结构”这种古怪说法,那是由于,惟有“表演”一词,才能标识精神的“既是又不是”、“不是却偏是”的自相矛盾的辩证关系。
此外,邓晓芒对精神的本来面目的描述,是在中西文化的对比和衬托中完成的。精神的奥秘到底怎样?我们或许并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对精神到底不是什么和不该如何有了清晰的认识,那么,对于精神本身,也就庶几近之了。这种表述的方式,古人称之为“烘云托月”,冯友兰曾名之为“负的方法”,其实,当然也是“辩证法”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正如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为了回答“艺术是什么”,先一一澄清了“艺术不是什么”,如,艺术不是物理事实,不是功利活动,不是道德活动,不是概念知识,等等。克罗齐说:“真理用斗争的方法不断使自己摆脱一个又一个的错误;……要是不批判关于真理问题的不同答案,那么任何人也不可能成功地揭示真理。”邓晓芒也是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凸显“真理”的。如此,《灵之舞》还是一部中西文化比较与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著作。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邓晓芒继承鲁迅又力图超越鲁迅,尝试在哲学的层面上,深化和推进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启蒙。《灵之舞》是西学东渐百年之后,终于姗姗来迟的中国人自己建构的一个现代哲学体系,同时,它也是一部中国文化的自我批判的著作。其批判力度和思维深度,是20世纪中国从未有过的,或者至少是罕见的。在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上,《灵之舞》是一部不可绕过的杰作。
然而,《灵之舞》这部杰作,十余年来却颇遭冷遇,几乎不见哲学界任何评论。这究竟怎么回事,倒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以我浅见,除了《灵之舞》以随笔体形式做哲学,显得不太“学院”,甚至“不伦不类”(邓晓芒自己也说过,这是一本不好归类的“怪书”),因而不为学院派人士所青睐之外,大约有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这是一部难以估价的著作。如前所述,《灵之舞》是一部凝视神秘和言说神秘的作品,是一部货真价实的终极关怀的形而上学著作。尽管神秘是生活的背景,尽管人人生活在神秘之中,但并非人人都能意识到这一背景,“百姓日用而不自知”,长此以往,我们便遗忘了与神秘的联系,丧失了凝视神秘的欲求和能力,或者,不再有形而上的憧憬、不再有终极关怀的真正需要,因而无从领会和无法衡量《灵之舞》的价值。
其二,这是一部难以评论的著作。为什么?其首要原因,是由于批评的原则一如克罗齐所言,“要了解但丁,就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平”,然而,邓晓芒的思辨水平,决非中国的一般哲学工作者和普通大学教授所能企及。例如,许多学者都已意识到,个体意识和独立人格是中国文化中颇为欠缺的元素,正是由于缺乏这一元素,致使我们至今尚未实现现代性。但是,学者们的思考往往也就到此为止。然而,“个体意识”和“独立人格”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很少有人能够盯住不放深入追究的问题,邓晓芒就是这少数几个人之一。《灵之舞》的探索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为多数学者所鞭长莫及,自然难以评论。
其三,这是一部惹是生非的、令人恼火的著作。《灵之舞》有两个阅读层次,即哲学的层次与文化批判的层次。纯粹哲学的层次隐,文化批判的层次显。于是,多数学者最为关注的,就是本书的文化批判的层次。在维护和宝爱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学者,特别是在现代新儒家看来,邓晓芒的批判简直胡来,好比一击粗暴的重锤砸碎了他们最珍视的花瓶,不光令人痛彻肺腑,而且徒留满地狼藉。于是产生两种反应。第一种是情绪激烈的反应。要么指责邓晓芒“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非常肤浅”,要么指责邓晓芒“偏激”。第二种反应是:嗤之以鼻,不予理会。第二种反应似乎姿态更高,更为多数学者乐于采纳。于是,《灵之舞》便不得不缩到角落里,去咀嚼自己孤独的命运。
书自有自己的命运。古人云,“兰生空谷,不为无人而不芳。”《灵之舞》既是一部少见的好书,自然会慢慢地赢得它的读者,慢慢地产生它的影响。它的影响,未必发生在学术界之内,却早已鲜花般绽放在青年学子之中。当初,邓晓芒在此书的前言中说:“我充分估计到人与人相通的困难,并准备接受孤独的命运。”他自己是打定了主意,“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不曾料到,“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终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网络上曾流传一种说法,当年《灵之舞》出版后,某些青年学子的问候语一度变成了:“你读过《灵之舞》了吗?”我也大致属于首批阅读《灵之舞》的读者之一,我也曾活生生地体验过想要问人是否读过《灵之舞》的强烈冲动,我也曾经斩钉截铁地对同龄人说过:“《灵之舞》是一定会再版的!”时隔十余年,这部著作终于以单行本的形式再版,这大概是它的价值逐渐得到普遍认可的一种证明。
这是一部凝视神秘和言说神秘的书。这是一部灵魂之书、生命之书,因此,这也是一部能够震撼灵魂、变化气质的书。好像是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说过,一本书读前和读后是不同的,阅读之后,读者的心灵肯定发生了某种变化。这种说法显然太乐观了。许多书读过,直如水面的落叶相似,不留下丝毫痕迹;它们以徐志摩式的潇洒,翩然告别心灵:“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能够改变心灵的书,自身就须是心灵之书,这样的书为数甚少,而《灵之舞》想必位列其中。这是一部启蒙之书,它具有豁然开朗的效果和促人觉醒的功能。最后,这也是一部浪漫主义的书。有理性,也有激情;强调普遍,也强调个别。凝视神秘,说不可说,诗化哲学,这本是浪漫主义的事业;美学,实为浪漫主义运动所催生的一门学问;艺术家是第一个人或本真的人,这是地道的浪漫主义者的观念。在如今这个世界性地“拒绝浪漫”的时代里,邓晓芒或许算是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