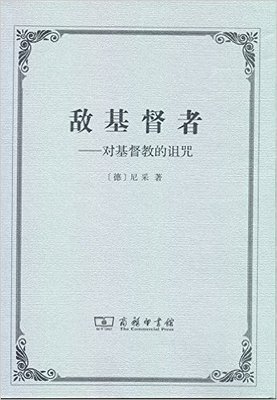
《敌基督者》是一本由尼采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15.00,页数:12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敌基督者》精选点评:
●首先,很好读,很好读,没有论证真的是太好读了…(捂脸)买这本是因为不太理解哲学史中所谓“在白天点燃灯笼”的人怎么杀了上帝,以及核心概念权力意志(永恒轮回则读另一本《如是说》),没想到一头扎进尼采就出不来了…(而且!尼采竟然也是老陀的铁粉!我好激动!)结合着译后记来看,对原始基督教、佛陀、耶稣和保罗(我是直接把他约当于宗教大法官了)的评说并不是多么富有原创性的思想,对我来说,这本书最耐读的一部分在于p91-p97对于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权力意志内涵的的完整表述。他把人依照权力的大小(本能的类型)分为三类,出世禁欲本身不是罪恶,首陀罗 僭取 了超人的特权才是真正的卑劣。而当他论及超人的时候,“禁欲对他们来说是自然…”“罗马…千万年的工作…”一系列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最纯粹的基督徒尼采对世人的祝福。
●解基督之毒
●我总觉得这本书是可以算进入尼采的入门书。对基督教的期盼,也是对现代性的批判,怨恨到颓废。永恒复返和自然,将是这本书的回答。
●世上只有一位基督徒,就是耶稣。
●读的是定哥和猛大合译的译本。| 对于身处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文明世界之外的人而言,读完畅快淋漓。尼采的冷酷和坚定同样具有天才的煽动力。对新教的指控戛然而止后,最后的「反基督教法令」让全书升至最高潮。
●基督教是一个关于怜悯的宗教,而基督徒式的怜悯(自怜)妨碍了人的“vitality” -- 即活力,生命的活力。上帝死了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一个黄昏时期的开端,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变得越来越非理性和不可思议。杀完上帝之后,谁会擦去我们身上的血?什么样的水能够供我们清洁自身?
●让我做了一夜噩梦
●尼采不用晦涩的方式,也能进行颠覆和价值重估。仇恨、谎言、颓废--对基督教的批判极端、彻底甚至到了毁灭的地步。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否全对,这些文字击中了我,甚至在我迷惑是否该相信上帝存在时给了我理由去拒绝相信,但现在我还是不能坚定地说我是无神论者,我还在想原因。
●如今找个时间再读一下,兴许能懂一两句
●“尼采是烈酒”,此言不虚,像我这种意志卑俗的人就被他的激情冲得头昏脑胀。在全局上结构严谨,又几乎在每个局部上高度紧张地不遗余力地诅咒,这种控制力令人叹服。 当然这样的批判模式不局限于基督教,尤其是在神权几乎已完全失势的今天。有趣的一点:尼采爱耶稣,而敌基督教。同样的思路,我们也可以爱孔子,而敌儒教;爱马克思,
《敌基督者》读后感(一):简单记录一下
1.首先是方法问题。《敌基督者》是对如何用视角主义操作哲学的一本精致说明书(更出名的是《道德的谱系》)。尼采本人也逃不出视角主义的诊断。这是一个足够公平的哲学方法。
2.“现代道德哲学”的当代攻击者(麦金太尔、威廉斯)都是尼采的忠实学徒。
3.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一个世俗版本的基督教体系,实践理性的意志能力最终指向的是上帝的戒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义务论伦理学本本质上是律法主义的神命论。这是2的深层动力。
4.中国人信基督教无论怎么折腾,恐怕也逃不出洪秀全及其追随者的水平。
5.无神论是一神论的激进变种,二者并不敌对。一神论的真正敌人是多神论。
《敌基督者》读后感(二):极致癫狂的信徒
世人大多生活在藐视与被藐视的视线之中,克制自持的“成年人”更倾向于巧妙地隐藏这种不知从何升起的自我优越感,而毫不掩饰地全然宣泄这种情绪的,要么是疯子,要么是聪明的疯子。 这种藐视所包含的目光带有很多层面,不仅仅是对于善恶是非的基本评判,也有全然凭借自身好恶所指责的价值观念。较为奇怪的一点是,我是十分厌恶键盘侠的,既不愿意与之争吵,也不愿意与之交谈,但这本书还没有引起我较多的不适。这是蛮奇怪的,推崇的方式一直是冷静自持的讨论,这本书所用词汇之猖狂让我觉得尼采真是“疯了”,要说和尼采一样憎恶基督教吧,我对苦行修士的生活又抱有很大的向往,并且是生来有罪论的坚定拥护者。思来想去,也琢磨不到缘由,只好暂且归结为尼采本人极具癫狂性质的魅力了。 尼采在这本小册子中提出了对基督教严苛又刻薄的评论,“对人类本能的破坏”、“上帝的火鸡”、“完全病态的享乐主义”…基督徒,特别是教士,以一种愚蠢又完全自私的形象生活在这本册子里,但即便他如此抨击了,我也仍然无法改变自身对于基督教和上帝的看法,依然保有着强烈的想要成为斯多葛信徒(甚至是苦行僧)的念头。“真实的人类欲望”是可怕的,社会沉淀已久的观念影响也是可怕的,在这样一种“出生即是为了赎罪”的想法里,坦然面对真实欲望必然引向最为病态的毁灭。比起痛苦万分的死,还是一般痛苦的活着吧,毕竟要想当精神病人,也是需要天赋呀。
《敌基督者》读后感(三):谎言与非谎言
大概无需因本书陷入信仰的纠纷,尼采的骄傲也会令他不屑于此。基督教只是个名字罢了,一切自甘贫瘠、自我否定的生命,一切助长了懦弱的行动,他都要抨击诅咒。
他怨恨信仰的欺骗——所谓原罪、爱与救赎,如此损害着生命、庇护着弱者而降格了人的力量。他要以真相打破欺骗:世界没有意义,没有拯救,这个无感情的星球从未爱过他们,也从未为了爱与温暖存在。但世人需要谎言,因为真相并不如甜酒怡人——成为悲伤的苏格拉底不如集体困于无知、大梦于千古的谎言,这兴许也能算种历史传统。于是宗教成全了美梦,尼采被断为疯癫。是谁定义了正常,并不重要。
世界因此幸运,不捅破真相能让最多人安然有序。但循着历史的永夜回望,川流尽皆无影,孤独的强者却在书页里永远如烈火夺目。高傲、残酷而冰冷,此人过早洞察到了迟早无法活在田园美梦里的现代世界,而主动去与未来的困局碰撞。
极北的山地,浩瀚雪夜,就此永恒般渴望着未来的、重估一切的门徒,又轻蔑地走过现实中哀苦的众生,否定着怜悯、甚至嘲笑同情为一种共同堕落。愚蠢的人,他会说。他渴盼强者,他要光荣的希腊、伟大的罗马,要狄奥尼索斯把世界醉成一场狂欢,要踏足深渊之上的危险绳索,要生命颠覆所有建构、走向至高无上的意义。
疯狂不可救药,但那种近似的英雄主义,孤独又灼烈的星辰,人类历史里怎会有过这样的美丽。
《敌基督者》读后感(四):批判与人性
《敌基督者-对基督教的诅咒》书评
长久以来浸润在基督教的文化圈中,我也萌生了加入基督教的想法。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想要完成从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到客观唯心主义的转变是极其艰难的。曾经有看到一个说法,信基督实则是人类精神惰性的体现。这是一种说法。一个人一生最根本的就是要获得个人精神上的独立,在此之上构建起个人的人格大厦,从而得以在世俗中行走而仍为人。目前看来,仅有两种方式通往这样的终点。一为通过不懈的探寻,延展自身的精神世界,在探索中最终获得精神的独立。二是通过宗教这样的捷径,将个人的精神与人格依靠在这样的第三方,从而达到个人行走于世的基本条件。
在尼采的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基督教的不满,认为这样的宗教教义从根源上就是在磨灭人类的健康天性。但人类的天性是什么?就当代体验与观察看来,是贪欲,是暴力,是无知。诚然,其他美好的品质同样存在与人类身上,可从未见过极致的善或健康天性,但在人类社会极致的恶、暴力与无知却是比比皆是,更为广泛的实践。在这里首先简单地将贪欲、暴力与无知归为低劣的本性(自然你也可以认为这属于高贵之举),而另一方面自然处在其对立面。既然同为天性,人类却极易表达出更低劣的本性,却极难表现出所谓高贵之天性,这样的事实是否可以得出人类的天性中很大一部分被这样的低劣所统治着。
在没有对人所谓的健康天性做出解释的基础上,如何能够展开这样的陈述?我尚未阅读过尼采的主要著作,不过对其的超人意志所有耳闻。最根本的根本,尼采总是在书的序言中写到,自己的著作是写给极少数人阅读的。这也等于他自己也承认,所谓的超人意志也如同他在书中所批判的上帝一样,对于普通人而言如同无法够到无物。更甚,常人对于他所认识到的人类自由意志所能体现出的力量几乎是无法企及。我曾听一位基督徒说,加入基督教,不需要你很聪明,不需要你有何等的智慧,需要的只是一颗虔诚的心。这是基督教的普适性。这也是基督教与尼采批判观点的根本分歧所在。他认为基督教是弱者的宗教,没错,基督教就是弱者的宗教,是那些无法在精神上企及超人意志般的强者,基督教提供给他们一个捷径能够通往与那样境界相似的“应许之地”。
或许尼采忘了,这个世界是弱者的世界,而非强者与英雄的国度。强力的精神意志并不具有感染性,相反的是,具有极强的个体性。既然无法将弱者的精神从深渊中拯救,又何必将其唯一的倚靠挫骨扬灰?既然本就是两条不同的康庄大道,或许发自内在的强力意志所带来的精神圆满更能够体现独立性的特质,但这并不代表着靠着上帝的搀扶,走向终点就必然是耻辱与卑劣。
何为宗教?宗教又是从何处起源?相信尼采与我皆可认同的就是,宗教本身都是人类自身的创造物。为何人类要创造这样的事物?因为人类有这样的需要。这样的宗教性深深的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尤其是精神上的弱者(而这样的弱者是人类这个种族的主体)。或许,是说或许,某位拥有着独立精神意志的超人正是因为在人类的根本之中看到了这样的事实,而选择了创造上帝,创造诸神,引领着精神的弱者前行,而免于陷入更深层次地迷惘与堕落。就如前所言,精神的弱者最大的特质就是对自身躯体的虚弱控制力,堕落就如同一个沼泽与深渊,这样的人只会在其中越陷越深。
“上帝所选中的是世上柔弱、愚蠢、不高贵、被鄙视的人”(《哥林多前书》1:27)尼采对这段进行了批判,指出:正是这个公式,颓废获胜了。背后很大的问题是,强大的人,拥有强力意志的人需要被上帝选中,愿意被上帝选中吗?而非弱者又会走上信仰的道路之上吗?到底这样杞人忧天的批判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到底是认为基督教颂扬弱,还是自身对弱的深恶痛绝,以及对低于自身精神阶级的人的鄙夷的一种放大。所谓对精神贵族的推崇,不仅仅是推崇拥有这样的精神特质,更是对没有能力企及这样特质的人的遗弃。显然,倘若佛教、基督教等具备了尼采所推崇的这样的特质,整个人类社会势必会更加不稳定。倘若连最后一个为弱者敞开的避风港都要被强者所占领,那么强者最后也势必被大多数的弱所淹没,在其中自取灭亡。
当任何一个人想要反对另一个人时,最根本的条件必须是先去了解你所要反对的人。从这本书中,可以见得尼采也是这么做的,既然要反对基督教,那么最首要的就是去了解基督教。不过以尼采这样强烈的仇恨的视角去阅读圣经,又怎么可能读得基督教徒所理解的圣经呢?每行每个字母都被极端化,无论是什么都达到了极端主义的顶峰。从这样的根本上去立论,又如何会不得出那样不健康的结论。
同时,为了批判而不惜抬高伊斯兰教,并且是从性别角度来支持自己的批判,显得极其令人反感。对于尼采个人对女性的歧视,确实也不是很明白这样的对女性精神的鄙夷是从何处冒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