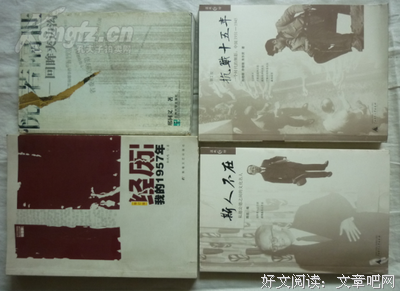
《隐痛与暗疾》是一本由魏邦良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1.00元,页数:26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隐痛与暗疾》精选点评:
●只是还行。
●某些评判真是诛心之论啊!
●一般般,在同类作品里写的算一般的了
●千万不要看,一看必后悔
●书中描述现代文化人的另一面,比较偏重八卦,其实每一个都有很不堪的地方,名人也不例外,出名已经获得荣誉与好处,牺牲一些隐私也是说得过去的,这可能是一个通例吧。作者对于别人讲鲁迅的不是又很愤慨,却是有些自相矛盾的,鲁迅难道就可以例外吗?他的阴暗面都是明摆的着的,说一说又有何妨?
●爱好八卦的可以看看
●八卦得很地道。
●脱离历史局限性,哗众取宠的小市民八卦读本,而且比方舟子差远了……
●珠海0803
●挺好玩的文学名人小八卦文集,当消遣吧,虽然作者试图还原真实历史,但靠几本回忆录,肯定不够,所以只能是八卦文……跟中行爷爷的八卦文比,还是差了点。人家中行爷爷有第一手的史料嘛。
《隐痛与暗疾》读后感(一):值得推荐?
以前,我有意识的抵制这种书,一方面我厌恶猎奇心理,更多的还是不
想承认我曾经崇拜的名人有灰色的一面,可以说是一种莫名的强迫症
结,现在觉得看看也无妨。不过看多了也就麻木了,并且感到无趣,其
实没有必要再翻历史的故纸堆,这根本不能改变什么。不要谈以史为
鉴,这镜子是铜的,即使能映出影像,也是模糊的,变形的,以致扭曲
的。
《隐痛与暗疾》读后感(二):《隐痛与暗疾》:“最杰出人,却始是最普通人”
追寻已远--晚清民国人物素描
作者:吴方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月
定价:23元
作者简介:吴方(1948—1995),生于北京,祖籍安徽怀宁。曾辍学做工。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曾为《文艺研究》杂志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会研究人员。著有文学评论、近现代思想文化随笔等文字。
吴方先生已经去世,对他的书说三道四,有失厚道。只是想说,我对半文不白、东拉西扯、旁征博引的文字不感兴趣,也看不懂。我喜欢那种机智的文字,尤其喜欢骂人的,这样的作品读起来有感觉。偏激也是灵气的一种。
80年代以降,流行“翻案风”,这也许是一种新的“解读”吧,但让我受不了。小品文盛行了,周作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在八、九十年代翻了身,猪悟能在九十年代成了偶像,胡兰成在21世纪初红得紫起来。反面形象成了正面人物,原来的崇高开始受到怀疑。颠覆正统、骂名人成了出名的一种途径。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周作人,似乎比他的哥哥周树人成就还要大,更应该受人们的尊重。毛泽东在评价梁漱溟时说,“而你(指梁)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08、107页)。也许毛这么骂梁先生,梁先生有些冤枉。而现在为稻粱谋的“学问家”们挖空心思地把周作人抬起来,抬得比鲁迅还要高,显然是下定决心“人咬狗”、“发宏论”,故意美化周作人,这些人瘸腿走路,还觉得自己是特立独行。
“最杰出人,却始是最普通人”,本是《柔石日记》中的一句话,魏先生用作一篇文章的题目,他是想更准确地把握一个人的本质,对于柔石而言,他在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认识了柔石的高不可攀,在《柔石日记》中认识他的普通,尊崇柔石还是照旧,只不过觉得距离近了,看得更清了。魏先生这种评论人看人的方式是值得推崇的。对于世人,我们当然不能像某些新锐那样,撒尿和泥,捏个像,自己下跪磕头之外,还要诱惑他人跟着作揖。
魏先生在书中评论了不少名人,讲了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曹聚仁为自己的一次性交易强词夺理做辩护、海子自杀不为诗、胡兰成对女人情感的玩弄、周作人的自我美化与辩解、沈从文与萧乾这对师生的恩恩怨怨、苏雪林对鲁迅前恭后倨尤其在人家死后大加挞伐。读他的文章让我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学问。为人不可“以一眚掩大德”,当然也不能为发表“独特见解”而乱翻陈年老账,把萤火吹成日月星辰,误导非专业人士。我想,人总应该有些良知,总不能明明放个了屁,却非说自己吃了美味佳肴打了个饱嗝吧?!
《隐痛与暗疾》读后感(三):人物岂能诛心?
因为《温故》系列才买这本书,但开始的两篇文章让我很失望。
对于历史中的人物,知人论世一直是后人对他们进行解读的应有之义,可我在读这两篇文章时都从心底涌出一股压抑不住的辩驳的声音。
开篇文章,讲现代社会的“孝顺”问题,缘起是北大吴小如对自己儿子的公开批评,作者文章写作选取角度很新,甚至用《新闻调查》中天津郝麦收一家立“亲子双向自立协议”做对比。用传统文学评论的观点看,魏邦良先生在说吴小如先生的事情时是否弄清了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当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孝顺”上时,魏邦良先生却不讲“情”,反讲“理”,如果魏邦良先生有孩子的话,问问自己妻子在老年生病时,自己年迈无能为力时,是否期望同一个城市仅有的一个子女帮助自己?而当这个儿子以“发烧”为由推辞时,年老体弱的您又会是一个什么心情?自己老伴卧床,这个自称“发烧”的儿子为了财又与老人远道而来照顾的小儿子电话会晤时,你是否也会气血攻心呢?是否也会怒从心头起呢?
魏邦良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多次提及,让老年人理解年轻一辈,是,很多情况是应该让老辈人明白年轻人的生活负担,但是试问哪位“开明”的老者能理解自己的儿子忙碌到1年半时间根本不来看自己一眼?魏邦良先生,您也马上要40岁了,如果您有儿女您也会这么教导他们吗?
魏先生似乎很看重天津那个订立“亲子双向自立协议”的家庭,不好意思,什么叫“双向”?在签订协议之初,郝家儿子甚至写过遗书,您看到的是最后大团圆的结局,您能否想象万一郝家儿子当时轻生死掉又如何呢?这是不是很有可能的一件事?要不为什么要写遗书呢?既然魏先生这么赞叹这个家庭的做法,您是否又会和您的儿女订立“自立协议”呢?
我不知道《新闻调查》为什么会举这样的例子,没有看完整的节目我无从理解它选择这个家庭的原因。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在历史解读时论及人物不得不提及的话题,在讲到一个人的行为选择时,总应把人朝好的方向理解,不能不掸以最坏的想法推测人,可是在魏邦良先生的这两篇文章,我不停的在问自己,他的点评为什么总让我有“小人”的感觉(可能类似于魏先生看韩石山的文章),举例为证:
在第二篇文章《失去勇气之后》中论及刘大杰和曹聚仁先生,魏先生点评曹聚仁说“但他那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用心良苦的辩白,却使他内心的懦弱暴露无疑。他越是虚张声势,越是强词夺理,越说明了他内心的软弱——不敢正视自己的丑行,不敢正视问题的实质。”说曹聚仁的行为是“欲盖弥彰”。
典型的“诛心之论”,太可笑了。如果曹先生不提这件事,您魏邦良根本不会知道,既然曹聚仁他提了他就没准备“盖”,曹先生自己彰显的这段历史在魏邦良笔下反倒成了“欲盖弥彰”了?嗯?曹先生自己说出的历史,反倒在魏邦良笔下成了对自己的辩白呢?一段根本无人知道的历史自己如果不提出来跟谁辩白?
不过除了开篇的两篇文章我极度不喜欢外,魏先生之后的文章却提供了不少有趣的细节,魏先生对胡适、顾颉刚的文章都很值得一看,有意思的还有他对沈从文与萧乾、胡乔木等人的描写。
《隐痛与暗疾》读后感(四):于历史的细微之处见精神
用了一天的时间看完了魏邦良的《隐痛与暗疾---现代文人的另一种解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仅仅是对这个出版社感兴趣,对现代的文人感兴趣罢了。书中提到的人物我再来逐一的点出来,因为说到的也是一些侧面,难免会有误差,但这种评论评论的评论也仅表示我的一点自己的观点罢了。很可能以后会看到我观点的暗疾,但至少今天在看完之后,我的观点是如下的。
首先出场的是北大教授吴小如,他之所以受作者的关注在于吴教授对待儿子的不耐烦态度,甚至开骂了自己不孝之子,言辞还很激烈。在此,我仅要说的是在这桩事件上是儿子的不对,因为人老了总是会怀旧的,而儿子该怀有对父母一种最虔诚的尊敬,除此,没有什么好谈的,古有: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现今,现代化的浪潮里,一种最原始的情感不该丢失吧,狐死犹首丘。
关于诗人查海生的死亡,并不是殉诗,而是他面对自由的艰难选择,而在每一个关键的选择点上,主人公的查海生都没有能够真正的把握住。文理分班,他听从了班主任的决定学文;进入北大学法律,毕业后却教哲学;随后,他决定南下海南创办报纸,因为父亲而中途夭折掉;于是,他就生活在一种矛盾之中,当难以调和的时候出现了分裂症,导致了最后的极限。
想起王小波的话: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不是别人手中的行货。
萧乾与沈从文的恩怨离合折射出一个文人该怎样对待政治的态度,萧乾本身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气质多一点的人,却在解放后不断的受到了政治的招安,几乎要成为御用文人了,却在1957年被“引蛇出洞”政策吸引了出来,于是,成为右派。沈从文在博物馆工作,默默无闻,对政治的态度是不信任,所以,他没有加入任何政党,闷头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胡乔木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1941年成为毛泽东的御用文人。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一度深切体味到毛的意图,于是,一系列的理论文章纷纷出炉。但一旦不能体会到毛的真实意图的时刻,他便开始了一个滑坡。看来,在政治人物面前尤其是最高领袖面前并不总是威风八面的,时刻绷紧的神经随时都有崩掉的危险。
苏雪林对鲁迅的谩骂攻击而是在1936年之后,她没有选择在鲁迅生前出鞘,自然心知肚明,而她的谩骂跟王朔、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的谩骂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属于鞭尸型,反正死人已经不会说话了,于是就有恃无恐起来了。而她对胡适的崇拜也仅仅是人身的,因为她的头脑是近文学远哲学的,而胡适正是讲述《中国哲学史》的。
胡适的弟子很多,如唐德刚、顾颉刚、罗尔纲。而整整领会那个“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实验主义观点的乃是唐德刚,他说过,胡适不是神而是人,胡适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的不伟大。从而引来了苏雪林的不满。罗尔纲是经常感情化历史的,如记录的沈从文第一次在中国公学讲课的话“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爱因斯坦指出了智慧与知识的区别,学校教育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培养智慧。智慧就是独立思考能力。胡适也同样强调这一点,但他同样没有走出乾嘉学派的考据癖,开起来历史的倒车,倒在了故纸堆里去了。爱因斯坦却创立了广义相对论,在天文物理上随后的霍金《时间简史》问世,那位只有几根手指在动的奇才也在智慧的生涯上迈出了一步。
张爱玲与胡兰成,丁玲与胡也频,都是出自后者主动的追求,在女人的逻辑里,被爱总是值得珍惜;在男人的逻辑里,女人赐予的爱恋却总是珍惜不起来。当张爱玲说出了那个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我只是萎谢时,她感动得只是读者,风流如胡兰成者是不可能回头的。丁玲也是深深的掩盖起自己对冯雪峰的爱恋,这仅是逻辑的悲剧。
人们可是喜欢那个《浮生六记》里面的女主人公,芸。因为她公开自己的丈夫纳妾,还为丈夫张罗着妾的来源,后来,才发觉因为如此是她不能生育。想起江冬秀也就可以理解了,当胡适把曹诚英肚子搞大的时候,她威胁要杀掉两个儿子。于是,看来还是肚皮说了算,最后,曹诚英留美,回国后在结婚之际却被江冬秀说穿,于是,远赴峨眉山准备出家,在别人劝阻下未果,但也郁郁而终。